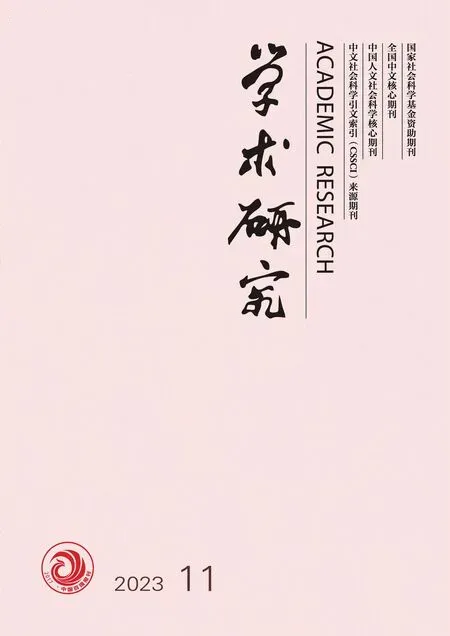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饶 琳
可以认为,从黑格尔至马克思的时代是哲学史的时代,人们普遍开始回顾历史并在历史中探索时代的精神特征。这种对哲学史的重视有着其特殊意义,而黑格尔的哲学史思想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马克思也称黑格尔的哲学史计划是庞大的,他的研究是伟大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1 页。但马克思也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史受他的思辨的东西影响,妨碍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发现。这也是后来的哲学史研究者对黑格尔的一个批评。同样的批评似乎很少出现在对马克思《博士论文》②即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文中简称《博士论文》。的研究中,人们反而热衷于发现其中所隐藏的马克思后来的思想线索。这种态度的差别大概源自我们渴望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发现哲学真正的历史,却只希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找到马克思思想的萌芽,然而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看来,他的《博士论文》是一项严肃的哲学史研究。因而,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于他们对伊壁鸠鲁哲学观点的比较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哲学史观中的立场分歧
马克思在准备及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期间,他的哲学史观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青年黑格尔派,另一方面也直接来自马克思对黑格尔著作的大量阅读。③[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24 页。其结果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对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的理解中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承认古希腊之后的罗马哲学精神是古希腊哲学精神的延续,但是对于这种哲学精神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与现实的关系二者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发展和哲学精神的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相关性。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他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Idee)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5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18,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1986, S.49.同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logischen Begriffe)了。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Fortgang der geschichtlichen Erscheinungen)。”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35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S.49.黑格尔表明了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本身,因此他认为:“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Persönlichkeit)和个人的性格(individuelle Charakter)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9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S.20.相同的观点在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也可以看到:“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Persönlichkeit),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170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137.
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很接近,同样认为哲学史并不在于哲学人物思想的记述,不是历史人物个性的表达,而应当表现出哲学的体系及其精神。另外,马克思将哲学史的研究等同于哲学的研究。如果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在说明哲学研究的内容,那么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则是对哲学史的一种哲学规定,同时这也认可了基于哲学史进行哲学表达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Wesen)来展开。”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70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7.进一步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哲学史方面的认识,至少关于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的认识和黑格尔是相同的。这种相同的哲学史观,反应在二者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认识上,则表现为他们都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及其同时代的斯多亚和怀疑主义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哲学精神的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观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斯多亚、伊壁鸠鲁和怀疑派的哲学作为自我意识哲学的阶段。这种观点既是哲学的,也是哲学史的。黑格尔认为,在哲学层面,伊壁鸠鲁哲学、斯多亚和怀疑派代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哲学问题上,它们将古希腊哲学当中存在的普遍与个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具体化。其中具体化的普遍就是精神,这种哲学发展成为总体就是斯多亚哲学;而具体化的个别就是自然,它把自然存在和感性发挥为总体就是伊壁鸠鲁哲学,两种冲突的哲学原则在怀疑派那里达成了统一。⑥[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101 页。就伊壁鸠鲁哲学而言,它更多代表了斯多亚哲学的反面,但二者都在主体层面将哲学的原则普遍化,因而表现出哲学的自我意识。而在现实层面,黑格尔认为:“在罗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质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荡净尽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做实存的主体(existierendes Subjekt)——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inneren Freiheit)中去。”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0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19,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1986, S.255.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的自由、不动心、漠不关心、宁静不摇、平静不扰等等,在哲学层面,其屈从于一种独断意识,是对意识的主奴关系的妥协,在现实中则表现出精神对现实世界的逃避。黑格尔认为,正是这种意识的主体形态造就了哲学的自我意识。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146 页。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虽然同样认识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7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23.但马克思却认为这些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是被遗忘的对象。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7 页。
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形态,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中,哲学通过发展成为总体哲学,它的发展和完善是通过对哲学和与哲学相对应的世界的规定完成的。总体哲学最终导向哲学反对世界,这种反对的形式就是总体哲学通过哲学规定导向必然性。马克思在《笔记》中这样论述:“以前作为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已成了规定性;而曾经是存在于自身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变成了否定。”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38 页。马克思认为,在总体哲学的规定当中,实际上是内部分离的,不仅仅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是如此,在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同样是如此。在总体哲学之后的自我意识所代表的个别主体性正是这种分离的表现。因此在与总体哲学的关系中,自我意识表现出反对总体哲学的斗争。这种自我意识并非避世的和消极的,而是哲学积极的斗争形态。
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力量朝向总体性进发,人类的意识存在克服内在矛盾达成统一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属于意识本身。⑥[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Ⅲ·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96 页。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本能是趋向于统一(自我意识就是一种自身统一)。⑦[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12 页。G.W.F.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9, S.139.而在这种哲学统一的另一面,表现为哲学内在的矛盾,主观与客观、本质与形式、个别与普遍等,它们显示为意识的内容以及意识的运动,并构成哲学意识发展的各个环节。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注意到了哲学在走向总体之后的分裂,哲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哲学的自我意识表现为总体哲学转向主体的个别自我意识,因而并不是哲学逃回到精神的自由世界才有了自我意识,而是哲学通过自我意识表现出它的自由精神。
二、感觉认识论与原子观念的考察
上述差异也反应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认识上。对于伊壁鸠鲁的哲学,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只是停留在感觉思维的层面,因而在概念思维的层面是缺乏的。黑格尔将伊壁鸠鲁的感觉看作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认识论,并认为:“感觉(Empfindung)是非理性的(alogisch),没有理由的。”⑧[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54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2.在黑格尔看来,虽然伊壁鸠鲁对感觉做出了概念式的判断,但是判断的依据并不是概念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基于感觉表象。对此他说:“在伊壁鸠鲁这里,对象的表象的自身同一性,也是作为一种意识中的回忆,不过这个回忆是从感性事物出发的;图像、表象乃是同意一个感觉的东西(Empfindung)。”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56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4.黑格尔将伊壁鸠鲁的哲学判断作为一种意见(Meinung),而且认为意见的标准在于感觉,要看感觉重复出现时是否始终如一。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56-57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4.黑格尔称这种以感觉为标准的判断“是一个很琐屑肤浅(trivialer)的过程。因为它只停留在感性意识的最初阶段上,停留在对一个对象的直观(Anschauung)、直接的直观的阶段上”。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57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5.这种否定意味的观点代表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尤其是感觉认识的基本评价,黑格尔并没有否定伊壁鸠鲁认识论的正确性,但是黑格尔却认为这种正确是肤浅的、琐屑的,是对于那些最初的知觉所进行的表象作用的机械说明。基于这种认识,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在原子的认识上采取了同样过于简单的认识原则。黑格尔评论说:“关于不被看见的东西,伊壁鸠鲁所采取的真理标准,是一个极轻率(leichteste)而现在也是很习见的标准,即:与所见、所闻的东西不矛盾。因为这样一些思想中的东西,如原子、表面的分解物,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并不能看到。诚然我们可以看到和听到某种别的东西;但是那被看到的东西,——和那被表象(Vorgestellte)、被想象(Eingebildete)的东西,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既然把两者分开,那就不会有矛盾了;因为矛盾要在关系中才发生。”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60 页。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8.这里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评判,其语气类似于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所做的评论,称他将原子论矛盾的双方分别置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以此来规避矛盾。如果按照黑格尔的分析,伊壁鸠鲁并没有通过别的什么方法来规避原子论的物质与形式的矛盾。但是,马克思却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认识归给了德谟克利特,那么在马克思的认识中,伊壁鸠鲁的哲学认识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呢?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探讨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哲学史上为什么伊壁鸠鲁会重新思考原子论哲学。④对于该问题,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也曾提到这种现象,他认为:“像这样的复兴只能被认作借那有限的先行的形态以深入认识自身的过渡,或者被认作通过必要的文化进展的阶段把那业已过去了的东西重新经历一遍罢了”。他评价这种现象是把木乃伊带到活人里面去,因此黑格尔并不认为这种哲学能够真正达到哲学的观念及其精神。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50 页。在《笔记》中,马克思就说:“相当有意义的现象是,构成纯粹希腊哲学的那一套三个希腊哲学体系,即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都从过去已知的东西中吸取各自的基本要素。”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67 页。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具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6、17 页。正是借以这一问题的探索,马克思认识到:“在伊壁鸠鲁那里,概念(Begriffs)的最一般的形态是原子,因为这是它的最一般的存在形态,可是这一存在本身是具体的并且是一个类概念(Gattung),但是同时它对其哲学概念的更高的特征和具体化来说,又是个种概念(Art)。”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68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6.基于此,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一来,原子是一种例如个人、哲人、神的抽象的自在的存在(Ansichsein)。这是同一概念的更高的、更进一步的质的规定。”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68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6
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论述并没有和黑格尔以及其他研究者一样,按照伊壁鸠鲁哲学本身的划分来展开,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有专门提到。在考察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之后,马克思认识到:“原子作为概念的直接形式只体现在概念的直接不存在之中,也适用于哲学意识(philosophischen Bewußtsein),这个原则就是这种意识的实质。”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43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47.由此,马克思说:“同时这也证实:我认为确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伊壁鸠鲁所采用的分类是恰当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43 页。马克思的动机表明,他认识到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作为原子概念的表现方式直接表现为原子规定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原子概念以及原子概念的规定并非原子作为感观对象获得的,而是原子作为思维的对象已经被意识所捕捉。
以上表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认识是从他的原子观念开始的,他认识到,在伊壁鸠鲁那里感觉并不真正表现为认识的原则,真正的原则是基于原子观念的规定,这种规定在感觉认识之外。在马克思的《笔记》中,他说:“观念性转入原子本身。原子中最小的东西对于表象并不是最小的,而是某种与表象相类似的东西,——此时不能想象出任何规定性的东西。原子所固有的必然性(Nothwendigkeit)和观念性(Idealität)本身仅仅是某种想象的偶然的东西,对原子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原则仅仅表现为:观念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只存在于这种对于它们本身来说是外在的想象的形式,即原子形式中。伊壁鸠鲁的彻底性就达到这样的程度。”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38 页。MEGA2,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9.
因此,我们可以解释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对于伊壁鸠鲁哲学总体态度上的差别。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在伊壁鸠鲁的认识中把握到的是将感觉作为意识与原子的中介,因此感觉作为真实的标准取消了概念的必要性。可以说,伊壁鸠鲁的哲学观点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不具有思辨性的、流俗的常识观点。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49 页。对于黑格尔而言,伊壁鸠鲁哲学所处的哲学发展阶段决定了他对伊壁鸠鲁哲学以及自我意识的解读,所以黑格尔的探讨所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哲学史线索。在这样的解释当中,伊壁鸠鲁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是古希腊哲学原则在主体关系中的延续。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直接表现为总体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
与此对应的,在黑格尔看来是意见的和琐屑的内容,在马克思这里却表现为一种认识论上积极的以及属于意识本身的规定。在黑格尔看来,“伊壁鸠鲁漂泊在一些什么也不能说明的不定的说法中。”④[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62 页。他的概念、抽象和实在之间是杂乱无章的、混乱的关系,但在马克思那里,伊壁鸠鲁对原子的规定中所表现为矛盾的地方反而是一种理论内的,以及属于哲学自我意识表达上的有意为之。所以可以认为,与黑格尔相比,在相同的问题上,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做了更加积极的和同情式的理解。这也是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之后放弃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而选择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这样的哲学史线索的一个原因。它表明,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所对应的哲学观念的相关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出现了分歧。
三、哲学史的不同哲学底本
对比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并不高,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的准则学,其真理标准是简单、琐屑、肤浅和机械的。⑤[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58 页。在关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认识上,黑格尔执着于弄清楚伊壁鸠鲁哲学中本质、原子和感性现象之间的关系,但他最终陷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不耐烦和不屑中。黑格尔的态度部分源自他在《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对意识的发展所形成的固有认识。与《哲学史讲演录》相比,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讲述到自我意识阶段时,所举的例子只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而没有直接提到伊壁鸠鲁主义。在这部以“意识的自身经验”为主题的书中,黑格尔进行考察的线索主要围绕意识的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等展开,其考察的内容影射在哲学史中便是诸种“精神现象”或“精神形态”。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这种自由作为一个自觉的现象出现在精神史中,是在斯多亚主义那里,其下一个环节是怀疑主义。⑥[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33 页。G.W.F.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163.之所以说黑格尔在他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论述中采用了精神现象学的底本,表现在黑格尔仅仅只是将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斯多亚哲学的对立面来看待,因此在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及其内容上也表现出与斯多亚哲学相反的态度。对于伊壁鸠鲁哲学,黑格尔有所肯定的地方是他的道德学,因为在这里,伊壁鸠鲁表现出了与斯多亚派同样的原则和结果。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75、83 页。也正是因为黑格尔在论述伊壁鸠鲁哲学时所采用的哲学底本是他的精神现象学,使得黑格尔更加着重于考察伊壁鸠鲁的感觉认识论,并试图从中寻找到与他在意识的经验考察中相匹配的结果。
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哲学底本更多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1839 年底,马克思在其《笔记》的基础上,集中开始对黑格尔逻辑学进行研究。②[民主德国]埃·朗格、英·陶贝尔特:《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 年第2 辑。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正式确定了他《博士论文》的题目和框架,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到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观点的影响。③这一点在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le Heinrich,1957—)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著作Karl Marx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 中也有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范畴对伊壁鸠鲁原子理论进行了重建。同时参见凌菲霞:《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新解——基于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传记视角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 年第2 期。在马克思针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中,核心内容是对原子论的考察,主要围绕二者对原子的规定,即原子的物质与形式、存在与概念(本质)的二律背反为线索展开。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中对原子的认识达到了概念的高度,而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把握是黑格尔式的,即将概念理解为高于存在与本质的由存在与本质环节发展而来的统一,④[德]黑格尔:《逻辑学Ⅱ》,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01、214 页。只是马克思将原子概念的两个环节表述为“纯粹物质性的存在”(Existenz eine rein materielle)和“纯粹形式规定”(reine Formbestimmung)。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3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S.35.同时,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将原子概念的两个环节及其矛盾客观化了。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3 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概念最终通过个别性(Einzelheit)进入现实性(Wirklichkeit),⑦[德]黑格尔:《逻辑学Ⅱ》,第243 页。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299.而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天体就是原子概念的现实性(Wirklichkeit)。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0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S.55.在具体观点的细节方面,马克思以原子的三种不同运动方式: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排斥运动,分别代表了原子的物质性规定、形式规定和原子概念。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6 页。原子通过运动关系将否定包含在自身之内,因而关于原子的规定具有了辩证性。与此相对应,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论及原子论的部分,也提到在哲学史上对原子运动的关注带来的对原子的思辨的规定。他说:“运动作为原子和虚空的另一个关联,完全不同于这两个规定相互之间的单纯并列和漠不相关。”⑩[德]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149 页。而在论及排斥运动时,黑格尔认为:“这个排斥(Repulsion)的意思是通过单一体(Eins)自身而设定诸多单一体,而这意味着,单一体亲自来到自身之外,而且这些如今位于单一体之外的东西本身仅仅是单一体。这是就概念(Begriffe)而言的排斥,一个自在(an sich)存在着的排斥。”⑪[德]黑格尔:《逻辑学Ⅰ》,第151 页。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187.而马克思在论及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排斥运动时,将排斥理解为一种原子的自身关系很明显来自黑格尔。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6 页。另外,在关于原子的质的讨论部分,马克思说:“由于有了质(Qualitäten),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9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S.40.这里的质被认为是设定的原子的规定性,并且具有内在矛盾和否定的特性。这种对质的论述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认为的质(Qualität)作为一个直接的(unmittelbarer)或存在着(seiender)的规定性,⑭[德]黑格尔:《逻辑学Ⅰ》,第92 页。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S.118.以及将这种规定性作为“一种以肯定的方式设定下来的否定”①[德]黑格尔:《逻辑学Ⅰ》,第94 页。的观点是相同的。
无论是总体线索还是细节上的论述,都表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所采用的辩证法大部分来自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考察。可以认为,这种以逻辑的辩证关系和原子的规定为线索形成的新的叙述方式,就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不同于伊壁鸠鲁本人以及黑格尔的重新分类的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观点上分歧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分析中采用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底本,而马克思则采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底本。这个因素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差别变成了黑格尔哲学内的他的精神现象学和他的逻辑学的关系。这种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回过头来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精神的不同理解。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它消极的一面。所谓消极可做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作为意识发展的环节,在它的辩证运动中,推动意识发展的、作为意识能动条件的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本性,或作为自我意识存在环节的欲望(Begierde)、承认(Anerkennens)和哀怨意识(unglückliche Bewußtsein),因而自我意识本身仅仅作为意识经验的结果被呈现出来。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11-144 页。G.W.F.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139, 146, 163.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完全成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之前,它始终受到外力的束缚和驱动,因而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其消极的一面。另外一方面,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史上反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作为凝固的东西抽象地守着自身,只在个人内心中追求快乐和幸福,并对外界表现出被动。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第146 页。
而对马克思而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底本不仅仅只适用于马克思对原子论的分析,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天象”进行考察时,马克思分析了伊壁鸠鲁的意识经验,这里的意识直接是自我意识,并沿用了在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考察中得出的原则,即纯粹概念对一切必然规定性的否定。马克思说:“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Abstract-Einzeles)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7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S.39.从原子论到自我意识,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将原子论的逻辑原则运用到了自我意识的考察中。因而在自我意识的经验中,它“感觉”(felt)到的,不再是受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驱使,而是精神的自由。把这个原则推广开来,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在伊壁鸠鲁那里,“他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质就是他的现实的自我意识的本质。”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169 页。因而“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vergegenständlichte)、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54 页。MEGA2, erste Abteilung, Band1, S.51.
因为原子的逻辑原则优先地被考察了,因而它同时作为自我意识的原则就使得自我意识不再是作为一种本能的冲动而发挥作用,它的经验也不是以零碎的、变动不定的、混乱的方式进入思维之内。因而,自我意识的积极性首先是意识的能动性。它使得伊壁鸠鲁能够在面对古希腊以降的神学世界观和哲学观念时,保持独立的思辨能力,不盲目跌入意识形态与哲学的空洞假设之中。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55 页。至此,马克思也表达出了他对抽象个别自我意识自由的追求和对神学意识批判的双重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