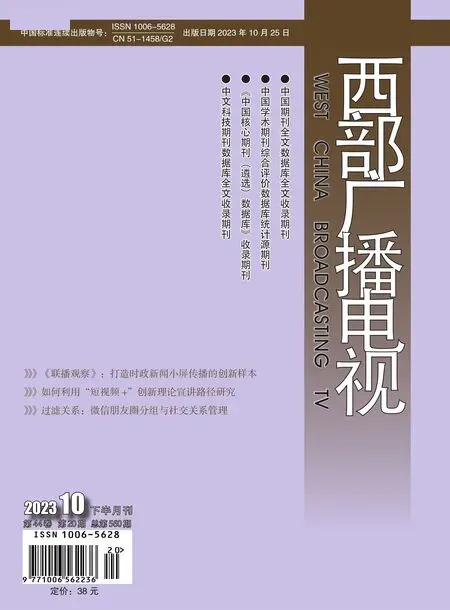试述新时代戏曲电影的“影” “戏”观
程小平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曲艺术作为被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早期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戏曲电影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电影类型,早在1905年,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便拍摄完成。从此,古老的戏曲艺术与时髦的电影艺术开始结合,传统的艺术趣味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由此可见,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戏曲同频共振,水乳交融。
1 “影” “戏”关系的回顾与反思
1.1 以戏为主导:从戏曲到“影戏”
在中国电影史上,“影戏”是对中国早期电影的一种特殊称谓,代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风格和电影观念,反映了电影和戏曲的深刻渊源。据《申报》记载,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是上海徐园“又一村”,1896年8月11日在此放映了“西洋影戏”。由于电影最初是在茶楼戏院所放映,因此得名“影戏”。虽然影院诞生之后,茶楼戏院不再作为观影的场地,但是“影戏”这个名称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特色传承至今。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戏曲电影是中国早期电影独树一帜的类型片。从内容上来说,早期中国电影内容大都是折子戏片段,选取戏曲片段中最具精华的部分用电影将其记录和呈现出来。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便是选取了最精彩的几折,如将“舞刀”“请缨”“交锋”等片段搬上银幕。戏曲电影从制作风格来看,无疑是话剧式的,语言要求咬文嚼字、文采斐然;人物经历要求跌宕起伏;结构要求充满冲突;创作方法要求起承转合;影片的场景布置也都是高度舞台化的。并且,演员在镜头面前的表演也带着夸张,这种表演方式不能单纯地归结于戏曲的影响,而是整个默片时代的演剧特征。中国电影与“戏”的更深层次联系在于它与古代戏曲的伦理传统的接续[1]。在1923年出品的《孤儿救祖记》中,郑正秋通过一个悲欢离合的伦理故事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主张电影的作用是教化。早期电影工作者努力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创方向,由于当时的电影手段还比较单一,忠实地向戏曲学习的态度使得戏曲电影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1933年中国第一部有声京剧影片《四郎探母》上映,这时候的戏曲电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动作表演,声音的加入使戏曲可以完整地表现唱、念、做、打。此阶段的戏曲电影,除了商业价值外,艺术价值还没有发挥出来。此类戏曲片更多是对戏曲舞台的记录,可以将其称之为舞台纪录片。作为中国人民的主要娱乐形式,戏曲无疑是家喻户晓的,所讲述的故事能引发大多数观众的情感共鸣。因此,戏曲电影在这个阶段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的是早期电影创作者看到了戏曲的商业价值,必然的是因为其要借助戏曲的本体来完成一个新的媒介形式的呈现。
1.2 以影为主导:从“影戏”到“戏影”
20世纪中期,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家和以费穆为代表的电影艺术家,对中国戏曲电影从“影戏”转化为“戏影”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电影诗人”称号的费穆,在1937年与著名的戏曲艺术家周信芳合作《斩经堂》,这部戏曲电影得到了田汉的称赞:“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他的此番评论肯定了戏曲电影存在的意义,传统的戏曲艺术依靠电影的艺术形式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观点也成为历代戏曲电影研究学者的共识。
对于戏曲电影的概念,高小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中这样写道:“用电影艺术形式对中国戏曲艺术进行创造性银幕再现,既对戏曲艺术特有的表演形态进行记录又使电影与戏曲两种美学形态达到某种意义的融合的中国独特的电影类型。”1948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由费穆先生导演、梅兰芳先生主演的《生死恨》诞生。戏曲电影《生死恨》,不再是采用固定镜头进行舞台记录,而是在场景布置上采用实景拍摄,比较突出的是影片中出现了一架巨大织布机。1960年,崔嵬、陈怀皑执导的《杨门女将》精准地找到了戏曲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契合处,创造了我国香港电影的票房奇迹,提升了戏曲片在中国影坛的地位[2]。从戏曲电影的发展脉络上来看,这些具有实验性质的戏曲电影中所探讨的正是戏曲电影化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与内地戏曲电影齐头并进的,还有香港的邵氏黄梅调电影。著名导演李翰祥所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包含大量的镜头调度,所呈现出的戏曲电影本质是以电影为主导,依靠黄梅戏这种地方戏的唱腔完成叙事,在电影方面进行了较多的创新。1980年的《白蛇传》更是一次对戏曲电影拍摄手法的综合使用,该影片成为当时的国产票房冠军,引发了观影狂潮。“京剧电影工程”在2011年7月启动,该工程由京剧界的艺术家、电影界的艺术家和许多青年新秀共同组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谢瑶环》等戏曲电影拍摄完成。2015年,《霸王别姬》作为我国首部3D戏曲电影走上银幕,这是与时代审美气质相融合的大胆尝试。2021年,《白蛇传·情》运用4K技术和计算机动画技术,重构了戏曲电影的影像魅力,戏曲电影的大片时代正在到来。纵观戏曲电影的百年历程,技术的更新换代推动着其从“影戏”到“戏影”的革新。
2 “影” “戏”叙事的呈现与变奏
2.1 形象塑造:人物角色的重塑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戏曲吸纳了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等不同的艺术形态,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气质,其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不断成熟。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井井有条的角色体系,在悠久的戏曲表演传统中,戏曲人物形象越来越规范化,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难以表达复杂的现代人的思想情绪和内心情感世界。那么,经典的戏曲形象应该如何在银幕上焕发时代生机呢?
戏曲电影《白蛇传·情》以现代意识为指向,使白素贞的形象实现了从“妖”到“仙”的人格升华,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钟情”一折中,电影版删去了舞台版“游湖情节”的烦琐程式动作,以影像语言构建了唯美的画面。正是通过对两个人物行动的改编,使人物角色的情感世界更为贴近当下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白素贞身上那种排除万难也要追求婚恋自由,不甘屈服命运的人生态度,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需求,这也是它能获得市场和艺术双赢的深层原因。此片对法海的形象也进行了人性化改编,这里的法海心怀慈悲,和白素贞没有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对白素贞不是一种权威的压迫,而是一种“人性化”的规劝。角色的创作离不开艺术审美的需求,离不开受众与市场审美的需求,这就要求塑造角色时,既要考虑文化特性,也要考虑市场特性,在观众面前保持新鲜感的同时,赋予角色更丰富的性格特征,使经典角色再现市场活力。
2.2 主题表达:时代价值观的重塑
何为作品的价值观?通俗的解释就是一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在白蛇传的戏曲故事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演变对于主题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戏曲故事的流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需求与时代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白蛇的故事从诞生以来一直受观众欢迎,它的艺术魅力跨越了传统和现代,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白蛇故事的每一次创作都能够丰富主题内核,也改变着剧作家的创作观念,对戏曲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塑造了容貌艳丽、蛇蝎美人的白蛇形象,通过白蛇与人类的相处表达出人妖不能共存、殊途不能同归的“色戒”主题。明代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成为白蛇故事成型之作,在该作品中,白娘子有了人的性格。清代黄图珌在《雷峰塔》中对白娘子的形象不断丰富和加工,美化她的性格,故事主题肯定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将昆曲以及其他剧种常演的《白蛇传》加以整合和改编,将白娘子与法海的矛盾冲突由人与妖的斗争改为自由与反自由、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戏曲电影《白蛇传·情》结构上保留了戏曲的传统,但是在内容编排和对“情”的解读上打破了以往舞台版的演绎。影片中传统的价值内核已经悄然改变,“人若无情不如妖,只要有情妖亦人”的思辨主题代替了原来的自由抗争主题。《白蛇传·情》的主题突出,在传统故事的框架下,“旧瓶装新酒”,比起传统舞台戏曲化处理,电影版对于“情”的认知更具有人情味[3]。值得注意的是,结局是“情”与“理”的和解,佛祖将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再修千年,这是佛祖对于“情”的肯定,观众也在这种表达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3 “影” “戏”美学的差异与共通
3.1 虚实相映:写实与写意的博弈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神似”,在描写故事和刻画人物时以“传神写意”为重点。中国传统美学融入了整个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挖掘和利用,已经成为戏曲电影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写意作为一种美学观念、美学思维,是中国戏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种高度凝练的情感表达,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道家崇尚逍遥,追求超脱的人格自由,讲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审美理想,具有东方特质的思想基础构成了写意性的思想精华。追求神似的戏曲舞台刻意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其“离形得似”的戏曲观念,促使观众突破生活的表象进行艺术欣赏,可以说写意性是中国戏曲的本质内涵。
戏曲电影《穆桂英挂帅》中,杨文广与其妹杨金花奉佘太君之命,去汴京打探情报,手中握有一根马鞭便是骑马,身边配有一条木桨便是划船,戏曲中的砌末元素将写意性和虚拟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戏曲而言,演员的表演无疑是其艺术的核心[4]。开门的动作由演员往前一推而成,关门则是演员双手一合,演员的表演是实的,但进行的是一种虚拟演绎的纯粹艺术化行为。而在电影中,布景与道具一切都是实在的,电影营造的是与现实生活一致的幻觉,从而寻求观众的认同,进而达到情感的共鸣。
一味讨论两者的纪实和写意的差异会让戏曲电影止步不前,只有辩证地去看待才能产生别具一格的审美感受。两者都以生活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戏曲的虚拟性和电影的纪实性是辩证统一的,两者辩证的关系是戏曲电影自由创作的基础,恰当镜头语言的介入可以营造出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
3.2 融戏入影:戏曲美学的电影化实践
戏曲电影不是对戏曲的简单搬演,而应该是全新的艺术形式[5]。一方面它是西方技术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具有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技术的突破让戏曲电影在纪实与写意之间的博弈中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中,“电影性”压倒了其“戏曲性”,电影中没有非实物的虚拟表演,场景和空间完成了实体化。并且,受益于技术的发展,独属于电影的镜头美学与充满动作性和想象性的戏曲身体美学实现了结合,展现出了戏曲电影的写意美和意境美。
唯美化和奇观化的视觉效应,将“电影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白蛇传·情》中大多数镜头都来自特效画面,其中带给观众视觉冲击最强的无疑是“西湖环境场景”“盗仙草场景”,以及全篇特效的核心“水斗场景”。“水漫金山”长达6分钟的特效,塑造了戏曲电影《白蛇传·情》的仙侠水墨风格,其观赏性是戏曲舞台所不能比拟的。另外,这部电影中对于戏曲的唱段进行了现代音乐化的处理,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片尾曲《谁的思念》成功出圈,戏曲乐队除了琵琶、二胡、古筝、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外,又融合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等西方音乐元素。以“影”为核的戏曲电影并不拘泥于传统戏曲的虚拟化、程式化,以及以演员为中心的舞台表演的方式,还会创新采用现代化、影像化的叙述方法。
《白蛇传·情》以极具电影感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戏曲电影的桎梏,赢得了市场和艺术的双重肯定,但仍然面对着很多的质疑。总体而言,对于戏曲电影来说,它是一次“影” “戏”相互交融的典范,更促使我们对戏曲电影“影像美学”的未来进行思考。在新时代,需要更多优秀的戏曲电影来传播中华民族之美。
4 结语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具有极强的民族奇观性和艺术魅力。戏曲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必然会走进公众的视野。但在新时代,市场狭小始终是戏曲电影所面临的缺陷,然而技术的更新换代必然推动着戏曲电影从“影戏”到“戏影”的革新,为戏曲电影提供新的发展空间。《白蛇传·情》电影化的选择固然不是很成熟,但它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使更多人看到戏曲电影在新时代仍然有着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