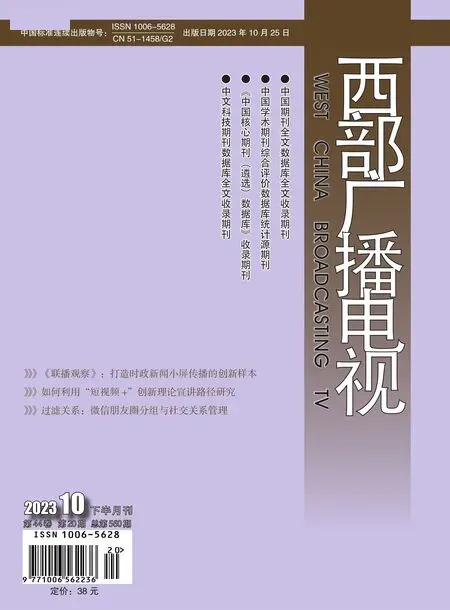国产科幻电影中基于视觉语法的反乌托邦式世界建构
王宇坤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1 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现状
科幻电影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电影类型,其凭借对未来世界灿烂的描绘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忧思,在全球吸引了大量的影迷。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人类对科学的无尽幻想与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1902年,导演乔治·梅里爱成功地将《从地球到月球》和《第一个到达月球上的人》这两部科幻小说搬上了银幕,拍摄出了人类首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开创了科幻电影的先河。百年来,电影这种能够运用可感知的视听符号建构起一个虚拟象征世界的新载体,成为人类科学幻想的新阵地。美国电影学者约翰·巴克斯特认为,科幻电影这样的现象或许终会有一天被人们视作比其他艺术门类更完整地代表着产生他的这个年代的历史性烦忧[1]。描绘人类末世图景,反思文明发展危机的反乌托邦构想更是科幻电影中常取之题材。国产科幻电影近年来呈现探索与发展的趋势,且大多基于反乌托邦科幻背景,如《流浪地球》《上海堡垒》《明日战记》。因此,研究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反乌托邦意象建构,分析其视听语言符号的艺术建构,对人们更好地认识国产科幻电影发展现状,为今后拓展海外科幻电影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国产科幻电影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影视行业是文化产业政策的关注对象。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有关影视融资、影视作品产权保护、电影院重映等政策,为影视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政策扶持。目前,我国影视行业呈现出连年迅猛发展的态势,电影供应量、影视机构数量、观众观影期待都在不断增加,整个行业繁荣发展。影视行业产业上游主要有资金提供方、内容提供方及数据监测服务提供方,中游有影视内容制作方,下游主要有影视平台、影院以及衍生变现服务企业等。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影视行业市场规模达2 349亿元,同比增长23.2%,中国文化娱乐支出仍然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此外,院线数字化是当前中国影视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数字化银幕不断强化其主导地位。如何提高影视作品质量,拓宽行业营销渠道,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影视行业,也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2 科幻电影中的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被视为一种想象的空间,其构建与社会的生产和实践过程密不可分,因为空间始终是具体化、时态性和历史性的。在电影作品中,反乌托邦主题经常被用来探索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对人类自由、权力滥用和社会控制等议题的思考。反乌托邦电影中常常描绘出通过极权主义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情节。这种统治可能表现为专制政权、智能化监控系统、独裁领导等形式。例如《1984》中,世界被虚构的“大哥”全方位地监视和控制;还有一些反乌托邦作品中,社会常常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群体,并受到不公正的分配和压迫,比如《饥饿游戏》系列中,富裕地区的人享有优越的生活,而贫困地区的人被迫参加致命的竞技游戏。还有的反乌托邦电影展示了科技的恶性发展和滥用,以及其对社会和人类自由的影响,如《机器人总动员》中,机器人代替人类从事各种工作,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荒废。
反乌托邦科幻电影起源于欧美,是现代西方社会反思现代性思潮的艺术分支。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集中反思了现代性所固有的弊端、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认为大屠杀并非偶然,而是现代管理体系之理性原则的产物,即所谓的“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都会》和《阿丽塔:战斗天使》都以此为主题。《大都会》反思了劳动异化、阶级斗争、现代化大工厂管理方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器人、仿生人)所引发的严峻社会矛盾问题;而《阿丽塔:战斗天使》则反思了人体改造技术导致的主体性危机、地球生态危机,以及外星殖民技术所带来的文明异化问题。这些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的创作源于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和对潜在问题的担忧。它们通过将科技、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趋势推向极端,揭示了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隐患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些电影所展现的反乌托邦世界,旨在让观众意识到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激发人们对其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反乌托邦的意象描绘了上述问题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和病态图景,为人类社会起到了一种警示作用。然而,不管是人工智能、人体改造还是劳动异化、社会两极分化,都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是人类社会追求工具理性的尖端科技必然产生的结果。
3 视觉语法概述
视觉语法是一种用于分析和描述视觉元素之间关系的框架,它主要用于艺术、设计和摄影等领域,以及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中。视觉语法关注的是视觉元素之间的组织和排列方式,以及它们对观看者产生的视觉效果。该理论探索了如何使用线条、形状、颜色、纹理、对比度和空间关系等元素来传达特定的意义和情感。与语言中的语法类似,视觉语法也有自己的规则和结构,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图像中的元素如何相互作用,并通过这些元素的组合来创建视觉上具有吸引力和有意义的作品。在语言学中,语法是描述词汇、短语和句子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的体系。类似地,视觉语法描述的是视觉元素(如线条、形状、颜色等)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方式。通过将语言学中的语法概念应用到视觉领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视觉元素之间的规律和效果。此外,视觉语法和语言学的交叉还体现在视觉故事叙述方面。视觉语法可以借鉴语言学中的叙事技巧和结构,通过合理的排列和组合视觉元素,创造出有连贯性和流畅性的视觉叙事效果,引导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和情感体验。其中,多模态话语分析就源于20世纪末的语言学功能理论,社会符号学家韩礼德(Halliday)在语言功能系统中提出三大语言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克瑞斯(Kress)和勒文(Van Leeuwe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视觉语法的三个意义层面,即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勒文和杰维(Jewitt)在《视觉分析手册》中又详尽阐述了有关影视作品研究的视觉语法模型框架与运用,建立了完整的视觉语法理论体系[2]。西方学者将视觉语法理论广泛应用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影视等领域,而国内视觉语言分析多停留在静态的、二维的文字与图像层面上,鲜有对影视作品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电影艺术作为一种综合艺术门类,其包含文字、图像、色彩、声音等符号元素,恰好是一种多模态的语篇类别。本文从视觉语法的三大意义层面上,对当下国产科幻电影的反乌托邦世界建构进行分析与阐述。
4 国产科幻电影反乌托邦图景建构的视觉语法分析
4.1 再现意义
在视觉语法中,克瑞斯和勒文认为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与概念再现。叙事再现中存在着“矢量”,这一动作传递概念又可以分为行动、反应以及心理三个具体过程。在动态模式的电影中,这种“矢量”的传递过程无处不在。
在《流浪地球》中,影片开头主人公刘培强与其父亲韩子昂、儿子刘启在户外告别。画面中,刘培强始终作为一名动作的发出者,拥抱儿子观星看海,将自己的特殊铭牌交给父亲,希望二人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末日中存活下来。在这段画面中,刘培强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其儿子与父亲,强烈的动作“矢量”在图像层面上传达出一种无声且悲痛的离散之情。作为反应者的韩子昂与刘启,更延伸了这种动作传递,从刘启的反问中观众得知了重要的末世背景信息,从韩子昂的眼光中能感受到刘培强执行任务多半是有去无回的悲剧结局。此时,声音与字幕又在心理层面上传递了影片三个重要事件:木星撞地球、人类逃往地下求生、主人公执行任务拯救世界。画面与声音、字幕三种模态的交叠,使得影片在开场一分钟内就已经叙述且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末世氛围。
概念再现中不存在动作“矢量”,而是表达一种概括的、稳定的、和没有时间限制的精华[2]。影片《独行月球》中,陈述“月盾计划”这一核心大主线剧情时,影片运用了数字动画与定格动画这两种模态来呈现画面。从复杂的公式演算图纸,到拟人化“地球爷爷”被撞毁情景,再到卡通公仔宇航员造型,色彩鲜艳的卡通画交融,抽象概括了小行星“π”撞击地球这一末日概念。卡通电视机与卡通观众形象更简洁地表达出人们在末世降临的背景下反乌托邦式的荒诞行径。这种丰富多样的视觉认知元素都可以被看成是不同模态的语言陈述,通过和谐、平衡、变化、统一的色彩和形状的铺排、搭配与架构,这些元素能形成特定的图像或影像,从而有组织地传达意义[3]。文字与声音层面,定格动画中卡通像素构成的“GAME OVER”(游戏结束)字样、背景解说中以及画面中出现的《和平精英》《末日空投》游戏概念等,这些游戏概念元素通过一系列的搭配,架构出一个荒诞的末日前夕世界图景。这一系列展示虽然不含有惯常的实景展示,但是能通过卡通游戏、动漫动画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完整的概念。
4.2 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强调的是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观看结构,其视觉语法系统主要包含接触、社会距离、态度、情态四个认识维度[4]。互动意义在语言功能中对应的是人际功能,因此在这一维度上讨论的便是多模态的符号与受众的交互关系。在科幻电影中,创作者们通常要利用当下生活的日常图景基础,添加和延展出科学幻想部分。
《流浪地球》中,影片分别运用了特写、近景和中景的景别,展现出了熟悉的教室、课桌、校服和转笔的学生,背景音正是同学们在朗读朱自清先生的《春》的声音与回答问题的学生的声音。这些声画符号元素建立起的日常中学上课的熟悉图景,瞬间拉近了观众与影片的距离。随后而来的电子屏故障,让整个明亮的课堂陷入黑暗,昏暗杂乱的场景与前者的明朗、美好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强烈的反乌托邦氛围。这一气氛渲染的成功,离不开导演精心选取的拍摄角度,无论景别如何变换,拍摄视角总处在一个水平视角上,仿佛观众就坐在此间教室,亲身目睹了这一乌托邦场景的破碎,拉近了观看者与影片的社会距离,增强了代入感。
除场景、声音等模态的视听符号建构,国产科幻影片对影片人物的眼神捕捉更加强了交互意义层面上的接触关系。《流浪地球》在第1小时46分到1小时48分的视听呈现中,执行最终任务的主人公刘培强的目光出现了7次,第7个镜头主人公甚至直接望向摄影机,眼神与观众对视;《独行月球》在第1小时44分钟到1小时46分钟,片中人物眼神交互画面出现了17次,分别有主人公独孤月、马蓝星以及地球上观看直播的观众群体。多次眼神交互给观看者传递了强烈的感情,推动影片达到情感高潮,在反乌托邦的未来末世下,又颂扬了乌托邦式的英雄人物。
在交互意义的情态方面,情态值又可以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在《流浪地球》《独行月球》《明日战记》三部国产科幻电影中,开篇都有一段关于末世背景的介绍性声画阐述[5]。《流浪地球》呈现了一系列未来新闻报道灾难画面,加上大全景展现生存恶劣的环境;《独行月球》用媒体报道、抽象动画和解说词呈现末日前的混乱;《明日战记》以纪录片视角客观展现战争、天灾、外星入侵等事件。三部影片在表现路径上的选择虽然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选取的反乌托邦建构方式,皆为客观、真实且贴近生活的。“联合国”“各国政府”这些语言符号都在三部影片的这三段架构中出现。这种官方语境下的表述,加上火山喷发、海啸和人群恐慌等拟新闻报道实拍,加深了可信度与真实度。相较于另外两部科幻电影,《独行月球》采用了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色彩运用,使得其在情态方面属于中等,而不同于另外两部采用原彩显示的高情态展示。但《独行月球》实质上属于喜剧,而非“硬科幻”电影,因此中等甚至偏下的情态更能展现出其荒诞的末日世界观架构[6]。
4.3 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对应语言功能语法中的组篇意义,克瑞斯和勒文分析并提出了构图意义的三种资源,即符号元素在整体中放置不同而得到的信息值、取景度以及显著性。影视作品相较于静态图像,其在构图方面需要参照的因素更多,不仅取景框中二维视觉的构图需要慎重考究,在时空层面上架构的三维构图更加重要[7]。
《独行月球》中,在影片第1小时45分钟时,画面以主人公独孤月手举核武器“宇宙之锤”为中心,从右向左完成了一个近180度的旋转镜头。在二维层面上这一段画面可切分为三个相对静态的图像:主人公与彗星“π”、主人公与深邃寂寥的宇宙、主人公与蔚蓝色的地球。第一幅图景主人公独孤月手举“宇宙之锤”作为前景居于画面中央,与正面相对位于右侧后景的彗星“π”,形成了渺小与庞大的视觉对比。彗星“π”散发着的陨石尘埃在光的映射下如同怪物的触手一般占据了整个画面,而渺小的人类主人公此刻即将被这只“怪物”吞噬。第二幅图景中主人公依旧作为前景位于画面中心,而后景则是漆黑一片的宇宙,主人公与“宇宙之锤”则是纯黑的背景下唯一的光,在孤独感的包裹下突出了主人公的形象。第三幅图景中,地球在左侧作为后景出现在主人公独孤月身后,依据透视原理,原本庞大的地球此刻在画面中看起来如此微小,甚至在形态上小于作为人类的独孤月。此番构图配合影片主题曲《回家之路》,形成了一整套空间叙事:渺小的人类义无反顾冲向彗星只为守护家园。
5 结语
近年来,国产电影随着我国经济与实力的发展而开始深入探索科幻题材影片。我国科幻电影尚需要时间发展成熟,剧本与科幻世界观架构显得单一且浅薄,离“硬科幻”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路,但是可以看到,国产科幻片正在用新的方式来呈现对未来世界灿烂的描绘,积极传播国家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