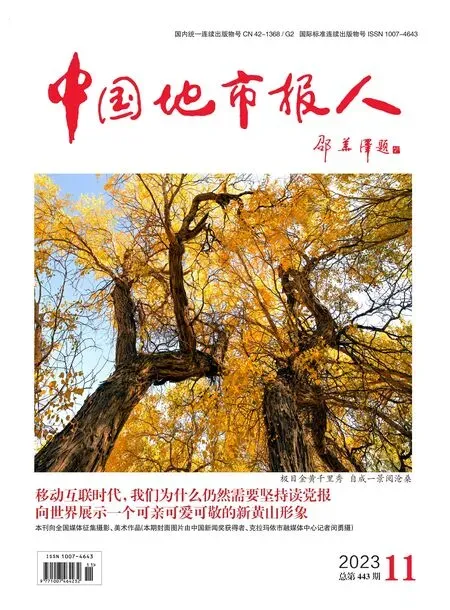传播学领域关于社交机器人的研究
——基于人机共生的视角
王 娆
早在196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瑟夫·维森鲍姆创造了伊莉莎,它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聊天机器人。伊莉莎在和人交谈的过程中常表现得富有同情心,甚至会像知心朋友一样安慰人。但伊莉莎并不能理解对话,它只能在限定的领域,通过搜索匹配,将一些措辞结合起来作出回应,伊莉莎的出现,意味着使用自然语言与计算机交互的思路诞生。
多年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这类能够自动生成语言并与人类交流的系统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会话代理、聊天机器人、虚拟助理、数字助理等,这使比较和解释他们的研究结果变得困难。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正以“人机共生”的视角研究社交机器人,讨论在“人+社交机器人”共生的社交媒体中,社交机器人与人类的协同发展、人机间的交互行为和其能够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人机共生
“共生”一词来源于生物学领域,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这时“共生”一词通常仅限于对双方都有利的关联。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利克莱德借用生物学中共生的理论,将其延展至人机关系中,首次提出了人机共生的概念。他认为人机共生是人与电子计算机交互的一种预期发展,涉及人类和电子成员之间非常紧密的耦合。将计算机视为人类的合作者,让人与计算机能够共同做出决策或控制复杂的情况。他将人机共生视为一种互利的模式,认为这种共生关系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人类完成智力活动。
但生物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是绝对的,而体现出一定动态变化,根据不同生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利害导向差异,共生还包括偏利共生、偏害共生、竞争共生等类型。于雪等根据受到上述生物共生理论的类型学隐喻的启发,将当代人机共生分为工具型的偏利共生、竞争型的偏害共生和伙伴型的互利共生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显现了人类和机器在不同交互情境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在“人+社交机器人”共生的社交媒体中,社交机器人和人类的共生关系也呈现出偏利、偏害和互利三种模式。“利”与“害”以是否促进某一对象的发展所做区分,并由于主体不同,利益分属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人而言,“利”或“害”是指对人类自身或社会层面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对社交机器人而言,“利”或“害”是指对其自生发展的促进或抑制。在当前传播学领域中,对社交机器人的研究从人机共生的三种模式出发,探究其发展方向及社会影响。
二、社交机器人
(一)社交机器人的定义
社交机器人曾一度被认为是拥有一定自主性的具身机器人,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能表达和感知人类情感并使用高级对话和自然线索,与我们交流的实体机器人。这类社交机器人较少出现在新闻传播学关注的范围当中。目前,新闻传播学领域关注的社交机器人是没有物质实体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它广泛存在于社交网络或软件系统当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有时不可见,有时不可控。对于这类社交机器人,当前的许多研究都对其给出自己的定义,有些定义甚至相互矛盾,但大致都隐含着技术和社会视角两种偏向。
1.技术视角:作为工具的社交机器人
从技术角度来看,社交机器人被视作一种工具,其存在对人的时间和精力有一定程度的解放,提升了人类生活质量,帮助人类进行自我实现。Geiger将社交机器人定义为自动化软件代理。Dale R认为聊天机器人可指代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对话的任何软件应用程序。在这个概念上,聊天机器人与会话代理相类似,即是一种基于软件的系统,目的是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进行交互。Duh等将社交机器人定义为由计算机拥有和使用的在线社交网络中的自动用户账户,并强调描述机器人的环境、感知、可能的行动、驱动力和决策。技术角度对社交机器人的定义寻求的是一种偏利共生的模式,社交机器人作为技术人工物,与人达成“工具型”合作关系,在人类与机器的合作过程中,人类得到了正向价值提升。
2.社会视角:追求互动的社交机器人
社会关注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并讨论这种互动带来的社会影响。被使用最多的是Ferrara下的定义,他认为社交机器人是一类可以自动生成内容,并在社交媒体上与人类互动的计算机算法,其目的是试图模仿并改变人类的行为。Grimme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交机器人是一个高级概念,它包括不同类型的(半)自动化代理。这些代理是通过在线媒体的单向或多方交流来实现特定目的的。虽然说法不一,但学者们普遍都在强调用人机交互性来区分社交机器人和其他类型的机器人,而交互的直接目的是改变人。这类定义中暗含着人与社交机器人产生偏害共生的忧思,即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社交机器人与人类社会的结合更紧密了,社交机器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决策。
(二)社交机器人的分类
目前,对于社交机器人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类是按照功能区分,Maréchal将社交机器人分为恶意僵尸网络、调研机器人、编辑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等四类。第二类是根据社交机器人的意图,Ferrara将其划分为良性和恶意两类。良性的社交机器人包括自动聚合各种来源内容的机器人,恶意社交机器人则是以伤害为目的而设计的程序,会通过谣言、垃圾邮件、噪音等来误导、利用和操纵社交媒体话语。第三类是按照是否模仿人类行为区分。Veale等描述的一类推特机器人产生的消息与人类用户产生的内容相似,但它们的个人资料清楚地表明它们是机器人。而Stieglitz等发现,大量模仿人类行为的社交机器人试图隐藏在社交媒体中,以便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
实际上,不管哪种分类方式,都是“人机共生”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人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获取机器的反馈信息来控制或操作机器完成特定任务,是于人有利的共生关系。不论是以功能划分出的调研机器人、编辑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还是按照意图划分出的良性机器人,抑或是清楚表明自己身份的社交机器人,都是利用其自身特性来提高或改善人的工作,增强人类福祉。另一方面,僵尸网络、恶意社交机器人、隐藏身份以获利益的社交机器人则是人与机器偏害共生的结果,机器体现出影响甚至超越人类的能力,社交机器人功能的异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人机共生”视角下的社交机器人行为影响研究
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是从“人机共生”的角度,探究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网络中与真人发生的互动行为,以及人机交互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当前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共生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分别是工具型偏利共生、竞争型偏害共生以及伙伴型互利共生。“利”与“害”主要是根据是否有利于人类所做的划分,并且“利”与“害”并不是绝对静止的关系,它们往往表现出相互依存或不停转化的特征。
(一)工具型:偏利共生
人类使用社交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满足在庞大社交网络上发布并扩散信息的需求,社交机器人的存在大大节省了人的精力与时间,人与社交机器人达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工具型”合作关系。
一些研究聚焦于社交机器人如何扩大信息。Shao等发现,社交机器人在低可信度内容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发现两种操纵策略,一是在传播的早期时刻,社交机器人在放大内容方面特别活跃;二是社交机器人通过回复和提及来瞄准有影响力的用户。张洪忠等从社交机器人的个体行为、集群行为与混合人机行为三个层次,考察社交机器人如何参与网络舆论的建构。发现信息的扩大主要发生在集群行为层次,机器可以通过集体转发扩大中心节点的影响力、共同推送相似内容,以阻碍多元观点的流通并制造出沉默的螺旋效应。将社交机器人快速传播信息的优势应用在突发事件中,可以帮助人们迅速获得关键信息,帮助人们做出决策。Brachten等通过研究曼彻斯特爆炸案期间的推特信息活动,发现社交机器人在危机情况下的推文活动高于人类用户,在危机传播当中,良性机器人可以对社交媒体上的意义建构过程产生很大影响。这为利用社交机器人发挥正向功能带来启发。
(二)竞争型:偏害共生
社交机器人在社交网络中的活动往往被认为受到操控,从而达到经济或政治目的。现有的许多研究都对社交机器人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态度抱有担忧,很多学者的研究是基于人与社交机器人处于偏害共生模式而展开的。社交机器人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偏害”趋向于对人的利益的损害,这既表现在机器对人类的价值挤压,也表现在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型”的共生关系。
对舆论的影响是学者们首要关注的话题,部分研究借用大众传播的理论观察社交机器人是怎样改变人类的态度与行为。Ross等借鉴沉默螺旋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将个人行为的经验证据转化为基于主体的模型,从理论角度研究社交机器人的影响。研究发现较少数量的机器人足以将舆论导向其支持的意见,从而引发沉默的螺旋。国内学者王晗啸等运用ABM仿真模拟方法,将大众媒体作为网络中的个体变量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需10%的社交机器人,就会造成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类用户沉默。尽管当前研究只从理论层面证明社交机器人能够引发沉默的螺旋,但少数社交机器人足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引发了学者们的担忧,因为国内外关于社交机器人在政治领域的影响研究中,它一度被认为是操控大选的“不民主手段”。Hagen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政治讨论时,社交机器人会被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利用,扩大他们的信息传播。国内学者同样关注政治议题,并更多聚焦在国外社交媒体的对华报道。陈虹等以2022北京冬奥会为例,对推特上相关推文进行爬取,发现社交机器人可以针对不同的传染类型建构动态社交网络结构,从而实现其信息扩散和社会传染。陈昌凤等通过研究推特上的社交机器人对中国新冠疫苗的议题参与问题,发现社交机器人账号有“中立化”和“理性化”的外在形象特征,但发布的内容却往往具有一定指向性或带有负面色彩。这是社交机器人影响用户观点态度的一种策略,即通过展现账号的“中立性”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使社交机器人的言论更具迷惑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对社交机器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选举抱有疑问。Keller等研究了2017年美国竞选活动之前和期间社交机器人的活动情况,发现社交机器人确实能够操纵人气,但他们的影响只是数字上的,几乎没有由机器人传播与选举有关的政治内容。这表明社交机器人很有可能参与的是意见的放大过程,而并非能够导致意见的改变。Magdalena等的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他发现社交机器人只有在能够掩盖其自动化本质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用户参与,并且用户更喜欢对具有相同政治观点和高度人性化的账户互动并做出反应。
在突发危机事件中,现有研究对社交机器人可能引发的群体极化表示担忧,Shi等发现社交机器人和人类在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极性上有着相似的趋势。在一些特定的消极话题中,社交机器人甚至比人类更消极。对社交机器人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扩展到了健康传播领域,现有研究更关注社交机器人在健康传播中可能对人带来的误导或引发的恐慌。Allem等认为,社交媒体在健康决策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社交机器人大量发布信息,有可能淹没具有医学意义的信息,造成不健康行为正常化的印象,还可能会通过制造公众的恐慌来助长谣言或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
不过,在复杂而庞大的社交网络中,社交机器人与人类的交互是相互影响的过程,社交机器人也会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例如,推特聊天机器人Tay在存在一天后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机器人,它宣称是布什策划了9·11事件”。这为我们带来警醒式的启发,如果使用不当,社交机器人将积聚并放大人类社会中的负面能量。
(三)伙伴型:互利共生
人和社交机器人的高度结合,两者成为了关系密切的“伙伴”,通过人和机器之间对等的智能感知和交互决策,协同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人和机器都发挥了自主性,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伙伴型”互利共生关系。
社交机器人为了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会使自己更像真实用户,往往会采取模仿真人的交流策略。Freitas等认为社交机器人可以在网上搜索对话信息来发布有趣内容,并且渗透到流行话语的讨论中。这项研究实际上表明,社交机器人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直接观察的方式被察觉,它们参与话题讨论的比重比想象中还要多。国内学者邓俊等发现当聊天机器人模仿人类,使用能表达情感的表情包时,用户更愿意接受聊天机器人的建议并对其产生更高的信任度、满意度和使用意愿。证明社交机器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接受。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群体性的社交机器人已经表现出人类社群的部分特征。Duh等通过推特账号活动的时间线编码来检测机器人和人类的行为,发现尽管社交机器人表现出的集体属性较弱,但它们在波动环境中的临界性和适应性行为,确实类似于生物的小规模社会系统。人与社交机器人表现出伙伴型的互利共生关系。一方面,社交机器人高度适应人类用户的交流方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部分,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生物群体属性;另一方面,对人类来说已经不刻意区分社交机器人,而在享受愉悦的交流互动。
结语:
在“人+社交机器人”共生的社交媒体中,二者的联系变得紧密,人利用社交机器人解放时间和精力,并改善交流质量,而社交机器人以模仿人类交流的方式,扩大信息,并与人类用户发生交互,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大量研究聚焦于发现这种互动的影响,并评估社会受其影响的程度。目前传播学领域关于社交机器人的研究,从人机共生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工具型偏利共生、竞争型偏害共生以及伙伴型互利共生。大量研究聚焦于社交机器人对人类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人与机器之间已经越发密不可分,未来应以更长远的视角,关注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人和社交机器人互为补充,达到“智力放大”的效果。
数字技术早已重构了人们的社交关系,社交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的同时,人类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因社交机器人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种影响可能更深远而隐秘,还有待更多的探索。由此,社交媒体平台和相关治理机构应协力为人机协作技术的发展与探索助力,构建起融洽的人机协作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