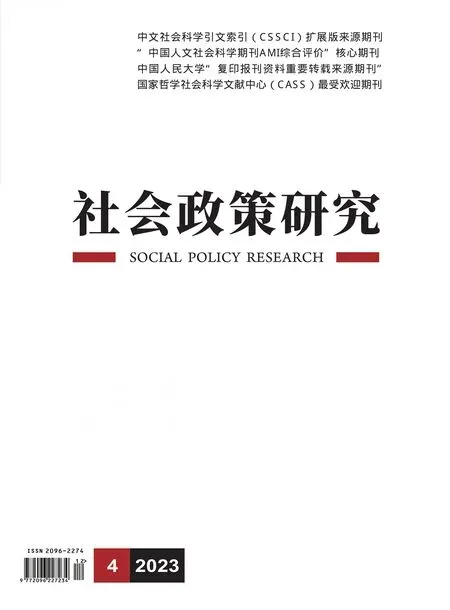儿童早期福利的国外政策实践与中国路径选择
廉婷婷 乔东平
儿童早期是生命周期的开端,机会与风险并存,需要高质量、多样化、灵活性的福利供给。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 成员国较早启动儿童早期福利政策实践,以应对儿童早期不平等、家庭养育能力不足、人口出生率低与结构失衡、人力资本不足等挑战。2021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亦强调“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括对儿童早期养育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情境与国际经验,从社会保障制度层面设计儿童早期福利整合支持的政策框架。本文以吉尔伯特社会福利政策的分配基础、分配内容、服务输送与资金来源为分析框架,选取四类儿童早期福利政策实践的国别代表,分析其经验,明确责任分工、对象资格、福利内容、递送机制、质量标准、管理机制等要素,探究如何通过福利制度设计投资儿童早期发展,为我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体系完善提供参考。
一、儿童早期福利的概念框架与国际共识
(一)儿童早期发展与儿童早期福利
儿童早期主要有0—3、0—6、0—8 三种年龄段界定(岳爱等, 2019;Laveric & Jalongo,2011)。针对儿童早期的讨论集中于教育、照护和发展等领域。联合国以及相关研究采取“儿童早期发展”的概念,支持儿童身心成长,保障每个儿童“最大限度地存活与发展”,OECD 国家使用“早期儿童教育与照护”框架保障儿童权利、支持家庭发展,为有工作的父母提供早期教育和托儿服务(Moss, 2012)。前者通过干预儿童早期阶段的身心发育保障权利平等;后者强调实施早期教育与照顾的整合性项目(Haddad, 2002)。但是,何为儿童早期福利未达成共识①以“儿童早期福利”与“早期儿童福利”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无法检索到有效文献。1985年Meckel R.A.发表的文章“Protecting the Innocents: Age Segregation and the Early Child Welfare Movement”提及“儿童早期福利”但未解释内涵。本文对“儿童早期福利”的概念进行界定,避免“早期儿童福利”可能引起的“儿童福利”的早期阶段的误解。。从我国儿童福利保障实践看,偏重侠义上的福利,更多聚焦于救助,为困境儿童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与健康保障,“特殊儿童”和“保基本”是主要关注点;广义福利涉及直接面向儿童的义务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健康保障等。我国儿童福利的部分内容回应了儿童早期阶段的需要,但尚未从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协同设计儿童早期福利整合支持框架。
儿童早期福利框架整合性地回应儿童早期及其家庭的福利需要。不仅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儿童的需要,还侧重儿童所在家庭的需要,强调生命全周期的福利设计。通过制度性的福利供给满足儿童及家庭的福利需要,特别是对弱势儿童特殊需要的福利回应。国家、社会如何通过资源调配回应儿童早期的成长需求以及其外延的家庭发展需求是儿童早期福利设计的核心议题,是对儿童早期发展供需关系的制度性平衡。
基于此,本文提出“儿童早期福利”概念,即国家、社会、市场等主体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宗旨,为满足0—6 岁儿童及其家庭普遍和特殊的福利需要而采取的任何福利供给形式和保障制度措施,以实现儿童福祉。儿童早期福利注重对儿童权利以及儿童福利需要的服务、现金、实物等方面的制度回应,强调国家、社会、市场等不同供给主体与家庭在儿童早期福利需要回应中的关系和责任共担,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
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既是对儿童早期福利制度的整合性设计,又是儿童福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通过采取经济性、服务性等国家干预手段回应0—6 岁儿童的现实需要而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或行动准则,回应儿童早期福利需要,保障儿童早期基本权利。政策具有预防性、补救性、发展性等不同特性,包括以促进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生存发展与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政策内容,以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等形式呈现。
(二)实施儿童早期福利的国际共识
生命初期是儿童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将对个体、家庭、社会与国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相关政策和行动为个体成长以及认知、社交和情感技能增强的机会提供基础(Conti &Heckman, 2013)。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艾斯平·安德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意在消除儿童贫困和极端经济不平等(Esping-Andersen, 2002)。研究表明,在儿童早期阶段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可以提高后期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成就、减少健康方面的不平等、降低犯罪及暴力的发生率,并能提升个体成人时期的健康水平与经济能力、个人福祉及生产力(Dua etal., 2016)。同时,儿童早期投资具有利益外溢性,包括为劳动力市场积累人力资本,缓解社会分层的固化趋势,促进代际公平,提高公共资金的回报率等(孙艳艳, 2015)。接受高质量早期照护与教育服务的儿童能够在短期内(部分是长期内)改善发展结果,在消除贫困和不公平方面的干预效果明显优于后期(Abbott etal., 2003;Carneiro & Heckman, 2003)。
儿童早期的政策规划与行动是国家满足儿童早期需要的福利手段,有助于解决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79年世界儿童状况》引发国际社会对儿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注。2000 年《达喀尔行动纲领》确定早期儿童照顾和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同年,UNICEF 发表以“儿童早期”为主题的《2001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虽然政府在民众的生命周期中为其提供与日俱增的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开支,却并未在早年关键阶段支持其能力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4)。目前,美国、英国、瑞典、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了儿童早期综合支持计划。
二、国外儿童早期福利政策行动的类型分析
根据儿童福利领域常用的补缺型/选择型与制度型/普惠型的划分(Wilensky & Lebeaux,1965; Titmuss, 1968),本文把发达国家儿童早期福利分为四类进行分析:典型补缺型、典型普惠型、兼容普惠型、由选择型转向普惠型,分别以美国、瑞典、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以吉尔伯特社会福利政策分析为框架,系统梳理各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的特点,根据我国当前儿童早期福利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方向依次呈现四种类型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
(一)典型补缺型:以选择性福利为主要形式的美国儿童早期福利设计
美国儿童早期福利覆盖范围广、投入大,具有立法先行的特征。国家有条件地为早期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支持,建立基层化福利服务输送体系和多样化现金援助体系。尽管部分服务有普惠趋势,但整体呈补缺取向。从政府资金使用和分配上可以看出,现金援助和服务保障等是现实主义取向的,倾向于支持因家庭能力不足、不能享受良好早期养育环境的儿童。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政策关注处境不利儿童的保教和健康。美国在20 世纪30 年代实施0—6 岁儿童整体教育计划,1965 年实施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ject),《开端法案》(1981)规定为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提供医疗、教育、营养、社会适应等免费服务。2019 年出台《工薪家庭儿童保育法案》,要求系统支持残疾婴幼儿的需要,更好地协调照顾和护理服务等;建立幼儿保育计划,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都能获得相应的服务;规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0—13 岁儿童保育方面的资金分担比例,面向3—4 岁儿童保育项目全面普及,提供全时间段服务①详见Child Care for Working Families Act 原文.。通过实施“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提供食品券、电子卡、健康体检、膳食营养、咨询服务等,为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和0—5 岁儿童提供健康支持。
第二,实施以“开端计划”为基础的多领域福利服务的联合供给。最初该项目为贫困儿童提供营养、教育、医疗、照顾等服务,满足其早期成长需求。后续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完善项目管理标准、拓展服务时长到全天全年、鼓励家长参与、扩大儿童资格范围。为50 多个州的城市与农村的儿童及家庭提供多样化服务,促使0—5岁儿童在中心、家庭、儿童保育伙伴等地点获得全面发展①详见HEAD START OFFCIE 关于该项目的公开资料,https://www.acf.hhs.gov/ohs/about/historyof-head-start.。2017—2018 年数据显示,89 万人(含孕妇6 千余名)获得卫生服务、残疾人服务、家庭服务中心服务和特定服务(如儿童危机干预与心理健康、受虐儿童保护服务、儿童支持计划、育儿教育等)②详见HEAD START OFFCIE 关于该项目的公开资料,https://www.acf.hhs.gov/ohs/reports.。政府一直维持儿童早期发展策略,将1995年面向0—3岁婴幼儿的“早期开端计划”与“开端计划”合并,福利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创新服务形式,扩大经费投入,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全阶段、系统性服务。
第三,早期福利供给采取自上而下的递送方式。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下属的儿童和家庭管理局(ACF)负责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并协调和监督各州工作③详见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网站,https://www.acf.hhs.gov/about/history.。5 岁以前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主要依靠福利部门完成,5—6 岁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负责。ACF 下属的“开端计划”办公室和儿童保育办公室(OCC)在早期护理和教育项目中提供资金、培训和技术、监督等支持,强调国家责任的同时重视家庭功能的发挥,保障家庭拥有自主选择儿童保育方式的权利④详见《儿童保育法案》(Child Care Act1979)第1121 号法案中的解读,https://www.congress.gov/bill/96th-congress/house-bill/1121/all-info.。
(二)选择型转向普惠型:以逐步普惠和综合支援为顶层框架的日本儿童早期福利设计
日本儿童早期福利受少子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覆盖全周期、全领域的育儿支援制度,建立以《儿童福祉法》为框架的统一性国家政策体系和儿童早期综合发展计划。近年来,为应对少子化危机,育儿支援制度已由选择性供给转向普遍性供给,育儿责任的国家性和社会性更加凸显。福利取向由“扶贫救助”取向转变为儿童与家庭“自立与援助”取向,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日本分层次普惠服务是基于国情和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型福利选择。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全面支援、全阶段的综合性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1947 年《儿童福祉法》最早提出育儿支援服务,多次修订后作为基本性和综合性的儿童福利法律依据。一系列单行法律就照顾、教育、医疗、营养和家庭教育等作出规定:一是孕产妇纳入儿童早期福利范围,出台《母子福祉法》为孕产妇及新生儿提供营养和健康服务等;二是建立以家庭为取向的育儿支援制度并推进其普惠式、全阶段和综合性发展。《新少子化对策》(2005 年)取消父母是职工的资格限制,鼓励社区参与;《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15 年)扩展育儿支援至全阶段。《儿童及育儿支援法》(2019)推进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企业主导型限额内免费);0—2 岁儿童低收入家庭保育免费。《关于强化儿童及育儿政策方案(试行)》(2023)逐步扩大育儿支援领域,涉及服务、津贴、育儿假等。
第二,形成保育、教育、医疗、保健、贫困救助、伤害预防等为核心的儿童早期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津贴类型,福利供给责任由国家—社会—市场联合承担。实施“新支援制度”,明确三种给付类型和地方育儿支援的推进措施,由社会承担所有费用,完善管理机制①育儿支援政策原文见:内閣府の政策.政省,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inseido/law/seishourei.html.。地方育儿形式及育儿机构类型多样,呈现出运作市场化、申请资格认定规范化、机构类型多元化、监管全程性等特征,调动企业、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团体等多主体参与。
第三,通过“横向网络”和“纵向网络”搭建全国性共助体制,实行信息共享机制。横向网络由儿童早期福利的各部门构成,纵向网络由各个地方儿童育儿协会组成。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雇佣均等与儿童家庭局、内阁府成立的儿童育儿总部负责国家层面的育儿支援制度及政策的推行、监督及管理,都、道、府、县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育儿支援政策。国家的社会保障审议会、儿童育儿协会和地方各级的儿童福利审议会负责监督。在服务递送上,建立从国家再到市、町、村和基层儿童福利机构的渠道,通过儿童咨询所、福利事务所和家庭儿童咨询室、保健所和市町村保健中心、母子健康综合支援中心以及各类育儿机构提供服务。
(三)兼容普惠型:以投资儿童及家庭为核心的英国儿童早期福利设计
英国儿童早期福利兼顾儿童与家庭,早期投资与儿童本位理念突出,政策具有延续性。英国强调托育与教育一体化,建立以儿童和家庭双核心的现金津贴、服务保障、税收优惠等供给体系,并通过税收和储蓄账户的形式调控福利资金,规避家庭育儿风险,减轻家庭责任,调节不同阶层之间的福利水平。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儿童早期福利政策呈现体系化特征。《婴儿生命保护法案》(1929)、《儿童法》(1908)、《母亲和儿童福利法案》(1918)等明确提供儿童早期福利与保护。《国民健康服务法》(1948/2006)建立免费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与社会保健法》(2012)②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12, https://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0-12/health and social care.html.导向公平、效率与国家责任结合,妇产与新生儿服务是重要内容。学前教育政策采取家庭支持取向,强调人力资本建设。1998 年《支援家庭》《幼儿保育税收法案》《应对儿童保育挑战:全国儿童保育战略》等推进普惠性服务。《儿童保育十年战略》(2004)和《儿童照护法》(2006)③详见Childcare Act,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6/21.促进了保教一体化进程。《每个孩子都重要》(2003)④详见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Every Child Matt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very-child-matters.由事后救助转向预防,重点关注贫困儿童、残障儿童、孤儿院或家庭收养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吸毒或有不良行为的特殊儿童。《重要的0—3 岁》(2002)、《早期基础阶段方案》(2005)及《保护处境不利儿童:实践指南》(2009)等改善全体儿童环境的同时关注弱势儿童。《早期教育阶段法定框架》建立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标准,逐步强调质量与一致性,加强家庭与机构的合作。《儿童法》(2016)和《早期教育和儿童保育:法定指导》(2014/2023)①详见Statutory guidance Early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arly-education-and-childcare--2.作为儿童早期福利的综合指引,明确规定对象资格、福利领域、服务内容体系、质量标准、收费标准和责任分工等。
第二,建立集保育、教育、社会服务、健康保健、发展咨询等整合式早期服务体系和现金转移支付体系。自“确保开端”(Sure Start)计划实施以来,英国为5 岁以下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教育与保育、大龄儿童课前与课后看护、家长与儿童互动游戏和活动平台提供、保育员支持、卫生健康服务,并为家长提供教育、咨询和信息服务,家长教育、产前与产后课程、家庭关系课程、拓展性家庭服务(如家访)等(Hall & Eisenstadt, 2011)。所有学龄前儿童均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与营养咨询服务。现金援助涉及16 岁以下儿童的福利津贴②详见Claim Child Benefit, https://www.gov.uk/child-benefit/what-youll-get.、家庭津贴及产假、双亲离世儿童的监护人津贴③详见Guardian's Allowance, https://www.gov.uk/guardians-allowance.、初级个人储蓄账户(ISAs)④详见Junior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ISA)的介绍,https://www.gov.uk/junior-individual-savings-accounts.和托育与教育津贴⑤详见Childcare You Can Get Help Paying For 的介绍,https://www.gov.uk/help-with-childcare-costs.。
第三,组织形式与责任分工明确,分领域管理。英国教育部负责规划托育教育,地方政府依据本地情况落实、拨付资金,提供信息和培训。教育标准局(Ofsted)负责监督、管理、注册儿童早期托幼服务,服务提供方为各类学校,政府承担免费时长的费用。健康保健服务由卫生部管理,设立专门的NHS 委托服务理事会进行统筹和监督,由地方临床委托服务组织(CCGs)推进及落实,服务质量委员会(Care Quality Commission)负责监管。税务海关总署(HMRC)负责提供部分税收优惠或津贴。儿童福利办公室负责儿童福利津贴发放、特殊弱势儿童及家庭的服务保障等。
(四)典型普惠型:以普惠性家庭支持为导向的瑞典儿童早期福利设计
瑞典儿童早期福利实施普惠性家庭支持的方案,福利政策与劳动政策高度结合,建立以《儿童权利公约》为框架、涵盖多领域的政策体系,强调育儿的国家责任。通过津贴、保险和服务等形式保障家庭的育儿能力,尽可能多地支持家庭。福利覆盖范围广,涉及儿童生存和发展的各领域和全阶段。提升育儿质量的同时支持父母工作,保障经济发展,并继续提升福利水平,形成良性循环。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国家政策与国际公约并行,重视儿童权利和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以家庭支持取向为主,同时支持儿童及其父母。2018 年瑞典将《儿童权利公约》纳入法律体系,确定儿童各项权利保护要求,成为《儿童和父母法》《教育法》《关于为部分功能障碍人士提供支助和服务法》《社会服务法》的解释参照①详见瑞典政府办公室公告,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8/03/new-legislative-proposalon-the-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其中,《带薪亲职假法》规定,婴幼儿18 个月以内的,父母每天工作6 小时或全休;年纪8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每天工时减少1/4;父母可在儿童8 岁前使用育儿假。福利资金来源于税收,根据父母的收入支付育儿假工资,即使不满足工作要求也能享受较低的津贴(Duvande etal., 2010)。
第二,儿童早期托育与教育服务、早期语言发展及阅读服务、早期健康计划是福利服务的主要内容。一是保育服务,1 岁以上儿童可享受由政府公共财政补贴的托育和学前教育服务,3 岁以上儿童免费时长每年可达525 个小时②详见瑞典官网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的介绍,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80_en.,6 岁儿童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学前教育。二是为0—3 岁儿童开设的BookStart 项目。由市政府、托儿中心和图书馆合作的图书捐赠计划,目的在于促进0—3 岁儿童的早期语言发展③详见Council, S.A.2018.Fem pilotprojekt utforskar hembesök och möjligheter till samverkan.[Five pilot projects explore home visi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Stockholm: Swedish Arts Council, https://www.bokstart.se/.,与家访项目结合提供培训、亲职教育等服务。三是儿童健康计划,0—6 岁儿童享受家访、母乳喂养与饮食咨询、身体检查、接种疫苗、听力和视觉检查等免费服务;免费在儿童保健中心和校卫生所看病或在医院住院治疗。孕产妇保健服务由政府承担相关费用(何玲,2009)。
第三,采取国家干预模式,实施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瑞典教育署、司法部、文化部分别主管学前教育、儿童保护、文体娱乐等政策设计和服务规划,儿童福利和保健主要由国家卫生与社会事务部负责规划④详见瑞典政府办公室官网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的介绍,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of-sweden/ministry-of-health-and-social-affairs/.,地区级下属部门和地方下属部门负责落实。设立国家儿童权益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国家平等监察员办公室,监管全国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工作。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责任分工,《社会服务法》规定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门机构提供相关的儿童福利服务,政府设置日托、半日托等,鼓励市场提供托育服务。
三、国外儿童早期福利政策的共性逻辑与经验启示
系统梳理四国儿童早期福利的政策经验后发现,尽管福利方案侧重点不同,但背后存在共性逻辑,可以批判性地讨论其适用性和政策意义。其中,体系化、投资取向、关注家庭、精准化供给、责任共担等经验有助于我国特色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的完善。
(一)国外儿童早期福利政策行动的共性逻辑
基于国情、社会福利制度和历史发展经验,四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与制度呈现出差异与共性(见表1)。儿童早期福利制度的安排与其社会现实背景和需要相适应,因此在制度选择、政策设计与福利供给方面表现出差异。19 世纪中后期至20 世纪80 年代,在“国家家长主义”的政策取向下,西方儿童福利开始由补缺型走向普惠型,福利对象由“失依儿童”逐步转向全体儿童(乔东平、谢倩雯, 2014)。《儿童权利公约》生效后,发达国家更关注“儿童权利”和“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尽管各国的政策选择各具特色,但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和行动选择仍具有内在一致性。
国家社会现实情境、福利理念与“国家—社会—家庭”的关系导向直接影响儿童早期福利对象与福利供给责任的选择,并通过多样化的福利供给形式支撑儿童早期福利递送。基于四国儿童早期福利制度安排特别是对象选择、福利内容、提供策略与资金来源的设计可以看到,福利制度取向和福利目标决定了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中的责任分工和给付原则;而独特的儿童早期福利理念直接影响福利对象及其福利水平。此外,由于各国儿童福利模式和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机构的类型不同,在服务提供路径和对象资格上存有差异。其中,服务提供路径通常分为家长申请、政府评估或无需申请直接享受等。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在不同福利项目的供给上也存在年龄、内容和普惠程度的差异,体现出精细化的设计思路。
(二)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设计的经验启示
基于吉尔伯特社会福利政策框架以及四国政策选择逻辑,可以从分配基础、分配内容、服务输送与资金来源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维度总结国外共性经验。
一是基于本国国情的福利理念和福利目标选择福利对象。相对于其他福利供给,儿童早期福利的对象覆盖范围更大,对象资格和条件限制较少,通过分类设计的方式惠及特殊儿童及一般儿童,具有显著的普惠性或某些普惠倾向,投资儿童特别是投资其早期成为共识,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的价值选择。
二是强调制度框架的整合性与政策体系的联动性,投资儿童和家庭支持取向并重。各国原有单行政策逐渐变为全国性、多领域的整合型政策,并与劳工福利、妇女福利、家庭福利和儿童福利衔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儿童早期福利制度与政策框架。通过多种形式提供早期照顾、营养与健康保健、早期教育与发展、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等方面的综合性支持,将儿童早期发展的各项需求视为一个系统或整体,从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上整合回应。
三是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和多层级的服务输送网络确保福利内容高质量供给。各国“立法先行”,中央设置明确的专门机构负责统筹管理全国儿童福利工作,地方政府的监管和落实以及基层设施的完善、多领域多形式的福利服务机构保证福利的供给和可获得,通过专门的监管机构和服务监控标准保证服务质量,培养一线专业人员开展儿童早期服务等。福利项目组合、福利对象资格以及福利递送形式等均采取了精准化、精细化的思路,并以基层服务作为福利递送的重要手段。
四是政策设计与国家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在不同领域细化,各国基于社会福利制度类型规定责任分工。总体上,各国中央政府统筹福利保障的资金,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和税收为主。在福利资源分配方面,根据儿童早期福利的普惠倾向进行全国调配,并由各分层福利递送的主体补充。但在具体领域上,各国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普惠性供给及部分普惠性供给的形式给予处于生命早期阶段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
四、我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的实践路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采取“集体主义与平均分配”的价值取向,经历“家庭主义与补缺救助”再到“适度普惠”的转变,城乡二元是重要特点。完全照搬国外经验不符合实际情况,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福利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应在国际投资导向和普惠福利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儿童早期福利体系,选择性地借鉴国外共性经验探讨本土特色方案。
(一)我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的实践转向
2010 年后,我国社会政策开始关注儿童早期发展,为儿童早期福利政策框架的完善提供支撑。国务院将0—3 岁儿童早期教育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提出“促进0—3 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作为重要民生保障项目。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2020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分别提出建设普惠性托育与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要求。《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全生命周期健康理念,针对孕期、儿童等阶段特点实施科学孕养,加强早期服务。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由此可见,我国越来越重视儿童早期的照护、教育、养育、健康和综合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是综合性和整合性的过程,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应予以相应的干预和支持,但是,当前我国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以回应单一福利需要的宏观指导为主,缺少统一且相应的实施方案和整合行动,福利供给网络仍不完善。随着我国现代福利思想、社会结构和家庭养育功能的转变,传统儿童早期福利供给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亟待完成儿童早期福利政策的框架化设计和体系化建设。因此,在推动“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背景下,对处于能力发展关键期的儿童提供支持和保障,特别是惠及全体儿童的福利服务,有利于增强儿童福祉、家庭幸福以及国家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将普惠型儿童早期福利以国家的整体性议题设计,整合现有的儿童早期健康管理与保健服务,建立面向儿童全生命周期的成长支持、发展保障的服务网络。包括大力发展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完善学前教育服务特别是教育与托育的联动服务,增加儿童早期综合干预和伤害预防服务,强化对处于困境状态的儿童及其家庭整合支持的特殊性服务等。
(二)建立中国特色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体系的思路
一是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将全体儿童作为政策对象,在国外“普惠”经验基础上强调“充分”福利,实现本土政策“普惠”与“充分”的双重考量。普惠,即逐步取消儿童早期福利对象资格限制,以达到服务对象的全覆盖和服务供给责任的共担。充分,即以需要为导向提供充足服务,确保服务内容的多样以及相对公平的实现,确保服务数量、服务种类的充足性和服务供给类型和层次的差异性,以达到儿童早期享受到的结果相对公平。如为普通儿童和大病儿童或残疾儿童提供相等数量和质量的早期健康干预服务,看起来是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但实际上他们的需要程度不同,应提供额外的针对性服务给大病儿童或残疾儿童。充分的福利服务要有所侧重,保证无论是普通儿童还是大病儿童的健康医疗需要都得到满足。
二是儿童早期福利政策设计应与其他儿童福利相衔接,与社会福利、劳动福利相结合,建立支持儿童与支持家庭的双核福利制度。基于国际“家庭主义”与“去家庭化”的争议探索本国道路,建立普惠性与选择性结合的多层次福利服务与现金支持体系。以整体视角分析儿童早期阶段,整合性回应儿童早期需要,打破区域和层次限制,建立全国性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将儿童早期的照顾、营养与健康、教育与能力发展、特殊干预与救助等进行整合设计。
三是在当前法治建设的背景下,积极推动儿童福利立法,保障儿童早期福利内容及其高质量递送。借鉴国外儿童福利早期政策立法经验,优先通过政策设计推进儿童早期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和打通已有的教育福利、医疗福利与困境儿童福利的供给网络,搭建地方、区域和国家不同层次的福利输送网络,建立精细化、标准化与可持续性的服务管理机制,确保福利递送的可及性与高质量。
四是逐步探索国家统筹下的政府、社会、市场与家庭的责任共担机制,确保资金与资源的可持续获得。儿童早期福利并非是单纯的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选择问题,其共同的前提是如何确保处于早期阶段的儿童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发展。明确儿童早期重要性的共识是福利责任分工的前提。单纯依靠政府、社会或市场难以满足庞大的儿童早期福利服务供给的需要,应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厘清福利责任边界(廉婷婷、乔东平, 2021),形成责任共担、分级明确的分工方式,实现家庭守位、政府归位、社会到位、市场补位的福利保障。
五、结语
建立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体系具有可持续性意义,有助于个体、家庭与国家形成互助关系。儿童早期福利政策行动是回应儿童发展及家庭养育需要的国家福利手段,尽管因国家制度、时代背景、福利思想等因素导致各国福利模式有所差异,但“投资儿童”“家庭支持取向”“政策整合”“体系联动”“高质量服务”“责任共担”已成为儿童早期福利制度体系设计的共识,也是各国促进生育、提升人口质量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开始将福利重心转向“一老一小”,关注儿童早期的照顾与支持。将儿童早期福利纳入国家议题,建立中国特色儿童早期福利政策体系,可以整合性地回应儿童早期福利需要与权利保障。国家通过政府、社会、市场等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福利保障;家庭也应积极改善自身的育儿能力和资本状态,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