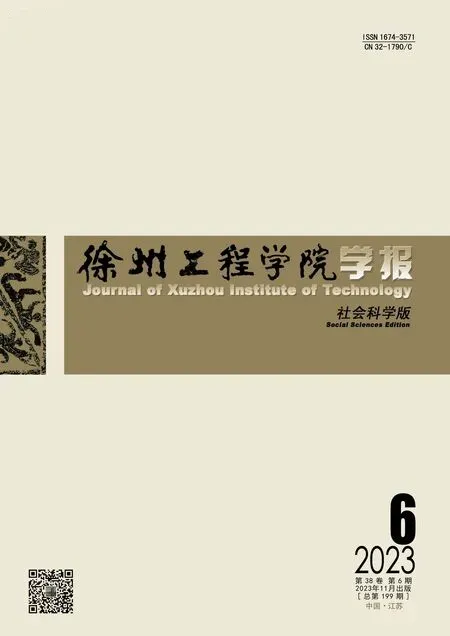互文性视域下《上海孤儿》中的身份建构与女性意识
王桃花,黄锦豪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当代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2018)被称为“英国移民三杰”。《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表现出石黑一雄善于运用“碎片化记忆”这一手法编织故事的娴熟技艺。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该作品中存在大量关于身份的思考,并主要从主人公的片段式回忆(方宸,2012)、双重家园与双重移民(王飞,2020)、空间(何锦秀,2020)等角度展开研究,但至今尚未见有学者探究互文性对小说中主人公身份建构的影响与隐喻。互文性是《上海孤儿》的一个突出特征,“互文性”概念指的是“任何文本都犹如一副马赛克镶嵌画,一切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由于互文势必涉及到其他文本,因此,互文内容的理解过程依赖于读者的能动参与。对文本进行互文性分析能够挖掘隐藏文本之外的意义,“可以为语篇的生成和理解提供一个意义关系视角,并进一步揭示文本怎样在特定情形下有选择地使用话语秩序、建构社会身份”[2]。石黑一雄在创作小说时,刻意互文英国文学里的经典人物形象,并且直接让相关作家与作品名出现在故事中,足以表现他是在有意采用互文手法,通过读者的参与,来完成小说角色的身份建构,身份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身份焦虑走向身份认同的过程。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虑》一书“界定”章节中指出:“身份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3]身份认同则是与身份焦虑相对的心理状态,即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获得尊严与尊重。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孤儿》的互文性特征探究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构建过程,分析作者如何通过互文手法展现和隐喻主人公不同人生阶段面对的身份焦虑和取得的身份认同,以及作者在互文选择时所体现的女性意识。
一、与《远大前程》的互文性戏仿:班克斯的身份建构
“戏仿(Parody)作为一个后现代小说叙事技巧,通常被称为反讽式引用、拼贴或借用,不是局部地再现源文本,而是对源文本的戏仿、异化和戏谑。”[4]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毫不隐晦地直接将影响其创作的作家作品通过角色之口说出来。班克斯(Banks)与长谷川上校(Colonel Hasagawa)在交谈时,上校直截了当地说起自己对英国文学的喜爱:“还有你们的文学——狄更斯的小说、萨克雷的小说,还有《呼啸山庄》。我特别喜欢狄更斯的小说。”[5]251-252石黑一雄是在提醒读者:这些文学作品为班克斯英国身份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基础,里面的人物与情节也隐喻了他对自己身份的疑惑与追寻。《上海孤儿》对《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互文性戏仿体现在小说的多方面。
(一)对人物命名和人物形象的戏仿
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乐于设置影子人物,“在每个人生阶段,石黑一雄都为班克斯设置了一个‘影子人物’,分别是儿时伙伴山下哲、英国寄宿学校校友安东尼·摩根以及养女詹妮弗”[6]132。即将多个角色相似的人生经历集中体现在一个角色之中。《上海孤儿》中的人物命名与人物形象都体现了作者的戏仿意图。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菲利普叔叔(Uncle Philip)的名字显然是对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作品《远大前程》里的主人公菲利普·皮利普(Philip Pirrip)名字的戏仿。《远大前程》中,皮普(菲利普·皮利普在小说中多以Pip作为名字出现,以下都采用皮普代替菲利普·皮利普)是作为受资助者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而石黑一雄笔下的菲利普叔叔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资助者的身份出现的,因为菲利普叔叔从小对班克斯照顾有加,班克斯也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父亲,最后也是他出谋献策才让班克斯至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作为代价,他却得眼看心爱的女人成为他人的妾。拥有相同名字的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下,一个成为受资助者,另一个则成为资助者。而班克斯在小说中则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他一方面获得来自军阀顾汪(Wang Ku)的资助,另一方面又作为资助者收养一名孤儿。作者通过戏仿这一手法成功构建了班克斯截然相反的双重身份,体现了战时孤儿对于身份选择的混乱,隐喻了班克斯成长过程的身份焦虑,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直到小说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菲利普以完全相反的身份被作者通过戏仿的手法安排在故事中。
此外,《远大前程》中的马格威奇(Magwitch)和哈维沙姆小姐(Miss Havisham)有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把培养另一个人当作自己余生的目标,但他们的目的却不一样。前者把皮普培养成上等人是一种变相的补偿,因为他希望皮普帮他完成一个逃犯不可能完成的人生目标。后者则是为了报复情人对自己的遗弃,因为她痛恨这世界上一切男人。这两个人不同的一面也集中体现在菲利普叔叔身上。一方面,当年他为了让班克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才联系了顾汪实施了后面的资助计划。另一方面,此举也是为了报复班克斯的母亲戴安娜(Diana),因为她是他永远无法得到的女人,他坦白道:“这许多年来,我通过顾汪间接获取快感,就好比是自己也征服了她一样。我无数次地从想象中获得快感。”[5]270石黑一雄再一次通过戏仿手法将两个经典角色的特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仅丰富了菲利普叔叔的形象,还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正是彼时动荡世界里人们身份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二)对人生经历的戏仿
皮普和班克斯人生转折的开始标志都是一笔慷慨的资助。皮普是一位孤儿,在受到资助前过着极其穷苦的生活,后来他到沙提斯豪宅成为艾斯黛拉(Estella)的玩伴,并且疯狂地爱上了她,此时的他内心就有着一种成为上层阶级的渴望。后得到陌生人资助在伦敦混入上层社会,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黑一雄笔下的班克斯童年在上海租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母离奇失踪之后,他来到英国,受到了慷慨的姑姑的资助,这也是他过上完全不同人生的开始。
他们经历人生转折后都有类似的不和谐感。皮普来到伦敦后,成功混入了上层社会,但这也导致他抛弃了一些原有的美好品格,变得极其势利。当他的姐夫乔(Joe)去伦敦找他时,他感到一种不和谐,甚至愿意花钱来远离姐夫。“皮普与哈维沙姆小姐的会面以及来自陌生人的经济援助使他获得了阶级提升,让他产生了一种与过去人生脱节的感觉。”[7]当班克斯的父母失踪后,父母成了他心中的一道坎,甚至得面对来自身边人异样的眼光。“那些喜欢幸灾乐祸、动不动就拿别人的倒霉事来善意取笑的同学们居然在初次提到我没有父母时都表现得郑重其事,令我多少有点气恼。”[5]6班克斯第一次参加充满“上层”来宾的晚宴的时候,很想与他们也打上交道,甚至“想象他们中的某一个会对我产生慈父般的兴趣”[5]11。班克斯和莎拉(Sarah)及其他人一起共进晚餐时,桌上的其他人正在谈论有关母亲的话题。莎拉在饭局中途跑到卫生间,在班克斯面前吐露自己从小作为孤儿的伤心,班克斯也回应道:“我想我俩谁都没法在一个关于好管闲事的妈妈的专题讨论会上发表什么见解。”[5]61由此可见班克斯在经历人生转折后也有一种不和谐之感,彷佛与过去的人生脱节。
他们排解身份焦虑的方式都是以某种错误的执念作为出口。具体来说,皮普将努力成为上等人作为追寻身份认同的方式,而班克斯则选择努力成为名侦探。皮普的身份焦虑来自对艾斯黛拉的爱,他误认为只有自己变成绅士才能获得艾斯黛拉的爱,成为绅士的过程也是他试图消除身份焦虑的过程。“小说中,直接造成班克斯身份焦虑的便是在儿时父母双双失踪这一事件。同时,为了抵抗焦虑而追寻父母的过程也成了他苦苦建构身份认同的隐喻。”[6]205父亲失踪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山下哲(Alira Yamashita)邀请班克斯玩“关于克里斯托夫爸爸的游戏”[5]98,即扮演侦探来寻找父亲的下落。母亲是这样安慰他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案件由全城最棒的侦探来开展调查。我同他们见过面,他们对结果抱乐观态度,表示一定能够尽快破案。”[5]99在商讨将班克斯送回英国时,班克斯觉得自己此时不应该离开,因为他认为“侦探们正在全力寻找我父母的下落。他们是全上海最棒的侦探。相信他们定会很快就找到我父母”[5]24。由此可见,在班克斯心目中,找到父母下落的唯一方式就是诉诸于名侦探的努力,这个观念不仅是他心中所有的,还是身边的人一次又一次潜移默化灌输给他的。因此,他来到英国后不顾来自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也决意要成为一名侦探。姑姑对于班克斯的侦探游戏这样评论道:“这种年龄的男孩,老这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身心健康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得学会朝前看。”[5]10他的同学嘲笑道:“可要当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他的个头绝对太矮了。”[5]9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伦敦以侦探的身份获得了很大的名气。最终,他也固执地认为父母被关押在上海的某一处民宅之内,不顾一切代价也要以“侦探破案”的形式来解救父母,这个“破案”过程也就是他试图消解身份焦虑的过程。石黑一雄通过戏仿英国文学里赫赫有名的孤儿形象,迅速丰满了班克斯的形象,展现出不同时代下孤儿的相似身份焦虑,以及在构建身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阻碍。
(三)对故事情节的戏仿
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石黑一雄通过戏仿《远大前程》完成了班克斯身份建构,即从身份焦虑到认同的过程。皮普第一次返乡是源于哈维沙姆小姐的邀请,因为艾斯黛拉从国外学成而归。这次返乡对他来说是衣锦还乡,因为此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在伦敦混在上层阶级之中——与小说题目相呼应。班克斯第一次回到上海是因为他通过数年的资料搜集,已经对找出双亲的下落有了一定的信心。这次回到上海他不再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海鹦”了,而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侦探。这也是为何当班克斯与菲利普叔叔相逢时,当菲利普叔叔亲切地叫他“小海鹦”时,班克斯会回应道:“希望你不要用那个名字叫我。”[5]259此时他们两个都收获了一定程度上的身份认同,一个被乡里人敬仰为上等人,另一个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名侦探,但这个认同很快就要被打破。
不久后,皮普的恩主现身了,他发现原来一直默默资助自己的人是流放犯亚伯·马格威奇,而不是哈维沙姆小姐,他在这时终于猛然醒悟到原来哈维沙姆小姐并没有想要撮合自己与艾斯黛拉,这一切只是自己的一场春梦,他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冒着生命危险,费了好大功夫才来到他误以为关押他父母的房子,不料这些侦探行为跟他小时候跟玩伴山下哲玩的侦探游戏一样幼稚可笑,父母被关押在那栋房子里只不过是他幻想出来的一场梦。最后在菲利普叔叔的坦白下,他得知自己优渥的生活并非来源于慷慨的姑妈,而是来自母亲的委曲求全,母亲戴安娜答应留在顾汪身边做他的妾,作为条件,顾汪要对班克斯提供经济援助。此时他们又从身份认同转向身份焦虑,又开始了新的身份构建过程。
接着,皮普接受了这个事实,并马上振作了起来,改变了自己对待马格威奇的态度,把他当作自己的恩人,并决意帮助他逃离。班克斯重回上海后,自持侦探身份而自命不凡,在前往他误以为关押父母的民宅途中,狂妄自大,固执己见,认为所有人对他的帮助都理所应当。他身上不好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轻车夫开车带他去陈业家(Yeh Chen)的时候,由于离炮火太近,可能会有危险,年轻车夫提议回去时,班克斯却破口大骂:“你不懂却要装懂,狂妄自大,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蠢蛋。彻头彻尾的蠢蛋!”[5]207这与他平时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完全不同。当他来到警局后,不顾中日两方正在交火的战况,把自己寻找亲生父母下落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并大言不惭地说: “为什么在你如此繁忙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完全有理由提出自己的要求。”[5]212这与他此次上海之行另外一个初衷背道而驰——铲除战争的恶行,解决“中国危机”。在他心中的价值排序里,他把寻找自己亲生父母下落的任务置于两个民族的战争之上,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留情偏向他的“小家”而舍弃饱受战争苦难的其他民族,体现了他身上个人主义的特质,同时也体现父母在他心中的重要性。那为何最终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不一怒之下扣下扳机将菲利普叔叔杀死呢?本文认为他受到了《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影响,身为一个在英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高材生,且与长谷川上校直接聊过狄更斯的作品,他必定读过《远大前程》这部经典之作。因此,他在成长的过程以及追寻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对自己身份的思考等都可以从这部小说中找到共鸣。他发现自己与皮普人生轨迹的高度相似,或许正因为此,在真相大白之时,他没有被情感冲昏头脑,而是选择原谅菲利普叔叔。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有一种元小说的特征。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的小说”[8]。作者将自己创作时采用互文的小说展现在读者和角色面前,不仅帮助读者理解小说,还影响小说里角色的行为。
“整本小说讲的就是班克斯如何通过追寻父母,消除身份焦虑,最终建构身份认同的故事。”[6]206石黑一雄分别通过对人物命名和人物形象、人生经历、故事情节的戏仿,完成了主人公班克斯的身份构建,同时班克斯最终的幡然醒悟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他对《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理解,他最终的身份认同也是在反复试错中获得的。
二、与《名利场》的互文性戏仿:莎拉的女性意识
《上海孤儿》在多个方面戏仿了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的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小说里主要描写了两位女性角色,分别是阴险狡诈、充满算计的蓓姬(Becky)和美丽乖巧、渴望爱情的爱米莉亚(Amelia)。石黑一雄有意采用的互文手法主要起三个作用。
(一)补充莎拉的前半生经历,丰满人物形象
莎拉是《上海孤儿》中的女主人公,她自幼丧失双亲,是一个机敏、美丽的女人。蓓姬的“一生可谓是追求‘进步’的一生。 用她丈夫罗登的话说,她把毕生精力都用来追求一个目标,即‘出人头地’(advancement in the world)”[9]82。她的人生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她想靠婚姻改变阶级,后半部分是她通往上流社会之路。然而,她“能用来实现远大抱负的资源实在少得可怜:她从小父母双亡,身无分文,所能依靠的只有几分姿色和骗人的伎俩,当然还有她那铁石心肠”[9]82。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的笔墨集中在莎拉如何在上流社会摸爬滚打,淡化了她前半生的描写。莎拉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在一个晚宴上,直到小说结束,关于她的身世,读者能够知道的只是她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孤儿,但文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她是如何成长的,她是否被一个有钱家庭领养?她是否受过良好教育?她以什么职业为生?她是怎么在充满尔虞我诈的上层社会混得风生水起的?为何随着小说的发展,她的形象会突然正面了起来——她并非贪图钱财的人,她接触有钱有权阶级是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成为一个有识之士的贤内助,帮助他一起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关于她前半生描写的缺失让读者很难理解她是如何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以及为何她会有这种远大的志向。而石黑一雄之所以没有在小说中提及这一部分,则是因为他在文中暗示他笔下的这个女性角色其实是戏仿了萨克雷笔下的蓓姬,读者可以借蓓姬的成长经历来了解莎拉,弥补小说中缺失的前半生描写,进一步了解她身份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互文特征,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莎拉的人生全貌,以及了解她的身份是如何一步步被构建,了解石黑一雄是怎么在蓓姬原有形象的基础上作出创新。
(二)颠覆原有形象,形成张力
《名利场》主要描写了19世纪前期英国上流社会的全景,讽刺一批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外,对其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物,因此小说的副标题为: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莎拉最开始也不是以“正面”形象在小说中出现的。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晚会上,当时她正与两个中年男子交谈,班克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当时她明显是想取悦与之交谈的男人,我还是看出她在微笑中有某种可以将微笑即刻化为讥讽的东西。”[5]13当班克斯被莎拉吸引了注意力后,银发老者提醒班克斯说:“像你这样的毛头小伙没必要浪费时间追她。”[5]14“她带着一种目中无人的优雅神情穿梭在人群当中,目光左顾右盼寻找着——我是这么觉得——大概是要寻找一位她认为值得为之驻足的谈话对象。”[5]15结合两者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在莎拉的眼中,只有那些权高位重的人才值得她社交。为了与这些人拉近关系,她不惜伪装,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性格来达到她的目的。而像班克斯这样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和权势的“普通人”自然没有机会靠近她,莎拉也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在无名小辈上。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里充满了尔虞我诈,而莎拉能在伦敦上流社会里混得风生水起,且能做到游转在不同男人之间,足以证明她是颇有心机、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在班克斯没有成名之前,莎拉对他的态度可谓是不屑一顾。当班克斯在侦探界小有名气后,且受邀参加梅瑞迪斯基金会举办的宴会时,为了能参加这个晚宴,莎拉立刻“贴”了上来,对班克斯亲切有加,完全不会因为自己“见风使舵”而感到羞愧。这一切都能看出,莎拉给班克斯和读者的第一印象都是“蓓姬”式机敏、不择手段、放荡不羁的女人。
然而,随着小说的进行,石黑一雄却试图将莎拉塑造成一位“英雄式”的人物。读者发现,莎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贪慕虚荣、只顾享乐、追求浮世荣华的女人,她有更为崇高的目标:“我若要嫁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我指的是能为人类、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的人。”[5]45婚后的莎拉变得不那么像蓓姬,而是成为了“爱米莉亚式”的贤妻良母。“《圣经》说,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那么,女人就命中注定要成为男人的附庸。在父权文化中,温柔贤淑和无私奉献是女性最大的美德,爱米莉亚完美地诠释了肋骨的含义。”[10]168当她认准塞西尔·梅哈斯特爵士(Sir Cecil Medhurst)是那个值得她辅助一同成就大事的人时,她不顾世俗的舆论,坚持要与他结婚,一同前往上海实现丈夫的抱负。从前只要她的亲密对象稍出差错,她就会立刻毫不留情地离开。她可以像扔掉烫手的土豆一样甩掉在音乐会上一败涂地的剧院指挥未婚夫,直接将订婚戒指扔还给他。她曾与一名律师交往,但当他在案子败诉后,莎拉毫不留情地离他而去,转身投向了正在走红的年轻政府部长。但婚后的莎拉一改之前的形象,即便来到上海后发现自己的丈夫再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能力了,她选择忍辱负重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在遭到丈夫言语羞辱的时候,还是尽力在班克斯面前维持其体面的形象。塞西尔爵士在莎拉离去后跟班克斯说:“我一直对她说她应该走,告诉她应该去寻找爱情,我是指真正的爱情。这是她应该得到的,你不觉得吗?她这次离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寻找真爱。”[5]255-256莎拉此次离去的行为结合了蓓姬和爱米莉亚两者的特质,大胆无畏的蓓姬眼里从来没有爱情,只有钱财和名利;爱米莉亚眼里只看重爱情,但她太过懦弱绝不敢私自离去。石黑一雄在一个角色里揉合了经典名著里被众人所知的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角色,给予这个看似负面的角色一些正面的特质,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张力,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以及莎拉在追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艰辛。
(三)相似的悲剧命运体现石黑一雄的女性意识
“《名利场》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以男性为主导的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当时,女性是为了巩固男性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并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妇女的美德完全体现在对男人的服从程度上。”[10]166蓓姬的结局不算太惨,她获得了约瑟(Joseph)的遗产,保证她余生的潇洒日子。即便她坏事做尽,作者还是给了她一个体面的结局,因为蓓姬已经跳出了传统女性的发展模式——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每次都将命运紧紧抓在自己手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谋略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遗憾的是,她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都不是依靠自己打拼而来。她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依托男人对她的怜爱,这也就是她悲剧的根源。莎拉也同样有抗争命运的勇气与意识。当莎拉为了进入晚宴而使尽手段时,她为自己辩解道:“可我为什么不该这么做,克里斯托夫,为什么不该希望同这些人在一起?难道仅仅因为……命?”[5]44她曾跟班克斯说:“我不想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回首往事,却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我希望看到能引以为豪的东西。知道吗,克里斯托夫,我是个有抱负的人。”[5]44“但我决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把生命浪费在某个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但在人格上一钱不值的男人身上。”[5]45相似的是,莎拉从头至尾也都将自己当作男人的附属品,无论是攀附上流社会的人士,还是嫁给塞西尔·梅哈斯特爵士,她都没有跳出附属品这一角色。在她的世界里,想要成功做成一件事情首先是找一个可靠的男人,让其成为主心骨,然后自己再成为辅助角色,一同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当莎拉决定嫁给塞西尔·梅哈斯特爵士时,她不是出于爱情或激情,而是认为“即使是像他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名声再高,成就再大,身边还是需要有个人,需要有个人协助他”[5]131。当她发现塞西尔·梅哈斯特爵士已经没有能力在上海取得成就时,她选择了离开,但还是希望有一个男人能够依靠,于是邀约班克斯一起私奔。但班克斯还是忙于寻求父母下落而没有守约,让她再度失望。莎拉生活的年代比起蓓姬生活的年代,女性意识已有更充分的发展,虽然她也有抗争命运的精神,但莎拉还是遵循依附于男人的那一套模式,因此石黑一雄并没有给她一个完满的结局:她去东亚后在战争时期曾经被拘留,后来因为健康问题早早去世了。这体现了石黑一雄对新时代女性的期望,认为女性单单指望依附于男人是无法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莎拉最终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她在给班克斯写的信里提到“你一直有很强的使命感,在使命完成之前,我敢说你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全心投入”[5]285。这其实也变相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她在信中祝愿班克斯:“希望你已经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从此也可以去寻找已经快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幸福生活与人生伴侣。”[5]285但班克斯对此表示怀疑,觉得她并没有过上那种幸福生活。但莎拉的“亲密朋友”这么评价莎拉在东亚的生活:“莎拉和蒙·德·维利弗太听天由命。这对夫妻属于那种晚上出门从来没有事先计划,随便碰上谁都开心的类型。”[5]284由此可见,莎拉在人生后半段已然放弃了原有的理想,在身份焦虑之中过完了余下的一生。
三、结语
小说题目《上海孤儿》的英文原文When We Were Orphans可以直译为“当我们曾经是孤儿的时候”,笔者认为,作者在此采用过去时的原因是:整篇小说都是成年后的班克斯回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成年的他其实已经失去了孤儿这层身份,orphan一词在朗文在线词典给的英文释义为:“a child whose parents are both dead(父母双亡的孩子)”,成年的他已不再是孩子,所以也不再是孤儿。译者陈小慰在译后记写道:“重新把握过去的每一步努力都不断在印证着书中提到的女诗人那意味深长的诗句:‘一旦长大成人,童年便好比异国土地,离我们无比遥远。’”[5]288从他失去孩子这个身份时,他就成了自己的父母。当一个人成为了自己的父母,不仅是他完全成长的标志,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身份建构的标志。但对于孤儿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漫长,正如班克斯在文中说道:“我感到她在谈到使命感,谈到怎么也躲不开它时,一定也想到了她自己。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此类忧虑纷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对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就注定要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地追寻逝去双亲的影子。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否则将不得安宁。”[5]285-286对于孤儿来说,追寻双亲影子的过程也就是建构自己身份的过程,在身份得以建构之前,没有获得身份认同之前,被迫生活在身份焦虑之中,是无法获得安宁的。“对石黑一雄来说,《上海孤儿》中的孤儿只不过是一种隐喻,表达的是以未受保护的方式摆脱童年幻想。”[11]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孤儿》中的互文性特征,指出作者安排一些经典文学作家作品出现在小说中,通过与这些作品的角色形象、人生经历、故事情节等的互文指涉,表现出这些作品对石黑一雄创作小说时的影响,以及对故事中主人公的影响。石黑一雄在互文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创新,让文中男女主人公两位孤儿的命运交错在一起,让小说充满了丰富的层次感。总之,《上海孤儿》表达了孤儿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身份认同的坎坷,以及作家本人对身份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