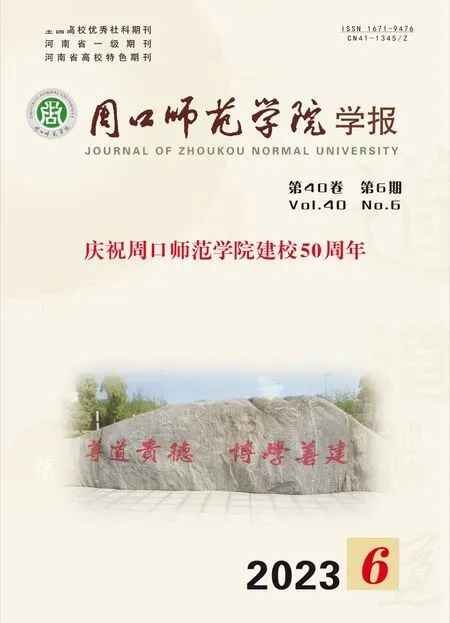显失公平法律行为源流考
夏 平
(广州商学院 法学院/外国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136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在《民法典》中被合二为一。之所以如此规定,笔者妄自揣测无外乎以下三点理由。一是,由单一客观要件构成的显失公平条款不足以否定合同效力,且与法律行为效力规制体系相冲突;二是,单一客观构成要件容易造成显失公平条款的司法滥用;三是,《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是将《德国民法典》中暴利行为一分为二[1-2],给人一种立法割裂之感。 但以上三点理由是否成立不无疑问。
首先,法律行为效力规制体系继受的是《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制度,该制度以意思自治为基石。自由协商的合同具有其合理性,无正当理由不得否定其效力。申言之,单纯的给付失衡原则在德国民法中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正当事由。但是,从比较法上来看,这并非一成不变的真理。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934条就直接继受罗马法中的非常损害规则,并将给付均衡理念作为否定合同效力正当事由。而且,奥地利著名民法学者德林斯基从非常损害规则中引申出一条等价原则,认为违反该原则可否定合同效力[3]。值得深究的是,《奥地利民法典》除继受了罗马法的非常损害制度,还在第879条违反公序良俗条款中增设了德国民法中的暴利行为制度。此种立法例在《捷克共和国民法典》亦可见,如《捷克共和国民法典》第1793条规定了非常损失规则,第1796条规定了暴利规则。也就是说,《民法通则》的立法例模式在比较法上并非孤例。其次,从《奥地利民法典》立法模式来看,我们亦有理由怀疑暴利行为理论与非常损害理论基础及立法功能似乎并不完全相同,不然,奥地利也不可能在其民法典中同时规定两种制度。罗马法时期的非常损害规则仅将显失公平作为其客观构成要件,其适用范围有限,不能作为调整合同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般规则,否则对法律体系将造成冲击。因为民法理论建立在形式公平之上,但形式公平并不一定得出实质公平。基于实质公平的现实需要,立法者往往会在形式公平之外做出一些例外规则[4]。 如法国民法典中的合同损害规则,就无主观构成要件,但其仅适用特定类型的合同,且此类合同的公平由立法者明确固定的权重比例。最后,将《民法通则》中的乘人之危视为暴利行为条款,显失公平视为准暴利行为条款的观点过于简单粗暴。因为,《民法通则》第59条关于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制后果与德国民法中的准暴利行为并不相同。所谓准暴利行为,指合同内容约定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极其显著失衡,即便合同当事人的主观心理不符合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但德国司法实务仍通过恶意推定规则认为合同交易中的受益人的行为不道德,进而按违反《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善良风俗一般条款而否认其效力[5]。相比而言,我国《民法通则》则是采可撤销与可变更的法律规制路径。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的立法例模式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更为相同。立法者不仅通过规定乘人之危规则继受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利行为,还通过显失公平规则继受了罗马法时期的非常损害规则。在这一前提下,笔者不由心生疑问: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力行为与罗马法中的非常损害规则是否存在理论基础差异?其构成要件与法律规制又为何如此迥异?面对上述疑问,笔者认为有必要考察,罗马法以降,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非常损害规则构成要件及法律规制的流变过程,以解心中之惑。
二、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历史变迁
(一)从短少逾半到恶意推定
非常损害规则的法律构成要件是短少逾半规则,即在买卖土地合同中,当买卖价格低于实际土地的价值的一半,合同可被出卖人废弃之规则。罗马时期,短少逾半不是因为受益人的恶意行为产生的,而是因为事实本身,并作为特别案件被规定在罗马私法中的[6]N248。赛克斯认为,不管是在戴克里先时代,还是优士丁尼时代,C.4.44.2(a.285)和C.4.44.8(a.293)文件中述及显失公平规则时并未带有恶意。而且,根据文件C.4.44.8(a.293)之规定,非常损害制度是严格与欺诈恶意、诡诈、弄虚作假和胁迫相区分的[7]41。
客观给付失衡中存有废弃合同的事由,这一事由被注释法学派称为恶意推定。恶意推定一次最早出现在伊纳留斯(Irnerius)的文章中,之后被瓦卡留斯,阿佐, 霍格修斯, 阿库休斯和斯蒂恩西斯 继承[8]。按照注释法学派的观点,所谓的“主观”恶意是“合法给付失衡幅度”质的界限点(这里质的定性,指给付失衡中含有所谓的主观恶意时方可适用显失公平制度,有点类似德国的暴利行为)。与此相比,非常损害则是“合法给付失衡幅度”量的界限点(有点类似德国的准暴利行为)。注释法学派文献中的恶意推定理论,是指从客观给付失衡中推定行为人主观具有可指责性。此推定被认为是学界的一种尝试,其试图统一“合法给付失衡”的2个界限点,即恶意和短少逾半。另外,注释法学派认识到,客观给付失衡中的“恶”并无真正的主观恶意,但它却显现出与恶意相似的后果[9]。依照乌尔比安的观点,即使不存在欺诈恶意,受害人也可以被赋予对受益人的恶意之抗辩。因为该交易自身带有恶意。具体而言:当某人因意思达成一致而负有某项义务之时,该义务也可能是因欺诈负有,依据严格法其受有(自己诺言的)约束,但他可以使用恶意抗辩,因为他是恶意的被负有义务,所以,他享有抗辩。同样,当协议中不存在恶意,但是标的自身包含有欺诈,那么受益之人以此约定索要给付的行为就具有恶意[6]。在法律文件C. 4. 44. 2(a. 285)和Ulp. D. 45.1.36(48 ad Sab)的共同作用下,学术界确立了“合同因短少逾半规则而被废弃”的学说理念[10]102。该学说也是现代法上的单一客观要件可以撤销合同的渊源。
因罗马法中的原始资料经普通法时代代表人物的加工,以后的学术界便将注意力转向恶意推定(dolus re ipsa)这一理念。尽管后来也有法学家一再怀疑dolus re ipsa的正确性,但该要件一直到新自然法学派都没有改变。因为当某人遭受损害已达逾半或者未成年订立了不均衡合同时,虽然合同内容可以被评价为不当或不妥当,但自然法学派对此合同效力只能接受。因为就该给付失衡之法律规制在自然法学门派下只能通过恶意欺诈和损害逾半规则两种路径。而恶意推定理论刚好回应了有些学者对非常损害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非常损害法律规制的解决方案直到自然法时代都未改变,他的内容经过注释法学派和后注释法学派被晚期学者确定。显失公平行为人有选择权,要么去补交不足的价款要么容忍被歧视一方废弃合同。
(二)恶意推定内涵:从公序良俗到诚实信用
在对罗马法律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与恶意相对应的善意(bona fides),在现代民法中也常被翻译为诚信,其中的fides意为“行其所言谓之信”[11]。《法国民法典》第1104条第2款将“合同应本着善意谈判、订立、和履行”认定为具有公共秩序性质[12]1300。申言之,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亦违背公共秩序。罗马法中受益方的道德评价涉及当事人的诚信。这一教义射程范围被古代晚期皇帝推行的基督立法强化了[6]N885。诚信的射程范围在罗马法中是合同拘束力的重要因素[13]151ff。宗教法对现代法的意义很大程度上都可归于诚信概念。就诚信而言,无关社会地位,每一个交易相对人均负有义务。梅尔茨巴赫认为,诚信意味着无论如何都要直接地、完全地履行合同[14]。简言之,诚信涉及的是契约严守原则。
与“契约严守原则”相对的是法谚“对毁信者不必守信”和“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不义或无耻行为主张任何权利”。前者在显失公平规则中可解释为:遭受暴利的一方可以不予履行合同,后者指的是获益人不得主张自己的合同权利。具体而言,“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不义行为主张任何权利”是教会法时期的法谚,后演变为法律的一条原则。之所以称其为原则,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15]。人们可以从该原则中引申出来很多规则,比如美国纽约法院在审理“格里斯诉帕尔默案”引申出一条继承规则,即“谋杀者不得根据其被害人的遗嘱继承其遗产”。有学者推断,显失公平规则亦是该法谚下的一种规则[15]。教会时期的法谚既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教会时期与诚信有关的法谚,后被欧洲大陆成文法中的善良风俗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所替代;放到英美法系,就演变为其普通法的普遍的基本原则。
受害人在无意思瑕疵的情况下得以背信不履行合同的正当化事由,是依据“对毁信者不必守信”的法谚。受益人有无毁信,只能从严重的给付失衡中加以推定,此种推定即为上文所言的恶意推定。德国通过善良风俗条款否定暴利行为的效力,使暴利之人通过合同设立的权利得不到主张。不过这一观点被瑞士法律所摒弃。瑞士民法并未将显失公平行为纳入公序良俗中加以规制,而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调整。瑞士学者中如Guach和Schluep认为,受益人从过分得利中获利,违反了应予顾及的先合同义务。谁违反了应予顾及的先合同义务,其行为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16]282。我国亦有学者认为,显失公平行为尚达不到违背公序良俗的严重程度,而是构成对作为较高道德标准的客观诚信的违反,主要表现为超过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必要范围损害他人的利益[17]。王利明也曾表达过合同正义原则、禁止暴利原则是在诚信原则基础上产生的观点[18]。
(三)恶意推定之内涵:从意思瑕疵到意志侵害
德国民法中的暴利行为结束了非常损害的教义适用,自此以“主观+客观”为双重要件的立法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我国《民法典》通过显失公平吸收乘人之危而形成二元模式,显然也是对德国范本的学习。但德国暴利行为中的主观要件是意思瑕疵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给付失衡,而我国的乘人之危曾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独立的意思瑕疵类型[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0条也曾明确将乘人之危解释为意思表示不真实。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其认为将乘人之危规定为影响意思表示之事由,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不管是大陆法系或是英美法系中,都难找到与之比较恰当对应的概念[20]。但从笔者考察的立法例来看,荷兰民法典就只吸收了德国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之一——滥用情势。早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乘人之危概念可与之对应。对此,当显失公平吸收乘人之危后,我国就有学者将显失公平法律行为放入意思瑕疵体系,认为其属于独立的意思瑕疵表示类型[1]。
非常损害规则在普通法时代,由注释法学派为其增设了恶意推定要件,该要件中的恶意与意思表示瑕疵中的恶意(dolus,欺诈)并不相同。所以,显失公平行为中的给付失衡与意思瑕疵导致的给付失衡在本源上并不相同。我国《民法典》将显失公平法律行为放到法律行为意志自由规制之下(即紧随欺诈行为与胁迫行为),与法律行为内容妥当性之上。该种体系安排,与瑞士民法体系相似。所以,在显失公平行为法律适用上,可参照瑞士法的解释学说。在瑞士民法中,显失公平并未上升为独立意思表示瑕疵类型,但从其体系位置来看,学者对其解释也多将显失公平行为理解为对当事人意志的侵害。与德国暴利的规范意旨相比,瑞士法中的过分得利的规范意旨是不再过分强调给付失衡背后行为人的恶意性,其关注的是给付失衡背后行为人未顾及对方,违背了来自诚实信用原则的先合同义务[21]N747。
三、显失公平法律规制手段的历史取舍
构成要件与法律规制手段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自然层面上的联系,而是法律规范层面上的联系。法律后果是法律对客观事实构成的法律评价,如何对显失公平的合同进行妥当规制,是立法者的判断问题。
(一)从罗马法上的“废弃”到现代民法中的“撤销”
戴克里先大帝对合同中出现非常损害的救济措施是宣告废弃合同,意在宣布合同废止,有无效性和撤销性之意,为与现代私法中的无效、撤销区别,本文将其译为废弃。如果买方不弥补剩余的价金,出卖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关于废弃一词的本质,虽历经几百年讨论,但学界依然无定论。究其原因,乃因该拉丁词是一个多义词,其效果在罗马法源中并不统一。废弃合同在非常损害中的法律效果涉及拉丁文。学者对该词的定性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废弃是使合同回复到先前的状态,即回复原状;另一种观点认为,其只是一个特别之诉需要执政官参与[6]N240-242。废弃合同的事由仅涉及客观层面,即给付义务之间的不均衡,就错误的意思形成主观方面很少被述及。因此,非常损害中的法律规制和因胁迫、欺诈、错误而合同回复原状不同[22]。回复原状是古典法对买卖合同的常规规制,可以查明确定的是,其被频繁适用于意思被妨害的合同[6]N246。 依据《查士丁尼法典》C. 4. 44. 2(a.285)推出的显失公平的法律效果之一也有回复原状之意。
罗马法中的废弃制度能否与现代法律规制中的撤销制度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对此,不同的立法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过当今主流观点认为,因laesion而废弃合同的法律规制手段Reszission应被现代立法中的撤销取代。少数观点仍然坚持在立法例中保留废弃,如意大利立法例。法国人也习惯将合同因合同损害而无效称之为撤销,而将其他情形称之为无效,如第1117条规定:因错误、胁迫或欺诈而缔结的契约并非依法当然无效,仅发生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撤销契约的诉权。
综上可知,撤销与废弃法律规制之间的界定是以损害(läsion)的属性为依据的。läsion的属性并未构成意思妨害,而是缺乏合同上对价,或者是不道德的剥削(但损害要因又不能上升到欺诈、胁迫之程度)。因此,废弃合同的构成要件要么是缺乏合同对价,要么是不道德的剥削[23]。 因多样性的客观要件事实(即多样性的剥削情事导致给付失衡之事实)之废弃与因意思瑕疵之废弃的法律规制并不相同。有鉴于此,《意大利民法典》并未将二者同时放在现代民法中可撤销的法律规制之下。虽然意大利的短少逾半规则通过增设主观要件改变了其事实构成,但从《意大利民法典》第1448条规范来看,并未脱离罗马法的传统[24]177。
(二)《德国民法典》中无效路径之反思
合同可撤销和合同无效两种法律规制路径均导致法律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罗马法对不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并不存在清晰的界定。它们的法律后果统称为无效或不生效力,与此有关的术语也有很多。那么,罗马法中的废弃合同中的法律效力可否按现代的无效规则处理?
在中世纪时,罗马法有关无效的素材被细分为无效性和可撤销性。普通法时期的学者开始研究一般法律行为无效理论,但当时并未取得有效结论[25]413。 无效性和可撤销的区别理论归功于萨维尼[26]536ff。依据萨维尼的学说,相比于可撤销的不完全无效,无效的后果是完全无效。通常情况下,无效性由违反法律引起,可撤销性由违反意志导致。只有出于重大的、与表意人意思形成过程中的瑕疵(意思瑕疵)有关的理由,法律才给予使一项意思表示具有溯及力地归于无效的权能[27]421。
从保护利益说角度来看,法律行为无效是因为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行为可撤销是因为其侵犯了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德国民法之所以将暴利行为定性为违反公序良俗的类型,以此打击暴利行为,是因为当时的暴利行为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此立法动机和罗马人制定非常损害规则并无而异,二者在当时稳定经济秩序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若立法者将显失公平作为调整合同主体一般私人利益失衡的规则,显然不应再将其纳入显失公平中以无效规则,而应将其放入可撤销当中加以规制。德国将暴利行为按无效法律规制处理,这一法律评价被其他国家认为过于严苛。
除此以外,无效自身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合同无效之后,依据不当得利返还将面临清算关系的不对等。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17条之规定,若因善良风俗无效,受益人对暴利者的给付无须返还。由此返还清算亦会进入对价失衡状态。德国司法界的做法是对显失公平的效力行为进行修正。首先暴利行为无效突破了抽象原则,无效的不仅是负担行为,还有处分行为[28]Rn230。易言之,物权行为不发生变动之效果。财产给付之人(暴利一方)主张返还财产的依据是物上返还请求权,而不是不当得利之债上的返还请求权。
其次,无效规制不利于合同的稳定。对此,虽有效力酌减规则使合同部分无效,最大化地维持合同效力。毋庸置疑的是效力减损符合当事人的推定意思,因此,在法教义学上是不可指摘的。但在一些法律案件中同样会遭遇一些问题。这些案件中的无效事由会追溯到法政策性保护性规范,即违反了合同出于保护社会弱势的一方当事人的规范(包括既有规定和尚未规定)。这里若适用合同减损,则会诱发更多的显失公平合同纠纷,司法部门显然不愿以此为导向给自身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进而拒绝否定合同效力。因此,大多数社会弱势群体无法通过司法路径阻止过分束缚自身权利的合同内容。只有在极少数的案例中,受益方才会面临合同被效力缩减的风险。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当大多数的合同受益方不会面临合法的规制时,那么优势一方就会以身犯险。因此,出于法律预防性之考量,效力缩减之路径应被拒绝[29]。易言之,法律的预防功能在此类效力缩减的案价将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弱势一方被授予选择权,即由其决定是否主张合同整体无效或部分无效。这里的选择权就是可撤销的法律规制路径。德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大多采可撤销的法律规制路径。
(三)罗马法变更路径之殇
罗马时期,非常损失规则的法律手段不限于废弃规则,还有赋予受益之人的变更合同手段[30]N7,具体内容参见公元285年的诏令C. 4. 44.2和公元293年的诏令C. 4. 44. 8。这两个法律规制手段不是二者择一的选择关系,而是若受益人不补足价金差额,受害人可以废弃合同[6]N857。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受益人剥削了相对人,但罗马法并不惩罚当事人,反而赋予其变更合同的特权。申言之,在非常损失合同中,变更手段优先于撤销。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针对显失公平行为均规定了可撤销与可变更两种手段。我国亦有学者认为,变更路径原则优先于撤销规制路径[31];司法变更合同条款时,原则上应模拟当事人真意,不宜直接套用相应的任意规则[32]。但是《民法典》仅保留了可撤销路径,删除了可变更路径。
显失公平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寻求三方利益的平衡,即遭受暴利的一方可以不予履行合同之利益、法秩序之安全利益、受益一方的合同维持之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合同撤销具有整体性特征,此点不能充分满足上述利益三角关系的期待。给付失衡问题虽通过撤销合同被消灭,但是在利益保护方面和合同秩序稳定上都留下了后遗症。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原有的显失公平情形下的法律行为可变更规制路径被删除后,应扩张部分撤销的适用范围,以构建有层次的救济体系[31]。这种通过部分撤销主义最大化地维持合同的效力观点,并未改变撤销法律规制手段的单方面性,部分撤销亦侵害受益人的意思自治。更妥当的手段是允许受益之人提起变更合同的主张,若受害之人同意则可以阻止合同被撤销。在受益人不愿意承担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愿意增加显失公平的给付,完全可以通过变更合同,恢复交易的公正性。只有当受歧视方不愿意变更时,合同才应被撤销。
从罗马时期受益人享有变更特权,到我国民法典删除变更手段,显失公平法律规制的目的也发生了嬗变。罗马法时期,显失公平法律规制的目的是恢复给付均衡。但由于显失公平主、客观要件的融合,这一法律规制的目的就被忽视了。因为,增设主观要件赋予了法官对受益之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即其行为是不是不可接受的。近现代显失公平规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矫正给付失衡,更多的是惩罚受益之人,所以,受益之人也就不再享有法律救济的手段。从这一点也可知,现代民法典中的显失公平制度是对普通法时期的恶意推定理念的继受与发展。
四、结语
罗马时期的显失公平规则在于修正不动产交易中的价格失衡问题,就价格失衡的原因而言,有主、客观等多种因素,很难上升为受益人之主观恶意,有鉴于此,罗马人更注重对合同的补救,而不在于否定合同效力。除此以外,当时的显失公平规则并无“主观恶意”要件的规定,这也导致其不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仅在有限的交易类型中适用。罗马法的立场深深影响了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奥地利等,这些国家的民法典均未规定显失公平主观要件,但均限制显失公平规则的适用范围。
普通法时期引入的“恶意推定”理念,扩大显失公平的适用范围,并在德国民法典中取得一席之地。但因为德国立法者将其放入违背公序良俗中以无效规则加以规制,其“主观恶意”的认定标准就较为严苛。从我国立法渊源来看,民法通则时代的显失公平规则深受罗马法中显失公平规则的影响,其未规定主观构成要件,并规定了合同变更制度。但在法律适用范围上,显失公平规则颇有滥用之嫌,远远宽与其他无主观构成要件的国家。反而在民法典时代,借助于其新增设的主观要件,显失公平规则本可以大显身手,却又出现司法慎用之局面,颇值深思。
《民法典》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二为一之后,学界对《民法典》第151条的解释,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将其视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利行为,进而借鉴暴利行为中的主观要件,即公序良俗的内涵对我国显失公平法律行为中的“主观恶意”加以解释;另一种是将显失公平法律行为视为独立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通过意志不自由的内涵对其“主观恶意”进行阐释。鉴于《民法典》第151条对显失公平法律行为的规制采可撤销规则,司法适用者对显失公平法律行为中的“主观恶意”的认定标准应相对缓和。通过上文考察,司法实务应摆脱既定思维模式,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内涵出发从新阐释显失公平之主观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