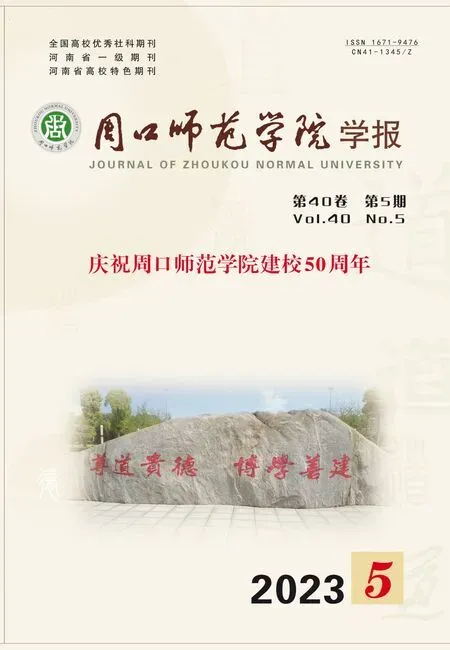风险论视角下的清代地方政府
张洪新,曹天睿
(1.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2.周口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在政治上达到了专制主义的顶峰,在经济上小农经济极度繁荣。以风险论视角,本文从统治者国家治理角度对清代地方政府中的特殊之处进行分析,旨在为理解清代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的运作提供一种观察视角,清代统治者所追求的代理人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之间的平衡,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状态。在清代地方政府运作中孕育了各种“畸形”现象,虽然维系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作,但却悖论性地催生了新的风险,最终反噬了清代政府本身。
1 理解清代地方政府:风险论视角的引入
如何清代地方政府的特殊之处,当前学人多有论述。例如,对于清代地方财政,在《州县官的银两》中,曾小萍提出了“非正式财政体系”,并从统治者加强中央对帝国所有资源的控制加以解释[1];又如,对于地方财政中的耗羡,陈锋认为,耗羡的征收反映出官员的贪婪和吏治的腐败[2];再如,对于清代地方政府的人事关系,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瞿同祖认为,幕友、长随之类的非正式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3]。可以说,学界在对清代地方政府分析,往往是单独就某一方面进行论述,而非联系起来。将财政问题归结于财政,将人事问题归结于人事制度安排,忽视了制度后面的设计与权衡,即从统治者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清代地方政府中特殊之处进行考察。
在笔者看来,理解清代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真实运作,可以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目前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主要有三种理论,分别是: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4],其认为统治者基于降低统治成本的需求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存在着稳定的模式即“行政发包制”;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5],则侧重于国家治理中存在的提高治理效率和维护政权稳定之间的矛盾,在应对这一矛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权威性制度安排[6];以及曹正汉等提出的“风险论”,其认为统治者不是基于统治成本或统治效率,而是基于统治者所面对的风险进行制度建构,从而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程度不同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曹正汉认为,统治者所面对的威胁,按来源划分为三种:民众叛乱的“社会风险”、统治者依靠军队和官僚系统所产生的“代理风险”以及外部军事“入侵风险”。在治理国家上,统治者追求统治风险的最小化,即力求同时控制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使其综合起来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最小化。
可以说,三种理论的相同之处在于,都立足于从整体上来阐释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风险论以中国古代为基础,作了较为整体的分析。因此,我们以曹正汉的风险论作为分析清代地方政府的理论视角,并结合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状况对清代地方政府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特殊之处进行论述。此外,在风险类型上,本文进一步提出统治者面临的不仅仅曹正汉所强调的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这两种风险,还有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建立在经济约束基础之上的另一种风险。
2 清代地方政府在风险应对中所孕育的三重“畸形”
在《说文解字》中,“畸”被解释为“残田也”[7],残田即是不规则的土地。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想要最大程度提高生产力,有连片的、规则的土地是必不可少的。可见,“畸”在古代社会有低效之意。对于清代地方政府,笔者以“畸形”来形容,就是指其特殊之处。清代地方政府的“畸形”,其根源来自于清朝统治者面对统治风险时所制定的各种正式制度。然而,自上而下所强力制定的正式制度使得州县官等地方代理人为维系地方政府的正常运作,不得不采取其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分解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从中央层面看,清朝统治者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代理人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但是,这三种风险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制度设计时就不仅仅防范一个风险,往往是一个制度兼顾多个风险。
2.1 经济:经制财政与非经制财政并存并行
中国古代各朝除了某一时期偏居一方,大都形成了统一。但广阔的疆域也使得统治者受到人力、物力和通信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直接统治。因此,形成以统治者为代表的委托人和以官僚集团为代表的代理人,即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层层的代理人来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但是当代理人与委托人发生冲突时,代理人可以利用与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进行利己活动。尤其是当委托链条较长导致较高的监督成本时,更提高了代理人利己活动的可能性,委托人常常面临着来自代理人追逐自身利益的风险。
如何应对代理人风险?对于统治者来说,以财政手段制约地方从而达到降低地方代理人风险是常用的手段之一,体现在制度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起运存留制度严格控制了地方财政的直接收入来源。在清代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下,重中央、轻地方,重起运、轻存留。州县地方行政经费向来存留不足,加之中央政府在国家财力不支的情况下,经常提高起运比例,消减作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的存留数额,地方存留的比例在清初至清末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二是,奏销制度严格规定存留地方钱粮的用处。在奏销过程中,若查出钱粮虚糜浮冒等情弊,视情节轻重,可对相关责任者处以独赔、分赔、代赔等不同承赔方式。情节特别恶劣者,则会遭受降职乃至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官员升转前,吏部须查明其承赔是否完结。
表面上看,清朝统治者通过财政制度规范似乎达到了降低代理人风险的目的。然而,伴随着清代人口的增加以及白银贬值,地方财政已经不足以支撑地方治理的需求。清代“文字中的法与现实中的法”差距则不同于前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在地方政府中逐渐形成了经制财政与非经制财政并存,并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央在财政上的控制。非经制财政作为经制财政之外的收入,主要有陋规、加派、挪用三个来源。
对于加派,时人张玉书说:“敢行私派,无所顾忌者,每借口督抚之宪檄与内部之咨文。盖每年正供赋额,各有抵销,遇有别项费用,部臣辄敕该督抚酌量设法,不得动用正项钱粮……但百姓除正供粮税之外,别无余物可以设法。名为设法,实为加派而已……部文一下,贪婪官吏,借端侵渔,本应设处者十之一,而私派者已十之五”[8],可见加派数额之多,也可窥见因统治者防范风险造成地方财政困难。
对于挪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某一方面急需的钱财,但是挪用并不仅仅有因公挪用有时也因私挪用,加之挪用后往往不能及时补足,最终造成地方大量亏空。挪用的情况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督抚因受贿、婪索而受制于属下,不得不任由属下亏空,并形成上行下效的亏空效应。二是布政使与府道勾连,狼狈为奸,上下扶同侵挪婪赃。三是徇庇属员,规避处分[9]。除了第三点外,大多和地方官员以及他们的上级官员的收贿贪污有关。
2.2 人事:非正式关系与正式关系并存并行
按清朝统治者的正式制度安排,清代地方政府在人事安排上只存在正式关系,即书吏和衙役。书吏和衙役在地方各有其职,其发挥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按照规定,书吏在地方政府中的工作主要有草拟公牍、准备例行报告、拟制备忘录、填发传票、填制赋税册籍与整理档案等。衙役则根据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工作,如马快负责巡查以及传唤,捕役负责缉捕盗贼,仵作负责验尸等。但中央规定的衙役数额不能适应实际的地方政治需要导致地方中有许多超出规定数额的衙役,即“白役”。虽然大量白役的薪水由州县官提供,但往往并不能做到。故衙役们往往对百姓行敲诈勒索之事以填己腰包,“差役一项,大都狐假虎威,以索诈为生涯,以恐吓为能事”,他们得到本官任何差遣,均可大做手脚,“腰有一牌,便声生势长,鱼肉细民”[10]。而书吏更甚,甚至出现书吏对州县官以文卷相挟的情况。书吏、衙役的负面作用日渐增长。对此,统治者也有所认识,雍正帝就曾经通过吏部下达谕旨指出:“直隶书吏积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县官因限期严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堕其术中,以后事件皆任其把持,为害甚大。”[11]所以,书吏和衙役这部分正式关系不仅欺压百姓,也不利于州县官自身工作的展开。
因而,为维持地方政府正常运作,在清代地方政府中,除了书吏和衙役等正式关系,州县官还私人聘用了长随与幕友等非正式人员。这些非正式人事关系与正式人事关系并存并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制约正式关系的作用。非正式人事关系的出现不仅仅与正式人事关系在体制内的负面作用有关,也与统治者防范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方面对代理人进行直接限制,在政治技能以及任官制度等方面也予以间接的管制。
首先,科举制度除了选拔有才学之人,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方面对官僚队伍进行统一和规范,以此降低代理人反叛的风险。统治者对于官僚的选拔并不是以实际的政治才能为标准,而是以儒家典籍知识为标准,以达到统一官僚思想的目的。当人们通过科举考试之后,尤其是任职州县官之时,却造成了儒家理想与政务现实之间的断层。儒家的经学教义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地方种类繁多的事务,这种断层导致了幕友的出现,例如掌管刑狱诉讼的刑名幕友和负责管理钱粮的钱谷幕友。州县官们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不得不将手中的代理权力一部分分散到幕友的手中。
其次,任官制度中的回避制和州县官的短任期则直接减少了代理人在当政时期培植自身势力的可能。回避制度古已有之,清代得到发展和完善。首先要回避本籍,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规定,“候补侯选知县各官,其原籍在现 出之缺五百里以内者,均行回避”[12],即州县官需要在距离原籍五百里之外任职。其次回避寄籍,寄籍是指官员不在原籍但是长期生活的地方。除了对州县官的地区回避,候补官员的地区回避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社会关系回避方面,主要是亲属回避和师生回避。亲属回避,包括直系亲属、同族亲属和外姻亲属回避。师生回避,包括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回避和受业师生回避。
最后,除了回避制度,清代州县官任职时期短也为人们所议论,有所谓州县官“三年一任”之说。不过,该说法并不准确,州县官分为实授、署任、代理知县三种,三者在任期上存在重大差别。实授知县的平均任期最长,为2.4年,大多不超过3年;署任知县平均任期为0.9年;代理知县的任数较少,任期也短,平均为1.5个月[13]。依据目前学界对于州县官任期的研究,不论何种类型的州县官,其任期几乎均不超过三年,可见州县官任期之短。
这样的制度设计为长随与幕友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一方面,长随与幕友作为本地人对于地方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州县官却对地方情况一无所知,加之任期较短,即便在任时对地方有所了解可以开始治理的时候,由于面临转任,使得很多州县官放弃原有的政治抱负,转而追求稳定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对地方风俗不了解也给书吏和衙役提供了擅权的机会。顾炎武对于回避制度曾言:“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得到官。而士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14]。回避制度使州县官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在路途中以便赴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书吏和衙役作为本地人比州县官更加了解当地的情况,加之书吏和衙役在衙门中具有一定的权力,使得州县官的权力旁落到书吏和衙役的手中,这也是州县官利用幕友、长随这类非正式关系监督书吏、衙役的原因之一。
2.3 行为:火耗由非法行为默认到合法化
在统治者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的第二种风险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和代理人风险类似,经济风险不利于国家治理的有效展开。但不同之处在于风险所处的位置不同,社会风险和代理人风险通常出现在以百姓为首的社会底层或者以官僚为首的社会中上层,但是经济风险则直接表现为以统治者为首的社会上层,是一种更直接的明显的风险。
低税收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降低社会风险,也是经济风险产生的背景。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在初创时普遍实行低税收政策,与民生息。清朝不仅实行低税收,而且更推行了税收的定额化。自清朝入关之初开始,一直以来的方针就是按照明代万历年间的原额(即依据明代的《赋役全书》)制定税额。在清代的《赋役全书》中土地面积及税额的原额均沿用了万历年间的数字[15],顺治年间该制度基本定型,即使后期人口增长也未改变。
在低税收和税收定额化的双重背景下,雍正即位之初即面临着经济风险。彼时,雍正帝的国库仅有800万两存银。户部银库并不是唯一出现短缺的地方,京师其他部院有各自独立的财政——这是沿袭明朝的做法——也存在着短缺的情况。国库空虚与地方存在着大量的无着亏空有关,如何改善地方亏空问题从而提高国库收入?答案是火耗归公。
一方面,火耗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并恶化了吏治风气。雍正即位时,户部的存银数由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5000万两降到800万两。官员贪污滥用造成各省钱粮亏空,富饶的江苏省赋税最重,藩司亏空也为各省之最。这表明国库空虚不是赋税收入少,而是由吏治腐败所造成的。对此,需要规范官员的收支行为,由暗箱操作转为公开,耗羡归公成了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远超正项钱粮的加派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帝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无论是面对经济风险,增加中央收入以改善中央财政疲软的现况,或者是为了减少百姓负担降低民变带来的社会风险,统治者都有理由也必须发动一次自上而下的财政改革。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统治者便先后在各省推进火耗归公,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各省对于火耗收入不收归中央的自由支配权。可以说,火耗归公在雍正时期是比较成功的,各省基本上都获得了较多盈余。但是随着乾隆即位,火耗归公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大大减少了各省的财政独立性,火耗归公走向失败。而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则成为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又一种“畸形”,即在火耗归公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仅使“火耗”作为一种附加税被公开,也使得这类法外附加税由非法到合法化,最终造成税外税的局面。
3 “畸形”在清代地方政府运作中的作用
可以说,为降低风险,清代统治者设计出各种正式制度。然而,为了维系地方政府运行,州县官在实践中构造了各种非正式的乃至有些“畸形”的制度安排,即在地方财政中,表现出经制财政与非经制财政并存;在地方人事关系上,表现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并存;在行为规范方面,表现出火耗的非法行为默认到合法化。这些“畸形”并没有导致政治的“死亡”。相反,“畸形”在清代地方政府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僵化的制度带来的政治上的不便,对百姓生活造成的困扰也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3.1 非经制财政的作用
非经制财政在清代地方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地方财政的补充、对上级呈递礼物以及维系下级吏役们的开支。
一是作为地方财政的补充。一个州县官通常要“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砺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阙职而勤理之”[16],这些职能的发挥无一不需要增加地方财政的支出。而地方留存的小部分钱粮中,大部分都用于与中央有关的军需和驿站,真正用于地方事务的却很少。非经制财政显然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州县官向上级官员呈送礼物的经济支撑。大部分京官的额外收入都来自地方官的礼金,冯桂芬云:“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17]。甚至自上而下形成所谓的“送礼政治”,对于州县官来说非经制财政为向上送礼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三是下级吏役们的开支。州县政府的正常运作需要很多经制外的书吏和衙役以及州县官招募的幕友和长随,这些人的费用也需由州县官自己支付。其中花费最多的当属幕友,据陶正清《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说:“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请幕宾,若浙江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就中所优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8]421,非经制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州县官招募幕友等助员提供了帮助。
总之,在央地关系中的财政方面,严苛的制度并没有按照中央设想实现对地方财政的绝对控制,相反,正是由于中央追求对地方财政的绝对控制造成了地方两大财政系统并行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摆脱了中央严苛的财政约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法外自主财权。
3.2 非正式人事关系的作用
非正式人事关系在清代地方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检吏”。这一功能的主要发挥者为幕友,汪辉祖曾说:“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总之幕之与吏,择术悬殊,吏乐百姓之扰,而后得藉以为利;幕乐百姓之和,而后能安于无事。无端而吏献一策,事若有益于民,其说往往甚正,不为彻底熟筹,轻听率行。百姓必受累无已。故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18]“检吏”其意正如汪辉祖所说为“约束书吏”,也是所谓的“幕友第一要事”。
二是“佐官”。如刑名幕友在开庭审理之后,如果是轻微的笞杖刑案件,刑名幕友代州县官作出批答,如果是涉及徒刑、流刑、死刑判决的案件,刑名幕友还要准备向上级呈报的关于案件的详细报告[19]。长随的辅佐功能体现在对仓、库、号、监、厨等的管理上。这些地方除厨房外,仓、库、号、监都配有相应 的公务人员,仓、库有户书和差役,驿站有驿书(或兵书)和夫役,监狱有刑书和禁卒,而“管仓”、“管库”、“竹号”、“管监”长随则代表本官管理地方的公务(包括管理书、差在内)[20]。
3.3 火耗归公的作用
火耗归公在清代地方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使得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据《清史稿》记载:“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佘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22]国库存银量也大幅度增加,康熙时期800万两,雍正时期6000万两,乾隆初期3400万两,乾隆后期7000万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统治者所面临的经济风险。
二是“有补于吏治”,使前朝时期的吏治风气有了改观,“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口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23]对火耗归公的积极作用,时人孙嘉淦曾言:“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数厘之额,提其所入于藩库中,以大半给各官为养廉,而留其余以办地方之公务。嗣是以来,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其已定之数,较之未定以前之数,尚不及其少半,则是迹近加赋,而实减之。且养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属员;办公有资,州县亦不敢苛求百姓。馈送谢绝,而摊派无由。故曰: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能为清官也。是则耗羡归公,既无害于民生,复有补于吏治”[8]666-667。
三是“无害于民生”,使民众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孟森对此评价到“前代以来,漫天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21]整体而言,在统治者对风险防范的制度建构下的“畸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有利于维持地方社会的正常运作。
4 “畸形”对清代地方政府的反噬:风险的再生
清代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三种“畸形”现象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畸形”终究是正式制度的异化。“畸形”所起到的正向作用并不能真正解决清代统治者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对于风险防范的地方政府设计悖论性地滋生了新的风险。
首先,非经制财政引发了新的代理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如顺治、康熙时代的官员陆世仪之言,“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24],非经制财政为部分官员攫取利益打开方便之门,具有代表性的是对火耗或者说是对火耗归公后养廉银的分配。
其次,在地方人事关系的约束上,州县官期望利用长随、幕友来制约书吏、衙役等人的贪腐行为,但很容易落入“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之中。一是,长随可以监督吏胥,反过来也就存在着相互勾结的可能性。幕友与吏役,两者名为制约,实为妥协。在制吏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长随反而与衙门书役结成了“盟友”。二是,作为知识水平较高的幕友也有较大可能与吏役勾结。例如刑名幕友,作为幕友中具有较强技术水平的群体,与吏役相互勾结,篡改案情。即使州县官想要秉公办案,也很难察觉。可以说,州县官想要以非正式关系制约正式关系的愿望是难以达到的。
最后,火耗归公改革虽然在雍正时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最终与历史上大部分并税改革一样,“提解既久,耗羡渐同正项,州县贪员,重新征收,于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私取养廉”[25],加派横行,腐败不止。
总之,新风险在制度设计中滋生,但是仍在“畸形”范围内。清代统治者仍面临着社会风险、代理人风险和经济风险。由于生产力限制、国家制度、专制统治的必然性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使得正式制度过于僵化,不可避免地会在表层制度下产生深层次的种种合法性危机。由于种种非正式安排并不是国家法定制度,反而为官吏的权力寻租留下了极大空间,从而导致了风险的再生。久而久之,在清代政府内部慢慢掏空了清代统治基础,最终造成了“天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