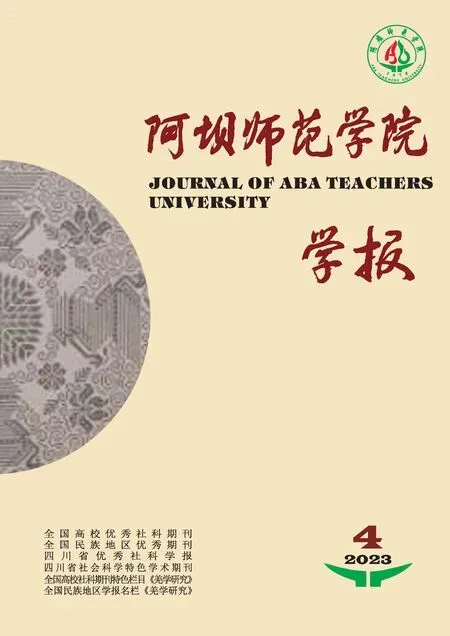英国殖民空间表征中的“同构-异质”观念研究
叶家春
西方的空间概念是殖民地想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划分并融入西方理解框架的方式在身份、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出界线。在西方对东方的“发现”之旅中,西方一直以一种欧洲中心的“科学态度”审视东方,好似把东方视为一个被观察的事物。对于19世纪的英国而言,其世界霸主的地位随着海上霸权、工业革命以及殖民扩张逐渐巩固,她创造的世界也在旅行叙事中被勾勒和刻画。大英帝国的强势文化力图将殖民者融合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造成帝国都市文化与殖民地景观的不可分割。殖民地的自然环境在衬托白人文明的同时,也反噬着西方的“进步”,是帝国与殖民空间书写上的“同构-异质”问题;世界博览会象征着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是以展示殖民地文化为基础,集中体现殖民空间图绘的“同构-异质”体;西方的工业文明,比如铁路和摄影,促进了其文化在殖民地的输入,同时也将殖民地异域因素带回欧洲,融入大都市的文学文化生产,产生出帝国与殖民地的都市文化“同构-异质”现象。与宗主国自然文化迥异的殖民地,促进了帝国的文化多元性,而现代都市国际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殖民主义从区域向全球的战略演变。由此来看,英国殖民时期的文学文化生产实际属于一种“同构-异质”的空间生产。
一、自然的“他者”化:殖民空间书写的“同构-异质”
自然是欧洲人征服外部世界的第一道屏障,要把缠绕在他们周围错综复杂的非欧洲景观定位在一个分类系统中。这不仅仅是面向外部世界建立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用西方的理性抽象出自然的图绘。在欧洲殖民非西方的进程中,自然环境和人群的特质被画上等号:第一,前现代或非现代文化与原始自然融为一体,甚至无法与周围的生态系统区分开来,而现代文化则以与自然保持距离和对自然的管控而著称;第二,温带气候才是“正常”的气候。无论是自然界的暴力,还是诱人而闷热的热带环境,在物理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都远离了欧洲。因此,“欧洲人就其本性而言,不仅是‘现代人’,而且是‘正常人’”①Derek Gregory. Power,Knowledge and Geography. The Hettner Lecture in Human Geography[J].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1998,(2):88.。
历史学家罗伊·布里奇斯(Roy Bridges)在《欧洲以外的探索和旅行(1720 -1914)》(Explo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Europe〔1720 -1914〕)中展示了旅行写作在这段时间里被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吸引的现象,“他们希望将非欧洲世界带入一个可能会受到影响、被剥削、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直接控制的位置上”①Roy Bridges. Explo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Europe(1720 -1914)[C]/ / Peter Hulme,Tim Youngs,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53.。帝国时期的旅行写作就应该在这样的世界语境下被考量。旅行写作弥漫着对种族优越感的信仰,这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结果之一,它和话语权力勾连。白人“教化”的权力不仅从未受到这种话语的质疑,还被视为一种高尚的救赎。在这种话语中,“他者”被置于沉默的地位,而白人去教化则是出于一种善和道德的需要。这种观点典型地体现在以描写非洲著称的康拉德的小说中。他对非洲的向往通过马洛传达出来:“要知道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我就对地图十分感兴趣。我常常会一连几个小时看着南美,或者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地图,痴痴呆呆地想象着宏伟的探险事业”②康拉德.黑暗的心[M].宋兆霖,选编.黄雨石,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131.。康拉德的作品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经常援引的文本,这些段落生动地展示了欧洲人在远离殖民主义现代性的“空白处”,为系统地掌控非洲的“文化”和“自然”而进行的斗争。当文明的欧洲人初到“黑暗”的非洲殖民地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一个名为《文明的前哨》的短篇小说中,康拉德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答案。他的主角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两名代理人:
他们在一个大房间里像盲人一样生活,只知道与他们接触的东西(而且都是不完美),但却看不到事物的总体方面。河流、森林、所有大地上在悸动的生命,都像一个巨大的空场。即使灿烂的阳光也没有透露出任何可理解的东西。事物在他们的眼前以一种无关紧要和漫无目的的方式出现和消失。这条河似乎从无处出现并流向无处。它流过虚空。③康拉德.文明的前哨[M].宋兆霖,选编.马小弥,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72.
“盲人”“无法看到事物的总体方面”,外界自然在两个人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空场”,一个“虚空”,这是最奇特的自然,一个没有空间的自然,河流可能从无处而来,流向无处。所以,这里的当地人也是没有名字的,野蛮的。两个主角在小说里被称为“促进贸易传播文明的先锋战士”。直到有一天,无所事事的两个人偶然在一份英国出版的旧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殖民扩张”。
它(报纸)大谈文明的权利和义务,大谈传播文明的神圣职责,大肆吹捧那些给世界的黑暗角落带来文明、信仰和商业的人们。加里叶和卡耶茨读了这些东西,大为惊奇,觉得连自己的身价也凭空增添了好几分。有天傍晚,加里叶手舞足蹈地说:“百年之后这儿也许会出现一座城市,会有码头、仓库、兵营,还有——还有——台球房。告诉你,老伙计,文明和美德——一切的一切都会有的。”④康拉德.文明的前哨:74.
这就是一种白人创造空间的假想,他们试图将野蛮的自然带入理性的范畴。在这些段落中,康拉德将“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对立重新定位为殖民文化和“他者”化自然之间的对立。
但是,并非所有白人都能这样理智地不受到非洲自然的影响。事实上,康拉德对非洲自然的描写总是带着白人的迷茫,甚至是恐惧。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想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来理解非洲大陆,但是所谓的控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殖民文化害怕混杂化,也害怕不同种类的杂交而使自己四分五裂。“殖民计划要求欧洲文化渗透到‘他者’自然中,但是也有一种可怕的可能性,那就是‘他者’自然渗透到欧洲文化中的逆转”⑤Derek Gregory. Power,Knowledge and Geography. The Hettner Lecture in Human Geography:13.。康拉德在谈到自己对于非洲的创作时就反映出这个逻辑。
正是非洲,这个罗马人常说新事物总会到来的大陆,摆脱了黑暗时代沉闷的想象奇迹,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兴奋的空白空间。未知地区!我的想象力可以描绘出这些有价值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忠诚的人,他们从边缘开始蚕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发起进攻,在这里征服一点点真理,在那里征服一点点真理,有时还会被他们的内心如此执着于揭示的神秘所吞噬。①Joseph Conrad. Last Essays[M]. New York:Doubleday & Page,1926:13.
康拉德赞扬白人在非洲的冒险精神和献身精神,并把这些行动的动机看作是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名利。但是,他心中富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还是会被“神秘”所吞噬。所以,在《文明的前哨》中,离开了黑人雇工的加里叶和卡耶茨,最终因为恐惧而互相残杀,相继死去。在他们死之前,无孔不入的大雾就是这样一种神秘。“无所不包,寂静非常,这是热带早晨的雾,这雾黏糊糊,能致人命,这雾雪白一片,死气沉沉”。大雾似乎掩盖了代表文明的汽船,人们能听见声音,感受文明的召唤却都看不见,找不到,“汽船一下子就消失在雾里,看不见了”②康拉德.文明的前哨:93 -94.。在康拉德的非洲冒险小说里,“贸易站”是荒野中的一个声音,因为代表着帝国话语而显示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即文明进步、开明的制度和道德观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仁慈力量。这种不可战胜性正是康拉德的目标。但是,两个人后来被发现死在浓雾里,自然最终战胜了西方的“进步文化”。
《黑暗的心》中,被当地人和白人奉为神一样的库尔茨先生,最终迷失心智,在临终时喊叫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③康拉德.黑暗的心:259.。这里的可怕,可能是指库尔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残忍,更可能的是,非洲深不可测的丛林带给白人的绝望。这位代表欧洲先进文明、以改造野蛮为使命的白人,却最终被野蛮性所征服,成为当地人的崇拜偶像。在马洛寻找库尔茨先生的途中,这种绝望不止一次地出现:“树木,成千成万的树木、高大、粗壮,一直向高处伸去。在它们的脚下,这只满身泥浆的小汽艇紧贴着河岸逆流而上……这情景让你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空虚而迷惘”④康拉德.黑暗的心:177.。虽然“进步事业”像一种可持续的理想,强化着这些光明的使者,然而,在荒野的影响下,所有由他们的教育、教养、职业、书籍和报纸编织成的道德观念似乎都消散了。作为《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一直客观冷静地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感到被自然吞没的威胁。“我感到我从来,从来也没有发现这片土地、这条河流、这丛林、这光彩夺目的圆形天空,竟会是那样令人绝望,那样阴森,那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⑤康拉德.黑暗的心:209.。白人害怕包围着他们的野蛮自然,那是因为,他们把这种自然与丛林中的黑暗联系在一起,这种“非自然的自然”又与把生活在丛林中的土著人假定为野蛮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丛林的一部分:一种不正常的自然创造的不正常的种族。
康拉德在小说中对自然的处理,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并解构了由当时的冒险和旅行写作所构建的帝国题材的神话色彩。殖民地的“自然”,在旅行写作中被视为与“他者”同等落后,从而强化了白人的优越性,同时,它又可以是帝国小说中吞噬了进步文明的黑暗,导致殖民者的迷失。这种矛盾统一在殖民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印证了殖民地和宗主国在殖民空间书写上“同构-异质”的关系。
二、世界博览会:殖民空间图绘的“同构-异质”体
世界博览会(World Exhibition)首次出现在19世纪中叶,象征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范。随着殖民事业的推进,世界博览会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对殖民地文化掠夺的集中展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殖民地文化不可分割,是一对“同构”体。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博会,声称要向600 万参观者展示人类发展的活生生的图画。以1889年法国世界博览会的埃及展览为例,人们可以看见“模仿的集市、东方宫殿、异国商品、自然栖息地上的殖民地土著……”⑥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M].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XII在按照真实比例修建的展厅里,游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错觉。事实上,这些展示只是被安排来表达欧洲文化和进化的历史地理秩序,这种秩序反映并再现在众多的帝国计划、符号和展览指南中。正如米切尔所言:“展览似乎不仅仅是为了模仿外面的真实世界,而是为了在无数的种族、领土和商品上叠加一个意义框架”⑦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XIV。
在格雷戈里那里,世界博览会是一个有双重意义的特殊空间。
一方面,它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里能够通过物质去追溯,往往是启蒙运动的纪念,这是一种叙事的进化,其中白色神话(white mythology)被明显地显露出来,并被视为带来了技术上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们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异国情调的一种模仿对抗”的空间,这是一个非理性的极限空间,充满了来自其他殖民文化的“麻醉、混乱的图像”,提供了一个殖民地世界的幻觉般的一瞥。①Derek Gregory. Power,Knowledge and Geography. The Hettner Lecture in Human Geography:80.
也就是说,世界博览会作为一种启蒙理性的宣传,也同时传达了“他者”文化——殖民文化的“混乱”。对于没有到过殖民地的欧洲观众来说,世界博览会给他们的地理学想象赋予一种民族优越感的预设。格雷戈里认为:“这是通过一系列策略实现的,这些策略远非局限于展览或博物馆和动物园,那些19 世纪欧洲展览文化的其他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殖民地的现代性”②Derek Gregory. Power,Knowledge and Geography. The Hettner Lecture in Human Geography:80.。
彰显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世界博览会其实就是一个“视界政体”,它选择性地展示掠夺而来的殖民地文化,典型地体现了权力和空间性的关系。空间性是后现代地理学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它和社会生产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探索尼尔·史密斯所谓的“深度空间”的四个时刻,即“典型的社交空间……物理程度与社会意图相融合”③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Nature,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UK:Black well,1990:214.。在知识、权力、空间性的语境中,空间性通常被理解为相对或相关的空间,也就是说,空间性被概念化为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相对空间永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永远是“在成为,在制造”的过程中。在列斐伏尔的理解中,“空间不仅是社会产品,也是社会行动的生产者和监管者”④Henry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l.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Blackwell,1991:568.,“空间秩序既是社会秩序的原因,又是结果”⑤Henry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145.。世界博览会就是一种空间秩序,它代表了社会维度的结构原则以及社会关系和过程的矩阵,这种空间秩序作为感知和社会交流的媒介,在表现权力和地位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世界博览会不是静止的、作为背景的环境,而是动态的、积极参与资本生产或者政治决策的战略因素,它是帝国主义展示殖民战利品的空间实践,具有意识形态性。
融入空间性和“视界政体”的世界博览会,为西方观看殖民地提供了一个完全可见的空间。在这里,殖民地以透明和沉默的状态呈现出来。在1889年的法国世界博览会上,“埃及展览是法国人建造的,代表开罗的是一条蜿蜒的街道,两边充满悬在上层的房屋和像凯特贝一样的清真寺……与展览其余部分的几何线条形成对比的是,这条仿街是以中东集市的随意方式布局的”⑥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当这样的表征和真实相遇之后,一位埃及人写道:“它旨在模仿开罗的旧面貌。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油漆都故意变脏了”⑦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换句话说,世界博览会并不是真实地反映被展出的世界,而是有选择性地呈现给观众。在凝视被看者的过程中,西方人的优越感来自于宗主国的权力话语体系。格雷戈里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世界博览会的特质:
首先,与早期的万花筒(cabinets of wonder)不同,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异国情调的物品并不像单一的——“稀有,罕见甚至是未经考验的创作”——而是在更大的秩序系统中作为地方的代表……其次,这种事物的排序将世界想象成一个透明的空间:完全可见,可测量和完全可知……第三,新的展览综合体产生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大都市公众被构建为知识的集体主体,既有匿名性又不可磨灭地标有欧洲的标志,因此参与了殖民现代性的项目……第四,这种共谋的言论取决于本质上是驯化的凝视架构。⑧Derek Gregory. Power,Knowledge and Geography.The Hettner Lecture in Human Geography:80 -81.
格雷戈里的总结揭示了世界博览会在本质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展览。这是一个以欧洲的标准建立的理性空间,展出的物品是挑选过的、带有“矮化”殖民地的目的。世界博览会不仅是一个以特定方式使物体可见的空间,也是一个隐喻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主办方对知识的呈现进行了协商和合法化。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宏观的生态空间的物化,也是殖民化的一种“机器”,因为它围绕着由“表征”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所赋予的想象权力而展开。
由此可见,殖民时期帝国的空间表征离不开殖民地文化,帝国的文化生产和殖民地是一种“同构-异质”关系。世界博览会的产生是帝国主义发展的缩影,而这种“先进”文化却是通过与“他者化”殖民地对比出来的。世界博览会展示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理想的殖民地世界,它不仅代表着异域风景,更重要的,是一种和西方逻辑理性完全背道而驰的殖民地文化。从主办方的角度来看,世界博览会往往位于展厅中心,以展示自己作为世界帝国首都的形象。知识传播和权力分配的不平衡状况,从西方以自己为坐标划分世界就已经开始形成。非西方世界“野蛮”的自然环境造就它们“混沌”的文化和性格,欧洲人有义务去帮助改变它们的“落后”。这是欧洲人的世界模式,也是殖民文化形成的基础。米切尔直言:“这些世界文化和殖民秩序的象征性表现,不断地被欧洲的游客所遭遇和描述,是伟大的历史信心的标志。在这样的现代娱乐场所里设置的场景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政治确定性”①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7.。展览、博物馆和其他景观就是这种确定性的体现,它们以“客观”的形式再现帝国的进步、文化和技术。“知识、权力和空间性”的关系在19 世纪殖民秩序形成时即交织在一起,为欧洲中心话语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世界博览会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在图绘殖民空间上的“同构-异质”关系,也掀起了类似的以殖民地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热潮。将世界作为一种展览打开,也同时打开了通往新观点的大门,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属下”观念,这些观点在权力的地图分布中,严肃地处理成为被边缘化的声音及地位,构成了帝国文化批评的新图景。更进一步说,将世界视为一种展览时,审美欣赏被转化为政治本体论。在展览中,殖民地的秩序是分离的,它远离了具体的特殊性、区隔化和序列化。因此,世界博览会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抽象秩序,通过协调和安排产生。“世界博览会不是指世界的展览,而是指像展览一样构思和把握的世界”②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5.。在整个19 世纪,“非欧洲游客发现自己也是一种展览,是欧洲好奇的对象”③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5.。欧洲学者替殖民地发言,是因为殖民地人民被默认“没有能力表达自己”④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5.,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自然被忽略。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殖民权力的运行,还呼吁要依靠当地居民的经验作为合法的意义来源,还原那些“没有历史”的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恢复他们的声音,而非遥远的想象或者接受固有的观点。在空间参与政策制定、决定文化优劣的情境下,空间背后的身份政治问题也被推到前台,也就是随之产生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殖民主义文学批评。
三、殖民地景观:帝国都市文化“同构-异质”现象
帝国都市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都市文化把殖民地文化构建为“他者”;另一方面,都市的消费循环和对异国的浪漫情调追求又把殖民地文化带回都市生活。矗立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刚完工时,迎来了众多惊叹和批评,其中,盖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就是批评者的代表。莫泊桑觉得它不伦不类,是巴黎最丑陋的建筑,所以,他选择在铁塔吃午餐,因为这是在巴黎唯一看不到它的地方。埃菲尔铁塔是为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而建造的,那次博览会不仅标志着法国大革命100 周年,而且第一次将殖民地城市的模拟建筑融为一体。这座铁塔的穆斯林尖塔、柬埔寨宝塔、阿尔及利亚清真寺和突尼斯清真寺,都是为了向大都市观众展示法国的殖民地而特意设计的。⑤Debora Silverman. The 1889 Exhibition: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ndividualism[J]. Oppositions,1977,(8):71 -91.埃菲尔铁塔在这里唤起人们对帝国都市文化与其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注意。格雷戈里评论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大都市文化向非欧洲景观的反向投射,在殖民规划话语和其他殖民文化产品中也变得司空见惯”①Derek Gregory. Imaginative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4):464.。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市景观传递出一种渗透殖民意识的征服欲。“对帝国来说,城市可能是最重要的作为象征性的首都和所在地,在那里,首都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表达可以被积聚、展示和获取。它们既保护帝国的认同,也作为一种服务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帝国的权威和勋章得以传递给继任者”②肯因.城市与帝国[M]/ /李在全,译.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72.。
异质文化是帝国主义都市文化环境中重要的构成因素,而工业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殖民地异质文化的输入。海上航道和铁路的开通,加速了文化互通的速度,铁路的出现更是宣布了一种全新的帝国符号。铁路不仅促进了旅行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的扩张,而且改变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和对世界的观念。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很形象地描写了人们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感受:“一股力量迫使它在它的铁路——它自己的道路上急驰,它藐视一切其他道路和小径,冲破每一个障碍,拉着各个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群和生物,向前奔驰……两旁的景物似乎近得仿佛可以抓住似的,这些景物老是飞离游客,一个骗人的远景老是在他心里慢慢移动”③狄更斯.董贝父子[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349.。人们用怪物和铁龙来称呼火车。铁路的出现对英国文化的影响在伊恩·卡特(Ian Carter)的《英国的铁路和文化:现代性的缩影》(Railways and Culture in Britain:The Epitome of Modernity)中可见一斑。卡特将铁路定位为视觉上的文化隐喻。《董贝父子》中的铁路意象在他的书中占据了专门的章节,小说中四次对火车意象的描写,在卡特看来预示了英国文化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从最开始把修建铁路比喻成地震,到后来适应铁路旅行之后,把铁路比作生命的血液,火车旅行于此成为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以“蒸汽本身的速度奔驰的怪物”预示着帝国主义力量的延伸和速度。于是,火车作为一种帝国的象征渗透到各个殖民地。“一旦铁路建设留下的伤疤被草花软化,铁路旅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火车在痛苦的风景中舒适地安顿下来,就像在文学叙事中一样”④Ian Carter. Railways and Culture in Britain:The Epitome of Modernity[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264.。
殖民地景观还通过19 世纪的另一项发明——摄影,丰富了帝国都市文化建构。“火车旅行和摄影之间有相似之处。在这两者中,景观都被框架化,感知行为成为一种共享的体验。在这两者中,都有一种景观或纪念碑呈现在眼前的感觉”⑤Tim Youngs. Introduction:Filling the Blank Spaces[C]/ /Tim Youngs,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Anthem Press,2006:10.。文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摄影征用的景色或者物品,以及游客对景观的观看,都强调了对所观看物品的占有,这体现了一种权力-知识关系,也建立起旅行、帝国主义、观看和摄影之间的联系。因此,皮特·奥斯本(Peter Osborne)认为:“摄影,特别是旅行摄影,构成了文化武器库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⑥Peter Osborne. Travelling Light:Photography,Travel and Visual Culture[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55.。事实上,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埃及之旅就与摄影师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他们进行了一次摄影旅行,其结果因为图文并茂而非常特别。法国研究所评论说:“多亏了这位现代旅伴(相机)的帮助,它高效、快速、始终一丝不苟”⑦Gustave Flaubert. Flaubert in Egypt[M]. Francis Steegmuller,transl.New York:Penguin Classics,1996:23.。图像与现实的精确对应,给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客观的确定性。1858年出版的第一批中东照片总集,即弗朗西斯·弗里斯(Francis Frith)的《埃及和巴勒斯坦》(Egypt and Palestine)和《被拍摄和被描述》(Photographed and Described)被《艺术杂志》(Art Journal)称为“一次超值的摄影实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东西完全是真实的”⑧Kenneth Bendiner. The portrayal of the Middle East in British Painting,1825 -1860,[D].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1979:314.。摄影把这种资本扩张的记录传播给国内的观众,使得这些记录成为全球关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个占有被观看对象的观念也在无意中传播开来。“旅行摄影最受欢迎的用途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想象旅行的一种形式,它还为中产阶级观众提供了在全球体系中识别自己的方式,他们的生命和财富已经作为一个殖民国家的成员投资在这个体系中”①Peter Osborne. Travelling Light:Photography,Travel and Visual Culture:56.。摄影配图是许多旅行书籍的重要特征,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它们对群体景观的操纵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旅游摄影更像是一种确认而非发现的过程”②Peter Osborne. Travelling Light:Photography,Travel and Visual Culture:79.。这里的确认,就是帝国的民族身份通过对“他者”的标记体现出来。在征服土著人民和传播帝国主义思想方面,摄影是一个无声但可见的伙伴。它告诉西方读者,殖民地的人和动物一样,是要被征服和控制的,野蛮人和野蛮景观需要文明。
可以说,对殖民地文化的记录和挪用,加速了帝国都市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学创作主题的多样性进程。帝国统治的成功不是全部因为武力,而诸如心理胁迫、引入破坏传统权威观念的新宗教框架,以及殖民官员与土著统治者之间的合作等非自然手段,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布劳特看来,殖民主义使得大量财富流入欧洲才造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因为,“1.欧洲的上层阶级依赖殖民主义;2.欧洲上层阶级在欧洲思想的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3.欧洲的上层阶级在形成一个一致信仰体系中存在着永久性的社会利益,这个思想体系将使殖民事业合理化,为它辩护,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它发展”③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M].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7.。文化并不是一个基本结构,而是和权力共生的,权力阐述文化,文化也支持权力。帝国都市将殖民地文化构建为异质的,不仅体现在它们如何将异域文化表现为外来的、奇异的、陌生的,还包括如何行动并掠夺其他文化。殖民主义强加给它所征服的人民的苛求、压制和复杂性,剥夺了他们创造自己历史的权利。都市文化和殖民地紧密相关,因为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过程。“殖民主义始终是一个同样重要和深刻的文化过程;它的发现和入侵是通过符号、隐喻和叙事想象激活的。甚至看似最纯粹的利益和暴力时刻也已经被意义结构所调和和包围。殖民文化不仅仅是掩盖、迷惑或合理化其外部压迫形式的意识形态;他们本身也是殖民关系的表达者和构成者”④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Anthropology,Travel and Government[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2.。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都市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大都市的文化开放性、多元和混杂性,使它们成为各种文化艺术的温床。在与异质文化的不断碰撞中,新的文学流派发展壮大起来,“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和被异国风情化的地域构成了多数现代文学和艺术的文化语境和美学基础”⑤Celena Kusch. Disorienting Modernism: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Cosmopolis[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2007,(4):39.。在国内和海外之间的空间和文化张力上,帝国主义文学通过设置“自我”与“他者”、“这里”和“那里”,强化了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的二元区别,模糊了殖民力量的多向流动和影响。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殖民地,这种流动和影响显然都在继续产生共鸣。当代都市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殖民主义本身的傲慢,以及对其特权的怀旧。“我们”和“他们”、“文明”和“野蛮”、“善”和“恶”的地理性分裂一直在起作用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
四、结语
英国殖民时期的空间表征与殖民地文化是相互构成的。殖民地自然的无序和“极端”,一方面影射了当地人的蒙昧状态,凸显了殖民者的理性与温和,另一方面也参与了帝国话语的生产,对帝国文化具有反噬作用。大都市文化的权力投射,反映了殖民主义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紧密关系,都市文化吸取殖民地的异域特点,滋养了各种杂糅的文化艺术。厘清宗主国和殖民地在文学文化生产上的“同构-异质”关系,正是对后殖民研究的回应。后殖民研究旨在要批判性地修正对西方以及历史上的欧洲的理解,从而将“他者”视为知识的主体而非客体。书面和视觉形式的殖民表征,包括旅行写作、小说、日记、摄影、地图和展览,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探索殖民权力的物质和想象的空间性,展示了殖民主义的文化地理,以及身份和表征的空间政治。把空间表征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介入后殖民研究,能够从物质层面扩大后殖民文学的研究视野,因为空间占有是殖民主义的直接反映,地理环境和种族的联系是殖民文化推行的潜在动因。可以说,在帝国的议题上,后殖民研究和人文地理学一直存在研究视野上的交融。后殖民理论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批判理论支撑。一方面,地理学现在被视为一组历史偶然的、社会建构的概念、知识和实践,而不是一种不变的、客观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复杂联系,构成了什么是“批判性”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不仅如此,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社会激进思潮,鼓励人文地理学家探索地理学想象更多的“黑暗”面。借鉴社会理论的批判模式,地理学想象在地缘政治、消费社会中包含的形象制作、图片和地图的生产,以及在建筑和景观的设计方面,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从文学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强调地理空间对作品主题的提升,可以从地理角度批判权力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中的形成过程切入,这也是从人文地理学入手研究英国帝国文学“同构-异质”特点的现实意义,并促进英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