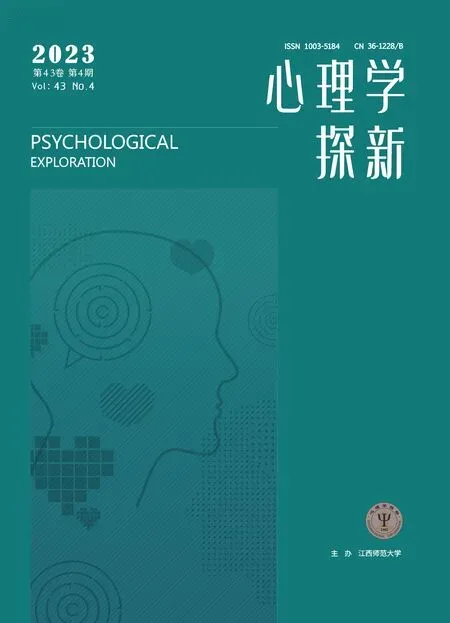“超华生”的胎动:郭任远激进行为主义思想的历史重估
王 勇,王佳慧,鲍晨烨,陈 巍,4
(1.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2.绍兴文理学院大脑、心智与教育研究中心,绍兴 312000;3.密苏里大学心理科学系,哥伦比亚 MO 65211;4.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绍兴 312000)
1 引言
2021年,在《比较心理学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之际,一篇题为《郭任远与“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100年之后》的文章赫然出现在其庆祝创刊百年的专栏上面,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Freeberg,2021)。“郭任远的名字可能没有被当下诸多研究动物行为的学生所认识。然而,他的观点对动物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中研究动物行为的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也引发了争议。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郭任远在1921年那篇文章(即《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中的一些关键思想,并论证它们与我们今天研究的相关性”(Freeberg,2021,p.151)。历史的镜头再次切回到20世纪初,将郭任远(Zing-Yang Kuo,1898-1970)这位世界心理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请到时代的聚光灯下。
对于心理学而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是个“疯狂的时期”(Boring,1929)。尽管新式心理学,即实验心理学已经绕过欧洲传统的意识心理学在美国大陆悄然出现,但旧式的思辨的概念宛如“幽灵”般依旧萦绕在美国心理学的上空。受达尔文主义的广泛影响,本能(Instinct)概念在动物行为上的重要性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美国心理学的精神领袖James(1890)在其巨著《心理学原理》中专门探讨了“本能”话题。他首次将人的行为与本能相结合,并提出人的行为与动物一样都是受到本能的支配。作为James忠实的追随者,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McDougall成为本能在心理学中的主要代言人。McDougall扩大了本能概念在个体行为领域中的解释范畴,并将更复杂的社会行为归因于个体的本能。由此,本能成为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全部行为的激发因素,成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来源和原动力”(McDougall,1908,p.26)。在此背景下,那些理论学家就像使用单词魔术一样把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用本能这一神奇工具来套用,例如合作本能,性欲本能等。这严重阻碍了科学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学的发展(Holt,1931)。
彼时,恰逢行为主义运动在美国心理学界狂飙突进。作为运动的发起人,Watson(1913)为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研究姿态——行为主义发出了宣言:“在行为主义者心中,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分支。它的目标是对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p.158)。然而,如果说本能理论可以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就只能回到内省式的意识分析,这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能否消解本能问题事关行为主义运动的成败。事实上,Watson在1907年就和神经心理学家Lashley一起开展过许多关于动物本能的研究。例如,研究过燕鸥(terns)的迁徙本能。没有任何训练的燕鸥能够从相隔1000多英里外的陌生地方重新找到回家的路(Watson &Lashley,1915)。尽管他们试图去解释燕鸥是如何做到的,但都徒劳无功。此后,Watson对本能的态度逐渐变得缓和。到1919年,Watson(1919)直接承认本能存在于生命早期,但强调习得的习惯很快会取代本能。尽管如此,本能问题依旧如同一座高山阻挡着行为主义者远眺心理学殿堂的目光。
随着问题的日益堆积,一大批围绕本能问题阐述的论文相继出炉,《是否存在本能?》《本能是假说抑或是事实?》……它们兴起了近代心理学史上名噪一时的“本能论战”。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郭任远凭借其极为激进且彻底的反本能观点,逐渐走入一众美国心理学家的视野。1918年,郭任远从复旦大学肄业后,负笈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师从新行为主义的旗手——Tolman。期间,他接受了Watson的行为主义主张,成为坚定的行为主义者,并极力主张将心理学建设成一门客观的自然科学。1920年秋,正值大三学期的郭任远作了题为《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的研讨报告,把批评的剑锋直指McDougall。同年冬,他将该报告整理成论文寄给美国权威刊物《哲学杂志》。由于观点过于犀利和出格,这篇文章直到1921年11月才被发表。旋即,McDougall(1921)回应了一篇长达48页的文章,并将其称为“超华生”(Out-Watson Mr.Watson)的行为主义者。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郭任远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系列批判本能的论著及相关史料,将郭任远的主张重新放置于国际本能论战之中,进而对他的理论进行审视与定位,并阐述其对于郭任远个人职业发展,乃至整个心理学学科的影响与价值。
2 郭任远反本能主张的酝酿与演变
在郭任远学术生涯的开端,“本能”问题无疑成为了他激进行为主义观点进攻旧式心理学的最佳“靶目标”。在1924年发表的《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一文中,郭任远仔细回忆了他关于本能思想变化的过程,并用他在那段时间发表的三篇文章作为划分间隔(Kuo,1921,1922,1924)。
2.1 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
在《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中,郭任远指出本能是一种习惯的倾向,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后天产生的习惯行为(Kuo,1921)。在他看来,新生儿降生后受到周围环境的刺激,从而产生各种纷乱的动作。在经历社会对于这些动作的筛选(对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行为进行奖励,对不符合需求的行为进行惩罚),新生儿会重复最后能够得到满意结果的行为。当再次面对相同的刺激时,新生儿就会自然而然地重复这一行为。此时,该行为就转变成为面对特定刺激的习惯性倾向。而这也恰好容易被那些没去深究其行为发生原因的心理学家快速地判定为“本能”。在对行为发生进行深入反思后,郭任远提出这些行为的背后本质是机能的组合。尽管看似种类繁多,其实只是几个基本元素,即反应单位以不同方式组合得到的不同反应。研究者无法发现本能是机能组合的原因在于本能的命名方式。出于对最后反应的偏重,导致他们注意不到其中包含的附属动作和机能组合。至于类似“飞本能”“性本能”这些在发育后期才表现出来的行为,它们是机能逐渐变化的结果。只是这个过程是内隐的,无法被外在观察者所观察得到。
郭任远不仅批判了本能的理论,还对其相关的实验结果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由普通观察法所得的结论——凡某项反应足以表示某类动物特性者都可以称为本能,是不可靠的。原因有两点:(1)某类动物出现相同的反应是因为其处于相同的环境,且得到一种遗传下来相同动作的方法。动物行为的产生会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而非单一的遗传影响。由此可见,“本能”不符合普遍认可的“不学而能”的条件。(2)种群中的社会性影响也是使得个体出现相同行为的原因。郭任远认为,有些动物本能的实验是不严谨的。以鸟飞实验为例证,Spalding(1875)仅由从未见过飞翔的鸟在同龄鸟能够飞的时候,它也能够飞的现象就得出鸟具有飞翔本能的结论。鸟能够飞是由于其机能组合已经成熟(如,翅膀发育完整),并且受到环境对它的要求(赶出鸟笼,强迫它飞)。鸟飞行为并非不学而能的,而是环境和遗传共同的结果。只是有些没有表现出来反被人认为是不存在。
此外,针对那些主张将本能视为行为上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心理学家的动机,郭任远进行了分类,并逐一批判。第一种是受达尔文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影响,认为每个本能都有适应环境的作用。对此,郭任远给出了两条反对的理由:(1)本能无法在每个时代都适用。行为和环境紧密相连,本能和行为也密切相关。随着新环境的变化,本能必然要发生改变。(2)个体的行为并不适应环境。新生儿对危险刺激进行积极反应,对有利环境进行消极反应的现象,足以说明个体刚出生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显然,这类学者的主张是矛盾的。第二种认为本能是一种冲动。它足以形成重要动力,从而驱使个体发生各项动作。这是McDougall等人的观点。他们深信人类各项活动的动机皆由本能的发生所致。对此,郭任远也给了两条理由:(1)新生儿的动作是由外界刺激而生,并非内在动力驱使。(2)个体只有与外界环境接触,才会有社会性。以Whitman(1919)的鸽子求偶实验为例,郭任远认为实验中的鸽子会向斑鸠求配是因为其生长在斑鸠的环境中,受到群落中刺激的结果。在他看来,鸽子与同类或者异类,甚至是非生命体求配是一样的自然趋势。这是社会刺激的结果,与鸽子的经验有关。
面对Watson(1914)对特殊本能的保留态度,即主张特殊本能以先天反应的形式存在,郭任远也没留有情面。他指出,Watson在新生儿行为的研究中,除了发现随机运动外,并没有找到任何特殊本能的迹象。由此,Watson被迫接受了本能出现的时间顺序理论,但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观点。所谓不学而能的动作,不是先天适应的表现,而是新环境与具有这些动作可能性的行为系统直接作用的结果。所以,个体的行动应用其与周边环境间的关系来解释。至于动作的原素,似乎不能称为先天或遗传的适应,除非证明细胞中有预先形成的部分(Kuo,1921)。
2.2 本能何来?
在过渡阶段,郭任远明确地提出为什么要在心理学研究中放弃本能的理由(Kuo,1922)。在郭看来,本能是一个“完结”的心理学概念。那些拥护本能的学者对本能概念的使用,如同原始人把那些行为中无法解释的神秘性质归因于神明的力量一般。除了冠以科学的名称以外,它并不能在解释行为发生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对本能概念的扬弃决定了心理学能否有资格成为一门自然科学。郭任远这一系列激进的主张背后的直接目的就是“无论反对本能者同意与否,我相信我们否认的主要动机是把心理学从‘扶手椅中的玄想’解救出来;我们是要从发生的心理学里面将这块绊脚石搬走”(Kuo,1922,p.346)。作为反本能心理学家,郭任远提出他的研究在本能心理学家结束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自James以来,几乎很少有学者继续深入分析和解释个体的行为是如何获得的。为此,尽管在实验证据匮乏的现实情况下,郭任远仍尝试提出一些试探性的建议。首先,郭任远再次重申反应单位假说的重要性。他认为,反应单位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可塑性和整合的多样性。这些特点能够有效地帮助反应单位整合成系统化的反应。至于反应单位如何形成本能,郭任远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方式:(1)同时整合(simultaneous integration);(2)时间顺序整合(integration in temporal order)。其中,同时整合是指将反应单元直接或间接地组合成一个单一且有组织的反应。具体而言,同时整合包含三种潜在的形式:①将最初的反应单位组成统一的反应。例如,幼儿学习站立时产生的反应。②将先前整合的行为组合成更复杂的行为。这种整合形式通常发生在个体发展的后期。例如,儿童学习写字的过程。儿童一只手要紧握铅笔,另一只手还需按住书本。同时,眼睛跟随笔尖运动、躯体姿势(头部、肩膀、手臂等)保持规范等活动又必须同时发生。这些活动本身又都是先前整合的行动组合。当被要求在写字过程中一起工作时,它们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复杂的、有组织的反应。③当新获得的习惯与已经习得的习惯的性质不相融时,个体就需要打破敌对的习惯,逐步重建新的习惯。例如,当成年人学习一门新语言时,他总是很难发出一些在母语中没有的音节。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旧的发音习惯,重新组织新的发音习惯。
当然,行为并不孤立发生的,每一个行为之前或之后总是跟随着其他行为。以一定规律,并按照一定的顺序展开的行为,郭任远把它们定义为时间顺序整合。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老鼠走迷宫实验。当老鼠学会走迷宫时,这一现象背后的行为暗示是它已经从先前组织起来的单一反应中选择了某些单独的行为,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新的序列顺序。另外,郭任远强调,为了把不同的行为归类成为一系列连续的行为,心理学家必须采取某种客观的标准,而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把动作按所成就的效果来分类(Kuo,1922)。为此,他将每一系列的行为划分为预备反应(preparatory reaction)和完成反应(consummator reaction)两种类型。他认为,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科学的描述,并不包含目的论,也不存在将某种生命冲动作为有目的的反应的驱动力。
同时,为了避免使用诸如“驱力”、“倾向”等容易给读者产生有灵论导向的术语,郭任远提议借用Tolman(1922)的文章中“行为集”(behavior-set)这一相对具体且客观的术语来替代。所谓行为集,郭任远将其定义为一种反应姿势或预期态度,它们将引导个体以某种方式对不同的刺激或刺激群体做出有区别性和选择性的反应。郭认为,个体在某一时刻产生的特定行为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环境、刺激的性质和强度、个体与刺激之间的历史关系、个体所拥有的反应系统的性质和类型以及频率、近时性等因素的影响外,行为集在决定个体将产生何种行为或者对何种刺激作出反应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行为集形成了一种“反应基调”(reaction tone)。这种基调会一直持续到完成反应的达到,或者直到它被其他反应基调所取代或修改(Kuo,1922)。
2.3 心理学需要遗传吗?
到了第三阶段,按照郭任远(1924)的话来说,这一时期所有的作战方针都变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他的观点日趋极端。郭任远把心理学被定义为一门研究与个体适应环境有关的生理机制的科学,特别强调适应的功能方面。所谓功能方面,即一种反应的效果或适应价值——积极的、消极的或冷漠的。这种反应效果建立了个体对其环境、社会或其他方面的一种新的功能关系。此外,郭任远站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立场上,强调所有研究都应该严格地执行实验室的客观程序,并坚持对行为的生理学解释。心理学中的任何争议问题都必须能够在实验室中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对实验室程序具有某种特殊的价值。否则,这些争议在科学心理学中就没有理由存在。正因如此,郭任远坚定地否定本能的概念,并指出所有遗传概念在实验室心理学中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和价值(Kuo,1924)。
为了厘清心理学的困境,郭任远尝试用生理形态学(physiomorphological)的术语来客观地描述心理现象(Kuo,1924)。具体而言,郭任远把研究客观心理学的学者面临的与遗传有关的问题归纳为两个生理形态学上的问题:(1)是否有任何神经肌肉模式与假定的遗传行为模式相对应;(2)假设存在与遗传行为模式相对应的明确的神经肌肉模式,它们与遗传物质(germ-plasm)有何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与胚种组织相关联。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实验室心理学的工作者还有一个双重任务:(1)必须确定每一种行为模式是否都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神经肌肉模式;如果有,那么(2)必须确定、定位并证明这种神经肌肉模式。郭任远认为,只有完成这个双重任务之后,他们才能合理地探讨心理学中的遗传概念。
在用客观的术语界定好这几个前置问题之后,郭任远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动物行为和生理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非常确凿的事实——行为模式没有明确、固定和不变的神经肌肉模式。这一事实不仅被本能的否认者所承认,也被许多本能的捍卫者所承认(McDougall,1921;Tolman,1922)。显然,双重任务的第一个问题已经被科学研究所否定。遗憾的是,许多心理学家借助诸如神经连接、突触抵抗等概念,直接假定了遗传反应与个体生理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人去费力研究这些关系的实际生理组成。即便是Watson(1919)也使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条纹肌肉的运动)来回避整个问题。在郭看来,一般的生理学概念被那些理论工作者当成了掩盖他们对行为起源和发展无知的“遮羞布”。这些乱象愈发让郭任远认识到心理生理学对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心理学需要的是生理事实,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验证的,而并非一般性生理概念的肆意套用。郭任远强调,对心理学而言,行为的最终原因是遗传、自然、上帝还是灵魂,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只要行为模式与神经机制没有固定的一对一关系,行为的遗传就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
基于这一阶段的深刻认识,郭任远开始对之前的反本能观点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他指出,在《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一文中的论点——所有所谓的本能归根到底都是后天的反应,这无疑是让自己承认了遗传和后天反应之间存在的区别。而主张那些复杂的反应系统是建立在反应单位的基础上,但反应单位本身是遗传的,这等于说自己又承认遗传的存在。只要存在遗传反应,无论多么简单,他们都有理由使用“本能”一词。郭任远坦言,“不是我走得太远,而是我对本能心理学家做出了太多让步,给了他们攻击的空当”(Kuo,1924,p.439)。为此,郭任远对那些妥协的观点进行了修正:(1)废除先天-后天二分法;(2)所有的反应都必须看作是刺激的直接结果,是有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3)遗传不是心理学的问题,因为心理特征的遗传无法在实验室中被证明。当下,科学心理学亟需发展心理生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实验技术。在客观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建设性纲领。这才是行为主义者需要去考虑、去实践的重要议题(Kuo,1924)。
3 余音
在那个元理论“百花争鸣”的年代,郭任远凭借其激进的行为主义观点屹立于本能争论的旋涡之中,这无疑揭示了“科学研究也需要意识形态吸引(ideological appeal)。这种意识形态由环境论(environmentalism)提供——主要归功于郭任远与Watson——随后紧密地与行为主义联系在一起”(Boakes,1984,p.239)。这种理论渗透的客观实验进路为当时停滞不前的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显示出极强的前瞻性与生命力。同时,它又深刻地影响着郭任远的学术生涯。
3.1 倡导以“行为学”研究来替换行为主义观点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Watson等人掀起的行为主义运动,其最初的目标是为了改造心理学的根本观念和方法,建立一个相对不受扶手椅教条或方法论制约的行为研究新领域。然而,结果是不尽人意的。即便是轰动一时的本能论战也在1922年以“未完成的姿态”潦草收场(Cravens,1978)。归根到底,旧式心理学并没有牺牲什么,以Watson为首的行为主义实践最终选择向传统心理学妥协。庆幸的是,Watson的士兵们不顾重重困难,拒绝投降。郭任远就是其中一员(Epstein,1987)。
在郭任远看来,这一切都是Watson主张的柔弱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为此,郭任远总结了自己的反本能主张,并提出行为科学的新构想。1937年,在题为《人类行为学导论》的文章中,郭任远正式为自己的新科学命名为“行为学”(praxiology),并以此来替代Watson的行为主义(Kuo,1937)。行为学的设想融入了郭在反本能阶段的诸多思想。具体来说,郭任远将行为学定义为一门专门研究动物(包括人)行为,并且是多学科交叉的新科学,其主要研究领域在于关注行为的个体发生和生理研究。与行为主义相似,行为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个体的行为。不同的是,行为学家将彻底抛弃诸如本能、意图、行为准备等概念,主张通过严格的实验室控制来获得关于刺激和反应的本质及其复杂关系的充分数据以及有关行为的生理和个体发生的基础数据(例如,神经功能、内部分泌物和其他代谢变化之类),进而使用纯粹的数学和物理术语对行为进行彻底的科学描述(Kuo,1937)。正是这样一个初步构想,在二十世纪晚期却成为让比较心理学摆脱生存危机的一剂良方,“行为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一个新的、全面的、多学科的行为科学的一部分。沿着郭任远建议的路线,人们正在努力建立这样一门科学”(Epstein,1987,p.249)。
3.2 推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扶手椅”走向“实验室”
如果站在心理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回顾这场争端,郭任远对于本能的批判包含了科学心理学势力对旧式“扶手椅”心理学的强烈不满。自Wundt创建现代心理学以来,心理学虽然摆脱了哲学的附庸,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其使用的方法,特别是所谓的实验控制内省法,一直让心理学饱受诟病。在经历这本能论战后,郭任远逐渐认识到即使是自己当时的主张,也没有摆脱哲学家扶手椅式的老把戏,只是没有实验证据的空想空谈(郭任远,1940)。那么,如何能够在实验室里追溯行为发展的起源,如何能够拿出实验的证据成为郭任远继反本能之后需要去直面的首要任务。
在郭任远看来,一个好的科学研究方法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科学数据都必须用定量或数学术语来表述;(2)在科学观察中,研究人员所报告的相同现象必须能被再现;(3)为了观察的精确和精细化,科学仪器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4)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使用记录仪器代替人工观察;(5)为确保科学上可接受的数据,控制实验总是必要的(Kuo,1937)。显然,这些条件都在将心理学研究朝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去推进。1923年,回国后的郭任远先后创建了多个动物心理学实验室。在严格的实验控制条件下,他开展了一系列颇具方法论创新的行为实验。这些实验结果不仅佐证并进一步发展了郭任远的理论观点,也为世界反本能运动新增了科学证据(陈巍 等,2021;Wang et al.,2023)。
3.3 未完结的反本能研究与使命
作为一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郭任远在这场本能论战中成为争论的聚焦点,也成为了唯一一位遭受到与McDougall一样多攻击的反本能学者(Krantz &Allen,1967)。按照郭任远(1924)的话说:“美国现在心理学家对于本能的问题的态度可分作数派:(1)极端赞成我的主张。(2)极端反对我的主张的,如E.L.Thorndike和Mm.McDougall等。(3)折衷派,如R.M.Verkes和John B.Watson等。(4)不赞成也不反对,惟随波逐流一无所主张。在这四派中,折衷派占大多数,赞成派人数最少”(p.H6)。同时,郭任远自信地认为,这些观点大多都是一些误解或者没有特别值得继续深入讨论并给予回应的必要(郭任远,1924)。
值得注意的是,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Watson和McDougall都曾向郭任远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其中,Watson曾在1922年对郭任远说:“我赞成你反本能的主张,但我不能如你那样极端”(郭任远,1929)。直到1926年,Watson才提出:“在人类反应的这个相对简单的目录中,找不出哪一种对应于当代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的‘本能’。于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本能——在心理学中我们不再需要这个术语”(p.1)。(1)也有观点认为,Watson是受到郭任远文章的影响才放弃“本能的遗传”见解(Hothersall,2004,p.482)。McDougall(1921)作为前辈曾向郭任远表达过委婉的妥协:“我们现在有一个两难论……(1)我们必须放弃机械主义而保全本能;或(2)我们赞成郭先生的主张,否认人类及动物的一切本能,而保全机械主义。至于我自己呢?我是宁舍弃机械主义而保存本能的观念的”(p.310)。为此,郭任远曾嘲讽道:“为了将本能从本能否认者的攻击中解救出来,不惜将它们投入柏格森学派(Bergsonian school)的形而上学荫庇之下”(Kuo,1929,p.190)。即便是Tolman(1922)出面斡旋,“我们应该持有心理学不该抛弃本能的信念”(p.152)。郭任远也未对自己的导师采取任何让步:“Tolman的物观目的论(objective view of purpose),不比McDougall直接爽快的灵魂论(animism)好,或者甚至比它更糟糕”(Kuo,1929,p.190)。可见,“发展心理生物学家郭任远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代表了一种绝不妥协的新行为主义支持者”(Griffiths,2004,p.610)。
4 结语
回顾历史,郭任远毕生致力于倡导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心理学。正是在对这种理论信仰的追求之下,郭任远每一次关于本能的思想转变都已经在其整体的认识论图景中被预设了特殊的位置。因此,无论是他早期对本能、遗传、意识、目的论等概念的持续的理论批判(陈巍 等,2021),抑或是后期对猫捉老鼠(王勇 等,2023)、动物搏斗(胡烨 等,2022),以及鸡胚胎发育的系统的实验研究(Wang et al.,2023),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在忠实地践行行为主义的历史使命。尽管现实处境如此不堪,晚年的郭任远仍在毕生积累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为行为的发生发展指明了认识论上的方向——行为渐成论(behavioral epigenesist theory)。其中,行为渐成的概念被郭任远定义为“从受精到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包括增殖、多样化和行为模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改变,这是发育中的生物体与其环境(内源性和外源性)之间持续动态的能量交换的结果”(Kuo,1967,p.11)。在郭任远(1967)建构的理论框架中,行为研究将成为一门包含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比较生理学(在生理物理和生化意义上)、实验形态学以及对生物体与外部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在内的真正的综合科学(synthetic science)。同时,它也将成为协调的,多层次的,跨物种的综合发展研究。为此,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任远仍在呼吁“建立一个大型研究中心,由各科学学科的专家……可以制定一个共同的发展计划,并集中精力,从不同的角度解决同样的问题”(Kuo,1970,p.191)。
历史证明,郭任远激进的行为主义思想,只不过是他作为“超华生”的胎动而已,其分娩、成长、成熟的阵痛与坚韧,或仍湮灭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但却无损其历史地位——“郭任远的写作跨越了大约50年(1921-1970),从1921年具有开辟性意义的重要论文《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开始,到1967年同样重要的著作《行为发展之动力形成论》结束。他剩下的33篇论文可以被看作是直接从1921年首次提出的建议和想法出发的具体步骤,并被详细阐述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系统性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一”(Greenberg &Partridge,2000,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