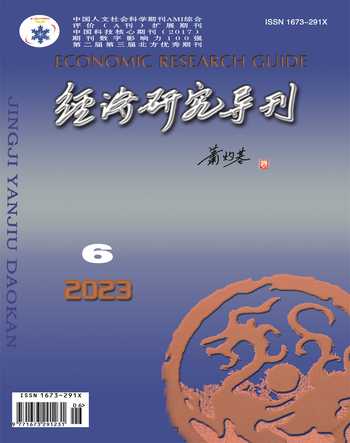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应用
郝彩霞
摘 要:科技与法律的相互摩擦推动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滞后性、科技的前沿性,科技与法律之间的碰撞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利用智能工具对证据种类是否能够进入诉讼程序阶段判定,是我国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与时代发展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按照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收集、提取、保全以及审查判断的纵向发展过程,不同证据准入阶段面临着与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相冲突以及证据标准、证明标准能否算法化问题。同样,社会中间的资本力量也影响着证据形成过程中的算法权力,自然而然会导致算法权力的异化。为了化解以上出现的矛盾,科学化进行案件事实认定,司法工作者们除了进行“理性主义”的思考外,也要适当进行“经验”上的补充,政法决策层也要对辅助司法的智能技术进行内外管理,以保证司法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数字时代;证据制度变革;证据推理;事实认定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6-0151-03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通过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规定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实现诉讼全流程线上化,并确定了区块链存证的效力。这意味着我国司法领域迈入在线訴讼的进程,充分实现了技术赋能司法的作用。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在符合在线诉讼规则所规定的网上办案条件基础之上,诉讼流程的线上化和网上化,对基于传统物理空间中当事人之间对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的流程产生一定的冲击。在网上办案过程中,承载着案件发生信息的证据必须上传至互联网平台,在这种传统证据电子化,电子证据结构化的网上上传证据的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形态多样的变化,现行法律规定的封闭式证据分类体系[1],在技术变革催生法律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了不适应。
最开始的“科技+司法”主要体现在类案、关联法条的推送、利用大数据进行定罪量刑,以及设计案件偏离度来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监督,限制其自由裁量的权力。以上科技的运用并没有嵌入到诉讼阶段或者法庭审理中,但随着技术的成熟,人工智能慢慢从问题求解发展到机器学习和对人类经验的模拟上。在司法科技化改革的浪潮中应当明确的是,人工智能在整个刑事案件,分析证明过程中,我们应对人工智能秉持着辅助性、有限性、可反驳的原则,避免成为技术的奴隶。
二、数字时代智能化对证据制度的机遇与挑战
(一)技术在事实认定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技术就开始服务于电子政务的建设。如今,传统的把纸质文件、线下签章等电子化工作已经基本建设完成,电子政务的建设必须再做升级,而目前普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各单位机构之间的数据通道打通,真正提升办事效率。数字化时代中数字治理已成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主要抓手,提高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电子政务的建设已基本实现信息的全覆盖,因而数字时代势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
司法人工智能受到市场逻辑的利益驱动以及政法决策层对于人工智能正面态度的双重驱动下[2],“人工智能+法律”的模式开始在实践中运行,人工智能也从早期的问题求解、专家系统发展到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人类思考的模拟等方面。无论是从人工智能现有技术发展阶段来说,还是对诉讼各阶段中的法律条文对人工智能内置程序代码化和算法化等存在的风险性而言,都应当始终秉持着有限、可反驳的原则来对待人工智能。因为机器不能替代人类,法律不是僵化的条文和生硬的程序指令,也并非是从吸取的海量数据中就能够完整诠释司法案件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二)数字时代司法观是追求高效率还是公平
科技革命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大数据治理中,人们常说我们是在用人们的隐私权利来换取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的便利,我们歌颂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但问题的来源往往出自技术的身上。在以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器劳动为特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早期生产阶段的现实条件,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中,“劳动”已经不再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技术革命的发展,价值增长不仅仅通过传统的耗费体力的劳动,更在于通过知识实现的价值增长[3]。互联网革命带来数据信息的互通,数据在数字时代毋庸置疑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基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数字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数字时代的司法观念已经逐渐从重视公平得出的实体结果,转变为以提高程序效率的同时,也注重公平的双重司法观念,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分工、社会体制的变化给司法领域带来了用技术赋予司法新使命的春风。对于利用技术在司法领域实现高效率的判案方式的同时,要理性认识科技带来的挑战,避免成为技术的奴隶。
三、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理论争议
(一)智能证据分类的程序准入问题
在提升政法综治工作智能水平时代背景下,构建证据种类准入的信息平台应运而生,势必催生出全新的证据类型,利用智能工具对证据种类是否能够进入诉讼程序阶段判定,是我国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与时代发展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种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以至于随着时代发展,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已经不能满足于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惑——大数据、算法生成提取的信息能否作为证据?
有学者认为,基于大数据的思维、方法、技术等复合型因素,且目前刑事司法从“打击犯罪”转向“预防犯罪”的价值导向,同时由于大数据能够根据个体之间的行为规律理论来对海量信息进行提取和比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与真实性,因此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较为妥当[4]。也有学者认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涉及法律推理、价值判断、法律解释的从事实发现到证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事实认定者需要充分运用司法裁判者自身的理性、经验和良知,因此,大数据分析只是事实认定的一种手段[5]。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技术不仅仅只有大数据还有其使程序运行的算法。有学者提出,利用算法对数据进行抓取、提炼、自动推理所形成的的材料,也应当成为一种独立的算法证据[6]。在电子数据还没有被列入法定种类之前,司法实践中是将电子数据转化为其他合法证据种类的。同样,在法律还没有对其进行合法规定之前,也可以将大数据证据、算法证据解释为电子数据或者鉴定意见。因此,有学者总结认为时代发展出来的各类技术性证据与法定证据种类不适用的难题,可通过三个阶段逐渐进行。“第一阶段为将大数据证据视为鉴定意见,第二阶段为将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三阶段为放弃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7]综上所述,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生成的信息还不能成为法定证据种类时,使用技术对其进行程序分类时应当如何界定呢?
(二)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的算法化问题
关于统一证据标准,孟建柱同志曾提出“要通过强化大数据深度应用,把统一的证据标准镶嵌到数据化的程序之中”。有学者指出,统一证据标准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现行法定证明标准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刑事诉讼阶段的统一性以及证明标准的价值理想化等问题[8]。关于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之间异同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证据标准属于证明标准的下位概念[9],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证据标准其基本属性是“程序准入”,对于证据的证明力或者证据价值问题不予以代码化和量化[10]。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中,第一项涉及证据的收集、提取和保全问题,第二项和第三项涉及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对于前者,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性较少,而后者除了对证据进行印证、逻辑推理之外还要进行情感、道德、价值的判断。概言之,对于证据要求包括“量”和“质”的双重要求,“质”主要体现在证据规则指引、单一证据校验、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量”主要体现为证据之间的系统化罗列和分类、证据模型的构建。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是通过机器的深度自主学习,以逻辑符号和公式进行输入,转换为“0”和“1”的计算机语言,对于证明标准难以算法化,即使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将人类的经验、推理方法自动生成可被识别的特征量,但在经验中还存在着偏见、歧视和刻板印象,而这些经验是不能够被用于证据判断的。
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更好解放生产力。秉持算法技术的辅助性原则,以算法和数据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降低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规范简单化的证据收集流程等方面发挥其作用,也可以更好地辅助司法裁判者进行判案。
(三)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权力异化问题
任何技术的使用必然会体现其使用者或者设计者的主观判断,技术本身的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解放生产力。同理,无论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犯罪进行预测,还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中嵌入案件偏离度分析,都是为了提高司法的准确性。但是,技术本身的中立性与使用者带有的主观意图之间天然地存在矛盾,也就必然地催生出了对于技术的不信任。比如,带有使用者、设计者主观价值判断的算法歧视,专业编写程序复杂化而无法将程序公开透明的算法黑箱,资本力量推动下的信息茧房等等。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算法权力,正是指背后潜藏着的控制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资本权力,而技术权力只是表征而已。面对算法权力可能会导致的社会风险,学界中存在着“唯主观论”和“唯客观论”两种声音。唯主观论者认为,算法的背后是人,首先是人设计了算法,其次是由人掌握着算法的具体功能和应用场景。唯客观论则认为,即便算法是由人进行主导,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也会发生人不可控的风险[11]。因此,在事实认定层面,算法利用其机器优势和架构优势,逐渐超出工具化的属性,在调配资源等方面逐渐作出实质性的决策。
四、数字时代背景下证据制度的理念反思
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由模糊、简单的立法条文到具体的制度改革的变迁,其中以诉讼制度转型和错案追究制度为基础的司法需求是促进证据制度改革的动因。在过去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办案人员漠视证据规则、没有证据意识导致的错案频发,降低了司法公信力,迫使司法机关进行立法回应[12]。
(一)经验与理性相结合的事实认定方式
借助智能工具对证据进行提取和收集是为了更好地辅助司法裁判者,且证明推理的过程是为了保证程序正义。从一个具有盖然性证据本身得到一个被推定出来的案件事实,这个案件事实本身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无论是追求逻辑上的严谨性还是推理过程上的可视化,都是为了保证论点的论证完整性。在科技证据利益强势造成的传统证据理论的冲击情况下,有必要保持理性主义的态度对证据进行证明推理,以及强化裁判者的经验在事实认定中作用。
(二)完善智能技术司法适用的内外管理
在传统的诉讼过程中,裁判者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在自由心证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行证据推理,以此得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为数据化事实认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限制裁判者作出自由心证减少偏见的同时,也造成了裁判者经验知识的贬值。在智能技术应用的内部管理上实行技术优化,在外部管理上对使用人员进行过程管理。
结语
达马斯卡教授在其著作《漂移的证据法》中总结到:“站在20世纪末思考证据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在探讨演进的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那些传统的用人类感官来察觉的事实与用来发掘感官所不能及的世界的辅助工具所揭示的真相之间鸿沟的扩大。”[13]早期的神明裁判、决斗、免于处罚的方式使得用来认定事实的主要方法并不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证据制度,同时期哲学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证据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发展到现在,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事实认定的科学化,在拓展人类认知能力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同时也要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制度问题进行观念和行动上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龙宗智.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J].法学研究,2005,(5):10.
[2] 钱大军.司法人工智能的中国进程:功能替代与结构强化[J].法学评论,2018,(5):15.
[3] 强世功.法理学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J].中国法学,1994,(4):9.
[4] 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可行性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6):8.
[5] 周蔚.大数据在事实认定中作用机制分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6):19.
[6] 杨继文.算法证据:作为证据的算法及其适用规则前瞻[J].地方立法研究,2022,(7).
[7] 郑飞,马国洋.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2.
[8] 蔡国胜.刑事证据标准指引的缘起,发展与功能[J].山东社会科学,2021,(9):7.
[9] 刘品新,陈丽.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2):15.
[10] 崔永存.刑事证据标准数字化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7.
[11] 周辉.算法权力及其规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6):14.
[12] 吴洪淇.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基本逻辑以1996—2017年我国刑事证据规范为考察对象[J].中外法学,2018,(1):19.
[13] 米爾建·R·达马斯卡,Mirjan R.Damaska.漂移的证据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