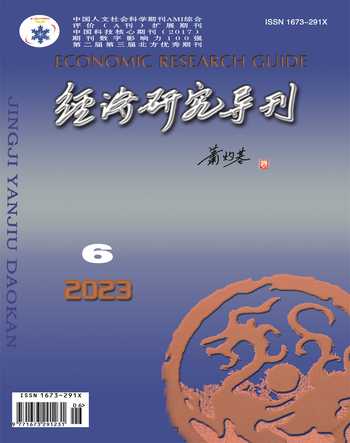论我国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郁华
摘 要:我国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机制尚未健全,破产程序未被充分利用,距离彻底解决执行积案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存在移送审查标准模糊、缺少简易衔接程序、相关费用衔接不畅等实践操作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应从移送的审查标准、简易衔接程序、执行费用的清偿三个方面对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进行完善,从而对提高程序衔接的适用率、优化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机制、改善社会对破产程序的接纳能力、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事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程序隔阂
中图分类号:DF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6-0154-04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以下简称“执转破”)是解决我国“执行难”问题的特有法律制度,自正式出现至今已有8年多。其重要作用之一是为执行不能积案提供退出路径。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已经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2019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中亦强调,需要重视执行和破产程序的衔接,打破执行案件转入破产重整、和解或清算程序之间的程序隔阂。实践中,为提升衔接程序的使用率,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在办理执转破案件过程中被赋予释明权。但实践证明尚未产生良好效果,办案人员在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后,当事人启动衔接程序的意愿仍然较低。
一、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概念
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建立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之上。目前我国仅有企业破产法,因此程序衔接启动的主体是企业法人,而不包括公民和其他组织。另外,民事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都是强制还债程序,在解决债权债务关系方面可以优势互补,二者的顺利衔接是执转破制度发挥活力的关键。两个程序衔接的前提是有已经生效且进入执行程序的法律文书,适格主体是资不抵债、丧失偿债能力的债务人,发生事由是存在债务人执行不能的事实。债务人非故意不履行义务,且已不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通过当事人申请来启动执转破程序。由此,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可以定义为:生效裁判文书执行过程中或清偿期已届满时,债务人执行不能,法院依申请将案件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法律程序[1]。
二、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困境
(一)移送审查标准模糊
关于执行案件移送审查的标准,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7年《指导意见》)具体规定了三个要件:被执行的主体是企业法人,相关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被执行人丧失清偿能力。理论上,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案件,除债务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老赖”执行难情形外,大部分便是执行不能的情况,后者一定程度上已经符合破产的条件,因此执转破的条件与我国《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条件具有高度相似性[2]。然而,执转破和破产程序当下的共同困境是启动难,规则的模糊性导致法院在审查时缺乏可操作性的依据。
直到目前我国仍未形成统一的具体审查标准,这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在某些地区执行法院作为负责将裁判结果执行到位的法律单位,其本身不具备审判业务人员,而审查适用破产程序案件对法官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因此,在执行案件数量庞大的背景下,本就缺乏专业经验的执行法官在有限时间内难以确定案件的具体属性,加之缺乏具體操作规范和审查标准,进一步加大了其工作难度。另一方面,一些试点地区的地方法院在2017年《指导意见》的指导下尝试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审查执转破案件审查规范。例如,浙江省高院要求的审查标准是:执行法院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同时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提下,决定是否适用程序衔接;广东省高院在同浙江省高院相同要求基础上,还要求债务人能够支付破产费用等。这些具体规定明确了本地执行法官判断案件是否进入“执转破”的标准,其各自的实践也为我国制定较为详细的审查标准提供了借鉴。但是各种标准中细微的差距往往会导致一个地区程序衔接工作的好与坏,从而造成全国各地之间实践差距较大,不利于涉及多个区域的案件审查工作,对债务人影响尤其重大。
(二)缺少简易衔接程序
案件的繁简分流是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方法。破产程序在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中扮演着解决债权债务关系的主角。破产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率不高,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作为将案件引入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也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其中包含各方主体对破产程序的“回避”心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作为法律和经济的融合,破产程序本身具有复杂性。在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种破产程序中,无论选择哪种都会经历时长至少半年的审理期。以破产清算为例,需要经过当事人申请、法院受理和通知,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召开,进入破产清算,债权人受偿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兼顾法律公平和社会影响,处理好法院裁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3]。第二,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对法官的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理想状态下破产案件审判周期都需要至少半年之久,而破产案件往往包含着复杂的经济问题,在具体审理时,又会涉及债权人债权、股东权利、企业职工安置、债务人人权保障等社会问题。在司法资源向执行程序严重倾斜现状下,破产审判队伍的人才供给和专业化程度都有所欠缺,加之法官本身的畏难情绪,便难免出现能拖则拖、当断不断的情况,降低了审判的效率。而且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长期以往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前述两点是基于破产案件案情较为复杂的前提下对破产程序复杂性阻碍执破衔接程序的论述。那么,在案情较简单明晰时,一般破产程序的审判效率是否会提高?答案应是否定的。由于破产程序只有单一的普通审判程序,没有简易程序,因此无论案情繁简,一律按照同样的流程审理。一方面,法官必须按照既定的复杂流程进行操作;另一方面,当事人以简单案情适用复杂流程而不能尽快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存在财产因时间久而减损的风险。因此,简单破产案件适用一般破产程序性价比低下。鉴于此,一些地方法院对简易程序进行了探索。但放眼全国,仍需要国家制定统一且具体的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并将其纳入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
(三)相关费用衔接不畅
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中的费用问题不仅关系到债务人可偿还债务的多少,还会对权力机关能否推进程序运转产生影响。“费用难题”主要集中在申请执行费用和费用的清偿顺位及金额上。2017年《指导意见》第15条是对执转破相关费用衔接的规定,但仅规定了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等项目,尚未提及申请执行费用的清偿方法。申请执行费用在执行程序中由债务人承担,但启动程序衔接机制后应当在执行中还是破产中清偿、清偿的顺位以及清偿的金额如何均无依据,各地法院的实践也有较大差异。
对清偿的阶段,大多数法院在启动执转破之后将申请执行费用并入破产程序中,作为一种债权或费用向执行法院清偿,方法主要是在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中予以保留或扣除。但是申请执行费用的清偿顺位在实践中呈现多样化和随意性,若不及时作出统一规定,将会在实践中引发当事人不满。现有清偿顺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债务人有一部分可供执行的财产之后,执行法院或破产法院从这一部分财产中先行扣除,是一种变相的优先清偿。二是视申请执行人获得债权的紧迫性而定。例如,申请执行人待实现的债权是其基本生活保障的费用或因某些紧急情况而迫切需要实现债权,此时法院在申请执行费用的清偿顺序上进行让步,优先解决当事人的迫切期待,灵活处理清偿申请执行费用。但实践中不能保证执行法院或破产法院对该种情况完全把握,在没有硬性规定的情况下难免出现法院为尽快结清申请执行费用、保证自身运转资金的充裕而不考虑当事人现实情况的可能。
在清偿金额方面,因2017年《指导意见》规定的缺漏,导致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执行法院最直接的做法是按照申请执行人申请的标的额来确认申请执行费用,但需要考虑到,当案件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后,民事执行程序尚未完成申请执行人期待的任务,其又已经被破产程序吸收,如果让被执行人同时承担申请执行费用和破产费用,将导致被执行人财产减损,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显失公平。实践中还存在的一种做法是按已经执行到位的款项和申请执行金额的比例进行执行费用的清偿,此种做法实际上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4]。无论如何,在执转破相关规定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各地法院仅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小心试探,而这种试探的代价可能是同案不同判、是以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为代价的。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对策
(一)明确移送的审查标准
现有审查标准的抽象化和多样化,使涉及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案件移送工作遇到障碍,法官在开展工作时无从下手。所以,应当确立和细化可操作性的程序衔接案件移送审查标准,具体可以分为执行法院和破产法院的审查标准。
执行法院移送程序衔接案件的审查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适用程序衔接的案件首先应当符合被执行人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即案件已执行不能。该细化实质上是对执行不能案件认定标准的把握,需要严格考察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已穷尽财产調查手段且已经采取强制措施,在法官内心达到确定被执行人已经没有清偿能力的标准。这在与对老赖“执行难”案件的对比下会显得格外清晰。若被执行人在受到强制措施的约束后依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此时继续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会限制其经济再生的能力,而且债权人也得不到很好的受偿。第二,被执行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与适用终本程序后法院进行财产复查期限相契合,以三年为宜,必要时可以进行适当缩短;或借鉴目前个人债务清理(类个人破产)中的处理措施,在被执行人所涉案件被定性为执行不能案件后,经执行法院审查后移送破产程序,破产程序中被执行人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后,被执行人接受一定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若债务人经济没有得到好转且无过分消费行为,即对剩余债务进行免责,终结债权债务关系[5]。
破产法院接收案件的审查标准也应当进一步明确,破产法院的审核宜将简单的实质审查和详细的程序审查相结合。一方面,执行人员在将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程序时,因其本身审理破产案件的专业化水平有限,为保证所移送案件确实需要进入破产程序,由破产法院按照破产条件进行简单的实质审查是有必要的。这样既可以保证案件适用破产程序的适当性,又不会因为过于详细的审查而浪费破产法院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程序衔接的精细化操作需要严格的程序规范,案件材料是否齐全事关案件的定性,事关破产法院能否公平处理被执行人的剩余财产、平衡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要进行详细的程序审查。
(二)设立简易的衔接程序
2017年《指导意见》中没有关于审理执转破案件的简易程序。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2018年最高院《破产会议纪要》中提出,我国破产相关立法中需要建立破产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为执转破简易程序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导向。在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视角下,程序衔接简易程序与单纯的破产简易程序有所不同,程序衔接简易程序是破产程序对执行程序成果的吸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民事案件类似,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案件也存在繁简之分,不同之处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有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案情简单、标的额小的案件可以选择这两种高效的诉讼程序,而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以及破产程序只有普通程序,无论案情复杂与否都需要走完整个普通程序,于司法资源而言是一种过度消耗,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涉及金额小的案件当事人来说是诉讼成本的增加,造成各方对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消极态度。程序衔接简易程序则可以起到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审理效率等作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作为个别执行和概括执行,民事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都需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民事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变价处置,可以为后续破产程序中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债务人财产处置方式提供便利,甚至可以省略而直接进行财产分配,这种内在联系使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更为紧密。
具体而言,程序衔接的简易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程序设计。其一,明确程序衔接简易程序的案件适格标准。目前存在以案件金额大小确定和以复合条件确定两种观点,笔者建议采取后者。借鉴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成功实践,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可以从案件标的额、债权人数量、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总额等方面进行界定。此外,当事人合意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也应予以支持。其二,需要缩减程序时间。因为民事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存在功能重合,执行法院确定执行不能后,实际上对债务人财产状况、债权人债权情况已经非常熟悉,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磨合”也已基本形成,此时可以适当压缩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时间和选定破产管理人的时间,适当减少相关公告的次数,加快程序进度[6]。其三,对公告和送达的程序进行简化。传统媒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面临当事人躲避、拒收的窘况,而通过公共媒介、电子媒介、互联网等进行公告和送达能够大大提升效率[7]。其四,根据程序的繁简调整诉讼费用。其五,需要建立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简易程序的救濟机制。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及时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的范畴内进行审理;当当事人认为简易程序损害其权益并有证据能证明时,应当给予其诸如可以提出上诉等救济途径。
(三)细化执行费用的清偿
申请执行费用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数额和清偿顺位,需要根据该“费用”的性质来确定。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申请执行费用的定性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申请执行费用是“费用”,应根据财产状况随时清偿;另一种认为是“债权”,应根据清偿顺位清偿。本文赞同前一种观点。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在交易之时就应当认识到潜在的信用风险。当风险发生时,为了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财产权益问题,公权力机关付出了成本,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为此“买单”,因此双方需要就自己的行为向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公权力机关付出费用,而这种费用优先于其自身权利。
对于费用清偿阶段申请执行费用能否为破产费用所吸收?笔者认为是不能的。在民事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的语境下,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一些成果为破产程序所吸收使用,且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存在一部分已经执行到位的财产,这些属于执行法院已经完成的执行工作。需要考虑到,执行法院和破产法院有时并非同一法院,此时如果破产费用吸收申请执行费用,那么前一执行法院的工作成果便得不到回报。因此,执行法院有资格获得回报,该笔执行费用应当成为案件全部费用中独立的一份,获得随时清偿的资格,但为了清偿的方便,可以与破产费用在最后一同计算。在清偿的金额方面,笔者认为按已经执行到位的款项和申请执行金额的比例进行申请执行费用的清偿更为妥当[8]。
对于费用清偿的顺位,一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获得优先清偿申请执行费用的资格。但当债权人迫切需要该笔费用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时,或者有其他迫切实现债权的事由时,就需要考虑到法院不能掌握全部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迫切性需求,所以可以在此类债权人向法院说明情况后,使申请执行费用的清偿后于该债权人债权的清偿。
参考文献:
[1] 张善斌.破产法研究综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523-524.
[2] 曹守晔,杨悦.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与协调[J].人民司法,2015,(21):23-28.
[3] 郭婧祎.破产程序简化的理论探究[J].求索,2018,(2):129-139.
[4] 王雄飞.执行和破产程序衔接具体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的执破衔接工作实践展开[J].法律适用,2019,(15):98-104.
[5] 王启江.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构下的立审执衔接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9,(11):30-40.
[6] 刘旭东.执破衔接视域下“执转破”要点透视及规范进路[J].河北法学,2019,(4):172-184.
[7] 王欣新.以破产法的改革完善应对新冠疫情、提升营商环境[J].法律适用,2020,(15):61-71.
[8] 范志勇.论“执转破”的启动与程序衔接[J].商业研究,2019,(7):143-152.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ivil Execution and Bankruptcy Proceedings in China
Yu Hua
(Beijing Aerospace Automatic Control Institute, Beijing 100854, China)
Abstract: The withdrawal mechanism of the case of inability to execute in China has not been improved, and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has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 goal of completely solving the backlog of execution cases. 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and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such as the vague transfer review standard, the lack of simple connection procedure, and the poor connection of related expenses. Theref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ivil execution and bankruptcy proceeding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review standard of transfer, the simple connection procedure, and the payment of the execution costs, so a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the procedure connection, optimize the withdrawal mechanism of cases that cannot be executed, improve the acceptance ability of the society to the bankruptcy proceedings, and maintain judici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civil execution procedure; insolvency proceedings; procedural estrangement
[责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