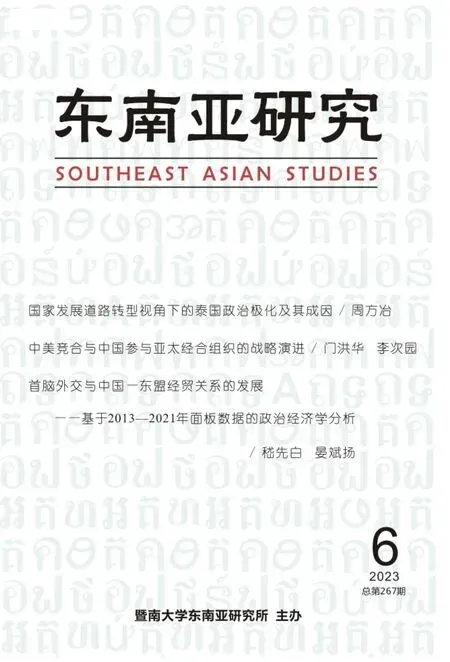庇护网络、多党联盟制与马来西亚“青蛙政治”的迷思
张孝芳 李志涛
2020年2月23日晚,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中的人民公正党阿兹敏派、土著团结党和在野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及伊斯兰党等在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的喜来登酒店举行会议。第二天,阿兹敏即携11名国会议员脱离人民公正党,支持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担任总理(1)Nigel Aw and Zikri Kamarulzaman,“Langkah Sheraton’ bawa Malaysia ke Jalan Buntu:Apa Seterusnya?” Malaysiakini,2020年2月26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353.。执政不到两年的希望联盟(以下简称“希盟”)政府由此倒台。3月1日,慕尤丁宣誓成为马来西亚新任总理。这一事件被外界称为“喜来登政变”。与马来西亚第14届国会选举的“全民海啸”引起的前一次政权更迭相比,这次政权更迭是在没有举行新的大选的情况下经由“青蛙政治”导致的。马来西亚政局长期存在的“青蛙政治”现象由此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议员像青蛙一样“跳槽”的现象并非马来西亚所独有,但其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频发令观察者和分析家咋舌。“青蛙政治”与族群政治被看作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两大困境(2)许利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与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丰富研究成果相比,目前学界对马来西亚“青蛙政治”尚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在“利益+制度”框架下分析马来西亚“青蛙政治”的成因。
一 马来西亚的“青蛙政治”现象
所谓“青蛙政治”,是指议员像青蛙一样从原所属政党跳槽到另一政党,或在独立议员与某个政党成员身份之间转换。这些跳槽议员相应被称为“政治青蛙”。马来西亚独立后,议员跳槽成为马来西亚州一级政治的常态,近年来又在联邦一级政治中频发。在以下时期,“政治青蛙”的跳槽行为更容易取得成功,“青蛙政治”现象也被更多观察到。
首先,当新政权组建时,“政治青蛙”跳槽的情况最为常见。2018年大选后,就有9名国会议员从巫统跳槽到土著团结党(3)《阿末扎希:已是政治伙伴,巫统不再起诉9跳槽土团议员》,《中国报》2020年7月14日,https://www.chinapress.com.my/?p=2113332。国会议员马智礼曾连跳两次,先从土著团结党跳到祖国斗士党,后高调加入人民公正党。第一次跳槽是希盟在国会中没有取得多数而败给国盟之时,第二次跳槽是人民公正党在马六甲州大选失利但取得柔佛州政权之时(4)《马智礼正式加入公正党,安华盛赞为党加入新力量》,当今大马,2021年11月27日,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600907。霹雳州议员西华苏巴马廉也接连跳槽,第一次跳槽即从民主行动党跳至民政党,恰逢希盟政府在霹雳州倒台之时,第二次跳槽即从民政党跳至土著团结党,正值土著团结党在霹雳州执政之时(5)《大马国民党属政治青蛙大联盟 社青团吁选民大选狠狠教训》,《中国报》2022年1月9日,https://www.chinapress.com.my/?p=2815569。
其次,政党联盟或者政党领导层内部产生冲突时也是“政治青蛙”跳槽的重要时机。彭亨州议员韩查惹化曾从国家诚信党跳槽至人民公正党,而后又跳槽至祖国斗士党,这两次跳槽都是在希盟内部安瓦尔和马哈蒂尔内斗之时(6)《傅芝雅:拥有蓝眼斗士党双党籍,韩查曾要求成为候选人》,星洲网,2021年3月1日,https://www.sinchew.com.my/?p=3144114。希盟执政后,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和署理主席阿兹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派在2019年12月人民公正党第14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决裂(7)苏莹莹、翟崑主编《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2-53页。。“喜来登政变”中阿兹敏派的跳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再次,有的“政治青蛙”选择在政党发展的关键时期跳槽。如沙巴民兴党副主席、沙巴州议员彼得·安东尼和州议员朱益努丁于2021年11月28日退出沙巴民兴党成为独立议员,而这正是沙巴民兴党宣布西渡之时(8)“Two Sabah DAP Assemblymen,Exsenator Quit Party”,News Straits Times,Juanuary 21,2022,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2/01/764739/。沙巴民兴党原为东马的本土政党,于2021年宣布将其组织扩展到西马,从而争取发展为全国性政党(9)《沙菲益强调西渡乃集体决定,反抨击安东尼分裂沙人》,当今大马,2021年12月29日,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604926。
“政治青蛙”一旦跳槽,其在国会或者州议会的议员席位相应从原政党转移到另一政党。随着“政治青蛙”的跳槽,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可能会丧失国会下议院或州议会多数的地位。尤其在执政党或执政联盟议席优势不大时,少数议席的改变往往可以改变议会中的多数派,此时在野党或在野党联盟如获得这些“政治青蛙”带来的议席,就会推翻现任政府,组建新一届政府。因此,“政治青蛙”的跳槽经常伴随着政权的更替。
在州层面,马来西亚州政府在非选举期所发生的更替基本都是“青蛙政治”的产物。1961年登嘉楼州议会议员跳槽引起该州政权更替,是马来西亚议员跳槽导致的首次政权更迭。1967年,在沙巴州政府组建过程中,两名州议会议员跳槽使该州单一政党组阁成功(10)许利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近年来,“青蛙政治”引起的政权更替在沙巴州、霹雳州、柔佛州、马六甲州等州接连发生。2018年沙巴州议会选举后,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获得29席,希盟和合作伙伴沙巴民兴党也获得29席,沙立新党获得2席。国阵迅速与沙立新党合作组建了新一届州政府。但在第二天,由于沙巴州巫统的四名议员和民统党的两名议员宣布跳槽至沙巴民兴党,这届政府成立不到48小时就宣布倒台,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宣布就任沙巴州首席部长并组建新一届州政府(11)《鹿死谁手 还看明朝》,《星洲日报》2020年9月25日,https://www.chinapress.com.my/?p=2206261。2020年2月“喜来登政变”后,随着土著团结党退出希盟,柔佛州的执政联盟希盟仅剩28席,而土著团结党、伊斯兰党和国阵同样有28席。由于州议员张发虎退出人民公正党,以独立议员身份支持由土著团结党、伊斯兰党和国阵组成的新联盟,使新联盟以29席对27席的简单多数执政(12)《柔州政局变荡 两年三任大臣》,《东方日报》2022年1月22日,http://xby.52hrtt.com/global/n/w/info/A1642394219694。2021年10月4日,巫统成员依德利斯哈仑和诺阿兹曼、土著团结党成员诺芬依迪和无党籍的诺依占作为马六甲州议员宣布撤回对马六甲州的行政首长的支持,导致马六甲州国民联盟政府倒台(13)《为政治青蛙正名》,《光华日报》2021年11月7日,https://www.kwongwah.com.my/20211107,其中依德利斯哈仑跳槽至希盟中的人民公正党,诺阿兹曼则跳槽至希盟中的国家诚信党(14)“Will DAP Endorse 2 Umno Reps Contesting under PH?”,New Straits Times,November 7,2021,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1/11/743244。
在联邦层面,由于以巫统为核心的马华印联盟及后来的国阵自马来西亚独立至第14届国会选举之前的历次大选中都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席,在第12届国会选举前更是拥有对联邦议会2/3 议席的控制权,“青蛙政治”对联邦政府组建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第14届国会选举即2018年大选后,在朝野议席接近的情况下,“青蛙政治”造成了联邦政府的更迭。11名人民公正党阿兹敏派的国会议员在“喜来登政变”后成为独立议员,之后其中10名议员加入土著团结党,1名议员加入砂捞越全民团结党。议员的跳槽不仅推翻了现在的政府,而且影响了新政府的组成。比如,山达拉代表人民公正党在昔加末区参加2018年大选,以5476多数票击败时任印度人国大党主席苏伯马廉获得该选区国会议员议席。2020年“喜来登政变”中,山达拉跟随阿兹敏退出人民公正党,之后加入土著团结党,并先后出任了慕尤丁政府的联邦直辖区副部长和伊斯梅尔·萨布里政府的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15)《4年政绩有目共睹,山达拉:党应我再战昔加末》,星洲网,2022年11月1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4203816。
尽管议员跳槽并非马来西亚独有的政治现象,但其在马来西亚造成政权更迭的次数非其他国家可比。因此,马来西亚的“青蛙政治”现象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采用“利益+制度”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马来西亚“青蛙政治”的成因。一方面,马来西亚以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为议员跳槽提供了利益激励。议员之所以跳槽,首先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在以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中,政党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和经济资源。不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具有不同的庇护网络,这就使议员有可能产生改换门庭的意愿。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多党联盟制为议员跳槽提供了制度便利。相对于两党制,多党联盟制下议员跳槽的对象有了更多的选择,跳槽行为也更容易成功。因此,多党联盟制为议员跳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窗口”。有意思的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和多党联盟制虽然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但却是马来西亚与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使马来西亚的“青蛙政治”现象最为突出。
二 以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青蛙政治”的利益基础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都盛行庇护主义。尽管菲律宾、印尼等国议员跳槽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但马来西亚的“青蛙政治”尤为突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庇护主义的形式不同。菲律宾的庇护网络以地方家族为中心,印尼的庇护网络以临时团队为中心(16)Edward Aspinall and Allen Hicken,“Guns for Hire and Enduring Machines:Clientelism beyond Parties in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Democratization,Vol.27,No.1,2020,pp.137-156.,而马来西亚的庇护网络以政党为中心。正如爱德华·阿斯平等学者在《选举动员:东南亚的恩庇与政治机器》一书中指出的:“相比之下,在马来西亚,政治家向个人选民分发现金或其他礼物的频率要低得多。与印尼或菲律宾的同行相比,他们也不太可能依靠自己的个人资金来承担他们的恩庇策略。恩庇政治在马来西亚仍然普遍存在;只是将选民与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恩惠都是政府或政党的施舍,而不是私人或个人礼物。”(17)Edward Aspinall,Meredith L. Weiss,Allen Hicken and Paul D. Hutchcroft,Mobilizing for Elections:Patronage and Political Machines in Southeast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2,p.4.在马来西亚,议员在政党之间跳槽之所以能给其带来收益,是因为其所处的庇护网络是由政党而非其他行为体所塑造的。在这种庇护网络中,政党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大批精英通过对政党领袖的支持来换取分享这些资源的机会。
(一)马来西亚庇护主义的历史起源
在沦为殖民地之前,马来西亚的庇护体系主要基于当地的文化传统运作。在这个地区经过和定居的不同人群通常会寻求庇护以躲避迫害、战争、饥荒或其他不稳定的情况。他们可以向当地的宗教领袖、村长或族长等权威人物寻求庇护。这些权威人物会提供被庇护者所需的保护、食物、住所以及其他基本需求。例如,在文莱帝国和苏禄苏丹国时代的沙巴和砂捞越,苏丹授予当地酋长权力来管理他们的领地和居民,酋长向臣民提供安全保护和食物,反过来臣民要保持对酋长的忠心和支持(18)Ivy Jugah and Arnold Puyok,“Political Patronage in Election:Impacts of the Coalition Change in Malaysian Federal Government on Sarawak’s Politics”,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Sembilan,Malaysia,October 27,2021,p.698.。
在沦为殖民地之后,马来西亚的庇护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殖民者的入侵和统治导致了这一地区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塑,庇护关系从基于文化传统转变为更加官方化的体系。首先,庇护对象为效忠殖民者的地方领导人。为了削弱当地的抵抗力量,殖民者有意分化当地社会精英。殖民者为服从殖民统治的酋长或宗教领袖提供庇护,从而培养忠诚于殖民者的地方领导人(19)Pawel Gliniak,“From Colonial Capitalism to Crony Capitalism: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Socio-Economic Model from the Malaysian Perspective”,Skhid,Vol.2,No.2,2021,p.7.。这些地方领导人通常基于殖民者的信任并在殖民者的指导下行使权力。其次,利用土地和资源实现庇护。殖民者通过控制土地和资源来控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们将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特权给予那些他们青睐的人选,从而稳固殖民统治(20)Johan Khasnor,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alay Administrative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60.。再次,继续利用地方领导人的象征性作用,保留原有的庇护关系。殖民者有时会组织象征性的仪式,并让酋长成为仪式的代表,从而向当地人传达殖民者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随着殖民者的撤退,殖民者将权力移交给了马来土著精英,庇护文化也得以延续。
(二)巫统的庇护网络
作为马来西亚主体族群,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就一直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以马来人为基础的巫统充分利用其长期执政的优势扶持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马来资本家,从而建立了以执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
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来人虽然自称“国家的主人”,但是在经济方面并不如华人和外国人。比如,马来人在1958年拥有8.9万家注册企业中的10%,占注册资本的1.5%,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4%,大量的资本由外国人和华人掌握(21)Lim Mah Hui,“Contradi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 Capital:State,Accumulation and Legitim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15,No.1,1985,p.60.。这样就引起了马来人的不满,他们开始尝试掌握经济方面的主导权。自1966年起,两大政府机构——人民信托委员会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开始培养小规模的马来土著企业。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赋予马来人许多特权,包括参与政府项目上的特权,一个关键的目标是将马来人在全国公司中的股权占比提高到30%以上(22)许红艳:《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93页。。在新经济政策下,巫统通过实施特殊招聘准则、在政府招标中优先土著客户、建立政府投资公司以支持土著公司和创建政府拥有的政府关联公司(GLC)来培养土著企业家。与此同时,巫统通过发行仅限于土著购买的打折股票和高利润的单位信托,培养普通马来人参与金融行业(23)Thoma Pepinsky,“Autocracy,Elections,and Fiscal Policy:Evidence from Malaysi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2,No.1-2,2007,p.146.。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产生了大量的马来人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不仅在企业中身居高位,而且和政府高层关系密切。
在新经济政策下,旨在保障马来人特权的国有企业很快就涉足核心部门,如运输、通讯、公用事业、能源和金融等,并向其他部门扩展,如建筑、制造业和服务业。政府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建立国库控股公司,或者通过购买以前的私人种植园和矿业公司的股票将其转变为国有企业或政府关联公司。1965年,马来西亚只有54家国有企业,但到1985年,国有企业总数达到1010家(24)Edmund Terence Gomez ed.,State of Malaysia,New York:Routledge,2004,p.195.。这些国有企业往往由政治家通过代理人拥有。在这样的庇护网络之下,到1995年,几乎20%的巫统部门主管是百万富翁。2006年,在马来西亚排名前50位的公司中,政府关联公司占总数的44%,占总市值的28.24%(25)M. Shahid Ebrahim,Sourafel Girma,Jonathan Williams and M. Eskandar Shah,“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atronage:The Case of Malaysi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Vol.31,2014,p.125.。这些政府关联公司成为巫统用来提高马来人地位的工具,同时也是巫统向被庇护者输送利益的渠道。时任巫统主席、总理纳吉布设立的“一个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简称“一马公司”),被看作是纳吉布及其追随者的提款机。2015年7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一马公司”有7亿美元资产流入纳吉布的个人账户。尽管马来西亚反腐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这7亿美元资产是政治献金”(26)吴宗玉、翟崑主编《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7页。,但这仍反映了巫统盘根错节的庇护网络。
1983年马哈蒂尔首次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马来西亚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大量巫统控股的企业被出卖给名义上巫统以外的商业精英,但这些商业精英大多都是和巫统高层私交甚好的马来人。私有化之后,巫统仍然靠着“独家开发权”来维护其庇护网络。例如,旨在吸引外国投资的巴生港自由贸易区(PKFTZ)项目最初由巴生港务局于1999年与私人合作伙伴合资。这些私人合作伙伴不仅获得了政府对该项目的独家开发权,而且没有参与任何竞争性招标。问题在于,PKFTZ以过高的价格购买了该项目的土地(大约每平方英尺25令吉,而将土地出售给PKFTZ的公司早前购得该土地的价格仅为每平方英尺3令吉),而这些私人合作伙伴的股东正是执政党中的资深政治家(27)Loo-See Beh,“Development and Distortion of Malaysia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atronage,Privatised Profits and Pitfalls”,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9,No.S1,2010,pp.S74-S84.。
此外,巫统主导的联邦政府对非马来人私营企业的相关限制导致华人企业在当地和全国的马来人政客、官僚和商人中寻求庇护。这就产生了所谓的“阿里巴巴”(Ali-Baba)非正式制度安排,即非土著商人(“巴巴”)通过分包或购买政府给予马来人(“阿里”)的权利获得商业机会。通过对社区的投资或对竞选活动的赞助,这些享有特权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将赚取的部分收入或租金缴纳给了他们的庇护人(28)Rabia Naguib and Joseph Smucker,“When Economic Growth Rhymes with Social Development:The Malaysia Experienc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89,2009,p.102.。
简言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以巫统为中心的庇护网络走向了制度化。为了从华人手中夺回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巫统积极培育国有企业和马来人企业家。巫统与国有企业和马来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既保障了马来人的特权,又让巫统获得了经济支持,从而维护了其执政地位。巫统通过庇护网络将资源输送给庇护对象,从而换取被庇护者对巫统的忠诚。
第一,巫统高层获得大量政府职务和经济收益。巫统在国阵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因此巫统主席也是国阵最高理事会主席和联邦政府总理。在各部部长人选上,巫统会将内政、国防、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分给党内高层,军队和警察的最高领导权也由马来人掌握。同时,巫统通常也会将执政州的州国阵主席即该州巫统主席任命为首席部长。政府高级职位的分配可以让巫统高层掌控政府的大多数核心权力部门,从而赢得这些高层对于巫统的忠心。除了政治职务,巫统高层还会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比如巫统的理事会成员会获得国有企业或者政府关联企业的股份和分红,也会获得马来资本家的巨额“政治献金”。前首相慕尤丁就被指控获得马来大亨赛莫达2亿3250万令吉的贿赂(29)《赛莫达罕见发文告“不想与政党扯上关系”》,星洲网,2023年3月18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4549104。此外,巫统高层的亲属也会被安排进国有企业和政府关联企业担任高管。
第二,通过发放选区发展基金和安排发展项目来庇护选民。几乎所有在职议员或有意成为议员的巫统成员都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这是他们与选民联系和互动的关键场所。拥有选区发展基金(也称为“拨款”)的巫统成员通常为其服务中心的费用(场地租金、工作人员工资等)提供资金。但国阵控制的联邦政府并没有给反对党议员拨款,而是将拨款分配给那些所在选区未胜选的国阵协调员。这些服务中心便于选民了解巫统,也便于巫统深入到选民之中宣传自身的优势和政策,解决选民的日常困难。以发展项目(如医院、桥梁和大学)的形式提供的恩庇,使选民认为政府对经济管理得很好,如果他们投票给反对党,就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可能会更糟(30)Sri Murniati,“Elite Feuds,Patronage and Factions:UMNO’s Demise”,in Edmund Gomez and Mohamed Osman eds.,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Intra-Elite Feuding in the Pursuit of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19,p.67.。通过这样的方式,巫统向大量选民提供庇护,从而换取他们手中的选票。
第三,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庇护企业和资本家。为了获得有效的经济资源支持,巫统控制的联邦政府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和资本家的庇护。大批马来人商业精英获得了相关领域的经营权,如涉足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的瑞农公司董事总经理哈利姆·萨阿德,以及涉足交通和通信行业的马来西亚航空董事长塔朱丁·拉姆利。旺阿兹米·旺哈姆扎、阿明·沙阿和纳吉布的儿子莫扎尼分别在房地产开发、港口设施和航运领域中获得经营权(31)William Case,“Malaysia:New Reforms,Old Continuities,Tense Ambiguities”,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1,No.2,2005,p.291.。在沙巴州和砂捞越州,木材砍伐许可证成为了国阵政府实现政治庇护的重要手段。
(三)反对党的庇护网络
和巫统一样,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等长期在野的政党也通过建立庇护网络来获取选民的支持。但作为反对党,它们不能像执政党一样直接利用国家资源来建立和维护庇护关系,因此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和“草根融资”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首先,反对党不能像执政党一样,通过政府的各级组织深入到每个选区,用资源来换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它选择了非政府组织来填补“空白”。在竞选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在阐明反对派的愿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向反对党推荐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并通过抗议、媒体宣传等活动提高竞选的热度,为反对党赢得了大量的支持。
反对党可以通过与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来获得支持,从而建立庇护关系。例如,华人非政府组织北婆罗洲华人协会在马来半岛的每个城镇都有分支机构,它首先在1953年与马华公会结盟,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与民政党结盟,1987年后一直与民主行动党结盟,致力于赢得华人的选票来推翻国阵的统治。这样的合作模式让反对党依靠非政府组织的经纪人或混合经纪人,使议员扎根于基层,其中经纪人代表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并与政党谈判合作事宜,混合经纪人则既忠于某一非政府组织又忠于某一政党,致力于在该组织与该政党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32)Meredith L.Weiss,“Duelling Networks:Relational Clientelism in Electoral-Authoritarian Malaysia”,Democratization,Vol.27,No.1,2020,p.106.。因此,反对党通过对非政府组织经纪人的庇护来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除了与现有非政府组织合作外,反对党也会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如1998年9月反对党成立了两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和马来西亚人民争取正义运动,以动员选民(33)Meredith L.Weiss,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8.。这些非政府组织与反对党建立了牢固的庇护关系。当反对党夺得州政权时,会将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任命为政治秘书或者地方议员,从而促进他们为政党服务(34)Meredith L. Weiss,“Going to the Ground (or AstroTurf):A Grassroots View of Regime Resilience”,Democratization,Vol.24,No.2,2017,p.277.。反对党也会将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吸纳进政党高层或者推为国会或者州议会议员候选人,如人民公正党将人权活动家黄庭、西华拉沙、沈子欣和蔡田等推为人民公正党议员候选人,并全力助其获胜(35)Meredith L.Weiss,“Edging toward a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Civil Society at the Gate?”,Asian Survey,Vol.49,No.5,2009,p.755.。
其次,反对党主要通过“草根融资”获得资源,如会员费、活动门票、捐款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维持政党与“草根”之间的庇护关系。以民主行动党为例,该党领导人声称,其党务运作和竞选活动的资金主要通过“草根融资”获得,即会员费和个人捐款。同时该党也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筹款活动筹集资金,包括举办公共论坛讨论热门话题等。此外,当选为州议员或国会议员的成员要向政党贡献他们津贴的一部分,从而构成党费的另一个来源。该党的商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出售《火箭报》(TheRocket)的收入(36)Edmund Gomez,“Monetizing Politics:Financing Parties and Eections in Malaysia”,Modern Asian Studies,Vol.46,No.5,2012,p.1383.。总之,“草根融资”既保证了政党获取相应的资金来源,又增强了政党和成员之间的关系。
尽管与执政党相比,反对党比较“穷”,但基于“草根融资”,反对党也可以通过捐助建立庇护关系。例如,针对沙巴和砂捞越的非马来土著选民,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近年来推行了由马来半岛与教会有联系的捐助者资助的微型发展项目(供水、电力、道路等),同时特别制定了创造性的福利援助计划,包括把老年人送到杂货店和流动保健诊所、在“福利日”和假日向穷人分发现金和食品、开展小额信贷计划,以及每年向礼拜场所和地方组织提供固定数额的捐助等等。反对党用这些措施来换取选民的政治忠诚(37)Meredith L.Weiss,“Duelling Networks:Relational Clientelism in Electoral-Authoritarian Malaysia”,Democratization,Vol.27,No.1,2020,p.112.。
这样,反对党在抨击执政60多年的国阵通过打造庇护网络来维持其统治的同时,也通过非政府组织和“草根融资”来建立自己的庇护网络。2008年反对党联盟——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组成的人民联盟获得了槟州、吉兰丹州、彭亨州和雪兰莪州的政权,自此开启了反对党在州一级政权大范围的执政之路。执政后,这些政党开始利用权力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庇护网络。
第一,给予政党高层和非政府组织高层以政府职务。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庇护关系,人民联盟对政府职务进行了分配。例如在2008年槟州选举后,任命1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为政府官员,随后又在两个委员会中任命了7名非政府组织成员。在雪兰莪州,人民联盟政府承诺,在12个地方政府的288个职位中,非政府组织和专业人士的比例为25%(38)Garry Rodan,“Civil Society Activism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Malaysia:Differences over Local Representation”,Democratization,Vol.21,No.5,2014,p.835.。在槟州,除了非政府组织获得的职务之外,其他职务基本由民主行动党高层担任,如民主行动党全国秘书长林冠英担任槟州首席部长,民主行动党槟州主席郑泽荣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等等。这些政党没有摆脱巫统的庇护模式,仍然通过政府高级职位的任命来获得政党高层和非政府组织高层的忠诚。
第二,建立服务中心方便选民。这些政党在州一级执政之后,为了向选民提供支持和服务,利用州政府资金建立服务中心,通常由其地方党部管理,旨在与选民建立联系并回应他们的需求。同时,反对党也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开展社区服务项目,像健康教育计划、环保活动、青年培训项目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支持和服务,满足社区的需求和解决问题,从而换取社区居民的信任(39)《阿鲁古玛:解民生,提升生活素质,助人满足感,服务动力》,星洲网,2023年8月7日,https://www.sinchew.com.my/?p=4890266。
(四)庇护网络与议员跳槽
马来西亚以政党为中心的庇护网络以两种方式为议员跳槽提供了物质激励。其一,由于庇护网络关涉利益分配,庇护主义往往和党内派系斗争交织在一起。庇护主义会导致派系斗争的增强,派系斗争会增加党内对庇护资源的掠夺。内斗总是会产生失利一方,当这些人被胜利者开除党籍或自我感觉被边缘化后,就会选择跳到其他政党,从而成为“政治青蛙”。其二,尽管巫统及其反对党都建立了各自的庇护网络,但它们的庇护网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议员选择加入哪个政党的依据,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政党的庇护体系,庇护网络的不同会让议员获得的利益不同。议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选择从原政党跳槽到另一个政党。
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可以直接使用国家资源,因此执政党内部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加剧了派系之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国有企业和马来人资本家在内的庇护网络的建立,巫统内部“金钱政治”不断滋生,促进了其内部派系的形成,而每个派系都可以获得特定的战利品。1987年巫统的分裂正是党内不同派系争夺庇护资源的结果。1987年时任巫统主席、总理的马哈蒂尔与时任财政部长的拉沙里以及原巫统署理主席慕沙之间发生权力斗争。在1987年4月举行的党选中,拉沙里以718票对761票输给马哈蒂尔。拉沙里和其跟随者随后退出内阁和巫统,并在1989年6月另组“四六精神党”,巫统正式分裂(40)范若兰、李婉君、(马来西亚)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第210页。。据马来西亚学者王国璋分析:“马哈蒂尔、拉沙里或慕沙即使不为个人财富之积累,也要为各自集团的政经资源而斗争,否则其政治生命即难以为继。”(41)(马来西亚)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唐山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当然,巫统也可以直接运用国家资源来拉拢反对党成员,特别是在州一级政治中。在巫统漫长的执政时期,政府发展项目几乎完全由巫统政客提供。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农村地区的贫穷选民似乎更重视发展和地方政治,而不是腐败和透明度等国家层面的问题。这样的偏好对拥有资源优势的巫统非常有利(42)Matthew Louis Wagner,The Dynamics of Vote Buying in Developing Democracies:Party Attachment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2019,p.81.。联邦政府可以利用金钱或者职位诱惑反对党议员跳槽,从而导致反对党主导的州政府倒台。比如,1994年,沙巴团结党带领的联盟赢得沙巴州选举,但是联邦政府通过策反其中的3名议员,导致州政府迅速倒台,沙巴巫统带领的沙巴国阵得以组建政府(43)Arnold Puyok,“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abah,1985-2010”,in Challenges in Malaysian Feder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IRASEC,2011,p.16.。
与执政党相比,反对党能提供的庇护资源很有限,它们不能依靠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马来人资本家来获得经济支持,也不能依靠政府机构去实现对成员和选民的庇护,所以党内较少因为争夺庇护资源而发生内斗。但如前所述,反对党仍依赖庇护网络来分配职务和获取选民的支持。在有限的资源中,反对党也会提供一些优厚的条件,如该党的某些高级职务,或者提供一些“庇护愿景”,即如果加入该党后成功夺取政权,将会被授予高级职位等,去拉拢国阵的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随着“两线制”的形成,反对党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州政权,甚至于2018年夺取了联邦政权,这些“庇护愿景”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现实性。比如原巫统的霹雳州议员再诺柏迪、诺丽阿诗琳跳槽至土著团结党后,再诺柏迪成为土著团结党霹雳州秘书,诺丽阿诗琳成为霹雳州行政议员,他们的职务在跳槽之后都得到了晋升(44)《新朋友加盟 蛋糕没增大·霹国阵上阵议席料生变》,星洲网,2022年12月15日,https://www.sinchew.com.my/?p=3035204。
三 多党联盟制:“青蛙政治”的制度基础
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政治遗产,马来西亚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威斯敏斯特模式”,包括君主立宪制、议会内阁制、两院制等,但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两党制不同,马来西亚出现了多党联盟制这一多党制的亚类型。在这一政党体系中,各政党之间形成联盟并在联盟旗帜下竞选,某一政党联盟只要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就可以组建政府。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首脑需要获得国会下议院多数支持,州政府则在州议会选举后产生,获得过半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成为州执政党或执政联盟(45)罗圣荣:《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9、74页。。为了增加自己在国会或者州议会的议席,政党采用各种手段去争夺议席,除了可以通过选举获得议席外,还可以通过拉拢其他政党的议员跳槽到本党来增加议席。相对于两党制,议员在多党联盟制下拥有更多的跳槽机会,跳槽议员可以在多个政党之间选择自己拟新加入的政党。就此而言,多党联盟制为“青蛙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窗口”。
(一)多党联盟制的形成
马来西亚宪法第116条规定:每一联邦选区选举产生1名议员;第117条则规定:每一州选区选举产生1名州议员。每个选区实行相对多数代表制,得票最多者当选。因此,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代表制。根据“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相对多数选举制倾向于形成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形成多党制(46)Maurice Duverger,“Duverger’s Law:Forty Years Later”,in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ds.,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New York:Agathon Press,1986,p.70.。但在马来西亚,单一选区相对多数代表制并没有导向两党制。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两大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的政党体系,而是出现了多党林立、某几个大党主导建立多党联盟的政党体系。这种制度选择,从马来亚独立之初主要政治家做出抉择时就已初步确立。
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者对居住在马来半岛上的人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从而将“马来人”土著化,也将“华人”(包括土生华人)同质化和他者化(47)林绮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历史剖析》,《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随着19世纪末大量印度劳工的引进,马来亚形成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二战后马来亚的独立建国之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迈开第一步的。1953年3月17日,马华公会与巫统达成协议,8月23日正式结成联盟。1954年12月,印度人国大党加入联盟。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马华印联盟成为执政党(48)李一平:《一党独大下马来西亚多党联盟政治的发展》,《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这一政党格局,固然和当时马来亚的族群构成相匹配,但也并非唯一的可能。在逻辑上,既有可能建立3个单一族群政党,也有可能建立1-2个多族群政党。正是政治家的抉择最终促成了前一选项的实现和后一选项的排除。
作为巫统的创立者和第一任主席,拿督翁认为要争取马来亚早日实现独立,就需要团结各族群的力量。为此,他主张开放巫统,建立多元主义政党,吸引其他族群的精英加入(49)蒋炳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1957—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5-166页。。如果拿督翁的主张得到实现,将打破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各组政党的格局,从而避免将政党建立在单一族群的基础上。然而,拿督翁的主张在巫统内部遭到激烈反对。拿督翁出走后,巫统推举东姑·拉赫曼接任主席。与拿督翁意图组建跨族群政党不同,拉赫曼力主将巫统塑造为马来人的政党,以争取马来人最大程度的支持。
拿督翁离开巫统后,1951年9月组建了独立党。拿督翁仍坚持其组建多族群政党的目标,即独立党应该是一个以马来人为中心、包容其他族群精英的政党。就其开放性而言,独立党应该是华人精英更容易合作的政党。如果当时代表华人精英的马华公会与独立党合作,具有广泛影响的多族群政党还有形成的潜在可能,但历史的发展有时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拿督翁没有邀请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的李孝式参加独立党成立仪式,但李孝式不请自到,在仪式上受到了冷落。由于对拿督翁心怀不满,李孝式在1952年2月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之际联系巫统吉隆坡竞选小组的领导人,给予巫统以财力支持,对抗拿督翁的独立党(50)蒋炳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1957—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8页。。李孝式与拿督翁的意气之争使马来亚政党政治的天平完全倒向组建单一族群政党一侧。
尽管接任巫统主席的拉赫曼坚持将巫统定位为马来人政党,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巫统还需要和其他族群政党合作才能使马来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自治或独立。吉隆坡市政选举所面对的选民结构直接促成了巫统与马华公会的合作。在吉隆坡,华人选民占37.7%,马来选民占33.8%,印度人及其他选民共占28.5%。当时吉隆坡被划分为四个选区,其中两个选区是华人占多数,一个选区是印度人占多数,只有一个选区是马来人占多数。这种局势对巫统尤其不利。但由于李孝式与拿督翁的意气之争,马华公会和巫统这两个立场相距更远的政党结成了竞选联盟,并在12个席位中夺得9席,拿督翁阵营只赢得2席(51)许红艳:《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2页。。吉隆坡市政选举后,跨族群政党联盟在其他的市政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接连得到复制,最终在马来亚独立后成为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基本架构。
在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分别代表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的三个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以联盟的形式相互合作,连续取得了几次大选的胜利。这三个政党的领导层基本上都是殖民时代英校出身的贵族子弟和资产阶级精英,容易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和价值观寻得共识,达致妥协(52)(马来西亚)王国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族群与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他们之间的稳定联合,为马来西亚这个新生国家的巩固提供了必要和有利的政治基础。著名政治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将其誉为“在新兴国家政治的整体范围内不可能的(政治)艺术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5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 年,第336 页。。
(二)多党联盟制所依赖的社会裂隙
马来西亚的相对多数代表制没有导向两党制,并不意味着“迪韦尔热定律”被证伪。根据乔瓦尼·萨托利对“迪韦尔热定律”适用范围的再界定,相对多数选举制的确在某个具体选区中因限制个体选民的投票行为而促进了两党间而非多党间的竞争,但选民只在他所属选区受到限制,而由选区性两党体系走向全国性两党体系的前提是两个政党碰巧在全国所有选区内都是参赛者(54)Giovanni Sartori,“The Influence of Electoral Systems:Faulty Laws or Faulty Method?”,in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ds.,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New York:Agathon Press,1986,pp.43-68.。因此,选举制度本身并不能决定全国性政党体系是两党还是多党。在空间异质性的条件下,全国范围内往往会出现多种“社会裂隙”(social cleavage)横切交叉的情况。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斯坦·罗坎提出,社会裂隙是政党体系变迁的动力(55)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Free Press,1967,pp.1-64.。一方面,由于政党是沿社会裂隙线产生的,社会裂隙越多,就可能产生越多政党。另一方面,当社会裂隙越横切交叉时,社会冲突就越可能是多维度的,就越需要较多政党来代表利益和主张各异的群体。因此,在选举制度之外,社会裂隙也影响到政党的组建和竞选(56)刘颜俊、王晶晶:《重访和超越迪韦尔热:选举制度、社会裂隙与政党数量》,《学海》2022年第6期。。
如前所述,马来西亚建国之初政治家的抉择使多党体系得以出现。这一多党体系和马来西亚的社会裂隙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如果说建国之初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分化和妥协,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社会裂隙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马来西亚学者王国璋指出:“回顾马来西亚从英殖民时代迄今的政治发展大致不离三条主线,即族群、伊斯兰、阶级。族群政治可谓马来西亚的根本现实,迄今犹是。伊斯兰政治原可视为马来政治一环,1970年代后却逐渐反客为主,分量直逼族群政治。阶级政治则至今未成气候,但也难谓无关痛痒,总会在阶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隐晦地发挥某种跨族群的政治力量。”(57)(马来西亚)王国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族群与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ⅶ页。在马来西亚,正是族群、宗教、阶级之间的多重分化构成了多条社会裂隙线,从而为多党体系的最终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动力。
第一,族群分化。作为典型的多族群国家,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并没有人口占优势的主体族群。1947年,马来亚总人口中马来人只占43.3%,而华人和印度人则占55.3%。尽管后来由于马来人出生率高于华人和印度人,马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但马来西亚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仍低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58)衣远:《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演变——基于认同政治视角的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华人与印度人都有不同于马来人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俗。基于这条社会裂隙线,马来西亚的主要政党大多是基于特定族群建立的。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伊斯兰党都明确规定,只有特定族群的成员才可以加入。民主行动党、民政党虽然一直反对政党族群化,并且自认为是非族群政党,但其选民基础和领导阶层都是华人,关注的也主要是华人利益(59)许红艳:《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66页。。此外,东马两州的族群与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主体的西马也有着巨大的差异,马来人在这里不占人口优势,甚至还没有华人的占比大,而真正的人口大多数是作为非马来土著的伊班人和卡达赞—杜孙人。相应地,多个东马本土政党在这两个州占据主导地位,如沙巴团结党、砂拉越民联等。
第二,伊斯兰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分化。伊斯兰教是所有马来人信仰的宗教,致力于维护马来人特权的族群政党巫统也把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条款写进了宪法。但巫统仍是一个世俗主义政党,仍主张建构一个以马来人为中心的世俗的民族国家。伊斯兰党早期也以关注马来人地位为中心,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党从族群权益转向聚焦伊斯兰,主张在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国”(60)(马来西亚)王国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族群与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54页。。为了同伊斯兰党争夺伊斯兰教正统地位,时任总理、巫统领导人马哈蒂尔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伊斯兰国”,但伊斯兰党的“伊斯兰国”与巫统主导下的民族国家建构在本质上仍是不同的建国方向(61)齐顺利:《马来西亚“伊斯兰国”与民族国家:争论、影响与趋势》,《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作为长期在野的世俗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对伊斯兰党的态度多次摇摆。为了推翻国阵的长期执政地位,民主行动党需要与伊斯兰党合作,但因为“伊斯兰国”问题,民主行动党不得不与其决裂(62)范若兰:《对立与合作:马来西亚华人政党与伊斯兰党关系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三,阶级分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巫统在城市地区造就了一大批新马来中产阶级。正是在呼唤社会公平、提升社会福利的新马来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安瓦尔在巫统党内和国家机构中快速晋升。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马来资本集团与新中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导致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决裂和巫统内部的分裂,安瓦尔的妻子旺·阿兹莎联合一部分追随安瓦尔离开巫统的政治精英,在城市新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创建了国民公正党(后更名为“人民公正党”)(63)陈戎轩、傅聪聪:《马来西亚社会转型与马来族群政党分裂——基于社会分裂结构理论视角》,《东南亚研究》2021 年第3期。。与巫统的分裂相类似,随着伊斯兰党的影响力从传统马来农村走向高度城市化的雪兰莪州,新马来中产阶级促成了伊斯兰党内部专业阵营与乌理玛派的分化,引发了“如何实现伊斯兰国”的路线之争,最终导致伊斯兰党的分裂与国家诚信党的建立(64)傅聪聪、陈戎轩:《社会转型、路线之争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分裂》,《南洋问题研究》2020 年第1期。。此外,在华人中,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华人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不同诉求的反映。
这样,族群、宗教和阶级多种社会裂隙的横切交叉导致了多个政党的产生。比如,在马来人同一族群内又存在宗教/世俗分化和阶级分化,从而导致伊斯兰党与巫统之间的竞争、人民公正党从巫统的分离以及国家诚信党从伊斯兰党的分离。因此,马来西亚难以建立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那样的两党制。但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代表制下,为了争取在更多选区获得议席,这些政党不得不在其社会支持基础允许的范围内结成不同的联盟参选,如此就催生了多党联盟制这一介于两党制与多党制之间的政党体系。
(三)多党联盟制下的议员跳槽
在多党联盟制下,不同的社会裂隙线造就了同一联盟内多个政党间的差异,从而为跳槽议员提供了远非两党制下可以比拟的更多选择。当议员从原政党跳槽到其他政党时,他自身所获得的议席自然会随之带到其他政党。当然,也有议员脱离原政党但没有加入其他政党而成为独立人士的情况,如沙巴州的尤索耶古原为民兴党成员而后成为独立人士,但仍是沙巴州议员(65)《否认向议长呈辞,尤索耶谷:我还是州议员》,星洲网,2021年10月16日,https://www. sinchew.com.my/20211016,还有马六甲州议员诺芬依迪也是类似的情况(66)《希盟开会商甲州选决定是否接受4变节议员》,星洲网,2021年10月20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3365118。无论是加入新政党还是成为独立人士,议员的跳槽都会引起相关政党之间议席的消长,从而影响到执政党联盟和在野党联盟在国会或州议会中的力量对比。
为了达到推翻现任政府或组建新政府的目标,在野党联盟可以吸引跳槽议员以使自己的议席过半。反过来,执政党联盟也可能有意愿接受跳槽议员,这样会使自己的议席更稳定地超过对方,从而减少被推翻的风险。基于联盟间竞争的目标,许多政党通过许诺更高的职位等方式来吸引“政治青蛙”。马六甲州议员依德利斯哈仑原为巫统成员,2021年受到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的拉拢。安瓦尔承诺,依德利斯哈仑若跳槽至人民公正党,便推举其成为新一届马六甲州行政首长(67)《马六甲州选后及陆兆福重话下的大马新政局》,星洲网,2021年11月27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3446833。原为砂拉越人民公正党副主席的砂拉越州议员施志豪在砂全民团结党主席黄顺舸的邀请下跳槽至砂全民团结党,成为该党最高理事(68)《施志豪苦战冀摆脱“青蛙“标志,薛华东甘为孺子牛》,当今大马,2021年12月9日,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602313。国会议员阿都拉迪原是巫统成员,2020年加入土著团结党,任联邦政府乡村发展部长(69)《马来政治海啸来袭,国阵失守堡垒选区丰盛港》,星洲网,2022年11月21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4282489。。此外,还有未能成功拉入本党但却成为亲近和支持本党的独立议员的情况,如朱嘉慕央在时任总理慕尤丁的引诱下脱离人民公正党,成为亲近和支持执政联盟的独立国会议员(70)《里察烈:砂盟18国会议员无人挺安华任相》,星洲网,2020年10月2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3115250。
由于同一政党联盟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还有一些“政治青蛙”选择跳槽至同一阵营的友党。柔佛州议员凯鲁丁拉欣、莫哈末赛益和法伊祖安原是国家诚信党成员,先后跳槽至人民公正党。人民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都是希盟成员,但这些议员的跳槽使国家诚信党礼让区部宣布与人民公正党礼让区部断交(71)《不满接纳友党议员跳槽 礼让诚信党与蓝眼断交》,星洲网,2021年3月2日,https://www. sinchew.com.my/?p=3148112。其中缘由,法伊祖安声称自己是因为党内冲突而被迫离党,凯鲁丁拉欣则声称是为了迎战来年大选。无论出于什么缘由,他们的跳槽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但会引起多党联盟内部的冲突。
四 “反跳槽法”与“青蛙政治”的前景
作为引发马来西亚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青蛙政治”在马来西亚国内饱受诟病,人们在媒体上经常指责“政治青蛙”。“青蛙政治可以造就一个政府,也可以摧毁一个政府,牺牲的就是选民憧憬的民主,面对青蛙政治,选民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这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论对“青蛙政治”的评价(72)《青蛙政治刽子手》,《光华日报》2021年11月8日,https://www.kwongwah.com.my/20211108。2022年4月12日,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弗丁·伊德里斯沙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展示了一件他购买的画作,画面背景是马来西亚国会,坐了一屋子的猿猴和青蛙。这幅画作迅速引发了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的共鸣(73)《雪兰莪州苏丹晒国会坐满猿猴青蛙画作,引发马来西亚民众热议》,澎湃新闻,2022年4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09580。有的政党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其他政党接受“政治青蛙”的行为,并表示要惩罚这些投机分子。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安顺区国会议员倪可敏就指出:“国内政坛这几年因为政治青蛙的投机行为搞得一片乌烟瘴气,人民真的受够了,因此拒绝青蛙,人人有责。”(74)《国盟为分裂华人票将组建青蛙大联盟,倪可敏吁全民拒绝投机政客》,《火箭报》2021年11月25日,https://therocket.com.my/cn/2021/11/25
但在现实中,马来西亚的政党对待“政治青蛙”往往具有两面性,因为“政治青蛙”既可以令其失去政权,又可以帮助其夺取政权。大马民主阵线创党人赛沙迪曾公开批评希盟中的人民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接受了“政治青蛙”,还嘲笑说:“巫统不就是靠政治青蛙夺权的嘛,导致无数个州政府倒台,才赢得州政权”(75)《韩丹批MUDA接纳“政治青蛙”,赛沙迪:巫统夺权全靠政治青蛙》,《光华日报》2022年2月15日,https://www.kwongwah.com.my/20220215,但他在任土著团结党青年团长时却高调欢迎巫统的议员跳槽至土著团结党(76)《批希盟接受“青蛙”被翻旧账,赛沙迪:所以我成立MUDA》,星洲网,2021年11月8日,https://www.sinchew.com.my/?p=3404455。马华公会马六甲州望万地区候选人郭钦汉曾评价说:当自己党派的成员叛逃时,会被赋予“青蛙”标签,但是当接受其他党派成员时,就会赋予他们“英雄”的称号(77)“PH’s Attempt to Legitimise ‘2 Melaka Frogs’ Laughable,Says MCA”,New Straits Times,November 9,2021,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1/11/743866。
如果说多年来“青蛙政治”的影响主要限于州一级政治,那么“喜来登政变”后“青蛙政治”的影响已严重危及联邦政府的可持续性。在2018年大选到2022年大选之间,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先后有50人次跳槽,这期间也三易联邦政府(78)苏莹莹、翟崑主编《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08、111-112、116页。。在“青蛙政治”之下,政府难以专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治理国家。消除“青蛙政治”乱象终成为朝野各党的共识。接替慕尤丁出任马来西亚总理的伊斯梅尔·萨布里在2021年9月13日与希盟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政治转型与稳定谅解备忘录》,宣布政府与希盟合力推动“反跳槽法”(79)《4月斋戒月开国会特别会议 马国首相承诺提呈跳槽法案》,《联合早报》2022年3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20324-1255393。2022年4月11日,马来西亚政府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提呈了旨在消除反跳槽行为的宪法修正案(80)《马组特委会制定反跳槽法 5月开特别国会才表决》,《联合早报》2022年4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20412-1261812。7月28日,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出席会议的209名议员一致通过《与反跳槽法案相关的2022年联邦宪法(修正)(第3号)法案》,以此来限制国会议员在当选后更换政党的宪法权利(81)《209议员一致支持修宪 马国通过反议员跳槽法案》,《联合早报》2022年7月29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20729-1297542。随着“反跳槽法”的通过,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2022年10月5日正式生效的“反跳槽法”,当选国会议员退党成为无党籍议员或加入其他政党,或无党籍国会议员当选后加入任何政党,必须腾空议席举行补选。11月19日的马来西亚第15届国会选举正是在“反跳槽法”生效的背景下举行的。尽管大选后出现了希盟、国盟、国阵三大阵营均不过半的局面,但政治博弈主要在于阵营之间的组合而非向其他阵营挖墙脚。“反跳槽法”的生效显然增加了政治生活的确定性。2023年3月6日,槟州议会正式援引“反跳槽法”通过动议,悬空了4名从人民公正党跳槽到国盟的州议员议席,议长还当场要求4名议员离开议会厅。这是“反跳槽法”通过以来,州一级议会首次援引这项法律应对跳槽议员(82)《槟州议会援引反跳槽法 悬空四国盟州议员议席》,《联合早报》2023年3月7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30307-1369971。
当然,这项法律仍有漏洞或者模糊之处。比如,2022年12月10日沙巴首席部长及沙巴人民联盟(以下简称“沙盟”)主席哈芝芝宣布,带领4名国会议员和11名州议员退出慕尤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他说这些议员在大选中是代表沙盟参选,他们都将继续留在沙盟,因此并不抵触“反跳槽法”。但慕尤丁声明,退党者参选时的党籍是土著团结党,因此根据“反跳槽法”,他们必须腾空议席进行补选。由于“反跳槽法”的“政党”定义并不区分个别政党与政党联盟,也没有处理政党身份重叠的问题,因此哈芝芝等人“退党不退盟”是否抵触“反跳槽法”引起了争议(83)《退党不退盟做法掀争议 马国反跳槽法绑不住政治青蛙?》,《联合早报》2022年12月18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21218-1344555。这起争议也有助于人们对“反跳槽法”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面对庇护网络提供的跳槽激励和多党联盟制提供的跳槽便利,“反跳槽法”所起的作用仍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一方面,如果庇护网络提供的跳槽激励足够强,即使议员因抵触“反跳槽法”而必须腾空议席,当他们参加补选的胜算几率很大时,他们仍可能选择跳槽。马来西亚专栏作家曾千恒一针见血地指出:“制订反跳槽法案只是表面功夫。很多时候,在野议员跳槽成为执政议员,是为了获得更多选区拨款或争取建设工程,也有不知廉耻的议员跳槽来换取内阁或官联公司职位,以及逃避法律制裁。”(84)曾千恒:《反跳槽法不是马国救星》,《联合早报》2022年8月4日,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20804-1299586另一方面,“反跳槽法”只是限制议员个人的跳槽行为,而政党在选后更换所属政党联盟并不算跳槽,因为议员并非脱离党籍,而是跟随政党从一个政党联盟跳槽到另一政党联盟。考虑到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是在多党联盟制下组建的,“反跳槽法”无法阻止同党议员集体脱离政党联盟,因此也难以杜绝类似2020年“喜来登政变”那样的政权更迭再次上演。从长期来看,要使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更加有序,还需要在遏制庇护网络带来的腐败及不公和增强政党间合作的稳定性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