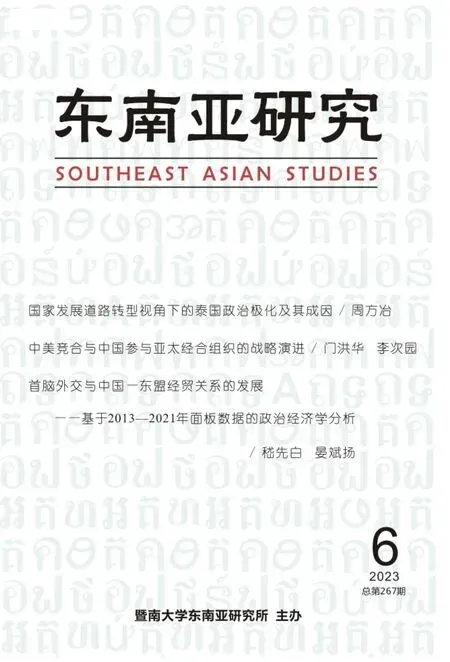中美竞合与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战略演进
门洪华 李次园
引 言
一直以来,为了塑造良好的地区环境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加强与地区组织的互动,努力融入到地区经济机制中。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构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部分,也是国际社会接触中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1)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8期;Stephen N. Smith,“Harmonizing the Periphery: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The Pacific Review,Vol.34,No.1,2021,pp.56-84.。然而,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竞争的战略压力。中美在国际组织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利益、观念、国际秩序、国际领导权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冷战后,中美在国际组织中大体经历了“战略摩擦——战略合作——战略竞争”的过程(2)张贵洪、余姣:《国际组织与中美战略竞争——演变、态势和影响》,《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亚太经合组织(APEC)作为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改变了中国以往没有参加任何区域经济组织的状况。迄今,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走过30余年风雨,中国始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并逐渐朝着引领者的角色转变(3)宫占奎、刘晨阳编《APEC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而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历史也是大国间相互合作与竞争的历史(4)Taylor Ian,“APEC,Globalization,and 9/11”,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36,No.3,2004,pp.463-478.。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中美竞合既是双边关系的如实体现,也是制约亚太经合组织开展合作的最大阻碍(5)Andrew Hammond,“US-China Rivalry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APEC Cooperation”,November 11,2021,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55666/us-china-rivalry-biggest-threat-apec-cooperation。2023年,美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试图重新利用这一框架与印太国家进行积极接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6)“Biden Should Seize APEC and ASEAN Opportunities”,CSIS,March 11,2021,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should-seize-apec-and-asean-opportunities。应当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关系不仅单方面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演变过程密切相关,中美关系的变化反过来形塑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以及推动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关系的演进。有学者指出,竞争与合作的复杂状态很可能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7)Adam P. Liff,“China and the US Alliance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No.233,2018,pp.137-165.,也极易影响中国与地区组织的互动关系。因此,探索竞合关系下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互动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历程,能够为中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有效参与国际组织提供重要的价值和参考。
当前,关于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涉及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互动关系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关系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阐述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历程、面临的难题与机遇以及未来愿景(8)参见宫占奎、李红年:《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当代亚太》2003年第10期;苏格:《亚太经合之中国足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杨泽瑞:《论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张蕴岭:《亚太经济一体化与合作进程解析》,《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贺平、周峥等:《亚太合作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Lok Sang Ho and John Wong,APEC and the Rise of China:An Introduction,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01,pp.121-169.,或者在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框架下聚焦于互联互通、经贸合作、能源合作等某一具体议题,或者探讨亚太经合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的互动等问题(9)参见田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李文韬:《中国参与APEC互联互通合作应对战略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路宇立:《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分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还有研究关注亚太经合组织对于中国在地区影响和国际地位等方面产生的功能性作用等问题(10)See Gary Klintworth,“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APEC”,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0,No.3,1995,pp.488-515;Mohamed Ariff ed.,APE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pp.104-123;Jenn-Jaw Soong,“Is China Becoming the Core of Regional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Chinese Economy,Vol.47,No.3,2014,pp.3-7;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然而,中美竞合关系作为持续影响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过程中必须考量的现实问题。随着中美关系“合作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或“竞争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互动模式成为常态(11)Jr. Joseph S. Nye,“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A US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8,No.5,2022,pp.1635-1651.,探索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竞争与合作对于未来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大国竞合关系与大国参与国际组织互动间关系的理论阐述为出发点,以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竞合关系的转变为背景,将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为核心线索,梳理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关系的转变历程,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评估,从而提出中国的因应之策。
一 大国竞合关系及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政治现象和国家间常见的互动模式,国家间互动受到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影响,是动态的发展过程(12)门洪华、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竞争:一项战略研究议程》,《当代亚太》2021年第6期。。大国博弈形成的竞争与合作犹如硬币的两面,不仅深刻影响国际组织的自身演变,也极大塑造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历程,还对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关系转变产生强力作用。
(一)大国竞合关系的内涵
大国竞合关系指大国间“建立合作机制与维持竞争关系”并存的动态性复杂状态(13)Timothy R. Heath,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Santa Monica CA:Rand Corp,2021,pp.1-20.,体现出“竞争中存在着合作”与“合作中存在着竞争”的特征(14)胡键:《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国际观察》2022年第1期。。在大国间长期博弈的过程中,基于实力大小、目标制定与策略选择等不同要素的影响,大国并非采取纯粹的完全合作或完全竞争战略(15)David M. Edelstein,Over the Horizon Time,Uncertainty,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7,p.15.,而是选择一种同时包含竞争与合作的策略,这导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合性特征。在国际组织中,大国间竞合关系同样普遍存在。一般而言,国际组织为国家间合作提供制度支撑与规范保障,致力于谋求国家间合作而实现共同利益。本质上,国际组织成为促成大国合作的有效工具(16)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p.249-252.。国际组织的成立与变革过程中充满着竞争要素,表现在决策机构的权力分布、议程设置和治理结构、权利和义务分配等方面,反映出国家间权力结构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大国博弈成为国际组织持续演化变迁的重要动力。而国际组织中的制度规范往往是不同行为体之间政治博弈的结果,深深烙上了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印记(17)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应当说,大国竞争与合作成为国际组织中大国互动的常态,深刻影响着国际组织的变革。总体上,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竞合关系是指,国际组织中的大国围绕着国际组织中的议题治理与发展方向等领域,在追求共同目标与互斥目标过程中形成竞争与合作的二元互动结构,本质上体现了大国相互依赖的复合互动状态。
从这一定义出发,国际组织中大国竞合关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动态性。大国竞合关系并非永久性呈现出单一的固化竞合结构,而是随着时间变迁,尤其是在国际组织变革中因受到不同要素的多重影响而产生渐进式或剧烈式的动态变化。二是相互依赖性。竞合关系本身蕴含着竞争与合作难以分割的特征,大国不仅围绕着国际组织中的领导权等稀缺资源、针对不同问题而提出的差异化治理方案等方面进行竞争,也会在应对共同威胁、追求共同目标时展开必要合作,体现出大国基于不同利益和差异化目标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大国在创造价值时进行合作,在分配利益时展开竞争,竞合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相互依赖性。三是不确定性。大国竞合关系受到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等内部维度与以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为核心的外部维度的双重影响,致使国际组织中的竞合关系变迁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18)关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韩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战略应对》,《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6期。。这种不确定性又与国家间的互动实践紧密联系,既表现为在不同问题领域中大国的政策选择是以“竞争取向”还是“合作取向”为主导的难以预测性,也表现在由于竞合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国际组织中大国关系的发展变迁显示出不可捉摸性。
(二)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竞合关系
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竞合关系既受到利益关系、能力分配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在身份定位转变与关键节点事件等进程性要素的冲击下而不断被塑造。
第一,利益关系的形塑。一直以来,现实主义关注相对收益和竞争,而自由主义关注绝对收益和合作,本质上,这反映了行为体对利益关系的认知(19)Quddus Z. Snyder,“Liberal Systemic Theory and the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9,No.1,2013,pp.209-231.。行为体间的利益并非天生对立,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共存是竞合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20)Tarun Khanna,Ranjay Gulati and Nitin Nohria,“The Dynamics of Learning Alliances: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 Relative Scop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9,No.3,1998,pp.193-210.。无论是对于单向度的竞争或合作还是复合的竞合状态,本质上都是对不同行为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表达,尤其是在不同问题领域中对国家利益差异性的看法产生的利益兼容性,成为区分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指标(21)Robert Elder and Nicole Peterson eds.,“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to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MA Perspectives,Vol.1,2020,pp.71-74.。对大国而言,在国际组织中双方的共同利益越多、差异性利益越少,大国会释放出更多的缓和信号,甚至会放弃部分利益来换取更多的其他战略利益,大国竞合关系会朝合作主导的方向发展;反之,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大国追求的目标出现分化甚至是存在分歧或冲突,在此背景下大国展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决心,不断采取竞争策略,大国竞合关系逐渐走向以竞争为主导。
第二,权力分配的物质基础。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权力差异所形成的等级制度产生竞争行为,同时在不同问题领域中,基于共同利益的分布,行为主体间也会保留合作空间(22)Jonathan Kirshner,“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World Politics,Vol.67,Vol.1,2015,pp.155-183.。国际组织本身反映了大国权力分配格局,如果国际组织中大国的权力分配趋于大致均衡状态,在利益目标的驱使下,国际组织中大国竞合关系会逐渐发展为以竞争为主导。而且,随着国际组织中大国权力分配趋于平衡,合作双方越是平等,就越有可能为获取支配地位而展开竞争(23)〈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3页。。一般而言,能力不对称的竞争较为罕见,能力相对对称分布的大国更容易产生竞争(24)William R. Thompson,“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No.4,2001,p.574.。国家实力和权力对比变化对国家行为起着基础性作用,权力转移不断加速必然会加剧大国权力竞争(25)Robert S. Ross,“It’s Not a Cold War: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No.2,2020,pp.1-10.。国际体系中逐渐衰落的主导国家和主要对手间的权力分配与转移造成的实力地位日益对称,所形成的权力等级制度越扁平化,大国从合作转化为竞争的风险就越高。同时,在国际组织中,大国实力差距扩大往往会催生大国合作占主导。因为,当大国权力具有明显差异时,现有权力格局难以改变,这种实力差距让实力劣势方无力发起大国竞争,只能采取合作态势。
第三,身份定位的转变。国际组织中的大国对彼此的身份定位存在差异性,不同的身份定位塑造了大国的政策选择(26)〈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差异化的身份定位影响大国对他国的威胁感知和动机把握,推动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竞合关系的转变。大国在对博弈对手的不同身份定位下所产生的威胁感知改变了敌对国合作或竞争的倾向,进而影响合作性战略与竞争性战略之间的适当平衡(27)〈美〉查尔斯·格拉泽著,刘丰、陈一一译《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当以竞争对手定位对方身份时,双方会夸大敌对行动,淡化合作诚意(28)Michael P. Colaresi,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国际组织将出现更多的竞争性因素,并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政策选择。必须指出的是,以竞争对手定位对方身份,并不是指竞争取代竞合关系成为大国互动的核心形式。大国持久性竞争中始终混杂着竞争与合作要素,尤其是在防止事态失控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29)Hal Brands,The Twilight Struggle: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2,p.7.。竞争对手的身份定位只是表明,竞争在大国竞合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非取代竞合关系。当大国以合作者身份定位对方身份时,基于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追求成了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优先选项,偶尔的竞争并不能改变大国合作的本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大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转变,不同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对彼此的身份定位一直在不断变化。在大国竞合关系中,确定恰当的身份定位对于大国在国际组中保持合作与竞争之间的适当平衡和避免冲突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重点避免不利因素的升级而导致的竞争向冲突的转变(30)Robert Elder and Nicole Peterson eds.,“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to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MA Perspectives,Vol.1,2020,p.3.。
第四,关键节点事件的冲击。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转折、一种新格局的形成、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都会迫使一个国家改变其战略思路(31)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关键节点是社会结构相对不确定的时刻,此时的行为体比正常情况下能更加能动地决定结果(32)James Mahoney,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Baltimore:JHU Press,2001,p.7.。从长时段来看,大国竞合关系导致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始终遵循着围绕“竞争与合作”上下波动的演进路径。不同时空中的关键节点事件常常会冲击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政策和竞合态势,改变原有竞合关系的平衡格局,有可能推动这种竞合关系朝着以合作为主导或以竞争为主导的结构发展。关键节点事件由不可预测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构成,诸如经济危机、地区安全、国内政局变动等突发事件等,成为影响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竞合关系变迁的重要时机。实际上,在国际组织中,处于竞合状态下的大国选择“一直竞争”或“一直合作”都并不是一个稳定策略,毕竟外部事件冲击不断促使大国在博弈过程中不停转变博弈策略(33)〈美〉汤姆·齐格弗里德著,洪雷等译《纳什均衡与博弈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64-66页。。因此,大国参与国际组织进程将充满着合作与竞争交替变化的灵活性。
(三)大国竞合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如前所述,大国与国际组织互动遵循着成本与收益的理性主义逻辑,大国利益关系类型是影响大国竞合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组织中大国利益兼容度与利益分布结构,以及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态势,可以将国际组织中大国竞合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或结构:“合作主导型”、“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型”、“竞争主导型”。上述三种竞合关系中内含的竞争与合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当竞争或合作某一互动关系占主导地位时,并非意味着另一互动方式消失,而仅仅是抑制了这一互动方式的频繁展开。在不同的大国竞合关系类型中,国际组织中大国对彼此的身份定位以及关注的核心问题有所差异,推动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双边关系出现不同转变。不同的竞合关系形成的差异化外在压力致使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广度与力度也有所不同,影响着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进程。
在“合作主导型”竞合关系中,国家追求的核心目标在于寻求国际组织中的持续性合作,国际组织中大国对彼此的身份认知呈现出“合作者”意象。换言之,国际组织中大国双方在分布着广泛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务实合作,有效推动大国关系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为大国参与国际组织塑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在这种结构中,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核心关切体现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如何成功地维持合作”,即大国围绕着共同目标进行大量合作,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中,基于协调基础上大国作出必要的妥协行为,呈现出较强的战略克制倾向。这种竞合关系既为大国参与国际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也为其进一步融入国际组织中并深入巩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因此,处于“合作主导型”竞合关系中的大国往往对参与国际组织的积极性较高,旨在扩大与其他成员联系,提高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当然,这一结构中的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竞争互动同样存在,而这种竞争仅仅是因为局部利益不一致出现的短暂不和谐,本质上是“合作中存在着竞争”的现象,很容易被“弥合”,难以对双边关系的性质构成根本性影响。
在“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型”竞合关系中,竞争或合作均有可能成为大国参与国际组织、进行战略制定的首要倾向,这取决于大国在具体问题上的目标追求与利益分布状态。一般而言,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的竞合关系意指竞合的平衡状态,即竞争与合作达到均衡的稳定关系(34)Devi R. Gnyawali and Tadhg Ryan Charleton,“Nuances in the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Coopeti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Vol.44,No.7,2018,pp.2511-2534.。这种互动状态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最佳组合(35)Stefanie Dorn,Bastian Schweiger and Sascha Albers,“Phases and Themes of Coopetition: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Vol.34,No.5,pp. 484-500.,往往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结构形式。当国际组织中大国关系处于竞合平衡状态时,不同领域中的问题导向成为塑造大国竞合关系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在国际组织不同的治理领域中,大国利益分布所形成的利益关系和战略关注度存在差异,协调好大国利益分歧进而形成高水平外交协作至关重要(36)Miller Benjamin,“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Great Power Concert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4,1994,pp.327-348.。同时,协调好不同领域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对于国际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大国关系的友好演进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这种竞合结构中,“管控竞争,扩大合作”进一步凸显了大国在国际组织中进行协调的重要性,大国博弈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加强协调”,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进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在这种结构类型中存在着共同利益与互斥利益,大国参与国际组织不仅仅在于协调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何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成了另一个核心诉求。
在“竞争主导型”竞合关系中,竞争作为双边关系的主导因素,“竞争对手”的身份框定了两国的根本关系,合作仅仅是在利益、威胁、实力发展以及外部重大事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间断性”结果。在这种结构中,国际组织中大国展现出的合作倾向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竞争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可以说,崛起国与守成国一方或双方一旦陷入“大国竞争”的战略取向中,竞争便成了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37)Hal Brands,The Twilight Struggle: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2,p.2.,既是大国实现自身目标极为重视的战略手段,也是大国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兼具“手段与目标”双重属性。因此,竞争主导下的竞合关系致使大国以“竞争对手”的认知逻辑来作为参与国际组织和制定自身政策的标准以及评判对方行为的依据,大国博弈关注的核心问题转向了“如何更好地进行竞争”。大国竞争框架下凸显的“获取竞争优势”的主导逻辑,使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选择出现了两种行为分化:第一,进一步充分发挥大国领导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导国际组织变革,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逐渐退出或弱化现有国际组织的作用,降低对原有国际组织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并试图“另起炉灶”进行国际制度竞争。
总之,在参与国际组织进程中,“竞争中合作”与“合作中竞争”构成了竞合关系状态下大国策略选择的核心内容。而大国竞合关系深刻影响着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利益关系、能力分配、身份定位与关键节点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竞争主导型”、“合作主导型”和“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型”的多样化竞合关系,由此决定了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与行为选择的差异。
二 中美竞合与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历程
作为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中国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和秩序建设的制度支撑,也为中国加强与地区国家联系、融入地区发展和参与地区治理提供了关键场所。尤其是在2001年、2014年,中国两次作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成功举办相关会议,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38)苏格:《亚太经合之中国足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期间,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竞合关系贯穿于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过程的始终。亚太经合组织不仅是促进中美沟通和展开多重博弈的重要机制,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与责任担当的提升,中美互动将成为影响亚太经合组织下一个十年发展的关键因素(39)张海冰:《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APEC:角色、挑战与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1期。。总体上,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竞合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合作主导型”竞合关系(1991—2000年)、“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型”竞合关系(2001—2011年)与“竞争主导型”竞合关系(2012年至今)。这种多样化的竞合关系形成的差异化外在压力,推动着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历经初始阶段、深化阶段和拓展阶段。
(一)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初始阶段(1991—2000年)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呈现出“战略漂流”的特征,但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中美呈现出“合作主导型”竞合关系。首先,美国仍具有相较于中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冷战结束宣告国际体系走向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霸权(40)Stephen C.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2002,pp.20-33.。为了实现霸权护持,美国需要防范和压制潜在竞争对手(41)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 S.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pp.5-53.。有学者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难以对美国造成实质性影响,美国实力并未衰落。”(42)Sean Star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7,No.4,2013,p.821.中国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两国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以美国占优势地位的经济非对称性使其在应对中美经贸问题时拥有更多主动性,表现出合作意愿。其次,中美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中分布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对美国而言,亚太经合组织被视为分享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红利的“搭便车”工具(43)Chandra Muzaffar,“APEC Serves Interest of US More than Others”,New Straits Times,No.29,1993,p.13.,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依托,其试图借助亚太经合组织来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贸易制度建设。一定程度上,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成为美国将自身权力有效投射到亚太地区的新战略(44)Ngai-Ling Sum,“The NIC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in Anthony Payne and Andrew Gamble 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996,p.233.。对中国而言,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地区制度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对经济上重新融入世界经济极为重要,对外交和政治上打破孤立局面同样意义非凡,同时也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一步。而且,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45)Joseph Camirelli,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Volume II,Cheltenham:Edward Elger,2003,pp.138-147.。
因此,中美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具有较强的意愿,两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地区机制中频繁互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合作的良好态势。而且,亚太经合组织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定期举行多边会晤的机会,共同探讨亚洲面临的机遇与危机,彰显了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价值(46)Alan Oxley,“APEC—The Next 10 Years”,APEC Study Centre Consortium Conference,1999,http://www.asia-studies.com/content3.html,April 23,2023,p.16.。基于上述背景,实力的有限性与接触世界的需求性决定了中国是以“积极融入者”而非“规则塑造者”的身份,采取更加包容、克制的态度与亚太经合组织加强互动,旨在防止政治上被孤立、促进与亚太国家的密切经济联系,最终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这一阶段,中国在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对具体议题采取差异化态度,谨慎对待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参加了1993—2000年举行的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极阐述中国关于亚太经合组织在加强经济合作与组织发展等方面的观点。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便阐述了中国关于亚太经济合作“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的四项原则与具体实施路径。在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进一步完善关于亚太经济合作原则的表述,倡议“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47)苏格:《亚太经合之中国足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在此基础上,1996年,中国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指出“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等的重要性(48)宫占奎、于晓燕:《APEC演进轨迹与中国的角色定位》,《改革》2014年第11期。。与此同时,中国注重技术合作与交流,提出加强科技交流、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的重要建议。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专业拨款1000万美元,设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以支持亚太经合组织《走向21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技能开发行动计划》等(49)《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1998年11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0011/t20001107_7944037.shtml。
同时,中国借用亚太经合组织平台,积极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在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双方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50)王逸舟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江泽民同克林顿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使两国关系又一次“开始解冻”(51)王嵎生:《亲历APEC:一个中国高官的体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0页。。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中美关系的佳话(52)杨泽瑞:《APEC 30年:机制·进程·前景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176页。。可以说,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这个舞台与其他成员特别是美国的接触,逐步消解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经济的生存空间(53)张纪康主编《了解APEC:跨世纪的世界主宰》,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这一时期,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主要体现如下三个特征:第一,顺应冷战后地区主义发展潮流,满足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快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54)刘晨阳:《亚太经合组织30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积极融入地区合作中,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重要经济发展平台,关注议题集中在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等领域,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第二,中国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与不同国家开展双边与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交流渠道受阻。通过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利用地区性多边机制,实现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的必要交流。例如,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和克林顿的首次会晤打破了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坚冰。第三,中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化建设较为谨慎,强调亚太经合组织的非机制化特征。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灵活的、务实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55)《江泽民主席在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1993年11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58/zyjh/t10450.htm。而且,中国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的核心内容在于“自主自愿的非机制化原则”,即中国希望亚太经合组织保持较低的制度化水平(56)田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总体而言,通过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不仅能够在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等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也能够为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与大国互动以及塑造地区环境提供有利契机,还可以向地区和世界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
(二)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深化阶段(2001—2011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期间中美大体上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均衡分布型”竞合关系,并如实反映在两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中。从对华战略定位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实现腾飞,中国逐渐被美国锁定为新世纪的潜在竞争对手。小布什在竞选期间便公开声称要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强调两国是“战略竞争关系”而非“战略伙伴关系”(57)唐家璇:《劲雨煦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美国固化了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并指出:“中国将必然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最主要潜在竞争对手。”(58)Brad Roberts,Robert A. Manni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China: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Foreign Affairs,Vol.79,No.4,2000,pp.53-63.从关键节点事件冲击来看,“9·11”事件成为推动中美进行合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它改变了美国对外部首要威胁的战略判断,“反恐问题”而非“大国关系”成为美国优先考量的外交事项。这一阶段,中美关系能友好发展极大程度上归因于“9·11”事件以及美国介入伊拉克(59)Peter Hays Gries,“China Eyes the Hegemon”,Orbis,Vol.49,No.3,2005,pp.401-412.。受益于“9·11”事件,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美两国对“恐怖主义”危害性的共同认知为双方战略合作提供了一定基础(60)Aaron L. Friedberg,“11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Survival,Vol.44,No.1,2002,pp.33-50.。应当说,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既存在合作空间,也进行着必要竞争。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战略协调成为两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重要互动方式。基于此,中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与美国积极展开合作,协调与美国的竞争性因素。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问题,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关注度下降,战略资源的有限也使美国对中国展现出诸多协调要素,这为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2001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重要标志,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进入深化阶段。首先,中国连续参加历次亚太经合组织各类会议,展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国出席了2001—2011年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非领导人会议,不仅主动参与经济技术合作和地区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努力发挥作用,还积极探讨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建设。应当说,从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和制订者,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显著特征。尤其是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主动设置议程。这次国际会议是在世界经济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小布什政府实行新亚太战略以及“9·11”事件给国际形势带来不确定性的总体背景下召开的,对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有着新的里程碑意义(61)贺平、周峥等:《亚太合作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在重申努力实现“茂物目标”基础上,中国积极将反恐问题纳入此次会议议程。会议形成了旨在加速实现“茂物目标”的《上海共识》,充分表明中国在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彰显了中国在该组织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62)苏格:《亚太经合之中国足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
其次,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各种会议上表达对组织发展、地区合作与经济交流等方面的新思路。具体而言,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始终是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基础,中国在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这两者的重要性,不断提出新路径。2003年胡锦涛第一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便指出:“为了促进各成员经济发展,亚太各国、各地区要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63)《携手努力,促进亚太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0日第1版。为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进步,2006年中国宣布将向亚太经合组织支持基金捐款200万美元(64)《推动共同发展 谋求和谐共赢》,《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9日第1版。。全球金融危机严重破坏地区与全球合作之际,200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坚持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切实维护亚太地区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尽快复苏(65)《合力应对挑战 推动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第2版。。应当说,中国始终是推进“茂物目标”的坚定实施者和主要力量。
最后,围绕亚太经合组织安全议题的限度问题,中国与美国展开了必要竞争和有效协调。亚太经合组织安全议题的产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出近年来亚太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态势,其背后隐含着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的战略博弈(66)刘晨阳:《APEC二十年:成就、挑战、未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9·11”事件后,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中,“反恐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议题。美国希望将反恐问题纳入到亚太经合组织的议程设置中,实现亚太经合组织的安全功能。很大程度上小布什政府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美国推行反恐安全政策的平台,试图将其打造为一个安全性组织(67)魏红霞:《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当代亚太》2006年第10期。。而中国也认识到,亚太经合组织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完全回避安全议题,而且有些安全议题对于保障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中国的策略是,在维护亚太经合组织现有合作方式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对亚太经合组织安全议题的衍生进行合理控制和引导(68)同④,第104页。。在此指导下,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上海会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此次会议的《领导人宣言》指出:“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应发挥领导作用。同时,我们需要就反对恐怖主义传达清晰而强烈的信息。”(69)《APEC〈领导人宣言〉全文——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中国外交部网站,2001年10月21日,http://www1.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wj_682290/200110/t20011021_9384065.shtml面对美国试图将安全问题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泛化的意图,中国谨防安全问题政治化,将亚太经合组织讨论的安全问题尽量限制在非传统安全上。2003年后,由于亚太地区各种传染性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发生,亚太经合组织安全议题开始从“反恐”向“保障人类安全”更为宽泛的概念拓展。在2005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新发传染病研讨会”倡议,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积极响应,该研讨会2006年在中国召开(70)《深化亚太合作 共创和谐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9日第1版。。此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多次会议中,中国始终强调人类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既保留与美国就安全议题展开合作的空间,也限制美国企图在亚太经合组织将安全问题政治化的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重新塑造了国家间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影响全球权力与力量格局变化的关键界标(71)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06页。,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逐渐接近。但是,在2011年之前,奥巴马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凸显出诸多协调因素,恰如学者指出的:“奥巴马政府以多边主义与加强联盟关系为核心,对华政策采取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战略。”(72)Deborah Welch Larson,“Policy or Pique?Trump and the Turn to Great Power Competi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36,No.1,2021,pp.47-80.
这一时期,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成员,中国注重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2003年,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促进发展中成员发展应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任务(73)《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第1版。。由此,中国主张要加快发展中成员经济发展,帮助他们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这也有利于发达成员寻找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最终实现各成员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第二,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不断进行新的议程设置。2005年,在韩国召开的釜山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主张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人的安全”合作,提高各成员应对新传染病的能力,得到了其他成员的高度赞扬(74)《深化亚太合作 共创和谐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9日第1版。。2006年,在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中国倡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港口服务网络,以加速本地区港口及配套行业的整合与升级(75)《推动共同发展 谋求和谐共赢》,《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9日第1版。。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的重要性(76)《深化互联互通 实现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2年9月9日第2版。。第三,在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发展中,中国积极提供新的理念。为推动亚太地区合作,营造良好地区环境,中国主张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大家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强调共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性(77)《深化亚太合作 共创和谐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9日第1版。。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各成员要主动建设一个清洁、和谐、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亚太地区。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与世界联系的增强,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进一步增强,在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基础上,尊重成员多样性、强调成员的共同发展,并积极承担起中国应有的责任,努力为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三)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拓展阶段(2012年至今)
随着2012年美国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概念,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竞争主导型”竞合关系。对奥巴马政府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战略对手,足以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性质(78)Chengxin Pan,“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4,2014,pp.453-469.。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何瑞恩直接做出“中美步入‘大国竞争’肇始于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的战略判断(79)Ryan Hass,“Performance Will Determine Prestige in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Global Asia,Vol.16,No.4,2021,pp.24-29.。随着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国竞争”回归,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尤其是拜登政府延续并固化了这种认知,在将中国定义为“体系竞争对手”基础上强化与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合作竞争”成为中美现阶段关系的常态(80)Joseph S. Nye,“US-China Cooperation Matters”,China Daily,June 19,2020,http://www. chinadaily.com.cn/a/202006/19/WS5eec010da31083481725411c.html。
这种竞合关系体现在两国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中:首先,美国试图弱化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由于美国缺乏对亚太经合组织的足够战略关注,加之亚太经合组织弱机制化,经历两次金融危机的经济治理失效,其有效性不断受到美国质疑。亚太经合组织甚至被称作“清谈馆”和“没有牙齿的对话场所”,在美国外交战略中被边缘化(81)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美国总统多次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说明这一组织并非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但是,美国政府从未放弃亚太经合组织,仍然试图利用这一组织来扩大与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达到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目标。其次,美国建立了封闭性合作框架,以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与之展开竞争。美国相继推出TP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打造亚太地区新的经济合作机制。最后,美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公开指责中国的外交行为。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过程中相继抛出“转向亚太”和“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概念,具有极强的针对中国的意涵。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美国再次谴责中国的外交行为。中美竞争关系导致的分歧不断,致使此次会议未发表领导人联合公报。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简直是将中美竞争关系公布于众,两国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展开激烈角逐(82)“This Year’s APEC Summit Set Out to Address Problems in the Pacific,but It Only Deepened the US-China Feud”,November 17,2018,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pec-2018-failure-us-china-xi-jinping-mike-pence-tension-2018-11。2020年11月,特朗普虽然出乎意料地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在线上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中继续对中国的外交行为大放厥词(83)Sebastian Strangio,“President Trump to Attend APEC Summit,Official Says”,The Diplomat,November 19,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president-trump-to-attend-apec-summit-official-says/。
应当说,美国并未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作用,反而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分化甚至弱化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建立针对中国的排外性合作框架。相较于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制度建设关注度和影响力的下降,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84)Jenn-Jaw Soong,“Is China Becoming the Core of Regional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Chinese Economy,Vol.47,No.3,2014,pp.3-7.。中国逐渐承担起引领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推动亚太自贸区和亚太共同体建设。
基于此,从十八大至今,除了2019年智利因故未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习近平出席了这期间的所有10次会议。其中,2014年中国再度承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望为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提高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面对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障碍,2015年中国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要着眼长远,完善亚太中长期合作战略框架,为亚太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85)《深化伙伴关系 共促亚太繁荣》,《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0日第2版。。2017年,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愿同亚太伙伴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协同联动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86)《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2日第1版。。2018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巴新莫尔斯比会议上,中国再次指明亚太经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坚持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87)《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9日第2版。。在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世界和亚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88)《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1日第1版。2021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0周年,习近平指出,这30年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30年,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扩展的30年。中方愿同亚太各成员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89)《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3日第2版。。2022年,习近平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强调:“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我们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亚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0)《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9日第2版。2023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落实布特拉加亚愿景,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推动亚太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91)《坚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9日第2版。。
这一阶段,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展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中国主动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原有理念与内容合作,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新发展观”以及互联互通等议题上持续表达中国观点。尤其是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上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线路图》,标志着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的正式开启(92)刘宏松:《中国参与APEC机制30年:角色与机遇》,《人民论坛》2021年第36期。。第二,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提出诸多创新性理念和议题。在亚太经合组织不同场合中,中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亚太伙伴关系和建设亚太共同体在推动经济合作与地区一体化上的重要性,为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注入新活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中国由积极参与者向未来方向的主动探索者和塑造者转变,以积极参与的姿态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与影响力(93)杨泽瑞:《论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第三,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彼此借重,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发展,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这一时期,中国参与的亚太经合组织各类会议都明确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一方面,亚太经合组织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地区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展现良好国际形象的关键平台,也为中国诸多理念和外交政策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提供了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诸多新理念和新路径有助于亚太经合组织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效凸显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团体意识,反映出各成员国共同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愿景。
三 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战略评估
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伴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原则,在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地区稳定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中国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展和技术合作、加强亚太地区联系、处理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应对地区治理危机和挑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太经合组织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平台,中国也成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建设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引领者。
第一,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角色由一般参与者向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塑造者与引领者转变。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初期,由于受到自身实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仅仅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加强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而非经济议题特别是政治安全议题比经济议题更具敏感性,亚太经合组织议题的扩展引起了中国的疑虑(94)田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因此,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保持了一定距离,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扮演着一般参与者的角色与作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体系进程中,多边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准则。同时,自身实力的综合发展也为中国进一步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认知发生变化,将亚太经合组织视为促进经济合作、加强地区联系与稳定地区环境的重要平台,中国逐渐在议程设置、理念指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潜力的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驱动者,对亚太经合组织提供技术、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有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前行(95)赵江林:《亚太经合组织:新阶段、新方案、新主角》,《当代世界》2013年第11期。。
相应地,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倡议能力和议题设定能力也大幅提升。2014年,中国主导亚太经合组织通过《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等,对亚太自贸区可能实现的路径、时间表和目标等进行研究,切实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96)《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第3版。。另外,中国相继提出并践行“亚太经合组织方式”“亚太命运共同体”“亚太自贸区”“亚太互联互通”等理念,在数字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等新领域探索发展路径,指引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方向。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和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97)《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3日第2版。。
第二,中国始终坚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基本理念与主要原则。亚太经合组织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循序渐进、非约束性和灵活务实等为原则的合作方式,有效适应了亚太地区的差异性与复杂性,推动不同成员在经济往来与科学技术上的互动合作。早在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便主张“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四项原则,这与亚太经合组织坚持的互利性、开放性、灵活性与非强制性不谋而合。在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实践中所坚持理念的认知。即使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之时,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仍再次强调“尊重差别、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应坚持通过这种方式为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进入21世纪,中国强化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力度,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符合本地区多样性的客观实际,是各成员加强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亚太经合组织应在吸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今后加强合作赋予新的内涵(98)《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2日第1版。。同时,中国响应亚太经合组织构建亚太大家庭的理念,认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纽带,是确保亚太合作处在正确轨道上的重要保障”(99)《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1月1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711/t20171111_9384056.shtml。可以说,无论是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稳定环境下还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中国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进程中始终强调坚持亚太经合组织基本理念与主要原则的重要性,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中国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观念创新与议程创新。随着经济实力和大国责任意识的增强,中国逐渐主动塑造和引领亚太经合组织的持续发展。中国早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初,就积极促进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1991年11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时,便针对亚太经济形势、亚太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等问题,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的多样性、互利性和开放性三原则。这是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上的首次重要贡献,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00)贺平、周峥等:《亚太合作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4页。。在之后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诸多观念创新,以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持续发展。中国在不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相继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的“四原则”、“五原则”和“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等,有效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联系。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提升,中国针对具体形势提出了“探路者方式”(pathfinder approach)、“亚太命运共同体”、“亚太自贸区”、“亚太互联互通”等理念,进一步赋予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新的时代内涵。例如,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充分表达了广大发展中成员的最大意愿,针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现实发展形势首次提出了“探路者方式”,克服协商一致原则与强化具体行动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101)曹宏苓:《APEC经济合作与中国产业政策选择》,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页。。在议程创新上,中国根据不同地区问题治理的需要,在地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构建自贸区等领域提出诸多中国方案。“9·11”事件后,中国在维护亚太经合组织现有合作方式和原则的同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将安全议题纳入亚太经合组织议程设置中,并进行合理引导和控制。到目前为止,亚太经济组织涉及的安全议题主要包括金融安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卫生安全、能源安全、备灾、反腐败、地区政治安全等(102)刘晨阳:《APEC二十年成就、挑战、未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亚太自贸区路线图(103)苏格:《亚太经合之中国足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充分说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愈来愈得到广大国家的认同。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强调建设和平稳定、共同富裕、清洁美丽与守望相助的亚太。
第四,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关注议题聚焦于经济合作与地区发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一直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核心议程和追求的主要目标,期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建立“亚太自贸区”等诸多理念,其本质在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成员国发展,以推动亚太地区发展。在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中,中国一步步走向亚太,亚太也一步步走向中国,中国已成为绝大多数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104)《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11月20日,https://www.mfa.gov. 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611/t20161120_9384054.shtml,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取得长足进步。在中国及其他成员的努力下,截至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相比30年前平均实施关税降低超过10个百分点,区域总贸易额增长超过7倍(105)苏格主编《APEC 30周年纪念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10页。。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历程充分表明,加强经济合作与促进地区发展是中国关注的关键议题。中国领导人在历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演讲致辞题目几乎都包含“合作”“发展”等关键词,表明中国重视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地区发展中的价值。甚至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初期,中国将开展经济合作认定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唯一使命(106)《江泽民主席在APEC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0011/t20001107_9384009.shtml。中国秉持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经济合作论坛,强调其不能偏离经济合作的宗旨。随着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程度的加深,中国突破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功能的认知,将其定位为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与繁荣的核心平台。习近平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大家庭,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能够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107)《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第4版。。
在促进地区发展方面,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108)《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11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511/t20151118_9384052.shtml。2012年,中国出资设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和“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并向亚太经合组织项目基金捐款,为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作出了贡献(109)《融合谋发展 创新促繁荣》,《人民日报》2012年9月10日第2版。。2016年6月,亚太经合组织首届城镇化高层论坛在中国宁波成功举行,通过了《宁波倡议》,为亚太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110)《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城镇化高层论坛在宁波开幕》,人民网,2016年6月2日,https://finance. people.com.cn/n1/2016/0602/c1004-28406341.html。中国始终强调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完善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架构,确保2025年实现全面联接的目标,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亚太互联互通网络。而且,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打造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的增长点。总体而言,加强经济联系、推动成员间合作、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始终是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五,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彰显开放的地区主义。一直以来,“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基本合作原则,在亚太地区整体合作框架下体现了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呈现多元性,包含东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成员无须像欧盟成员那样承受放弃主权的代价而趋于选择封闭,因而得以维持开放的特性(111)史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APEC方式》,《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第8期。,从而协调不同成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上的差异性。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不同场合中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的重要性。2001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继续秉承‘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为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作出贡献。”(112)《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2日第1版。亚太地区已建立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我们应该支持它们并行不悖地发展,努力形成兼收并蓄、优势互补的亚太区域合作格局。对于区域外机制,我们也要秉持开放包容态度,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113)《推动共同发展 谋求和谐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9日第1版。。2011年4月,胡锦涛强调,我们应该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尊重地区外国家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我们欢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积极参与亚洲合作进程,共同促进亚洲和平、稳定、繁荣(114)《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6日第1版。。习近平强调“开放”的重要性,指出:“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要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115)《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3日第2版。在2022年召开的亚太经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对于构建“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的重要性,指出:“历史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16)《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9日第2版。2023年习近平在出席美国举行亚太经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强调“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指出:“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加强相关区域经贸协定和发展战略对接。”(117)《同心协力 共迎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8日第2版。而且,中国不仅仅将开放的地区主义停留在理念层面上,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建设,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四 中国—亚太经合组织互动与中国地区战略优化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外溢到亚太经合组织的地区合作与制度建设中。如何恰当管控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间的竞争性关系,既对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进一步互动意义重大,也对中美双边关系朝向正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更对有效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不仅要继续深化与亚太经合组织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积极管控中美竞争关系,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地区战略。
第一,明确界定地区战略目标,促进中国地区战略优化。明确地区战略的目标和实施路径对于中国制定更加清晰和有效的地区战略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以建设性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全面参与各类磋商机制,将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推动地区秩序建设,打造战略依托地带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118)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现阶段,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地区战略目标。应当说,作为中国亚太战略的重要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制度支撑。中国可以通过减少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异质性利益,寻找更多的同质性利益,进而扩大共同利益。中国与亚太国家双边层面上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各领域间的交流,不仅能够弥合双方的利益分歧、实现良性互动,也可以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交流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亚太地区存在着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印太经济框架”等诸多合作制度,形成了制度重叠甚至是制度竞争局面。在“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的地区战略优化必须恰当处理亚太地区存在于不同层面的诸多制度,在重视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区分和整合不同机制间的作用。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实现“亚太自贸区”的两条重要路径(119)杨泽瑞:《论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RCEP和CPTPP是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有效补充。中国要推动RCEP与CPTPP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弥合不同地区制度间的矛盾与竞争,彰显地区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120)保建云、李俊良:《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经贸探索》2022年第7期。。而针对美国主导下的“印太经济框架”展现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中国要稳健应对,谨慎对待这一框架小集团属性和竞争特性,倡导开放包容的地区制度合作。
第二,持续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深入发展。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初期,其相关机制的完善和议题设置主要由美、日、澳等国主导。一直以来,中国在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中保持着相对低调、积极合作的态度。但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如今中国在亚太地区、全球社会经济和其他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21)金英姬:《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论与中美关系》,《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5期。,中国逐渐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中心角色之一,转变为地区规则的主动参与者和制订者(122)赵江林:《亚太经合组织:新阶段、新方案、新主角》,《当代世界》2013年第11期。。在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过程中,中国既要针对微观领域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必要合作,同时也要在宏观层面上强调有效的战略对接。其本质在于,要扩大共同利益、弥合利益分歧,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合作关系主导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将竞争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优势领域和广泛分布着共同利益的领域,中国可以推动亚太经合组织议程设置与实践开展,逐步形成机制化合作;也可以在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如经贸合作、地区安全与互联互通等深化互动,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共同体的形成。同时,积极推进中国的外交战略与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目标的联动至关重要。例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经合组织对接,尤其是对接亚太经合组织“后2020时代”愿景和“亚太共同体”建设,将为亚太地区发展与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和空间(123)参见苏格主编《APEC 30周年纪念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17页;杨泽瑞:《论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一方面,互联互通作为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共同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为双方提供了利益的汇合点和战略对接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在亚太地区的展开,在为亚太地区提供诸多公共产品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合作,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发展战略及合作倡议对接,实现协同效应(124)《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第2版。。此外,推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亚太共同体”之间的联结,既可以展示中国倡导合作共赢、强调共同发展的理念价值,也可以为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始终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互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逆区域化和单边主义趋势的回潮造成国家政策选择更加保守和封闭,多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受到冲击。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频繁组建诸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印太经济框架”等封闭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仅冲击着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也破坏着亚太地区的多边主义合作。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包容性和国际主义显著的多边主义理念,既聚焦本地区的合作进程,又强调与地区外的联系,能够成为中国有效管理共同利益、加强地区互动和推进多边主义的战略工具。开放的地区主义也是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在与亚太经合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其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各国可以积累合作经验,增强互信,从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实践奠定基础(125)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使得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可以获得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好处,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成果。因此,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要求中国在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在坚持互利、互惠、非歧视和包容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深化与亚太国家的互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建设。在此基础上,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还应保持对亚太地区外国家参与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保持开放态度,尤其是注重推动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不同地区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从而推动双边与多边、地区与全球的联动发展,使亚太经合组织兼具地区效应和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第四,妥善管控中美竞争态势,塑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仅深刻影响中美双边关系发展,也对中美在地区的互动与其他领域的交往产生重大影响。在影响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各种变量中,大国博弈具有关键性作用。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面临着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国发起的激烈竞争(126)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管控中美竞争态势,既有利于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深入合作,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持续发展。而且,亚太经合组织不仅是中美联系和互动的平台,而且是两国利益交汇的平台,其缓解和协调大国竞争的战略意义日益突出(127)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51页。。在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点与合作方向至关重要。中美两国要在双边关系发展中注入更多的“互惠”理念,以合作者或协调者而非竞争者的身份来定义彼此关系。中国要使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各领域发展不仅仅是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美国。两国应寻求建立如基辛格所称的“太平洋共同体”(128)David M. Lampton,“Reconsidering US-China Relations:From Improbable Normalization to Precipitous Deterioration”,Asia Policy,Vol.26,No.2,2019,pp.43-60;David M. Lampton,“China:Challenger or Challeng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9,No.3,2016,pp.107-119.。另外,百年变局下的国际体系充满着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国际社会中出现的诸如新冠疫情、气候问题等均可以成为推动中美关系走向合作的重要关键节点事件。
结 语
竞合复合关系作为国际政治中行为主体间的常见互动状态,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并深刻影响两国互动方式的转变。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竞合互动历经“合作主导型”、“竞争与合作相对均衡型”与“竞争主导型”竞合关系三个阶段,这种竞合关系的变迁既与中美利益关系的转变与实力对比的变化有关,也与美国对华身份定位相联,更与外部事件冲击下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历经初始阶段、深化阶段和拓展阶段,在坚持和倡导亚太经合组织的基本理念与主要原则以及推动其观念创新与议程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亚太经合组织的一般参与者到引领组织发展的塑造者和变革者的身份转变。
就目前而言,中美竞合关系的复杂态势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现实,并以进行时方式持续演进,不断塑造着中美在不同领域中竞争与合作互动关系的结构变化与进程变迁。而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竞合关系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将中国锁定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战略竞争”“多层次竞争”与“体系竞争”等,逐渐完善以“战略竞争”为主导的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现阶段,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互动关系逐渐走向以竞争为主导,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更是成了美国对华竞争的核心展开区域。2023年,美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举办了一系列相关会议,这为其扩大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实力提供了良好机遇,也为其重新思考和校正亚太政策营造了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应对美国发起的竞争,探索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好互动,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互动关系,实现中国地区战略的优化,成为当前不得不继续深思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