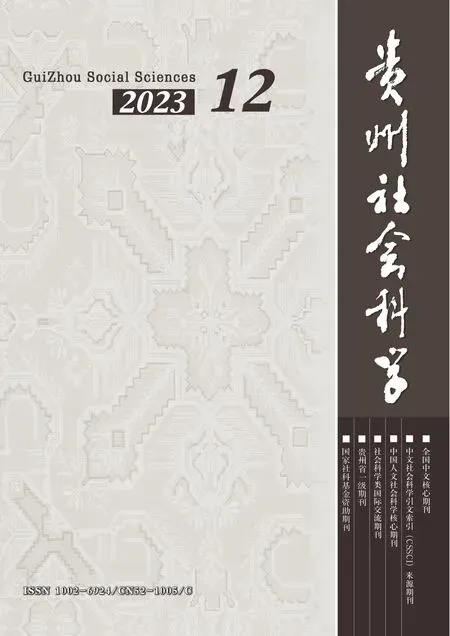以教育学科为筹码:战时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新探
江明明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因与校方当局意见不合,于1924年5月爆发学潮,随即远走上海,师生合作,白手起家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并以教育学科闻名沪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主体迁往贵阳,是为“黔校”(亦称“筑校”);部分师生留在上海继续办学,是为“沪校”。①由于抗战中经济形势的恶化,作为私立大学的大夏大学,黔沪两校生存均极困难,改为国立大学从而接受政府经费补助,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为此,大夏大学不断向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请改为国立。而教育部的考虑,则是将私立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夏大学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贵州省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的困境,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若改成“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大学就极有可能要永留贵州,这是大夏大学师生所不愿意的。由此可见,大夏大学向教育部商请改为国立,关键问题是“大夏大学”校名的保留与否。大夏大学校长为国民党元老、贵州巨绅王伯群,并拥有诸如何应钦、孔祥熙、孙科等一批位居“党国枢要”的强势校董。为改国立并保留原校名,大夏大学动用各种政治资源,自1938年至1942年,与教育部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博弈,尽管最终改国立失败,却在维持私立的情况下获得国民政府巨额补助,从而渡过难关。
以上是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的大致经过。对于这一问题,韩戍通过利用多方档案,详细梳理了大夏大学与教育部之间的博弈过程。②高振元通过进一步研究,不仅纠正了韩戍的部分观点,并且注意到了大夏大学沪校因为部分师生参加汪伪政权,成为大夏大学改国立问题中的重要“政治障碍”。③对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的研究,按理说至此已无余蕴。然而笔者在研究大夏大学最负盛名的教育学科时却发现,由于全面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及其教育学院迁到贵阳,而贵州本省并无国立大学和师范学院,再加上国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想以大夏大学充实贵州高等教育,一方面又极力加强对师范教育的控制,多种因素的交织,使教育学科在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中成为极其重要的砝码。因此,本文拟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聚焦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在本校改国立风波中的具体因应和历史命运,以期在此问题上有所拓展,并由此探讨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教育统制政策和教育资源配置问题。
一、迁黔后的大夏大学及其教育学科
1924年的厦门大学学潮,最重要的导火索是教育科主任欧元怀无故遭校方解聘,由此引发教育科学生率先抗议,并逐渐酝酿成全校规模的学潮,最后导致部分师生离校创办大夏大学。正因如此,专长教育学的欧元怀成为大夏大学的灵魂人物,长期担任副校长并实际主持校务。大夏大学自创校之始,教育学科即占特殊地位且最负盛名。自1924年至1937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夏大学教育学由“科”升为“学院”,下设教育心理系、教育行政系、社会教育系,并办有师范专修科,大兴民众教育和电化教育,成为国内教育学重镇。④当时各地学子到上海求学,若欲深造学教育,多半会选择大夏大学的教育专业。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并成立了联合大学第一、第二分部,共同内迁。第一联大迁往江西庐山,第二联大迁至贵州贵阳。⑥1937年9月24日,两校的先遣代表抵达庐山,开始筹备第一联大,租赁了四座大楼,并于11月1日开学上课。但随着战事吃紧,江西亦岌岌可危,第一联大的师生乃于12月全部下山,转赴重庆。1938年2月,鉴于两校实情和内迁现状,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召开联合大学行政委员会议,议决自1938年4月起两校“仍各分立”,以设在重庆的第一分部为复旦大学,设在贵阳的第二分部为大夏大学,“两校的教职员、学生各返原校”。⑦至此,联合大学宣告结束。两校皆为沪上私立大学之翘楚,又有联合内迁的这层关系,故此在后来改国立进程中,复旦和大夏都极为关注对方动态,互相参照。在复旦保留校名改国立成功后,大夏在向教育部申改国立时更是不断要求“援复旦前例”。⑧
之所以将设立在贵阳的第二联大划归大夏大学,则与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同贵阳的关系分不开。王伯群乃国民党元老,贵阳巨绅,是护国战争中策动贵州独立的关键人物。联大二部之所以迁设贵阳,就是王伯群的决定,并在“事先曾受不少师生反对”。但王氏“料定战事非短时期可以结束,西南大后方将为抗战之砥柱,而贵阳与重庆交通尚便,且又为高等教育之处女地,需要大学之灌播”。⑨因此,当时大夏大学的师生多数都选择长途跋涉前往贵阳的第二联大。既然如此,则第二联大自当划归大夏大学办理。除此之外,大夏大学亦有部分师生因故不及内迁,且考虑到失陷地区青年也有求学需求,大夏大学遂决定留守上海的师生租赁其他房舍,继续办学。由此,大夏大学在抗战中形成了黔校和沪校两部分,黔校为主体,沪校为分校。
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后,凭借王伯群的人脉,颇受贵州当局的重视和照顾。当时迁往贵阳的行政和文教机关甚多,惟大夏独能占用“最为宽敞、最具规模”之讲武堂。⑩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也因为王伯群的人脉运作,很快便调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成为大夏大学在省政府的有力奥援。有此基础,大夏大学很快便适应环境,再度发展起来。大夏大学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便开始积极以教育应对国难,改变教育宗旨,推行“国难教育”“救亡教育”乃至“民族复兴教育”,并由此调适教育学科。随着抗战军兴,形势丕变,大夏大学的教育宗旨自然再度改变,正如欧元怀所言,此时各级课程,“尤着重于战时教育及精神训练,以为强化抗战力量之准备”。而教育学科,以其在大夏大学的重要地位和学科特性,更是在大夏的抗战因应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大夏教育学院在迁移之初,依然保持着之前下设教育行政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社会教育学系的组织架构。甫一安定,教育学科的师生便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积极行动,编辑《贵州晨报》副刊《教育旬刊》,开设“贵州教育研究”讲座,进行贵州教育调查,编制抗战态度测验。这其中,有的如抗战态度测验等,直接关乎抗战,有的则是致力于通过教育对贵州进行研究和开发,间接为抗战贡献力量。
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夏大学来黔后迅速开展的社会教育。1938年3月,大夏大学就与贵阳县政府合作,“合办花溪农村改进区”,旨在“以教育经济健康为出发点,期对区内民众生活,作切实之改进,以增强抗战建国力量”,由社会教育系主任喻任声兼任该区主任,主持其事。为此,该区开办贫民疾病治疗所二所,布种牛痘并诊疗贫民疾病;组织合作社二十所,社员总数计六百四十三名,贷款总数达七千二百九十元;创办小本贷款一所,救济兼营小本商业之农民;设立民众学校五所,占地计三十余亩,鼓励农民种桐;成立民众阅览室一所,提供书籍杂志供民众阅览。除此之外,大夏大学还在花溪成立了农村改进社和农村抗战青年团两个民众团体,将乡村领袖和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共同改进地方事业。花溪农村改进区试办半年后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教育展览会以展现改进成果。除展览外,还举行了关注农村儿童成长的儿童音乐竞赛会、儿童运动会和宣传抗日的战时教育讨论会、民众演讲竞赛会,抗敌宣传游艺会。展览会显示了大夏大学在花溪农村改进区的巨大成就,试办期顺利结束,“当地农民亦至为感奋”。此后大夏大学极力扩充花溪改进区的范围,“以期收更大的效果”。大夏大学因在花溪的社会教育成绩卓著,后特受教育部嘉许。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训令私立大学停办教育学科时特许大夏大学继续办理,同时也要求大夏大学“今后应特别着重职业学校师资及社会教育专门人才之训练,以应建国之需要”。受此指令,大夏教育学院开始积极调整,期望自身能在抗战教育中发挥作用,以图生存发展。1938年10月,在邰爽秋的规划下,大夏教育学院将此前的教育行政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合并,组成普通教育学系,内分教育行政和教育心理两组;社会教育系继续保留,其下分设图书馆学组、民众教育组、电化教育组;增设职业教育系,内分农林、工艺两组。在大学教育学院创办职业教育系,这是大夏大学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职业教育系也获得贵州省政府支持,拨西社坡、瓦渣坡两处山地赠予大夏大学,以为职业教育系农林组造林之用。
调整后的大夏大学教育学科以社会教育为主体,在贵阳继续发展。欧元怀在演讲中向大夏全体员生呼吁,要“协助地方教育行政当局,推动社会教育,扫除文盲”。为此,大夏教育学院与师范专修科合作,组织进行贵州教育调查,并接受教育部指令,由社会教育系主任喻任声视察贵州社会教育。教育学系于1939年11月决议该学期进行“贵州中学或小学教师生活调查”“人格教育读物之编辑”及“训育应用测验及表格之编制”等专题研究。社会教育系则与基督教青年会展开合作,开办民众夜校。大夏大学还大力借助电化教育这一学术利器对贵州民众进行抗战教育教育和动员。1939年5月,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研究会与贵州广播电台合作举行播音演讲,唤起民众的抗战情绪,向民众灌输抗战中的生活常识,通过启发民智来动员民众积极抗日。1941年4月起,社会教育系更将对民众的电化教育常规化,“定于每星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在校内放映教育电影,实施播音教育,附近民众来坪观听者甚众”。因为兼办社会教育极具成效,大夏大学还受到教育部特别经费奖助。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大夏大学自该年度秋季学期起教育学系停止招生。1941年6月,行政院取消大夏教育学院,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议案获得通过。1941年9月,大夏大学黔校就接到教育部取消教育学院,将其余四院改为三院(法商学院合并)的指令。紧随其后,大夏大学的师范专修科也于1942年停办。以上就是大夏大学教育学科迁入贵州乃至最终被取消的历史概况。由于贵州本无最高学府,因此随着大夏大学及其教育学科的入黔与发展,对贵州的文教事业推动甚力。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如“贵州全省中等学校校长,绝大多数由大夏教育行政系及教育心理系毕业生担任。至于社教机关,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负责人,亦类为社教系毕业生充当”。“全省各地的教育机关,中等学校及县市党部等,因为大夏毕业生的增加,几乎变成了青一色。为此也惹起了旁人的羡慕,更使旁人嫉妒。”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对贵州地区的重要性,它作为大夏大学改国立的筹码之分量,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若想在贵州新创一所国立大学或者国立师范学院,就必须将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并入或拆解。换言之,教育学科之所以卷入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并成为部校双方博弈的筹码,也就势所必然了。
二、改国立预设下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的保留
正当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在贵阳逐渐发展之际,教育部却于1938年7月颁下私立学校停办教育学科的一纸训令。1938年初,陈立夫接替王世杰担任教育部长。一方面,陈氏对师范教育极度重视,认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另一方面,重兴高师教育也成为当时教育界面对抗战形势而发出的强烈呼声。两方意见合流,再加上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教育统制,教育部便开始有意将师范教育单独办理或收归国立大学办理。经过酝酿,教育部计划于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五校中各增设一所师范学院,并在湖南单独设立一所国立师范学院。而与之对应,教育部则下令自1938年度起各私立院校停办所设之师范或教育学专业。
该令一出,按理说大夏大学教育学科亦应在停办之列。然而蹊跷的是尽管教育部令“私立各大学之教育学院及教育学科取消”,却“惟大夏大学之教育学院保留”。大夏大学自以为本校教育学院得以保留的原因是“办理有年,成绩卓著”,因此备受鼓舞,积极调整教育学院的建制,以求更好地因应抗战建国之需要。然而奇怪的是,正当大夏大学教育学科更为蓬勃发展之时,却又于1941年收到教育部指令,令其自该年9月起,停办教育学院,并将教育学院各系学生分发至其他学校借读。教育部在1938年禁止私立学校办理教育学科时独独保留大夏大学,为何才隔三年,并且是在大夏大学教育学科蓬勃发展之时,却又突然令其停办?由此可见,大夏大学自认为其教育学科在1938年独得保留的关键原因是办学成绩卓著,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试问,如果当初是因办学成绩卓著而保留,此后办学成绩愈发显著,为何却反遭停办命运?其实,这一切的关键,乃是教育部一直预设大夏大学将要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贵州由于地处偏远,文化落后,近代以来一直希望建设一所贵州大学,以缓解本省的高等教育困境。早在1937年以前,屡经贵州各界人士请求,国民政府就已决议设立国立贵州大学。“后因抗战军兴,暂未执行”。与此同时,也正因抗战军兴,原本过分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校纷纷迁往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缺乏的内陆省份。因此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教育部极力运作,拟借此战时内迁之机,对全国高校进行资源整合,使全国各省皆能设有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从而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平衡。而具体到贵州,则大夏大学是唯一驻于省会贵阳,且拥有文、理、法、商、教以及师范专修科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因此站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立场而论,如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实为解决贵州拥有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这一目标最为便捷省力的办法。不仅如此,当时贵州亦无师范大学,而国民政府已有计划,要在“全国分区设立独立之高等师范六校”。而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又为大夏大学的“王牌专业”,大夏大学如改为国立,其教育学科自能兼办师资训练,解决贵州无师范大学的问题。更何况,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也绝非教育部单方面的意愿。早在1938年4月,就有传闻大夏大学正在进行改国立事宜。也正是在此时,教育部在指令私立大学停办教育学科时特许大夏大学继续办理。找到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也就不难发现,由于教育部和大夏大学均有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的意向,尽管尚未落实,然而在教育部眼中,大夏大学已是预备中的“国立贵州大学”。其他五所国立综合大学在没有教育学科的情况下尚需增设师范学院,而预备成为“国立大学”的大夏大学本就拥有极富盛名的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当然必须保留。这样一来,大夏大学一旦实现国立,则可直接以国立大学的身份,将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改为师范学院。反而无需像西南联大等国立大学那样再增设师范学院,贵州亦不必再单独设置国立师范学院,更是省却了一大笔经费,可谓极具“性价比”。
由此可见,大夏大学之所以能成为私立大学中唯一保留教育学科者,原因绝非仅是其自以为的办学成绩卓著,而是因为教育部已经预先将其视为“国立大学”了,自然可以“继续训练师资”。同时,这也反过来说明,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的雄厚实力,亦是教育部希望将其改为国立的重要砝码。那为何1941年教育部又下令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停办呢?则和大夏大学自1938年以来的改国立波折密切相关。
三、改国立风波中大夏大学教育学系的停办
关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1941年被教育部勒令停办,据当事人,大夏大学创始人,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的欧元怀所言,乃是因为此时国民政府决意在贵州创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在政府的主导下专门办理师资训练,以便“操纵其思想,从而间接统制青年与儿童的思想”。如此一来,为了避免专业设置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自然要下令停办。同时,刚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要等待四五年后,才有毕业生”,为了使其能迅速培养出师资,国民政府当局遂不惜“摧残我校的教育学院”,将其教育学系的学生分发至贵阳师范学院借读,使其能迅速充实,于创校之初即有各年级学生。由此反推,亦可佐证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之所以特许大夏大学保留教育学院,除了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声誉卓著外,当时贵州未有专门办理师资训练的单独师范学院,亦是重要原因。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创设与否,又与大夏大学改为国立的波折密切相关,并由此引发了1940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学教育学系先行停办的危机,可视为最终停办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的预演。
1939年1月31日,大夏大学正式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并于2月由王伯群借赴渝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之机晋谒陈立夫面呈备忘录,然未得回复。及至该年5月,大夏大学当局再度派王毓祥、王裕凯为校方代表向教育部接洽,希望改为国立,并提出两套方案:“一则黔沪两部均改国立,一则只将黔校改设,沪校仍予维持原状。若依前议,则请准保留校名,若依后议,则黔校更改校名,应请确定开办经费及经常费。至沪校方面恳赐一次拨给设备费十万元,并按月照现在补助款额补助沪校,俾得致力发展”。教育部将大夏大学的诉求提交行政院,然而行政院批复的结果则是“缓议”。
大夏大学与政府间关于改为国立的分歧,关键在于校名问题。依照政府的意愿,大夏大学自当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永留贵州。而大夏大学方面,学校乃师生们在反对厦大当局蛮横专制的学潮中共同创立,自创办以来,筚路蓝缕,极尽艰辛,校名凝聚了师生们的深厚情感,且大夏大学发展迅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拥有自身的历史传承。因此,改名贵州大学遭到大夏大学毕业校友的极力反对。而王伯群作为出身于贵州豪绅的政客,如若将大夏大学改成国立贵州大学,则可成为自己主政贵州的政治资本,因此其对大夏大学改名的态度并不激烈。但在现实层面,大夏大学不改国立,则难以生存。1939年6月在商议改为国立的校务会议上,大夏大学当局甚至讨论到如不能改为国立,学校是否还能继续办理的问题。故此,为了能顺利地改为国立,同时校名又不致消灭,大夏大学不断地提出折衷方案,如黔校改成国立贵州大学,沪校仍保留私立大夏大学的校名,而必须达到的目的则是黔沪两校皆能获得一定补助以求生存。然而,教育部从节省经费和教育统制的角度着眼,自然不愿为大夏大学沪校增加额外的补助。另一方面,大夏大学沪校以傅式说为代表的部分师生投靠了汪伪政权,成为大夏大学尤其是沪校的“政治污点”,更使大夏大学改为国立、保留校名、补助沪校的诉求又增添了一层障碍。傅式说是与欧元怀并列的大夏大学创始人之一,长期负责大夏大学的财会工作,是大夏大学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傅早年留学日本,交游甚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快便参与了汪伪集团主导的政治活动,由此遭到社会指责,并牵连大夏大学。由于傅式说一开始并未公开投敌,故此1939年大夏校长王伯群还为之辩解:“傅筑隐先生留东日久交游甚广,处此非常时期,不免遭人疑虑”,并宣称“客冬以还傅先生为表明心迹并爱护大夏计,即息影沪寓,不问校事”,撇清傅与大夏的关系,同时强调“全校师生莫不忠心耿耿”。但这一辩解很快便随着傅式说公开出任汪伪“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等要职并被重庆国民政府正式通缉而无形瓦解。不仅如此,受傅式说影响,大夏校内严恩祚、张素民、卜愈等一批师生均投靠汪伪集团,更使得大夏沪校声名狼藉。除此之外,第三党也趁机发难,在大夏沪校组织“护校会”扰乱视听。尽管大夏校方努力与汉奸师生撇清关系,但这一切都使得大夏沪校在重庆国民政府眼中“益滋疑虑”,成为大夏大学改国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政治污点”。
1940年6月11日,与大夏大学同在贵阳的私立湘雅医学院申请国立获得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69次会议批准,私立湘雅医学院于是年8月正式更名国立湘雅医学院,教育部每年拨付其日常费用20万元。同时,湘雅医学院附属的湘雅医院、湘雅护士学校则仍保持私立性质。湘雅医学院成功改为国立且保留校名,且附属机构仍维私立的情况使大夏大学看到了自身改为国立且保留校名的希望,为此,1940年6月15日,王伯群再度致函陈立夫,“重申前请,除本校上海部分与上陈情形不同,仍拟维持现状外,所有本校贵阳部分,拟恳钧长准予援照最近贵阳湘雅医学院前例,于二十九年秋季改为国立以利进行,实为公便”。换言之,援湘雅例,此时大夏大学改为国立的方案是黔校改为“国立大夏大学”,沪校维持私立原状。这一方案虽然不再要求对大夏大学沪校提供补助,但大夏大学此举仅是因湘雅成功而援例申请,并未如教育部所希望的那样改成“国立贵州大学”,自然难得教育部首肯,教育部的回复仍是“暂从缓议”。
不仅如此,或许是为了敲打大夏大学,教育部还在驳回其国立诉求的两个月后,即1940年8月指令大夏大学自该年度秋季学期起教育学系停止招生。教育部为何于此时发出停办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中教育学系的指令?这和当时陈立夫等人对贵阳师范教育的设想有关。1940年1月陈立夫曾经前往贵州视察,并指示“师资进俸与区域分配,亟须改进”,有意要在贵阳设立国立师范学院。而在此前,由于大夏大学迁入贵州,贵州省的中小学师资培养几乎由大夏大学教育学科所“包办”。因此,如若创办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势必要取消私立大夏大学的相关教育学科,以便维持国立师范院校对师资培养的“垄断”地位。
那为何只是取消大夏大学的教育学系,而非整个教育学院或职业教育系和社会教育系呢?一方面是因为此前教育部已有规定,准予保留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必须严格限制其教学范围和培养目标,改办乡村及社会教育系等,作为专门造就职业和社教师资的培训机关”。另一方面参照后来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学科设置我们可以发现,一般的师范学院,其学科设置多是遵循教育学加上其他各种专门学科的模式,贵阳师范即拟“暂设教育、国文、数学、外国语四系。”而且,从后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果真停办时各系的结局来看,也只有“教育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会教育系和职业教育系学生则被分发到其他学校。由此可见,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中和贵阳师范学院的学科设置相冲突的只有教育学系,故1940年8月教育部指令其取消的只是教育学系。这也说明此时教育部对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并无根本上取消之意,只是借机敲打。经过王伯群等人利用自身人脉的运作,或许也是因为此时贵阳师范大学尚未筹备就绪,最终教育部取消前令,核示大夏大学“教育学系本年度仍准招生”。大夏大学教育学系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一年后,随着大夏大学国立化问题的继续推进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正式筹设,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最终还是迎来了停办的命运。
四、再改国立博弈中教育学院的“牺牲”
1941年,大夏大学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很多教授也迫于生计而离校他就,大夏大学当局不得不再次为经费问题四处奔波。要长远解决这一难题,改为国立是大夏大学唯一的选择。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大夏大学改为国立,主要障碍有二:一是校名问题,改“国立大夏大学”还是“国立贵州大学”;二是政治污点,傅式说等一批大夏大学教授投靠了汪伪政权。随着大夏大学在校名问题上的不断妥协(黔校改名,沪校如旧但放弃补助),这一“政治污点”在大夏大学改为国立问题中的分量逐渐凸显。
尽管大夏大学校方、学生都努力与傅式说等投降教授划清界限,积极斗争。如在汪伪政府成立,傅式说在其中出任要职后不久,王伯群就立即在贵州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汪傀儡的伪组织,对于抗战前途有利无害”的播音演讲。大夏大学沪校学生则组织了上海市学生界讨汪总会大夏大学分会和上海市各大学讨逆协会大夏大学分会,积极发表宣言,进行罢课,以表明自身反对投降,坚决拥护重庆国民政府抗战的立场。然而,殊堪玩味的是,由于傅式说与欧元怀、王毓祥并列为大夏大学的“创校三巨头”,且长期负责大夏大学的财务会计工作,他的名字和大夏大学几近不可分割,因此大夏大学若公开批判傅式说,很容易引起别人对大夏大学与其关系的不当联想,从而导致适得其反,洗刷不清。所以,大夏大学校方,“无论是沪校还是筑校当局,其在各个场合涉及汪伪问题,均表示忠党爱国,而对傅式说等‘汪派’师生闭口不谈”。然而如此一来,在别人眼中,大夏大学亦有“包庇”傅式说等人之嫌,使自身在国民政府眼中变得“可疑”。
王伯群在大夏大学改为国立屡次不得要领后曾与陈立夫面谈,陈氏婉言相告:“在教育立场说大夏大学应改国立,如在政治立场恐弄巧成拙”。为何在政治立场上大夏大学改国立是弄巧成拙?陈立夫后来坦言自己“决无消灭大夏大学之意”,但大夏大学因为有傅式说这一“政治包袱”,自然不能援复旦大学例而改为国立。更有甚者,不仅教育部对沪校傅式说投敌“终怀成见”,就连任职教育部的大夏大学毕业生“亦不免同此见解,致对(黔沪)两校态度竟生轩轾”,不肯帮忙。由此,如何甩掉这一“政治包袱”,或者说如何洗刷自身的政治嫌疑,成为大夏大学方面的重要任务。王伯群一方面极力劝促大夏大学沪校西迁贵阳,从而自证清白;一方面则以大夏大学黔校教育学院为“投名状”,向政府输诚。
大夏大学沪校西迁贵阳的计划因沪校负责人的反对而最终作罢,牺牲教育学院以换取政府的谅解则逐步进行。陈立夫在向王伯群明言大夏大学改国立的关键在政治方面后,接着就建议大夏大学“可先将教育学院先改为国立师范学院,其余四院改为三院继续保持私立”。王伯群迫于无奈只得“原则上同意先将大夏大学最为重要的教育学院改为国立师范学院,扩大补助款,并待机再谋求改国立”。双方的“交易”一旦敲定,教育部迅即就向行政院提交通过了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国立师范学院的提案,不久,大夏大学请求政府特别补助十万元经费的提案也在行政院获得通过,牺牲教育学院以换取十万补助和再图国立的交易就此达成。很快,1941年6月,行政院通过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取消,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议案,1941年9月,大夏大学筑校就接到教育部取消教育学院,将其余四院改为三院(法商学院合并)的指令。而对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现有学生,教育部明令指示如下:“教育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教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教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一律借读四年毕业,毕业时仍由本校发给毕业证书”。紧随其后,大夏大学的师范专修科也于1942年停办。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毫无疑问是大夏大学为了维持生存,改为国立从而向国民政府奉献出来的“牺牲品”。并且,就对教育学院的处置来说,大夏大学可说亦被国民政府“欺骗”。最初陈立夫提出的建议是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国立师范学院,换言之,应该是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主体而“升格”成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但最后的事实却是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取消,另外成立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并且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亦只有教育学系的学生进入贵阳师范学院借读。由此可见,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取消,固然是贵阳师范学院成立后国民政府意欲统制师范教育的结果,亦是大夏大学在政校博弈中失利抛出的牺牲品。也正因如此,大夏大学校方才会在事后的论述中对政府此举充满怨怼。不仅如此,大夏大学黔校教育学科的“牺牲”,乃是为了洗刷沪校的“政治污点”而被迫向国民政府“输诚”之举,由此亦引发了大夏大学黔沪两校之间的矛盾。依照大夏大学黔校总部的设想,原本无须牺牲黔校教育学科,只要大夏大学沪校内迁贵阳,与黔校合并,即可解决危机,自证清白。一方面,此时大夏大学沪校在政治、经济上皆“问题日益严重”,并且“教部对沪校早存歧视,饬令停办之说近已有具体表示”,因此内迁是最好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大夏大学黔校若想继续谋求国立,还得再度牺牲其他学院,牺牲的缺口则由沪校内迁加以弥补。当时大夏大学为改国立曾有一方案:“将大夏大学现有之文法二院拨归贵州大学,大夏大学仍保存原有之理商二院,合自沪待迁教育学院,每院二系,共三院六系仍保存私立性质,再由部除现存补助费四十一万元外加拨二十万元,俾经济可以维持。”不难看出,该方案乃拟继黔校教育学院后再度牺牲文法二院,以助教育部创办国立贵州大学,亦借此表明“政治忠心”和换得筹码,希望能从教育部获得更多补助。若沪校西迁,尤其是教育学院能加入黔校,则可弥补文法二院的损失,组成三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建制并由此获得教育部补助,继续维持私立大夏大学于不坠。
然而,黔校总部的建议并未得到沪校负责人鲁继曾等人的赞同。鲁继曾对教育部因为个别人员附逆就对大夏大学歧视打压的做法极为不满,觉得这完全忽视了沪校大部分同仁坚守民族大义,恪尽职守维持大夏大学的忠贞与努力。由于自己身为沪校负责人,更感到教部的歧视乃是对自身人格的质疑,由此他在致王伯群的信中不禁反问:“根据现在沪校学生人数而言,是否足以证明本校在沪之声誉并未因少数人之行动而降低,且学生对于本校之信仰并未减退?”“教部对于现在沪校主持校务人员是否不能信任?”甚至因此提出辞职。不仅如此,作为与欧元怀并列的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的创始人,鲁继曾对于黔校因为改国立而将教育学院牺牲的做法更难表赞同,认为“部令裁并院系,影响殊大,深为系念……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尚未开办,而我校教育学院竟先受裁撤,将来教授学生如何安插善后,尤令人焦虑”。有此先例,沪校自然不会愿意再将教育学院西迁合并。此后尽管王伯群等再三建议沪校迁筑,鲁继曾等仍不为所动,甚至宁愿前往香港创办分校,亦不肯内迁贵阳与黔校合并。教部对大夏大学沪校的猜忌歧视和对黔校教育学院的摧残,对教育学科创始人鲁继曾的打击之深,由此可见。而通过大夏大学黔沪两校在内迁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沪校宁愿赴港校也不愿迁筑,我们也不难发现,大夏大学黔沪两校之间已生嫌隙,无法为改国立而团结协作。沪校的不合作,也使大夏大学失去了再度牺牲以谋国立的资本,成为其最终只能依靠强势校董以私立身份获取补助的重要因素。
五、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一大批私立大学纷请改为国立,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战时经济形势恶化,不改国立无以图生存。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同大学在谋求改为国立时,亦各有其资源和策略。而大夏大学在改国立风波中,除了已被研究者揭示的强势校董这一政治资源外,实力雄厚的教育学科,亦是其改国立的重要砝码,并且,这一砝码是和强势校董资源结合起来运用的。正因如此,大夏大学最终虽然依靠强势校董资源,在维持私立的情况下获得了政府巨额补助,表面上看似在与教育部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但也因此失去了自己最负盛名的教育学科,并引发黔沪两校的嫌隙,损失不可谓不惨重。而在国民政府及教育部方面,原想通过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以解决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困境。但最终却在既给予大夏大学巨额补贴以维持其私立的同时,又额外创设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两所“不经济不负责而且毫无设备有名无实”的大学,被蒋介石怒批为“以国家教育为儿戏”,可谓一败涂地。这种“双输”局面的形成,既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举措的恣意、专断有关,又和各大学汲汲于本校利益,缺乏全局观念密不可分,由此亦折射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统制的困局。
站在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立场,由此亦反映出其“教育救国”的无奈。大夏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学科史上都是极其特殊的存在。一批师生出于对厦门大学校方举措的不满,出走上海,师生合作创办了大夏大学。既是从压迫中反抗出来创建自己理想中的学校,自然要与已有学校有所区别。该校师生在规划学校时立志要“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注重师生合作、自由解放、读书救国。由于教育科的师生在离校风潮和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大夏大学创建后教育学科即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学科的核心人物欧元怀、鲁继曾分别长期担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教务长,实际管理校政,可以说,整个学校的实际运营,皆是贯彻教育学科的相关教育理念,可视为教育学科的“演练场”。欧元怀、鲁继曾等教育学科同仁,皆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出国学教育,学成归国则投身教育以图救国。正因秉持“教育救国”理念的欧元怀等人惨淡经营,大夏大学及其教育学科才得以逐渐发展,以一私立大学的地位,其教育学科却蜚声全国。
“九一八”事变前,大夏大学的教育方针还只是“为教育而教育”,认为只要积极贯彻先进教育学理念,使学生在学识及体格上的修养能日臻完善,就算已尽教育责任,即可完成“教育救国”之任务。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夏大学教育学人“觉国家民族日濒危殆,教育方针如不变,教育根本就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开始大力实施“民族复兴教育”和“救亡教育”。“七七”事变后,大夏大学教育学科更“着重于战时教育及精神训练,以为强化抗战力量之准备”,开设职业教育,着重进行社会教育,积极对贵州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和战争训练。可以说,自抗战爆发以来,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就积极调适以因应国难。然而讽刺的是,正在大夏大学积极以教育进行抗战之时,国民政府却极力加强教育统制,尤其是对师范教育实行“垄断专营”,全面禁止私立大学办教育学科。大夏大学之教育学科最初被教育部特许继续办理,还以为是自己多年来的办学实绩获得国家认可,故而喜不自胜,实不知其免遭停办的真实原因乃是被教育部视为“预备国立大学”。大夏大学迁黔后凭借校长王伯群在贵州的强大人脉,副校长欧元怀又出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在贵州的发展可谓一枝独秀,尤其是教育学科,几乎垄断了贵州省的师资培养。一所私立大学取得如此成就,自然引起其他方面的羡慕与嫉妒,也势必引起教育部重视,如能改为国立自然一举两得,否则势必要在扶持新成立的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之同时,压制已在贵州强势发展的大夏大学及其教育学科。而大夏大学沪校部分此时又正好有着投靠汪伪政权的“政治污点”,故此,为了保全本校,大夏大学教育学科最终难免成为挽救学校,向教育部“输诚”的牺牲品。私立大学之“教育”不仅不准“救国”,甚至要因“救校”而无奈牺牲。“教育”何以“救国”,“国家”又何以“救教育”,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令人嘘唏。
注 释:
①大夏大学教务处:《大夏大学学生手册·校史》,大统书局,1947年,第1—4页。
④江明明:《“教育”何以“救国”: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1—124页。
⑥欧元怀讲,宋成志记:《光荣的校史》,《大夏周报》第23卷第1期,1946年11月15日,第2页。
⑧周蜀云:《我在大夏的教学生活》,陈明章编:《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52页;高振元:《私立大夏大学与近代中国政治(1924—1951)》,第69—70页。
⑨欧元怀:《大夏大学的西迁与复员》,《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2期,1947年12月15日,第47页。
⑩周蜀云:《我在大夏的教学生活》,陈明章编:《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第52页。
整个混合汽修正过程很短暂,大约10s多就结束了。在混合汽修正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混合汽浓,氧传感器λ值为0.6,发动机抖动,缩短喷油时间;混合汽变稀,氧传感器λ值趋于1,发动机运转趋于平稳。由此可见,该故障车发动机抖动是由于混合汽过浓所导致的。
——从张骞在大夏所见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