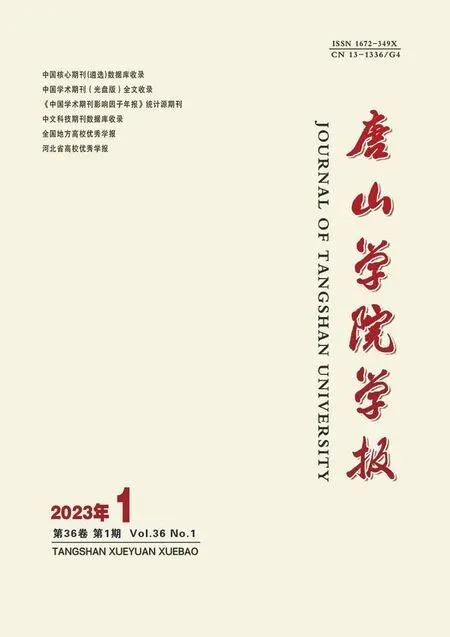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以价值互认、理论互动和实践互助为视角
高元博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抗日战争的洪流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秩序,促使其不得不在研判时局中尽快作出人生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边区凭借正确的抗日政策和开明的政治生态吸引了4万余名知识分子赶赴延安并融入那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1],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为边区建设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学界有关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选题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赶赴延安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政策、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革命贡献三个方面(1)例如:刘悦清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王海军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王海军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龚云的《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17期;杨军红的《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博士论文;张俊国、孙小利的《延安时期党凝聚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及其成效》,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5期;莫子刚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来知识分子之政策》,载《求索》2021年第3期。。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学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体现出“单向性”特点,即多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表征为“中国共产党政策动员→知识分子被动行动”的单向关系。本文试图打破这种单向性研究模式,从价值互认、理论互动、实践互助三个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以期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一、价值互认
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体的客观实践,对对象的现实态度和印象决定了主体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中国共产党是如此,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都从自身出发去认识和定位彼此的角色,试图通过对彼此的价值重估来为自身下一步实践找到基本参考。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重估认识到了知识分子抗日的革命性和群体积极性;知识分子也通过对比国共两党的抗日实践和知识分子政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抗日、团结民主的政党这一印象,最终认可并倒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积极抗战的一方。
(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和分析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从建党之初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经历了从定义到排斥再到争取的曲折发展之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将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群体。如陈独秀明确将知识分子确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2];毛泽东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3]。1927年,在国共两党的多次军事冲突中,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倒向了国民党一边,中国共产党逐渐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大失所望[4],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5]。大革命的失败和“左”倾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促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关门主义”,将知识分子排斥在了革命阵营之外,对其革命的积极性总体上持怀疑态度。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错误方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6]621由于错误的方针政策得到纠正,加上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趋于理性。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6]151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将知识分子作为争取和团结对象的正确方针。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有着很强的革命性,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游击战争中,他们都是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6]641。在正确的政策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实行优待政策以吸纳知识分子,延安由此“成了众望所归的抗战热土,成了抗日救亡和流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7]。
(二)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在探讨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必要明确两个基本问题,即究竟何为知识分子以及延安知识分子的基本构成。在美国学者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看来,“那些创造、传播、运用文化的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8]。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抗日洪流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具有以上特点外显然还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特征,他们有着高涨的抗日热情,渴望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但由于知识分子不属于独立的阶级,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其革命积极性和知识才干需要依附于特定阶级和社会而得到发挥。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延安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丁玲、冼星海、艾思奇、周扬、刘大年等是主要代表;二是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和延安本地原有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较早接触中国共产党或已经充分了解共产党的一批人,成仿吾、柳青等是主要代表;三是海外进步华人华侨和外籍记者学者,他们在人数上相对较少,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斯诺、贝特兰、陈龙等是主要代表。本文所要探讨的延安知识分子主要包括第一类和第三类。
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吸引吸收知识分子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屡战屡败,短时间内丢掉了大半个江山,同时在国统区推行独裁统治、压制抗日活动,加之由于经济政策不力所导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等,使得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态度经历了从支持到反对的转变。与国民党的政策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号召全民团结、一致抗日。在政治上,积极探索并力行民主制度,开展普选运动,建立参议会制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对延安充满向往。1937年,著名诗人柯仲平到达延安时说道:“觉得延安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与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延安比但丁写的天堂好得多,我要描写比天高万倍的党。”[9]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积极开辟抗日根据地,正确研判抗日形势,提出对日持久作战的方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基于此,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加积极,1937年从上海赶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刘人寿曾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我的心也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10]
国共两党在抗战背景下交出两张几乎完全相反的答卷,这使得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愈发全面,态度愈加积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先锋,是抗战到底的坚定力量,是纪律严明、开放开明的先进政党;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延安是革命的沃土,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无论是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将延安比作“崇高的名曲的开端”,还是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将延安形容为“乐园”,都体现出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认同。
二、理论互动
“互动”一词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重含义,有着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之意,其最大的意义是双方因互动而发生思想上的转变或行动上的改变。大量涌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在各领域都发生了诸多良性互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双方在理论上的互动。中国共产党帮助知识分子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确立了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理论研究旨趣都得到了重塑;而知识分子则发挥个人学术专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政治命题的提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铺垫,并在命题提出后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从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重塑
其一,中国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帮助知识分子完成了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重塑。在经典作家那里,归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而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1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放松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改造。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在对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明确强调要“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2)转引自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619页。。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依托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八路军政治学院等干部学院,面向知识分子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相关课程,选派李维汉、成仿吾等理论家定期为知识分子上课;毛泽东、洛甫、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经常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与知识分子进行理论交流,帮助他们尽快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理论观念和历史观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12]852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延安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正如艾思奇在《反对主观主义》一文中指出的:“我们曾从马列的原著、选集、概论之类的书籍里学取了很多的基本知识。”[13]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知识分子不断克服自身弱点,实现了自身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重塑。
其二,中国共产党倡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帮助知识分子确立了理论研究的旨趣和文艺创作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创作自由的前提下,倡导知识分子要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与知识分子互通书信,就理论研究相关问题提出诸多意见和建议,帮助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学术创作。正如张如心所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着重于它观察问题的立场态度,发现事物现象规律性的方法。”[14]在文艺创作的方向上,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将文艺创作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2]857。这就明确指出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理论研究,知识分子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方向、深入工农群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延安大生产运动、深入工农群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改正和弥补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对此,吕振羽在实践中总结道:“既然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么离开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研究历史,根本就不切实际,就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然歪曲历史。”[15]
(二)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一,知识分子引出“中国化”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作了理论准备。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照顾和安排下展开了理论研究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是导致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曲折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实现人民意识的觉醒,就必须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国化”“通俗化”。他们依托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解放》等开展了关于“中国化”的学术讨论。1937年,从贤(3)“从贤”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普遍认为“从贤”是一个笔名。陈占安教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及许全兴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两篇文章都将其当作笔名。近日,李亮教授在《“从贤”为艾思奇化名考辩》一文中指出其为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化名。在《解放》第23期发表《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当前文化运动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从贤认为,文化的力量是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文化界要联合起来动员最广大的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从贤指出,当前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用辩证法思想充分挖掘西方和本国的先进思想,“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对此“不能生吞活剥地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他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16]。次年,柳湜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中明确强调,要“反对无原则的洋化,反对死硬的贩运洋货”,在欢迎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要注意“融化它,要中国化它”[17]。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陈伯达的《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等,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推进“中国化”的重要性和现实性(4)艾思奇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探讨了哲学当前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强调哲学当前“需要来一个运动,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明确提出了“哲学中国化”命题。陈伯达在《解放》上发表的《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一文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目标、当前任务等,总结了党成立17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板的教条……17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的许多历史战争条件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理论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其二,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不断将其推向深入。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反响,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共产党也适时建立相应机构、学会、组织等帮助并引导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张申府、柳湜、杨松、艾思奇、和培元等学者都对这一命题有着深入研究。一方面,知识分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命题提出后的第二年,张申府在《战时文化》上发表了《论中国化》[19]一文,对“近年来有些人只认外国东西不认本国东西的风气”提出批评,认为“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他从五个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出中国思想见解的一大进步”。杨松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20]一文,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历史发展、成绩与缺失、当前任务和方法论问题等,指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不是为学马列主义而学马列主义,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我们是为了“改造中国,为了抗战服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与主要领域。1939年,柳湜在《读书月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化》[21]一文,高度评价了当前“中国化”这一学术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文化要吸收世界文化一切优良的成果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认为当前“中国化”口号的提出是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他明确强调要坚决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同时强调“中国化是贯通着学术的任何一部门的”,要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各方面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推进“中国化”。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20]一文中提出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一般任务和具体任务,强调一般任务是“克服当前我国马列主义者在思想文化理论战线上的落后”,而具体任务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尽快完成“对马、恩、列、斯之主要著作之翻译”,“争取马列主义者在自然科学上的地位”,“进一步做马列主义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工作”,等等。知识分子的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行路线。
三、实践互助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良性关系还体现在实践互助上。大批知识分子赶赴延安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知识分子尽快适应延安生活,让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知识分子也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专长,在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制定优待知识分子政策
由于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及当地工农群众有一定的差异,将要或已经赶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还有较多顾虑。为了尽快帮助知识分子放下思想包袱,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种优待政策,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为知识分子提供有力保障。
其一,政治上尊重知识分子。在全民团结抗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和主要领导人讲话中都体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充分尊重。1937年,毛泽东在《中日关系与西安事变》一文中明确强调要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要“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23]。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相继制定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等政策法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态度还是一以贯之的,到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继续强调知识分子“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并且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艺术和卫生等各行业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被重视”[24]。正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尊重态度,才使大量知识分子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中充分体现出重要价值。
其二,工作中吸纳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吸纳知识分子,主要体现在无论是普通工作岗位还是军队岗位都能大胆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在普通工作岗位上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方面,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在边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应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要以其学识和能力为评价标准,要“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25],让知识分子在“办学、办报、做事”中体现其自身价值。在军队岗位上,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明确强调,要采取“容”“化”“用”(5)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的知识分子政策,要结合知识分子的能力、长处与爱好进行工作安排,对于“已经考验(几年抗战工作已经是一种严重考验)有能力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以负责的工作”[26]458,不应阻断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
其三,生活中照顾知识分子。在延安艰苦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照顾知识分子的生活。如通过颁布《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陕甘宁财政厅关于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通知》《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中央关于工资的政策指示》等政策,明确规定在薪资待遇上对专家、文化技术干部等予以优待。据曾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生活津贴每月12元,供给大米、白面,到小食堂吃饭,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送到我们房间,摆满了窗台。中央宣传部有关宣传、文化工作的会议,也邀请我们参加等等。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6)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二)发挥知识分子能力专长
其一,知识分子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扎根工农群众推动先进文化的教育工作,帮助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知识分子积极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艾思奇充分认识到经典文献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多次建议建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并组织开展翻译工作,他强调“我们的理论工作水平还很低,不谈别的,仅仅翻译工作一项,就有着很大的空隙”[27]。基于此,党中央设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马列学院编辑部、延安解放社和社科研究会等出版机构和研究组织,委派艾思奇、范文澜、杨松、许之桢等大批知识分子展开了系统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仅1938-1942年间便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经典著作及讲话和书信100多种,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扎根工农群众,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只有在与工农交朋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才能体现个人价值。1942年7月20日,刘少奇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一文中指出,教育部门要“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去办教育和当教员”[26]383。在学校教育方面,面对延安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知识分子积极创办现代学校或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任教,成为学校教育队伍的主力军。如在中国女子大学初办时,四个主要负责部门的干部“有一名便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在白区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28]。在社会教育方面,知识分子担负起了文化扫盲、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帮助工农群众破除迷信等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知识分子相继创办了冬学、图书馆、识字组等学校和机构,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如《东方红》《地雷阵》《共产党好比红太阳》等),在丰富工农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发挥了思想宣传和教育功能。
其二,知识分子依托党报党刊等宣传媒介与国民党展开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夺取了革命话语权。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论战实质上是两党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事关两党各自政党形象的建立及其合法性的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引来了国民党一派知识分子的反对声,他们通过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以及指责中国共产党治下的边区消极抗战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达到摧毁中国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最终目的。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发起了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相继发表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中国只需要三民主义不需要别的主义》《论学术中国化》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公开批驳。其代表人物叶青认为,外国人创造的共产主义是舶来品,“它们的输入,或由于模仿,又由于趋新,因而皆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共产主义,也就不需要共产党”,只有三民主义适用中国革命,因为它是“博大精深的和丰富完美的思想”[29]。针对国民党文人的论调,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或依托党报党刊等媒介与其展开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艾思奇在其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文化特殊性》[30]一文,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他明确指出叶青等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的反动思想的特点”,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它是科学的理论,是科学的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普遍真理的指导下解决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充分做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叶青现在叫着的所谓‘把握特殊性’表面上看着举着三民主义旗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反对三民主义继续的实现,是反对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张如心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它是最善于了解中国国情,掌握中国革命规律性”的政党[31]。通过与国民党旗下知识分子的激烈论战,延安知识分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科学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了革命话语权,扩大了其在全国的影响力、组织力与号召力。
四、结语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等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延安真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在这座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的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32]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通过理论与实践上的互动与互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种互动与互助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升华,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蓝本。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营养剂。新时代,在处理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要充分继承延安时期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与知识分子结成更加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调动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