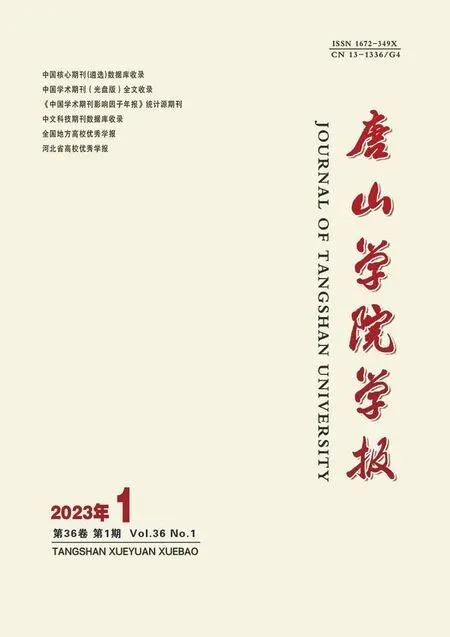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的基本特征
——基于其与外国记者谈话的分析
王晓荣,丁书瀚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19)
1935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南犯,欲以华北数省为跳板进而偿其独占中国之大欲。与此同时,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审度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主次后,打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不仅赢得了国内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而且更是吸引了国际关注——从1936年开始,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批外国记者冲破重重阻碍先后深入陕北进行实地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区的首批外国观察家。毛泽东将他们视为中国革命的宣传人,并与他们展开深入交谈。从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而理解这一思想通过外国记者们的报道为何能够对国际社会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产生重要影响。
一、对内动员与对外宣传相结合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近乎殉道者的精神第一次踏入陕北苏区。当他成功地在保安的窑洞中见到毛泽东,便将众多外界尤其是西方民众难以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问题一股脑地抛向了这位日理万机的苏维埃领袖,其中有关共产党对日政策的问题,不仅是斯诺迫不及待渴望了解的,亦是毛泽东乐于在百忙之中同发问者彻夜长谈想要说明的。毛泽东指出,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从根本上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武装抗日是唯一的救国之道,共产党早在1932年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如今更是主张实行全民族的对日作战。这一坚定立场在使斯诺感到钦佩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质疑:“全民族的抗战”是否真的能够实现?
斯诺的疑虑源于他1929年的一次绥远旱区之行。彼时灾区饿殍遍野的残酷景象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在痛恨官厅囤粮不赈的同时对众多行将饿死的难民无论如何也不愿起来反抗的行为感到费解,并由此认定中国人民缺乏斗争精神[1]188-190。这种认识也是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民众的固有印象——近代中国民众对于国家前途的麻木与个人命运的迷茫根源于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实行的文化垄断,并为因帝国主义侵略殖民而灾祸深重的民族命运所深化。这种民族精神上的不幸被西方世界观察到后反倒成为其轻视中国的依据,在抗战前夕即认为中国人民不具备对日作战的勇气与决心,断定中国必亡,因此也就没有实施对华援助的必要。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低估中国人民斗争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倾向,并竭力予以破除。他告诉斯诺,日本帝国主义无法战胜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共产党已经在其影响可及之处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动员。对于当时的陕北苏区,抗日动员已经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集政治宣传与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是共产党向边区群众普及抗日政策和纲领的主要途径。演员们在那些设备简陋、布景粗糙的短剧、歌舞和杂耍中饱含激情地演绎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种兼具直观形式与深刻现实意义的演出因易于为淳朴善良的中国民众所共情而深受喜爱,并在唤起他们民族意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深有体会的斯诺将其誉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巧妙有力的宣传武器”[1]99。
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动员唯有与经济动员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加令人信服的力量。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谈话中强调,要想动员全体人民投身抗战就必须改善民生。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条件是阶级斗争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当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曾指出,如果工农大众因受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而不能生存,那么要求他们抗日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阐述了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灾民等主张,并列举实例论证这些主张已经在苏区得到落实,民众的抗战热情因而空前高涨。
文化教育方面的动员也被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与贝特兰交流时强调,抗战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这是对日本在其占领区大举推行奴化教育的必要回击。此外,社会生活领域的动员也同样无处不在,斯诺在苏区考察时就对当地印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等口号的纸币印象极深。他在整理调查材料时总结道:土地改革和废除捐税等经济措施不仅赢得了贫农、中农的拥护,而且与抗日爱国宣传相结合,形成了争取小地主支持的社会基础[1]199。这是一个外国观察家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工作的充分肯定。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511,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2]480。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过程中,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战决心经过深入动员已被逐渐唤醒,这是毛泽东眼中决定抗战胜利与否的根本因素,也是他认为应当利用文学艺术、报纸杂志、外交活动等形式向国际社会开展宣传的重要内容。早在1935年,吴玉章等就将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时报》作为我党在海外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用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各项方针政策[3]。而于1936年以斯诺为代表开启的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热潮则意味着共产党开始借助西方媒体的笔触宣传中国抗战,其效势必更甚。
毛泽东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在与外国记者交谈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已经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抗战动员,并且从多个方面向他们解释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在与斯诺的交谈中,毛泽东以中美两国为例,将上海和纽约作对比,论证了中国不平衡的经济、不统一的国情反而能够削减日军攻占我国发达城市的战略意图;他告诉史沫特莱,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基于对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错误估计而采取的军事冒险行为,其后果将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当贝特兰问及抗战之初中国取得的成绩时,毛泽东则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未动干戈而夺取东北四省和“七七事变”后非经血战不能占领中国寸土的迥异情形为依据[2]375,论证了中国人民坚决而持久的抗战必然为侵略者敲响丧钟。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同贝特兰的交流中非常欣喜地谈道:中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已然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一改过去对中国在东三省沦陷和华北事变中不抵抗行为的鄙视,代之以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由衷敬意[2]375。这种变化深刻揭示了,对内动员带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国际上获得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而借助对外宣传进一步确立和扩大的民族认同又是争取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
二、争取外援与独立自主相并重
“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4]4001936年7月16日深夜,斯诺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这一段话,是他在询问中国能否不借助国际援助单独打败日本时毛泽东给出的回答。虽然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毫不讳言中国争取外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不单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特点,更是为了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一方面,身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经过在远东地区长期的殖民掠夺已然建立起完备的近代化工业体系,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军队素质较同时期的中国有着显著优势,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能够倚仗其强悍的武力攻城略地,并加紧扶植亲日派和汉奸,让他们四处放出投降主义空气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这在短期内使一部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必亡”的消极心态。毛泽东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这一时期中日战争相互对立的基本特点,即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并在其间驳斥因片面强调日军局部的、暂时的胜利而盛行的亡国论调时,将潜在的国际援助作为重要的论据。因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张联合世界上所有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借以加剧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达到缓解中国国内抗战压力的效果[4]487。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正义的、进步的卫国战争必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退步的侵略战争,但在缺少国际援助的情况下,这个胜利势必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战争时间延长,牺牲人数就会扩大,更会极大地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虽抗战系全体人民必须共赴之国难,共产党人仍致力于使人民最大程度免于战乱之苦,早日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4]401,而国际援助作为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自然为共产党人所必争。当然,这种争取需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之上。
如果不熟悉近代中国创巨痛深的外交史,要想理解毛泽东奉行一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是不易的。在全面抗战前夕严峻的情势下,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均对这种“有条件地接受国际援助”的理念表示质疑,但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争取外援如不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就会陷于投机主义的倾向,招致受制于人的危险。日本的武力侵华始于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战中,中方统帅李鸿章自恃有俄国的调停保证而疏于备战,并在外交上采取盲动主义[5]。当俄国未兑现承诺时,被搞得措手不及的北洋海军只能在汹汹袭来的日军面前败下阵来,结果中国不仅割地赔款,更引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40多年后,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重蹈覆辙,妄图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会议向日本施压而毕抗战之功于一役,因此不惜以主力部队与优势敌军硬拼消耗,最终拼到溃不成军也没能等到预料中的国际调解[6],上海亦于不久之后陷落,淞沪会战失败。这种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国援助之上的投机主义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抗战的主动权唯有操之于己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倘寄全部希望于外援,则在短时间内可能造成速胜论的幻境,然最终希望落空后便会坠入亡国论的深渊。
在毛泽东看来,避开投机主义的危险要求中国人民自觉自主地进行抗战,而对于潜藏于国际援助中的侵略主义行为需要更加警惕。甲午战败后,德国自诩对中国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之恩,便借故兴兵占领青岛;此后,沙俄又以援华抗德为由将军舰驶入旅顺港,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强租旅顺、大连的城下之盟。近代中国因接受此类“援助”而最终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例子比比皆是。殷鉴不远,这种打着援助旗号行侵略之实的伪善之举与如今日本帝国主义不加掩饰的战争行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深知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势必招来新的“援助陷阱”,因而强调对国际援助的争取必须以“不丧失国家主权”为前提。牺牲主权换来的援助即使能够驱逐日帝,将来也会化作扼杀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绞索。
将对国际援助的争取与对独立自主的坚持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毛泽东在面对外国记者的质疑时能够作出“没有友军,中国也能凭借自身的资源与自然条件坚持长期作战的”[4]487这一论断的依据。换言之,如果平等待我的国际援助求而不可得,那么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将独立抗战进行到底。
三、争取欧美与联合苏联相同步
1935年11月,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时,曾提出“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4]361,并认为相较于意在瓜分中国的英美等国,执意独占中国的日本才是当前最大的敌人。毛泽东结合一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斯诺等外国记者试探中共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时,毛泽东果断将美、英、法等未相助日本侵华的资本主义国家归入“友好国家”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列。
然而,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不会因毛泽东的讳言而改变,此类列强对华政策的变动大抵受利益驱使,自鸦片战争起便是如此;斯诺等个人对华的友善态度也不能代表其国政府,因此毛泽东深谙离开“真金白银”的利益仅靠口头上的痛陈利害是苍白的。于是在与斯诺的交谈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主张保护外国居民在华的私有财产,所有旨在和用于中国建设的外债都将被视为合法的外来投资并得到承认,中外双方先前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亦可暂缓修订[4]393-394。这些为实现抗战的总目标而作出的让步虽未脱离独立自主的原则范围,但已然出乎斯诺意料,不过在日后通过他的报道却成为给欧美各国开出的一颗定心丸。
抗战胜利前夕,在国统区曾有杂志刊出过“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最有利”的言论[7],而同样的观点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就已被毛泽东传达给了斯诺——他认为只有独立后的中国才是外国人来华从事合法贸易的最佳平台,也只有解放后的中国人民才能迸发出足以促进全世界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使中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中坚力量[4]393。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虽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却始终未能将这片它们垂涎已久的土地变为消费力足够强的商品市场和生产品大宗化的原料产地,原因在于因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贫穷落后的国情制约了中国人民生产和消费的能力。帝国主义者自己无力也不愿揭示这对矛盾,毛泽东则在争取他们援助抗战的过程中为其代劳了。此虽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讽刺,但在经由斯诺报道后不仅强化了欧美各国的援华意识,并且对它们此后的对华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相较于颇费一番功夫才争取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一直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但后者被毛泽东引以为友的同时亦为前者所深深戒备。斯诺在踏入苏区之前曾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并在进入苏区之后与毛泽东对话中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否会因受到苏联的支配而使内外政策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4]396的疑问;一年后史沫特莱到访延安时也就“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4]484的观点与毛泽东展开讨论。毛泽东从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向他们论证了苏维埃中国绝非苏联的附庸,唯有法西斯主义者热衷于借助这类谣言削弱世界和平阵营的力量;并指出,中国抗战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部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不相冲突。
在努力化解外国记者对苏联偏见的同时,毛泽东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他联苏抗日的决心。早在1935年红军落脚陕北时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过程中,苏联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支援中国抗击日本符合苏联国家安全的需要,因此苏联对中国抗战给予援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争取的。毛泽东据此明确了“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4]368。不久后他又指定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从陆路打通苏联”为行动部署之基础,就近获得苏联对红军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
除了在党内确立联苏抗日的方针,毛泽东还力图在党外同各方达成联苏抗日的共识。1936年,毛泽东曾多次致信国民党高级将领、地方实力派以及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联苏抗日的必要性。在给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毛泽东劝道:“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8]引荐苏联,有如引荐良师益友,赤诚之心令人动容。而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在毛泽东致宋哲元、宋子文、王以哲乃至国民政府的信件中更是被多次援引作为论据,证明曾在大革命中有助于中国的苏联同样会在抗战中施以援手,诸方为抗战胜利计亦须团结这位盟友。而今,红色中国迎来了首批国际观察家,毛泽东向他人的引荐就不再限于国内了。并且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他热情地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应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共同抵御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
毛泽东晓之以理、许之以利以争取欧美,同时消释误解、多方引荐以联合苏联,尝试在太平洋外线逐渐构建起一个用以围剿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包围圈。在20世纪30年代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毛泽东构想中的这个包围圈还将持续扩大。
四、倡议国际联合与抵制个别孤立相统一
有关毛泽东构建的对日包围圈的全貌,在他与斯诺曾经的交谈中有所描绘——“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4]391这是毛泽东对《八一宣言》中“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9]方针的发展,也是他抗战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发端。
抗战初期,日本一方面对中国展开军事进攻,一方面在国际上宣扬中国人民的抵抗是“妨碍远东和平的”,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论及此事时怒斥此为“意在不战而亡人之国”的谬论,认为日本侵略者口中的“和平”只是掩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4]485。毛泽东认为,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不会将侵略的范围局限于中国——以朝鲜为跳板谋取中国、以中国为跳板谋取亚太、以亚太为跳板向全球扩张是其侵略道路的必然轨迹。因此他反复向斯诺强调,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虽然将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全体中国人民头顶,但是更将自己置于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作为世界和平国家中的强大力量,既有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又有坚实的国力作保障,如能先行放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共同承担起抗击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友的责任,则不单中国的独立解放能够早日实现,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崩溃亦会加速到来。
同时,毛泽东对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侵略的斗争也保持着高度关注。他同斯诺详叙阿比西尼亚在意大利法西斯入侵下举国蹈于沦亡的惨景,与贝特兰交谈西班牙人民在其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下成功保卫首都马德里的经过。毛泽东不仅从中得出可供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准备着在未来同这些国家组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届时同样饱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必将成为中国人民最坚定的战友。
此外,日本的人民和士兵也被毛泽东视为可以团结的对象。毛泽东向斯诺断言,日本的侵略战争一旦失利,其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就会立刻兴起,中国抗战的胜利将与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1937年8月,毛泽东把“联合朝鲜及日本的工农群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写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由此将团结日本人民的主张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同时,毛泽东认为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大多受到本国法西斯主义军阀的愚弄和利用,我们对战争中俘虏的日军应给予优待,并加以教育和团结,争取将他们也纳入抗日的统一战线中。他告诉贝特兰,如果有日军士兵受到感化选择留在中国军队,即可在将来组成抗日战场上的“国际纵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而战。
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没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当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兴起并结为强盗同盟时,欧洲各国正因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衰落,又为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掣肘,深恐惹火烧身,故而对前者实行“绥靖政策”。其中,英国为保全其在华经济利益不惜与虎谋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默许日本的侵华行为,积极对日妥协。而美国位于大洋彼岸,远离法西斯主义肆虐的中心地带,因此在法西斯侵略者与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斗争中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是在英国妥协主义和美国孤立主义的制约下蹭蹬不前的。
率先深入苏区进行考察的外国记者们大都同情中国革命,因此并不回避与毛泽东讨论英美对日纵容的问题,毛泽东在这类讨论中主张将英美两国的广大人民和少数政客区别开来。他在与斯诺的交谈中指出,虽然一些短视的美国政客正大肆鼓吹孤立主义,认为远东的战火不会蔓及美国,但是众多美国人民已经开始自发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等民间团体来声援中国人民抗日。一年后,毛泽东同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再论孤立主义时指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若一味隔岸观火只会反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认为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美日矛盾的日益暴露终将促使美国政府摒弃孤立主义,主动担负起在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责任。
比美国的孤立主义危害更甚的是英国的妥协主义。毛泽东认为,英国政府在华北事变中消极应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调停请求以及拒绝实行对日经济制裁等行为实际上是为日本独占华北大开方便之门。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英国保守党政府依然企图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政府已因长期徘徊在法西斯势力与世界和平力量之间而饱受本国人民诟病,“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示同情”[4]503。他认为英国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转变与本国人民的态度密切相关,英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要求和监督政府坚决与法西斯势力划清界限。正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在报告中指出的——“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10]。
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的对日妥协主义与孤立主义等思想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且“大量的直接的援助尚有待于来日”,但是毛泽东与首批深入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的谈话内容连同其他访问材料一起,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借助报道、通讯、报告文学等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新闻封锁,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而且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向中国提供战争贷款并派出志愿航空人员直接参与对日作战,一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苏联成为最先出面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1938年,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和印度医生柯棣华等国际主义者带领医疗队来华支援抗战;更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密切关注中国抗战并积极募捐;国际舆论亦对日本侵华进行谴责……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五年里给予了中国军民极大的鼓舞。
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的对外交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深重的民族危机下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基本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抗战具体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这一对外交往思想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谋求民族复兴的斗争持续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