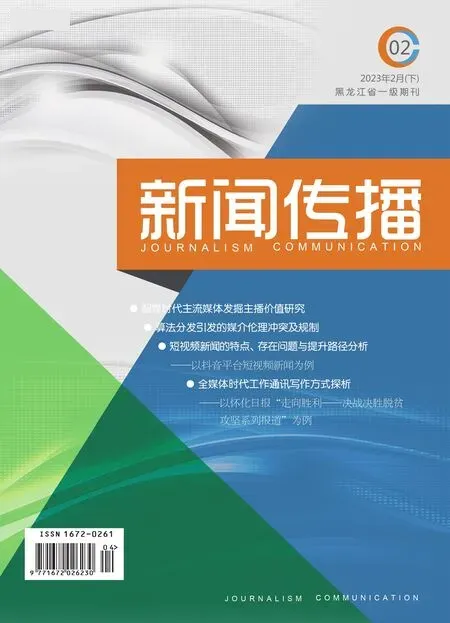戏剧理论对社交媒体议程设置失焦现象研究的适用性探讨
徐轶瑛 陈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70)
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都是由专业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完成的。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各类社交软件霸屏信息生活的边边角角,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参与意见交换,“反哺”舆论议程;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公共议题数据一再被深入挖掘,用户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被多方“投喂”议程。可见,当下信息社会的议程设置与社交媒体语境密不可分。
一、何为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失焦
集UGC、PGC和PUGC信息生产模式于一体的社交媒体原是可以成为广大用户进行公众议程设置的良好渠道的,但令人叹息的是新媒体议程设置的马太效应日渐显现,尤为突出的是,近些年议程设置失焦现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层出不穷。以2020年的“张玉环案”为例,背负故意杀人罪名26年的张玉环终于在53岁那年等来了无罪判决,原本应是对张玉环事件背后的严肃追问,更多媒体的镜头却转向张玉环前妻宋小女,一时间对宋小女的感动和赞美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在诸如“张玉环案”“鲍毓明案”“江歌遇害案”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议程设置失焦现象频发,这势必会削弱官方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性和权威性,甚至会导致舆论失控的混乱局面。因而,在社交媒体语境下解释与反思议程设置失焦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学界关于议程设置的学术探究也早已转向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功能机制及其效果评判等方面的总结性研究,但缺乏在不同理论的关照下对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和创新性分析。本文尝试探讨戈夫曼“戏剧理论”对社交媒体语境中议程设置失焦现象分析的适用性。
当然,首先还需简要厘清“议程设置失焦”这一概念。所谓议程设置失焦,借鉴过往已有的“舆论失焦”“议程失焦”的定义,例如严利华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失焦现象及其启示》[1]一文中关于“舆论失焦”的界定,又如韩梦佳在《透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自媒体的议程失焦》[2]一文中对“议程失焦”的解释,可以将“在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为刻意迎合公众的某种需求而枉顾事件的本质属性、过度消费其他属性,最终造成事件中心议题边缘化、严肃问题消遣化、复杂事件片面化的”这一现象是谓“议程设置失焦”。
二、为何出现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失焦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受“符号互动论”影响,于1959年提出“戏剧理论”,又称“拟剧理论”。他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建议,“作为技术的、政治的、结构的、文化的视角的一种补充,戏剧的视角可以构成第五种视角。”[3]该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舞台表演概念在人际传播中的运用而引申得出的,除了将戏剧元素引入到人际交往活动中外,还试图从戏剧的视角实际解决人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交往失调行为。虽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强调的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但是新媒体技术利用传播速度以此高度消解人际传播的时空差距,创造不同时空中的虚拟的同一情境和共同在场,这使得戈夫曼戏剧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可以突破传统人际领域的限制,该理论的适用魔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随之被释放出来。
谈及议程设置,显然“传统新闻媒体一直以来都只是个人议程设置的一个来源,个人经验、人际交流等因素也在影响着人们对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4]。步入社交网络传播时代,或新闻媒体或公众、个人的议程设置都逃脱不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客观来讲,社交媒体为戏剧理论与议程设置失焦的互通和关联创造了宏观上的共同语境。
(一)作为戏剧舞台的社交平台
戈夫曼认为社会就是个大舞台,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进行着各种表演。社会生活正如戏剧舞台一样,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即表演的各种场合,是表演者在短期中集中呈现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符号装备的场所;后台则相反,是表演者准备其前台展现内容的场所。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所有公开发布的成品都属于前台的表演,而收集撰写等环节则属于后台的部分。
社交平台这个舞台是开放、多元且个性化的。其前台展示着充满戏剧性和竞争力的表演内容,包含多角度多地区的新闻,涉及各个阶层;而社交平台的使用者在后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准备内容,提供了权威的背景。使用者通过在后台准备的图像、视频和文字塑造各自的虚拟自我形象,将新闻内容在前台传递。
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有关“电视场”“新闻场”相关的“媒介场域”。[5]过去的“电视”或“报纸”等主要媒介已经很少使用,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场域因为技术的更新迭代有所变化,同时也受到资本场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相关因素的影响。[6]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的实时推进,社交媒体的移动性和参与性允许公众从传统新闻中的被动观看者、局外旁观者变成新闻的“现场”参与者。由技术带来的公众主体性的多角色转变引起媒介场域的习惯变化,主流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场域内的利益争夺出现问题,他们的地位和权威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维护他们在过去的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颠覆传统的习惯才能有所发展。[7]
进入新媒体社交时代后,资本场、技术及习惯的相互联动让前台变得更为辽阔。观众不再维持原有的沉默,他们在前台的狂欢让前台呈现向前延伸的趋势,与观众席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后台得以窥视的“神秘感”不再,前台亦向后渗透,后台的空间越发褊狭。
在前台逐渐泛化的如今,属于前台的戏剧性竞争力逐渐侵占后台的专业性,技术给了观众进入后台的方式和可能,后台的审核机制被后置,原有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把关人的地位持续下降。
(二)承担角色扮演的新闻媒体与公众
戏剧理论提出角色、观众作为分析的要素,角色即在表演期间可以呈现的预先确定的行动模式,观众即与角色相对的做出其他表演的人。
在社交平台上如是而分。其中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的主流媒体利用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无疑占据着舞台上主角的地位;其他粉丝量较大、内容话题性强的自媒体账号起到了辅助主流媒体的配角作用;另外,公众作为观众暂时只能作为观众观赏演出。正如巴赫金所说,第一世界是统治阶级拥有绝对权力的官方世界,而第二世界是全民平等自由地参与的“狂欢式”的生活。[8]传统媒体、自媒体与公众正处在从秩序的第一世界向狂欢的第二世界的转变。
社交媒体中,使用主体可以概括为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账号、自媒体账号和普通公众账号三类。传统媒体依靠“把关人”地位和资源的继承,暂时依旧是舞台(移动社交平台)上的主角。自媒体借“人人都是记者”的东风,成为传统媒体的配角。公众则依靠“转发、评论、点赞”功能的兴起,上台参演。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观众在议程设置中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导致主角陷入了权力流失的恐慌,配角则选择了加入狂欢成为小丑。
以云南野象群事件为例,象群的路线、周边政府的应对措施等都由主流媒体进行报道,起着主角的作用;自媒体账号追随主流媒体的脚步,发布跟进的近距离细节,是舞台上的配角;公众通过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账号来观看事情的发展,是表演的观众。
新媒介赋权解构主角的权力,使主、配角与观众的位置发生了替换,主角逐渐配角化,引发主角的恐慌,进而造就原有的“深挖”后报道的新闻报道模式彻底改变,其表演的特征逐渐向取悦公众发生转变,触发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议程设置失焦现象频发。而在“流量”的驱使下,配角也急于剧目的推进,不再丰富角色和剧目内容,而是从主角的内容中获取、复制或拼贴吸睛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并不是剧目的主题,从而使议程设置的焦点迷失。移动社交时代则诞生一批良莠不齐的自媒体,由于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自媒体用小丑化的表演带来充足的“流量”,广告费则以自媒体引入的“流量”为单位进行计算,“流量”意味着金钱,自媒体通过“流量”的转卖攫取新媒体带来的红利。自媒体对“流量”的追求导致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令彼此纷纷面目全非、主动出击,而这样小丑化的表演无疑是议程设置失焦的推动因素之一。
(三)设定表演框架的新闻剧本
在戈夫曼看来,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更关心世界在人们心中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们心中对世界的认识和架构。“我所面对的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的任一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9]戈夫曼所说的这种经验结构就是表演的框架,它是“一种情境定义,是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做出的”[10]。
在社交媒体上,媒体会根据不同的新闻焦点呈现出不同的新闻剧本。这些不同的新闻剧本对应着不同的经验结构,也造成了不同的议程设置焦点。对于传统的新闻剧本而言,真实性、时效性、准确性是其基本特点,其目的是揭示事件真实意义,从而形成不受情感偏移的焦点。受制于“流量为王”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现状,原本“情绪让位于事实”的议程设置理论被迫解构。各类媒体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采用文本的格式化、程序化、片面化来直击社会情绪的痛点,将公众的情绪唤起视为议程设置的第一要务。
黑格尔认为,客观性来自于普遍者,具备实体性内容的普遍性并不是主观性的集合,但是当主观性无限制扩张时,我们的情感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从而使得事实和真相受到拒斥,并以此来取代或冒充客观性。[11]自媒体试图洞悉新时代个体或组织在媒介场域中的习惯,以此投其所好。从而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关注公众不感兴趣的本质属性,将议程设置的焦点表层化、娱乐化来讨好公众成为了更占优的选择。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剧目即议程设置的焦点。针对每个新闻,都存在核心议题和边缘议题。在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剧目是否属于核心已经不再重要,剧目是否具有争议性,能否带来更大的点击量和讨论量才是舞台上角色最关心的因素。
穿插剧本始终的台词是一场舞台剧的灵魂,也是引导观众心理变化的暗线。为了引起观众更多的讨论,舞台上角色们的台词越来越结构化。媒体使用口语化的词汇表达新闻,更加贴近观众生活,减少距离感,从而鼓励观众参与讨论,增加自身流量。同样的,他们还会使用标签化的语言,将新闻主体标签化,引导争议。
(四)作为印象管理的议题表演
前台行为可视为维系礼貌和体面的印象管理。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为印象管理定义,认为“他能通过表达自己来影响这种定义,给他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将引导他们自愿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12]”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各类角色而言,对议题的表演正是为了维持这种印象的管理。
在社交媒体上,主流媒体在追求流量的同时,通过各种专业数据、深度访谈相关领域专家及当事人等方式努力保持自己原有的权威正统形象。而作为配角的自媒体则有着复杂的印象管理。一部分自媒体努力树立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业形象,如丁香医生、博物、春梅狐狸等,而另一部分自媒体则不介意自己的形象娱乐化、戏剧化,采用低俗或戏谑的内容和形式吸取公众注意。对于公众而言,则在议题的表演中表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个人形象,这样的形象管理也为社交媒体上的议题表演增添了个性化色彩。
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类似印象管理的公众不断加强着相互之间的凝聚力。原先单个公众难以产生可以撼动议题的力量,而圈群和对话的存在将公众依照群体聚合,其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也逐渐增加。角逐的过程更是让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将价值判断的权力完全交给公众。公众在社交媒体时代拥有了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大的权力,却没有相匹配的能力,难免会造成议程设置失焦现象的屡次发生。
结语
综合上述探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对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议程设置失焦现象研究具有高度的理论适用性。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技术消解了人际传播的时空差距,使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全新舞台,作为传播者的传统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与受众一起在舞台上进行着各种演绎行为,而这种因过度演绎而频频出现的议程设置失焦在戏剧理论的解释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