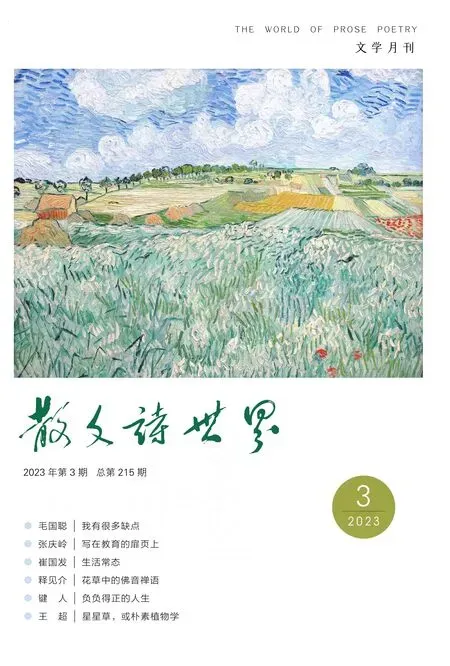远与近的撒拉地坡三章
普光泉(四川)[彝族]
藤桥河
梦里,我再次来到藤桥河,那河水干涸了,是魏晋的水,是唐宋的水,它的冷,它的清,都是出于虚构。只有月光流淌在河上。干涸,是空蒙里的那些叹息,以及众多石头施行的障眼法。
低下身子,靠着一棵树,像是靠着一个人的坚强;幻象彰显,我只要想起那个春天的光景,所有的树枝——便纷纷冒出花骨朵儿,便有三两只野画眉,嗓音清脆。
醒来。期待着某某人走近,我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河还是藤桥河,保持二十九公里,只是藤桥已古旧;还是有水,只不过水已不多,滋养不了原本存在的那么多细鲢鱼和那份快乐。
远与近的撒拉地坡
远远望去,撒拉地坡仅仅是一道山坡,有着别的山坡一样的沉默。脊上,那些树一动不动,墨色,如一个头上挂满露珠的夜行人。
撒拉地坡不说话。撒拉地坡的话由天说出,天之蓝,成就了空,而空近似于无限的缥缈,所有语言都暗含诗意。
走近了看,撒拉地坡不仅仅是一道山坡,栅栏内外,开满野花,那香是一份特别寂寞的存在。你来与不来,野花都开;你来与不来,那香都弥漫着所属的时间。
最中心的那片,是苦荞花,白色夹杂着粉红。风一吹,花蕊便撑开,蜜蜂再次迷恋,如我之所爱。
一个季节的寻觅,如获至宝,我想说的太多,“我想你了”,我把这几个字用微信发给你,却不告诉你——我独自躺在花开花落的撒拉地坡。
栅 栏
在七家寨,我常常深深吸入一口新鲜空气,好生看一眼栅栏,便使劲挖地。
在撒拉地坡,我种植苦荞,等待雨水。
高高的天空之镜,映照着我的无限江山,映照着我的栅栏,也映照着寨子的火葬地。
火葬地,是一个开满野花的地方,红色的白色的,总是开得那么野,没有人采,也没有栅栏分割。蜜蜂从远方飞来,舞动翅膀,身体的毛茸茸裹挟起暖意洋洋的甜蜜,我心甘情愿安静地做一个观者。
我和栅栏说话。栅栏是山寨的标配,它低矮、弯曲、倾斜;它的身上长出来的蘑菇,浸润着时间里虚空的黑而孤单。
我和栅栏说话。随时抓紧泥土的栅栏,是山寨的栅栏,是牛羊的栅栏,是我的栅栏。
城市遥不可及,是在我从山脊上眺望而不见踪影的远方。
我问自己,城市里有没有栅栏。我想到城市里不会有栅栏,就像城市里不种植苦荞,不饲养牛羊。我倒吸一口气,城市哪里要栅栏。
风又一次吹来,我的思考忽然穷途末路;风起风落,栅栏发出清脆的尖叫,而后随了我,回归淡然无奇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