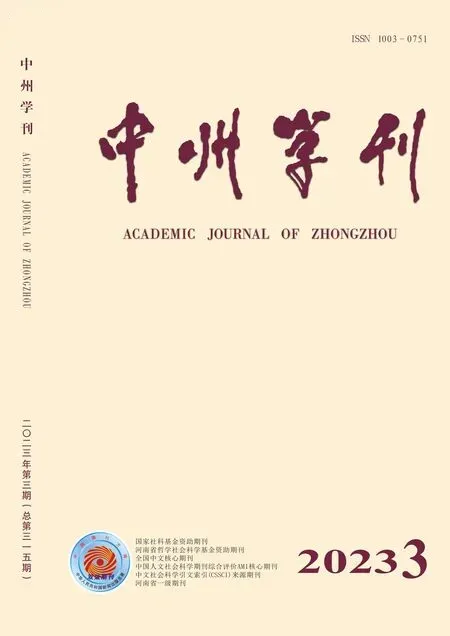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龚晓康
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西方哲学有着深远的传统。柏拉图把灵魂看作是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使人更加完备。笛卡尔以身、心为完全不同的存在物,前者具有广延的性质,后者具有思维的功能。自此以往,身心究竟为何种实体,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如何能有相互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哲学家的热烈讨论,并出现了众多的理论思潮,其中尤以物理主义最为流行。该学说主张一切都可归于物理的,应在物理世界中为心灵找到恰当的位置,并试图通过还原、实现、同一、随附、取消等来解释心灵现象。但是,物理主义难以说明心灵现象的起源。与物理主义相对的是唯心论,主张心灵对身体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理论无法满足物质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其他诸如泛心论、身心平行论、相互作用论、双重形态论、预定和谐论、偶因论等,皆各有其理论上的困难。
中国哲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大略而言,“心”有心脏、思虑、本心等含义,“身”则有身体、生命、体验等含义。至于身心之关系,主要有三个面向:首先,当“心”指心脏这种生理器官时,则其为“身”之感官之主宰,如《荀子·天论》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其次,当“心”指意识之思维知觉时,则其为“身”之灵明作用,如《荀子·正名》所言:“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最后,当“心”指先天道德本心时,则其可流行发用于“身”。这见于《孟子·尽心上》如下之表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可见,中国哲学在讨论身心关系时,更多地注意到了两者的和合关系。
21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中国哲学中的身心问题展开了讨论。一般以为,中国哲学虽然强调“心”对于“身”的主宰作用,但更多的是强调两者的互渗、交融乃至转化。杨儒宾认为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论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身体体现了心性,心性也形著了身体”[1]1。安乐哲等认为在儒家思想中“身心是一对‘两极相关’(polar)而非‘二元对立’(dualistic)的观念”[2]。但是,身心究竟是如何合一的,学者们的意见不尽一致。杨儒宾认为孟子形成了“心—气—形”一体化的身心观,“气”构成了身心的中间环节[1]11。成中英则强调“仁”在身心中的关联,“仁作为能力的美德和行为的愿望由个人尽心尽力地实现,因此它便与心和身都有了联系,并且在形成一个理想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行为的过程中,将身心联在了一起”[3]。
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论述,也为学界所留意。董平分析了王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的说法,认为这是要求人们贯彻“道—心—身”的同一性[4]。张孟杰等人认为,王阳明之身心学说非是基于身心二元对立的人学图景,而是秉持着“身心渗透论”的观点[5]。张再林认为王阳明学中“心”虽然超越一切,但却不能外在于血肉形躯的“身”,“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表明王阳明持“身心不二”的观点[6]。张新国基于王阳明心学的主体性结构,认为其既注重美德所从出的人的内在良知即“心灵”,同时也颇为注重人的道德行动展开的直接现实性基础即“身体”,从而建构了一种“即主体即本体、既重价值型塑又重现实关怀”的道德哲学新形态[7]。
从现有的文本来看,王阳明区分了“真己”与“躯壳的己”两重自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身心观。“真己”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为“大我”,其“身”为与物同体之源初场域,其“心”为源初场域之神感神应。但是,人只为形体而自为间隔,故落入“躯壳的己”即“小我”之中。由于“小我”意识的自我对象化及其执定作用,导致了身、心、意、知、物的分裂:“身”成为与心、意、知、物相待的生理基础,“意”则为与身、心、知、物相待的心理活动,由此而有“身”与“意”之间“非一非异”之关系。王阳明关于自我的两重区分,对于身心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大我”之身、心
一般人对于身心问题的讨论,乃是基于现实的个体生命而言,“身”为个体生命的生理基础,“心”为个体生命的心理活动。但在王阳明这里,“自我”存在着两重的区分,这就是“真己”与“躯壳的己”: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8]41
王阳明论证“真己”的存在,主要是基于“心”的主宰作用:人之所以有视听言动之功,乃是因为其以“心”为主宰。“心”发窍于人之身体,而有身体之感官活动,故“心”能主宰“身”。也正是因为心之主宰作用,王阳明谓“心之本体”便是“性之生理”,亦即是“真己”——本真之自我。与“真己”相待者,则为“躯壳的己”,其由感官所构成。需要注意的是,“真己”与“躯壳的己”存在着隐显二重化运作:前者作为心之本体,为隐;后者作为现世形体,为显。
一般人乃是基于“躯壳的己”来讨论身心问题的,这与王阳明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王阳明是如何规定“真己”身心的。
王阳明以“心之本体”为“真己”,而“本体”犹如太虚,涵摄天地万物。其谓:“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8]1442这也就是说,作为“心之本体”的“真己”,涵摄天地万物而为宇宙性的生命,故王阳明有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8]302
这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真己”,我们可称之为“大我”,亦即人之宇宙性生命。“大我”其实是一种源初的存在场域。何以如此?王阳明有“身心意知物是一件”的说法,谓五者之间相互融摄而不可割裂。
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8]103
就一般的观点而言,身、心、意、知、物当然是各别的存在,如何能“是一件”呢?王阳明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一方面,他认为身心之间存在着统合的关系,“身”之所以能视听言动,乃是因为“心”之作用;同时,“心”欲有视听言动,需以“身”之感官为依托。另一方面,王阳明基于身、心、意、知、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五者只是一件事情。关于这一点,他还有类似的说法:“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8]6下面,我们将对这种说法作进一步分析,以澄清五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
其一,“身之主宰便是心”。王阳明此处所说的“心”并不是从生理学的意义上讲的,而是“一天地万物以为心”[8]287的本心。在他看来,“心”为天地万物得以呈现的本体,而“身”只是心之本体的现实呈现,这见于他的如下之语:“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8]1069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认为“身”不能离于“心”,而“心”亦不能离于“身”:“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8]103人若无此本心,则无感官之知觉作用;无此感官之知觉作用,本心亦不能流行显现。最终,“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8]103。质言之,心身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之关系,既不能离心而言身,亦不能离身而言心。
其二,“心之所发便是意”。王阳明区分了“心”与“意”:前者为万物得以呈现的本体,为人人共有的同一本心;后者为本心依于个体之身所发动,表现为个体的意识活动。王阳明既以意识为本心所发动,也就表明意识之根源非是身体,而是灵明感应的本心。一般所谓的身心问题,乃是指作为生理基础的身体与作为心理活动的意识之间的关系,但在王阳明这里,本心与意识有着严格的区分,并不可笼统而言之。
其三,“意之本体便是知”。在王阳明看来,意识之所以有思虑认知的功能,其根本在于虚灵明觉之良知:“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8]53何为良知之虚灵明觉呢?良知广大,能容万物,故为“虚”;良知灵动,能感万物,故为“灵”;良知光明,能辨万物,故为“明”;良知觉照,能察万物,故为“觉”。良知之虚灵明觉,本无主客、内外之分,感物而动则为人之意识活动。究言之,人之意识之所以有思虑觉知的作用,乃是因其以虚灵明觉的良知作为本体。
其四,“意之所在便是物”。意识具有意向性的作用,其生起时必指向对象。这种意识所指向的“对象”,呈现于人则为“事物”。关于此问题,王阳明多次论及:“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8]103“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8]1429意识作为对象化的活动,其意向所“在”之处,即有“物”之呈现。如果说“物”真有其本质的话,那它不过是意向性的建构。
综言之,身、心、意、知、物五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身”为心之凝聚充塞,亦为“心”所主宰,是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流行生生不已,发动而为人之意识,是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识之思虑觉知,源于良知之虚灵明觉,是为“意之本体便是知”;意识生起必有其对象,而对象之所在即为“物”,是为“意之所在便是物”。简论之,身体之主宰便是本心,本心之发动便是意识,意识之本体便是良知,意识之所在便是事物,五者之间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秉持“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的身心观。
就“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而言,此时尚没有主客体的对待,亦即没有对象化的问题,并未形成意识层面的认知,更没有理论化的建构,故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场域。也就是说,在“大我”的层面,身、心、意、知、物五者互摄互入而不可割裂,共同构成了一种源初性的场域化存在,当任一维表现出来时,即以这种场域性整体为背景。质言之,五维中任一维,皆具有其厚度①。任何一维皆不可独立存在,而为其余四维之聚集:以“心”而言,其凝聚为身体,其发动为意识,其灵明为良知,其显象为万物;以“身”而言,其主宰为本心,其思虑为意识,其明觉为良知,其呈现为万物。究竟而言,“大我”之身心建构出了一个“世界”,王阳明谓其为良知的作用,“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8]120。天地万物的现实呈现,不过是良知的妙用而已。因此,王阳明此说实为一种“宇宙显现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宇宙生成论”。
如果“身”为心、意、知、物之聚集,那我们就不难理解现象学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了。胡塞尔对身体与世界的共构共生关系有这样的回溯:“从源初的身体性知觉出发,由低阶到高阶依次描述物体、心灵、精神诸区域的本质是如何构成的,而这些区域既是身体本身的构成层次,又是世界的显现结构。”[9]这种对身体与世界构成关系的逐层回溯,伴随着对自然主义——物质实在是不依赖于主观体验的最终基础——的分析与批判。不过,如果说胡塞尔的论述是一种逆向回溯的话,那王阳明则是一种顺向阐明:“身—心—意—知—物”构成了源初的场域,此场域以本心为主宰,依于本心而有身体的形成与意识的活动,依于意向的活动与身体的感触而有事物乃至“世界”的显现。无论如何,“世界”的显现不离人之身心活动,梅洛-庞蒂谓之为世界与身体的辩证运动:“我的身体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世界反射我的身体的肉身,世界和我的身体的肉身相互僭越(感觉同时充满了主观性,充满了物质性),它们进入了一种互相对抗又互相融合的关系。”[10]
当然,王阳明这种五维一体的身心观,只是表明了身—心—意—知—物浑然无间,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五者之间的差别。或者说,这五维只是体现了源初场域的不同面向,因此笔者同意高新民的观点:“心、身、物、知、意等概念表示的并不是不同的实在或属性,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同一实在的不同述说方式。”[11]身—心—意—知—物五者作为场域化的存在,处于前对象化乃至前语言化的阶段,既非混然同一,亦非截然有别。故也有学者指出,王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的说法,“并非指身等同于心,而是指二者在被对象化之前的相通相融”[12]。
“身—心—意—知—物”互涉互入,构成了人之宇宙性生命——大我。那何为“大我”之“心”呢?王阳明谓其为一点灵明:“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8]122依于心之一点灵明,人能与天地万物同体共感。故而,“大我”之“心”,不过是身—心—意—知—物所构成的源初场域的神感神应。何为“大我”之“身”呢?王阳明有谓:“志气塞天地,万物皆吾躯。”[8]1146天地万物既与“我”同体,那就是“我”之躯壳形体。故而,“大我”之“身”,为身—心—意—知—物所构成的源初场域的全幅显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是天地的‘心’,天地则是人之‘身’。”[13]质言之,“真己”作为宇宙性生命,“身”乃是“心”之形体,“心”乃是“身”之灵明。
因此,就“大我”而言,“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身心一如的,并不存在身心分裂问题。但在“小我”这里,身、心、意、知、物为各别性的存在,而有“身”与“意”对立的问题。那这种对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小我”之身、意
前文已指出,“身—心—意—知—物”所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人之“真己”。但是,这种作为宇宙生命的“真己”,毕竟要依于个体生命而现实化,这就有了作为现实生命的“躯壳的己”——小我。“小我”之形成,乃是因为“身—心—意—知—物”所构成的源初场域的破裂:人不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为形体自间隔了”[8]141,终而落入了“小我”。
但是,“躯壳的己”毕竟源于“真己”,而不能离于“真己”,这就存在着“大我”与“小我”的隐显二重化:“大我”为“身—心—意—知—物”之场域化,为隐,即暗默的向度,实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名言化者;“小我”为身、意之现成化,为显,即光明的向度,则有对象化、认知化、名言化的问题。王阳明谓:“以形体而言,天地一物也;以显晦而言,人心其机也。”[14]“身”与万物共一体,故为显;“心”只是一种灵明感应,故为隐。依于源初场域之“大我”,则有“小我”的在世显现;若是固执于“小我”,则将遮蔽“大我”。借用日本学者汤浅泰雄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大我”为心身的“基底构造”,“小我”为心身的“表层构造”②。不过,即使“大我”被遮蔽,也并不妨碍其为“小我”奠基,并内在于“小我”的身心活动。这也就说明,两重心身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不过,“大我”与“小我”的隐显二重化,并不是说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而是说自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面向:前者为自我的隐秘面向,属于本真之自我,不为常人所自觉;后者为自我的显在面向,属于现实之自我,而能为常人所自觉。
人若执定于“小我”而忘失“大我”,则将失却“五维一体”的源初场域,身、心、意、知、物不再神感神应,而成为各别的存在者。就“小我”而言,则有所谓的生理基础(身)与心理活动(意)分裂的问题。这种分裂的产生,关键就在于意识的对象化功能:“意之所用,必有其物。”[8]53本来,“小我”之“身”,为“心之形体运用”;“小我”之“意”,为“心之所发”,也就是说,“小我”之身体与意识皆依于本心而产生,为本心的发用流行而现实呈现者。但是,“小我”的意识活动有自我对象化的作用:意识活动的发动者成为“自我”,意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则成为“他者”。当人执定“小我”为唯一真实自我时,也就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源初场域中脱落出来,而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分化与对立。
这种意识的自我对象化,存在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意识将自身对象化,成为“小我”心理活动的发动者;另一方面,身体也被意识对象化,从而成为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不但如此,意识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将自我与他者执定为实在性的存有。“身—心—意—知—物”本为五维一体的前主客化的场域,然而,由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及执定作用,这种源初场域破裂而有身、意、物的各别存在。即,“小我”之“身”,由口鼻四肢所构成,具有视听言动的作用③;“小我”之“意”,依于身体而发动,是为“躯壳起念”;意向之“物”,具有时空的性质,成为认知与行为的对象。终而,“小我”成为主体,天地万物则成为客体。
其实,不但“物”能被客体化,“身”与“意”也能被客体化。也就是说,本心依于“小我”而有的意识活动,能将“小我”自身客体化。当“小我”被客体化之后,也就成为有限的存在者,必定追逐外物以求得满足,这就表现为自私之意欲:“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8]25此处所谓的“逐”,即是一种执定,由之而有“私欲”与“私意”的生起:一方面,依于“躯壳”,则有自私之欲望,意味着从万物一体中的脱落,“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8]141;另一方面,依于“意念”,则有自私之意见,落入意识的谋虑算计而遮蔽了本体,王阳明谓之为“私意气习缠蔽”[8]164。当然,无论是作为感性欲望之“私欲”,还是作为理性分别之“私意”,皆是溺于“小我”而忘失“大我”。
如此,“小我”之“身”,成为与心、意、知、物有别的生理性存在;“小我”之“意”,成为与身、心、知、物对待的心理性活动。当两者被视为不同的实在时,则存在着“非一非异”之关系:非异,故能相互交感;非一,故不能相互还原。
“身”与“意”之间的“非一”关系,乃是基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作用。“身—心—意—知—物”构成了前名言化的源初场域,然因意识的对象化作用而成为各别存在者:作为本心凝聚充塞之“身”,被规定为个体生命的生理基础;作为本心灵明发动之“意”,被规定为个体生命的心理活动。当这两个概念被建构起来之后,也就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实在,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不能相互还原,故存在着“非一”之关系。
“身”与“意”之间的“非异”关系,则是因为两者共同处于“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中,只是呈现的面向不同而已,故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实能有相互的感通:一方面,“身”为“心之形体运用”,“意”为“心之发动”,作为人之心理活动的意识,需要依赖于身体才能现起,所谓“躯壳起念”[8]33;另一方面,就个体生命而言,身体也只有在意识的参与下,才能有感知觉活动的生起。故而,小我的“身”与“意”之间,实为“非异”之关系。
当然,在身体与意识“非一”“非异”的关系中,“非异”关系其实更为根本。因为身、意共同存在于源初的场域之中,在根本上即具有“非异”之关系。“身”“意”被视为不同的实体,这不过是“小我”的主观建构而已。正如怀特海指出的那样:“至于身体和灵魂心智,更是打成一片,不可分割的了。那些纯界限完全是抽象的方便的说法。”[15]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只是一种言说方便,而误以为身心两者具有不同的实体,从而导致了诸种问题的产生,“只要我们仍旧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处理意识和生命的概念,心智与身体关系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16]。
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非一非异”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他心”的问题。依王阳明所说,“一人之思虑,其变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8]1479,这就是说,人作为经验世界中的感性生命,皆有相互感通的意识活动,其中的原因在于,心知思虑皆出于本心,而本心又为人人所共有。当然,人毕竟有形体上的差异,故人心也有阻隔的可能。王阳明区分了“天理之心”与“私欲之心”,以说明人心之间为何存在着感通与阻隔的可能:
只是此天理之心,则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私欲之心,则一个人是一个心。人如何知得?[8]1293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解读这段话。一方面,人人皆有共同的天理之心,而且,意识皆依此心发动,故个体意识之间能相互感通;另一方面,意识毕竟依于躯壳生起并为私欲所障蔽,故个体之间的心理活动非是完全透明者。究言之,自我之意识(我心)与他人之意识(他心)亦同亦异。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不是停留在意识层面来解决他心问题的,而是诉诸人人共同拥有的本心。
概言之,王阳明所论述的身心关系,实有“大我”与“小我”的两层区分。就“大我”而言,“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心”为与物神感神应之“本心”,“身”为与万物同体之“大身”,两者之间存在着源初的合一;就“小我”而言,身、心、意、知、物各别现成。意识与身体为共同构成现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着“非一非异”之关系:一方面,两者皆源于本心,故能相互交感;另一方面,两者为本心的不同面向,故不能互相决定。意识不可完全还原于身体,身体亦不可完全还原于意识,故王阳明有谓:“莫将身病为心病,可是无关却有关。”[8]876此正说明了作为生理基础的身体与作为心理活动的意识之间“非一非异”的关系。
三、身、心的“合一”
如前所述,王阳明关于身心关系的讨论,并非局限于现象界的个体性生命——“小我”,而是关联着本体层面的宇宙性生命——“大我”。两种自我之所以存在隐显的双重运作,主要缘于意识的对象化执定:意识执定“小我”为真实之自我,而失却作为源初场域的“大我”;意识若不再执定“小我”,则能回归作为源初场域的“大我”。其实,类似的思路亦见于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在与芬克的对谈中指出,通过身体现象而变成可以理解的生命体的“人”,具有双重的特征:“一方面他将自己置于澄明之中,另一方面他被拘系于一切澄明的地下。”[17]如果将此说置入王阳明的语境,我们可作如下之理解:身体“将自己置于澄明之中”,意味着身体不离于“身—心—意—知—物”源初场域的澄明;身体被“拘系于一切澄明的地下”,意味着对身体的执定导致了澄明之境的遮蔽。就作为宇宙性生命的“大我”而言,“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身心之间存在着源初的合一;就作为个体性生命的“小我”而言,因为意识自我对象化的执定作用,而有所谓身心分裂的问题。
意识的执定是如何生起的呢?这涉及“大我”向“小我”的转换问题。“真己”作为“心之本体”,具有自然的明觉,而“躯壳的己”的意识则有自我对象化作用,当意识将对象化的“天地万物”乃至“躯壳的己”认定为真实的存有时,也就打破了“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这种对“躯壳的己”与“天地万物”实在性的执着,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王阳明视之为“妄念”[8]69。因此,问题不在于人之身体,而在于人对事物的执着:“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8]135“诚身”并非是在身体上用功,而是要破除对于身体的执着:一方面,身体实为无常生灭者,并不能执其为恒常,“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8]863;另一方面,身体为“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之聚集者,确可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18],故功夫之始在于知晓生身立命之原,“止于至善岂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8]1318。当然,王阳明所言“求之吾身”,为广义的“修身”功夫。
职是之故,王阳明所论的身心合一之功夫,重在破除对“小我”的虚妄执着,以复归“大我”的自然流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对于身心问题的讨论,不在于“身”如何有“心”的思虑认知,而在于如何通过道德践履以实现身心的合一:就“小我”之“意”而言,乃是“诚意”之功夫;就“小我”之“身”而言,乃是“诚身”之功夫。无论是“诚意”还是“诚身”,皆是为了破除意、欲中所夹杂的自私,以克服“小我”的身心分裂,故王阳明谓两者只是一事:“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8]44因此,不论是“诚意”还是“诚身”,功夫只在一“诚”字。那究竟何为“诚”呢?王阳明释之曰“无妄”:“诚身之诚,则欲其无妄之谓。”[8]175所谓的“无妄”,就是意念中没有对“小我”的虚妄执着,而是出于本心的真诚恻怛:“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8]1070故而,这里的好恶并非出于“躯壳的己”的感性欲望,而是出于“真己”的怵惕恻隐。
可见,身心关系的问题解决,非是从“小我”的生理基础与心理活动入手,而是从“小我”向“大我”回归。由此,王阳明实现了“修身”视域的转换,不再是追求身体的生理性变化,而是破除意识上的虚妄执着:“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展开来说,只有意识得以真诚(意诚),才能破除对“小我”的执着以端正本心(心正);只有本心得以端正,才能挺立“大我”而修养身体(身修)。
“诚”之重点,就是要观当下一念发动之处,有无虚妄执着夹杂于其间。对初学者而言,需行省察克治之功夫,即在一念生起时观其是否为私欲所缠蔽,“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8]18。若无自私之意欲缠蔽,则为“不作一念”之功夫:“从目所视,妍丑自别,不作一念,谓之明。从耳所听,清浊自别,不作一念,谓之聪。从心所思,是非自别,不作一念,谓之睿。”[8]1292依此处所说,眼之所见者固然有美丑,耳之所听者固然有清浊,意之所思者固然有是非,只是不能落于自我之执念,这就是所谓的“无我”功夫:“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8]258只有破除了对“小我”的执念,才能回归本真的“大我”。
当然,“无我”是对自私意欲之破除,而非对“小我”的彻底否定。质言之,“不作一念”非是如槁木死灰般没有任何念头,而是说在念头生起处无有一毫滞碍。换言之,停止对声色的追逐并非废绝感官的作用,而是说不要为感官之欲望所陷溺,才能回归本心之灵明感应。王阳明谓之为“全”之功夫:“吾率吾灵而发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8]1480同理,发之于耳,则自辨乎声而不蔽乎声,是为“全聪”;发之于口,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是为“全嗜”[8]1480。故而,功夫的重点不在于止息感官的作用,而在于破除感性欲望中的执着。但是,人之执念透彻骨髓而沦为习气,并不能单单透过意识层面的认知而破除之,需是行事上磨炼的功夫方能将其彻底破除。这也就表明,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与其说是道德认知的问题,毋宁说是道德实践的问题。
从更深层次上看,“小我”的身心安顿实关联着对“大我”的体认,这就涉及如何回归万物一体之境的问题。由此,王阳明也开出了身心关系上的伦理维度。在他看来,众生本为一体性的存在,休戚相关而共同在世。“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8]89-90人人皆有万物一体之悱恻不忍,故他人之困苦荼毒切于吾身。人不能痛切感受之,只是因被私欲所蔽,故功夫之要在于放下对“小我”的执着,以回归与万物同体之“大我”。也就是说,只有突破“小我”的有限性,才能敞开与万物同体的存在场域。故而,自我身心之安顿,关联着所有众生:“惟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夫以天下为一身也,则八荒四表,皆吾支体,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间乎?”[8]1128因此在王阳明这里,与万物为一体并非神秘莫测之境界,而是个体生命同体共感的真切觉受。
人若能回归万物一体之仁,则一切视听言动皆为身心之妙用。王阳明下面这一段话,可谓对身心合一境界的最佳表述: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8]62
当人无有对“小我”的私欲执着而全能其万物一体之仁时,则能回归“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如此,一切身心之活动皆出于本心的自然流行,一切言行皆散发出德性的光辉。就此而言,身心本体也是仁体,良知学即是仁学。这里,存在着“小我”与“大我”身心的主动与被动的逆转。在“小我”层面,身心因被自私之意欲所缠蔽,故片刻不得安宁,“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8]1302,“小我”之身心看似为主动者,实为种种外缘限制而处于被动之中。那如何才能实现生命的主动呢?“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8]1302人只有通达功名利禄之无常,才能不为名利所困而实现身心的合一。此时,“大我”之身心转而成为主动者,“天君泰然,百体从令”[8]35。汤浅泰雄有类似的说明:在“无心”即无意识执定的状态中,“自我的‘心灵’与‘身体’中的主体的=客体的双义性消失了”[19],人若回归“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则能超越主客体的对待与限制,亦能使身心得以彻底安顿。
故而,阳明心学的这种身心合一说,既非指身体技艺之娴熟,亦非指洒扫应对之自然,而是指对本真“大我”的逆觉体证。修身之关键不在于泯灭“小我”的身心活动,而在于破除对“小我”的虚妄执着,以复归“大我”的身心合一。
余 论
综而言之,王阳明对身心关系的思考,其特色在于区分了两重层次。就“大我”而言,“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为整全的存在场域:“心”为隐微之本体,赋予天地万物以存有的意义;“身”为现实之世界,赋予天地万物以客观的性质;心、身只是“五维一体”的不同面向,故存在着本源性的合一。就“小我”而言,“心”为本心发动而有意识,“身”为本心凝聚而成形体,两者之间存在着“非一非异”之关系,执定之则有“五维一体”整全场域的破裂。这种对身心关系的两重区分,可以说为解决身心难题提供了绝佳的思路。“大我”之身心为绝待性的场域化本真存在,“小我”之身、意则有“非一非异”之关系,这就超越了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局限。
就中西方对身心关系的讨论而言,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前者基于人的两重生命而展开,重在讨论如何由“小我”回归“大我”的问题;后者则基于现实化的个体生命,重在讨论“小我”中身体与意识的交互作用。基于现实的个体生命讨论,“身”为形体层面的生理基础,“心”为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为各别存在的实体,故有身心的二元。同时,西方哲学对于身心关系的讨论,重在感受与认知等维度,虽有其理论上的价值,但并不能解除身心分离的痛苦。在王阳明这里,“小我”身心的二元对立,不在于心理(意)与生理(身)的分化,而在于意识对于“小我”的执着。只要破除了这种执着,就能实现身心的合一。可见,阳明心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此亦表明,中西哲学之间具有相互镜鉴乃至相互资益的可能。
注释
①笔者此说受到了杨儒宾的启发,其谓:“这种呈现最直接可感的向度当然是意识的,但意识扎根在前意识的基础上,前意识的向度又渗透到身体的向度。换言之,意识的明光后面还有层层的暗默向度为其支柱。”杨儒宾:《儒家的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版,第10页。②汤浅泰雄认为心身有表层与基底两重构造:心身的表层构造指掌控着运动器官的大脑皮质的体性神经系统,伴随着“有我”的“明亮的意识层”;心身的基底构造指掌握着内脏器官的皮质下中枢的自律神经系统,伴随着“无我”的“晦暗的意识层”。汤浅泰雄:《身体论:东方的心身论与现代》,黄文宏译注,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258页。不过,汤浅泰雄主要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讨论身心的两重构造问题,这与阳明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③王阳明虽然指出了“身”为心之充塞,但对“身”如何客观呈现的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说明。在笔者看来,“身”既为心、意、知、物之聚集,那其依于主体间性的作用,就能呈现出客观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