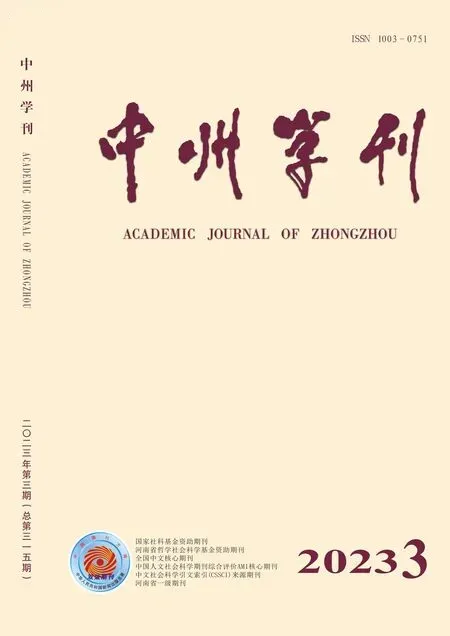《左传》文化精神的尚言内蕴
刘 梅
语言承载着人类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语言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尚言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我国现存商周史料中保存比较完整和颇具史料价值的古老文献《尚书》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都有对言辞的重要性的论述。如《尚书》中有“嘉言”“谝言”之说。“嘉言”出自《虞书·大禹谟》:“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1]86帝舜认为大禹之见“为君的能知道为君的艰难,为臣的能知道为臣的艰难,那么,政事就能修明,黎民百姓也会注重修德”很有道理,若能如此,嘉言就会被采纳,贤才就不会被遗弃,万邦就会太平。“谝言”出自《周书·秦誓》:“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1]570“谝言”是指那些巧善辩佞之言,君子容易产生疑惑。但无论是“嘉言”还是“谝言”都体现了对言辞的重视。《诗经》中的《大雅》有不少诗句表达了对言、辞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诗·大雅·板》云:“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2]1145《诗·大雅·抑》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2]1167这是人们重视言辞思想的客观显现,这也说明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言辞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重要意义也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拥有知识的贵族阶层越来越讲究言辞的修饰,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语言、追求辞令之美的风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1106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言语”也是紧承“德行”,可见其意义之重要。
《左传》作为春秋时期一部重要的典籍,其记载的风格各异的辞令蕴含了“言,身之文也”[3]418的语言文化精神,正像唐人刘知几所说:“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典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4]303士人们雅好辞章,注重文饰,追求立言不朽,彰显了一个讲求辞令文化的时代风格。
一、新体文言的语言追求
春秋时代,不光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上也发生了剧烈转型,开启了一个追求文饰典雅的语言变革时代,讲求辞令之美的创作走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赋诗言志,温文尔雅;行人辞命,曲回有致;君臣应答,含英咀华,新体文言的理论和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场文言变革中,《左传》以其卓越建树担当起文言变革的主力军。与商周以来古拙简奥、佶屈聱牙、句式简单、不尚修饰的古体文言相比,一种形式灵活、富有节奏、典雅蕴藉、注重修辞的新体语言已经形成。钱基博先生认为:“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章之规模具也。文言者,折衷于文与言之间。在语言,则去其方音俚俗,而力求简洁;而于文,则取其韵语偶俪,而不为典重。音韵铿锵以为节,语助吟叹以抒情,流利散朗,蕲于辞达而已。后世议论叙述之文,胥仍其体。自文言而益藻密,则为齐梁之骈体。自文言而益疏纵,则为唐宋之文。此其大较也。”[5]23“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5]21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懂得对直白的语言形式(言)进行自觉的文饰和美化(文)的时候,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文言变革的时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春秋时代实现了从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跨越,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随着新体文言的成熟,讲求辞采,崇尚辞令,渐渐成为时代的风尚。《诗经》在春秋中叶结集,辞采飞扬;孔子为《乾》《坤》二卦作《文言》,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春秋》绝笔于泣麟,“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4]8;《左传》步其踵武,典雅博奥,为史家之大观。于是《尚书》的凝重迟缓渐渐被清新典雅的风格所代替,预示着讲求辞令、洋溢着礼乐文明之盛的语言变革时代的到来。
二、建言修辞的语言风尚
春秋时代是一个注重修辞的时代,因为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事件都有赖“文辞之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3]1106可见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特别强调对文辞的重视。“子产献捷”的辞令显然不是即兴创作,而是精心准备,有备而来,甚至是以文本形式流传的,所以孔子才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叔向也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3]1189
刘勰用“建言修辞”[6]来概括春秋时代的尚言风尚。春秋时期,文言的创作与理论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了春秋时期文质彬彬社会风习下普遍的修辞意识和修辞习惯,同时彰显了“建言修辞”在社会实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春秋时期,辞令创作已经进入专门化甚至于职业化的时代,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对辞令进行精心创作,《左传》就是一部“建言修辞”的典范之作。正如刘知几所说:“《左氏》之叙事也……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4]330钱钟书先生也说:“刘氏举《左传》宋万裹犀革、楚军如挟扩二则,为叙事用晦之例。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史有文心之证。”[7]《左传》重之以文饰,建言以修辞,二位先生可谓道尽。
《左传》记载了不少建言修辞的事例,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3]410-411
秦穆公设宴招待重耳,子犯说:“我不如赵衰有文采,请您让赵衰跟随赴宴。”公子在宴会上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赵衰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退到阶下,拜,叩头,秦穆公走到下一级台阶辞谢。赵衰说:“君王把辅助天子的事命令重耳,重耳岂敢不拜?”在晋文公逃亡路上,赵衰以富有文采而担当赋诗言志的重任,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又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3]1535
“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吾子欲覆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苌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3]1542
读完这段文字,对于祝佗的口才,对于祝佗对历史掌故的谙熟令人叹观止矣。定公四年,刘文公受周王之命在召陵会合诸侯,策划进攻楚国的事宜。这次会盟,卫国的子行敬子建议卫灵公带上祝佗,因为子行敬子认为诸侯大会一定会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祝佗出色的口才就会发生作用。对于祝佗的口才之好,孔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8]77果然,周人准备在歃血的时候“长蔡于卫”,他们的理由是“蔡叔,康叔之兄也”。这时祝佗摆事实,讲道理,娓娓道来,谈到周代历史掌故如数家珍,有理有据,最终说服周人“长卫侯于盟”。这些都是春秋时期追求“建言修辞”的明证。
范宁在《春秋谷穀梁传·序》中谓《左传》“左氏艳而富”[9]。所谓“艳”,唐人杨士勋疏曰:“‘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虽然范宁评价的是《左传》的文辞,而实际上“文辞可美”却代表着整个春秋时代的“文言”特征。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自觉的文言思想和修辞意识已经形成,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使得春秋文言改变了以往文辞凝重古板的特点,呈现出流畅而灵动、文雅而夸饰的新的美学风貌,彰显出灿烂华美富艳夸饰的艺术境界。章学诚《文史通义》云:“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10]因此要想达到愉悦雍容、温文尔雅的教化目的,就必须修辞,必须文饰。修辞的过程即是对语言艺术化美化的过程,这也就成了早期辞令创作的“建言修辞”。
三、立言不朽的精神追求
司马迁写《史记》要将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1],以求扬名于后世,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左传》就明确表达了这种“立言不朽”的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3]1087-1088
在穆叔看来,像范宣子那样从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一直到晋主夏盟为范氏,世代为官,累世荣光,这充其量只能称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而像鲁国大夫臧文仲那样身没言立,声名传于后世,才能称为真正的“不朽”。因为高官厚禄只能代表地位的尊贵,是无法与“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相提并论的。
春秋时代,文学、史学、哲学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在交际活动中对言语艺术的重视,使辞令表达成为春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春秋辞令,作为春秋时代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既包含着时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蕴含着时人对辞令历史作用的认识。出于对辞令历史价值的思考,春秋时代人们精心修饰辞令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自身修养或完成使命,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希望自己文雅的辞令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下来,他们希望辞令也能够不朽于世,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立言不朽”思想尤其成为春秋以来士人的精神追求,这无疑说是在人生的价值观方面为“建言修辞”的语言追求作了一个摇旗擂鼓的呐喊。
由此可见,《左传》不仅讲究“建言修辞”,注重对语言的修饰,而且在精神追求上也崇尚“立言不朽”,显现了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一“立言不朽”观点的提出也是基于春秋时代辞令运用的实践,人们在实践中对辞令的重视和运用促使春秋辞令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四、文士集团的初见端倪
文士集团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像梁园文士集团、邺下文人集团、金谷雅集、兰亭之会总能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丝竹唱和、诗酒风流的旖旎画面,但说起文士集团的形成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文士集团已经初步形成。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子产从政的故事: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3]1191
子产处理政事,择其能者而用之。冯简子能够决断国家大事;子太叔外貌秀美又有文采;子羽不仅了解四方诸侯的政令,还能辨别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职爵位、尊卑贵贱、才能高低,并且还善于辞令。裨谌善于出谋划策,但裨谌为人喜静不喜闹,所以在安静的野外思考就能有正确的判断,在喧嚣的城里谋划就会失败。每当郑国有不能决断的外交事宜,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四方诸侯的情况,并且让他多写一些有关外交辞令的文稿,然后和裨谌一起驾车到野外去,让他看看策划是否可行,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来做出决断。如果可行,就把任务交给子太叔去执行,以应对诸侯宾客,所以,子产执政的时候很少把事情办坏。
春秋时期,郑国作为蕞尔小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时常受到他们的挤兑,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但郑国虽然不是军事大国,武力不如别国,可在文化上却非常繁荣,有着悠久的让人注目的诗书传统。子产执政期间,就把郑国一批富有诗书教养的文士聚拢到自己的周围,各尽其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群策群力,在政治外交上担当着重要角色,也因此标志着一个应对四方、雅好辞章的文士集团正在形成,而且《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记载也与这段文字相辅相成: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8]185-186
从“草创”到“讨论”到“修饰”再到“润色”,清晰地展示了文士之间相互切磋,各尽其能,从而共同完成辞令创作的全过程。傅道彬说:“春秋时代士人集团文武分途,一批熟悉礼乐经典、长于辞令表达的文士从士人集团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支新的并渐渐取代武士集团的新兴力量。比起武士的披坚执锐、叱咤风云,文士们更熟知典章礼乐,娴于辞令,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独立的文士集团是春秋时期的辞令创作和歌诗活动的主体力量,也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12]
我们再来看看《左传》记载的在郑国的三次赋诗活动:一次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赋诗;一次是《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的赵孟再次经过郑国时的又一次赋诗活动;还有一次是《左传·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这三次赋诗,文士相聚,丝竹管弦,唱和应答,辞采飞扬,特色各具,让我们看到了文士集团的渐趋形成。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垂陇赋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3]1134-1135
《左传·昭公元年》赋诗: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3]1208
子皮赋《野有死麇》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3]1209
《左传·昭公十六年》六卿赋诗: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
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3]1381
襄公二十七年,郑简公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叔段跟从郑简公,赵文子让七子赋诗以观其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的第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赵文子对其赋诗都一一作了评价,垂陇赋诗俨然就是一个文雅风流的文人聚会。
过了数年,赵孟再次经过郑国,在历史上又留下了一次诗酒唱和、赋诗言志、其乐融融的赋诗佳话:赵孟、叔孙豹、曹大夫三人路过郑国,郑伯想要同时享燕他们。先是由子皮向客人通告,这也是当时的礼节。礼节完毕之后,赵孟赋《瓠叶》,取其古人不以微薄废礼,虽瓠叶兔首犹与宾客享之,表示希望一切从简,一献即可。但是飨礼上,郑伯仍然备以五献,赵孟再次向子产表达了自己希望一切从简的愿望,一献即可,并且说明此行只不过是路过郑国,并非专门来聘问郑国。飨礼完毕又设宴款待。在宴会上叔孙豹赋《鹊巢》一诗,穆叔之意或比赵孟为鹊,以己为鸠,大国主盟,己得安居,借此对晋国和赵孟的安鲁之功表示赞美,赵孟谦虚推辞说自己实不敢当也。叔孙豹又赋《采蘩》一诗,子皮赋《野有死麇》,都是对赵孟的溢美之词。赵孟赋《常棣》,是取其第四章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2]571的意思,表示晋鲁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当时各国的卿大夫在礼典之上,以诗代言,各为其国,也可谓用心良苦。
昭公十六年夏季四月,郑国的六卿在郊外为韩宣子饯行。韩宣子说:“请几位大臣都赋诗一首,起也可以顺便了解了解郑国之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所以,韩宣子说:“孺子好啊!我有希望了。”子产赋《羔裘》,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用以赞美韩起,所以,韩宣子说:“起不敢当。”子太叔赋《褰裳》,取其“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意为若宣子思己,将有褰裳之志,若不我思,将会另行寻求保护,所以,韩宣子说:“有起在晋国执政,不会再劳烦您去侍奉他国,我们会保护郑国的。”子太叔拜谢。韩宣子说:“好啊,您说得对!只有有所警戒,才能善始善终。”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在此次宴会上,郑国六卿所赋之诗皆不出郑国之外,而且都表示友好,韩宣子非常满意,气氛极为融洽,这分明又是一次诗酒风流的文人雅会。
从子产用人各尽其能,把一大批贤能之士都笼络到自己的周围,到《左传》记载的发生在郑国的这三次赋诗活动,我们可以看出郑国浓厚的诗书传统,文化上的繁荣。实际上他们有意无意的文人雅会、诗酒唱和标志着文士集团的渐趋形成。而且这渐趋形成的文士集团也展示出了自己的风采,是春秋时期辞令创作和歌诗活动的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了春秋时期辞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在春秋历史文化的舞台上也不啻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土壤上,“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辞令创作表现出职业化专门化的倾向,文言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独立的文士集团渐趋形成,立言不朽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把那一时代的语言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文饰典雅、立言不朽的语言追求和精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辞令应对彰显了《左传》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精神,那些或直白或委婉的语言所生成的表达效果显示了《左传》语言文化的巨大魅力,把春秋时期的辞令文化推向了高潮。因此《左传》不仅让我们欣赏到精彩纷呈、极具魅力的辞令应对,也让我们领略到了春秋时期美轮美奂的辞令文化,很难不让人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气质心生神往。时至今日,每每读到《左传》,仍然感到是在享受着一场温文尔雅、丝竹唱和的语言文化的饕餮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