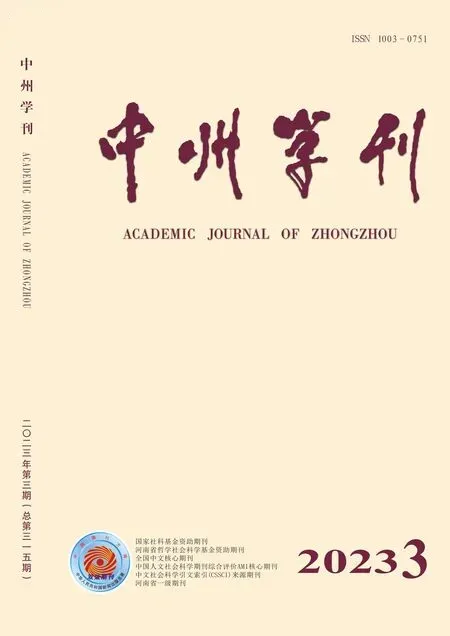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体系探论
王晶波 马托弟
有关生命、疾病与社会的考察,是近年较受关注的论题之一。唐代敦煌地区是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不同民族对疾病的认识以及由之形成的医疗观念有着显著差异,同时,由于地处西北边陲,敦煌的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生的数量、水平,药物的供应、配制,民众的观念认识等,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传统巫术和不同的宗教治疗仪式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利用敦煌材料对医疗相关问题进行的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极有特色①。这些研究基本勾勒出了敦煌古代医疗史的大体面貌,使我们对敦煌古代医疗的认识进一步清晰起来。不过,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偏重于文献或具体问题的讨论,对敦煌疾病医疗的整体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而敦煌材料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观照那一时代医疗、社会等整体情况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些繁杂的文献中找出相关材料,探寻、分析唐五代时期有关医疗卫生组织、医疗资源、方法应用等涉及医疗体系的内容,可以为全面复原与认识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医疗史的情况,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角度。
一、唐代敦煌的官方医疗组织及其特点
根据《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等资料,得知唐朝中央设有太医署、殿中省尚药局、药藏局。“虽然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三大中央医疗机构组织严密并且集中了当时医中才俊,但是其服务对象是皇室、官僚贵族、宫廷、禁军、官奴婢等,除非有皇帝特诏以及发生大规模传染病,否则这些医疗机构并不负责为平民疗疾。”[1]26-27
唐朝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在地方州府设医药博士及医学生。《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记载:
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几,医学博士、学生并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2]1314
根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有州学、县学、医学,“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3]68。P.2657《唐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记载:“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3]69可见,唐代敦煌设有医学博士和医学生。敦煌所在州沙州按人口属于下州,如果按照《新唐书·百官志》中的医疗机构设置,沙州应该只有一个医学博士,十个医学生。这对于三万左右人口的敦煌来说,实属杯水车薪。“唐代的官方医疗机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使命都非为平民服务,其组织机构和规模也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典章制度和诏书中经常提到的医治平民的字样,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种‘姿态’罢了。”[1]32
即便如此,官方医疗机构的设置,对医学的提倡和示范作用仍不容小觑,对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人才的培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政事·医方》记载了开元十一年时复设地方医学博士的诏书,其中记载了地方医学博士对地方社会医疗的价值:
神农鞭草以疗人疾,岐伯品药以辅人命,朕诠览古方,永念黎黍,或荣卫内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叹息。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将何以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4]595
安史之乱后敦煌由吐蕃管辖,唐代设立的医疗机构不复存在,但是吐蕃的医学书籍和医药知识又成为敦煌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宗教信仰与敦煌的佛教、道教医疗
唐代佛教盛行,作为唐代管辖区域的敦煌,其佛教信仰繁荣程度较之中原有过之无不及,吐蕃及归义军管辖时期,虽然未见官方医疗的资料,但是敦煌所存邈真赞中却多有对僧人医术的称赞之词,如P.4660《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称赞翟法荣为:“五凉师训,一道医王。名驰帝阙,恩被遐荒。迁加僧统,位处当阳。”[5]484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称赞索崇恩为:“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5]721P.466O《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对金光明寺索法律的称赞为:“堂堂律公,禀气神聪。行解清洁,务劝桑农。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5]360P.466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称赞索智岳为:“寒松比操,金石齐坚。上交下接,众听推先。殷勤善诱,直示幽玄。药闲中道,病释两边。”[5]474
从以上对敦煌僧人功德的记述,可以看出,这些僧人除了以其高深精湛的佛教知识和修养受到崇敬之外,他们还发挥自己的医学才能尽心为当地民众服务,因此受到广泛赞誉,充分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寺院和僧人在民众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吐蕃管辖敦煌以后,“学术文化从官府转向寺院。这时,除了民间医家依旧收授徒弟外,寺院医学就显得格外重要。‘五明’是作为高僧应具备的条件,而‘五明’之一的‘医明’,就是精通医学。过去‘医明’只是僧侣生活和传教的辅助手段,到这时随着‘医学’的废止,传授医学知识和为民众疗疾治病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僧侣身上”[3]68。
敦煌医学文献里有诸多佛教治疗疾病的药方,尤其是密教文献里有诸多治病的内容。P.2665、S.6107《佛家方第一种》里面记载了药物配佛教咒语治疗眼病、耳病、腰脚疼的药方。另外,S.6151《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是有关观音疗疾的经典,S.5741号文书《观世音不空绢索心王神咒经》中有“观世音不空绢索心王神咒和眼药法”[6]478,北7468《如意轮王摩尼别行印》中有一组手指押印法,其中有“以头指恰(押)大母指,此(令)一切诸病人疼痛便差。以头指恰(押)大母指下节文,令病人得睡。以头指恰(押)大母指背上节文,温(瘟)疟除差”[6]80-481的内容。
除了佛教医疗,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道教医疗文献。道教是唐代的国教,唐代道观遍布全国,其盛行程度虽然不如佛教,但是在民众的信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吐蕃管辖敦煌后,“道教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着,只是以宫观为中心的道教由此走向衰落,道教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往往借助占卜术等其他形式存在”[7]23。道教信仰渗透在民众生老病死的各个层面,在医药领域,道教自然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道教炼丹求仙的追求是以治疗疾病、保证身体的健康为前提的。从东汉末年以来,治疗疾病一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之一。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诸多道教的医药资料,除了道教的辟谷方和疗服食方,还有P.4038《道家方》[8]673-677,其中包括十二个医方,涉及治白发、声哑、鼻疮等生活中常见的疾病。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道教医疗在敦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医疗角色[9]89。道教的医学多以求仙为目的,佛教医疗药方虽然充斥着不少咒语及夸大药效的表达,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药方在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甚至养身、强身健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当时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敦煌的多元民族医疗资源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居的地区。“敦煌地区从汉代建立敦煌郡起,就是多民族居住区域,这里有汉族移民,也有少数原住民族,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大量的其它民族移居敦煌地区,如吐蕃人、吐谷浑人、鄯善人、龙家人、粟特人等。”[10]36
伴随着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民族医药医疗成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的重要特色。敦煌祆教文献中有和疾病相关的内容,“小儿疾赛神”记载小儿疾患,即需祈赛小儿神,共十六位女神。“此十六个女神并拥护小儿,其小儿未满十二岁。此十六个神变身作恶形,却与小儿作患害,……欲得小男女无病患,每须故故祭此神等,小儿即得病愈。”[11]63北敦00256《摩尼教残经》中有“缘此法药及大神咒,咒疗我等多劫重病,悉得除愈”②的记载。S.3969、P.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轨》中记载摩尼寺教堂中有病僧堂,“佛医瑟得乌卢诜,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身之异号也”③。摩尼教《下部赞》中也有治疗疾病的内容。景教《志玄安乐经》中有治疗疾病的记载,敦煌出土景教经典《尊经》,“据吴其昱研究,《尊经》中《摩萨吉思经》,萨吉思是居住于叙利亚东北的艾那长老,擅长医术,精通希腊哲学及医学,和景教主教来往密切。因此,这里的《摩萨吉思经》应该也记有希腊科学内容,甚至记有希腊医学方法,若果如此,则又和布拉依克出土药方有关,至少它们有一个共同来源”[12]393-394。
吐蕃医疗是敦煌民族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火灸疗法》《古藏文灸法图》《吐蕃医疗术》等,《吐蕃医疗术》是吐蕃医术、医方的合集,涉及生活中常见的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用药简单易行。同时,敦煌吐蕃药方里有关于冷疾、解酒药、解毒药等药方体现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药物的配方就地取材,是研究藏族医药文化的重要资料。火灸法也是藏族独特的治疗疾病的方式,体现了藏族民众在艰难的地理环境中的生活、生存智慧。
除了多元宗教中包含的医药医疗,在敦煌也发现了一些域外医药文献。如《医理精华》《耆婆书》等,其中《耆婆书》用梵语、于阗语两种语言抄写。“这些敦煌出土胡语医药文献流传甚广,并且其中的外来医药知识对敦煌出土汉语医药文献产生影响。”[13]59-60“敦煌文献中所显示的医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涉及药物、药方、药具、疗法,乃至治病去疾的术数、法术甚至咒语,这些医学资源的来源也是相当广泛的,既有来自中原的历代中医家,也有来自敦煌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有的来自中亚、印度乃至波斯等殊方之地。这些医学资源汇聚在敦煌一地,既为敦煌民众的日常健康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为中外医学文化的交流做出显著的贡献。”[14]265多民族医疗及域外医疗丰富了当时社会的医疗资源。
四、敦煌民间的自我医疗
除了以上的官方医疗机构、佛道教医疗组织、多民族医疗体系之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民间自我医疗的内容,如简单易行的单药方、灸疗、食疗及禁咒法。
1.敦煌单药方
敦煌医药文献中,有多种单药方、选方。《单药方》不见于古今书籍收录,因每病只有一种药或灸一个穴位或一个禁方,因此马继兴将其命名为《单药方》,涉及85个药方,每种疾病只用一种药或艾灸一个穴位,可能是敦煌医人或者普通家庭使用的实用医药手册。《单药方》中涉及的疾病有:流鼻血、蛊毒、鬼魇死、恶疰入心欲死、急黄疸黄、急疳、赤白痢、恶肿疼痛、蛊水遍身洪肿、偏风、冷痹、癫狂、疱、花疮、火烧疮、恶疰、疗(丁)疮、妇人多失子、失音不语、鱼骨在咽、小儿霍乱、妇人月水不止、避孕、产后腹痛、难产、心痛、温痒、风病、产后出血、小便不利、腹胀心痛、恶疮、女人带下、产后小便不通、产后胎衣不下、舌肿、秃疮、不孕、生女不生男、头风、眼流泪、胎死腹中、盗汗、小儿舌疮、痔疮、烂唇、蜘蛛及蚕咬人、小儿惊啼、小儿夜啼、疟病、咽痛、夫妻感情不和等[15]179-194。
《单药方》中所记载的疾病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疾病类型。敦煌医方中还有妇产科、儿科等疾病的药方,内容丰富而具体,突出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不仅具有医学价值,而且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现着古人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同时有关美容和养生的药方,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单药方是唐五代时民间应对疾病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多次下颁药方或刻石给民众提供医疗方便。这一方面是写本时代抄写书籍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单药不仅易得,而且比多味药方价格要便宜,这对贫苦民众来说,是最实用的医疗方式。敦煌文献龙.3096《药价文书第二种》对当时的药价有详细记载:
鞭鞘一条,上直钱□□文,次一文五分,下□□文。
郁金花一分,上直钱六十文,次五十文,下四十文。
麝香一分,上直钱一百二十文,次一百一十文,下一百文。
丁香一分,上直钱三十五文,次三十文,下二十文。
白檀香一两,上直钱五十文,次四十文,下三十五文。
□上直钱五十文,次四十五文,下四十文。
□下四十五文。[15]506
由敦煌《药价文书》可知,唐代药物价格分为上中下三等,将此药价与同时期普通民众的收入与其他生活、生产用品的价格,甚至是借贷的价格比对,可以得知普通民众对医药资源的可得性并不高。S.9987-B2《备急单验药方卷并序》的序部分记载了普通民众获得医药资源的困难及单药方的便利之处:
时人遇疾,枉死者多,良药目前,对之不识。葛氏之鄙,耻而不服,误之深矣。且如猪零(苓)、人粪能疗热病,急病,取对目前,岂得轻其贱秽弃而不服者哉?人之重信古疑今,如幸黄帝、仓公、和、缓、扁鹊之能,依用自取鸠集单验,始晤(悟)天地所生,还为天地所用,触目能疗而救急易得,服之立效者一百八方,以人有一百八烦恼,合成次劳市求,刊之岩石,传以救病,庶往来君子录之备急,自验,代劳致远,深可救之。[16]49-50
唐代释智严译《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中提到了穷人用单方的记载:“譬如有一贫病之人求医疗疾,以其贫故医处单方。于时贫人病愿除愈,药价贱者服之病除。何以故?是贫病人以无力故。”[17]950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说:“故古方或多补养,或多导泻,或众味,或单行。补养即去风,导泻即去气,众味则贵要,单行则贫下。”[18]19
2.灸疗法
灸疗法是敦煌地区普通民众的重要医疗方式,敦煌出土的P.2675《新集备急灸经》卷首记载了灸法的简单易得:“今略诸家灸法,用济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诸家杂忌,用之”,“神验无比”[8]201。
于赓哲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中认为:“就基层民众中使用的普遍程度而言,灸、针地位的兴替发生在唐宋之际。在唐代,灸疗法主要的是掌握在普通民众而不是医师手中,手法简单粗放、廉价易行,因此,灸疗在唐代不少地区基层民众日常医疗活动中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宋代,灸疗法在民间的重要性逐渐降低。”[1]154-155P.2622《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天行热疾方”中就是用灸法治疗骨蒸:
治天行时气热疾后变成骨蒸□人,灸病人手臂内大横文后四指□上量四指三壮,手足左右同壮灸。[15]324
另外,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灸法图。《外台秘要》引《崔氏〈别录〉灸骨蒸方图》的序文记载了灸法图的优势:“此方扶危拯急,非止单攻骨蒸,又别疗气疗风,或瘴或劳,或邪或癖,患状既广。救愈亦多,不可具录,略陈梗概。又恐传授谬讹,以误将来,今故具图形状,庶令览者易悉,使所在流布,颇用家藏,未暇外请名医,求上药,还魂反魄,何难之有?遇斯疾者,可不务乎。”[19]233可见灸法一直是普通民众医疗的重要方式,敦煌没有医理的药方尤其是单方中也有灸疗法,每种病只灸一个穴位,简单易操作。
晚唐五代宋初,雕版印刷技术在敦煌医药知识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使得灸疗法进一步为民所用。例如P.2675《新集备急灸经》写本,书题下标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可知“其原为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8]200,P.2675正是据“京中李家”的印本抄写而来的。写本卷首题记为:
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或居偏远,州县路遥;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灾疾,药饵难求,性命之忧,如何所治。今略诸家灸法,用济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诸家杂忌,用之,请审详,神验无比。[8]201
从文中可知,“京中李家”书坊编印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流行于当时的诸家《灸经》汇集成册,用印刷的方式将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出去,以便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20]62。
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社会还流行着和灸疗法相关的节日风俗。P.2721《杂抄》中所载:“八月一日何谓?其日以墨点之,名为灸,以厌万病,大良。”[21]171正是古代八月一日“点灸”治病防病的节俗仪式。其中的“以墨点之”的“墨”当系朱砂调和的特殊之墨,对此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节候赏物》有“八月一日,赏点炙枝、朱碗子”[22]111的记载,其中的“炙枝”是蘸取朱砂在小儿眉心点灸的工具,“朱碗子”是研磨、调制朱砂的碗,更可能是装有调和好的朱砂的碗。朱砂作为药材,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这种在穴位处进行点灸的方式,应当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病、防病功效,因而古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厌万病”。实际上,八月一日天灸节,又被称为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治病防病的日子④,相关习俗历史久远,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敦煌地区这一节俗的存在,对当时的民众而言“不失为是一种带有神异性和信仰性的医疗手段,同时也是古人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体现”[23]30,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灸疗”的流行。
3.食疗法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食疗本草》的部分内容,《食疗本草》是唐朝孟诜所著,孟诜完成后,张鼎在此基础上又补89种,共计227条,没有传世本。敦煌本《食疗本草》共记食物26种,连同所附医方共82条,所记食物为石榴、木瓜、胡桃、软枣、榧子、芜荑、榆荚、吴茱萸、蒲桃、甜瓜、越瓜、胡瓜、冬瓜、瓠子、莲子、燕蕧子、楂子、藤梨、羊梅、覆盆子、藕、鸡头子、菱实、石蜜、砂糖、和芋,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各个方面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食疗本草》中涉及的食物都是常见的果蔬,对普通民众来说,简单易行,在日常饮食中就能预防或治疗一些疾病。除此之外,从当时敦煌节日风俗中也能看出食疗在当时民众生活中的影子。例如P.2721《杂抄》所记:“六月六日何谓?其日造酱、曲,及收枸子,大良。此月三伏日何谓?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疢。”[21]171
4.禁咒疗法
敦煌医药文献里保存了一些含有咒禁疗法的药方,是了解唐五代时期民间医疗的重要资料。从敦煌文献来看,唐五代时期,咒禁术一般用于治疗当时医学无能为力的妇女难产、鬼疰等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咒禁和符印疗法的‘适用疾病’要么是死亡率高,要么是难以治愈,要么是其病因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导致,要么是带有一定的传染性。在碰到这类疾病的时候,古人就会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咒禁、符印疗法。”[1]116其中治疗妇女难产的资料较多,不再赘述,治疗心理精神方面疾病的药方在传世资料中较为少见,这里略为列举讨论。
P.3144《不知名医方》第七种“疗鬼疰方”记载:
上先以墨笔围所痛处,于圈内书作:“腊()蚀鬼疰,人不知,急急如律令”,若未全差,洗却更书,永差。[15]238
P.2622《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仙人治病方”:
取好朱砂、麝香水研之,书头上作九天字□白车。腹上作白马字,两手作丸金,两脚作丸土字□此法,体上书此字,病除之。[15]328
唐代时,咒禁术在医疗活动中,不管是从从业者的规模,还是从咒禁术适用的疾病范围来说,都有缩小,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下降[24]61。从敦煌文献来看,禁咒术所占比例也不大,这和学者们对唐代整个医疗环境的研究结果相符。“可以这样说,巫术疗法虽继续在唐代社会医疗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其阵地已经逐渐萎缩。医巫必然要分离,这是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规律,但是就唐代而言,医巫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因为正如前文所论述,民间草泽医人基本还是‘医巫不分’,主流医学家们的思想中,虽然有了很多对迷信的排斥,但也有一些咒禁符印疗法的残留。在面对棘手疾病时,咒禁符印疗法依然被经常使用。”[24]67可见咒禁术在唐五代时期敦煌民众的医疗史上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民间自我医疗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民众面对疾病时的重要医疗选择。除此之外,佛教、道教中的宗教医疗也是当时民众面对疾病,尤其是医药无法治疗的疾病的选择。敦煌佛教《患文》、道教《病差文》《发病书》都有对宗教斋会治病仪式的记载,是当时社会重要的医疗资源补充。
结 语
医疗从来不是单纯的医药问题,它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医疗机构及医人群体来说,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有完整多元的医疗体系,官方、佛教、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医疗是敦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医学水平来说,敦煌文献中的医药抄本即可体现出敦煌医学的较高程度,中医有五脏论、内难经、伤寒论、灸法、药方等,吐蕃医学则有火灸法等具有藏族特色的药方及医疗术,另外还有丰富的域外医学作为补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价格便宜、简单易行的单药方、艾灸、禁咒、食疗等医疗方式是他们面对疾病的主要医疗选择。民间自我医疗是当时社会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袁仁智、潘文主编:《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陈于柱:《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殊方医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明:《敦煌的医疗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田永衍、秦文平、梁永林:《敦煌出土医学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甘肃中医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圆空:《〈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郑炳林、高伟:《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②图版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66页。录文参照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③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录文参照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第225页。④从敦煌文献来看,唐宋之际的敦煌不仅有八月一日“点天灸”的习俗,还有在八月一日洗浴、去垢的节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