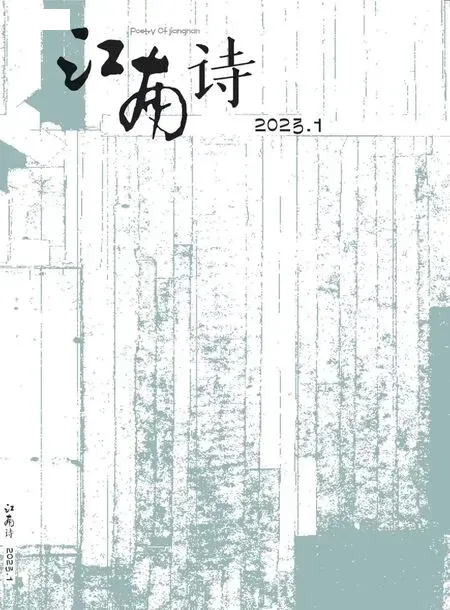醉与醒
◎冉 冉
一
在我有限的醉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20多年前那一次。当时我和老朱,正沉迷拳术的车队司机李,还有他在林场工作的朋友陈,四人一起从乌江口的学校出发,循峡谷野路逆江而上,无目的地乱走了大半天。时近黄昏,暮霭渐渐弥满山野河谷,我们困乏又饥饿,四处却不见人烟。随着夜幕严严实实合围,打头的李看中了一处岩凹:这儿不错,岩凹可以遮挡风雨,小块草地可以生火。我们驻足捡来干柴点燃篝火,取出背袋里的面包水果红肠和两瓶“百花露”(色近蜂蜜的当地果酒,后劲儿相当大)——当几个人吃饱喝足大声“吼”歌时,地下摆放的食物狼藉,酒瓶已空。同伴的满面酡红让我也察觉到自己的醉——是那种脸发烫心跳加速,肢体自由唇舌欢悦的醺然。透过劈啪炸裂的柴火,我听到寡言老陈在喋喋不休——大家唱熟悉的老歌,跳自创的舞,精瘦的李还即兴演绎了一套“醉拳”。在酒意和夜色掩护下,身体心意都冲破拘限极尽张扬,连趔趄踉跄的脚步都那么自然合拍。
篝火燃烧了整宿,有人打盹儿有人继续说笑,却并没有感觉多困。我面向岩壁站了会儿桩,然后一直盘腿静坐。待明火转为炭火,手脸耳轮虽然依旧温热,知觉却渐渐清明。黛蓝的穹顶下,河谷醉卧着,林中隐隐传出夜鸟低弱的呢喃。松香草香,游弋的音声,野樱桃的酸甜……手在暗中兴奋地捕捉动弹。有什么东西在贴近我?天空星云群山流水飞鸟鸣虫,都与身体交汇难分彼此。刹那间似乎灵魂出窍,而意识却又能清晰区分,那轻盈的飞升不是梦,而是醉。
多么欢悦,多么曲尽其致的曼妙的醉!
适度的醉,是身心解绑顾忌打破,是意念的天马行空,感官的全然敞开;是新鲜地见,无碍地听,纯粹地闻。此时此刻,你会重返少年的天真自在与率性痴狂。
多年后,当我读到“感性部分陌生化是唤醒人们重新经历过的感觉,感性全息陌生化是引领人们经历从未经历过的感觉。感性全息陌生化是诗人怀着原始感受之纯净心境,不以别人和自己第二次见到的目光打量事物,而是以第一次见到的目光打量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生活,唯有这样,诗人才有可能进入人与世界极其本关系的本真状态,抵达汩汩的生命本源,从而获得比高峰体验更浓重的原始体验”(戴达奎《现代诗欣赏与创作》)时,不禁会心一笑。要获得那样的婴童之眼赤子之心,成为饮者大约是最便捷的方式之一吧?无待多言,古今中外有太多诗人文士与酒有不解之缘——微醺、浅醉或大醉后,有人率真如孩童,有人癫狂如赤子,那是面具去除后肆无忌惮的自由状态,原初的生命力得以自然喷发,隐秘的意志无羁地展露,此际或会进入给“存在”“万物”“第一次命名”的通灵状态。只不过,作为催化点燃诗人创造力的“酒”,可以是高粱麦黍酿出的琼浆玉液,也可以是飞蛾投火的炽热爱情;可以是让天地动容的至善至美,也可以是叩问幽玄的执拗探询……还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源于生命自身的悲切伤痛或欣喜。
二
在《黑夜史》的后记里,博尔赫斯写道:“一册诗歌不外乎是一系列魔法的练习。那谦逊的魔法用他谦逊的媒介来极尽所能。”在施法过程中,老年的博尔赫斯常常让人感觉沮丧又得意,智性又野道,煞有介事又满不在乎。阅读他的诗,就像在倾听一个盲眼智者的吟哦,或是看一个顽皮魔术师的演出。让人着迷的,是诗中那些着魔中蛊的名词——
沿着他们漫长的世代/人类筑起了黑夜。/起初它是盲目不可见的睡梦/和将赤脚划破的荆棘/还有狼的恐怖。/我们永难知晓是谁打造了那个词/来指称那道黑暗的间隙/是它分割了两种幽冥之光;/我们永难知晓它在哪个世纪成了/星辰空间的秘语。/还有人造出了神话。/它被指为静默的帕西之母/他们编织命运/而人们向其敬献黑羊/和预示它结束的雄鸡。/伽勒底人交给他十二宫;/门廊交给他无限数的世界。/拉丁语的六音步诗将它塑造/还有帕斯卡尔的恐惧。/露易斯·德·莱翁在其中看到了/他颤抖的灵魂的故土。/如今我们感觉到它无穷无尽/如一瓶陈年的酒/而无人能够将他凝望而不晕眩/而时间已将它满载了永恒。//再想想它或许并不存在/若没有那对脆弱的工具,眼睛。(《黑夜史》陈东飚译)
世代、人类、黑夜、睡梦、赤脚、荆棘、幽冥之光、星辰空间、秘语、神话、黑羊、命运、恐惧、颤抖的灵魂、陈年的酒、晕眩、永恒、眼睛……数十个经诗人点化的名词,织入我们从不曾看见却又理所当然的神秘网络,构成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能指世界——连接它们的动词和介词都是陌生而恰适的。疑惑与神奇之处在于,在施法的当儿,那些道具(名词)是怎样一一来到他面前的?发现召唤它们的是直觉还是智性?那最初的盲不可见的梦,将赤脚划得鲜血淋漓的荆棘,穷追不舍的恶狼,尤其是深不可测的黑夜……都是被加诸人类的永无止境的惩罚?其后的词既跟眼(幽冥之光、黑羊、雄鸡、十二宫)耳(秘语、六音步诗)鼻舌(陈年的酒)有关,也跟智性相连(命运、时间、永恒等)。在对词语的驱遣上,博氏看似唾手可得,任性不羁,同时又分外警醒,始终保持着疑虑玄思。这种介于醉和醒之间的平衡状态,或许就是智者叠加魔术师的状态。
三
说到醒,记起来的还有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布莱希特。
本雅明认定“布莱希特是本世纪最自如的诗人”。乔治·斯坦纳更具体地表述为:“对他来说诗歌几乎是一种日常探访和呼吸。”这个生活在现代主义盛行的20世纪里的异类,以简单直白客观的语言,“对二十世纪人类状况的经验做出生动的反映,它们追踪我们当下生活的样式,描绘一个世界的画面,而这个世界又是我们在不脱离现实的情况下能够分享的”(卡尔·韦尔费尔语)。有论者因此将他的写作归为“工具式实用式的抒情古典主义诗歌”。
一个孤独的清醒者,用一种颠覆性的平民视角看待事物,“拒绝充当圣人,远见者,博学家,预言家”,如同艾略特论及的吉卜林,“智慧具有压倒灵感的优越性”,更关注周围的世界而非自己的悲欢,更关注自己与他人感觉的相似性而非独特性。布莱希特置身于作为主流模式的现代诗之外,远离流行的艰深歧义、私密性、自我内心独白,“几乎是当今仍在写作的唯一的社会诗人,唯一其形式与题材一致的社会诗人,唯一名符其实的政治诗人”(H.R.海斯语)。
也有人批评布莱希特:当他认同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含混观点,将理性推到极端时,实际上就是认同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的原理,以历史必然论解释自由的概念,并对不惜一切代价实践历史目标的力量献上溢美之词。在宗教意识衰落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取代经验常识的超越性历史哲学,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正因为用辩证法否定常识,才使得他的诗歌产生出某种奇特的双重意涵,从而丰富了作品的面向。
四
由醉与醒这两个多少显得简陋的字眼儿,想到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日神+酒神比喻理性与意志的关系,认为希腊悲剧艺术是阿波罗形象和狄俄尼索斯精神结合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这两种力量相互冲突制约的结合物——
“日神让人迷恋于生命的梦幻而忘记人生的痛苦;而酒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
尼采认知的酒神是最原始最本源的艺术本体,对希腊悲剧的重要性远大于日神,它既能使人从人生痛苦中获得悲剧性的陶醉惬意,同时又携带着毁灭性冲动,因而需要日神帮助承担起拯救与调和的职责。问题在于理性主义世界观兴起后,狄奥尼索斯的生命意志被阿波罗的理性原理持续侵蚀,极大阻碍了艺术、生命和社会的发展,尼采因此呼吁恢复希腊悲剧中的狄奥尼索斯准则,重新尊崇酒神精神。
有论者将唐诗里的“醉与醒”类比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放浪形骸洒脱不羁的“诗仙”李白,沉郁顿挫穷绝工巧的“诗圣”杜甫,或可视作酒神与日神类型两类诗人的代表。
以“酒神—日神精神”观照,史蒂文斯所创“星期天上午”“最高虚构”及“田纳西的坛子”等经典意象,其蕴含的希腊式肯定生命的精神内核与沉醉—迷幻之诗歌结构,对生命意义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或有借希腊悲剧艺术“神启”的美与力,拯救现代人类“精神荒原”的用意。
三岛由纪夫读森鸥外《寒山拾得》和泉镜花《日本桥》,得知森鸥外以“明晰”为作文的第一秘诀,不能忍受任何暧昧不明,任何对语言想象的滥用。泉镜花则更多诉诸身体感官,用语色彩绚烂,追求“整体的知觉”而非单一事物的明确(名为小说却意不在人物性格或事件,而是作者自己的美感告白,其文体特色全系于此)——三岛将其描述为“理性的酩酊”。接下来,三岛说森鸥外毕生没写过大长篇,不免让人疑心像他那样绝顶理智明晰又极度节约的文体,或许很难写出洋洋洒洒的大部头来(笔者不由联想到也是毕生没有一部长篇问世的鲁迅先生)。相较之下,泉镜花则太适合写长篇了——他的语言好似一道洒满花瓣的脉脉流水,色彩华丽地前行,作者带点微醺的陶醉跟读者一样随水漂流。他的故事没有核心主题和理智牵绊,因此得以延展出森罗万象绵延不断的物语世界。至此,三岛所论的日神与酒神式作家/文体的分野也就非常清楚了。
从东方到西方,由酒神精神主导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队列巨星辈出声威赫赫,阵容似乎更为强盛,然而真正的大师巨匠其实都成就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双边角力。对创作者而言,明晰的理性秩序与原始生命力的冲动缺一不可,假象的快乐和太一的快乐都是面对人生痛苦选取的策略而已。至于这共居某一肉身内的两种力量谁占上风,可能更多取决于冥冥中的无形之手,生命本尊大抵是无能为力的。不过话说回来,造物之秘,谁又能真的知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