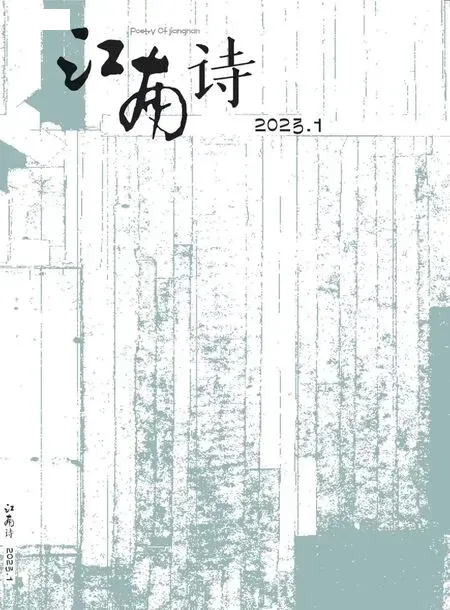马林·索雷斯库诗选
◎[罗马尼亚]马林·索雷斯库 高兴/译
马林·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1936—1996),罗马尼亚当代代表性诗人。主要诗集有《时钟之死》《堂吉诃德的青年时代》(《咳嗽》《云》《万能的灵魂》等。诗歌外,还写剧本、小说、评论和随笔。
索雷斯库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罗马尼亚诗坛的。为了清算教条主义,他抛出了一部讽刺摹拟诗集《孤独的诗人》,专门嘲讽艺术中的因循守旧。他的不同的声音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艺术个性渐渐显露出来。他的写法绝对有悖于传统,因此评论界称他的诗是“反诗”。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个深刻的哲理。他自己也认为“诗歌的功能首先在于认识。诗必须与哲学联姻。诗人倘若不是思想家,那就一无是处”。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一位罗马尼亚评论家说:“他什么都写,只是写法与众不同。”
自由的形式,朴素的语言,看似极为简单和轻盈的叙述,甚至有点不拘一格,然而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出一个象征,说出一个道理。表面上的通俗简单轻盈时常隐藏着对重大主题的严峻思考;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时常包含着内心的种种微妙情感。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诗的话题,因为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高兴)
思想的边缘
只听见一阵噪音噗嗤作响,
那些陈旧的念头
游弋着
飘向思想的边缘。
天哪,它们从那里
一个一个朝外跳下,
犹如夏末,一根一根神经
从叶子的边缘坠落。
只听见一具灰烬肉身
从我的灵魂爬下,
大片大片的光总在流泻,
在天空的道道边缘上。
迁 移
别再徒劳地搜索山,
如果山的面前有朵云,
最好还是在云中
将它找寻。
而如果云的下端
停栖着一只蝴蝶,
继续挖掘云将毫无意义。
在这只昆虫的爪子中
搜寻山吧。
当然,你们只有片刻的功夫,
因为蝴蝶的影子,
连同整座山,
不可能不暴露在下面。
到那里去寻找山吧。
你们要快快地挖掘,
不然,山会迁移到第一片叶子上。
就这样,在跳跃中,通过路上遇见的一切,
它会渐行渐远。
门底下
今天这一日子
一如往常,从门底下
塞给了我。
我将眼镜架上鼻梁,
开始
读它。
没有什么特别的。
据说中午我会有点忧伤,
原因并没有明确说明,
我将继续爱着
昨日我留在其中的光。
第一版报道了我同水,
同群山,同空气的条约,
以及它们那企图进入我血液
根据需求分析,我们选了光网络来建设南昌大学公寓网,实现有线无线一体化,南昌大学公寓光网总体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和头脑的荒唐要求。
接着都是些一般性消息,
有关我的劳动力,
有关我的生存之道,
有关我的良好情绪
(但对于肝脏状况
却只字未提)。
我的这份生活
也不知是在哪里出版的,
上面充满了
不可接受的错误。
蜘蛛来到
蜘蛛携带着壁毯
来到我面前,
请求我为它印上
一个人的
形状。
因为——它解释道——我的形象
同被遗忘在那个角落的群山,
同它罩住的云朵和蝴蝶
完美匹配,
可以赋予普遍的死亡
以多样性。
我勉强露出笑容,
但身体总在摇晃,
弄断了好几根蛛丝,
因为我过着动荡的生活。
以我为榜样,
群山充满了植物,
云朵轰鸣,
蝴蝶拆掉了羽翼。
蛇看见一支笛子
蛇在每棵树上
都看见一支笛子,
并演奏着孔洞。
犹如皮提亚的嘴巴,
这些笛孔
为倾听者
发布一道道预言!
看见一条蛇在徒然地演奏时,
你们该想到,某个地方
有棵树。
我也充满了孔洞,
可以让天空舞蹈。
地 图
首先,请让我用教鞭
将三处水域指给你们看,
它们在我的骨头
和身体组织中清晰可见:
水用蓝色描绘。
然后,两只眼睛,
我的大海之星。
额头,
最干燥的部分,
通过地表的褶皱。
每天都处于
持续的形成中。
那座火焰岛是心脏,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已有人居住。
假如我看见一条路,
我想那里肯定有
我的双腿,
不然,那条路就毫无意义。
假如我看见大海,
我想那里肯定有
我的灵魂,否则,它的大理石
就不会掀起波浪。
我的身上
当然还存在
其他白点,
一如我明天的思想
和际遇。
用感觉
那五大洲,
我每天都在描写两种运动:
绕着太阳的旋转运动
以及绕着死亡的
革命运动。
这大概就是我的地图,
它还将在你们面前
展开一段时间。
休整学习
瞧,我一步也不想多走,
只愿停留于此,一动不动,
紧挨着其他松树,
正好有块松树之地空着。
我也开始
长出地衣和苔藓,
蚂蚁们朝我走来,
请我指出北方的位置,
可我毫无兴致,
我曾到过那里,
为何还要再让它们徒劳地
上路。
长路走过后,
你最好在某地安定下来,
一生过完后,
你最好不再言语。
我是松树,
我已开始
用我全部的松针
刺死风中的
一声叹息。
蛋
唯有在浴室
你还能呼吸,
泡在肥皂云雾中的人
不禁让我想起
那座归还的天堂。
将一部分重量
转让给水,
我遇见更加深沉的梦,
仿佛冬季,白雪之上,
我朝着地下的圣者俯身弯腰。
我已忘记所有的轮子和衣裳,
水又一次充盈我的生命,
仿佛在特别特别古老的年代。
而为了更多的放松,
瞧,我甚至可以将血管切割,
甚至可以用大指头,
为这原始的水,就像为蛋那样,
涂上彩绘。
字母表
丢失第一个字母时,
他没太注意。
他继续说话,
小心翼翼地避开
含有那个字母的
词。
接着,他又丢失了一个,
好像是字母A.
太阳,月亮
只好死记硬背。
然后,又丢失了一个,
幸福,爱情
开始不再理解他。
最后的字母
插在一个音节中,
犹如一颗疲惫的牙齿。
现在,他能听见,看见,
却不再掌握生活的词语,
绝大部分组成生活的词语
他都已丢失。
用指尖
天际线是个亲切的圆圈,
所有的存在物都在其中用指尖
相互触摸。
房子和道路
伸出手臂,
用指尖相互触摸。
每样存在物都必须
留在先驱们
用粉笔
标记好的地方。
瞧,我跳出圆圈,
忽然,光从我的身体,
就像从施洗者约翰
被截断的身躯射出。
演 出
左边——一个老头,
右边——一个老太。
老头的左边——一个女孩。
女孩的左边——一个男孩。
所有人左边和右边都挨着其他人,
形形式式,听其自然。
而在所有人面前——舞台,
唯一的舞台,
我们正在观看一场话剧。
剧目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换过,
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
舞台上有点新鲜玩意,
时不时地变换
大厅里的座位。
老头往右边
挪了一个座位
把胡须落在了
我的膝盖上,
女孩坐到了男孩的座位上,
满脸通红地看着
玩偶的什么东西。
所有人一个一个轮流
变换着座位,
唯独我不愿放弃
自己的座位。
我的缺乏通融实在令人恼怒,
观众们确实怒气冲冲,
推搡着我,
但我十分固执,
纹丝不动地坐在原位。
直至所有观众,
纷纷贪求我的视角,
坐在我的头顶,一个
叠在另一个之上,压迫着我。
永动机
在人们的理想
和理想的实现之间
总是存在着
一种水平差,
甚至大于
最高的瀑布。
可以合理地利用
这种希望落差
在它上面建造点什么
比如,一座
水力发电站。
即便如此,获得的能量
仅仅够我们
点几根烟,
那也不错,因为,
抽着烟,我们便可以认真考虑
一些更加了不起的理想。
安 逸
太阳将我打击得太重,
我将你放在窗口,
就像放在一张蓝色的纸上。
思想将我打击得太重,
我将你放在前额,
就像放在奇迹创造者
圣母的圣象上。
死亡将我打击得太重,
我将你放在心头,
就像放在一扇
爱情屏风上。
此刻,你一离去,
太阳,思想
和死亡,会以十倍的愤怒
把我争夺。
就像七座城池
争夺荷马那样。
单行线
一天, 我看到自己
晃晃悠悠地从几只瓶子里走出,
顶着相当糟糕的名声,
也许,那名声,我并不在乎,
因为我还吹着一支助兴小曲,
并将新意识放到了眉毛上。
我迅疾坠落在事物旁,
就像一道瀑布,
宇宙中的一切都得坠落,
几百万年来一直在坠落,
见了鬼似的坠落,
而我竟然能在万有引力之外,
在书籍和思想之间,
自以为是地待了这么久,
每每想到这,我就禁不住要笑。
好 像……
梦的形成令我着魔,
有时,我仿佛觉得
听见它们在作业,同我相连,
但对此我还不太确信。
假如我久久凝望一棵树,
我仿佛听见叶子中一个声音:
“好像他曾是一棵树。”
假如我看见地图上的北极,有一个声音:
“好像他曾是北极。”
不管怎样,你得朝这些近乎偶然的
事物使劲吹吹气,
就像一颗在自我消耗中
令一束束光生锈的星星。
房子,水,地点,女人
你都得如此清楚,
以至于第二眼看去,
房子变成女人,
再一次看去,变成大火。
有一段时间,
我直接对梦闭上眼,
就像一个孩子用帽子
一下子变出一群群蝴蝶。
现在,我整宿醒着,
坐在越来越大的黑眼圈中,
琢磨着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书 房
天亮了,当然,
听,公鸡在歌唱,在书房——
我那垂直的庄园。
农人,每天早晨
都得给所有家禽喂食,
我也会去给我的书籍
投些大粒的咖啡。
我专注地望着它们,
一连数上几遍;
一天夜里,我梦见
它们全都逃跑了。
唯有书脊还待在原处
丝毫不差
整整一年,我都没有发现。
我轻轻摩挲着书名,
肚子里奇怪地涌起一股股胃液,
就仿佛将去参加一场宴会。
比如说今天吧,
我对暴食的荷马就特有胃口。
我读着,读着,
目光投向窗外时,
我惊奇地注意到,
屋墙边,那些真正的母鸡
不时地也感到了
吃点蛋壳的需要。
在梦面前
夜晚,我坐在我的梦面前,
就像坐在一块屏幕面前。
我知道它们正盼着我早点入睡,
好开始致敬播放,
庆祝我又度过了一天。
节目由塞壬合唱队拉开帷幕
(打从为尤利西斯歌唱之后,声音依然沙哑),
她们试图要说服我
转向伊斯兰教。
然后放映了几个拍摄好的镜头,
从我的所思所想,
从我的未竟之事,
从我同太阳即将的合作。
接着展现
最伟大的事实,
最美的邮票,
最美的墙上绿马,
最美的心灵——
但你能记住所有这些吗?
我也有一个小型乐队,
专门用来歌唱我的事迹,
用声乐和器乐:
小提琴,扬琴,门把手,鱼鳞甲,蛇鳞甲,
鳄鱼鳞甲。
活水,死水
呷了口这水后
我一下子变得独立自主,
就像东方的教堂,
塔楼林立,乳白色梦一般。
我握着水瓶,心醉神迷,
眼中全是中魔的水滴,
每滴水都清晰地映照出我的面容,
正被神奇的痒振动。
多好啊,我找到了活水,
所有传说都在寻找的活水。
那是死水——一只云雀对我说——
池塘里舀来的死水。
那么,它又是怎么发力的?
我反问那只自作聪明的云雀。
——同样的水,在胸口突突跳动,
对于一些人是死水,对于另一些人却是活水
树
雨中,我靠在一棵树上。
它同大地有着联结。
树皮下,我感受到长满老茧的手掌,
宛若装着天空的词语,在沙沙作响。
愤怒的雷声不时地传来,
乌云在暴雨中复仇。
一道迷途的闪电闯来,
我们俩立马用手将它折断。
胆怯袭上心头,我逃向田野,
雨滴打弯了我的腰。
它承受着垂直的风险,
随时都有可能点起大火。
这奔跑的孤独……
这插入泥土的孤独……
我哭泣着返回,将它抱在怀里。
沉重的暴雨陪伴着我们。
虚 无
我不再打磨虚无
用我那易逝的生命。
我难道还要一大早就起床
用花朵为它添加光泽?
还是让它打磨我吧。
在永不消逝的死亡中,
就让它用清冽的泉水
天天为我的花朵念咒施魔。
铃 铛
每晚,光一熄灭,
我就会听见一只铃铛,
梦里我追寻着它
不是下雨,就是飘雪……
我走啊走……那只铃铛
在世界尽头响起。
在世界尽头我就像小牛犊
望着妈妈的新门。
一颗星穿过天空,万千火花中
一朵火花点亮阴沉。
它叮当作响,只是
在听见我的梦的时刻。
像条章鱼
希望粘着我,像条章鱼
像只吸盘。
强健的臂膀紧抱着我,
退潮的浪涛挤压着我,
那些浪涛赤足返回月球。
血液的潮汛,地上的潮汛。
大海一动不动。
在怪异的引力下,唯有你
翻腾着,涌向白雪覆盖的山脊。
水 滴
我望着水滴怎样坠落,
均衡,间隔适度,
平静,从不逾越分寸,
四周戴着一圈光晕。
这可是对我的惩罚
——多么严酷、难以置信的恨!——
每一滴
我都在等着一触即发。
但当我死死盯住的目光
在紧张中溢满泪水时,
我被恐怖石化,
不知不觉演化成钟乳石。
而天花板上的水滴
还在徒然地坠落。
歌
树如何站着死去?
鸟如何飞着坠落?
飞翔中,鸟在问:
树如何站着死去?
眼盯着死去的鸟纷纷
坠落在摇曳的枝柯间
那些渴望飞翔的树
棵棵决意要站着死去。
你也是旅人,
陷入一只梦见花儿的窠臼,
你一半消失在飞翔中
另一半同根一道浸入盐里。
带熨斗的装置
带熨斗的装置
是诗。韵脚,
熨平空白,按压着推进
犯下近乎完美的罪行:
凭借梦的模糊边界
让你混入清晰的光线中。
熨斗,沿着烙印游走,
在深渊的边缘建立秩序。
爱情,用一颗颗星星
将我誊写在稠密的画布上,
死神,那伟大的熨衣女工
正提留着熨斗,把我找寻。
宽 恕
我对这片天空犯下了罪行,
因为深的山谷和黑的回音:
我用眼睛在它身上砸开了
一个个窟窿,请你们大家宽恕。
此刻,天空正在崩塌,
力图叫停它,纯属徒劳。
在星星的注视下,你安上
水槽,为了火焰之泪。
天空流向大地,整个大地
变成一座穹顶,今天,有人
正从其他天空望着
我们的眼,那一只只反叛的眼。
睡 梦
献给母亲
我漂流在一条河里,仿佛双手已被
绑紧,仿佛全身已被一股温柔的
力量抱住,仿佛在天上寻找一个
面包的圆润,在岸边同一只蝾螈结亲。
我在眼睑下洗涤着一粒粒沙子
整个贝壳在一瞬间幻变成了她
我如眼泪般滑落在一张脸上,
那张脸鼓励流泪和哭泣。
在河里面朝天空哭泣,你也是
一条河,河床在不断地运动……
——松开我的手吧,这样,我便能
游泳,在这汇入大海的哭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