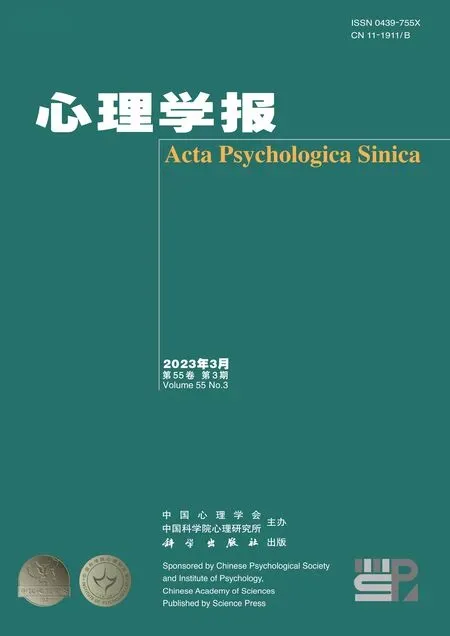从疫情控制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
杨中芳
·“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
“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征稿(2019年底)截止后,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将全世界置于历史危机之中, 这便有了杨中芳提出一条探研中国人“我”的新构想——中庸行动我。以“我”为纲, 王辉等人讲述的是:辩证思維的我在企业领导者行为中的表现及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张建新、张妙清等人讲述的是:中国人“外圆内方”的我, 其方圆间的变化是西方人复现不出来的; 王俊秀分析公平感在时间上的变化, 讲述了中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 纪丽君等人用多年研究的众多实验讲述:中国人宽广的时间知觉, 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的自我连续性和社会变化观, 从而帮助中国人有效应对各种灾难和挑战; 李纾等人用疫情中收集的18个国家的数据讲述:历史危机时善于变通(权变的跨期选择)的特长抑或成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竞争优势。
组成本专栏的6篇文章用心理“科学共通语言”, 不约而同地尝试讲一个中国人“我之为我, 我之变化”的故事, 冀学报读者能从中收获一二, 引发更多后续的研究兴趣。
专栏特邀编委:张侃、李纾、刘力、张建新、王俊秀、王辉、许燕、蔡华俭、陈欣银
从疫情控制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
杨中芳
(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本文撰写的目的是, 藉助分析COVID-19疫情控制的应急心理机制, 提出一个思考中国人“自我”的新架构, 希望未来它能成为研究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新进路。沿用中国传统流传下来、但却一直被沿用至今的中庸思维, 以及其内涵的“阴阳思维”及“全息思维”作为立论基础, 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它是指个体在选择及执行解决问题之具体行动方案时, 依现实“情境需求”, 灵活地“协调”出一个最恰当的“行动我”, 以配合集体战疫的需要及功效。“中庸行动我”这一构念的提出, 不仅只是为了解释战疫的成效, 更重要的是它欲反映出中国人思维“灵活性”的根源, 从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自我”的另类进路, 不再只是以跨文化研究进路所关注的“本质自我”为主要立论基础, 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现有的知识内涵。
我, 行动我, 中庸行动我, 中庸实践思维, 阴阳思维, 全息思维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1)一张试卷考全球
自从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由于此新冠病毒散布迅速, 全球各地几乎没有意外地都同时被波及, 也几乎没有容许太多“谁向谁”学习的时间。各个国家大都在以“盲人摸象”的方式, 依自身所能提供的资源在处理危机。同时, 全球媒体都夜以继日地将各地发生的情况向全世界放送。各类数据的收集者也以又快又多的方式传送他们的资料, 令这个正在持续的灾难, 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超大科学实验场。各领域的科学家们更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及数据库, 作各种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试图理解应对疫情的关键因素。文化心理学家当然也不例外, Gelfand等(2021)的研究是最新的一例。
(2)文化成为关注点
当前(2021年)有些国家, 包括中国, 疫情控制得比较早、比较快、也比较有成效; 有些国家正在康复中; 而另有些国家则在第二、第三波、甚至第四波的疫情中挣扎。人们不禁要问: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奉劝老百姓自律、筛检、追踪、围堵、确诊/死亡清零、施打疫苗、防范复发、最终恢复正常”这一程序在处理疫情。为什么有的国家或文化可以快速地动员当地老百姓、在没有受到太多阻力的情况下, 推进这一程序; 而另一些国家则举步维艰、屡屡受阻、拖泥带水、乱成一团, 甚至一直在原地踏步?
最为一般人广泛接受的答案当然是:各国国情不同。这里, 国情基本是指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许多国外媒体及学者认为, 中国所以能迅速控制灾情及恢复社会正常运转, 在于国家体制因素, 政府可以一声令下, 人民全面服从, 从而得以快速实施对策、完成任务、解决问题[1]Gelfand等(2020)即是用“文化松紧度”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追踪文化心理学研究者, 多年来采用跨文化范式所提出的解释架构, 基本上大都与这一论述吻合, 只不过他们是用像“集体主义”的概念为总称, 所提出的一组相互紧扣的心理特性(认知方式、价值观、自我/人格特征等), 作为解释文化间行为差异的基础。
(3)新的研究思路
本文作者反问:中国真的因为民众全面服从, 而能快速控制疫情吗?作者否定这个答案的做法是, 先拆开上述的“文化特性组合”, 不把它们放在“集体主义”这个篮子里一起看, 从而缓解了许多绑在一起的“刻板印象”。再把中国人放回到自身历史/社会/文化的脉络中, 去审视个体战疫行动的心路历程, 从中探寻战疫成效从何而来。
沿用一条有别于主流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中庸实践思维”进路(杨中芳, 2022b), 本文作者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 作为探讨中国人展现应急“灵活性”的线索, 来解释为什么在疫情危急的情境下, 老百姓能迅速地、自动自发地、甚至发挥想象力地, 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2]最新见到的一个自述报告反映了这一现象:“我在的学校据说做了8次核酸检测。东北秋天很冷, 几万师生, 大家连夜排队做检测, 很不容易。听学生说, 开始没有组织经验, 可是第二次以后, 按照各个学院班级, 首尾相衔, 师生各入检测帐篷, 井井有序, 提高了效率。”。
本文将分4个部分作论述。第一部分先简述为什么需要开辟一条本土进路来解释战疫行动背后的心理机制; 第二部分, 作者通过对三个传统概念的诠释——“阴阳思维”、“全息思维”及“我观”, 说明它们各自可能与中国人战疫过程中所展现的应急灵活性有关。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 作者在第三部分, 提出了“中庸行动我”的构想。在“人/境一元论”的基础上, 提出“格局我”、“差序我”、“运势我”及“阴阳我”四个子构念, 来对比主流进路提出的“私我”、“公我”及“团体我”的自我构念。然后, 沿用“中庸实践思维”中“时中”的场依性构念, 以及“用中”的协调性构念, 提出“中庸行动我”是由具体情境所唤启的各种“我”的协调结果, 从而展现了应对不同时间、情境及关系的行动灵活性、自主性及创造力。
基于这一“中庸行动我”的思考架构, 作者在本文最后, 综述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并建议一些未来研究中国人“自我”的方向及重点。
1.2 走出跨文化研究进路
在媒体广泛的疫情报导下, 人们亲眼目睹一些欧美国家, 特别是美国[3]主要是因为有关该国的报导比较多及全面。的普通百姓坚持不肯戴口罩、不禁足、不打疫苗, 认为这些都是妨害了个人的自由及人权的场面。让即使不懂科学研究的人, 都深深感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可以如此巨大, 甚至影响了人们性命攸关的抉择。人们更加认为, 被文化烙上印记的个体“价值观”是造成本次战疫成功与否的主要原因。
相反, 像中国这些疫情控制的速度及效率比较高的国家, 则被认为是因为强调“集体大于个人”, 个体因而被这一文化烙上印记, 而具有以下心理及行为特征:听从明确的指示, 没有自己的主见; 思想不开放, 不接受改变; 也因此没有灵活性。
主流跨文化心理学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是缔造这一“刻板印象”的始作俑者。由Triandis (1987)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 经过Hofstede (1980; 2001)加以延展, 找出5个区别文化的价值维度, 并得出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亚洲国家被试, 显现了高权力距离、对不确定性容忍度低, 及自我约束力强的一系列“价值组合”[4]对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研究为代表的跨文化思考进路, 杨中芳(2001a)曾撰文详细评述。。而这一组合后来又被发现与个体的“认知闭合需求”这一人格特征有关(Webster & Kruglanski, 1994), 从而令“价值组合”又填加了缺乏开放性的元素。
之后, Schwartz等人(Schwartz & Sagiv, 1995; Schwartz et al., 2012)用19个人类基本的“普世价值”, 分为五大群组维度, 来分类各个文化[5]五个群组为:(1) 保守价值−安全、顺从及传统; (2) 自我超越−仁慈、利他及普世(平等)主义; (3) “利己” (self-enhancement)−成就、权利及适当享乐; (4) 自主−个人自由及创新; (5) 容纳/接受改变 (openness to change)−寻求刺激(热爱新鲜、勇于冒险)及适度享乐。。其中有两个群组——“自主”及“容纳改变”, 充分反映了其内容的“西方价值主义”。“自主”, 并不是指个体“主动自愿”地去做事, 而是指热爱自由及“特立独行”, 只作自己爱做的事。这里内隐的逻辑似乎是:只有做“反社会”的行为才算是自主。同样地, “容纳改变”也不是指心胸开放, 愿意接受并参与改变, 而是指喜欢寻求新鲜刺激及做冒险的事。
当用这5个“普世价值”维度来划分许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时, 一般都预测, 在“保守主义”指标上得分比较高; “自主”及“接纳改变”指标上得分比较低。但是, 韦庆旺(2019)在他的研究中, 加入了“中庸”价值选项后, 将得分与上述5个价值维度相印证, 发现它在“自我超越”得分比较高[6]不少中国哲学家, 如冯友兰(1947)等, 认为自我超越是中国人一生的追求。; 但是在“保守主义”价值及“自主”这两个看似在两个极端的维度上, 得分都在中间, 表明中庸价值“既不保守、也不是没有自主性”。
这一结果不仅打破了过去一向对“集体主义”国家民众的刻板印象——他们是持保守主义及没有自主、不开放、不接纳改变的。同时也展示, 反映传统中庸思维的价值观, 并不能全靠跨文化以“普世”概念作为进行比较的基础, 也不能全以这些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作为判断的依据。可能还要从对自身文化作整体的、系统的探研, 才能避免“以偏盖全”之弊。这也是朱利安(2018)拒绝用“差异”, 而用“间距”来理解不同文化思维特点的原因。他认为文化之间找到的不同, 不只是量的差异, 还要放回到它们自己传统的思维体系中去理解。
总体而言, 用跨文化进路来研究各文化的心理与行为差异, 有其一定认识上的优势。用二分架构做实证研究, 比较容易找到一些宏观概括性的结果及解释。然而, 这一优势也正是其劣势, 它的局限性是结论过于笼统、缺乏深度。跨文化研究找出的文化特点, 不应是研究自身文化及行为的终点, 而是起点[7]详见杨中芳(2022b)论及主流进路与本土进路的差异。。
本文作者认为, 要对自己文化民众作深入探研时, 需要采用一个有别于“跨文化”的思考进路, 以增加研究者的想象空间, 从而令研究更为全面、多元。多年来, 她一直主张应启用一条“中庸思维进路”来思考问题(杨中芳, 2008c; 2022b)。
1.3 进入本土研究进路
沿用本土进路作社会心理学研究, 是要在当地社会/文化/历史的脉络中, 详察当地人在生活事件里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并用一套庶民思维[8]见Bruner (1990)。老百姓惯用的想法, 例如, 中庸思维。也有学者用“素朴”一词(Peng et al, 2006)。, 作为“文化释义系统”来理解及解释其背后的心理意义, 从而令研究成果能更贴切地反映他们的心理活动[9]杨国枢先生称之为“契合性”, 是要做本土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杨国枢, 2008)。。
就以上述各个国家对同一个简单动作(戴口罩)的不同反应为例, 本土心理学研究者, 可以深入各国各自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去探寻“为什么?”的答案。例如, 美国人对戴口罩的极为抗拒, 对中国人, 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来说, 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如果追溯到美国人两百年前挣脱英国统治的开国历史, 以及所一直传承下来的个体自由、独立精神, 可以看出, 它不但反映在他们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 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不戴口罩”这一日常行为多么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崇尚“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Hsu, 1983)。
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本文作者一直试图在自身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 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在面临这一大灾难时, 可以如此快速地动员起老百姓、使之积极应对, 并速见成效。它显现的不只是所谓的“集体主义”、“相依自我”的价值观, 而还反映一般老百姓的应急灵活性。在全国进入战疫的紧急状况时, 除了政府/军队体制的动员优势之外, 有没有什么个体心理机制, 让大家很快地由“各顾各的”转变成“万众一心”、“听从指令”、甚至“争先恐后”、“相互监督”地确保任务达标或超标?
2 灵活性的传统心理资源
本文作者认可并接续朱利安(2018)的观点, 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特点之一, 是把思维视为是“资源”, 思维越模糊不定、越模棱两可、越有机会依情境作多样的“即兴发挥”, 从而提高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 亦即增加了生存的灵活性。她认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 “阴阳消长思维” (简称“阴阳思维”) “有机全息思维” (简称“全息思维”)以及对“人/我”的构想(简称“我观”)[10]由传统“人”观所引发的对“我”的设想。是促使人们在应急时刻展现了行动灵活性, 从而转危为安的三大思维源泉。
在对这三个思维作进一步说明之前, 有必要先对文化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些流行构念作一个回归原义的调整。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特点是来自语言的模糊性(朱利安, 2018)。中国单字的多义性, 使得使用者往往依自己的知识背景对其涵义作各种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在跨文化的领域, 为了要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能力, 以便可以被主流学术刊物录用, 常常都作了“西化”的处理[11]这本身也反应中国人行动的“情境中心主义”。。经年之后, 后进学者就忘记了原意, 并“以讹传讹”, 变为“事实”, 制造了不少偏见与误解。
2.1 阴阳思维
主流跨文化研究经常将中国人的传统阴阳思维翻译为dialectical thinking, 再翻译回中文, 成为“辩证思维”, 以致现在在中国心理学界也只用“辩证思维”来描述本土思维方式, 而很少人用“阴阳思维”这一词[12]内地学者称之为“辩证思维”也有其历史的脉络, 在此不表。[13]传统中医有“辨证思维”, 其依据之一也是阴阳思维, 但意义与西方的辩证思维绝然不同。。而“辩证思维”是希腊思想家们相互用正反辩论以求取“真理”的思维方法, 与阴阳思维完全不相干。
阴阳思维中的阴及阳, 虽然看似相互对立, 但却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概念。在阴阳思维中, 对立面的“并存”, 是“必要”条件, 但并非“充分”条件。蔡锦昌(2000)曾指出, 阴阳在中国传统思维里, 是指二气, 在《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就易理来说, 道之体为太极, 道之用为阴阳。把阴阳关系处理好, 就是“得道”。可见阴阳思维的重要性。
在这一论述中, 阴阳不是“两个干干净净的矛盾元素同时出现”,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前后交替出现”。这一变化过程的重点, 除了“时间”上的前后次序之外, 关键现象是“阴转阳、阳转阴”, 而这转换的动力是来自个体作为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 个体作为一个“用道”者, 要做什么及怎么做, 才会使阴转阳、或阳转阴, 到“恰到好处”的程度, 以致令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也就是说, 如何将这一转换过程为自己所活用及善用[14]俗称“拿捏”的过程。。所以, 中国传统的阴与阳没有矛盾, 它们是行动者的作为所可能带出来的后果态势。
本文作者认为, “时间前行”及“阴阳互转”这两个概念, 都必须与行动者合为一体来看, 才体会到阴阳思维对行动“灵活性”的影响。这种对未来的“转念”即有激励行动者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 也有安抚情绪/心灵的作用, 令下一步的应急思考不受太多的情绪干扰。普通老百姓, 不管自身是处在好或坏的处境之中, 只要自己尝试去改变, 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形势自变, 都会有“将来向相反方向反转”的心理准备, 从而在逆境时会保持适度的镇定, 期待情势好转, 再试图去改变现状; 在顺境会保持一定的警惕, “未雨绸缪”、不让自己陷入泥沼[15]杨中芳(2010)称这种“转念”为“逆向因应思维”。。这样, 在选择应对行动方面, 也有“可进、可退”的空间, 加大灵活处理的幅度。
不少研究支持这一论点。例如, 孙蒨如(2014)的一项研究指出, 人们在用“故事完成法”说故事时, 不管是正向故事起头或是负向故事起头的讲述者, “接续”下来的, 都有“朝相反方向走”的现象, 其中“正转逆”的预期较大。同时, 这种转念思维大者, 在作冒险性投资时, 较趋保守。林玮芳等(2014)在叙说困境故事时的字语分析研究中也发现, 出现最多的是反转词。
李纾等(2009)在汶川地震做的心理和谐调查研究, 发现的“心理台风眼现象”——位于震中区的居民、有较高的心理和谐感, 内容包括自我状态、家庭氛围、人际关系和社会态度等4个维度(任孝鹏等, 2009)。更早纪丽君(Ji et al., 2004)在SARS危机时发现类似的转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灾民身陷最坏的情况, 因而预期将来不可能更坏, 心情反而平静下来。这些研究结果似乎在说明, 由阴阳思维带来的“转念”, 对人们处理危机情境起了重要的缓冲作用[16]“危机就是转机”是最常用一句词语。。
2.2 全息思维
全息思维是基于阴阳五行论得出的一套思维体系。中医理论最能说明全息思维的道理。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全身是一个有机体, 其内部是由具有“相生相克”关系的各个部分组成, 每部分的功能有赖全身各部分都能运作正常。其中一处有问题症状, 其原因可能是多部门的失调, 治疗方案也不像西医那样作“精准打击”, 而是在消除症状后, 用综合调养、增加体能来防止再度出现病症。
把全息思维用在理解个人与其环境及他人的关系上, 是要将行动者放在其身处的情境一起看, 用回答“我在这个处境中要怎么做”这一问题作为行动的主要考虑。也就是说, 在具体生活处境中, 个体要看清自己在整个“社交场域” (或称“格局”或“剧本”)中的“位置” (或称角色), 以便对自己所需承担的责任及义务(或称举止、规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行动者先将自己安顿在“天、地、人”的架构中的做法。先熟悉剧本、熟悉自己所扮演角色及与剧中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简称“定位”), 再通过排练掌握如何演好该角色及与其他角色的搭配, 一起把故事演活。
个体的“全息思维”, 在这里是一种“情境中心”的思维方式[17]许烺光(Hsu, 1981)在其比较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著作中, 用“情境中心” (situation-centered)一词来刻划中国人的行为。, 增加了人们应对不同情境的灵活性, 不似主流进路所关注的“人格特性”那样, 是超越情境的“本质”特点。同时, 这一全息思维, 因为是在情境中来定位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它也促进了参与者的准确互动及临场协调, 从而增加了应对灵活性。
2.3 “我观”
在汉语中, 原来没有“自我”这个名词, 只有“己”或“我”。而“己”与“我”的差别, 翟学伟(2018)认为, 前者是一个文化对自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念; 而后者则是人们在实际生活操作中所表现的“自己”。但是, 在一个单字前加上另一或几个字, 以更明确其意义, 是中文一贯的做法。例如, 公我、私我; 真我、假我等。倒是“自我”这一词, 在“我”前加上一个“自”, 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明确性, 所以在当今中国心理学研究中, “自我”算是一个已被惯用了的外来语[18]有一說法是, 它是由日本语借来的。。在本文中, 主要用“我”, 但在涉及西方主流心理学研究时, 有时也会用“自我”来表明两者的差异。前者是行动实践的我; 后者是特性认同的我。
中国传统有关“己”或“我”的探研, 不限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层面, 它也有深厚的哲学、精神传统[19]近10多年, 在神经认知科学也有很丰富的研究成果, 参见:朱滢, 伍锡洪(2017)。。在西方主流心理学领域, “自我”一直是被视为是一“物”来研究, 关注点放在个体内在的本质及其特性, 认为个体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一本质。刘述先(2000)曾指出, 在中国传统思维里, 从来没有把这样的本质抽离出来,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想法; 也没有把内在的我与超越自身式的我分割来看的构想, 从而没有对脱离自身的纯粹心灵追求; 也不去了解原子式的存有问题。这说明对“我”的思考进路, 从一开始中西哲学的思考就不一样[20]相同的论点, 参见:朱滢 (2007)。。
而且, 超出主流学者预期的, 在一个他们所谓的“集体主义”文化里, 会有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时间及精力, 从不同的方面讨论“己”或“我”的问题。下面是一个对这一问题, 以它与灵活性的关系为焦点所做的概览。
2.3.1 “我”的开放性
在哲学层面, 中国传统思维是以一元化思想作为主导, 但并不压抑多元, 流行的是“三教合一”的思想。对“我”的论述也是如此。人们把儒、释、道三家“我”视如资源, 内藏于心, 在用时将其中最受用的部分拿出来[21]南怀谨曾言:儒家是粮铺; 道家是药铺; 佛家是杂货铺。。这是由哲学的高度来看“我”的灵活性。
刘述先(2000)曾指出, 儒家阐发的性智, 道家阐发的玄智, 以及佛家阐发的空智, 对中国传统“我”的思维有“三足鼎立”的影响, 从而令中国人在应对人生不同的境遇时, 上述三家不同的“我”成为可用的“资源”, 可以比较灵活地做到“进可攻、退可守”[22]相关的论述甚多, 例如, Peng等人(2001); Wang & Wang (2021)。。
2.3.2 “我”的可塑性
上述“我”的开放性也带来了它的可变性。在传统儒、释、道的思想中, 都有“无我”的印记; 个体的“个我”是要逐渐被淡化及超越的, 作为向上修养的终极目标。儒家的“我观”除了不执着己见, 提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之外[23]出自《论语·子罕》。, 还提出要能接受自己是有缺点的, “反身求诸己”是“自我超越”的一个渠道。杨中芳(Yang, 2006)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己”是“塑成” (becoming)的概念; 西方主流的“己”则是“既成” (being)的概念。这个塑成是通过“做人” (person-making)的过程来完成。
代表儒家的孟子心学, 在论述人禽之别时, 分别了“小体”和“大体”。前者类似“己私”的概念, 有如现今人们惯用的“小我”一词, 它是封闭、排他的; 后者是真正的“我”, 是开放、包容性的, 所谓“万物皆备于我”, 不但隐涵了“天人合一”的观点, 同时也开启了“大我”理念。因此, 自我超越的另一途径是将“己”的边界逐渐扩散到“个我”之外, 形成包括自己及他人的各种“大我”层的构想, 反映了“我”的可改变及可塑性。
这与西方“自我”理论中, 强调“自我”的稳定性、一致性及有边界性, 从而以改变外界环境来成就自己的想法, 不可同日而语[24]见Sampson (1985; 1988)。因此, 改变自己顺应形势并不被认为是软弱或没有“自主性”的表现, 而是从实践中去优化自己成为文化理想之“人”的途径。这一“我”的可塑性无疑增加了对事务不同看法及理解, 也扩展了行动本身的可能性及多样性。
2.3.3 “我”的流动性
在社会学领域, 有关“我”的论述就更加“形象”, 也让人容易理解了。老百姓的语言中, 最常用的有关“我”的两对阴阳词语是“大我−小我”及“公我−私我”。它们在中文中意义很相似, 都有“大圈套小圈、以个我为中心”的意思。在此仅用“大我−小我”说明论点, 可以类推至“公我−私我”。
在“大我−小我”这一组对立词中的“大我”与“小我”, 并不是逻辑意义上完全分开的“矛盾”概念。它们虽然是相互“对立”的“人多、人少”概念, 却必须摆在一起来看才有意义。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或“大我包小我, 小我包大我”的概念。而且两者所指涉的对象都是流动的。这与西方主流思维中分辨的公我、私我及团体我, 都清楚地指涉单独个体的、对内/对外的“我”, 以及其所经常交往的团体中表现的“我”, 可谓大相径庭[25]Triandis (1989)是较早提出自我的三个面相:私我、公我及团体我的学者。他定义, 私我是个体依自身的特性及喜好所表现的我; 公我是与他人交往时表现的我; 团体我则是自己在所认同或归属的团体中表现的我。。
例如, 个体的一个“大我”可能是自己的“家”, 包括自己及所有可称为“家人”的人。费孝通(1947)曾指出, 中国人的一个“家”字, 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 “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堆, “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 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 大到数不清, 真是天下可成一家。同时, 称这个“家”之为“大我”, 是因为相对于被“家”包住的“个体”这一“小我”而言; 但是如果相对于包住它的社区而言, 这个“家”也可以是“小我”。这时, 个体所居住的“社区”成了“大我”, 而“家”反而成了一个“小我”。为自己的“家”清除垃圾, 乱倒到社区街口, 是不顾“大我”、只完成“小我”的行动。
这种动态的“大我”“小我”流动性及互转性, 是必须靠被前面所讲的“全息思维”中的“社交场域”来“定位”的。可以这样说, 没有代表“场域”的“局”或“剧本”, 以及自己及他人在“局”中的“定位”或“角色”, “大我”及“小我”到底是指涉什么, 都无法落实。这种流动性及不确定性, 常会令人不安、不知所措[26]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最常问的就是:“这是个什么局?”、“这是什么情况?”。。例如, 杨中芳(2001b)在一个有关回答20题“我是谁?”的问卷调查中, 发现当香港大学生被试, 由于是处于“真空”的研究情境下作答, 往往想不出20条可以回答这一简单问题的答案, 于是乎有“语无伦次”、“乱填”的现象出现[27]这里也再次说明, 自我认同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朱滢, 2007)。。
2.3.4 “我”的多层性
上述“大我−小我”中“大我”及“小我”所指涉人群的不确定性, 也说明了“我”的多层性。费孝通(1947)用小石投入水中的波纹作比喻, 可谓是最经典及传神地表明了中国人“我”的多层结构[28]许烺光(Hsu, 1971)有类似的论述, 还加入了西方佛洛伊德的深层结构。由于篇幅关系, 在此不赘。。中心点是个体的“个我”, 层层波纹向外扩展的同心圆, 逐层包括了更多的“与自己有关系”的人, 由家庭开始、到学校、到单位、到社会(村、乡、市、省等)、再到国家, 一路可以到“全人类共同体”。这每一层, 在某一个“社交场域”都可能是被唤启的“大我”, 或相较之下的“小我”。
这样的多层结构, 容许中国人的“我”, 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极富弹性。有如川剧中的变脸者, 储备了不少可能的“我”。但是, 这些“我”大都以“尊尊−亲亲”定下“双轴自我”的大致规范来行动(翟学伟, 2018)。不同的时间及“场域”下, 这些储备的“我”中的一个或数个, 会被唤启成为引导行动的主力。
基于这一多层性所引发“我”的灵活性也说明, 为什么人们在一般“蝇营狗苟、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情境中, “我”可以是“形形色色”的, 个别差异很大。有些人可以是非常“自私”的, 因为被唤启的总是那私自的“个我”; 有些人则无时无刻不以某一个自定的“大我”作为行动的依凭。但是, 一旦像这次疫灾的突然爆发,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个体的“国家我”、“社区我”、“家庭我”会同时被唤启, 目的也很一致——活命, 因此配合了政府的动员, 完成了历史性的使命。
如果我们用“个体生活在具体情境之中”的观点, 而不用跨文化进路所使用的“文化烙印个体”观点来看“文化”与“个体”的关系[29]杨中芳(2001c)建议使用的“文化/个体”关系论(第160页)。人们在文化的指引下, 会依情境变化, 动态地、灵活地协调出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行动。,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我”, 其个别差异可以很大, 人们有一定的自由度去做他们选择的“我”, 然而, 在抗击疫情中他们表现出的速度与效率, 即被西方跨文化学者从外表看到的所谓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行动, 实际上却不只是“顺从、听话”的结果, 而是个体“大我”的自发表现。而这些不同的“我”, 都是由“全息思维”下, 不同的“场域”所引发的。
2.3.5 “我”的场依性
由前面有关“我”的流动性及多层性的讨论, 己经清楚地看出“场”的重要性, 以及“我”必须在“场”中安顿的重要性[30]见:林以正(2010)。。这种由情境不同而引发之“我”的角色变换, 自然增加了行动灵活性。有时由一个“我”出发, 行不通; 可以换一个“我”, 来走走看。
2.3.6 “我”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杨中芳(2001c)曾指出中国人的“己”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协调“大我”与“小我”的两难困境[31]第170页。。当两者“不可兼得”时, 传统理想的行为准则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其反映的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对“自我超越”价值观的形塑。但是进入21世纪, “个人主义”价值高涨, 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愈来愈普遍。这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理念之所以在当今的生活中, 还是不断地被强调, 也正是因为“两者之不可兼得”的盛行。然而, 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 老百姓并不是分分钟只按“大我”来行事, 而是费尽心思去协调这两个“我”, 以便过上“心安理得”的好日子。
细数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或戏剧, 内中的情节, 不管是喜剧或是悲剧收场, 说的大都是“大我−小我”不能两全所带来的张力。例如, 忠与孝、国与家的无法两全。这两种困境中的“小我”还都不是指“个我”; 遇到真正的“个我”之私, 就更要花些心思来协调, 才能“名正言顺”地登场。可以说, 在强调更大的集体有优先权的情况下, 人们的心思, 并不是如西方学者们看到的那样, 放在听话、服从、整齐划一等行动上, 而是放在解决这类“大我−小我”的利益冲突之上。
表达如何解决此类困境的日常用语,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可谓多如牛毛, 仅以公我私我的冲突为例:先公后私、公私分明、假公济私、公私兼顾、公而忘私等等, 林林总总。这些还都只是一些指导原则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会依自己的处境, 想出诸多办法来协调两者, 令自己能过得更安逸一些。可以说, 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这方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唾手可得的例子有, 丈夫或妻子瞒着对方积攒的“私房钱”, 就是“家庭我”与“个我”在经济上的解困之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协调都增加人们处事的灵活性及创新力。
2.4 疫情中的“我”
当然,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处境中, 所界定的“大我”、“小我”之间没有重大冲突, 像奥林匹克运动员在为国家争光之际, 也带来个人的荣耀。在这次疫情中, 一个人的国家我、社区我、家庭我及个我都同时被唤启去做同一件事, 那就是用“自我节制”——“封城”、闭关、隔离、禁足、检测、戴口罩等, 来共同达到消除和抵御病毒的目的, 所以人们在这些“我”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 从而加大、加快了行动成效。每个人每一个层次的“我”中所包括的他人, 目标都一致, 大家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相互鼓励。甚至, 人们还运用超高的想象力, 编出各种形式的幽默, 来化解因为这些节制所带给各种“小我”的不便及苦难。
或许, 我们可以把对疫情的应对分为两个阶段。一开始, 老百姓在信息缺乏及谣言四起的混乱中, 通常会采取“静观其变”, 先作“自我收敛”, 跟着上级政府的指令, 摸清“情况”再说。但是, 当疫情迅速升温、人们意识到其致命性后, 人们在照做之外, 会唤启自幼培养出来的“大我”思维资源——“顾全大局”唤启, 从而由原来的“被动”变“主动”, 这时人们展现了极大的积极性及创造性, 而绝不是唯命是从, 更不是对集体的“依赖性”, 也不只是与“他人”的“互依性”[32]Markus 与Kitayama (1991)用“独立自我−相依自我”这一个体认知基模, 来分类全世界各国子民, 成为用以解释文化间情感及行为差异最热门的理论。, 更多的是自主性, 是主动地去参与和共同解决问题。
2.5 小结
以上从对三个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解说, 提供了中国人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中所展现灵活性的可能来源。在涉及应急时刻, “转念”思维起到了视“危机”为“转机”、“处变不惊”而寄望未来、安定人心的作用; 在衡量整体情况的“局势”之后, 令一般常有利益冲突的“大我”、“小我”能同步前行, 形成“万众一心”的气势。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人能“收放自如”的“我”是行动灵活性的主要源头。
以上的分析, 除了是想在一个本土脉络里, 理解现今正在中国发生的疫情大事, 也想借之反思过去对“自我”研究的狭隘性——看到的只是中国人是具有“集体主义”、“互依我”这些“特性”, 没有注意到人们生活动态的一面。如前所述, 文化与个体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模塑后者, 而是后者在前者的指引下, 如何灵活地处理事务、表达自己, 以便过上好日子。这种对中国人“我”的再认识, 提供了一个研究“自我”的新进路。
3 中庸行动我
“中庸行动我”是指个体在选择及执行解决问题之具体行动方案时, 依现实“情境需求”, 灵活地“协调”出一个“恰到好处” (“中”)的“我”, 作为行动依据, 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功效。
这一“中庸行动我”的构思, 源于本文作者多年从事“中庸思维”研究所建构的、作为一套中国文化释义系统的“中庸实践思维体系” (杨中芳2008b)。它是指个体在为人处事时, 如何思考、选择、执行行动方案的文化指引[33]Sternberg (1999)称它是一种思考“偏好” (preference), 似乎也很恰当。, 其中还包括一个反思/修正的“行动优化”过程。这些指引的目的是要让个体的心理及生活达到“内(心)外(界)和谐”的状态(杨中芳, 2010)。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的“心性论”特别提到“操则存, 舍则亡, 出入无时, 莫知其乡” (告子上), 它是一种“实践我”的思考代表(刘述先, 2000)。传承这一论点, 中庸思想体系也是“实践”性的, 因为它的思考重点是放在“怎么做”上, 而不似主流心理学研究主要考虑的是造成外表行为背后的个体“本质”原因[34]前者是思考“how?”的问题; 后者是思考“what?”的问题。。它之所以是一套体系, 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中国传统的“天、地、人”宇宙观, 以及“阴阳”及“全息”认识/方法论为其立论支柱。在这一体系内, 前面所述的三种传统思维资源即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沿用这一“中庸”进路来思考如何作“自我”研究, 须对主流惯用的思考进路作大幅度“换脑袋”的动作(杨中芳, 2022b)。本文作者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 就是想捕捉前面所述有关中国人“我观”中的“收放自如”概念。下面在对这一构念陈述的过程中, 作者会以主流进路的思考重点作为对比。
3.1 “行动我”的定位机制
沿“中庸进路”探研中国人的“我”, 首先要放弃去问“我是什么?”, 而是去问“在当下这个情境, 我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 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目的?”要回答这些问题, 行动者要先将自己“安顿”在所处的情境之中, 再从这个安顿下来的“我”出发, 去寻找可行的行动方案。这个“安顿”的过程, 在这里, 被称为是“定位”。
“行动我”的提出, 是基于一个动态的宇宙观——世界是不断随时间向前变化的, 及一个主动参与的“人”观——“人”是“天、地、人”的一个主要组成分子, 所以在生存过程中, 是积极地融入当下时空走势一同前行。行动者在每一个时空的天地间都必须先安顿自己, 再去作协调的工作, 因此表现的“我”都不一样, 没有所谓永恒的、属于自己的“本质”或“真理”的“我”。
“行动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 个体与其处境是“合而为一”的, 而不是如主流进路那样, 把个体与环境先分为独立的两段来审视。然后再将它们分别进行分类后, 再进行“配对”的动作, 以便找出两者交互作用的“最佳组合” (杨中芳, 2022b)。
“行动我”中有4个主要面相, 反映它与环境的一元观点, 也反映“我”因情境变化而变化的流动性与灵活性:(1)格局我——对自己在当前处境中之位置的确认, 以及由这一“定位”所唤启的“适当”举止[35]2020年东京奥运男子10米跳台银牌得主杨健, 因不满裁判“压分”, 表现有失风度, 被网上狂批“没格局”、不能“融入大局”。; (2)差序我——把注意力放在社交“局”中的关系网内, 将其中涉及的他人放入层层的“大我”、“小我”圈层里, 再按照相对应的格局及规范与他们交往; (3)运势我——把自己放在大时空、大走势(世事是随着时间不断地向前变动)的背景下, 来思考自己要如何“借力使力”地往前行; (4)阴阳我——认识及接受自己本身有正、负两个面向, 让自己有更多的资源来协调与外界环境的融合。这种被主流思维认为是“辩证自我”的特性[36]“辩证自我”是由Spencer-Rodgers等(2009)提出, 指对“自我”的认识具有相互矛盾的人格特性。, 可以被视为是行动我考虑“怎么做”的一种资源。知道自己要在何时利用自己的优点、何时避开自己的缺点, 以达到自己行动的功效。
3.2 中庸的协调机制
作为行“中庸之道”的行动者, 在综合所处情境的大局, 定下了各种必须照顾到的“我”之后, 最终要协调出一个“恰到好处”的“我”, 作为行动者思考最佳方案的基础。这个协调的原则即不是找平均数、也不是委曲求全的妥协, 更不是在“搞平衡”[37]冯友兰(1940)在“释中庸”一文中指出: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庸俗主义、妥协主义及投降主义。。而是按实际情况, 找到即能达到“行动我”所想达到的目标, 又能不引起外在太大张力的“内外和谐”的心理状态。因此, 这一状态也可视为是中庸行动我, 是否成功地协调了在某一特定情境中被唤启的各种“我”的效标。以此可见, 中庸行动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
4 中庸行动我、灵活性与心理健康
以上对“中庸行动我”的构思, 是由实地详察老百姓在战疫期间的行动/现象, 而提出的一些新想法, 目前还没有所谓“有的放矢”的实证研究来直接支持它与灵活性及心理健康的关系。然而, 行之有年的“中庸心理学研究”却累积了不少三者关系的研究, 支持了遵行“中庸价值”的“行动我”确实具有思考及情绪控制的灵活性, 并且与心理健康有一定正相关。下面将目前己有研究成果作一个简单的整理及综述, 部份內容择录自杨中芳(2022a)。
杨中芳(2010、2022a)曾两次综述了近25年所累积的、与中庸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 由黄金兰等(2012)改编的“中庸实践价值/信念”量表[38]原量表共16题, 测量8个中庸价值/信念:天人合一、顾全大局、两极感知、着重后果、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不走极端、以和为贵(杨中芳, 赵志裕, 1997)。(简称黄、林、杨中庸量表), 在经过进一步的因素分析后, 得出两个子因素, 被命名为:(1) “拔高视野”——用全息思维、阴阳思维来理解自己当前所面临的处境, 作为“自我定位”的基础; 以及(2) “自我收敛”——控制情绪、沉着应对、以忍、让、不过火, 作为“自我协调”原则(杨中芳, 林升楝, 2014)。而“自我定位”与“自我协调”正是“中庸行动我”的核心构念。是故, 作者将用这两个大主题来分述它们与灵活性及心理健康的关系。综述的最后, 将就“灵活性”作为“中庸行动我”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进行专节综述及讨论。
4.1 拔高视野与自我定位
具有“拔高视野”者是指那些习惯用“全息思维”及“阴阳思维”来看问题的人。在此具体地指在黄、林、杨“中庸信念/价值量表”中, 在“拔高视野”因子得高分者。
4.1.1 拓宽思考范围、唤启多元自我
全息思维的一个面向是把“个我”放在更大、更宽广的场域中来思考, 从而令前述各种不同的“我”可以被唤启, 并成为行动我的协调对象。黄金兰等(2014)发现在黄、林、杨中庸量表得分高者, 在实验室通过唤启, 其认知作业展现“整体优先”现象。这一结果显示具有中庸价值观者较易于拓展自己的视野。
张仁和(2010; 2021)曾用了两种思维训练操作来看“我”在被放大及去中心化后, 对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他用了“正念训练”, 令心理空间增大, 致使思考灵活性增强; 另外, 他要求被试用“我、你、他”三个主词来叙说同一个切身事件, 发现当主词由“我”变成“你”、再变成“他”时, 人们的情绪由极端转向平衡, 而且拓展出更为宏观的心理视野, 进而带出更为丰富且均衡的多元自我。
4.1.2 预测走势、决定行动方案
全息思维的另一个面向是对事件作“古、今、来”的形势考虑。余思贤等(2010)编制了一个“长期取向” (个人从广阔的时间视域中诠释当下经验的取向)量表, 发现其得分与中庸“全面思维”中的两个主要维度“注意范围(大)” 与关注“因果关系”呈显着正相关[39]沿用前面所述跨文化思维研究中holistic thinking的构念化。。在杨中芳、林升栋(2014)的一个研究中, 也发现这一“长期取向”得分与吴佳辉、林以正(2005)的一个以意见整合为主题的“中庸量表”中的“多方思考”维度有显着正相关。同时它也与一个包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内容的、面对未来的逆向“因应思维”有很高的显着正相关。这一结果反映关注形势的走向, 是选择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考虑。
4.1.3 拔高视野、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
高瞻、李炳洁(2014)的研究发现, 黄、林、杨中庸量表中的“拔高视野”得分, 调节了精神质(包括离群、孤独、有罪恶感等)与贝克抑郁症自评量表得分之间的正向关系。“拔高视野”得分越高, 两者的正相关越强。这一结果似乎显示, 抑郁病患者看自己的角度越高远, 与他人相比, 其对自我的评价越差, 从而加强了抑郁情绪。这一结果反映中庸思维中的“拔高视野”对自我评价也有一定的影响。
4.2 自我协调与收放自如
自我协调是指“中庸行动者”在情境所定位的“大我”的需求, 以及“个我”的需求之间寻找一个“最恰当”的行动方案。有些情境, “大我”优先, 没有商量的余地; 有些情境容许“个我”作较高程度的展现; 但是, 还是要作“自我收敛”, 以便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选择收放自如的时间与情境是中庸协调的重要因素。
4.2.1 “中庸我”的场依灵活性与心理健康
林升栋(2005)沿用Markus及Kitayama (1991)有关“独立我−相依我”的特性问卷调查, 但将得分在中间者, 也就是认为自己同时具有独立及相依特性者, 称为是具有“中庸我”者[40]Markus及Kitayama (1991)的研究视这些受试为对自己“认识不清”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同时具有矛盾特性的”。后来被Spencer-Rodgers等(2009)称为具有“辩证自我”者。, 发现他们与有“独立我”及“相依我”者相比, 在认知操作方面有更强的场依性, 显示更具情境中心特色。
吴佳辉(2006)询问了大学生有关面对不同的对象(如父母、手足、朋友、陌生人等)能表现不同自己的程度、信心及效度, 并称之为“自我拿捏”。他发现这一自我拿捏指数与中庸思维、自我清晰度及社会自尊均有显着正相关。
郑思雅(Cheng, 2009)用了“辩证自我”为测量工具, 探讨了正负特性并存的自我概念与“应急变通”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确实发现两者有正相关, 而且与许多心理健康指标都有正相关。应急变通性(coping flexibility)是郑氏提出的一个人格特质构念, 指人们在遇压力事件时, 能依情境的“受自己控制”程度, 决定自己要采取主动或是被动行动策略的能力(Cheng, 2001)[41]她的构念与西方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相仿, 与自我行动的策略规划(contingency table)有关, 理论还是以自我控制外界为主, 与中庸行动我的协调是有差别的。。然而, 从她的研究中看不出为什么有“辩证自我”特性的人, 会对自己的“控制力”敏感到以之作为应急时应采取什么行动的准则。“辩证自我”这一构念与“中庸行动我”中的“阴阳我”的关连是无庸置疑的。前面说过, 阴阳我的善用自己的优缺点, 倒可能是人们在应急时用以选择行动方案的准则。“受自己控制”可视为是自己在当时处境中善用自己的优点。
然而, 只是依处境做不同的行动还是不够, 林玮芳(2008)在研究了中庸思维与人们应对传统性及现代性冲突的两种策略时, 发现相较于那些将两种价值区分开来并用于不同生活范畴的区隔者, 采取整合策略——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作整合成为一个生活范畴者, 与中庸思维得分有显着正相关, 与心理健康指标也有正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中庸整合还是更重要的。
上述这4个研究似乎指出, 有阴阳思维的“中庸行动我”, 具有依处境改用不同行动思考及策略的能力。反映由场依性带来的行动灵活性是与心理健康有关, 因此可以视为是因应危机的“资源”。
4.2.2 自我收敛、情绪/行为管控、人际/心理健康
“中庸行动我”在按“恰到好处”的原则寻找“最佳行动方案”时, 首要的条件是懂得“自我收敛”, 也就是关注自我行动的“适恰度”、做到“适可而止”。几个研究在比较“正常”及“偏离”样本时, 探讨了黄、林、杨中庸量中的“自我收敛”因子在自我及人际关系处理的作用。
高瞻等(2014)比较了正常人与抑郁病患者之间在黄、林、杨中庸量表逐题得分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忍让”一题的得分有最显着的差异。这一结果说明, 可能是由于缺乏忍让的协调, 导致人际关系不良, 进而形成抑郁症状。
高瞻、蔡华玲等(2013)发现抑郁症病患在黄、林、杨量表的“自我收敛”得分与大部分SCL-90指标, 以及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得分, 均呈显着负相关。接着, 高瞻、李炳洁(2014)用同一组病患, 研究了“情绪调节灵活性”在“自我收敛”得分与病人自评及他评抑郁症状之间的作用。结果发现它起了加强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 自我收敛价值, 通过情绪管控的实践, 可能通过人际关系的改善, 最终导致焦虑及抑郁症状的缓解。
彭敏等(2016)曾比较了一个“一般家庭”样本的父母和一个因子女有问题行为前来做家庭治疗的“求助家庭”样本的父母, 在黄、林、杨中庸量表的“自我收敛”得分的差异。结果发现“一般家庭”父母具有较高的自我收敛意识。他们在对自己的家庭作“功能自评”时, 在内部沟通、情感介入、行为控制三方面得分都比“求助家庭”高。同时, 这两个样本, 在“自我收敛”得分与“行为控制” (家庭成员共同应对生活事件的管控能力)评分之间都找到显着正相关。表明自我收敛与家庭成员有序、良好的相处有关联。
4.2.3 中庸协调与人际/心理健康
叶晓璐、张灵聪(2014)在研究中庸思维与投资及与人交往策略的关系时, 发现高中庸思维者, 不但在投资方面采取“不保守、不冒进”的策略, 在与人交往方面, 也同样采用既考虑他人的投资回报、也争取自己应得利益的策略。这一结果表明, 中庸行动者具有协调自我需求及保持人际和谐的意识。
王慧、张灵聪(2018)用一个“宿舍人际关系”诊断工具, 调查了大学住宿生在宿舍内解决人际冲突之道。结果发现, 在被问及, 目前“在自己内心欲望需求与外在顺从需求(个人行为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之间所处的平衡状态”时, 那些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具中庸特色的“内外皆平衡”者, 其宿舍内人际困扰得分最低。而且, 他们更多地选择以合作而不是竞争来解决问题。那些认为自己是“内外不平衡”者, 则多采取回避方式。
李原(2014a)有关在职妇女如何处理“事业我”及“家庭我”的互促−冲突压力时, 发现中庸的“全面思维”缓冲了因工作负面压力所带来的“工作−家庭”失衡感; 同时增强了工作的正面好处, 从而改善了两个“我”的平衡感。
王轶楠(2020; 2021)指出对中国人而言, 在社会情境中, 所定位的“大我”及“小我”, 固然有一定的价值冲突, 但是如果能协调成功, 例如能做到“完成大我、成就小我”, 那就会带来高自尊。她的研究结果发现, 具有这种协调自尊者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4.2.4 中庸行动我的自主性
自主性在心理学是指行动的动力是来自行动者内心意愿(自控), 而非来自“为他人而做” (他控)或“被利诱而做” (利控)等。过去不少研究者都认为, “中庸行动我”因需要在不同的情境按不同的“我”来行事, 同时又要在“大我”与“个我”需求间作协调, 反映的是看似不自主的软弱、被强迫行为。然而, 林以正(2014)发现黄、林、杨中庸思维高者, 在解决冲突时, 除了会综合考虑很多不同因素, 以寻求最佳行动方案之外, 他们也认为自己的协调行动是出于“自控”。这一结果与杜旌、姚菊花(2015)在研究人们心中的“中庸行为”时得出的结论相同:中庸行为不是被动的、与大家保持一致的从众行为, 是个人主动感知环境、预测未来变化所进行的自我调整。所以, 它是一种主动配合所处环境的自主行为。
4.3 剖析灵活性的心理机制
在对中庸研究的综述中, 杨中芳(2022a)屡屡发现中庸思维影响人们生活作业, 大多是以另一个变量为中介。那就是, 灵活地处理情绪或人际问题。通过自主调控、以自我“收放自如”的灵活性, 来达到内心与人际的和谐。这一中介变量促使中庸思维与利他行为、正常家庭功能、心理健康、及幸福感等都有正向关连。下面就在人际处理、情绪调控、时机掌握及应急变通四方面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述。
4.3.1 人际处理灵活性
郭轶等(2016)在研究抑郁症患者的中庸思维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时, 发现人际关系处理的“应对效能”起了中介作用。“应对效能”是一种旨在“把事情做好”的灵活操作。中庸思维能够通过这一效能, 减缓抑郁症状。
李启明、陈志霞(2016)以自编的中庸实践量表探研了中庸思维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发现心理弹性(力量、韧性、乐观)和情绪重评, 在两者之间起了中介作用。这里, 心理弹性以及情绪管控都可视为是一种处世灵活性。
毕重增(2016)发现中庸思维调节了人际交往中, 遵循规则与自我表达自信的相关, 高中庸思维者倾向于突破规则的藩篱, 灵活地去表达自己, 从而增加了表达的自信。这个结果说明, 中庸思维自我表达的灵活性, 增加了自我协调发挥的自信心。
Chang等(2020)访谈了新婚夫妻婚后怎么作自我调节的策略[42]她用主流自我研究中的self-regulation构念, 意思是对自我行为作调整, 借以与外界和谐相处。。发现受到传统文化对夫妻关系规范的压力, 夫妻双方会采取两种“和谐”相处之道:一是“虚和谐”; 另一是“实和谐” (黄囇莉等, 2008)。前者是与对方的家庭维系表面的礼尚往来, 在对方面前也尽量压抑内心负面情绪, 表现外表和谐; 后者是真诚的履行与对方家庭和好相处之道, 以及与对方维系良好的感情交流。夫妻不管在作虚和谐或实和谐的行动时, 都会用一些中庸思维价值, 如以和为贵、不走极端等, 来作自我调节的说辞, 以达到内心的平和。
4.3.2 情绪调节灵活性
汪曼颖等(2014)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庸思维高分者可能透过“自我调控”避免对负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 来达到调节情绪致“中”的状态, 并借之获得对低激发正向情绪刺激的较佳记忆。而中庸思维低分者较容易停留在负向情绪里无法抽离。相同地, 李原(2014b)的一个研究, 也发现中庸思维调节了由生活压力事件所带来的负向情绪处理, 从而增加了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黄敏儿等(2014)研究了情绪灵活性在中庸思维与李怡真(2009)提出的安适幸福感(peace of mind)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易晓敏(2010)发现将情绪灵活性分为认知评估及情绪表达来测量后, 前者在吴佳辉、林以正中庸量表中的意见整合性与幸福感两者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而后者则中介了这一整合性与社会支持感的正向关系。
这两个研究说明中庸思维通过在不同层面的情绪灵活处理, 提升了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情绪发生之初能作出灵活转念, 延长正向情绪, 减低负面情绪, 从而令自己不致太受情绪影响, 增加安适的幸福感。同时, 到了情绪需要抒发时, 又能灵活地表达, 不会过于影响人际和谐。
4.3.3 时机掌握的灵活性
林玮芳等(2014)发现中庸思维者的转换思维与心理适应能力的关系, 是受到转换时机的影响。亦即, 在悲伤打击中要快速作“抽离”转念; 但在喜事临门时则要先体验一阵美好心情, 再作“思危”转念,才能维持良好心理适应。这一研究说明, 即使是“转念”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几个与企业建言行为相关的研究也指向掌握恰当时机的重要性。马鹏、蔡双立(2018)在家长式领导的条件下, 发现中庸水平高的员工, 在感觉有上司支持感的情境下, 更容易提出促进型建言。段锦云、凌斌(2011)的研究指出, 中庸思维中的“见机行事”是建言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两个研究似乎都显示, 中庸思维水平高的员工基于灵活性强, 懂得抓住时机, 作恰如其分的建言, 从而成功率比较高。
5 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本文作者一向强调, 本土进路并不在于推翻现有主流思维的研究范式, 而是认为, 心理学研究在整个科学研究发展的进程中, 仍没有像物理学那样,到达用实证研究来追求大型解释人类心理定律的阶段, 而是还处在所谓的“描述性”阶段, 重点在于发展一些小型的“说法”, 并用实证研究去探看这些说法的普遍性(Campbell, 1979)。故此, 对要研究的现象做深入、细致的描述及理解, 应是当今心理学研究最关键的一步, 而本土进路正是想把这一步做好(杨中芳, 2008a )。
所以, 研究是不是本土, 并不在于所使用的方法, 而在于研究问题从哪里来, 以及要怎么去构思。现在大部分学子做研究的程序, 是先在期刊上找能出版的题目, 再去现实生活中找对口的现象, 把它们连在一起。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令我们自己的研究永远是他人成果的附属品或“应声筒”。
以下是本文作者对未来进行“中庸行动我”及应急灵活性研究的一些建议。
5.1 拆开“一篮子”的刻板印象
有关中国人“行动灵活性”的研究这么少, 主要因为主流进路的研究重点在对自我“本质” (人格特征)的探讨。过去不管在跨文化认知方式, 或价值观的探讨都出现用“一篮子”特性来描述一个文化的现象。在本文前面的综述中, 不管是“认知闭合需求”或是“集体主义”价值观, 都与“没有思维自主性及灵活性”的特点连在一起, 从而让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是不具备灵活性的。例如, 经常听到的论点是:“认知闭合需求”较高的文化, 人们更倾向于事前做好计划与规划, 来降低风险; 而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中生活的人们, 则通常拥有更高的弹性。
本文对“中庸行动我”的分析, 说明上述的刻板印象必须拆开来看。中国人对“我”, 甚至对世事, 所持的态度是开放的, 愿意主动去配合外界的改变。这不就是“开放性”、“自主性”的表现吗?为何这些不能是灵活性的资源?对剌激的追求, 喜欢新鲜事物, 接受人生挑战就一定是灵活性产生的唯一途径吗?拆开这些攻不破的牢笼, 去作独立思考, 应是当务之急。
王登峰(2012)在提倡人格研究本土化时, 曾指出, 在测量中国人的“开放性”人格特征时, 如果只是根据西方的理论构想来编制测验, 实际上有可能完全“验证”西方的理论构想。但其内容结构却与中国人的实际开放性特点相去甚远(王登峰, 崔红, 2006)。这一点, 本文作者非常认同。
5.2 对已有研究构想的逆向解读及审视
有了“中庸行动我”的构念, 许多目前描述中国人的一些论点则可以作重新诠释或反思。例如, 在主流研究中, 有关人们的“内隐人格理论” (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的构念[43]由Dweck等(1993)提出。, 总是认定中国人有“人格即成, 就不会改变”的说法。但是“行动我”中的“局格我”、“差序我”、“运势我”及“阴阳我”都隐含“我”的“情境中心”取向, 是不断地在变动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指出“人”会随“环境”改变的文化故事。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论”。在许功余(2007)的一个研究中也确实发现, 被试非但预测具有正向人格特征者, 会有负向行为特征出现; 同时也预测具有负向人格特征者, 会有正向行为特征出现。这里展现的是对“人”看法的多样性及灵活性。
另外, 命运可协商的信念(negotiable fate belief)[44]由Chaturvedi等(2009)提出。, 如用老百姓能懂的术语就是“天命由我来决定”, 原是为了激励“人”的积极性:不断地去努力, 不言放弃。但是, 如果沿用阴阳思维中的“时间”及“转念”的构想, 可以将关注点由相信命运的可 “协商”性[45]命运如果可协商, 还叫“命运”吗?, 变为是对自己未来转运的期待(受苦者有“苦尽甘来”的期待:享乐有“乐极生悲”的预料), 从而令现时的积极努力或自我节制, 可以是面对“未来”的准备。这里展现的是阴阳思维带来的处世应对灵活性, 而不是一种内在的、对命运的“信念”。这个例子想指出的是, 用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可以带来许多对旧有研究领域的新想法, 从而扩大了思考空间。
5.3 重新构思“行动我”的场依性
前面曾讲过, 中国人战疫的灵活性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行动我”的“场依性” (field dependence)。其实, 有关场依性的研究一直是早年跨文化认知心理学中的重要一环。得到的结果通常是, 亚洲国家被试的场依性较西方国家被试强。为了免除测量工具因“文化”造成的差异, 研究者曾刻意地选用一些比较不受文化因素影响的认知作业为测量工具, 如在一些背景框框中找出主试给出的“样本”线条等, 来看被试会否受背景框框的影响, 给出较多的错误判断[46]这一类工具简称FLT (Field-Line Test)。有关这一测验本身带来, 对“场”的文化差异, 见Kitayama等人(2003)。。这样一个看似“泛文化”的简单认知操作, 后来也被指出是内含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场”的偏见, 认为“场”对人们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是一种“干扰”, 而不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见杨中芳, 2010)[47]见该文第28−30页的讨论。。在本文中, “场”被认为是协助人们找出适当的“行动我”的依凭及线索。因此不管未来对“格局我”、“差序我”、“运势我”或“阴阳我”的研究, 都应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探研、去发展研究工具。
5.4 探索“退”带来的灵活性
最近看到西方媒体的一个励志广告, 标题是:“我走得很慢, 但是我不会后退。”对西方人而言, “退”代表的就是懦弱。另外一个中国台湾企业的女总裁在接受访问时提到, 做任何事都先做“最坏的”打算, 才能让她有余地去应对各种挑战。“中庸行动我”的行动方案中, 含有有进有退、可攻可守的思想, 这是灵活性的一个资源。
杨中芳(2022b)曾指出, “退”代表的是一系列的行动锦囊, 可称之为曲线思维, 包括:(1)退——增大全息思维的时空; (2)让——唤启互动与保持心安; (3)忍——恢复冷静作理性思考; (4)等——蓄势待发; (5)绕——绕道超前; (6)避——躲过一时、等待转机; (7)放下——不被执着卡住等。
现有的本土心理研究中, 以对“退”及“忍”的论述及研究最多(例如, 黄囇莉等, 2008; 林以正, 2018; 林以正, 黄金兰, 李怡真, 2011; 林玮芳等, 2013; 林瑋芳, 2022)。李纾团队(Zhao et al., 2018), 将“让”字用郑板桥对“吃亏是福”的原解, 来反映“阴阳思维”及中庸“内外和谐”之运作, 并探研了它对中国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此类研究课题是向“灵活性”方向探研的窗口。
5.5 开发“中庸行动我”的新协调策略
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 中国的现代化带来许多新的、类似“大我、小我”的冲突, 需要作协调。过去认为合理的协调, 现在可能己经不再被大多数人接受了。例如, 在东京奥运期间, 又有人提出“让发挥得较稳定的队友赢, 以增加团队得第一的机会”的合理性。显然这一种协调, 己经不再为大多数人接受了, 人们及选手自己都不再认为这是一个会产生“内外和谐”的行动方案。那么, 还有没有什么协调方案是更能令现代人达到双赢的?这是考验“中庸行动我”的创新力的课题。
在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的两难困境没有上升到“国家我”的高度, 但是其复杂度可能更高, 需要更高超的协调技巧及创新能力。例如, 夫妻及双方大家庭的关系, 职业妇女的家庭我−事业我的双重压力、人际互动中的多方利益冲突等。有一些职业, 如庭内/外调解员、社区纠纷调解员、派出所警察、街道管理员等, 都可以是研究“协调”的资源, 提供更多的线索来找新的“中庸”之道。
5.6 连接中庸行动灵活性与创新行为及可持续发展
过去对“坚持”与“韧性”研究的构思都视它们为人格特质, 是人们最终能够战胜困难或成功的心理素质。但是如果从行动灵活性的角度来看, 持久努力以及所获得的成功可以是“中庸行动我”展现“随机应变”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48]邹智敏(2009)的一项探讨大学生坚韧性的认知来源的研究, 发现活在当下、摆脱固执、吃亏是福、知足常乐、阴阳思维及顺其自然, 是六大思维要素, 在遇到失败时将气馁转换成继续努力寻求出路的动力。。也就是说, 应变能力令行动者可以不间断地生存及发展下去。由“随机应变”所产生的持久性是动态的, 人们要不断地关注到新的形势的出现, 找出新的思考及手段来应对之, 才能向前迈进。
过去许多学者误认为, 由于中庸思维注重用“平衡与妥协”来解决矛盾, 因此减低了创新所需的碰撞, 两者应该呈负相关, 也确实有研究得到这样的结果(例如, Yao等人, 2010)。这显然受限于西方主流研究进路对“创新”的构想, 认为创新就只有是与原有状态呈“断裂式”的分离, 因此必须靠寻求刺激、特立独行, 来培养创造力。如前所述, “中庸行动我”是容纳改变、而不是封闭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理由推论中庸思维是阻碍创造力的发挥。也许, 用“阴阳协调”的角度来看创新, 会对中庸思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想法(杨中芳, 2022a)。
现在已有一些研究对中庸思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新的发现。杜旌等(2018)尝试将创新细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创新。发现中庸的“执中一致”价值取向对渐进式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49]“执中一致”是指的是个体与周围情境互动时保持一致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激进式创新则有显著抑制作用。张光曦、古昕宇(2015)研究了中庸思维与员工个人创造力的关系。发现中庸思维中的整合性与和谐性与员工创造力有正相关。反映了中庸思维是通过协调整合来创造持久的发展。杨海(2019)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另外一条线索。作者将创造力细分为两个面向:流畅力和独创力。在以实验法唤启了阴阳消长思维后, 被试在流畅力的表现上得分显着高于控制组; 在独创力上也较高, 但差异没有达到显着水平。这些结果显示, 阴阳消长思维有可能是通过“转念”产生较高的思考灵活性, 从而表现了较快、较有持续变化的创造力。
在这三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是, 创新的定义可以扩大, 加入渐进式的创新; 引发创新的动力, 也可以不由寻求独特及刺激而来, 而是由运用阴阳“转念”带出的思维灵活性, 或是如5.5所述, 为了协调现有生活中的两难困境而提出的新的行动方案。
5.7 中庸灵活性的培养
在本文中, 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应急灵活性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储存了许多的思维及行动可能性及可行性, 有如一个蓄水库, 在用时可以抽调出来应用。“中庸思维”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资源库, 提供应急时所需的灵活思考及行动协调。在现今中国的社会里, 对中庸思维的刻意培养己经成为古迹。但是它能扩大思维资源的功能, 还是不应被忽视, 可以通过“现代化”教学技术及手段, 让它成为培养思维灵活性的基本功。
5.8 中庸行动我作为人格研究的架构
这是本文作者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最重要的目的及寄望。在前面的论述中, 提到中国人“我观”的实践性、可塑性。“听其言、观其行”也一直是老百姓“看人知觉” (person perception)的重要依凭。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个体的行动来研究“人格”, 这一个用来理解个别差异的构念?
许烺光(Hsu, 1971)曾提出用“仁”的构念来把个体的个人面及社会面放在一起来刻划“人格”的建议。他认为个体协调自己的需求, 与和其一起生活中的他人对自己的需求的结果, 可以作为研究个别差异的重点。为此他还建议用一个叫“个体−社会动态平衡”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的构念来研究人格, 因为它能反映多层次的个别差异。最近周明洁等(2021)探研中国人人格中的“外圆内方”结构, 可以说是许氏理论一个展现, 顾及到了个人及社会两个层面的关注与协调。
这里要指出的是, “中庸行动我”的构想正与许氏的观点吻合, 它的“格局我”、“差序我”、“运势我”及“阴阳我”都置个体与其环境于一体, 来思考如何行动。上述“外圆内方”可以是中庸协调后的行动我。所以它可以发展成为未来人格研究可用的理论框架, 特别是有关应对危机灵活性的个别差异研究。
6 结语
本文沿用本土进路, 针对中国人处理COVID- 19疫情的速度及效率, 给出了一个新说法, 并提出一条探研中国人“我”的新构想——中庸行动我。
本土心理研究进路关注个体的社会实践, 试图在自身社会/文化/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当地人生活行动背后的意义。这次涉及全球的疫灾, 正好给了一个大范围、近距离观察人们实际行动的实验场。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展示本土研究的“正在进行中”。
由这条思考进路切入, 第一步是去用心观察老百姓的生活细节, 从中发现现象, 再提出问题, 再把它们变成研究课题。现今在全球逐渐走向两极化的时刻, 心理学脱离“移植、拿来”时代, 走向“自主研发”, 也算是顺应潮流吧!
所以本文写作的第二个目的在于, 增加对问题思考的多样性(叶启政, 2008)。作者认为, 缺乏多视角、多面向、多层次思考空间, 一直是当前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及缺失。
本文的第三个目的是想说明, 主流进路与中庸进路的互补性。沿用中庸进路的研究成果, 即可以是主流进路研究成果的一个补充; 也可以是在那些成果的基础上所做的, 对“文化−自我”关系更深入、细致的探研。
最后, “中庸行动我”的提出, 是把中国人“我”的流动性、灵活性及创新性作一个寻根式的巡礼, 作为日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是为了鼓励有志作中国人心理学研究的学子, 可以换一个“脑袋”来思考许许多多的研究课题。
致谢:感谢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张仁和提供资源、参考文献及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提供编辑协助及修改意见。
Bi, C. (2016). Norms and self-confidence: Perceived tightness- looseness and the doctrine of mean.,(1), 106−113.
[毕重增. (2016). 有规则才有自信:松紧度感知与中庸思维的作用.,(1), 106−113.]
Bruner, J. (19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D. T. (1979). Qualitative knowing in action research. In M. Brenner, P. Marsh, & M. Brenner (Eds.),(pp.184−209). London: Croom Helm.
Chang, J. H. (2010). Focusing zhongyong conceptualization on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big-self system.,(1), 145−157.
[张仁和. (2010). 聚焦中庸实践思维体系于心理空间与大我系统.(1), 145−157.]
Chang, J. H. (2021). Balance and harmony: Unpacking the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self-equanimity.,, 177−243.
[张仁和. (2021). 平衡与和谐: 初探自我宁静系统之特性与机制., 177−243.]
Chang, S. C., Chang, J. H. Y., Low, M. Y., Chen, T. C., & Kuo, S. H. (2020). Self-regulation of the newlyweds in Taiwan: Goals and strategies.(8-9), 2674−2690.
Chaturvedi, A., Chiu, C., & Viswanathan, M. (2009). Literacy, negotiable fate, and thinking style among low income women in India.,(5), 880−893.
Cheng, C. (2001). Assessing coping flexibility in real-life and laboratory settings: A multimethod approach.,(5), 814−833.
Cheng, C. (2009).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coping flexibility: A multimethod approach.471−493.
Choi, K. (2000, Apr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Social Sciences Concepts: Indigenous and Western, Taipei.
[蔡锦昌. (2000, April).. 东西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与”他者”学术研讨会.台北.]
Du, J., Qiu, Y., & Yin, J. (2018). Does zhongyong hamper creativity? An empirical multi-level study.(2), 378−384.
[杜旌, 裘依伊, 尹晶. (2018). 中庸抑制创新吗?——一项多层次实证研究.(2), 378−384.]
Du, J., & Yao, J. (2015). Zhongyong: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llectivism.(5), 638−646.
[杜旌, 姚菊花. (2015). 中庸结构内涵及其与集体主义关系.,(5), 638−646.]
Duan, J., & Ling, B. (2011). A Chinese indigenous study of the construct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e of Zhongyong on it.(10), 1185−1197.
[段锦云, 凌斌. (2011). 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结构及中庸思维对其的影响.(10)1185−1197.]
Dweck, C. S., Hong, Y. Y., & Chiu, C. Y. (1993). Implicit theori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likelihood and meaning of dispositional inference.,(5), 644−656.
Fei, X. (1947).Shanghai: Shanghai Observation Press.
[费孝通. (1947).. 上海: 上海观察社.
Feng, Y. (1940).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冯友兰. (1940).. 上海:开明书店.]
Gao, Z., Cai, H., Tang, G., & Xu, L.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ng-yong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symptoms.(9), 1298−1300.
[高瞻, 蔡华玲, 唐淦琦, 许律琴. (2013). 中庸思维与抑郁症状之关系.(9), 1298−1300.]
Gao, Z., & Li, B. (2014).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ngyong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205−220
[高瞻, 李炳洁. (2014). 中庸信念/价值与自评抑郁症状之关系的深入探讨.205−220]
Gao, Z., Yang, Z., & Li, B. (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outpatients and nonclinical people on zhongyong belief/value., 192−204
[高瞻, 阳中华, 李炳洁. (2014). 正常人与抑郁症病人在中庸信念/价值的比较.192−204]
Gelfand, M. J., Jackson, J. C., Pan, X, Nau, D., Pieper, D., Denison, E., Dagher, M., van Lange, P. A. M., Chiu, C., & Wang, M.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ightness− looseness and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A global analysis.(3), 135−144.
Guo, Y., Li, X., Huang, X., & Zhong, C. (2016).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efficac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s' zhongyong thinking-style and mental health.(1), 23−25.
[郭轶, 李雪晶, 黄新英, 钟婵. (2016). 抑郁症患者应对效能在中庸思维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1), 23−25.]
Hofstede, G. (1980).. Beverly Hills, CA: Sage.
Hofstede, G. (2001).(2nd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Hsu, F. L. K. (1971).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and Jen: 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1), 23−44.
Hsu, F. L. K. (1981)..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Hsu, F. L. K. (1983)..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su, K. Y. (2007). Chinese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 behavior associ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3−79.
[许功余. (2007). 华人性格与行为关连性的内隐理论及其对人际互动的影响.3−79.]
Huang, C. L., Lin, Y. C., & Yang, C. F. (2012). Revision of the Yang & Zhao’s Zhongyong Belief-Value Scale.,, 3−14.
[黄金兰, 林以正, 杨中芳. (2012). 中庸处世信念/价值量表的修订., 3−14.]
Huang, C. L., Chong, Y. J., & Lin, Y. C. (2014). Seeing tree or fores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perceptual processing and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49−65.
[黄金兰, 锺育君, 林以正. (2014). 见林或见树?——整体处理与中庸的关联性., 49−65.]
Huang, L. L., Cheng, W. J., & Hwang, K. K. (2008). Pathways toward voicing: Ren (forbearance)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vertical relations.,, 3−76.
[黄囇莉, 郑琬蓉, 黄光国. (2008). 忍的历程与自我之转化., 3−76.]
Huang, M., Tang, G., Yi, X., & Sun, S. (2014). Zhongyong thinking facilitates social adapt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flexibility., 88−112
[黄敏儿, 唐淦琦, 易晓敏, 孙莎莎. (2014). 中庸致和: 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作用., 88−112.]
Ji, L.-J., Zhang, Z., Usborne, E., & Guan, Y. (2004). Optimism across cultures: In response to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utbreak.,(1), 25−34.
Jullien, F. (2018).(L. Zhuo, Trans.).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5)
[朱利安, F. (2018).(卓立,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Kitayama, S., Duffy, S., Kawamura, T., & Larsen, J. T. (2003). Perceiving an object and its context in different cultures: A cultural look at new look.,(3), 201−206.
Lee, Y. C. (2009).(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wan University.
[李怡真. (2009).(博士学位论文). 台湾大学.]
Li, S., Liu, H., Bai, X., Ren, X., Zheng, R., Li, J., Rao, L., & Wang, Z. (200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of May 12.(3), 87−89.
[李纾, 刘欢, 白新文, 任孝鹏, 郑蕊, 李金珍, 饶俪琳, 汪祚军. (2009). 汶川“5.12”地震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3), 87−89.]
Li, Y. (2014a). The influence of job stressors on work-family bal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yong thinking.−
[李原. (2014a). 工作压力因素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 中庸的调节作用., 177−191. ]
Li, Y. (2014b). The influence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yong thinking., 184−194.
[李原. (2014b).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在职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184−194. ]
Lin, S. (2005).(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林升栋. (2005).(博士学位论文). 中山大学, 广州.]
Lin, S. (2014).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n-yang convertibility thinking and person perception.,, 78−88.
[林升栋. (2014). 阴阳转换思维与看人感知的关系初探., 78−88.]
Lin, W. F. (2008).(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aiwan University.
[林玮芳. (2008).(博士学位论文). 台湾大学.]
Lin, W. F. (2022). Forbearance in Chinese culture. In C. F. Yang & J. H. Zhang (Eds.),(Vol. II, Chapter 19). Wu-Nan Publishing Co, Taipei.
[林玮芳. (2022). 华人文化下的忍. 见杨中芳, 张仁和(编).(中册, 第19章).五南出版社, 台北.]
Lin, W. F., Deng, C. H., Lin, Y. C., & Huang, C. L. (2013). Stepping backward or moving forwar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i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45−84.
[林玮芳, 邓传忠, 林以正, 黄金兰. (2013). 进退有据: 中庸对拿捏行为与心理适应之关系的调节作用., 45−84.]
Lin, W. F., Huang, C. L., & Lin, Y. C. (2014). Timing makes a difference: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Zhongyong belief/ value and yin-yang convertibility belief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89−107
[林玮芳, 黄金兰, 林以正. (2014).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中庸与阴阳转折的时机., 89−107.]
Lin, Y. C. (2010, Apr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and Psychiatry: Multiplicity and Change of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林以正. (2010, April).国际文化精神医学会议: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及社会变迁, 上海.]
Lin, Y. C. (2014). Coupling hardness with softness: Autonomous compromises in Zhongyong.−
[林以正. (2014). 外柔内刚的中庸之道: 实践具自主性的折中原则., 221−235.]
Lin, Y. C., Huang, C. L., & Lee, Y. C. (2011). Stepping backward or forward: Flexibility of situated forbeara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57−100.
[林以正, 黄金兰, 李怡真. (2011). 进退之间的拿捏: 忍的情境变异性与心理适应., 57−100.]
Liu, S. C. (2000, April).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Social Sciences Concepts: Indigenous and Western, Taipei.
[刘述先. (2000, April).. 东西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与“他者”学术研讨会, 台北.]
Ma, P., & Cai, S. (2018). A cross-level analysis of motivation internalization of the effect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yong thinking.88−96
[马鹏, 蔡双立. (2018).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激励内化机制研究——中庸思维调节下的跨层次分析., 88−96.]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2), 224−253.
Peng, K. P., Ames, D. R., & Knowles, E. D. (2001). Culture and human inference: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traditions. In D. Matsumoto (Ed.),(pp. 245−26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ng, K. P., Spencer-Rodgers, J., & Zhong N. (2006). Naïve dialecticism and the Tao of Chinese thought. In U. Kim, K. S. Yang, & K. K. Hwang (Eds.),(pp.247−262). Springer.
Peng, M., Lai, P., Bao, G., Yang, Z., & Chen, X. (2016). The Zhongyong thinking characters of clients for family therapy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functioning.(2), 263−267.
[彭敏, 赖平妹, 鲍广林, 阳中华, 陈向一. (2016). 家庭治疗求治者中庸思维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2), 263−267.]
Ren, X., Bai, X., Zheng, R., & Zhang, K. (2009).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harmony., 85−106.
[任孝鹏, 白新文, 郑蕊, 张侃. (2009). 心理和谐的结构与测量.(1), 85−106. ]
Sampson, E. E. (1985).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dentity: Toward a revised concep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order.,(11), 1203−1211.
Sampson, E. E. (1988). The debate on individualism: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ir role in personal and societal functioning.(1), 15−22.
Schwartz, S. H., & Sagiv, L. (1995). Identifying culture- specific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1), 92−116.
Schwartz, S. H., Cieciuch, J., Vecchione, M., Davidov, E., Fischer, R., Beierlein, C., … Konty, M. (2012). Refining the theory of basic individual values.,(4), 663−688.
Spencer-Rodgers, J., Boucher, H. C., Mori, S. C., Wang, L., & Peng, K. P. (2009). The dialectical self-concept: Contradiction, change, and holism in East Asian cultures.(1), 29−44.
Sternberg, R. J. (1999)..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 C. R. (2014). Yin-yang reversals and extremity judgm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Yin-Yang thinking mode., 108−130.
[孙蒨如. (2014). 阴阳思维与极端判断: 阴阳思维动态本质的初探., 108−130.]
Triandis, H. C. (1987). Collectivism v. individualism: A reconceptualisation of a basic concept in 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 In C. Bagley & G. K. Verma (Eds.),(pp.57−89). London: MacMillan.
Triandis, H. C.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3), 506−520.
Wang, D. (2012)..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王登峰. (2012)..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Wang, D., & Cui, H. (2006). Chinese openness: Western openness personality dimension and Chinese personality.(6), 1−10.
[王登峰, 崔红. (2006). 中国人的“开放性”—西方“开放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的人格.(6), 1−10.]
Wang, H., & Zhang, L. (2018, Janua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Zhongyong Psychology Conference, Xiamen, China.
[王慧, 张灵聪. (2018, January).. 第五届中庸心理学研讨会, 厦门.]
Wang, M. Y., Lin, S. J., & Yeh, Y. Y. (2014). Emotions unexpressed: The influence of Zhongyong thinking on attentional and memory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stimuli.−
[汪曼颖, 林淑菁, 叶怡玉. (2014). 喜怒哀乐之未发: 情绪性刺激注意力与记忆的中庸思维体现., 18−48.]
Wang, Y. (2020). The identity modulation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self-esteem theory.(3), 185−192.
[王轶楠. (2020). 身份调和器理论: 一个新的本土化自尊理论的提出.(3), 185−192.]
Wang, Y., & Liu, J. (2021). The fusion of small-ego and large- ego: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s of syncretic self-esteem.(4), 568−575.
[王轶楠, 刘嘉. (2021). 让小我融入大我: 适恰自尊的积极心理学意义.(4), 568−575.]
Wang, Z.-D., & Wang, F.-Y. (2021). Ternary Taiji Model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elf: Centered on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 cultures.. doi: 10.1177/00221678211016957.
Webster, D. M., & Kruglanski, A. W.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6), 1049−1062.
Wei, Q. W., Han, Y., Yan, Y. T., Guo, Z., & Xu, R. B. (2019).The conclusion report of the project (14CSH038) supported by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China.
[韦庆旺, 韩悦, 鄢玉婷, 郭政, 徐如冰. (2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SH038) 结项研究报告.]
Wu, C. H. (2006). The nature of self-handling: Self-variation and self-certainty.,, 259−281.
[吴佳辉. (2006). 自我拿捏的本质: 自我变异与自我确定., 259−281.]
Wu, C. H., & Lin, Y. C. (2005). Development of a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scale.,, 247−299.
[吴佳辉, 林以正. (2005). 中庸思维量表的编制., 247−299.]
Yang, C. F. (2001a). Are the Chinese really collectivistic? An essa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e, value, and individual. In C. F. Yang (Ed.),(pp. 107−150).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01a). 中国人真的是集体主义的吗?——试论文化、价值与个体的关系. 见杨中芳(主编).(pp. 107−150).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Yang, C. F. (2001b). My search for the Chinese self. In C. F. Yang (Ed.),.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01b). 我的“自我”探索: 一个本土研究者的自述. 见杨中芳(主编).——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Yang, C. F. (2001c). Big-self and small-self: The Chinese view of self-other relationship. In C. F. Yang (Ed.),(pp. 365−404).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01c). 中国人的人己观: “自己”的“大我”与“小我”. 见杨中芳(主编).——(pp. 365−404).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Yang, C. F. (2006).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 Towards a person-making perspective of the self. In U. Kim, K. S. Yang, & K. K. Hwang (Eds.),(pp. 327−357). New York: Springer.
Yang, C. F. (2008a). Indigenization within mainstream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 F. Yang (Ed.),(pp. 161−186).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08a). 从主流心理学研究程序看本土化的途径. 见杨中芳(主编).(pp. 161−186).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Yang, C. F. (2008b). The study of Zhongyong action-oriented thinking mode: Toward building a new system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In C. F. Yang (Ed.),(pp. 435−478).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08b). 中庸实践思维研究——迈向建构一套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 见杨中芳(主编).(pp. 435−478).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Yang, C. F. (2008c, April).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eaching Committee and the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mittee of CPA, Guangzhou.
[杨中芳. (2008c, April).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和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广州.]
Yang, C. F. (2010). Multiplicity of Zhongyong studies.,(1), 3−96.
[杨中芳. (2010).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探讨的初步进展.(1), 3−96.]
Yang, C. F. (2022a). Zhongyong psych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F. Yang & J. H. Chang (Eds.),(Vol. I, Chpater 5).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22a). 中庸心理学研究: 起源、现状及展望. 见杨中芳, 张仁和(编).(上册,第5章). 台北: 五南出版社.]
Yang, C. F. (2022b). Maybe, we should try to rethink about how to study the Chinese?In C. F. Yang & J. H. Chang (Eds.),(Vol. I, Chapter 3).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Co.
[杨中芳. (2022b). 要不, 换一个脑袋来想心理学?——中庸思维作为一条本土进路. 见杨中芳, 张仁和(编).(上册, 第3章). 台北: 五南出版社.]
Yang, C. F., & Lin, S. (2014). What does Huang, Lin & Yang’s Zhongyong Belief/Value Scale really measure?, 159−77.
[杨中芳, 林升栋. (2014). 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到底在测什么?., 59−77.]
Yang, C. F., & Chiu, C. Y. (1997).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Symposium on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Taipei, May 29-31.
[杨中芳, 赵志裕. (1997).. 第四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研讨会, 台北.]
Yang, K. S. (2008)..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Co.
[杨国枢. (2008).. 台北: 五南出版社.]
Yang, H. (2019).(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heng-Gung University, Tainan.
[杨海. (2019).(硕士学位论文). 成功大学, 台南.]
Yao, X., Yang, Q., Dong, N., & Wang, L. (2010).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1), 53−57.
Yeh, C. C. (2008). The kneading exercis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An essay on indigeniz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 F. Yang (Ed.),(pp. 53−76).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叶启政. (2008).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搓揉游戏: 论学术研究的“本土化”. 见杨中芳(主编).(pp. 53−76). 台北: 远流出版中心.]
Ye, X., & Zhang, L. (2014). The effects of Zhongyong thinking mode on decision-making in different situations.8, 77−87.
[叶晓璐, 张灵聪. (2014). 中庸思维对不同情境决策行为的影响., 77−87.]
Yu, S. H., Lin, Y. C., Huang, C. L., Hwang, K. K., & Chang, J. H. (20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347−375.
[余思贤, 林以正, 黄金兰, 黄光国, 张仁和. (2010). 长期取向思维与心理适应之关联., 347−375.]
Zhai, X. (2018). Confucian-style self and its practice: A study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124−134.
[翟学伟. (2018). 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 本土心理学的探索.124−134.]
Zhao, C.-X, Shen, X.-C, Rao, L.-L, Zheng, R., Liu, H., & Li, S. (2018). Suffering a loss is good fortune: Myth or reality?(3)324−340.
Zhou, M., Li, F., Mu, W., Fan, W., Zhang, J., & Cheung, F. M. (2021). Round outside and square inside: The latent profile structure and adaptability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9), 1−16.
[周明洁, 李府桂, 穆蔚琦, 范为桥, 张建新, 张妙清. (2021). 外圆内方: 中国人人际关系性的潜在剖面结构及其适应性.(9), 1−16.]
Zhu, Y. (2007)..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朱滢. (200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u, Y., & Ng, S. H. (2019).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朱滢, 伍锡洪. (201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ou, Z. (2009). The hardiness of 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ts construct and influence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邹智敏. (2009).(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
Zhong-yong action self 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COVID-19 crisis management
YANG Chung Fang
(Center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is paper adopts an indigenous approach to explain why China can contain the COVID-19 Crisis swiftly and efficiently. For this purpose, it proposes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for studying the Chinese self—the Zhong- yong action self.
The action self refers to the self, activated by the situation an individual is facing, based on which the actor thinks about and decides the proper action to tak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beside the individuated self (the small self), many other more inclusive selves (the large selves), such as the family self, the community self, and the country self, are being mobilized at the same time, all of which demand the actor to exercise self-control and to help others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defeating the virus. This concerted effort thereby creates strength and flexibility in managing the crisis.
In every-day life situation, the many selves activated may demand conflicting actions from the actor. An adoption of the Zhong-yong deliberation process negotiate the most appropriate action, to help maintain inner peace and outer harmony with others and the flux environment.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new formulation will lead to new direc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elf.”
Chinese self, action self, Zhong-yong action self, Zhong-yong action deliberation, Ying-yang thinking, holistic thinking.
B848
2021-07-21
*本文部分论述是依作者在2020年5~11月期间, 通过“本土研究营”微信群, 每周发表的疫情观察, 共12篇。
杨中芳, E-mail: yangchungfang2@gmail.com; 现任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