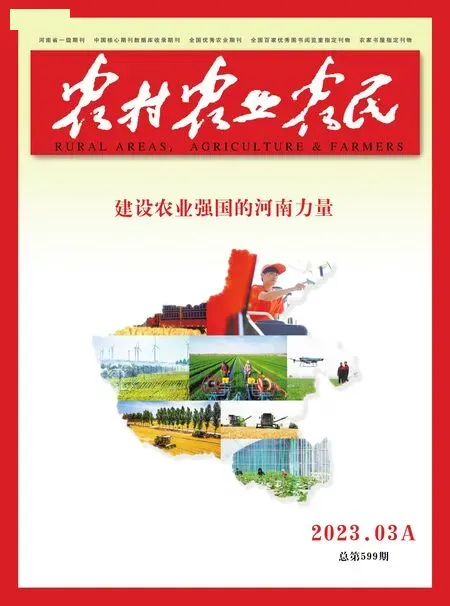以农耕成就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周 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在我国上万年的农耕实践中,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世界,创造出了许多杰出的农耕成就,铸就了中华文明不朽的精神标识。发掘提炼反映中华文化特质的杰出农耕成就,展示传承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既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的有益探索,也是扎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努力方向。
二十四节气
春华秋实,夏长冬藏,二十四节气揭示了天地运转互动形成的时间规律。它的魅力在于将复杂的天文、气象、物候等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教会每一个中国人辨认时间,形成了横跨大江南北、各民族都通用的时间标准。各地在二十四节气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践创作和总结出大量农谚作为配套,帮助农民把握天时、地利。首次采用二十四节气划分四季的《太初历》在公元前104 年启用,仅靠简易装置和肉眼观测,推算出一年为365.2502 天,与现代技术测算的结果仅相差0.008天,运行120 年误差不足1 天,从根本上保障了“不违农时”。《太初历》比西方古罗马的《儒略历》早了半个世纪,而且精度更高。二十四节气里有“天”,如小雪、大雪等气象;有“地”,如惊蛰、小满等物候;还有“人”,如大暑、小寒等感受,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观。因为农耕,中华民族在2000 多年前就掌握了时间的秘密,让我们在应对重大挑战和面对严重挫折时都表现出难得的历史感、从容感。
耕读传家
“耕读”不仅指的是白天种地,晚上读书,更有一边劳作、一边悟道的意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来都是打通的。我们以天地为榜样,在农耕中感知发现天地互动的经验规律,提炼升华后转化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准则。耕是物质收获,读是精神慰藉,构成了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于是有了“耕读传家久”的共识。家长久,国才安定,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秘诀。做任何工作都提倡读书修心,唯“耕”与“读”是绝配。传统上,中国人读书不仅为获取知识,更重培育德行。农耕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德育教化功能。以农为生,必须敬天地,按农时地利操作;孝父母,传承劳作经验;睦邻里,相互接济救助;俭用度,备灾年不时之需;勤四体,偷懒骗不了肚子,等等。“耕”与“读”形成了形于外、修于内的呼应,在农耕劳作中更能体悟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帝范·务农篇》载:“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返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因此,在历代科举制度中,从来都对农家子弟敞开大门,而对工、商、匠、兵者多有限制。许多以科举走上仕途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农民。乡村成为支撑传统社会赓续的人才蓄水池。
村落营造
安居才能乐业,无论在哪里从事农耕,不管是依山还是傍水,中国人都能就地取材营造村落,并与当地自然风貌融为一体,不仅能遮风避雨,还富有审美情趣。村落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居住形态、组织形态,唯有中国人把村落的精髓完整传承下来,并带到了现代社会。传统观念里,城市仅是异乡漂泊的寄宿和飞黄腾达的跳板,唯有村落才代表了安全和归宿。在传统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在村落中出生、老去,出相入将、巨贾富商大都会选择叶落归根,把一生的财富、知识、声望、理想带回到村落,沉淀凝结下来。村是家与国重要的连接和过渡,既是共荣共生的“大大家”,也是自立自足的“小小国”。村落里不仅有民居,还有戏台、广场、宗庙等公共设施;不仅有建筑,还有生活中必备的各种技艺如酿制、编织、缝纫、印染等,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传统社会,村落营造主要靠互帮互助完成,过去的农民几乎是全能的,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变身瓦工、泥匠和各类手工艺人,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设自己的家园。我国已经认定了6819 处国家级传统村落,再加上省市县的认定,总数多达几万处,是中华文化的“实证”和“活证”。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传统村落保有量最大的国家,每一处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情感。
造田垦殖
农耕可以狭义理解为“为了获取热量,以生命体为对象的劳作”,采集、渔猎、游牧等都属于农耕。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种植活动是农耕的高效方式,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可以更稳定地传承发展文化,“土地就是命根子”的观念才会根深蒂固。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天然适宜耕种的土地并不多,“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许多地方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南北水土分布极不均匀,南方水多缺土,北方水少有土,中国农民因地制宜创造了各种造田方式。在水大的地方,通过水田、垛田、圩田、架田、高畦深沟、桑基鱼塘等方式,把水患之地变成旱涝保收的福地;在山多的地方,通过梯田、淤地坝等方式,增加耕种面积,并通过优化山顶、山腰、山底的功能配置,维持生态良性运转;在缺水的地方,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并采用砂田、区田等方式,解决保墒、保肥的问题;甚至在沙漠中,也能开凿坎儿井造就片片绿洲。面对盐碱地,中国人创造了一整套办法进行改造。农民在田块上开沟起垄,形成耕、耙、耢、耘、耥等耕作技术体系,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造田垦殖不仅没有破坏生态,反而成为生态增益的良性举措,形成了独具美感的田园景观。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天人相参,从来没想着要征服自然,总是顺势而为、应时而作,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适应中生存发展。因地制宜的造田垦殖就是践行生态文明的典范。
辨土肥田
人类社会的早期种植业都是从刀耕火种起步的,面临着土壤退化、生态恶化的问题。土地产出不稳定,会带来间歇性粮食危机,加剧部落阶层分化;频繁弃耕迫使不断迁徙,也会激化部落间矛盾,带来战争、奴役等。幸运的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找到了解决之策。汉代的《氾胜之书》详细记载了如何辨土肥田,使之“精熟肥美”。宋、元、清的农书对此也多有记述,成为农业生产的核心技术。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畜粪尿、秸秆、陈墙土、灰烬等生产生活废弃物进行发酵腐熟等处理形成肥料,根据土壤特性施用以增强地力。这项技术得到了广泛持久的应用,粪便等不再被嫌弃,而是用心收集起来,乡村再无废物,人居环境变美了,疾病传播被阻断了,健康文明从此起步。“粪是农家宝,种田少不了。”生长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几乎所有人都有拾粪的经历。到20 世纪末,在中国农村还能随处看到农民用腐熟人粪尿施肥的场景。中国的土地越种越肥沃,被一些西方人称之为奇迹。辨土肥田作为一项养地措施,能够被全体中国农民所掌握,传承到今天也是奇迹,而且它深深地嵌入到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更是奇迹。辨土肥田的实践将辩证思维方式和循环生态理念深深地根植到中国人的心底。变废为宝,香变成臭,臭也能变成香,这是辩证法最生动的实践诠释,所谓“道在屎溺”中。人立于天地间,既要索取生存资源,也要回馈涵养自然。我们以辨土肥田的方式参与到了自然生态循环当中,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部分。
驯化嘉良
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当前国内广泛栽培了840 多种作物,其中有一半原产地在中国。中国先民很早就有意识从自然界驯化选育优良品种。丰富多样的地理气候条件,为我们驯化和培育良种提供了丰富的生物基因资源。距今7000 ~8000 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用狗尾草和野生黍,培育出最早的人工种植农作物——粟。夏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形成了“嘉种”的概念,认识到“母强则子强,母弱则子病,择种不当,贻误岁计”。根据春秋时代的《周礼》记载,国家专门设置了司稼官员,组织品种选育并定期公布品种的适应性,指导各地选用良种。当时已经有了杂交育种,能够选育出作物的晚熟品种和早熟品种,动物杂交技术也比西方国家早1600 年。受到连理枝的启示,汉代发明了嫁接技术,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不同种类果树嫁接的方法。清《授时通考》中,记载了小米品种500 多个,水稻品种3429 个。中国人巧妙利用了自然变异,以人的需要引领作物进化方向,形成简便易行的良种选育方法。现在,仍有不少地方农民保留着自选自繁自育的习惯,有的民族将良种稻穗作为登门结亲的伴手礼。优良品种选育贯穿了中华农耕发展史,至今仍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核心。许多传统良种传承上百年,性状不退化,在稳产性、抗逆性、适应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值得现代种业学习借鉴。
物种引进
中华文化始终坚持包容并蓄,主张吸收借鉴一切外部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先民从世界各地引进农作物新品种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引种需要智慧,更要胆识,要解决长途运输保温、保湿的难题和本土驯化的技能,还要克服层层关卡的磨难。据不完全统计,自先秦到晚清,中国从域外引进粮食、蔬菜、水果、饲草、花卉、药植和林木等各类植物物种300 多种。外来物种的引入直接对中华文明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4500 年前,小麦传入我国黄河中下游,逐渐成为旱作的当家作物,强化了北方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引入越南的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推广,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继而推动中华文明重心向南迁移。明代引入了番薯和玉米,带动了山区经济繁荣,明清600 多年间,中国人口连续跨过1 亿、2 亿、3亿、4 亿大关,与这些引入的高产作物有直接关系。胡、番、洋、西代表了不同时期对外引入良种的取名特点。萝卜、白菜原产中国,我们各有偏爱;胡椒、番茄、洋葱、西兰花等引入物种,现在三餐也离不了。这些外来物种很好地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我们常说五谷、五味等概念内涵也因为引入物种而不断改变。当然,中国农业物种和技术对外传播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著名的稻米之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都是文化与技术交流的见证。这些都证实,开放性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和主动选择。
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是中华农耕实践的突出特点,也由此锻造出中国人勤劳的品性。唯有“勤”,才能在大量的农耕实践中发现、总结和利用生物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唯有“勤”,才能弥合人与自然的生存矛盾,摆脱“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在不伤害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取得更多收获,满足自身需要,实现与自然相生相伴。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和光温资源,农民采用间种、套种、轮作等耕作制度,水稻-小麦、小麦-玉米等轮作方式现在依然常见。中国是最早利用豆科植物固氮增肥特性的国家,现在仍普遍采用大豆与粮食作物轮作、套种来增产和维护地力。在农牧交错带,采取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的农牧交错生产方式,生态脆弱地区也长期维持了生态平衡。为了克服病虫草害,巧妙利用了生物间捕食、寄生等关系。在晋代,人们已经总结出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方法,成为世界上利用天敌关系防治果树害虫的最早记载,实践中还有放鸭防虫除草、蛛蜂防虫等多种方式,利用中草药防治动植物病虫害的“中医农业”。复合种养代表了精耕细作的最高水平,将人类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如稻鱼共生系统,在稻田里养鱼,水稻为鱼提供了活动和庇护场所,鱼可以吃掉水稻上的害虫,还能活化水体增加氧气,互惠互利,一块田两样或多样收益,将勤劳汗水转化出更富足的生活。
乡村礼俗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在于设计了两条传承路径,一条是文字,不管是记录在书籍或是附在实物、技艺之上的,是有形的文化;另一条则是行为,我们的祖先把世代奉行的理念、准则掰开揉碎,将抽象的“大道理”场景化、行为化、大众化,以节庆、礼仪、规范、曲艺等方式融入日常生活,转化为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是无形的文化。中国近代以前,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农村,不识字,乡村礼俗的教化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乡村,每一个人都有家规家教家风护身,从生到死的人生大事都有礼乐安排,一年四季重要节点都有节庆相伴,潜移默化地把生物人改造为能够承担责任的社会人。尽管以前农民大部分不识字,在乡村礼俗的浸润下,每一个人都被注入了文化基因,都是文化火种。日用不觉,知行合一,身心一体,化有形于无形,乡村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更强的生命韧性。我们常讲“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乡村礼俗适应了不同风土,各具特色,但在文化内核上却高度统一。最妙的是我们还有“移风易俗”这一招,不断地矫正乡村礼俗与文化发展方向背离的部分,做到了常用常新。
乡规民约
乡规民约为乡村自治提供了显性化的制度载体。虽然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乡规民约来自宋代的“吕氏乡约”,但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的周朝,至今仍是国家治理的根基,被宪法所保护。我国的乡村自治经过几千年实践,在明清时逐渐完备。乡规民约的制定、实施已经不简单是当地村民的自发共识,而兼具历史、道义、民主合法性,并得到官方认可,在区域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违背会受到来自村民、社区、政府等多方面的压力,对个体的约束更好地保护了村落集体利益,增强了村落的内聚力。乡村自治适应乡村地广人稀居住特点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体系,培养了中国人自力更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个体太渺小,家庭也不足以对抗灾害,只有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才能与天地对话。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共同体,依靠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实现长治久安,锻炼了中国人最底层的自立意识。乡规民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出入相友、礼俗相交、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与现代社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内涵高度契合,为传统村落进入现代文明打开了通道。这些杰出农耕成就涵盖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每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息息相关,满足了广大农民安身立命、婚丧嫁娶、社交祈福、情感慰藉、身心健康等物质和精神各方面需要,形态多样、各具功能,有着三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它们所包含的技术、规范、习俗、礼仪、制度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的乡村实践形态,没有深奥道理和华丽辞藻,只有日常劳作和起居生活,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传承体系。二是它们是在长期农耕实践中逐渐形成并持续完善,没有明确的发明人或设计师,是像庄稼一样在乡村大地上长出来,每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都用汗水、泪水浇灌过,是历代中国农民的集体智慧结晶。三是它们穿越历史洪流来到现代社会仍保持着生命活力。在许多村庄,传统农耕的印记随处可见,不仅基本保持了原有形态,功能还在不断丰富,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恒久的价值。实践性、大众性、活态性既是这些农耕成就的共同特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历史悠远、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农耕是其最重的“底色”。“农”是先天之本,“耕”是后天之力。“农耕”既是生产方式,更是生存之道。这十个方面的杰出农耕成就是我们理解我国“三农”问题、发现乡村多元价值的重要窗口。我国已认定的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集中代表了这些隐匿在乡村生产生活日常中的杰出农耕成就。走近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追求、道法自然的智慧、守望相助的风尚、勤劳朴实的性格、崇根敬祖的情怀、自立自强的气度,就会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