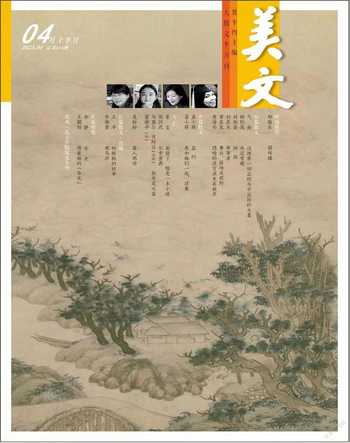隔壁传来的嗓音
[法国]马塞尔·贝阿吕
船上唯一的主人
我站在一艘大船的驾驶台上。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我看不见他的脸。船速有些超自然,那样的速度载着我们一路向前,我对那个人大声叫喊:“停船!停船!”我听到他回应:“你是船上唯一的主人。”这句话顿时让我惊慌失措,我们的船进一步增速,我绝望地朝四面八方观望。我怎样才能中止这场令人眩晕的竞赛呢?船骨犹如鱼雷一样滑行,仅仅在水面掠过,给我的印象是,只要稍有移动便会让我们倾覆。在某个时刻,随着我的目光在波浪上漫游,我看见浪峰上显现出人头。这片辽阔的水域是由上百万张扬起抛向无限的面庞所组成的。然后,我心怀恐怖地想到,我们盲目地飞速行驶肯定会撞坏并吞没那些面庞。然而,我也依旧心怀恐怖地意识到,通过打破那载着我们一路前行的平衡,要停下来甚至是减一点速,都会把我们抛进那一簇簇被淹没了身子的人头当中。“停船!停船!”现在颇有讽刺意味地轮到那个嗓音大声叫喊了。为了不去看我们将要不可避免地撞上去的礁脉,我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我听到我的嗓音犹如回声一样回应着这个影子:“我是船上唯一的主人!”
最后一班地铁
车厢慢慢空寂了起来,在每个站点卸下更多一点它所运载的人类货物。我站在一个白日梦中,眼神迷失于一张张脸上。然而,坐过站的感觉把我从那种恍惚状态中唤醒,我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就在那时,我突然完全彻底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趟地铁再也不会停下。这盲目的列车载着意外的货物,沿着任何地图上都不曾标注的一条路线前行。我再一次看着那些脸。要是我不知道它们真正漠然的话,我就会相信,在这些不承认自己知道正在进行这场历险的匿名乘客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领悟。最后旅程的伴侣!……毫无疑问啊!……没人给我选择:他们困倦或失败的脸上没有露出明显的预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交谈,但他们的嗓音流露一种察觉不到的细微差别。一个秃顶的胖子断然声明他的烹饪偏好:“你能在哪里找到上好的鹌鹑?在阿尔巴尼亚!”两个额头过大的孩子位于一个女人的两侧,那个女人疲倦地点点头,而另一个较老的女人则在她的前面喃喃低语:“我告诉过你,你一生都要抚养尸体……”距离这可怜的一家子两步开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动了动她那松弛的、涂绘过的嘴唇,仿佛她嘴里含满了苍蝇。突然,一个衣着寒碜的人站了起来,举起帽子,故意做出一种讽刺性的致意,用最大的声音嘲笑:“前往地狱的乘客们,上车了!……”这些话并未引起騷动,那个人重新坐下,再一次捂住他那张鬼脸。短暂的一刻之后,一个脸颊粉红、身着弄皱的老处女服装的大个子女孩,倾过身来向我坦白,说她在孩提时代就从公墓中偷走了一件小小的瓷花瓶。但这些话真正带着疯狂,并未阻止车厢那单调的声音一刻——在那条漫无休止的钢轨上,一节节车厢滑行得越来越快。
桥
有一座将要跨越的桥。彼岸就在那边,隐藏在一片从激流中显出的浓雾里。在这乳白色的屏障上,两个高高的、一动不动的哨兵显现出轮廓,仿佛他们自己就穿着雾霭的斗篷。一想到要对抗这两个卫兵,我就害怕得浑身冒汗,当我走近他们,他们也许会具有威胁性,不管怎样,我都无法回避他们的提问。“你从哪里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会问。
我转身,仿佛这个问题确实在我的耳朵里响了起来。在我身后,是我走过的一条条路、一个个地方和一座座城市,那么多,因此我根本无法用几句话就描述出来。我从哪里来?从生命的夏天而来,从快乐的四肢伸展,身体变得健康的暖和的草甸而来。万物真的都在那种明显的静止下逃逸了?我们真的消逝吗?突然,你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封冻的平原边上,那里将被黑暗吞噬,被雾霭团团围在两个威胁的卫兵之间。“你从哪里来?你干过些什么?……”
现在,这座将要跨越的桥就在那里,这唯一的桥横跨在激流上,朝着一片无形的河岸而延展。另一个卫兵,甚至会用更可怕的嗓音说:“你到那边去干什么?”因为这座桥是边界,彼岸是另一个世界。为了从这边到那边,我不得不对抗那两个哨兵,而他们跟雾霭和夜色越来越融为一体。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怎样说明我想到那边去干什么呢?
我就这样跟自己沟通着,走近那座桥的起点,很快就发现自己距离那两个哨兵只有两步之遥,他们的黑色轮廓扩展,他们纹丝不动的身影开始让我安心下来。他们不就是石头雕塑吗?我的害怕大错而特错!无疑,担心另一边甚至就更加错误了。当我在这种新获得的勇气的影响下,一路轻松愉快地前行之际,雾霭突然就散开了,让路给繁星满天的夜晚,而当我一跨过那座桥,幽灵们就前来迎接我。

好理由
隔壁传来了阵阵嗓音!为了听得更清楚,我披上睡衣起床,把耳朵紧贴在墙上聆听。隔壁酝酿着何等的密谋!机会想要我从如此荒诞可笑的位置上,用耳朵去见证何等戏剧性的事件!当我听到我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我就想到迅速穿上衣服,跑出去警告他,但此时已经时过子夜,那位朋友住在很远的地方,于是我就找到好理由,让自己相信这事与我无关。第二天夜里,我再一次坚守岗位聆听。这一次,隔壁的阵阵嗓音提到了我的兄弟的名字,这名字犹如子弹一般射回来。我应该赶快跑去报警。然而,谁又会相信如此泄露的事情呢?我把耳朵紧贴在墙上偷听别人谈话,难道不是我的错吗?是的,因为我得知我无权得知的事情而有罪,难道我不是更有罪的一方?于是我决定什么也不说,无论隔壁传来的嗓音谈到的事情可能多么令人惊讶,我都要守口如瓶。尽管如此,我从晚上一直睡到黎明,深受到那种可怕的好奇心驱动。当我听到针对我最亲爱的人的神秘阴谋的策划升级,我的心就开始收紧。那些嗓音提到我的兄弟之后,又提到了我心爱的情妇,然后还提到了我多么爱的小妹妹!针对他们每一个人命运的密谋都安排好了,而我却没有迈出一步去开口说出实情。然而,就我在那么多罪行中都有同谋嫌疑来说,我的羞愧感便油然而生。如今在墙上敲击会有什么好处,叫喊谋杀会有什么好处。我知道,我知道!那不会是把我自己的邪恶展现给世界吗?最后,当我听到它们通过了对我自己的判决时,夜幕降临了。我认命了,已经被击败,筋疲力尽,让自己倒回到床上,把脑袋埋在毯子下面,挡住隔壁传来的阵阵嗓音。
渴望鸟儿
我的塔是一座被水域包围的灯塔。作为它死去的灯和破镜前面无用的观察者,我有时会透过死者的灵魂居住的不透明的深处,看得见一艘船侧有洞的巨型轮船,停靠在粉红色水泡的底座上。我生活在那里,远离夜晚也远离白天,在风暴和拍岸的碎浪下面一千多尺之处,被掩埋在沉默中,掩埋在那从不曾敲响时辰的闪烁的影子中。我的心被记忆的空缺所照亮,有时我会逐渐开始把我那些奇异的沉思默想放弃给它们自己的存在方式。横跨在铜楼梯井两边,我以一条螺旋线走下狭窄的楼梯,抵达我那苍白的、我那温柔的少女的潮湿的居所,那里的软垫上镶嵌着活珍珠。她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她的嗓音就像生长在沙里的花。然后,就像尘世间的情侣纠缠在一起,我们重新无声无息地走上去。成千上万闪光的鱼,在星星般巡视的魔幻圈子中环绕我们的爱。一些鱼游来,把人形的嘴巴粘贴在窗玻璃上,或者露出充满死去的野兽表情的圆眼睛。然而,当它们的鳍掠过我们的玻璃墙,我们就稍稍紧紧拥抱,以免听见我们内心响起遥远的翅膀拍击声。
快乐的笔
有一天,那些吵嚷着要求表达的念头汇集成了一股洪流,根本不顾我的存在,几乎把我卷走,我的笔发出的单调的擦刮声渐渐变成了低语,声音逐步大了起来,开始跟我思想的喃喃声不愉快地混合。说实话,也许我的笔经常不经我的授权就这样闲聊,但由于我依附于我的句子和谐的展开,不允许我分心片刻去听它的语言。停下写作,就很容易让那两个不和谐的嗓音立即中断,但尽管我是直接原因,那个不该我负责的嗓音,太让我感兴趣,因而我不想让它沉默。
当我的笔越过纸张而奔跑,它现在就哼着什么,就像是在哼唱讽刺小曲,因为它那个让我全力应对的生活及其阴暗面的严肃性主题,那哼唱愈加刺激我。最终,为了与这种娱乐达成一致,我试图转录这支沉浸于雄辩的笔的嘲讽性闲聊。然而,我立即就听到了只有一种单调的擦刮声。因此,我恢复了那支小小的嘲讽之歌。那并不意味着没有听到它。天知道,自从那时起,它单单是为我的启迪就涌现出了何等的精神错乱!
黑暗的第六道墙
那在我的睡梦中对我谈话的嗓音。在白天的边缘上,当临近的钟楼响起奉告祈祷钟,把它青铜的嗓音的锤击如雨点一般落在我的睡梦上,我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因此晨鸟飞离落魄的山峦。但我因为无法界定它,无法重新捕获它,就感到了一种无法容忍的莫名的不安。那就像墙后传来的一声未知的呼唤,一条你无法自信地查明其起源的电话消息。当你试图理解那些话语,你就因为寻找意义而精疲力尽。然后,这同一种莫名的不安就消失了,不再有关于夜间消息的问题。我再次被那台机器缠住、掌控,处于那写下叙述的拨号盘的监狱中,而且,根据同化作用的法则,跟喋喋不休的人喋喋不休,跟撒谎者撒谎,跟小偷偷窃。整天都是电话、来访者、朋友。因此,在这样的喧嚣中,尝试集中精神,哪怕片刻也行。没有考虑傍晚,孩子美妙地唠叨,还有可爱的小情人可爱的叽喳声。在这无益的干扰中间,在这令人愉快的折磨中间,只有回忆的不可能性。我有效地抵达了黑暗的最低一层,越过黑暗的第六道墙:面向所有的来者打开的门,被幼虫生物捕食,在一个虫子麇集的立足点上,优柔寡断成为规范,妥协成为法则。我的专业活动、友好交谈,我的孩子讨人喜欢地出现、我的欢乐甚至我的愉快,一切都变成了一团原料纤维,窒息那从我存在的中心发出的一声叫喊。
门 闩
我本来应该对所有的眼睛展现我们全新的幸福,就像富有的贵族遗孀展现她们的珠宝,就像电梯操作员展现他的傲慢,就像单身汉展现他们裤子上的皱褶。但我们几乎不关心具有童话之光和焰火的蜜月。我和我娇小的妻子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每天傍晚匆匆上楼,走向我们的房间。
从最初的那个夜晚,我就突然发现了她不安的睡梦。有一次,我惊醒过来,发现她不在我身边,便在过道上赶上了她。由于这些危机让我非常担忧,我就打算阻止它们带来的影响,便在门上又安装了一把锁。这完全是白费劲儿!她的神经的状态赋予她一种预见力,而那种能力只有在她醒来之后才会离开她。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锁能让她找不到钥匙呢?还有一次,她穿着睡裙在楼梯上游荡,我不得不把她从那里带回来。
我担心她可能找到通往赌博场所的路,或者在过道上遇到危险,便求助于唯一有效的补救方法:我在門外加装了一根门闩。一旦我的妻子合眼睡觉,我就默默地穿上衣服出去,把门闩上,不幸的是,这样做就把我关在了外面,一直到清晨。但从此以后,当我回到床上,我都发现那个流浪者在深深地熟睡,这就让我免于承认我采取的安全措施的必要性、穿过灯火通明的房间久久漫游——唉,在那些房间里,我现在仅仅展示我闷闷不乐的表情。
到了黎明时分,当她看见我在她那漂亮的脸蛋上俯下身来,那个囚徒便想象我也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在每天晚上都分开,而我是唯一知道的人。
泪水之杯
从我的房间,我观看在早晨的太阳下环绕那座老教堂的队列。当天使般的嗓音汇聚的合唱朝我升起,我就感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于是我偷偷弯起食指,想去拭掉那我以为不过是一颗泪水的东西——为什么心有时候竟会这样融化呢?——但我注意到我的眼睑充满一种液体,从我的眼里喷涌而出,直至流下我的脸才停止。我从壁炉架上迅速取来那个水晶杯,几分钟之内,这股洪流在流干之前就盛满了那个杯子。我立即想起我必须去买一束睡莲,就是每个星期天,那个颤抖的老头都要在教堂门廊给予路人的那种花。我拿着那些就像是装备着青铜铠甲的白色之心的花朵,回到房间,把水生的梗茎剪成恰当的尺寸,插在那个杯子里面。那些花接触到从我自身流出的这种液体,我必然称之为我的泪水的液体,便像大甲虫慢慢张开了深色的萼片,然后张开白色的花冠,依次展现雄蕊的金色纺锤体。同时,它们不停地生长,一直长到从杯子中满溢而出,充满整个房间。现在,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这种在我四面八方继续移动的植物之中,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变成巨大的白帆,每一根珍奇的花粉之茎都是振动的金色管子,音乐从那里逸出,起初温和,但后来不断膨胀,直至变成一曲庆祝凯旋的圣歌。在那片歌唱的花朵的基座中央,一队白色和金色的大天使,仿佛以一种好像绝不需要结束的上升动作来运送我。
(责任编辑:庞洁)

马塞尔·贝阿吕(Marcel Béalu,1908—1993) 20世纪法国著名奇幻作家、诗人,早年与立体主义诗人马克斯·雅各布过从甚密,时常交流文学经验, 但主要靠自学成才。他的作品主要有《体验夜晚》《死者日志》《半睡半醒间的故事》《无人称的奇遇》《大潮》《磨坊的喧嚷》《业余猜谜爱好者》《生者》《1936—1960年诗集》《1960—1980年诗集》等多种。其作品想象独特,充满奇幻色彩,在20世纪法国文坛上具有不小的影响。

董继平 重庆人。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四届普利策奖得主作品译者。少年时代开始文学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向文学翻译,在国内多家文学期刊上主持译介外国诗歌。获得过“国际加拿大研究奖”;参加过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作家班,获“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担任过美国《国际季刊》编委。译著有外国诗集三十余种,自然文学及散文集二十余种,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秋色》,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鸟的故事》,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山野考察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