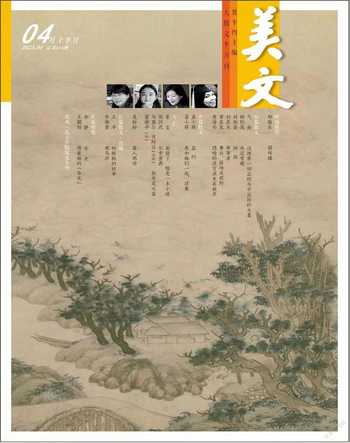洄游
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鱼类有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叫洄游,这是一种有规律的往返迁移,贯穿着鱼的生命始终。我的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从家到学校,再回到家;从西安去别的城市旅游,再回到西安;从冬天游到温暖的春天里,再回到最熟悉的雪地……剥落旧的外壳,再一遍遍洄游到过去,周而复始,好像一直都在原地,又好像是绕着这个原点画了一个又一个的圈,但就像有些洄游的目的和路径并不一样,每圈和每圈也是有所不同的。也许这种圈跟树的年轮一样,也是生命的一种行进轨迹吧。
我喜欢冬天,要是谈到我的冬天,就必须谈冬天里的树。在北方,最常见的树在冬天都脱了枝叶,光秃秃的,直指着天空,那姿态有时候是一道优美而流畅的曲线,是美人低头时无意间露出的一截雪白的脖颈;有时候是戛然而止的,是生硬的,是文人嘴下冷峻的纹路。它的树枝是国画里最经典的鹿角的画法,每处枝节的拐角,都是笔墨停顿手腕用力的一笔;它的树干也不需要点苍,自然布着岁月的霉点和风沙的刮痕。这是我现在最常见到的树,不过,以前的树是不一样的。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操场旁种了很多树,只有到入冬的时候,树叶才真正大片大片地往下掉,给人一种迟到的秋的错觉。铺在地面上厚厚的一层,刚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落叶底下就发出些簌簌的声音,好像惊扰了鱼的美梦,然后这些声音开始在脚下飞快地游动起来,脚的触感变得绵软湿滑,惹人发笑,止不住的快乐从脚底往上窜。要是积了厚厚一层雪,脚下的世界就更丰盈了,一个脚印下去,身子就往下一陷,雪是坚实的,地面是湿软的,好像踩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要是世界颠倒过来,我猜鱼在水里游的时候,看到水草和漂浮的树枝可能也会觉得那是树吧。
我和我的朋友就像思琪和怡婷,我们爱文学,雪就是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雪填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用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天马行空的修辞填满冬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往人潮的反方向走,在喧闹的人群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却又和别人迥乎不同。有时候笑着闹着,有时候则肃穆着赶路,我们有要紧事要做。走进操场,世界骤然间就安静下来了,树干上贴着便签“这是雪国”,肃立了一会儿,屏息凝神地往里走。我们步子迈得轻,可每一步落下,脚下还是会发出雪被压实时“吱呀”的碎响,有声音的人走进了没有声音的世界。
雪地在月光下格外地亮,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明明走在操场上,我们却好像顶着风雪,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雪地荒原上,有时候亦步亦趋,有时候相互搀扶着,心里有只火炉噼里啪啦地烧着。为了排遣赶路时的寒冷和寂寞,我们常在手里攥上一小团雪,一遍遍地把它握紧,压实,等到雪球完全变成一个坚硬的冰球,手心变得滚烫起来了,我们就立马把它往火炉里甩去,加上一把炭火。慢慢地,雪下得越来越大,覆盖了所有声音,我们没有任何顾忌了,卸下了所有的戒备和包袱,我们变回了两棵树,变回了雪花电视机里的两个噪点,变回了最纯洁最无知的孩子。我们在雪地里又跑又跳,然后猛地扎进雪地里打滚,然后以坠落的姿势仰面倒进雪地里——雪地是猫咪腹部紧绷而柔软的触感,或者说,来摸摸我的心吧,也是我抚摸猫咪时心脏的触感,一戳就陷进去一个小坑,然后慢慢地回弹。
躺在雪地里看着天空,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小片湖泊。天真的好黑啊!书上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眼睛是纯正的黑色,我以为自己就是那一小部分人,还为经常收到的关于头发和眼睛乌黑的夸奖感到窃喜,后来发现我的眼睛在阳光下是隐隐的红棕色,头发也是,不过我并不难过,转头又为这独特的另一面感到骄傲去了。酥麻的寒意像鱼一样游过了身体的每个角落,但是湖水始终没有结冰。
这时候的天空是我从前的眼睛,一朵朵雪绒花从无垠的黑色里缓慢而坚定地落下来,像一曲悠扬的牧笛。哼着、唱着,我们交错的视线和树的枝桠拉成了歪歪斜斜的五线谱,雪下大了,从五线谱里纷纷地落下来,变成了无序的音符,在深夜里缓缓地游荡。压在树冠上,树白了头,以一种果实累累的姿态虔诚地俯下身子;堆在树枝上,树枝成了一段莽黑的山脊;撞到树干上,就“叮”地一声磕掉一块树皮,露出一小块白色的芯,像刺猬的肚子一样在寒风里瑟缩着。我的一部分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被磕掉了,永远地留在这个雪夜,深埋在柔软的雪地里,等着我一遍遍地洄游。
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两棵在霜风里并排立着的树,时不时笑得乱颤,叶子簌簌落满地,笑累了,就靠在对方身上歇一会儿。鱼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两颗纽扣般的小眼睛,在水面上吐泡泡的声音也是铁板上滋滋冒泡的声音。有些鱼很神秘,像鰻鱼,年幼的时候就要经历一场长达多年的旅行,从马尾藻海游到淡水去,等到成年了,再循着这种在幼年时就深入它们身体的大海的气息游回海洋。
为了考上好高中,妈妈给我找了更好的补课老师,不过那地方很偏远。上完课的时候,我们赶着公交车回来,车里人很少,也没有人说话,在一整首小夜曲里,只有车厢慢慢悠悠晃荡的声音,不断碾过松动的井盖、落叶和一些细长的车辙。因为路远,我们不用盯着还有几站下车,不用去想是把中午的饭热一下还是煮个泡面,不用赶作业收拾第二天的书包,在这个车厢里,强势的母亲和倔强的女儿疲倦地靠在一起,女儿的摇篮也成了妈妈的摇篮,女儿的美梦也是妈妈的美梦,女儿感受到的树啊鸟啊鱼啊,不爱看书的妈妈在梦里悉数梦了一遍。
妈妈没有感受力吗?妈妈不爱美吗?妈妈不可爱吗?妈妈始终是世俗的人吗?我那个时候不懂,但是我以为我懂。我以为我懂很多道理,但是书和长辈们没有告诉我的是,道理只有真正经历了才会理解。
她们挨得很近,手臂像脐带一样依恋地环绕着,黑白的树影和灯光像飞鸟一样在她们脸上掠过,好像被时间赐予了某种剥夺的权力。光和影实在是太神奇的东西,当光落在母亲脸上的时候,她的脸砰地一下饱满起来了,她平时总是蹙着眉,可当她真的熟睡了,卸去了母亲这个身份,那道皱纹变成了一道浅浅的光洁的疤痕,像是阖起来的第三只眼;光落在女儿脸上的时候,则显示出岁月对年轻的苛刻,眼下郁积的青色,鼻翼浅浅的纹路,脸颊上的色斑,这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些她在镜子里苦恼的东西,在光下显得异常清楚。
车颠簸着,驶进了一条树叶繁茂的小路,摇曳的树影投在女儿脸上,她年幼的脸突然变得娴静了,眼眶因为阴影显得更加深邃,眼角变得细长,半边脸埋在黑暗里,伏在母亲肩头。很少有人说她俩长得像,大家都说女儿像父亲,可能是因为她们实在都像在一些太不起眼的东西上了。她们的脸庞像,是方脸,有一个圆润的弧度;她们的眉毛像,是弯弯的柳叶眉;她们的皮肤像,很敏感,过敏的时候身上一挠就是一道红印子,但还是挠……女儿更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像父亲,可能是因为爸爸在心里总是一个完好的形象,可能是妈妈从记忆里就是胖胖的样子,母亲也乐得别人说女儿像她的父亲,因为确实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从小就知道妈妈以前很漂亮,是生了我之后才开始发胖,再也瘦不下来了。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看,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不懂这个道理。小时候看《淘气包马小跳》,马小跳因为妈妈剪了短头发,觉得长头发的漂亮妈妈不见了而哭了一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个情节记下了。有一次,妈妈去理发店把头发剪短了些,新烫了波浪卷,我也学着马小跳,跟她大哭了一场,然后我的妈妈就像马小跳的妈妈一样,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有些无奈又有些好笑地哄着我,说以后不剪头发了,都留长头发,我这才抽抽嗒嗒地止住了哭,心里是特别特别的幸福,感觉自己变成了书里的小孩。
妈妈留了几十年的长发,从我有记忆起,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去理发店烫一次头,带着一股刺鼻的理发店的味道回来。刚开始头发是很紧绷的卷度,像扑克牌上的国王;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记忆里最熟悉的样子。这个样子出现在我没出生的旧照片里,出现在拥挤的小学门口,出现在补课班的最后一排,最后出现在高中的出租屋里。后来她生病了,剃了寸头,就再没去过理发店,后面的头发扎脖子了,都让我帮她剪。我老摸她的头发,不扎手,像连刺都被烤软的毛栗子,她的头发每天都长得飞快,像小孩一样,每天都变一个样,没过多久,就长到眉毛了,这时候摸起来已经像毛绒绒的小猫了。
随着我的成长,那些年我们爆发的像洪水一样猛烈的争吵,那些不断突破水位线的情绪,暗流一样涌动的争端,逐渐变回了它们最本质的样子,轻轻柔柔地包裹着我们。她愤怒的样子在荡漾的水波下变得柔和了很多;她斤斤计较、小气吝啬的样子,波光映着居然还有点可爱。有时候,我在平静的水里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穿着她从前的衣服,嘴角不自觉地含着笑意。我变成了妈妈的镜子。
如果非要拿河水这么不稳定的东西来划分垂钓区域,那么有人生在河的这边,要经过陡峭泥泞的斜坡,伐木取道才能到达垂钓区;有人生在河的那边,天生就是钓鱼俱乐部的会员。在这种规则里,我总是一名偷渔者,撑着船划到河的那边,放下钓鱼线。有时候,我心里是一种隐秘的难以启齿的快乐,说到底,有谁会真的在意这些拿流水规定的所谓的禁令呢?有谁会在乎船上的一个小孩子呢?但更多时候,一种无根无萍的恍惚慢慢地把我环抱住了。年复一年的,在宁静的夏夜里,紧绷的鱼线就像突然拉响的警报,我的记忆绕着这根鱼线飞速旋转着,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船上的小孩子与怪鱼的争斗,直到我长成大人,退出这个偷渔的游戏。
在我可以被当作小孩的这些年,我们住在一栋七层楼的老楼里,有着非常厚的蓝玻璃。风一吹,对楼的一排排蓝玻璃在阳光下像被拂动的风铃一样,有的露出正在做饭的泥塑般的小人,有的映着蓝莹莹的影子,有的紧闭着,像正在腌制果脯的糖罐。所有的景物都是流动的,天然构成了一幅倾斜着的湿答答的油画,如果一直盯着头顶上方的一朵云看,没过一会儿,眼睛就被云牵着跑走了。
往下看,这条路上的人并不多,都是不急不缓的步调,从拐角出来走到树荫里头,他们人生的片段就在我的眼睛里播完了。我试着打断这样的相似,刚开始带着一种打招呼的羞赧,声音单薄得像蚊子哼哼:“嘿,下面的人!”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我在喊他们。
没有水波,甚至没有涟漪,索性眼睛一闭大声喊:“下面的傻蛋,我在你们上面!”然后涨红了脸,飞快地缩在窗户下面。有人停下来了,跨着篮子四处张望着,像电视机里的小泥人,但始终没有人抬头看看。这一切实在是太奇怪了,明明从楼下看起来我也应该是一个正在探头探脑的泥塑般的小人,顽劣的、胆怯的,一个金灿灿的小人。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楼上的人和楼下的人是隔着一层说不清的障壁的,有时候甚至就像在河的两岸,如果我在河的这岸,那对岸的人是听不到我的声音的,如果我是一名偷渔者,就更没道理打破这份宁静。于是,这条小路就变成我一个人的了。
没有树能长到七层楼这么高,小小的我就成为了树们的主宰。潮汐是跟着风一起来的,小路上涌起了一阵绿色的波涛,准确地说,我并不知道潮汐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有些是人发出来的,有一下没一下扑扇的蒲扇,沙沙的扫地声,浪一样驶过去的车轮声此起彼伏地拍打着窗户……有些是树发出来的,树心深处的震动引起了树叶的共鸣,像洪水来临前一样摇晃着巨大的树冠,下暴雨的时候,水雾就从这里升腾起来。最令我着迷的是,有些声音听起来属于其中之一,但源头却更像另外一个。
这些树好像一只酣睡的猛兽,每一根毛发都在阳光下舒展又自在地打着盹,那些鸽子往往会在它变换睡姿的时候像虱子一样一头扎进另一侧的身子里。我常会想扔一个粉笔头下去,惊走这些懒惰的鸽子,事实上,我就这么做了。
像抛出鱼钩一样,粉笔在空中有着漂亮的弧度。扔到树冠里的时候,只有一个波澜不惊的小水波,好像被某種怪鱼当成食物一口吞掉了;有时候会落进楼下荒废的小院子里,在被人遗忘的世界里,粉笔头掉进爱丽丝的兔子洞里都不会奇怪;有一次不小心落在某辆倒霉的车上,沉闷的一声,我猛地把头缩回去,心脏跳得厉害,再探出头的时候,车前盖上的阳光有了某种光怪陆离的弧度,歪着嘴不怀好意地笑。
我屏住气,对面老楼上的光影像水波一样缓缓流动着,有一棵树绿得极其鲜艳,好像淌着湿漉漉的羊水,长着一双小羊羔般黑曜石的眼睛。我的脑子变成了被风吹乱的书页,急切地搜寻着掌握不多的法律知识,但是冒在我眼前的统统是一些青春文学,关于少年与法律,灰暗的前程和痛苦的父母……我跑到桌子前,在一张废纸上写下刚刚的烦恼,然后把这张纸折了几折,用力地撕开。直到撕不动了,就把两只攥满碎纸片的手直直地伸出窗外,坦然地面对即将拷上的手铐。我的胸腔里面吹着一股英勇的风,所有内脏都像手缝里的纸片一样哗啦啦地动,手一松,这些纸片就立刻飞了出去,身体随即泛上了一种失重感,感受着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我的烦恼,和以前的每一个烦恼一样,全都散在风里了。
并不是所有的纸片都能被放飞。有时候,手心的汗会粘住一些纸片的蝉翼,这些小家伙在手掌虚弱地动弹着,它们和房间里那些涂上颜料的石头,还没有经过烧制的陶器一起被留下来了。我常常觉得它们就是斯蒂芬·金口中被滞留在过滤网孔里的淤泥,那些不愿意离开你我的东西。
窗台下边的那一排石头是我们从山下的小溪里拾回来的,有的被我涂上了各种图案和颜料,有的只是粗粗勾了线,细嗅有着淡淡的河腥味;衣柜上面的几个花朵状的盘子是和妈妈在陶吧捏出来的,因为没有烧制就带了回来,现在的质地就跟粉笔一样又干又脆,爬上了很多细小的裂痕,变成了干涸的河道;在盘子旁边,一个一米高的白色玩具熊靠在墙上,它是逛超市的时候我央着妈妈买下的生日礼物,我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书里的小孩,而拥有大玩具熊和拥有答应孩子永远留长头发的妈妈一样,都是书里面最幸福的情节。
那个时候我只爱上语文课,其他课要么是语文课紧张轩昂的前奏,要么就是作战对象。战场无处不在,铅笔是最常用的武器,手肘是最亲切的耳语,在大家都埋着头记笔记的时候,飞快地在五颜六色的批注旁写下最新的情报,用手肘抵着课本慢慢推向桌子的另一边,再迅速地碰一下那人的手肘,就完成了对接。有时候,课桌也是我们的战场,淡淡的铅笔印,一擦就成了黑乎乎的一团,内讧也在这里发生,两条手肘在三八线左右拉锯,反目为仇。
纸条是最忠实的信鸽,飞跃了大半个教室再回到我的口袋。为了防止消息被我妈窃取,我总是把它塞到书包的内兜,夹在书页里。可总是在我忘掉它的某一天,它以一种光明磊落的姿态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妈洗书包的时候,它和书包里的其他杂物、书本,被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子上,我心里突地一跳,知道秘密泄露了。
于是,对这些纸条,我有了更狡猾的处理方法,撕碎扔进垃圾桶是下策,我一般会撕碎扔到窗外。拉开纱窗,再用力顶开玻璃,各种声音顺着缝隙挤了进来,黑夜张开了它寒风凛冽的嘴巴。在风里,纸片像突然有了生命一样,一面闪着泠泠的稍纵即逝的光,波光脆弱地颤动着,一面隐匿在黑夜里,用单薄的羽翼庇护着幼稚的心事,我们的字迹在这两面不断的翻转中,被揉进了每一条水波里。在这些纷飞的纸片上,亮面与暗面、黑夜和白昼飞快地交替着,在我一次次跑到窗口放飞这些纸片的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也顺着风不回头地飞走了。
有一次,我在裤兜里摸到了一个有些硌腿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发现是一个又硬又皱的纸团,稍微一搓就有白花花的纸屑往下掉。它逃过了我妈的搜查和岁月的处决,但字迹已经被水氤得看不太清了,仔细辨认也只认出了两句话:
“那个,你的脸磕青了,当时没来得及问,没事吧?”
“哎呀!你别担心了,我是谁呀!肯定没事。”
其他的话认不出来了,更多的话,也散在风里了。我早都忘了这些纸条上的内容,只是这个没有被放飞的纸条和屋子里其他的老物件一起,证明了我的记忆有个来处。
我抓了一把网孔上的淤泥,摩挲着淤泥里的小颗粒,沿着河道慢慢地走。这条河,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过,在佛坪,倚着山奔腾下来的水,被人们试图修缮成县城里规规整整的河,但水是活的,水底的秘密和人们的想象力是不被拘束的。看着城里的河,总像在看着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长相平淡的女人,看着这条河,却忍不住想里面会不会有数米长的大鱼在翕动着嘴巴慢慢地游,河上的水波会不会也是它吐出的氣浪。抓着栏杆,目光从对岸的山体一寸一寸地往上挪,起初,山体和夜色不过是墨的浓淡之差,越往上,越是辨不出山的轮廓,只觉得原先静谧凉爽的夜突然变成了笔直的望不到顶的山崖,满山的寂静吹动山林,四周传来哗啦啦的声响和雾一样飘渺的回声。我立在山脚,变成了华山求道的弟子,越害怕,越要往上看。头顶上的星星,刚开始只是一两颗,越看越多,后来漫山遍野的都是星星,没星星的地方,黑压压的就是山。
眼睛被山风吹涩了,才回过神来。看到爸爸妈妈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赶紧跑到他们中间去,把他们的手一拉。心里感觉有点异样,托起妈妈的手在灯下一看,才发现上面多了层松垮的褶皱。小时候抓蝴蝶,等到蝴蝶的两个翅膀并在一起的时候,猛地用食指和大拇指把它的翅膀夹住,一阵猛烈地抽动后,手指上沾了一层滑腻腻的鳞粉,还印上了部分翅膀的图案,像不均匀的斑点。现在这层鳞粉覆在了妈妈的手背上。我的嘴唇上下动了动,半天说不出话,心里有点苦楚,有点悔恨,汪洋的爱在金色的灯光下沸腾起来。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原来,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鳗鱼也从这条河,游回马尾藻海去。我的日子过得囫囵吞枣,很多细碎的小事,妈妈、姥姥都记得比我清。我记得最清的是一些重要节点的画面,比如我不想上学了,背着书包去曲江书城,从书城出来的时候正赶上落日,几千扇高楼的玻璃都在重复着落日的情景,夕阳像酒液一样从一扇玻璃流淌到另一扇玻璃;比如我下了晚自习往家走,雨下大了,所有人都举着伞在这场雨里模糊了面目,我混迹在人群里,从伞下伸出头,贪婪地吸着水汽;比如我考上了大学,和爸爸在隔壁小区的空地上散步,爸爸说,我们就是在这里孕育出了一个伟大的奇迹。我心想,这不是离家、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吗?后来他说,每次我去上晚自习,他就和我妈在这些楼房旁一遍一遍绕着圈走,心里是忐忑的斗争和烧不灭的希望。对于他和他的亲密战友而言,这里就是最伟大的战场。
要么是这里,要么就再往回游,循着这种在幼年时就深入身体的大海的气息游回海洋。长大之后,我走路开始喜欢看天、看窗户、看云慢慢流到天的另一边去,我不想当被楼上默默观察的傻蛋。有一次,我躺在高中的出租屋里,听到楼上传来的练琴声,不断重重地重复着三个音符,突然意识到不管我搬到哪里,好像总能听到这种搭配的琴声。重重的三个音符,让过去的记忆砸醒了我,像山崖上空灵的雾气一样把我包裹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幼年的经历早在我身上烙下了印记,是这些记忆塑造了现在的我,也决定了我未来的走向。我可能必须得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想走写作这一条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洄游到这些旧时光里,它们会告诉我,为什么我回到西安就如乳燕投林,我不够了解这里,但那灰色的城墙、雾蒙蒙的天、扎实磅礴的土地早就不知不觉地扎进了我的身体,像根系一样生长,再从我的笔尖钻出来。是哪些记忆构成了我性格里谨慎的一部分,哪些构成了果敢,又是哪些构成了爱;我最爱的这些人,是他们的哪个时期碰撞挤压出了现在的我,又是哪些困难,将我烘干定型……如果来得及,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写在我的笔下。于我而言,写作的一部分是为了抒发,另一部分是为了爱。
写这些话,像在晒一床压了很久的被子,好多微小的尘埃,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着。万千波涛的马尾藻海,无数欲语还休的回忆与画面,在我梳理自己的过程中,给了我一个归处。
(责任编辑:孙婷)

刘旭晨 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读。作品散见于《三秦都市报》《华商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