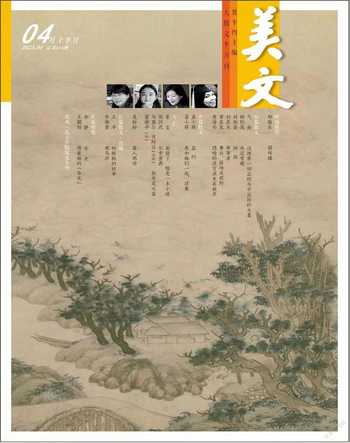肇事者
刘星元
刚才,我就极其突然地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场事故对责任双方而言固然是场意外,对我而言似乎也未尝不是。有时候,似乎意外的属性并非奇迹,并非小概率事件,在它从潜伏中跳到光天化日之下后,就会连锁发生,如多米诺骨牌。这是另一场相比而言微不足道的意外——事故发生后,我们这些目睹者几乎是一致性地迅速而有违常理地跳过了车辆的损益,将目光聚焦到了肇事者身上。肇事者有些特殊,它是一头骡子。
事故发生在护城河大桥西侧的主干道上,那头拉着地排车的骡子,在所有事物中最先遭受到了意外的冲击。那头负重累累且行进在一段不算短的上升坡面上的骡子,它许是气力突然不足,许是被周围的什么事物吓了一跳,许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想用自身为饵玩一次洗涮世人的游戏。总之,在所有人都未能预料到的时机里,它一个失蹄,便拍倒在地,紧接着,失去前拽之力的地排车开始了反叛,迎合着路面的坡度持续下滑。驾驭骡车的人向着骡身及时挥出了皮鞭,暂时抑止住了地排车继续下滑的趋势,但最初的波动还是以环环相扣的共振效应激发了出去,堆积于地排车里的建筑钢管如滚木礌石,早已冲开木质挡板的拦截,撞击到跟在后面的小汽车上。受损小汽车的车主跑到车前,先是看了一眼损毁的保险杠,继而又扭头看了一眼肇事者,竟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显然,对于这样的事故,他之前并未预料到。同样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另一位驾驶者——那个五十岁左右、黑瘦的中年男人,把肇事的骡子猛抽了几鞭,将它驾驭到路边,从骡车上匆匆忙忙又踉踉跄跄地跳下来,刚要举步向着小汽车奔去,又突然想到了什么而停下,用缰绳将骡子拴在了旁边的绿化树上。随后,黑瘦的中年男人紧跑了两步,停在了受损的小汽车面前。那款受损汽车价值不菲,在这座县城里,已经算是高档货了,不知道骡车的主人对这些有无了解。骡车的主人先是蹲下,用手摸了摸保险杠凹陷的区域,继而又站起来,半躬着身子,向着汽车车主不停地说着抱歉的言语。陈述所见,我用了一个很普通的词——踉踉跄跄。在这场事故里,这个词归属于驭骡者,然而,我从未在之前遇到的那些驭骡者身上,看见过如此狼狈的动作。之前所见,驭骡者都是脚步稳健者,无论是举手扬鞭还是抽鞭袖手,无论是弹腿上车还是跳步落地,都显得极为熟稔和潇洒。
在这场事故中,涉事雙方均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慌张、无奈以及不知所措。即便是如我这样路过的业余或者职业看客,脸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涂抹着好奇、疑惑甚至幸灾乐祸的粉彩。此刻,肇事者已经安静了下来,它用长长的鬃尾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身体,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感兴趣。它就这样迅速从漩涡中抽身而出,把后续的麻烦抛给了驾驭者,就像是在外面闯了祸的纨绔子弟,若无其事地转身走进自家的高门大院,将处理这些麻烦的活计全部抛给了当家的父兄,自己则怀揣着事不关己的心思作壁上观,甚至连壁上观都懒得观。
这起事故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并不清楚,因为我早已提前离开了,因为诸多对一些人而言微不足道的小事还在等着我去赴约。每天,我都要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哄娃养家……这些琐碎之事以结绳之状驱使我如骡马一般奔走于自己的生活轨迹里。在小人物的生活里,固定的轨迹预示着行止的安全,它死板、无趣,却让我不敢躲、不能躲、也不愿躲。背离既定轨迹,或许会让我体会到暂时性的欢悦,然后欢悦之后,迷路的我、失路的我、出轨的我,又将何去何从?因此,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克制着、隐忍着、趋同着,尽量不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交通事故”,哪怕这“交通事故”只是一些小摩擦。一起由骡子引发的意外事故,如果非要与我牵扯上什么关系,那它也只不过是既定生活里的一个小波澜,是我生活里的对立参照物,它的作用,便是警示我要更为安分、更为守己、更为规规矩矩。如此而已。
只是我没想到,这起无关我分毫的交通事故,还是给我留下了浅浅的后遗症,最为明显的症状,便是让我零零碎碎地想起了一些与骡子有关的故事。
在诸多的词语组合里,“驴子拉磨”是个相对固定的短语,以这个固定短语为基座,我们还创造出了几个颇令人认同的歇后语。读高中时,遇见过一道歇后语补充题,题干就是“驴子拉磨”。语文老师讲解时说,答案可以是“任人摆布”,也可以是“跑不出这个圈儿”。
我们每个人原本都是一个相对独特的知识收容器,但有时候,我们又会被不断收容进来的同质知识左右着、修正着、曲解着,让我们的相对独特性被更多的普遍性所稀释,更改着色泽、质地,逐渐融入且适应了整个群体,也逐渐泯然于众人。比方说,在我微不足道的知识体系还未趋同群体知识之前,我的实有见闻中,最先学习到的是“骡子拉磨”,而非“驴子拉磨”。拉磨的是我邻居家豢养的骡子,我至今仍不能知晓到底是骡子还是驴子更适合从事这项工作,从众多人的经验中提取出的汉字短语中猜测,似乎驴子更为适合、但在物资贫乏的时代,“选择”二字本身就意外着奢侈,对于普通人而言,根本就没有被赋予是奴骡还是役驴的选择权,更不要说骡与驴兼得的痴心妄想了,于是,他们碰见哪个牲畜就只能擒住哪个牲畜来为自己效劳。就如在濒临溺毙的困境中,只要能有一株苇草被我们抓住,那就是抓住了希望,至于那株苇草耐力如何、能不能承载住我们的重量,危急时刻,困境当前,我们无暇顾及。
继续来讲述这头骡子的故事。邻居家是开磨房的,因为只收取磨下来的糟糠或者极少的钱币作为酬劳,磨房的生意甚是兴隆,本村及附近村子的乡亲都会来此磨面。阅读过几位作家回忆儿时乡村磨坊的文章,他们说,作为乡村以及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磨房里人声、畜声与磨声交织协奏出的,是一首乡村高山,一曲乡情流水,不谛那被贬谪到凡间的天籁,令人迷醉,纵然世事变迁,纵然沧海桑田,仍令人心心念念,无数次午夜梦回,那声音、那场景,总是会一次次接引自己于怀乡中还乡。不知道这些句子是他们真情实感的复制输出,还是因浓郁的回忆而扭曲变异出的虚假再创作,反正放置到我身上,迟钝的我体会不到这样的感情。更确切地说,我其实很讨厌磨房,讨厌磨房里传来的声音。
邻居夫妻俩很勤劳,凌晨四点,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与其他行业一样,磨面也要讲个先来后到,但在邻居家,那先来者确实太过“先来”了——有些乡亲太过忙碌,白天错不开时间,往往是晚上将粮食送来,嘱托明早帮着磨,邻居夫妻俩也总是先磨完这些“隔夜粮”,才会去磨当日送来的粮食。必须承认,邻居越是勤劳,声音便越是噪杂、频繁。是等候着的磨面者发出的忽高忽低的嬉笑怒骂声,是往来磨房的人们杂乱的脚步声,是粮食在石磨的碾压下喊出的绝望的悲恸声,这些声音常常吵得我睡不着觉。虽然骡子拉磨时自身几乎不发出声响,但它却是这诸多声音的漩涡中心,是这些声音有力的助推者,也是打乱我正常生活秩序的肇事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污点,代表着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行。我想“清污”,我想“复仇”,然而它却长居磨房,只是偶尔晃荡于院内,我又能拿这头深居简出的畜生怎样呢?所谓的泄愤也只不过是爬上墙头,用眼睛向着邻居家的院子狠狠地剜几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有一年年末,我终于抓到了“复仇”的时机——不知为何,邻居居然破天荒地将骡子拴在了门前的榆树下。见四下无人,我捡了一根杨树条儿,悄悄摸到它的屁股后面,蓄足力气,挥起杨树条儿狠狠抽向了它。遭受抽打之后,它并未如人或其他牲畜一般用喊叫声来释解疼痛,而是伏腰起跳,将其中一只后蹄踹向了我。幸亏我站得稍远、跑得迅疾,未被踹飞在地,饶是如此,骡蹄踹来的那一刻,我还是感到左胳膊上顿了一下。当时并未在意,但到了晚上,胳膊便开始疼了起来。避开家人,我脱下衣服查看,才发现胳膊上烙着一块红印,印呈椭圆形,稍微高于周围的皮肤,用手一触,忍不住呲牙咧嘴。幸亏是冬天,幸亏穿了厚厚的棉袄,倘若是夏日,我怀疑自己会伤筋动骨。虽然疼,但我并不敢告诉大人,毕竟这完全是我自己无事生非,结果也只能咎由自取。伴着疼痛,我在心里咒骂着那头骡子,用上了从村妇骂架中学来的恶毒语言,那语言里密布着很多涉及生殖的字眼——尽管那时,我尚不知,与村妇骂架不同,因为被咒骂的对象极其特殊,我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陈述了某种事实。除了关乎生殖秘密的谩骂,我还咒它骡失前蹄,咒它一生拉磨,咒它天天遭受皮鞭的抽打。甚至,我还以死亡诅咒它,咒骂那骡子早死早托生,托生下来依然是畜生。
不久之后,邻居家的骡子果然死了。尽管邻居说是老死累死的,我却忐忑不安——原本,谩骂和诅咒只是一种让自己的口头或心尖爽利的自慰器械,而它一旦迎合了后续发生的事实,便从时间顺序上篡夺了验证、丈量事物的先知身份,也会让施咒者或幸运或无奈地背负了伦理上的凶手之名。
生时为奴,死后作饷。贫瘠时代,无论我们对牲畜如何倚重,待它们死去之后,仍然不能免遭刮斫之刑。那一年,邻居家将死了的骡子挂在门前的榆树上,请来村里的屠夫用尖刀剥皮,以备斫骨断肉,大锅炖煮。被脱去皮囊之后,它怎么看都不是一头骡子,倒像是麋鹿之属。悬在榆树杈上的它,羞耻地并拢着包括那条曾经踢中我的后腿在内的两条后腿,似乎在隐藏着什么。许多年后我定居县城,在县城的街道上,我发现很多肉铺喜欢将牛羊等牲畜挂在专用的金属架上,现杀现刮,现割现卖,以示新鲜。我喜食肉类,但这样血腥的举措总是让我不适。虽然我无法判定这种不适算不算是矫情的体现,但是我却明确知晓,这种不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邻居家的那头骡子死去之后仍未能幸免于刀斧的际遇。
和睦的邻里关系常常需要在小处培养、维持,几句问候、几样食品、几次举手之劳,都是保养这种关系的好肥料。那次,邻居家为了继续保养好这种和睦的友邻关系,给我们送来了一块煮熟的骡肉,我母亲将肉切成片儿,摆在盘子里,让我们蘸盐吃。我吃过驴肉,本县的某个乡镇,肉驴生意声名远播,俗语“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则是他们最响亮的招牌,但恕我直言,其实味道并不出色。对一种食物的喜与爱、厌与恶,往往是在与另一种食物的对比中实现的,虽然我始终没有向邻居送来的骡肉伸出筷子,但我依然坚信,与骡肉比,驴肉确实可称为珍馐。我是说,因为想入非非,邻居家送来的那块骡肉,让我干呕了很久。
一些东西看起来很重要,但也只是看起来重要,其实它们并未重要到受益者不能失去这种重要的程度。骡子死后,邻居家的磨房依然存活了好些年,他们将石磨掀了,上了一套机器设备,代替那对原始的组合,继续咀嚼着粮食,折磨着粮食,分离着粮食。与骡和磨比,机器的轰鸣声更甚,新的肇事者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的睡眠。两害相权,我很想念那头已经死去的骡子。
在我的视野里,一头骡子能够闯入的人类社会的最大群落,便是县城。这些年,各地纷纷出台“限畜令”,先是省会城市,继而是普通地级市,如今,一些县城也开始效仿,以通告、通知和告诫书的名目,排拒了牛马驴骡等一批大型畜类的进入。或许是还没来得及跟上时代的步伐吧,我所在的这座县城,尚未有明文的限畜举措出台。
这是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几乎每座县城都在紧急谋划着如何在水平范围和垂直高度中扩充自己,而对建筑物的破立之举,便是实现这一规划最为快捷的方式。在县城,诸多的建筑性作业几乎日夜不休——既日夜不休地拆迁着,也日夜不休地建设着。
我所居住的县城里,时常可以见到拉着地排车行走的骡子,它们往来于各个工地之间,为不同的施工队运送建筑材料。地排车内,或整齐码放或杂乱堆积着钢筋、木材、铁管、沙土、水泥、卡扣、空心铁柱等建筑材料,这些材料往往会高出地排车的挡板很多。材料里以钢筋最细最长最韧,往往是五分之三的躯体躺在车斗内,五分之二躯体垂在车斗外,那垂在车斗外的部分,又总是耷拉在地面上,钢筋与路面摩擦着、撞击着,发出嗤嗤啦啦的尖锐之声。或许是早已适应了这声音,拉车的骡子总是充耳不闻,只沉默地低头走路。一些机动车和电动车同向超越了它,并呼啸而去;另一些机动车和电动车逆向擦过了它,也呼啸而去。喇叭声、刹车声、油门轰响声甚至是路人的谩骂声相互交织,这些声音有的纯属无的放矢,有的则指向明显,正是对骡车的警示。拉着地排车的骡子却以事不关己的态度自顾自地前行着,不紧不慢,并不因外界的提醒而左右自己的步伐。除非是确实把路走偏了,除非是驭车者皮鞭抽下来,它才会将方位校正过来。驭车者多是来自县城周边村庄的农民工,与几家建筑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包工头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们便会赶着骡车前来,在不同的工地间周转往返。
妻子的舅姥爷早年间做过包工头,县城里,许多建筑是他带着人垒砌修建的,许多建筑也是他带着人捣毁拆烂的,这其中不乏他亲手建起又在许多年后亲手拆毁的建筑。对骡车产生兴趣之后,我向他请教为何要用骡车运送建筑工具这个问题,我的配套问题是——用机动车运送建筑材料岂不是更迅速更方便?舅姥爷则告诉我,小型机动车车斗要比地排车短小,有些建筑材料过长,无法运送这些物品,而大型机动车租金又过高,没有哪个包工头舍得花这样的冤枉钱。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骡子的可靠度,他说,与其他能够运送货物的大型牲畜比,骡子性情温顺、吃苦耐劳、易于驾驭,并不比机动车辆逊色。不知是刻意隐藏还是觉得无关紧要,舅姥爷并没有告诉我,骡子其实是天阉者,而我却总是固执地认为,骡子的品性,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作为驴和马杂交后的产物,骡子是我们咒骂用词里“杂种”的原型之一,在机械类运输工具尚未大行其道之前,它绝对是运输工具中的翘楚,是两种大型畜类家族联合贡献出的骄子。甚少咴嘶、可堪负重、耐力持久……它几乎集合了父系和母系家族身上所有的优点。这是一次质的创造,是生育史上的奇迹。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代际蜕变,却需要付出不可逆转的毁灭性代价——不孕不育。这四个字是人类以及其他动物身体里偶然可见的隐疾,但放置到骡类身上,竟然成为了绝对性的标配。因为这四个字对于它们每个个体而言,诸多的优点只能聚集于自身,不可继承。蜕变只能到此为止,惊艳只能到此为止,妄图继续优化的雄心也只能到此为止。作为特殊功能障碍者,尽管那些器官是完整的,但是器官的作用早已经丧失,开国雄主即是亡国之君,它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依赖驴、依赖马、依赖父系和母系的基因,创造自己、成就自己,最后再毁灭自己。
驴咴叫、马嘶鸣,无论是在自由驰骋还是在遭受奴役之时,无论是在内心欢悦还是在背负悲伤之时,其他动物都会选择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去享受、去深思、去反抗。然而,骡子却甚少动用自己发自肺腑、吐于口舌的声音——对此,一些民间故事也常会选择它们编排杜撰,用调侃的腔调叙述着它们的失语。骡子,它们臣服于命运的胯下,就如宫殿深处的那些不全者一般。
那么,请让我重新回到那起由骡子引发的交通事故中。既然安分守己是骡子的固有标签,那么肇事或许并非它的本意——在被不可逆的命运阉割之后,它只需沉默,只需俯首,只需规规矩矩,只需负重而行,若无意外发生,将永远不会成为世间的肇事者。
(责任编辑:孙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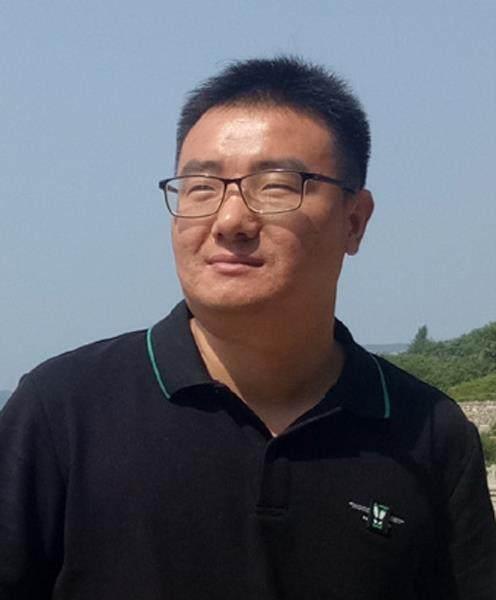
劉星元 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天涯》《钟山》等刊,散文集《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曾获山东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齐鲁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