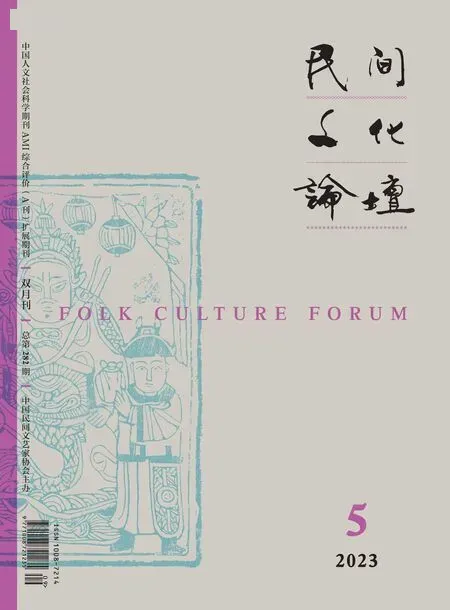门文化特质的民俗学解读
—— 兼议民俗学研究建筑的当代价值
马延孝 刘智英 马知遥
建筑是为了“遮风避雨”“隔湿避瘴”,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庇护所。“以此为基础,加以技术和艺术上的创造,最后演变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实际上建筑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包括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深刻地反映了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进步。”①张晓春:《生态建筑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年,第38 页。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建筑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建筑本身,还应包括建筑背后的精神层面。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也认为:“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②梁思成:《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林洙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第25 页。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门在人们的生活中极其重要,正如《论语·雍也》云:“谁能出不由户。”起初,门区隔了建筑的内外空间,满足了人出入建筑空间的需求。随着人类审美需求的产生,门逐渐具有了教化、规范、调节等民俗功能。民众的生产、生活离不开与门有关的民俗。门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民间文化的浓厚缩影。大到城市、宫殿,小到四合院、天井院住宅,门的种类形式极为丰富多样,有城门、宫门、殿门、庙门、院门、宅门、房门、屋门等等,其雕刻装饰和色彩处理,极富文化内涵,形态上显示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征。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需求的变化,与门有关的建筑材料、外部形式、设计理念等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门的建筑材料、色彩搭配和尺寸大小,展现自己的个性,提升建筑的美感。此时的门已完全有别于传统建筑的门,门所蕴含的文化中传统文化基因减少,增加的是现代文化因子。弄清楚传统建筑的门及其蕴含的文化,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要想整体把握建筑的文化表征和深刻内涵,从民俗学的角度解读建筑,可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一、从生活民俗的类型性看门文化的复杂性
“生活民俗是指衣食住行方面的民间习尚。”①高丙中:《中国民俗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98 页。生活民俗最初以满足生理需要为目的。“类型性是生活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指的是某些民俗在内容或形式上的大同小异。”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21 页。
门本身具有物质生产、民间科学技术、民间艺术等方面的民间知识。门文化包含民俗诸多的类型。从信仰民俗看,门神的生产机制就包括造神、役神、祀神、娱神、酬神等程式,而每一个与门神相关的程式又涉及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岁时节日、民间科学技术等单一或多元民俗类型。从夯基开始直至完工的诸多建房程式中,立门与上梁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因此民众十分看重立门这一活动,仪式感满满。立门前,主人请风水先生选择黄道吉日。选择吉日的原因,来自于民间禁忌,忌讳冲犯“太岁”。即在时间上要求选择吉日良辰,避免与太岁所在时辰相冲;在空间上,地方性民间知识的不同,促成文化内部持有者关注立门过程中的不同工序,继而形成不同的习俗。立门常与对联配套出现,诸如山东立门常出现“安门增万福,立户纳千祥”“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就是要借助民间信仰表达求吉避祸的心理诉求。浙江建德市新叶村和兰溪市诸葛村,门梁上有一摞“七色布”,一端缠绕在门梁上,一端飘在外面,露出部分的长度有三到四寸。当地村民皆有在门槛下放置五谷、布头和铜钱的习俗,旨在祈愿有吃、有穿、有用。“传说如果造房子的主家对待风水先生和大木工匠不够尊重,他们会在那两个位置上放些不吉利的东西,使房主人家永远不能发达。”③陈志华,李秋香:《中国乡土建筑初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69 页。从这里看出,门槛对民众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故民众对它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安徽省黔县一带,人们在上门楣的时候,要杀公鸡祭拜门神,淋血于门口,并念祷词:“鸡血淋到东,恭贺东家添儿孙;鸡血淋到西,恭贺东家必添丁。”上门楣为立门最后一道工序。门也叫门户,有了门户,也就意味着有了房子,有了房子就能娶妻生子,继而壮大家族。长江下游地区民间立门,最讲究的是门缝的严密,有“紧门缝,开新门”的俗语。木匠在制作宅门的过程中,故意把门做大几分,等到装门的时候才刨去多余部分,称为“紧门缝”。如果门缝不严丝合缝的话,就难免有鬼祟之物溜进宅院作怪。青海土族在立大门这天,在太阳升起来之前,主人需外出挑水,路上禁忌回头、歇息;回避红白喜事、病孕之人;门框立起来之前,禁止外人进门;门框主梁用桃木雕出花纹,同房屋大梁一样,正中凿洞装入粮食、财物等。
民俗的类型性是追求共性与认同的,它是集体创造的结果,且过程中十分注重集体传递与传承。虽然各地工匠由于地区不同呈现出了关注点与工序的不同,但是往深层里去追溯,都是在追逐“求吉避祸”这一核心内容的文化表达。各地民众达成的共识与认同是一致的,只是地域特殊性在门的规范上有了些许不同,不断进行着文化的调适。立门这一民俗仪式在各地表现出类型性,借助诸多民俗类型完成地方性知识的呈现与阐释,涉及到民间信仰、民间传说、居住民俗、民间习语、禁忌民俗等。在立门仪式中,民俗的类型性成为文化阐释的依据,在复杂的程式中借助地方性知识完成门文化的具象与抽象。从立门这一生活民俗包含民俗类型性的特征延展出门文化的特性之一的复杂性。反过来,门文化的复杂性也对应于民俗文化的类型性。目前,城镇化大背景下,不同的地域城乡界限进一步模糊,二元对立被打破,许多农村或多或少改变了原先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与城市文明的交织交融,使得解读建筑空间的复杂性进一步得到强化。城镇化语境下门的文化内涵发生了变革,扬弃与嬗变同时存在,使得门文化可能不再是最初的形态。门文化中逐渐渗透了精英文化,不再封闭、传统。门文化在现代化中不断调适,其结果使门文化愈趋复杂化。引入新的民俗类型,需要新的民俗类型再书写,增添与拓宽民俗文化被书写的新路径,因此,通过填充内容,改善形式,转变思路,调整方向,完善原有的民俗类型,则成为后民俗时代民俗学的出路之一。从门的生活民俗上看,借助门文化的类型性完成地方性阐释,使得复杂性的门文化阐释更加条理而系统,同时,与门有关的民俗类型将充盈门的整体文化阈值,丰富门文化的内涵。可见,门文化的复杂性成为民俗类型性的存在土壤,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提供民俗类型不断完善的给养。
二、从艺术民俗的规范性看门文化的界定性
“将经验和观念变为规范的过程,就是民俗文化中经常见到的对某一民俗的约定俗成。”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20 页。规范性是艺术民俗的特征之一。为了协调生活,民众在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同时,也用规范化的艺术民俗构成行为准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民间思维映射在门文化里,并在不逾制的前提下不断修饰和美化各类“门”。在符合地方性惯制和当地审美文化的条件下,尽其所能增加门的艺术感。门是一户人家的“脸”,它的雍容华丽或者破败不堪分别印证着家庭的兴盛与衰微。尼采说:“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②王路:《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中华建设》,2010 年第2 期。《黄帝宅经》也云:“宅以门户为冠带。”而这一切在实践方面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民间艺术,诸如门饰、雕刻、剪纸、灯彩、书法、纸马、榫卯、彩画等都是门文化的主要载体。
体现民间工艺高超技艺和深刻内涵的首数各种各样的门饰,如门钹、门环、门簪等。门钹在北京、山西等地宅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为铜、铁制,形状中以六边形居多。门钹的边沿雕镂如意云头,中央凸起如碗形,上用扣子挂一个门环。门簪在镶嵌上也很讲究。平板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书画、雕花、锓字三种形式,素面门簪只做单纯的涂饰,或蓝或绿,与门扇保持一致。以北京四合院为例来看,普通人家装两个,大户人家装四个。
民间工艺中表现艺术最集中的当属雕刻,包括木雕、石雕、砖雕等。宋以来苏州古典私家园林以及古民居的建造几乎是“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很好地佐证了民间雕刻在建筑中的重要性。当然民间雕刻还渗透到建筑的方方面面,瓦当、吻兽、屋脊、墀头、廊心墙、攒尖屋顶等都印有民间智慧的痕迹。旧时有品级的官员府邸大门可用兽头装饰,称其螺蛳,有的地方说是九龙之子之一的椒图。雕刻工艺也体现在门心板上的门刻。门刻的内容往往因世事、身份而多变,“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是商贸之家门刻的内容;“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是读书人家门刻的内容;“遵先公祖训,克勤克俭;守二字真言,唯读唯耕”是普通百姓门刻的内容。这些门刻内容体现了不同身份的人追求理想生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门饰不仅可以通过单一方式表现规范,还可以通过组合方式表明文化归属。“山东鄄城一带,住宅大门大致分三种:即殷实人家‘起脊门楼’,砖墙瓦顶,脊两端有兽,脊中央插三支钢戟,漆皮门扇,门楣挂大匾;中等人家造‘鸡架门楼’,左右两个砖垛,上架横木为梁,梁上砌三行青砖,两扇板门,用锅底灰染成黑色;贫寒人家,住宅不成院落,土墙一道,留个豁口为门,门扇不过几个木条钉个框子再夹些酸枣枝或者秫秸,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蓬门荜户’。这种规范功能还体现在北京、山西的四合院、三合院的门上。”①马知遥,刘智英:《民俗学视角下门文化的功能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7 年第1 期。门饰也可以呈现身份等级,如北京四合院的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等通过不同工艺表现对应的规范。
主人的经济政治地位规范着门及门饰,反映了家庭境况和身份地位。高门大户、朱门彤扉对应蓬门荜户、衡门柴扉;不同的生活品味通过不同的民间艺术装饰,不论是动物、植物、文字等形象,都表现出各异的审美、特定的家风,商贾爱财、书生好读、农夫勤耕;不同的民族,通过规范性的门饰认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带有规范性和指向性的民间艺术强化了门的物理空间和文化内涵的界定能力,通过门上带有规范性认同特征的民俗符号界定了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体。反过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进了一家门就成一家人。“门”发挥了文化空间中自我身份界定的作用。千百年来,门文化早已突破了原有的实用功能,是家户向外展示自我最直观的文化指符。小到宅门、大到城门,门文化界定性通过阻隔、连接空间、展示身份、暗示地位等手段,增强了群体凝聚力。门文化的界定性与民俗文化的规范性二者的呼应从历史文化根源上看,来自于天、地、君、亲、师不可动摇的门当户对的等级制度,福、禄、寿、喜、财作为上至王公贵胄下至黎民百姓共享的认同规范与文化归属。
随着西方文化的渐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现代建筑中出现代表身份多元与领域延展的门,带有欧美、中东等地域风格,但其外在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②梁思成:《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第32 页。,西艺也仅仅是基于丰富的遗产完成中国风格的“艺术的进境”③同上。。当代中国门文化依然呈现出特定文化圈内的文化凝聚力和共享的规范认同,在审美文化的呈现中,通过二者特性互动对原有的身份、领域与文化归属完成追溯与强化;基于二者在文化深层次的同一根脉,通过二者特性的不断呼应完成新时代传统与现代在门上结合的命题。
规范性作为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一直与门文化的界定性形成对应,并且使得门文化的界定性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门文化的界定性也强化了民俗规范性强有力的现实凝聚力。门文化的界定性与民俗的规范性互相交织,共同强化着身份、领域与文化归属,二者形成双赢。
三、从信仰民俗的变异性看门文化的延伸性
“在民间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从古至今始终纵横交错地呈现出许许多多具有信仰色彩的事象,或表现在行为上形成了某种手段或仪式,或表现在口头上形成了一些信仰的语汇或口头文学,或表现在心理上形成了影响精神生活的某种力量。这些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具有信仰色彩的事象,都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不断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①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267 页。这些信仰的载体都是依托于民间智慧创造出来的,诸如仪式、器物、符咒等。
与门有关的庇佑祈福、禁忌规制形成物化的民间信仰,包括门神、字牌、符咒、卍字、兽牌、狮子等。门神追根溯源,最初来自于古人的庶物崇拜。庶物崇拜指的是经过人工制造的器物,《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与庶民年节之时都需“祭五祀”,东汉郑玄注云:五祀为“门、户、井、灶、中霤”,祀门居于五祀之首,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在汉代,人们对门、户的原始性自然崇拜已然异化,门成为“蛰伏之类”的界限,“蛰伏之类”既包括了现实中的毒虫猛兽,又包括了超现实中的鬼魅妖魔。人们认为蛰伏之类入户害人必然经过门,于是门祀就从五祀中脱离出来,开始不断赋予社会性职能,但是起初还未有具体的物象来统一规制。那时的门神雏形主要肇始于图腾、祖先、英雄的崇拜,聚焦于观念上的存在物,包括赋予神力的仿制品、画像、生殖崇拜、神话人物等。其后,民间出现了把桃木板挂于门上的现象,俗称“桃符”。古代尊桃树为仙木,认为能驱邪制鬼。古人遂把桃木雕成人形,意在驱鬼辟邪。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其傍,百鬼畏之。”随着时间的演变,老百姓门户上出现了虎形象,以虎作为门神,源于原始的虎图腾。人们认为虎是神兽,镇宅辟邪,庇佑一方。唐人《酉阳杂俎》曰:“俗好于门上画虎头”,这是画虎守门风俗最好的写照。除了代表吉祥的虎外,家禽鸡也出现在门上。鸡在中国民间文化中视为吉祥物,鸡鸣报晓,鬼怪避之;鸡食毒虫,五毒骇之;鸡可入药,百病祛之。晋人王嘉《拾遗记》讲到鸡“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魑魅丑类,自然伏退”。同时,“鸡”与“吉”同音,是吉祥文化在民间的象征,而且民众相信凤的形象就来源于鸡。《山海经》称凤凰“其状如鸡”。基于上述原因,鸡的形象自然会被俗民争相贴于门上,供奉为神,我国四川、江苏、山东、河北、山西一带依然沿袭。“大江南北,都有《鸡王镇宅》传统年画。”②殷伟编著:《图说门神》,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20 页。接着门神出现了文字形式的演变,“酉”字在很多地方充当了门神的作用。究其民俗学解释,有多方面。其一,“酉”字相传为姜太公的名讳,而且太公又是酉时出生;其二,“酉”通“有”,有富有的吉祥寓意;其三,“酉”与属相鸡有关系,按照民间思维“酉”自然也少不了灵气。因此,许多地方民居都会贴“酉”字,天津有民谚为证:“二十九,贴倒酉;三十夜,守一宿。”在门神家族中,形态变异最多的就是历史或神话人物,且每一个门神都有独特的民俗学解释,地域不同,门神不同;需求不同,门神也不同。人物类的门神普及最广的要数神荼、郁垒、钟馗、秦琼、尉迟恭,除此之外还有武将门神孙膑、庞涓,文官门神魏征、包公等。人物类门神的形式与时俱进,“样板戏中的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等打胜仗的英雄成为动乱年代的‘门神’;在20世纪80 年代大量印刷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九大元帅戎装骑马像’也被庶民百姓贴在门上威风凛凛地作了守护神。”③戚序:《心灵的渴求——浅论门神源流及其演化》,《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3 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神形态越来越拟人化。从虚拟的观念变成植物(桃符),从植物演变成动物(虎、鸡),从动物又变成人类文化特有物(酉、聻),从文化特有物到人类本身(钟馗)。时间上门神不断演变,空间上门神各司其职。早期的门神遍布各处,大到路口、寨口、山口、桥头等,小到宅门、厅门、帐门、闺门、门侧、门楣、门扉等,都能找到其身影。除了前门门神大放异彩外,后门有唐代股肱之臣魏徵把持。山东潍县专门贴在猪圈门上的“栏门判”(又称“打猪鬼”),民间用意是为猪消灾祛瘟。俗话说“大门辟邪,二门祈福”,大门张贴的门神主要用于辟邪,二门或内堂张贴寿星等人物门神,祈求家庭吉祥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神张贴地点不再受限制,不再遵循原来的惯制。门神时空形式的变异主要在于:“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加强了,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对自然力的恐惧,这使得人类对物欲的奢求无限度地膨胀起来。这一现象也反映在门神上,即人们双重祈祷的重心逐渐从辟邪向祈福转移,辟邪意识逐渐削弱,祈福意识成为其主要内容。”①戚序:《心灵的渴求——浅论门神源流及其演化》,《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3 期。
门神在时空上的变异性体现了民俗的基本特性之一的变异性。不断演变的门神推演出了门文化研究的延伸性,反过来,门文化的延伸性是基于门这一实在的物质载体进行延伸,并不是没遮拦,既保证民俗学视角解读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又保证了方向性。人们对生活幸福美满祈愿的渴求,不会终止,且因时因地变异着,这种民俗文化的变异性使得门文化的延伸性有了源源不断的民间资源,门文化的延伸性也规定民俗变异性的出发点和临界点。
四、从节日民俗的稳定性看门文化的复制性
“岁时节日,主要是指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131 页。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岁时节日民俗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期相对地固定下来并相沿成习。
门作为家户的“门脸”,建筑内外空间的连接口,每逢佳节来临,节日的气氛在门上表露无遗。有关门的习俗程式繁琐,历代延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不同的节日,各地以不同的形式装点着自家的“门脸”,但是整体观照与门有关的节日习俗并查阅相关民俗志发现,每个节日总有标志性的民俗元素与门“如约而至”。
正月十五,俗称元宵节,火树银花,万众云集,是民间活动最为活跃的节日之一。届时家家户户将灯笼挂在门上,节日文化通过“门”这一载体表现出来。这亦是元宵节称为“灯节”的缘由。《深泽县志》记载当时的岁时民俗:“元宵,张灯于门,结烟花,架火树银花,前后三日。”《泽州府志》记载:“上元设脯糒果醴,悬灯于门外,列炉焰名曰‘人火’,有范土像人物者,中空吐焰,光彩腾灼。”《水龙吟》也写道:“少年闻说京华,上元景色烘晴昼。朱轮画毂,雕鞍玉勒,九衢争骤。春满鳌山,夜沉陆海,一天星斗。正红球过了,鸣鞘声断,回莺驭、钧天奏。”大量的民俗资料显示,元宵节张灯的习俗是与门有关的全民性礼俗。清明时节,插杨柳于门上的民俗事象十分常见。《吴中岁时杂记》:“清明日,满街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武进岁时记》:“清明节,居民插桃花、杨柳于门,以祓除邪祟。”除夕,家家户户门上贴春联、换门神、贴画鸡、钉桃符,门前爆竹齐鸣,洒扫门闾。此外,正月初五送穷出门;农历二月二撒灰围门;农历三月三采荠菜悬于门;立春鞭土牛、贴春贴;谷雨贴符;端午节门上插艾叶;重阳节撒酒门前;腊月大寒杀鸡等,无一不与门文化息息相关。
节日的稳定性开展,维系了民俗的稳定性,稳定性成为民俗基本特性之一。门文化的稳定性使得逢年过节时,门与特定民俗符号如约出现。岁时节日期间的民俗文化元素反映在“门面”上的具体内容和称呼,由于地域、民族、习俗之不同而不同,诸如贴门笺,亦称“挂千”“挂签”“挂钱”,天津称“吊钱”,鲁南叫“过笺”“花纸”,江苏南通叫“喜笺”等。同一事象有多种称呼,不明就里就会产生文化误读。通过民俗学的视角能够透视与门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各种事象,发现其文化本质的属性,形成地方性知识的比较与串联,找到节日民俗的稳定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佐证。从节日文化在门上民俗指符的定期出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体现出门文化的稳定性。特定区域的地方性节日中表现出的门文化,从整个节日的普及范围以及应用数量上看似乎破坏了稳定性,但纵观地区历史发展,门文化的内核依然没变。以门为信息载体,通过民俗符号完成地方性知识的巩固与传承。由于其稳定性,在空间上由面到点,与门有关的民俗文化被同一文化空间的民众争相效仿。在时间上,这些节日习俗自先秦两汉就已产生,一直传承到现在,代际体现其稳定性,形成与节日有关的门文化习俗,体现门文化的可复制性。反过来,门本身有其固有的建筑文法。其特点在于建筑构成有其固有的内在机制与衔接模式,通过一定的模式和形制进行复制,形成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形式系统。门文化是基于此系统而编织成的形而上的结构体系,如清明门上插柳的文化习俗,通过定期的重复的视觉效果,最终达到心理映射的默许,伴随这种单纯、持续、重复的程式实现俗民的情绪与情感的累积,汇聚成民众的根本文化诉求。门文化的复制性从时空两方面通过现实呈现的稳定性不断地复制着先前的文化,使得民俗的稳定性更加牢固。当代建筑在西方与现代化转译过程中,他者节日开始介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文化的兴盛,使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但是,抛开多样性的外在肌理,其最根本的还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民间追求福禄寿喜财等现实情感的复制,强化着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因此,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为门文化的复制性提供了保障,门文化的复制性在时空上不断强化着民俗文化稳定性,二者形成双赢。
五、从仪礼民俗的服务性看门文化的实用性
“人生仪礼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156 页。人生礼仪的实现过程具有民俗基本特性之一的服务性,而这种服务性往往通过各类民俗类型展示出来。
门作为中国建筑文化元素的集大成者之一,充当了人生礼仪展示的重要物质载体。诞生仪礼作为民俗事象一直在民间十分重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产妇临盆之际,人们借助开“门”的象征仪式,把家中里里外外的门都打开,迎接新生儿的降临。民间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产妇开骨盆,保佑母子平安。与门有关的求子仪式中,摸门钉最为典型。门钉是门板结构上构件铁钉的钉子头,横竖排列形成一种装饰。门钉的色彩和数量代表了封建社会时期主人的地位和权势。摸门钉风俗大概在清代才出现,地域也限于中原地区,尤以北京、河南等地盛行。年轻已婚妇女,必到正阳门摸城门上的门钉,当地人称“宜生男”,原因有三:第一,“钉”和“丁”谐音,古汉语中“丁”指男人,如“壮丁”“丁口”等,“门”又音“问”,这样“门钉”就变为“问丁”,具有祈求男丁之意。第二,门钉有辟邪作用,没病防病,有病祛病。第三,门钉的数量为九,古代单数为阳,同时,门钉的形状像男根,隐含着生殖崇拜。与诞生仪礼相对应,民众离世习俗也与门文化息息相关。青海河湟地区汉族在人去世后,卸下堂屋大门的门扇作为灵床。无论天气冷暖,屋门一直敞开,直到出殡后才能安装回去。人们相信,门洞大开便于灵魂出入。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家缺少床板,用门扇代替床板再好不过了。江浙一带父母去世,贴白纸,扎素牌楼。当年门扇需张贴蓝色纸,次年用绿色,第三年恢复红色。三年为一周期是因为老人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在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盛行的古代,忠孝一直为人敬重的品质。对于失去亲人悲痛的心情,不易且不便表现在脸上,于是,门就成为了传达其情感的载体,孝顺的人会受到他人的尊敬;同时,贴纸也是给鬼神看,“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素纸的张贴说明自己是个孝子,鬼魅就不会惊扰孝子。对于用色浓淡方面,随着亲人去世的时间推移思念之情逐年递减,通过门上约定俗成的色彩饱和度来表现感情的强弱,让人一目了然。
人生仪礼通过展示与象征服务于人与人、人与环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服务性是民俗基本特质之一,它是民众统一的意志与行为践行中满足特定需求催生出的特质,也是仪礼民俗基本特质之一。门在仪礼民俗中充当了物质载体,在特定场域中体现出其服务性的特质,离开了特定的场域,门仅仅作为普通物质而存在。如在婚礼中,民间文化赋予门在特定场域的地方性知识信息,门作为男女双方各自门户的标志。整个婚姻仪式的进行、衔接与延续都离不开门,从上门提亲开始,经过拦门礼、新娘出门、新娘过门、回门,完成门当户对的连理结合需求。正因为门文化贯穿于婚姻仪礼当中,才能实现过程承启、情感表达、阻隔抵御、强化稳固与需求满足,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换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缔结。从上述门文化的服务性不难看出,实用性是门文化的特质之一。反过来,门文化的实用性要求民俗文化能够服务于现实,那些在现实中无法体现服务性的门文化,只能封存于历史之中。如史前社会中早期穴居与巢居满足采光、通风、出入而出现的门。随着时代的演进,门文化的一些原始实用性不复存在,而新的文化信息不断投入、填充到门文化中,使得传统的门愈趋于新功用及美学的实用性偏向。“1983 年在河南偃师尸沟乡发现的早商城遗址中,可以明显看出东西两侧城墙均开两个城门,而且相互对位。”①周力坦:《中国传统建筑的门文化与形式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10 页。虽然它的原始文化的实用性随着封建王朝的倾覆已不复存在,但是它被时代又簪嵌入了新的文化实用性,对于考古学、美学、建筑学、史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实用。
要想实现民俗文化的服务性与门文化的实用性二者共赢,必须保留与传承传统的物质遗产,文化的再加工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具有施展的空间,实用性才能熔铸其中。不可否认,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审美趋同化,新型技术、艺术思潮等当代文化指符侵占了门的民间文化份额,但是无论门文化如何的丰富,门作为“门”文化存在的基础,仍然是它的本体。其民间文化历史的固有属性依然存在于“门”这个本体,只是与过去传统文化影响下门的实用性一枝独秀的局面有所不同,当下社会呈现的是与时代文化、外来文化、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同存在于“门”之上,拓宽了其实用性的场域。因此,民俗文化在仪礼中的服务性满足了门文化的实用性需求,门文化推陈出新的实用性需求为民俗的服务性提供大展拳脚的场域,引导中国门文化向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六、民俗学视角研究建筑的当代价值
建筑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从形式层面来看,建筑的外部形制、物理空间记载了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即使发生在建筑内外的相关活动消失,建筑本身的形式语言和空间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民众仍能通过信息的采集和知识的获取,从而获得建筑相对应的时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体悟。从载体层面来看,建筑的外部形制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可能完全传承下来,只有让建筑“活着”才能全面展示其所记录的真实信息,建筑的物理空间以及在物理空间内发生的活动共同构成和表述着建筑所呈现的文化。从研究层面来看,“如果仅仅对物理空间进行形态学的描述和认识,不联系建筑内进行的人类活动,也并不能全面解读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尤其是,不能关照建筑及其活动作为历史的产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也不能进一步认识建筑背后更为广泛的制度及信仰、风尚等社会思想情况,因此也就无法明了建筑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①郭华瞻:《民俗学视野下的祠庙建筑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论文,2011 年,第6 页。
常青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建筑的一些内在含义是经由场景和仪式来表达的,只有探究逝去的场景和仪式,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昔日建筑的价值和意义。”②常青:《建筑学的人类学视野》,《建筑师》,2008 年第6 期。在一些国家,民俗学被看做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学科归属来看,把民俗文化学也归类到了人类学一级学科下。许多高校设置民俗学硕士、博士点,授予学位的类别有文学、法学等。不尽一致的主要原因,就是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尚在健全成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有较大的区别。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特有的文化现象。
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其研究领域正在日益扩大。从早先的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扩展到包括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岁时节日、人生仪礼、信仰民俗、民间艺术等在内的民俗事象。民俗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作为随着人类发展不断改变的建筑文化,与民俗的关联更是日趋密切和广泛。
运用民俗学的知识和方法,分析与建筑有关的民俗事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熟悉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内核,即价值观。“要想真正了解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了解传统民俗事象对建筑的影响,以及建筑对人民生活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对民俗学的研究,建立起民俗学与建筑的联系。”③韩宝山:《在建筑设计中注意对地方民俗特色的保护》,《建筑学报》,1985 年第12 期。
以往关于建筑和民俗的研究大多处于割裂状态,民俗学和建筑学各自按照学科属性研究特定的对象和内容。即使二者偶有交集,更多的是浅层次的。“在民俗学领域,有关建筑工匠的信仰,如厌胜、上梁、立基等礼仪,有关生活方式、行为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已被陆续揭示出来,这些民俗事项均和建筑密切相关;建筑界对民俗活动、民俗心理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①郭华瞻:《民俗学视野下的祠庙建筑研究》,2011 年,第5 页。建筑学研究民俗方面更多注重实践操作,收集了大量的现象与事例,至于现象背后的地方性知识解读往往并不十分全面,而且建筑学更多关注地方匠作并在已有的经验构架中因地制宜地内容填充,渐入缺乏深度的俗套。以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建筑,成果较少,这就相当于在房子上雕龙画凤,却没有坚实的地基,仅仅凭着感觉走,这会造成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往往倒是最生疏的一样。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是区分室内与室外等物理空间的建筑部件。门既可以作为建筑的一个部件,也可以成为一座完整的独立建筑。门是中国传统建筑演变中造型演变最多的建筑部件之一。门文化所体现的符号意义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的重要元素,它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经过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化,已然和门浑然一体,成为门的另一种象征物和民俗指符,成为门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②马知遥,刘智英:《民俗学视角下门文化的功能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7 年第1 期。与门有关的生活民俗需要类型性阐释,同样,与门有关的信仰民俗也需要类型性阐释,二者都能推演出门文化的复杂性;与门有关的信仰民俗具有变异性,与门有关的生活民俗也具有变异性,二者也能推演出门文化的延伸性。由此可见,与门有关的民俗文化都具有民俗基本特性。关注与门有关的生活民俗的不同点,门的某一民俗特质就会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门的民俗基本特质与门文化的特质却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类型性——复杂性、规范性——界定性、变异性——延伸性、规范性——复制性、服务性——实用性。这种民俗特质与门文化一一对应关系长期的累积,为民俗学研究建筑提供了可行性。从现实层面,门的民俗文化包括生产、生活、艺术、信仰、传说、节日、礼仪等民俗,这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平台。从文化层面,二者文化特质的一一对应关系,具有一致性和双赢性,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深层的文化共性。而这一文化共性得以实现的原因,得益于我国建筑文化的内核是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断定,体现在建筑上则是几千年整体性建筑形制的约定俗成。即使有小部分的修缮式的更迭,但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使本土性居住环境长久稳定下去。中国的门文化仅仅是中国建筑中的一个元素,其他的建筑元素或者建筑本身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民俗文化,在文化层面上二者也存在着文化特性的一致性与双赢性。从民俗文化研究门文化的可行性也为民俗学视阈下的学术探索建筑文化提供了借鉴意义。
毋庸讳言,我国特色的建筑要想适应未来的科学动向,诚然要不断学习西洋之法,不然就会步入本土主义的窠臼,而且当下建筑文化中也出现国际交流的痕迹。“东北满族民居、青海土族民居、新疆及中亚塔吉克族民居的平面布局多有相似之处。”③张力智:《桃花源外的村落——中国乡土建筑的研究拓展及其意义》,《建筑学报》,2017 年第1 期。但是,我们也应该追溯我国本身的建筑文法,提炼传统建筑的中国质素,而这种质素与文法离不开民间,离不开传统,正如欧美街心纪念性雕刻物是经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一样。建筑史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建筑是历史的反映”。建筑把几千年历史积淀熔铸成为凝固的记忆,民俗学是让这部分记忆恢复与活化,民俗学关注建筑不仅仅关注建筑的过去与现在,不仅仅是把建筑封闭到历史的大牢中解读“传统”,更是在动态发展中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阐释过去或现在建筑中蕴含的民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还关注建筑的未来。民俗学的介入对建筑设计与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元素,打破“国际式”建筑,打造“新中式”建筑,成为践行“民族的即是世界的”最好的现实佐证。同样,建筑的存续与发展也会推动民俗演化。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说过:“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①吴良镛:《北京宪章》,《时代建筑》,1999 年第3 期。,这将是建筑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乡土建筑熔铸时代元素,呈现多元发展之势,但是依然脱离不了固有的结构,在建筑布局、民俗特色、雕刻艺术、装饰图案、相地风水等中加入时代性元素,从现实、抽象、象征方面丰富了民俗文化内涵。现当代建筑不断地创新,为地方性知识提供可展示平台以及可发展空间。“民俗文化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影响力空前重要,民俗文化从作为地方区域发展的产业资源逐渐向作为实现地方认同的象征载体转型,民俗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中国‘地方性知识’形成的关键问题。”②张士闪:《关注民俗传统的现代转型——〈2012:中国民俗文化年度发展报告〉述要》,《中国文化报》2013 年2 月8 日,第3 版。民俗文化在地方性知识中的份额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空前重要,它借助现当代建筑的先锋性,将民俗元素、传统符号、乡土标志与先进技术、思潮理念融入到建筑中完成共生共存。引入民俗文化的现当代建筑成为其最好的广告,昭示民俗文化当下的生命张力,消弭地缘文化缺乏活力的弊端,拉动地方文化发展的马达,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特色的建筑美感。
总之,民俗学是在扩大学科研究对象并规范自身范式过程中找到与现当代文化的衔接机制,而建筑学是长久在西方单向度的文化输入中体悟到传统文化回归的价值,二者可行性的建立正是互补双赢,表里共生的开始。它利于找到二者的平衡模式,出现新的碰撞与交融,探索出“新中式”更多的理论性可能,完成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命题中的传续与发扬。建筑学与民俗学的未来也在追寻这一理性之路中嬗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