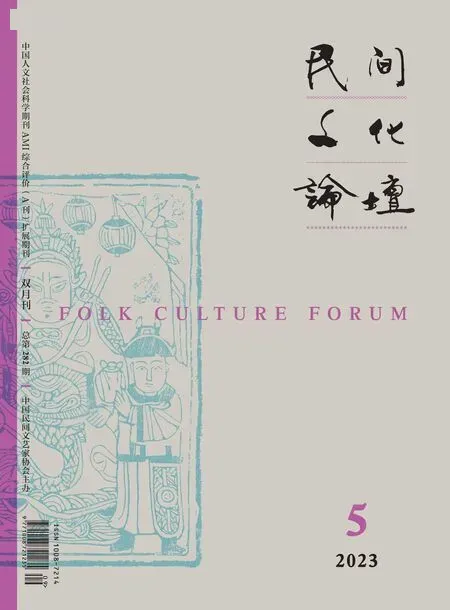多民族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 郝苏民民俗学思想评述
李建宗
人生阅历决定学术视野,对于一位学者来说,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仅增长了自己的见识,还在历练中形成了特有的豁达和睿智。从20 世纪30 年代到21 世纪30 年代,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如果把这一时间段与一位学者关联在一起,一方面是鹤龄或高寿的美誉,另一方面是漫长的人生。就人类社会而言,有些时段显得相对平静,而有些阶段比较喧嚣;与此相对应的人生,要么一帆风顺,要么跌宕起伏,其中不乏艰辛与坎坷,抑或充溢着几分浪漫。当一位学者到了晚年,不免会出现回顾人生的情形。此时也许在情感世界掀起一股汹涌的波涛,也许内心平静如水而坦然面对消逝的时光,或者是一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慨叹。每当回想起生命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迹,会有一种人生无愧的感觉。郝苏民出生于1935 年,2023 年已经接近90 岁高龄。长期以来,他的辛勤付出与默默耕耘,不仅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期刊编辑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的无私奉献惠及学界。杨圣敏在评价郝苏民时指出:“他不仅是西北民大的学术领袖,在全国民族学和民俗学界,也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①杨圣敏:《热情如火的学者和掌舵人——郝苏民先生》,《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年,第36 页。
一、以多民族研究打造民俗学学科建设团队
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学科建设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但又不太容易的事情。20 世纪90 年代,国内高等院校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当时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已经开展学科建设,而西北地区的很多高校的学科建设意识还比较弱。在学科建设中会遇到怎样建设,围绕什么建设,如何打造研究平台、整合研究团队等一系列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团队负责人的视野和魄力。20 世纪末,国内很多高校的优势学科是中文、历史等传统专业,相应地在民族院校有特色的学科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史等。当时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基本上分布在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因为这些高校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与学术传统。恰恰相反,以上学科正好是西部高校的“短板”,当初的学科建设存在诸多困难。就当时的西北民族学院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优势学科,学科团队负责人郝苏民结合学校的优势学科,以长远眼光精心谋划,开启了民间文学与民俗的学科建设之路。朝戈金曾经从领军人物的角度谈到郝苏民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①朝戈金:《领军人物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西北民族研究》,2015 年第1 期。
郝苏民所学专业为蒙古语言文学,早期从事蒙古语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研究,多次在蒙古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还在同属蒙古语族的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地区进行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考察,搜集、翻译、整理了一些蒙古语族群的民间文学。他先后译编《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②郝苏民、薛守邦译编:《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年。,编写《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③郝苏民编:《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选编《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④郝苏民选编:《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在搜集、整理和译编蒙古语民间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蒙古语口头传统与民俗研究,出版《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⑤郝苏民:《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朱刚在评价这本专著时指出:“孰不知一个优秀的民间文艺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兼通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民俗等诸种学科的学者。《透视》的作者就是上述学者中的典型之一。”⑥朱刚:《沉钩漠海 独得珍宝——评郝苏民及其专著〈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3 期。在《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中,郝苏民把蒙古口承语言文学看作文化,并且强调蒙古口承语言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郝苏民曾经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口承语言民俗”方面的课程,强调在口头传统的研究中注重文化语境。就像在《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的“引言”中所说:“换言之,我们所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现今而言,应该是指包括中国56 个民族的传统文化。”⑦郝苏民:《引言·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4 页。郝苏民早期对于蒙古口承语言民俗以及八思巴文的研究奠定了他在民俗学界与蒙古学界的重要地位。⑧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入门(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在学科建设中科研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当初的西北民族学院既没有民族学系也没有社会学系,只有利用全校的力量组建科研平台。经过郝苏民不懈的努力,1984 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西北民族研究所”⑨郝苏民:《仍是机遇:需从澄源正本接力起——关于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课程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2 期。,意味着西北民族学院的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平台诞生了,郝苏民带领的团队围绕这一平台开展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研究生培养和服务社会,当时的“西北民族研究所”在西北高校中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平台。1998 年,在“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基础上,西北民族学院成立“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是一个教学系和研究所合一的机构。⑩郝苏民:《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1 期。它既是科研平台,又是教学机构。围绕此平台,郝苏民团队一方面开展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民俗研究,另一方面承担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由于郝苏民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在学科建设中能够打破学科边界的局限,以民俗学为中心带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由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在郝苏民看来,学科的边界是人为确立的,在学术研究中学科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他一直倡导“大社会学”的学科观,“大社会学”就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在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科建设中,以民俗学为基础,同时围绕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展开,后来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又拓展了社会学的园地。郝苏民认为,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不断提升学科理论,同时还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团队建设过程中,郝苏民以“大社会学”的学科观建设学术团队,在团队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以“大社会学”的布局来谋划团队建设和学科发展。“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长期招聘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高级专业人才,同时根据学生实际鼓励本学科点的硕士研究生攻读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在现有的学科团队中,依照成员的学科背景为他们规划研究方向。还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委派团队成员,以便提升他们的学术水平。就像马戎所说:“郝先生对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建设下了许多的功夫,特别是对年轻人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培养与扶持。”①马戎:《郝苏民先生对北京大学民族研究的支持》,《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7 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团队建设,一批年轻人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有些已经发展成当前西北民族大学学科点的学术骨干力量,为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实现多学科发展对于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郝苏民看来,学科交叉与学科互鉴是学术研究进展的重要途径,学科边际是人为设置的研究“圈地”,只有突破学科边际的局限,从学科型学术转向问题型学术,才能在研究上实现突破。当然,要突破这种局限性,需要学科带头人的视野和魄力,否则难以打破已有的学科边界和范式。正因为作为团队领头人郝苏民独特的学术视野和从事学科建设的能力与魄力,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得以快速发展,在西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为学术界公认。特别是在多民族研究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多民族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多民族民俗研究的前瞻性与独特性
西北地区具有丰富的多民族民俗,郝苏民小时候在宁夏银川市的一个多民族社区生活,1960—1962 年到甘肃省夏河县的甘加草原,在这里他接触到藏族文化并学习藏语。由于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背景,1971 年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蒙边界进行考察,在考察期间郝苏民居住在蒙古族牧民家里,和当地蒙古族牧民进行深入交流。长期以来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使他对西北多民族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甘肃甘南、内蒙古锡盟的这一段时间,郝苏民先生经受过多元文化的浸润,在自己的身上形成了一些“自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使他吸收了多元文化,生活经历使他对多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1991 年,西北民族学院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学位点开始招生,在本学科点上,最早的几届研究生选题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多民族地区,围绕多民族民俗开展研究,田野点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地的蒙古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藏族等多民族地区。当然,还有部分研究生在汉族地区选择了田野点。后来,西北民族学院民俗学学科点研究生的选题范围逐步扩展到国内多民族地区。郝苏民强调民俗学研究的“他者”立场,经常提醒学生在“自我”研究中要跳出定势思维。他倡导民族文化需要从多角度开展研究,并非本民族的学者一定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也体现了郝苏民的学术视野和胸襟。郝苏民指出:“事实上我们这个自然形成的志同道合的学术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总体都系田野民族(俗)志‘从业者’,但内在的学养(学历、志趣、认知)背景,也呈现了多元因素,既有属于主体文化的民族,又有属于少数族群多元文化及不同性别的成员,也存在甲研究甲、乙研究乙,也有甲乙互换研究对象的事实,更有懂主体与母体两种文化、语言的研究者,同时也存在相反知识背景的从业者,及乙研究丙等现实。凡此种种,不正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早已形成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种历史铸就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的事实吗?”①虞耕:《缘起:各讲各自的在场故事》,郝苏民主编、袁同凯等著:《笑问客从何处来: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故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年,第19 页。郝苏民一直认为,在西北地区多民族文化中,汉族民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研究生论文中,出现了一些有关汉族民俗文化研究的选题。
在西北多民族民俗研究过程中,郝苏民团队深刻地认识到多民族文化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及“多元一体”思想的重要性。正如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多元一体是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文化现象,对于‘一体’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是56 个独立的多元文化的简单拼凑、总和,而是56 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源点,并在历史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中,既保持特色又彼此渗透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凝结成一个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价值追求。”②蔡秀琴:《“一体”与“多元”——访著名民间文化学专家郝苏民先生》,《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3 期。郝苏民在多民族民俗研究过程中,长期探索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多元一体”分布格局,关注多民族民俗之间的内在联系,郝苏民在回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强调“多元一体”③郝苏民:《二十一世纪:世变方激,中国回族研究急需社会学/人类学的大视野》,《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4 期。。在甘青特有民族的文化形态研究过程中,郝苏民团队从社会现实出发,“对五个特有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融、互补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和勾勒,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乃是‘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论点。”④郝苏民主编:《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序言”,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2 页。郝苏民与费孝通、谷苞等之间有着一定的学术交往和交流,他们的学术思想对郝苏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元一体”成了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郝苏民在学术研究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探索和分析多民族民俗文化,在当时无疑具有独特性和前瞻性。正如在《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的“引言”中,郝苏民论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指出:“在这个宏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中,既包涵有每一个个别民族纵向的具有个性特征的传承文化;也包涵着各民族之间横向的扩散,即相互接触、影响、吸收、互补、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为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的文化。”⑤郝苏民:《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引言”,第4 页。20 世纪90 年代,在郝苏民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对“中华民族”有了深入的理解,同时认识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多民族民俗研究的意义。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郝苏民能够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切入研究蒙古族民俗,可见他的认识的高度。正如林继富、覃奕指出:“郝苏民是感受者、参与者,也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融入学科建设思考的开拓者。他在开展民俗研究时强调多民族互动,即呼应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①林继富、覃奕:《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郝苏民民俗学建设思想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第3 期。
郝苏民团队进行西北多民族民俗研究,首先对具体地域和民族的民俗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弄清楚特定地域/民族的民俗特征。其次,通过比较的方法进一步分析研究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的异同。在多民族民俗研究中,郝苏民一直强调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他看来,多民族共有的文化大部分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郝苏民曾经组织研究团队以丝绸之路的视野对甘肃、青海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五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开展调查研究,研究成果为《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②郝苏民主编:《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在这本著作中呈现了甘青地区多民族的文化形态,在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为多民族文化的“异”“同”关系及多民族民俗同质性形成机制,核心思想就是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袁同凯、康红欣在评论这部著作时指出:“郝苏民的《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一书综合运用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与辨析了甘青地区特有民族的文化形态以及各民族间民间文化相互影响、各自变迁、互化的动态过程。”③袁同凯、康红欣:《从〈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一书说起——纪念郝苏民先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60 余年》,《青海民族研究》,2018 年第2 期。
长期以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强调地域/民族的特殊性,而较少关注不同地域和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同质性。郝苏民在多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探讨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其实这是郝苏民的心系国家胸怀天下的体现。毛巧晖在评价郝苏民时指出:“他在教学、研究、办刊中,注重‘跨学科’研究,始终把推动多民族文化交流作为毕生事业。”④毛巧晖:《郝苏民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在场者”的历史表述》,《民族文学研究》,2020 年第4 期。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中,郝苏民深刻地认识到,探讨中华民族认同是多民族民俗研究的使命,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们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就要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里的民俗学。”⑤王彦龙:《改革开放40 周年、中国民俗学诞生100 周年——郝苏民教学人生与学科建设访谈记》,《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4 期。
三、多民族研究生培养的育人实践探索
郝苏民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学科建设者和期刊创办者,更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多年来,郝苏民招收多民族的研究生,利用本民族学生的语言优势开展多民族民俗研究,但他经常提醒研究生,不要局限于本民族的“主位”研究视角。郝苏民倡导对本民族之外的“他者”进行研究,正如他所说的,在自己的研究生中有藏族同学研究回族民俗,有羌族同学研究藏族文化,等等。多民族口头传统的研究是郝苏民关注的重点领域。在研究生复试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少数民族考生,总是要问询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郝苏民长期探索研究生教育创新模式,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教育教学中传递学术的薪火。正如马东平指出:“郝苏民先生一直把自己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看待,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学者、研究者。”①马东平:《情系民俗 拓荒深耕——郝苏民先生学术事迹评介》,《甘肃社会科学》,2015 年第3 期。在研究生培养中,郝苏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对每一个学生有很高的学术期待,同时注重学生之间的差异,能够因材施教。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和阅读书目的指定环节中,作为导师的郝苏民非常认真和慎重。经过导师和学生之间不断沟通和商定,直到发现论文选题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之后,根据学生的选题内容开出一份阅读书单,对研究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以每位研究生的志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②郝苏民:《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1 期。
在课堂教学中,郝苏民的授课风格独特,经常在讲授过程中能够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在分析和阐释过程中运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导学生尽快形成学科意识,以便在后面更好地开展研究。在课堂上,硕士/博士研究生经常为他对民俗文化的深入分析所吸引,同时他善于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每当讲到一些关键的地方,有时候突然停下来进行讨论,考查学生分析和认识民俗文化的敏锐性和学理性。在学生培养过程中,郝苏民一方面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在读书和写作方面;另一方面,在学术讨论中善于以沙龙的形式进行,营造一个轻松的研讨氛围。在每周的师生见面会上,学生到会之前桌面上已经摆好了茶杯、甜点,这样的氛围冲淡了讨论和汇报的紧张,学生在沙龙式的讨论会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者的成年礼,也是人类学的学科共识,还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学位论文基本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生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基本技能。就像周亚成所说:“而我最受益、感受最深的是先生的田野教育,我从先生那里知道了田野、懂得了田野、实践着田野,在先生的引导中开始了以田野为主的学业、事业之路。”③周亚成:《郝苏民先生与我的田野之路》,《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146 页。在郝苏民的主导下,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点长期把田野调查作为民俗学研究的立足之本,一直践行着民俗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民俗学学科点上的每位研究生都有扎实的田野调查经历,各自也有很多的田野故事。为此,郝苏民主编了一本田野调查报告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故事》,其中收录32 篇田野调查报告。谈到本书的缘起时郝苏民指出:“由于书写惯例的影响或某种‘误解’,研究者们自己的田野故事最终也没有呈现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之中。”④虞耕:《缘起:各讲各自的在场故事》,郝苏民主编:《笑问客从何处来: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故事》,第16 页。
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生培养,开放办学是非常必要的。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对民俗学学科点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郝苏民先后多次拜访费孝通、钟敬文等学科领域的学术泰斗,在学科建设与学生培养方面不断向他们取经。就像董晓萍所说:“郝先生无数次地来往于兰州和北京之间,不知疲倦、不辞辛劳地向钟老、向费老请教各种学术问题和工作问题,前辈学者们也都尽心尽力地提供帮助。”①董晓萍:《钟老的西北情与郝先生的中国梦》,《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25 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郝苏民团队进行了很好的合作。2001 年7 月,由北京大学与西北民族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兰州召开,费孝通给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揭牌。马戎曾经提到,“这些年来北京大学的民族问题研究离不开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和学者们的大力支持,其中与我们最早建立合作关系并始终给予我们重要支持的就是西北民族大学的郝苏民先生。”②马戎:《郝苏民先生对北京大学民族研究的支持》,《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8 页。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团队对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点早期委派研究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还推荐研究生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对外交流是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动力。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生教育中,郝苏民不仅仅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学术合作,同时还积极推动与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通过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郝苏民多次邀请国内有影响的学者来西北民族大学开展学术讲座,把国内前沿学术动态通过讲座的形式传送到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点,使本学科点的师生受益。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郝苏民具有国际视野,很想让学生了解国际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前沿领域。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强调学生的英语水平,鼓励英语水平高的学生阅读英文原著。正如袁同凯所说,“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恢复不久,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还局限在国内,缺乏国际视野,很少有人能看到英语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郝先生看到了。”③袁同凯:《西北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孵化基地的奠基人和引路人——献给恩师郝苏民先生八十寿诞》,《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159 页。郝苏民还邀请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来西北民族大学讲学,2010 年6 月16 日邀请美国后现代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到西北民族大学做了题为《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15 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sited Ethnographic Research)的演讲。④[美]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满珂译,《西北民族研究》,2011 年第3 期。1990 年11 月15 日至18 日,苏联通讯院士、吉尔吉斯斯坦学者苏三洛·穆哈莫德·牙斯孜教授到西北民族学院进行为期4 天的学术访问。⑤振一玉:《苏联著名东干族学者苏三洛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2 期。郝苏民先后多次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1991 年5 月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考察了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⑥学林:《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教授访苏归来》,《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2 期。,1997 年赴日本讲学⑦依白:《郝苏民教授赴日讲学》,《西北民族研究》,1997 年第2 期。,2000 年参加在韩国举办的第3 届亚细亚民俗学会国际学术大会⑧《省民俗学会会长郝苏民教授出席在韩国举行的亚洲民俗学会年会》,《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1 期。。通过短期的学术交流,郝苏民领略了一些国外学人的学术风格,掌握了一些国外学生培养的信息。
经过自己辛勤的付出,郝苏民桃李满天下。昔日门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还有一些成长为期刊编辑。据统计,截至2014 年6 月,以郝苏民为主导的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学位点共招收研究生157 名,其中150 名获得硕士学位。硕士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二考取博士,他们中有些在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获得博士学位,有些完成博士后流动站的学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间文学方向)博士点自2004 年开始招生,至2014 年6 月,有23 人获得博士学位。①郝苏民:《几门学科在这里,我们“爬坡”走过30 年(代序)》,《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7 页。郝苏民的研究生培养具有格局意识,起初的格局主要是西北多民族地区,后来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点的研究生生源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蒙古国、韩国等国家的访学和留学的学生。②郝苏民:《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1 期。跨区域、多民族研究生的培养旨在开展多民族研究,以便进一步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机制。
四、服务学界和社会的情怀与担当
学界每当谈到郝苏民的贡献时,《西北民族研究》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期刊具有王铭铭所说的“同仁办刊”特色。③王铭铭:《郝师这个人物》,《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40 页。《西北民族研究》自1984 年创刊以来,郝苏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把其打造为学术界的精品。学术期刊是为学术界服务的,是展示学者学术成果的平台。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能够起到引领学界前进的作用,把最为前沿的学术成果刊发出来,引发学术界的讨论。长期以来,《西北民族研究》刊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与学者成果展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北民族研究》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关注青年学者的成长,扶持青年学者成才。曾经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论文的青年学者,有些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骨干力量。就像郝苏民指出:“《西北民族研究》积极扶持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各学科青年学人,自始至终坚持无偿并付稿酬刊发研究生、博士生优秀田野报告和新品佳作。”④郝苏民:《改革开放40 年之于我们——从〈西北民族研究〉出世成长的故事说起》,《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2 期。
《西北民族研究》创刊时,刊载关于西北民族研究领域的论文比重稍大一点,后来登载的文章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办刊宗旨是“立足甘肃面向西北,心怀全国对话国际”。这与主编郝苏民的学科思维和学术思想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为了提高办刊质量,主编郝苏民特别注重高质量的自来稿,同时在约稿上下大功夫,高质量的稿件使其成为品牌期刊。在郝苏民看来,尽管登载高质量的稿件是刊物生存发展的前提与保证,但对于读者来说,刊物的外在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追求稿件质量的同时注重刊物的装帧,每一期刊物的封面、封底、扉页、插图、开本等,其中都凝聚着他的思考和智慧。郝苏民的学术视野和艺术眼光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就《西北民族研究》的纸张问题,他多次与印刷厂不断沟通和联系,定期进行更换。2014 年《西北民族研究》编辑部在招聘编辑时,优先录用了一名美术专业的应聘者,后来在刊物的装帧设计以及微信公众号编辑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郝苏民在主编《西北民族研究》期间,每一期的“卷头语”是刊物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特色。刘锡诚于2013 年评价主编的随笔体“卷头语”时指出:“从1986 年起主持《西北民族研究》学刊以来至今30 年期间未曾间断,以每期一篇‘卷头语’的形式和文体留下来一串串脚印。”①刘锡诚:《序言》,郝苏民:《骆蹄梦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1 页。每一期的“卷头语”抓住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评析,篇幅短小,语言精练。《西北民族研究》曾经的“卷头语”体现了主编郝苏民先生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感受与睿智思考,其中也呈现了主编的语言风格。就如郝苏民所说:“这其中认认真真的近20 年生涯的兼职编辑,做嫁衣的冷热惊险与作秀,留下的是‘卷头语族’之类,香也罢,臭也罢,原本如此,求一个真字罢了。”②郝苏民:《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田野随笔》“后记”,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236 页。郝苏民担任主编期间,书评是《西北民族研究》的一个常设栏目。除了专门的书评杂志,比如《中国图书评论》《读书》《书屋》等,国内很多期刊都不刊发书评文章,《西北民族研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刊发书评的刊物。
对于学术界来说,办刊也是一种服务。正因为郝苏民具有强烈的服务学界的意识,愿意把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西北民族研究》上面,精益求精,为学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组“《西北民族研究》学刊发展笔谈”中董晓萍指出:“杂志风格严谨而开放,稳健而创新,不拘一格,不定调子,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为国家社会文化建设和多学科建设长期服务,贡献重大。”③董晓萍:《多民族、多学科、文化自觉的综合性刊物》,《西北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在偏远的西北,《西北民族研究》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地方社会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郝苏民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费老在1988 年为《西北民族研究》的题词是‘从实际出发,研究西北社会经济情况,为开发边区做出贡献。’”④郝苏民口述、毛巧晖整理:《做学做人终身求》,《民间文化论坛》,2020 年第1 期。《西北民族研究》作为登载西北多民族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在服务地方社会与国家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 世纪在中国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民俗学界的学者广泛参与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了中国民俗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域。郝苏民利用西北多民族民俗研究的优势,凝聚团队力量,积极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平台。2005 年成立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通过这一平台开展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最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郝苏民领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旨,即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对标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呼吁抢救和保护西北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文化(包括口头传统)。⑤郝苏民:《UNESCO 的新动议与我国口头/非物质遗产的抢救保护和申报——以西北人口较少又无文字的民族遗产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3 年第1 期。在此基础上,郝苏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研究甘青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保护机制⑥郝苏民:《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语言问题的讨论——从甘青“小民族”语言说起》,《甘肃社会科学》,2004 年第5 期。。郝苏民不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还热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活动中。曾江指出:“作为中国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近十年来,郝苏民承担了很多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⑦曾江:《在田野中积累地方性学术经验——访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郝苏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9 月19 日,第A03 版。通过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意在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意义。
无论是在学科建设还是学生培养中,郝苏民清晰地认识到民俗学是一门服务社会的学科。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一定要有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意识。郝苏民认为,一流的学术成果应该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与此同时,郝苏民也经常强调,在服务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理性。在他看来,学理性不足的研究成果服务地方社会的功效不大,甚至还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对民俗文化的研究不深入,就会在认识上出现问题,这样的成果在服务地方社会时不会有效。他还强调运用研究成果服务地方社会一定要谨慎,需要反复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论证。郝苏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保护过程中,认识到学术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一所学校,一个学科,一份期刊,一位学人。西北民族大学出现过一个“王牌学科”——民俗学。直到当前,有一本在国内学界有影响的刊物——《西北民族研究》。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界每当谈到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和《西北民族研究》时,就会提及郝苏民。郝苏民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眼光,胸怀天下的情怀,在从事西北多民族民俗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并在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和主编期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经惠及学林。扎格尔指出:“郝苏民教授是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①扎格尔:《学术研究者的典范 学科建设者的表率》,编写组:《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第86 页。郝苏民不仅仅给西北民族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奉献学术界,服务国家和社会,可谓筚路蓝缕创伟业,胸怀天下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