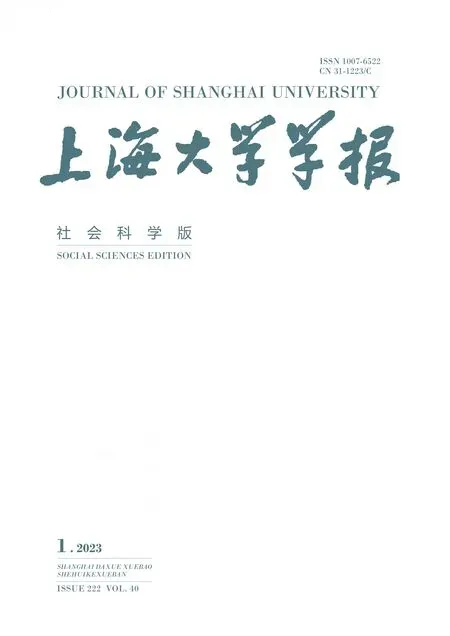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邵明珍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理学名家,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有着颇高造诣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朱熹批评过的名家名作相当多,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作家作品的批评呈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前者因为朱熹的揄扬而声誉日隆,后者则因朱熹的“批评”而备受非议,直到今天都未完全摆脱被“污名化”的处境。本文即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批评为例,对朱熹文学批评中的道德批评及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作一梳理和分析。
一
朱熹对屈原的揄扬,与其对扬雄的批评正好一正一反。在朱熹之前,班固等人对屈原的“露才扬己”以及自沉不无微词。而扬雄对此的议论,即“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1]则引发了朱熹强烈的不满与批评。
汉代对屈原评价比较突出的还有刘安、司马迁、班固与王逸。其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论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2]2481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显然持肯定态度。对屈原及其作品,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2503司马迁对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之高度评价,来源于淮南王刘安;对此,班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刘安论屈原“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实”,他进而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认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对屈原“沉江”之看法,显然与扬雄的观点基本一致。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对屈原的揄扬,但有意思的是,朱熹忽略班固却把矛头对准了扬雄,究其原因,或是因为扬雄有所谓的“失节”之过。据此,朱熹一方面对屈原及其作品大加褒扬,另一方面则对扬雄大加挞伐。
朱熹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主要集中在“忠”:
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3]255
在《楚辞集注序》中又说: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3]16
在朱熹看来,屈原处处体现着“忠君爱国之诚心”。如论《九歌》,朱熹认为是屈原见民间祀神歌舞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3]46至于《九章》,则是屈原“虽不得于君,而爱慕无已之心,于此为尤切”。[3]195针对前人批评的《楚辞》之“怨君”,朱熹也多方曲加辩护:
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4]4288
其实,《楚辞》中明显的“怨”之特色,并不妨碍其成为伟大的作品,朱熹为了强调屈原之“忠君爱国之诚心”,坚决否定其“怨君”,对某些篇章之释读,明显有牵强附会之处。
关于《楚辞》之怨,历来有着两种不同的评价。葛晓音总结道:
《骚》作为楚辞的代称,常与“风”并列,……但是《骚》诗产生不久,在汉代就遭遇了极端不同的评价。……刘勰对《骚》的看法是一种折中之论。大体来说,从魏晋以后,直到北宋以前,由于取尚雅正的观念十分流行,对于《骚》的示范意义始终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两种对立的评论。……经过西魏北周及隋初的文学革命,初唐以来对于《骚》的负面评价就日见增多,一度占据了主流地位。其批评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辞的华艳,二是内容的怨诽。……在杜甫的时代,视《骚》为怨靡之源的传统看法仍然影响很大。……杜甫为《骚》正名的意图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影响。直到白居易才肯定了《骚》之怨思得风人之遗意。[5]
可见,《骚》之“怨诽”是其客观存在的特点,而且,对其“幽忧愤叹之作”,在朱熹之前一直有着负面的评价。费衮《梁溪漫志》记载:
邵公济博,著书言:“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6]
很明显,即便在南宋,对于屈原及其《离骚》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据费衮之理解,司马光不收屈原作品,乃是因为屈原“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屈原之自沉,亦不合“圣人之中道”。而朱熹却有意淡化了屈原“怨君”之色彩,认为其作品“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还将《诗》《骚》并举,大大提高了《离骚》的地位:
《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辞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然学者之所急,亦不在此。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7]475
在拔高屈原之同时,朱熹对扬雄之批评可谓不遗余力。朱熹对扬雄批评的焦点在于“仕莽”,他反司马光等人对扬雄之维护,大笔直书“莽大夫扬雄死”。[8]在给尤袤的书信里朱熹明确说明了他的意图:
蒙教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9]
“失节”在朱熹看来乃是扬雄最大的人生污点,其《楚辞后语序》云:“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3]221就是因为所谓的“失节”,原本是“圣人”的扬雄在朱熹眼里几乎一无是处:
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同日语。[4]4237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4]4235
可以说,朱熹几乎完全改变了历来对扬雄的正面评价:“司马温公、王荆公、曾南丰最推尊扬雄,以为不在孟轲下。至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书‘莽大夫扬雄卒’……文公此笔,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10]朱熹在论及《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时也针对扬雄说:
只是上文“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谓明哲者,只是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是见几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扬子云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说话,所以它一生被这几句误。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义处,又不如此论。[11]
朱熹如此不遗余力地贬低打压扬雄,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失节”以及批评了屈原:“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3]249
事实上,扬雄并非如朱熹贬斥的那样不堪。班固就对扬雄的评价不低:“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1]3583三国时李康也曾论及扬雄:“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仲舒之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12]对此,有学者解释说:“通过一串排比句,征引故实,阐明高洁之士不希求没有价值的富贵权势。”[13]明显把扬雄看成并非“希世苟合之士”,而是门庭冷落的“高洁之士”。南宋洪迈也为扬雄辩护: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真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14]
洪迈之论,显然相对公允。其实,自中唐以来,直到朱熹之前,原本有一股尊扬的思潮,却因朱熹之挞伐而消歇。[15]46元代以后,道学定于一尊,对扬雄的评价基本延续了朱熹等人的看法。
二
屈原与扬雄,经过朱熹之品评,一个被刻意抬高,一个被打成“反面人物”。与此相类似的是,朱熹对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也是一正一反,而褒贬的标准同样也是“忠节”观念。
与扬雄批评屈原相类似,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曾经对陶渊明之“弃官”不无微词:“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16]王维写作此信意在说服魏征后人魏居士出仕,其中确实也流露了王维委曲求全的处世态度,但考其本意,乃是为国求贤、为魏征家族后人着想,不该因此而受到指责。而朱熹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褒贬,其起因也在于所谓的“失节”: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则纪逡、唐林之节非不苦,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翛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17]3662
朱熹之所以高度评价陶渊明的作品“士皆自以为莫能及”,就是因为其“耻复屈身后代”之“高情逸想”。相反,王维“失身”于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朱熹曾在北宋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基础上选录《楚辞后语》52篇,其中收录王维《山中人》等三篇,他在《山中人》题下云:
《山中人》者,唐尚书右丞王维之所作也。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独此篇与《望终南》、《迎送神》为胜云。[3]275
可见,朱熹评价作品的好坏完全依据其所谓的“失节”与否。由此,他过度拔高陶渊明作品的地位:
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诸篇……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而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7]762-763
朱熹把《诗经》《楚辞》及汉魏古诗作为第一等,认为是学诗、作诗的“根本准则”。在他看来,《文选》所载的汉魏古诗,郭璞、陶渊明的五言诗,可以附骥于《诗经》《楚辞》之后,价值仅次于《诗经》《楚辞》,同样可以作为学诗者的范本。
与之相反,原本在当时就经受了严格甄别而不再是“问题”的王维“失节”,到朱熹这里又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并且由于朱熹之批评,此一所谓“污点”至今还是影响评价王维及其作品的重要标尺。在朱熹之后,元人对王维气节的看法基本延续朱熹的评判,如作为道学家,刘因在《辋川图记》中完全因袭朱熹之观点:
后世论者,喜言文章以气为主,又喜言境因人胜,故朱子谓维诗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程子谓绿野堂宜为后人所存,若王维庄,虽取而有之可也。呜呼!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况可以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彼将以文艺高逸自名者,亦当以此自反也。[18]
元人吴师道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他在《辋川图》后题曰:“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水间,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19]直到现代,学界还在延续朱熹以来对王维的“污名化”评价,如范文澜即如此谩骂王维:
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20]
事实上,两《唐书》关于王维“受伪职”“失节”之记载与史实有不少出入。首先,君相代表的朝廷对突发的叛乱局势严重误判,是导致王维以及大量官员陷入敌手的根本原因。其次,安禄山下令将王维等“迎置洛阳”,王维却因企图逃跑而最终被叛军以“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的方式“缚送贼庭”。最后,王维是肃宗收复洛阳后,第一批被严加甄别的陷贼官员之一,王维出狱后,朝廷也没有将其“下迁”“责授”,而是“官复原阶”,还受到皇室成员的高度礼遇,而王缙也未因替王维“赎罪”而受到削职处理。但学界长期以来在对王维的陷贼、复官、参禅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明真相,由此造成对王维的种种“误读”和污名化。究其根源,我们不能不认为,此事是朱熹先以理学宗师之尊导夫先路,而范文澜则以著名史学家之威望而推波助澜。[21]
三
朱熹以“忠节”为核心的道德批评,其成因或许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朱熹是一个强烈关怀现实政治的道学家。南宋特殊的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环境,迫使南宋士人尤其是道学家特别注重现实政治,也更强调文人之忠节。熟读与朱熹有关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与给大家留下的道学家的刻板印象不同,朱熹并非一味地谈论心性等抽象的理论问题;虽然他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隐居深山精研道学,但他其实是非常关心民瘼、关怀现实政治的人物。他曾写信给友人说:“在官一年,不能为民兴利,而除害亦未能尽,此为可恨也。”[7]1119他甚至渴望像王安石那样可以“得君行道”:
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孝宗复召,先生一辞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见也。[22]123-124
朱熹反对南宋朝廷奉行的求和政策,为图改变,不仅与主张恢复的陆游、辛弃疾与陈亮等声气相求,而且还多次写信给朝廷重臣试图扭转时局:
熹也虽未获与闻其详,然有以见贤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尝一日而忘天下之忧,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旷其职盖如此。……盖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根本也。……此熹所以于前日之书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7]281-282
黄干作为其弟子与女婿,对朱熹之思想了解较深,他在《行状》里也如此论曰: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23]
朱熹关怀国事,“无一念不在于国”,但考朱熹一生行事,有大量时间是在“隐居”讲学中度过的,真正出仕的时间不是太长。其“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有他自己的考虑:“熹前幅之尾所禀,尤愿垂意。盖不合而去,则虽吾道不得施于时,而犹在是,异时犹可以有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则吾道不惟不得行于今,而亦无可望于后矣。……前日虽尝言之,然自觉有所未尽,故复喋喋于此。忠愤所激,至于陨涕。”[7]296其不合即去,是为了万一以后自己政治主张被采用,即便自己不能做官,归隐林下,也在所不辞:“熹再辞之章并一疏上之,……不知圣意定何如?自觉疏拙,无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颠踣。若得话行而身隐,乃为莫大之幸耳。”[7]448可见朱熹追求的是真正的“话行”,也即是自己政治主张的被采纳。余英时指出:“‘推明治道’是‘三先生’儒学的最精到的所在,也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推明治道’必然仍是道学的中心关怀。”[24]117“三先生”即受朱熹推重的宋初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余英时关于朱熹等理学家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有如下分析:
本书涉及理学家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内圣”之学为始点,但是他们同时也都是承担着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大夫,最后必须归宿于“得君行道”或“致君泽民”。即以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张栻、吕祖谦、陆象山、陈傅良、叶适等人而言,也没有一个是例外。……他们从事于“内圣”之学也主要是为了生活实践,而政治实践更占有特殊的分量。他们有道不行则退而讲学的意识,但还不能想像学问可以脱离实践而自成一独立领域。[24]590
朱熹很羡慕王安石之“得君”,而南宋偏安的现实,更激发了朱熹强烈的责任感,他与力主恢复的陆游、辛弃疾以及陈亮为友,乃是因为与他们有同样的政治诉求。朱熹因此特别在意“君臣大义”:“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17]3850洪兴祖补注王逸《离骚后叙》已经不无借题发挥之意,朱熹在《楚辞辨证》卷上称赞洪氏曰:“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近岁以来,风俗颓坏,士大夫间遂不复闻有道此等语者,此又深可畏云。”[3]188朱熹更是如此。
其二,朱熹对“忠节”重视与其家庭环境之影响也不无关系。朱熹叔祖朱弁曾出使金国十六年,全节而归,因忤秦桧而废死。父亲朱松早年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为北宋末较为知名的理学家,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相友善。朱松于北宋末登进士第,南宋初任尤溪县尉。后值宋金对峙,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和议,贬任江西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未至任病逝。受此家族背景之影响,朱熹有着强烈的国难家仇,这也影响到他将强烈的现实关怀投注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
其三,道学受到打压,朱熹个人、亲友以及同道在庆元党禁之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庆元党争中,宰相赵汝愚贬死,朱熹也被列为伪学党魁而被弹劾,监察御史沈继祖“遂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二年十二月,落职罢祠”。[22]127-128其弟子蔡元定遭受伪学之殃,被贬道州而卒。周密指出:“遂责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25]对此,陈振孙也认为:“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26]朱熹晚年花费大量时间编著了《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音考》与《楚辞后语》等作品,当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人生遭际密切相关。受庆元党争之刺激,朱熹晚年大力弘扬屈原之“忠”,与之相应,对扬雄之评价则尤为严苛。“王莽和庆元党禁的罪魁韩侂胄同为皇室外戚,在王、韩以及扬雄、韩党新贵之间,朱熹有意识地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附会和影射。自身经历和命运,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性。”[15]46
其四,宋代特定环境下对“忠节”之重视以及史学、文学领域的道学化、义理化倾向使然。《宋史·忠义传》序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27]在史学方面,有学者指出,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28]以“唯道德主义”为标准,史学诠释的“义理化”,正是宋代史学的重要趋向。朱熹作为道学家,其历史与文学之批评,其“道德主义”与“义理化”倾向尤为明显。
其五,朱熹作为理学家,其“道在文先”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批评以及史学批评。朱熹的文学史观受师友辈的影响,他曾与黄铢同学于刘屏山,朱熹曾在书信中论及老师之诗学好尚:“某闻先师屏翁及诸大人皆言: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冲淡萧散之趣,不免于尘埃局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诗,亦不可以不熟读。……更须熟观《语》、《孟》等书,以探其本。”[7]473-474黄铢亦谓:“文学太史公,诗学屈、宋、曹、刘而下,及于韦应物,视柳子厚犹以为杂用今体,不好也。”[7]1137可见,老师、同学之好尚对朱熹的文学批评有不小的影响。作为理学家,朱熹的“道先于文”的观点,更是他衡量作家作品的重要准则: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欧公之文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4]4314
在给当时宰相的上书中,朱熹提出:“惟明公留意,取其强明正直者以自辅,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厉俗,毋先文艺以后器识,则陈太傅不得专美于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于明公矣。”[7]293就文学鉴赏与创作水平而言,朱熹不失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但他作为一个理学家强烈的道德判断以及由时代政治与个人遭际引发的对作家作品的道德批评,难免会有借题发挥之处,他对上述四位作家之评述,就充分体现了此一特点,而由此带来的局限也在所难免。
四
近数十年来,学界对朱熹的道德批评多有反思与批评。
针对朱熹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论述,莫砺锋指出:“朱熹对作家人品持过高的要求,并且常以人品的高下作为判断作品价值的唯一根据,这往往会导致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甚至导致完全取消审美判断而仅仅以道德判断作为作家评论的内容。”[29]蒋立甫在《楚辞集注》的校点说明中也指出:“朱熹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始终为其理学思想所左右。他为了‘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盛赞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但却批评屈原为人‘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他虽然理解屈原的创作‘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但又对其中‘跌宕怪神’的内容与‘怨怼激发’的感情不无微词。这一切也就限制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全面领悟,抹煞了屈作中最光辉的批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朱熹《楚辞》研究的局限性所在。”[3]4
扬雄在朱熹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北宋王安石、司马光等都对扬雄有很高的评价,目为孟、荀之亚。如王安石说过:“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30]644还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为扬雄辩护:“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仕不仕特其所遭义命之不同,未可以议于此。”[30]1293-1294司马光对扬雄的评价也相当高:“扬子云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31]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扬雄入祀孔庙,之后扬氏著述作为儒家的代表之一,被纳入科举考试科目或出题范围中,可知北宋后期尊扬思潮之强大。但自从朱熹在《通鉴纲目》大书“莽大夫扬雄死”之后,扬雄的人品著作皆为儒者所轻。直至明代,理学定于一尊,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但在罗贯中加工创作的《三国演义》中,论及所谓“小人之儒”即以扬雄为例: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32]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对扬雄之看法基本沿袭了朱熹对扬雄之批评,其影响更是到了家喻户晓之地步。延及清代,康熙对《资治通鉴纲目》的“莽大夫扬雄死”词条的批注影响更大:
洎莽篡国之后,雄以前朝旧人,不于此时亟引而退,与龚胜、薛方、郭钦、蒋诩诸贤并驱争先,乃复贪恋爵禄,隐忍不去。虽位非通显,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节已亏,况于称莽功德与夫《剧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直笔深贬之也。……程颐子有言:饥饿死最轻,失节事最大。观《纲目》所书莽大夫扬雄死,则雄之失身于莽,尽东海之波不足以湔其耻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岂不深可叹哉,岂不深可惜哉![33]
康熙如此“放大”扬雄的所谓“失节”之罪,由朱熹之点评借题发挥,称“尽东海之波不足以湔其耻”,明显是为警告那些对清朝怀有二心的前朝遗老。有学者呼吁:“南宋时,因为理学和当时形势的需要,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否定了扬雄的人品;清初,康熙皇帝为统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亲自上阵批驳扬雄。这一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至今还影响着包括《辞海》在内的工具书对扬雄的评介,应该纠正。”[34]作为一代大儒,扬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哲学、思想、语言学与文学方面均有很高的建树,而不同历史时期出于不同政治需要对其人品的抹杀,必然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到对扬雄的客观评价。
陶诗在南北朝时评价并不太高,王运熙的《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认为:“南朝文论家对陶诗的杰出成就大抵认识不足。……陶诗爱发议论,表达人生观,语言质朴平淡,……但因其不尚华藻,缺乏骈体文学的文采,故不受重视。……《文心雕龙》全书论述作家面颇广,却只字不提陶渊明。”[35]李剑锋指出,朱熹将陶渊明与《诗经》联系起来的言论,“遂对后代读者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朱熹看重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要将陶诗立为《诗经》之后诗之‘根本准则’,……陶渊明为人在宋代被儒学化,陶诗也几乎同步被经典化”。[36]在陶渊明为人儒学化、陶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朱熹特别标举他的“不事二姓”之“忠节”,其影响极其深远。宋末元初,蔡正孙编了《和陶诗话》,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陶渊明致敬,“在宋末元初的历史语境中,陶渊明的身份不但是隐士和诗人,他还是忠义的象征。在南宋遗民,包括月泉吟社诗人、谢枋得等人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个在易代世变中坚持士人操守的文化符号,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新朝合作,在文化上不认同新朝,特别是传说中陶渊明不书新朝年号的做法在宋元之际被大书特书。……从史实上看,沈约的记载可能并没有依据,但到后代,这一问题已经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选择性地相信这一事件是事实,从而又从文化上内化为行动”。[37]元代处州人陈绎曾论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38]突出的就是陶渊明之“忠义”。由此而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识,也难免有某种局限,比如对陶渊明为何归隐,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解释为因陶渊明不能适俗或者“不事二姓”。所幸也还有学者对陶渊明归隐之真相做了深入的探讨,如陈培基认为:“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39]之后,范子烨《陶渊明归隐的真相》一文更进一步梳理了陶渊明在当时政治风云中的各种关系,由此揭示其归隐乃是为了逃避刘裕的政治清洗。
朱熹对王维及其作品,因为所谓“失节”而被抹杀,对后世的王维研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上引范文澜对王维的“谩骂”与“污名化”已无需辩驳。当然,也有学者对王维做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如林庚指出,王维是盛唐时代高潮上产生的“一个更为全面的典型,……王维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深厚造诣乃使他成为最有普遍意义的代表人物。……以晚年辋川诸作为代表,……那样幽深而寂寞。实际上,王维在当时却并非以这类诗流传人口。……王维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出色”。[40]王运熙在《陆机、陶潜评价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现存十来种唐人选唐诗,……尤其重视五言律诗。对诗人,往往最推崇王维”,[41]对王维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则比较客观;但这些都难以扭转历来对王维所谓“失节”带来的偏见以及长期被“污名化”的不公正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最终成了科举考试并从此是天下文人的惟一官方注释。正统性战胜了多元化,其代价是思想的禁锢”。[42]莫砺锋在其《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一文中也认为:“朱熹认为作家的人品与文品应是统一的,他的观点会导致把道德判断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43]朱熹强烈的道德批评意识与现实关怀,体现在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一正一反的具体批评之中,以道德评判代替文学批评,以“忠节”作为衡量其人其作之准绳,由此产生的偏颇相当严重。而作为一种批评传统,它对后世文学批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