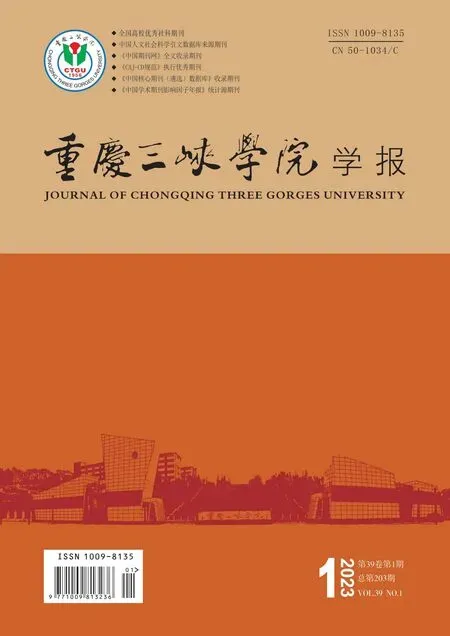《汉志·诗赋略》收录辞赋标准蠡测
白少雄
《汉志·诗赋略》收录辞赋标准蠡测
白少雄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由于《汉志·诗赋略》叙论的缺失,致使前四赋的分类标准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记辞赋数量庞大,作者众多,出现诗赋名称颠倒和作家作品混乱的情况。鉴于汉代“品第论赋”的主观模糊性和辞赋范围的宽泛性,班固只得根据讽谏精神和学术源流依次划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未能细分其中小类,其中渗透着班固自身的分类思想。
班固;《汉志·诗赋略》;分类标准;“品第论赋”
在《汉志·诗赋略》的研究中,前四类赋的分类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因班固未留下阐释说明的叙论,致使争议一直不断。涉及若干问题,例如《汉志·诗赋略》中,前四类辞赋是否真的存在分类?其中的分类标准为何?诗赋略中的混乱记载是班固有意为之,还是刘向父子的失误所致?这些问题的考辨,对《汉志·诗赋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不揣浅陋,拟对《汉志·诗赋略》叙论的缺失情况、前四种赋的分类标准以及形成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辨析其中的分类标准。
一、前人对《汉志·诗赋略》前四类赋分类标准的讨论
关于《汉志·诗赋略》辞赋的分类情况,前代学者曾做积极探索,南宋郑樵首先提出批评:“刘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缘刘氏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班固不知其失,是致后世亡书多而学者不知源,则凡编书惟细分难,非用心精微则不能也。”[1]835“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1]836这种观点成为后世“汉志不明类例”论的源头。晚清姚振宗对此加以驳斥:“前以刘氏胸中无伦类,此又以班氏胸中亦无伦类,不知己之所言乃真无伦类耳。”[2]11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汉书·艺文志》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诗赋之例盖以体分,无所谓别集、总集”[2]329。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不同意姚振宗的文体说,他视文章体裁为《汉志·诗赋略》的分类标准,认为:“有聚文章体裁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杂’、‘小说’、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赋、‘杂赋’、‘歌诗’七种是也。”[3]49实际上,这种观点也属于以体分类的说法,但不同于姚振宗的推崇态度。姚名达认为,“其法草创,前无所承,原无深义”[3]49。在他看来,“《诗赋略》分为五种,而前三种概以一《赋》字为标题,漫无区别……其分类律例亦无足重轻”[3]49-50。孙德谦的观点与此类似,也认为《汉志·诗赋略》无须再细分子目:“史家之《艺文志》,余尝谓区立门类,在乎辨明家学;子目之分则近琐碎,似不必也。”[4]17他从学术源流的角度进行辨析,认为区分门类本为理清学脉源流,“其于子目也,可分则分之,若不知学问之流别,而强为分合之,则非慎言之道也”[4]18。若《汉志·诗赋略》强分子目,实非明智之举,故“班氏之不规规于尽立子目也”[4]18。而明代胡应麟认为《汉志·诗赋略》所载内容“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5]255。清代章学诚继承胡应麟的“总集说”并加以发展:“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6]1239将《汉志·诗赋略》中的前三类赋、杂赋定性为“别集”“总集”。刘师培延续了这种观点:“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7]115-116进一步阐释其来源:“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7]116在“别集”“总集”说的基础上,刘师培进一步细化“别集”为三类并探求其来源。章太炎也对辞赋来源进行辨析:“《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8]249在综合刘师培、章太炎说法的基础上,顾实对前四赋加以定性:“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也。”[9]138“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也。大概此类赋尤与纵横之术为近。”[9]140“荀卿赋之属,盖主效物者也。”[9]142并对杂赋的性质做出推测:“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者欤。”[9]144
不同于刘师培、顾实等人四类分法,叶长青根据《汉志·诗赋略》序文的解读,将四类辞赋归为两类:“陆赋之属,属于屈赋;杂赋之属,属于荀赋也。”[10]155段凌臣持论相近:“屈原、陆贾二家,实可相通。陆所异于屈者,或偏于纵横耳。由是言之,则陆贾、孙卿二家,皆屈赋之支与流裔;而辞赋一体,实南人所独擅也。”[11]122将前三类赋合而为一,统归于“屈赋之属”,凸显辞赋之间的学术流变。熊良智认为《汉志·诗赋略》中辞赋的分类标准乃源于孔子删诗之意,根据《诗经》的分类方式,将前三类赋定性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颂体之赋,而失去作者姓名、不明流别的杂赋,仅属附录而已。这种分类思想源于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即“赋者,古诗之流也”[12]。基于《汉书·古今人表》九品论人的情况,李士彪认为《汉志·诗赋略》的分类标准也用此法,即“屈原赋之属为上品,陆贾赋之属为中品,荀卿赋之属为下品”[13]。杂赋则是“无作者或佚名之赋,无从以赋家品目”[13]之作,亦属以人划分辞赋的观点。而王晓庆以“风谕之义”和“形式美丽”为汉人评议赋作的标准,认为“讽谏与尚丽具有统一性,讽谏以针砭时弊来维护统治,尚丽以颂扬鸿业来维护统治,但二者又是矛盾的”[14]40,故而二者完美结合,是汉赋评价的理想标准。因为“屈原、枚乘、司马相如、王褒们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优于陆贾、枚皋、荀卿们”[14]40,所以“屈原赋类为上品,陆贾赋类为中品,荀卿赋类为下品”[14]40。此结论与李士彪一致。孙振田认为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屈原及《楚辞》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关系,《汉志·诗赋略》所收屈原赋之属是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作品,并非仅据楚辞体(骚体)为准则。出于前三类赋在数量上平衡的需要,《汉志·诗赋略》又依据赋作的文辞水平分为陆贾赋之属和荀卿赋之属,前者文辞较佳,后者略逊于前者[15]。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前人已经认识到《汉志·诗赋略》中前四赋的分类标准非常复杂,出现了“不明类例说”“文体说”“体裁说”“别集总集说”“风格说”“品级说”“汉代诗学说”等多种观点,诸家所论对辨析前四类赋的分类标准以及相关问题均有重要价值,启发后人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面对如此繁琐的情况,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独立的标准,为此,程千帆先生归纳出六种不可单一作为标准的因素,即不可以地域、时代、气息、主题、巨细、声音等六种之一单独为分类标准[16]255-256,唯有“合此六者,源流董之,庶几近焉”[16]256。
要之,《汉志·诗赋略》的分类标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乃是多种分类条目错杂融合的结果。既然分类标准难以确定,那么,《汉志·诗赋略》所收录的辞赋作家是否真有标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余嘉锡先生曾言:“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17]65由于《汉志·诗赋略》序论的缺失,致使其中辞赋的分类标准难以明晰,但班固绝非任意为之,仍有分类标准存于其中。前人对此已有所注意,据《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18]1701刘光蕡解释为:“经籍之重,自孔子始,故从孔子说起也。然不自孔子生说起,而从孔子没说起,为《汉书·艺文》作缘起,见此《志》叙艺文有别择之意,非漫无去取而录之也。”[19]3从《汉书·艺文志》编纂的预设目标来看,正是为了避免书籍亡逸,“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20]226。故班固不可能任意书写,其中所提到的“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8]1701就是指“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18]1702。在张舜徽先生看来,此正是书目二次整理的过程,“《七略》原本,于每书名之下,各有简要之解题,故为书至七卷之多。由其为簿录专籍,自可任情抒发。至于史册包罗甚广,《艺文》特其一篇。势不得不翦汰烦辞,但存书目。史志之所以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者,亦即在此”[21]176。史家欲编纂历史,势必会对前代文献进行整理剪裁,在刘向父子的基础上,“孟坚删《七略》之浮冗,取其指要,作《艺文志》,以入《汉书》而备篇籍,自《七略》既亡,后人藉以考见群经授受源流者必于此志。无此志,是中国无学术史矣”[22]198。但因年代久远,其中的记载难免出现损毁讹误。即使如此,《汉志·诗赋略》所收录的内容“在当日各为分类,班氏必能辨别体裁”[4]18。如章学诚先生所言:“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6]1238现在之所以出现分类模糊的情况,和其中所载辞赋大量亡佚、叙论缺失等问题密切相关,正如孙德谦所说:“班《志》于一类后,既作后论以究学术之得失矣,其于一略之中,再用总论者,何哉?盖后论祇及一家,总论则包举全体也。”[4]16由于《诗赋略》中只存总论,没有后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但从现有的文本来看,《汉志·诗赋略》的收录记载渗透着班固的分类标准,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汉志·诗赋略》中前四赋的排序情况
除说明性质的叙论之外,《汉志·诗赋略》中的文本记载,也是考辨分类标准的重要途径。惜记载亦非完整无误,《汉志·诗赋略》的诗赋名称倒置和作家作品归类则是其中的争论焦点。章学诚先生对诗赋名称倒置表示疑问:“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6]1239此言极是,《诗赋略》名称倒置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不然。这是辨析《汉志·诗赋略》分类标准的一个重要途径,亦体现了班固内心的真实选择。叶长青对此解释:“赋者古诗之流,以源流言,故先诗而后赋,而诗赋名略也。至所收篇第先赋后诗者,赋起于战代,五七言诗则起于汉世也。”[10]152从学术源流的发展规律来看,应该是诗前赋后,《汉志·诗赋略》赋前、诗后的顺序正是根据作品的产生时代所决定。段凌臣则认为:“中国文学体裁之伟大,当以辞赋为最。汉世为赋之极盛时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远非歌诗所及。故以赋居前,次诗于后,正所以著赋之盛且大也。”[11]101“至诗赋二名相次,实当时习惯使然,无顺逆之可言也。”[11]101在汉代,辞赋成就远超诗歌,这种情况导致了诗赋名称的倒置,而在社会上仍习惯于诗赋并称。
在名称上,《汉志·诗赋略》本是诗前赋后,收录顺序则为赋前诗后,这与班固对辞赋价值的判定有关。在他眼中,辞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23]3。此与古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当时的情况是诗的地位远在赋之上。班固命名为《诗赋略》,正是为了顺应当时社会的观念,尊重诗的重要地位,但又不满于辞赋的地位低下,试图提升汉赋的社会地位,认为汉赋不能尽是“调笑之作”。在编纂《汉志》的过程中,班固将自己的辞赋理念融入其中,努力扭转时人对汉赋的看法。他借鉴古诗的内涵精神,反对汉赋的过于华美,形式大于内容。为此,他追溯学术源流,从古代先贤所留下的文章中汲取滋养,大儒孙卿和楚臣屈原“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8]1756。这正是他心目中辞赋学习的榜样,如清儒程廷祚所言:“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4]38汉赋也是如此,班固力主汉赋继承古诗的讽谏精神,打破辞赋之间的界限,使得汉赋和古诗具有同样的讽谏作用,为汉赋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他之所以强调讽谏精神作为辞赋的精神内核,这是由讽谏的作用所决定的,《白虎通义》载:“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纳诚也。”[25]226“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25]235“明王所以立谏诤者,皆为重民而求己失也。”[25]237班氏深知讽谏的作用,故将这种精神融入文章是其创作的重要动力。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屈原作为讽谏君王的忠臣代表,自然会被其视为精神榜样,故而将《屈原赋》之属列为首位。
在这之后,本应是《荀卿赋》之属。在文坛地位和后世影响上,屈原与荀卿可谓并驾齐驱,不分轩轾。“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7]110《屈原赋》和《荀卿赋》皆是后世文章的渊薮,其辞采华茂、论辩绵密、想象奇特、铺张扬厉等特征,对后代文人的创作影响很大。虽然如此,但屈原赋实是荀卿赋的源头,学者们讨论两人的辞赋成就时,多将荀卿放在屈原之前,“盖崇儒之故,不足为宗”[11]121。按理说,《屈原赋》之后应是《荀卿赋》,但班固无视陆贾的生活时期晚于荀卿的事实,而将《陆贾赋》列于《屈原赋》之后,“此以贾赋实密迩屈原,孙卿不过以北人效南体,故倒置其时次。其微义亦昭然可证也”[11]121。虽然荀卿、陆贾得益于屈原辞赋的熏染,但陆贾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屈原赋,体现出继承演变的学术特征,故紧随屈原赋之属,列为第二。而荀卿对屈原赋的摹拟痕迹较重,未能实现自身创作的突破,故被班固列于陆贾赋之后。通过三者的位置排列,展现出内在的传承关系,体现出班固探究学术源流的思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班固将《屈原赋》之属放在首位,而将《荀卿赋》之属放在第三位,正是为了凸显汉代思想的发展演变。虽然孙卿和屈原都是具有讽谏精神的作家,但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汉初黄老思想是统治阶层的主流思想,尤其是窦太后,更是黄老思想的忠实拥护者,致使儒家思想深受压制。此时的学术现状非是带有儒家思想的荀卿辈所能代表,只能由具备汉代文化思想特色的作家作品进行呈现。而陆贾等人的作品可以更恰当地反映由秦入汉的文学特征,展现汉初文学的过渡性特色,故将《陆贾赋》之属列为第二。虽说汉武帝时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真正成为正统,但社会思想的发展接受,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样的顺序安排能够更妥帖地展现西汉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最后便是那些主题相近的杂赋,这是《汉志·诗赋略》中地位最轻的赋作,故置于四类赋的末尾。虽然其中缺乏讽谏精神,但“杂赋亦非滥厕总杂之谓,其义例隐有可寻”[16]258。程千帆先生将杂赋的特征概括为四:无作者、无年代、署主题、名称多冠以杂字。前两项是“当日著录之困难”[16]258,后两项是“当日匡救之方法”[16]259。由于时间仓促,未能彻底理清杂赋,班固只能将辞赋略分四大类,此便是《汉志·诗赋略》前四类赋划分的基本情况。
关于《汉志·诗赋略》记载混乱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扬雄赋》的归属上。姚名达对此质疑:“孙屈二家,作风如一,何缘而判为二种。”[3]49“既与屈原不同,何缘独置《扬雄赋》于《陆贾赋》之后而悉列其他数家于《屈原赋》一种中?除非不问作风之同异而惟体裁之同异是问,否则殊乖分类之义。”[3]49-50张舜徽先生认为“扬雄赋本拟司马相如,乃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录扬雄赋隶陆贾下,斯已舛矣”[21]372。朱保雄也认为:“司马相如赋,《汉志》列入屈赋之属,而杨雄赋列入陆赋之属,殊不可解。”[26]150扬雄原本摹拟司马相如而创作,却归入《陆贾赋》之属,看似不可解,实则不然。班固将《扬雄赋》归入《陆贾赋》之属,正是体现其对《扬雄赋》的肯定。扬雄是他摹拟学习的榜样,对其影响很深,“其论大抵本诸扬雄”[27]20。从文坛作用来看,扬雄对整个东汉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一代,文学论者,首推桓谭、班固,其后则有王充。谭、固皆盛称子云,充之论出于君山,故谓东汉文论,全出于扬雄可也”[27]19。由于扬雄文坛巨匠的身份和成就,班固便将《扬雄赋》归入《陆贾赋》之属,这一举动正是为了凸显其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重要地位。
在班固眼中,陆贾是汉代文学的代表,《答宾戏》曰:“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谭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斯非亚与!”[23]2020《汉志·诸子略·儒家类》收录“陆贾二十三篇”,视其为儒家学说的传人和代表。与班固同时期的王充也对陆贾的创作水平评价极高,“《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28]1169。正如刘知几所言:“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29]438陆贾不单是编纂思想著作的学者,也是汉代辞赋的发起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30]134。“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30]134在创作过程中,陆贾展现出自身的思想深度与时代特色,正所谓“汉室陆贾,首案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30]698。刘勰将其视为汉代辞赋的开创者,以“扣其端”“首案奇采”称赞他的辞赋成就,以“典诰”“辩之富矣”评价其创作特色,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关于典诰的特色,刘勰曾加以解释:“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30]394-395陆生写作选用古代的训典文体,用词古韵典雅,明白晓畅,气势雄浑壮阔,庄严厚重,彰显大汉王朝的昂扬气势和蓬勃张力,这与班固所追求的创作理念非常接近。由于陆贾的文学成就和行文特征,班固将其作为西汉文学的代表,而把“扬雄赋十二篇”列于《陆贾赋》之属,正是为了彰显他的辞赋成就,视其文章为西汉文学的典范之作。虽然扬雄和司马相如都是辞赋大家,但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司马相如赋是天才想象的结果,而扬雄赋则是苦读思考的结晶。孟坚以扬雄为汉代辞赋创作的典范,着重表现其为汉赋发展积极寻求出路的探索。
如果说班固收录《扬雄赋》入《陆贾赋》之属是对西汉辞赋典范的肯定和总结,那么,司马相如赋归入《屈原赋》之属,则因其追溯前人足迹的作法使然。司马相如效仿前代先贤,发挥辞赋的讽谏精神,与屈原辞赋的特征一脉相承,故将其归为《屈原赋》之属,这样看来,问题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志·诗赋略》没有记载矛盾的地方。例如,“枚皋赋百二十篇”质量较差,尽是调笑之作,张舜徽先生评价为:“大抵皋之为赋,病在速而贪多,又嫚戏不闲雅,故为世所诋娸,而散亡甚早。《隋志》著录《东方朔》《司马相如集》,独无《枚皋集》,非无故也。”[21]355-356不属于顾实所说的“主说辞者也”,不应列于“陆贾赋之属”。“《朱建赋》二篇”本应在“《枚皋赋》百二十篇”之前,根据时间来看,“平原君文帝时卒,此当在陆大夫之次、枚皋之前,疑转写之误。观下一条注‘枚皋同时’,明是承上文而言,尤可证也”[2]318。此外,“《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于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6]1241。关于班固的分类安排,章学诚先生也表示疑问:“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猥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谓以人次也。《秦时杂赋》,列于《荀卿赋》后,《孝景皇帝颂》前,所谓以时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6]1239-1240《汉志·诗赋略》中辞赋排列的杂乱现象,确实存在“以人次”“以时次”的双重情况。可见《汉志·诗赋略》中,仍存在着一些矛盾的记载,说明班固对辞赋的分类仍是较为粗疏,尚有疑虑留存。面对这种情况,不必求其完备,“刘《略》班《志》于六略,或论或阙,自有权衡。善读书者,贵能心知其意,不必求其齐同也”[21]372。虽然《汉志·诗赋略》记载中存在着一些难免的混乱讹误,但班固确曾对前四类辞赋进行过精心的划分。只是分类标准并非单一,乃是数种因素相互融合,彼此之间也有先后的顺序考虑。由于时间仓促,短期之内难以厘定整合,不得已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和杂赋四类,对所存的具体小类未能理清。同时,由于某些原因未留下说明性质的叙论,给后人的研究辨析带来了困难,但班固确有自己的分类思想融于其中。
三、《汉志·诗赋略》中前四赋的分类标准
由于《汉志·诗赋略》中存在记载讹误、叙论阙如等情况,为其义例辨析增添了困难,但仍有踪迹可循。作为东汉时期的辞赋名家,班固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从汉人的辞赋评价体系入手,更能接近《汉志·诗赋略》中辞赋分类的本意。“品第论赋”是汉代辞赋评论的重要标准,《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8]2829汉宣帝将辞赋等级分为两类,即“与古诗同义”的“大者”和“辩丽可喜”的“小者”,可以“虞悦耳目”的同时,还具有“仁义讽喻,鸟兽多闻之观”的作用,充分肯定了辞赋的现实价值。
根据“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可知,王褒等人所写的辞赋多是叙述事情、描写事物的文章,追求华丽的辞藻,重视铺排张扬的文风,形式大于内容。虽然汉宣帝将“与古诗同义”的大者和“辩丽可喜”的小者并重,但更喜欢清新明快的辞赋。西汉王朝的强盛国力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共同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进程,在文坛上呈现出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铺张扬厉的文辞特征。正如刘勰所言:“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30]672由此可知,“第其高下”的标准是辞藻的华美、风格的明快清新等形式内容,并非以说理议论为划分标准。但辞藻华美、风格明快是较为主观的判断,没有一个固定尺度,究竟何种文章才能算是达到标准,难有一个准确衡量。汉代皇室的辞赋评审标准影响到班固的创作思想,使得《汉书》的编纂过程渗透着分等思想。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他将人分为九等,“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18]861。既然论人可以等级评价,那么论赋也可如此,“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31]79。《汉志》承接《七略》把人按类划分的做法,在《诗赋略》中,前四类辞赋以人名而非形体来统领,这顺应了辞赋发展的自然轨迹,“自唐以前,无古赋、排赋、律赋、文赋之名”[32]1016。在当时,汉赋作为新兴的文学体裁,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可供借鉴,只能暂时以人名代称,这是文学规律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七略》的分类编排往往名实不符,这也就成为《汉志·诗赋略》记载混乱的一个原因。由于辞赋作者与文章风格不相符,班固又以人物品第来划分,难免出现这种混乱记载的情况,但并不意味《汉志·诗赋略》没有清晰的分类标准。在他眼中,大儒孙卿和楚臣屈原是作赋以讽的代表,而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8]1756。由此可知,班固将讽谏精神作为划分辞赋类型的主要标准。
班固如此重视辞赋中的讽谏精神,也和当时的礼乐恢复密切相关,包含着其对礼乐复兴的希望。光武中兴之后,结束了社会的动荡,班固奉旨编纂《汉书》,将“润色鸿业”作为自己的创作主张,辞赋创作也是如此。《典引序》曰:“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23]2159在他将宣扬汉德与辞赋创作相结合的同时,章帝承接了明帝未完成的礼乐事业,但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汉书·礼乐志》载:“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濅以不章。”[18]1035当时明帝觉察到礼乐制度的破坏情况,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古礼,但因事先准备不足,未能彻底解决,这就促使章帝继续推进恢复礼乐的相关措施。班固深知礼乐对大汉王朝的重要作用,他目睹了帝王修复古礼的举动,便将自己的思考凝聚到辞赋的创作之中,正如他在《两都赋序》中所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23]3-4班固将汉赋与礼乐进行联系,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23]1,乃“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23]3。他确立了赋体的崇高地位,使得辞赋与古诗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意图通过向君主献赋达到谏言的效果,促进国家礼乐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在《汉志·诗赋略》的整理过程中,班固将这种思想与辞赋作家的排序分类相联系,以讽谏精神作为辞赋作家的最高标准。孙卿赋和屈原赋是“作赋以风”的典范,属于同一类型,但作为大儒的孙卿和屈原身份不太相同,再加上屈原忠君爱国的品格以及自沉汨罗的悲剧结局,故而列《屈原赋》之属为《汉志·诗赋略》之首。
但《汉志·诗赋略》中的分类标准并非单一,而是多种分类标准融合并存。除了讽谏精神之外,学术源流也是班固分类的重要标准。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刘、班区别此三种赋,本以源流。”[16]257班固如此重视学术传承与其思考汉赋的发展道路有关,他不满于汉赋多是“调笑之作”的现实,试图提升汉赋的地位和扭转时人对汉赋的评价。为了突破这一困境,班固从前代赋家的创作经历中汲取营养,最终确定学习扬雄以经学入赋、以才学入赋的做法,以此来实现自己的辞赋理念,“及孟坚、平子为之,《幽通》《思玄》,析理精微,精义曲隐,其道杳冥而有常,则《系辞》之遗义也。班固《两都》,诵德铭勋,从雍揄扬,事核理举,颂扬休明,远则相如之《封禅》,近师子云之《羽猎》,其原出于《书经》”[7]137。前代典籍成为班固写作的动力源泉,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典籍、强调学问便成为其辞赋创作的思想指导。在编纂《汉志·诗赋略》之时,班固将这种思想渗透其中,学术传承也就成为其辞赋分类的重要标准。
通过现存《汉志·诗赋略》的收录记载可知,诸赋中确实存在着源流关系,“屈原诸作,当时皆谓之赋。《汉艺文志》所列诗赋一种,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无所谓骚者”[5]248,“自荀卿、宋玉,指事咏物,别为赋体。杨、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诸作,遂俱系《离骚》为名,实皆赋一体也”[5]248。《汉志·诗赋略》所载并无所谓骚者,词赋当时都称为赋。骚赋虽是两名,实皆一体,荀卿、宋玉受益于前代骚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也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学风。虽然两类作者的创作来源一致,但形成的特色各有不同。正如章学诚先生所说:“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6]94古人编书注重学术传承,讲究承前启后,《汉志》是“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17]12,预设价值就是“穷源至委,竟其流别”[17]18,那么,其编纂自然也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可以说,班固心中所设定的分类效果就是完美地呈现学术脉络的传承演变,正所谓:“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6]94依文本来看,“屈原赋”是“陆贾赋”和“荀卿赋”的源头,三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汉志·诗赋略》所展现的是三类赋的学术流传。由于所处时代的差别,陆贾赋呈现出不同于屈原赋的文风,其身上呈现出明显的过渡特色,然而荀卿赋也是受屈原赋熏染影响的艺术结晶。这样看来,辞赋实则是楚人所独擅长的体裁,陆贾赋和荀卿赋之属乃是其支流与后裔。不单是三类赋的大类之间,在前三类赋的各自小类之中,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传承关系,“陆贾赋”之属便是溯源学术源流的典型示例。陆贾本是汉初辩士,上承战国遗风,在大汉一统之后,纵横捭阖的时代结束,纵横策士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其文风呈现出由秦入汉的过渡特征,班固将“陆贾赋”位列第二,反映了学术源流的发展轨迹,体现了汉代文脉的转变过程,故将枚皋、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辞赋都归入此类,呈现了西汉辞赋的历史与成就。在辞赋史上,“汉人赋冠绝古今,今所共称,司马、扬、班十余曹而已。余读《汉志》,西京以赋传者六十余家,而东汉不与焉。总之当不下百家”[5]252。“然班氏本《七略》而芟之者也,志之于略仅三之一,则西汉诸词赋家,亦仅半存而已。”[5]252“西京之赋,已不啻百家,不必东汉也。”[5]252“陆贾赋”之属呈现了汉代辞赋的成就和辉煌,故仅次于“屈原赋”。
西汉辞赋数量众多,名家辈出,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可谓“一代之文学”,同时,作为新兴文体,汉赋自身的复杂性也十分明显。从赋自身的定义来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33]282,“敷布其义谓之赋”[34]91,“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30]134。由此可知,赋的包容范围非常广泛,凡是文辞铺张、写物图貌之文均可归入赋类,《汉志·诗赋略》的收录内容正是如此,“凡用韵之文,其行文用诗赋之体者,均可以诗赋视之”[11]120。可见其所收汉赋的范围很大,多数文章都可以算入辞赋之中,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汉志》诗赋一略,实包举一切纯文学之篇章。故自广义言之,凡非诗之文体,多以入赋。此于《诗赋略》体例自见之。”[16]249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辞赋,试图确定单一的分类标准,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知,汉代辞赋本身的复杂性也是《汉志·诗赋略》未能实现统一标准的重要因素。
由于汉赋具有很大的兼容性,使“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8]245。这必然导致汉赋丛杂猥多的情况,为辞赋分类增加难度,只能“略加区分,约为五种。其实细分缕析,犹可多出数种,未必即此五种已为定论也”[21]371-372。当刘向父子整理辞赋诗稿之时,见到的都是“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8]248的抒情之作。在质量上,虽有高下之别,但数量十分庞大,短期之内难以弄清,只得区分大概。鉴于汉代辞赋的复杂程度,班固承接这种做法,自己设定讽谏精神和学术源流为辞赋的分类标准,但汉代“品第论赋”的风气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这就导致《汉志·诗赋略》中难免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只能尽量地找到平衡点以保证两者之间的协调。因此,在大类排列当中,按照品第论赋的要求,班固依次划分四类赋的等级,同时又以讽谏精神和学术源流为主要标准,排列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的先后顺序,但汉代辞赋成果众多,仓促间难以理清,便没有细分小类,只是自己清楚内在标准,《汉志·诗赋略》没有留下叙论可能正是这种心理的折射。
四、结语
《汉志·诗赋略》的分类标准作为《汉志》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该类研究的进一步展开。通过辨析其中前四赋的分类思想,可以还原《汉志·诗赋略》记载的原始风貌,把握时人对辞赋的评价标准以及辞赋本身的文体属性,梳理汉代辞赋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成就,为解决班固的辞赋观以及《汉书》中辞赋家的历史书写等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可以说,探析《汉志·诗赋略》前四类赋的分类标准,对《汉志》乃至整个《汉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术史价值。
[1] 郑樵.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5]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8] 章太炎.国学概论·国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2015.
[9]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4.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0] 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 段凌臣.汉志诗赋略广疏[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12] 熊良智.《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J].中州学刊,2002(3):58-64.
[13] 李士彪.三品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06-108.
[14] 王晓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文献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15] 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12-120.
[16] 程千帆.闲堂文薮[M].济南:齐鲁书社,1984.
[1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 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注[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5.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9.
[21] 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 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4.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3]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4] 程廷祚.青溪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25]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6] 朱保雄.汉志辞赋存目考[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27]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8]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9]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0]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1]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2]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7.
[3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4] 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2016.
A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Standard of Ci fu in
BAI Shaoxiong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narra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the first four Fu has become an unresolved problem.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recorded Ci Fu and numerous authors, the names of poems and Fu have been reversed and the records of writers and works have been confused. In view of the subjective fuzziness of Fu evaluation and ranking and broad scope of Ci Fu in Han Dynasty, Ban Gu had to divide it into Qu Yuan’s Fu, Lu Jia’s Fu, Xun Qing’s Fu and Zao Fu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and the academic origin. Although he failed to subdivide the sub-categories,Ban Gu permeated his own classification thought in the division of Fu.
Ban Gu;;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u evaluation and ranking”
I206.2
A
1009-8135(2023)01-0087-13
白少雄(1989—),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生,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