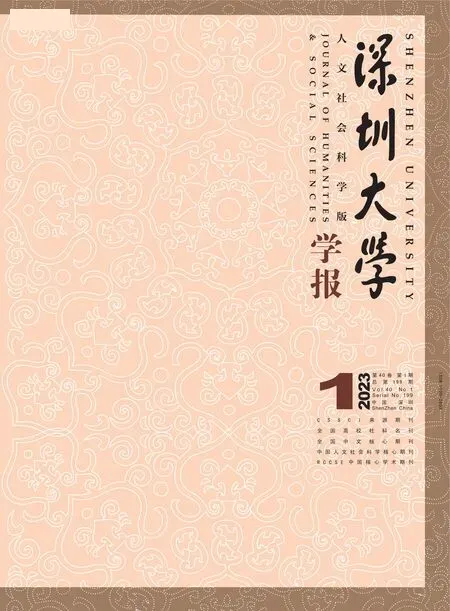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杨伟涛,李 倩
(1.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国传统文化对 “情” 独偏重,《诗经》《尚书》《周易》等早期典籍①中 “情” 字已多有所见,如《尚书·康诰》篇描绘,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1];《诗经·宛丘》篇描绘男女爱慕之情,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2]。 “情” 是人待人接物的心绪反应,《礼记·礼运》释义和肯定: “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3](P316)传统典籍中 “情” 之义及其类别丰富,或指感情、欲情之义,或谈心情、神情之义,并认其为实情②。 “性” 是物或人天然所就的本性、特质, “性者,生之质也”[4](P377);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 ”[5](P265)人性即是个体和人类的天然、本然之性与不事而自然之性;中国传统哲学透过天道、天命、人道,探寻人性之学,如《中庸》谓之, “天命之谓性” 。尽管古《说文解字》将 “情” 释为 “人之阴气有欲者” ,与指称 “人之阳气性善者”[6](P502)的 “性” 相区分,但儒家哲学凸显人性构成中 “情” 的要素,着重于 “情” 与 “性” 的内在关联,认为情乃是人之性接于外物之后的外在表现。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孔子的 “仁” 既有爱人的情感意蕴,又内含先天之质性;《礼记·中庸》赋予 “喜怒哀乐” 之性、之情之 “未发” “发而中节” 分别为 “中” (大本)、 “和” (达道)③之德[7](P53);孟子以情释性,将具有情感意蕴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荀子以性说情,认为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正名》)。 “性” 与 “情” 及其与 “天” “命” “道” 的关系在先秦后期《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被一并贯通: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 ”[8](P88)并另区分说,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8](P92)徐复观研究指出,在先秦, “性与情,好像一株树生长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长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所以先秦诸子谈到性与情时,都是同质的东西。”[9]言性与情、言情与理,成为 “情” 概念内涵的规定性和主题。汉代董仲舒直言: “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谓天之有阴阳也,情亦性也。 ”[5](P267)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性情论及其理情说富有深意,作为原始儒家性情论和理情说的源初型态,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发展以及性-情-理关系学说奠定了深厚基础。
一、孔子的仁爱性情论与仁智礼统一说
孔子尚 “仁” ,提倡 “仁爱” , “仁” 被作为中心范畴、全德之称,张岱年评述, “孔子对于中国思想之贡献,即在阐明‘仁’的观念。”[10]冯友兰解释,作为孔子 “一贯” 之道、中心之学说, “故《论语》中亦常以仁为人之全德之代名词” , “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11](P62)。孔子论 “仁之本欤” 之 “孝” 、 “仁之方” 之 “忠恕” ,都表达人本性之 “情” 的展现;孔子提倡 “仁、智、勇” 三达德之 “智” ,重在 “人情事变” 之德的是非恰切;孔子尚礼, “克己复礼” 意在以礼挈情,通过修心、修身,以理性规范引导内在情念。
(一)仁爱的性情意蕴
孔子于 “性” 有简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2](P253)此是在天道本源上理解人 “性” ,他没有另谈人性的篇章,是以子贡曰: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2](P65)。 孔子于 “情” 方面也少论,其在《论语》有二处见: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2](P187);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毋喜”[12](P283)。 然而,孔子仁学、仁爱思想深蕴着人性体悟和 “情” 的意蕴。孔子以 “爱人” 为 “仁” 的本质规定,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2](P182)爱人之 “仁” 以性、以情,即 “无情不仁” , “仁者情志,好生爱人”[13];《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有 “唯性爱,为近仁”[8](P101);宋代程颐(伊川)曰: “仁则性也”[14];朱熹另释: “盖仁者,性之德而爱之理也”[15],都明确表达和肯定 “仁” 作为人性之爱的特征。《庄子·天道》篇记述老聃和孔子关于仁义之性与情的谈话,孔子答老聃曰: “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4](P200)孔子将仁义予以肯定和视作人之性,兼爱无私为仁义之情。冯友兰讲述孔子仁学认为: “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11](P60);另述孔子认为: “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就是‘仁’的主要基础。”[16]爱人之 “仁” 始乎人的血缘亲情, “为仁者,爱亲之谓仁”[17];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6](P55) “仁” 由基于亲族关系、近乎自然心性的亲情孝悌而起,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12](P3,P6)仁者由孝而弟悌、友信、泛爱众,至 “恩及四海” ,由 “小仁” 及 “大仁” ,着重以近于人之本性的心性、性情的真实表露和交融作为人伦关系以及相互交往的基础。孔子以自然性情的孝亲为起点,通过尽心竭力的推己及人而推扩仁爱,建构普遍的人际关怀伦理。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12](P91)基于爱人,当子贡问: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P253)对子贡所言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之德,孔子称赞, “必也圣乎! ”[12](P91)推己及人的 “忠” 、 “恕” 之道以及博施济众之德均源于人们自然心性而生发的移情、同情之心。冯友兰诠释同情心与 “仁” 、与人之性情之间的关联, “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 ; “《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也。”[11](P46-47)李泽厚指出,仁不只是血缘关系的原则,也是心理原则,把外在的礼内化为心理情感;仁也是人道原则,仁的主体内容是社会性的交往要求和相互责任,并被建立为贵族、氏族、自由民之间的某种博爱的关系;仁也是个体人格,仁成为人不须服从神的个体自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伟大人格。[18]孔子以 “仁” 为君子之道和人的本真规定,他常常告诫君子、弟子、民众谨记和力行仁道: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12](P114)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2](P49)言语中显露着本怀仁心的深情和志向于 “仁” 的追求。依孔子看来,仁者不仅能顺应自己的自然情性,而且还具备恭、敬、忠、信、敏、惠等情怀,孔子对樊迟问 “仁” 而告知需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12](P147);当子张问 “仁” ,孔子则强调 “恭、宽、信、敏、惠” ,以为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2](P255)。仁爱性情的显用有着丰富意蕴和充沛之情。仁爱不仅是血缘亲情之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普遍之爱,即泛爱众;至宋明儒者张载、王阳明等将之扩展为 “民胞物与” 、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9],彰显仁心之爱的深厚、广博。
(二)以知利仁,因情以礼
孔子对 “仁” 和 “知” 相提并重,他常将二者对举并论: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12](P135);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2](P4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12](P87)樊迟问 “仁” 、问 “知” ,孔子分别告以 “爱人” “知人”[12](P182)。 “知人” 在于 “里仁” “处仁” “知仁” “体仁” 和 “利仁” ,即对 “仁” 所知和应用恰切;若对 “仁” 少知、未知, “仁” 则无所措置、不得其旨,即 “未知,焉得仁? ”[12](P68)体 “仁” 之情要做到博学问思、从容中道, “仁” 则自得其中,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2](P279) “知” 与 “仁” 结合体现了伦理和价值理性。孔子申述为官之道,既要做到有知,又要守仁,并动之以礼,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12](P236)其意味着 “知” 和 “仁” 、 “礼” 之情应相需结合,通过知人、知命、知礼、知言以求仁、知仁、得仁、利仁。 “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20]蒙培元先生关注于孔子 “知” 之性情内涵: “孔子所说的知,又不能完全归结为通常所说的知性范畴,它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毋宁说是知解、理解的问题,知解、理解便有内在情感在其中。因此,知主要不是中性的科学认识,而是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也就是价值认识。 ”[21](P76)孔子将 “仁” 之 “知” 言说为依 “礼” 行 “仁” ,认为君子应立于礼、约于礼、守于礼,如子曰: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2](P89)孔子通过告诫儿子伯鱼而启示弟子: “不学礼, 无以立”[12](P249);并另有明辨: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12](P111) “仁” 和 “知” 以 “礼” 为外在规范标准,《礼记》有 “礼也者,理也”[3](P414);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3](P366);由此, “礼乃是理性化的道德追求”[22]。如颜渊问 “仁” ,孔子回答,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2](P172)通过约束自我并使个体纳入社会礼制,则为体仁。孔子另回答颜渊 “礼” 的具体要目: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2](P172)而 “礼” 也以 “仁” 为内涵和心理依据,是人们之间情感需求的凝结, “礼” 必须注重于人内心的真性实情,即 “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责,且亦甚可贱矣。”[11](P45)孔子提醒人们: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2](P33)孔子谈到孝亲与孝终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2](P18)孔子将礼作为尽孝的标准,认为礼以敬重之情为其本质内涵,孝亲、奉亲之事上需出于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而且,外在形式的礼仪应以内在的心理情感作为内容依据,否则,不可谓真正知礼、真心行礼和真切尽孝, “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11](P45)孔子谈德礼与为政治民相关,也突出因情以治,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P16)君上治民,如果以政令训责民众,用刑罚威逼民众,那么民众对刑政和君上缺乏认同感,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廉耻感和自律之心,犯政乱刑之事难以禁绝;君上如果凭借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和以礼仪引导教化民众,民众内怀羞耻愧疚之心,自觉认同礼义法度和端正自身行为,自绝于违法乱政之事。 “民之于仁也, 甚于水火”[12](P237);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7](P55)富于真情实感、注重于感化民众的德礼和仁情才是安民治政、社会安定的根本途径。
二、孟子的心统性情论和理义节情说
孟子引告子之言 “生之谓性”[23](P278),力辨与论证人性之善;他所谈人性之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四心与 “仁义礼智” 四端,内蕴和表露着情感的因素,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肯定孟子 “四端皆情”④;孟子论证人之 “四端” 性善,在于人情恰切。孟子以心之官能之思, “小体” “大体” 之分,以道德、性理说 “情” ,探讨人之道德的可能性以及情感与理性的统一的问题。
(一)为仁由义,四端之心为性为情
孟子继承和弘扬孔子 “仁” 学,将仁规定为人的本性, “亲亲” “恻隐” 为 “仁” , “亲亲,仁也”[23](P305),并由此达及仁民、爱物,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3](P356)孟子注重以 “义” 行 “仁” 、居 “仁” 由 “义” ,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23](P184) “义” 在于爱之合宜、行之当理,《礼记》说 “仁” 和 “义” , “仁以爱之,义以正之”[3](P363),汉代贾谊论 “仁” 和 “义” , “失爱不仁,过爱不义”[24](P65)。 孟子告诫统治者和世人,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23](P177)孟子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常举 “人乍见孺子入井” 之例,认为怵惕恻隐之心是人的自然心理感受,属于人的天性实情;孟子由此阐发,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四端之心开显,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并显见于人的音容举止、举手投足,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3](P341)孟子以四端之心将仁义礼智德性化、内在化。 “四端” 之心可直解为四种道德情感, “孟子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将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范畴统统归结为情感问题,以情感为其内在的心理基础。”[21](P175)四端心善、性善,也意味着情善,即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23](P283)孟子认为情乃性之才质,其本然都是善的;至于现实中人们性情感表现相悬殊甚或无定数,非因天之降才资不善或相殊,而在于其放逐本心、良心之因使然,陷溺其心而不能尽其性和尽其才。东汉学者赵歧在其《孟子章句》中指出: “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情从性也,能顺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谓善也。若随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动之故也。”[25]孟子赋予 “性” 以逻辑在先和价值优先性,由人的本然之善性发出真情实感可以成为现实之善;而人之所以有现实之不善,乃是因为人的情感受到外物的诱动。孟子多处所谈的良心、本心即道德心、善良之心,以道德情感为基础而向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 “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26]因为心善、性善以及情善,所以孟子要求存心养性、反求诸己以 “存心” 、求 “放心” ,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3](P292);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3](P214)饮食之人之所以不能以仁义礼智之性存心,是因为他们不能拒绝耳目之欲的诱惑,养其 “小者” 或从其 “小体” 而 “失大” 。孟子要求人常做自觉的工夫,不陷溺于耳目感官欲望的放纵之中,把放失的善性良心找寻回来,并 “扩而充之” ,使四端善心和性情善质完全呈现出来,就是尽心、尽性,并由此同超越性的价值本源( “天” )相契合,即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23](P331)在治理国家方面,孟子提诫统治者以仁心、仁闻泽被众民,以德教仁政平治天下,因为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23](P337)仁政本源于人心性情,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23](P83)仁政、善教者注重于以情感人、以德服人、教化民心、恩泽百姓,使民众心悦诚服、举首望之,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23](P77)以仁之情爱民、以义之德服人远胜于以方命苛政虐民罔民,以坚甲利兵暴民驱民。 “孟子把他的整个‘仁政王道’的经济政治纲领完全建立在心理的情感原则上。”[27]
(二)情善以理,且仁且智
孟子阐明人们既有共同的自然情欲,也有共同的天然性情,更应遵循共同的义和理。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 并相信, “圣人,与我同类者。 ”[23](P285-286)心之同然既为欲、情,也为理、义,而应以 “义理悦心” ,汉代贾谊说 “义” 为 “理” , “义者,理也,故曰‘义者德之理也’”[24](P99); “心兼爱人谓之仁,……行充其宜谓之义” ,由之, “人主仁而境内和矣,……人主义而境内理矣”[24](P91-92)。孟子注重于将口目耳鼻之欲性与仁义礼知之心性比较,并分别以 “命” “性” 言之,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父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23](P370)孟子虽然承认人之物质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天命难免的事实,但视其并非为人的根本特性,在君子眼里更多将之视为 “命” ;君子强调的人之根本性乃是人之区别于禽兽的社会道德性情,是人的真正天性,而少有将其归为 “命” 。孟子也将上述欲性与心性分别以 “小体” “大体” 称谓,并断言,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3](P295) “大体” 乃指心之官所思之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及其情感的呈现,是人异于禽兽、君子异于小人的天性情感; “小体” 指出自耳目口鼻方面的感官欲望和自然情感,其实现与否决定于外物环境和命运节遇。自然情感缺乏自在纯净或内在提升以接近于天命的可能性;而道德情感则求之在我,如能反身自躬求放心,则意味着回归本性良心,明乎礼仪廉耻和义利之辨。人应先立乎 “大者” 、养其 “大体” ,以仁义礼智根于心,以道德情感控制自然情感,使情欲得以合理的实现。仁、义、礼、智之性显露于孝悌、敬长等天命之情,且仁与义、智、礼相需配合,孟子曰: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23](P196)偏离仁义而追逐耳目口欲的 “小体” 之情是为非智或不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23](P85) “仁” 和 “智” 俱存是为君子、圣人,孟子曾引子贡曰: “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23](P66)仁人、君子理应既仁且智,以义理调节、控制自然情欲。
三、荀子的以情说性与以理节情、以礼导情说
荀子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以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28](P357)荀子主张性恶、情亦恶说;如果放任情欲,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28](P373)荀子主张以理节情、以理制情,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
(一)情不可免,以情说性
荀子与孟子一样肯定人人有相同之性,他在多处表达尧舜禹与桀跖、君子与小人之性同,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28](P383)荀子从人之自然生理欲求和感官的本能之情等方面认识 “性” ,认 “情” 为 “性” 的实质表现或内容,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28](P357,P369)宋代学者杨倞对之解释曰: “性者成于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质体,欲又情之所应,所以人必不免于有欲也。”[29]“情” 的本质或根据也基本属于人性内心的东西,所以谓 “天情” ,表明着情感的本然性。荀子也和孟子一样常常将 “性” “情” 对举或连称,意谓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且多处肯定 “人之情” 相同或 “人情所同欲” 。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28](P377,P379)引文中的 “性” 或 “情” 、 “情性” 或 “性情” ,都有与 “欲” 接近的地方,与 “情之应” 相类。 “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28](P497) “情性” 表达 “性” 和 “情” 之间的密切关联。荀子另有区分性、情之说,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28](P109)杨倞对此注曰: “言天性非吾自能为也,必在化而为之也” ; “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诱而为之”[30](P144)。 在此, “性” 以及性情是本然的、先验的,所以 “不能为” ;而好恶、喜怒等情之应则是经验的、直觉的、实然的,由于现实感应而有不同的表现。虽然荀子常常以人之情同而说性同,是君子、禹桀、小人所同性同情者,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28](P44)然而现实中人们实际好恶表现、地位命运之差异在于行为举止以及风俗环境影响使得 “情之应” 有差别使然,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 , “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 “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28](P44-45)在性、情方面,人们既有出于先天本然的一致性,又有后天环境和个人举止造成的情之应方面的差异以及可以修为的方面。
(二)以理节情,礼以饰情
荀子提倡 “知” 和 “理” , “是是、非非谓之知”[28](P15);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28](P239)。 他认为无法根绝、也不主张取消人的欲望和情感,而是主张以理节情、以理制情、以义制利、以义制事。由外物引发的欲情,当人缺乏理知、不懂得礼法的时候,是没有节制的;人心具 “有知” “有义” 即认识 “礼” 或 “理” 的能力, “义者,理也” ,可以引导情欲得到节制,使认识和行为 “中理” “合礼” 。 “以理制情” 即以理性原则指导人的情感生活,即 “使心之所可中理” ,行为合于社会理性法则、普遍规制化的 “礼” 。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28](P369) “以理制情” 并不禁止人的情欲,而是提倡兼其情、制焉情,以理导欲、节欲, “圣人纵(通‘从’)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28](P349);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同‘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28](P368)出于理性的导欲胜于去欲,节欲胜于寡欲。他常说: “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贵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28](P369)人之实情,必不免于有欲也, “欲不可去” ,所以荀子反对单纯的 “去欲” “寡欲” ,主张以心之虑、人之知禀于 “心之所可” “心为之择” ,通过 “导欲” “节欲” ,以达到 “中事” “中说” “中理” 。 “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28](P95-96)情之 “理” ,荀子也用 “义” 表示, “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28](P263) “义” 根本在于节内外、上下之情, “正义而为” 。 “中理” “正义” 之行在于像孟子所主张的达到既知且仁、既仁且理,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28](P200-201)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28](P239)否则, “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28](P295)
古代思想家提倡 “礼” ,并主张 “礼以饰情” (《礼记·曾子问》)。 《中庸》云: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7](P55)管子云: “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31]《郭店楚简·语丛一》篇也称: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8](P188)以上引文表明礼是缘由人之亲亲之情、尊贤之义而生发、制作。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28](P15)同孔子一样,荀子将 “礼” 视作 “知” “理” 的外在化以及 “情” 的规范。 如北宋张载讲, “礼者理也”[32];因此, “对中国人而言,合理的言行和执行活动,必须合乎‘礼’,事实上,‘礼’与‘理’往往呈现相通性。 ”[33]由于性、情、欲之私己和无节制,荀子主张忍性情,慎积习, “称情而立文” ,即缘依人情以制礼文,并主张归之于礼义的王制。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扰’,驯服义)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28](P376)荀子礼义学说从人与人之情与性相同而主张 “养情” 、 “导情” ,而不是 “禁情” , “术礼义而情爱人”[28](P18), “故礼者,养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28](P300-301)人之 “性” 、 “情” 可通过性 “伪” 、心 “择” 开显出适度有节之礼文,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功谓之伪。 ”[28](P359)即人凭 “有知” “有义” 之心,对情作出抉择,向礼义规范过渡,使 “情安礼” ,成为道德的人,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闲闲、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28](P435)义和礼在于使得 “仁其里” 以及 “行义遂理” ,使得仁之情恰得其所、适得其道。礼文是心 “择” 有为、 “性伪” 之 “外在化” 的结果,根源于人对自然性情有待完成的自觉,对道德人格和社会礼义文化的追求。 “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说,礼的价值就在于:一方面,使人的情感得以适当的表达;另一方面,使得人的行为符合应当性原则的要求。”[34]礼义是以理知对情的恰当规范,在于饰情、导情,使性情或欲情中理、中流。 “合乎情然后当于理” , “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陈,是礼之中流也。”[28](P306)唐君毅评价荀子的礼义之理性意义说: “荀子所以不重纯知之思想上之理与物理,其根据之理由,正在荀子之唯以礼义文理之全理,为真正之理为大理” ; “大理与偏曲小理相对,大理者礼义文理之全理,亦即与只辨坚白同异之纯知之推理,即只求偏知物理之事相对者也。”[35]
中国哲学注重于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将人性与天道、天命紧密相关,人性获得人生形而上学的本体、本然意蕴。在道德个体起源的思考中,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尽管关于人性论表述内容不同,但对于性情问题的关注和理情说方面都有契合相似,或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认为人受之于天的自然禀赋为性,性发为情,表达情的普遍性;在培养人们的理、知、智时,则重在于理情、知情、导情,既仁且智,称情立文。他们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主题和气质,将道德根源、提升发展与人情世事紧密关切。东汉王充评述情性说: “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36]蒙培元评价: “将情感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来对待,作为人的存在问题来对待,提出和讨论情感的各个方面,比如好恶之情,喜怒哀乐之情,‘四端’之情,敬畏之情,等等,并将其安排为心灵的重要内容,成为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主要话题,则是儒家哲学所特有的。 ”[21](P9)之后宋明理学、明清儒学,以及现代新儒学都关注和继续发扬儒家重情、理情之说,使儒家哲学独显关注和解决人情事变的性理、人道特征,从而避免将理性与情感割裂,走向玄思抽象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偏途⑤。现代新儒家熊十力认为: “西洋学人将理智与情感划分,祗是不见自性,即不识本性。吾先哲透明心地即谓本心,即从情之方面,而明心曰仁。仁之端曰恻隐,恻隐即情也。然言仁,便已赅智。……然言智,便已赅仁义礼智信等等万德……识得本心原是情智不二之体,……正常之情,即中节之和也,即性也。性情无二元。宜深体之。”[37]梁漱溟将与情相关之理称为 “理性” “情理” ,区别于 “理智” 和 “物理” ,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 ; “所谓理者,即有此不同,似当分别予以不同名称。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 ,人类所以异于一般生物在于其要求生活之合理性追求,而且 “以理智为人类的特征,未若以理性当之深切著明,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38]现实生活中人们注重 “动之以情” 与 “晓之以理” 并举,讲求通 “情” 与达 “理” 相统一,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独特标记。
注:
①学者冯天瑜研究元典及其精神,他认为作为古代文化产物的元典及其包蕴着的民族元精神,对后世产生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他总括中华元典,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
②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中专门提到了关于 “情” 的理解问题,他以《庄子》为例,探讨了 “情” 的3种用法: “一种是情实之情,这种用法的本身,没有独立意义;另一种实际与‘性’字是一样……第三,是包括一般所说的情欲之情,而范围较广。”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329.)
③朱熹曾区分情之未发为性、为中,性之已发为情、为和, “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谓之和,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 (朱熹.朱子大全·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49.1206.)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 (朱熹.朱子大全·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49.659.)
④朱熹说: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8.) “性不可言。 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 (朱熹.朱子语类(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89.)
⑤李泽厚从根本、本源、根源以及人生在世、生活世界谈本体,而非像西方哲学从形而上学或超验存在谈本体,并认为 “‘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 (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5.)但是相对来说,中国哲学有 “道体说” 、 “仁体论” , “而爱的情感只是仁体的显现之用” (陈来.仁学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17.),或者说是 “道体” 的显现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