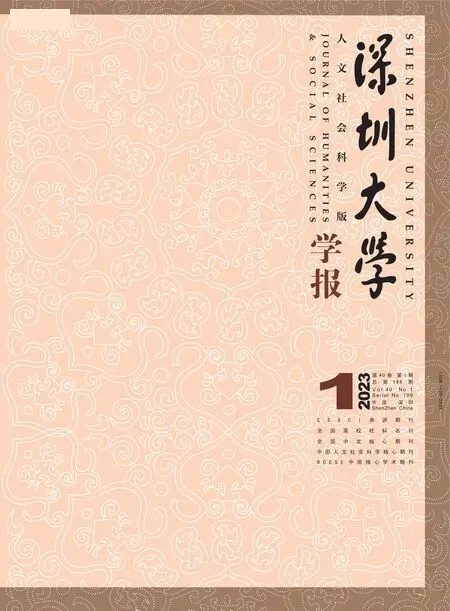当代 “本质主义” 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罗崇宏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疫情等现实问题,以及文论中 “间性” (如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理论的生成问题,促使当代文论开始从以 “人” 为中心的 “人文主义” ,向重新思考 “人与物” 关系的 “后人文主义” 转移。而这一切又都笼罩于 “间性” 的思维模式之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是 “反本质主义” 。就当代文论知识生产的演绎脉络而言,反本质主义既承接了 “文化研究” 范式下的 “反精英主义” 话语模式,同时也预示了当代以 “思辩实在论” 和 “事件论” 为代表的、具有 “反语言论” 倾向的理论走向。不过,要搞清楚这些带有前瞻性的、学界尚处于探索阶段的理论走向,就有必要返回到当代文论的 “历史现场” ——本质主义那里,也即通过对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中曾经盛极一时的、源自西方的本质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界的知识旅行的梳理,以期对当代文论的未来发展与走向有更为清晰的思考与认识。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回到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探究以 “主体性” 和 “本体论” 等概念为中心的 “本质主义” 文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旅行与话语建构。
具体而言,研究以 “主体性” 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就是通过对 “形象思维” 的理论旅行及其影响的探讨,进而研究 “主体性” 话语的生成;而研究本质主义的另一个关键词——本体论,则是通过对 “向内转”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零度写作等概念的梳理,从而探究当代本体论文论的生成过程。
一、 “形象思维” 与文学主体性
从源头来看,当代 “形象思维” 的话语论争始于1950年代,到了1980年代这种话语论争开始与本质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密切相关。一些文艺理论家如朱光潜、李泽厚等纷纷撰文讨论有关 “形象思维” 的理论问题,并使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如果说此时的 “人学” 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领域,那么 “形象思维” 的讨论则主要聚焦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不过,国内学术界所使用的 “形象思维” 概念大多沿用了苏联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Belinsky)的 “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的定义。在文学活动的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4个要素中, “形象思维” 强调艺术家通过创作活动而对世界进行诗意化反映。可以说,对于形象思维的探讨几乎是和以 “人” 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潮同步发生的,它们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初期主体性文学理论的知识脉络。
(一) “形象思维” 的理论旅行
如果把自1980年代以来批判话语语境中的文论视作 “本质主义” 的理论知识,那么1980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于 “形象思维” 的讨论,则可视为探索文学 “本质” 的滥觞。对于 “形象思维” 概念的讨论可追溯到1950年代中后期,且从讨论者所使用的理论资源看, “形象思维” 的语义最初是从苏联理论家别林斯基那里 “旅行” 而来。在1839年发表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别林斯基提出 “诗人用形象思索;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P96)。 到了 1841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概念》一文中又提出 “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来思维”[2](P93)。 就其源头而言,学界一般将 “形象思维” 的 “原点” 追溯到黑格尔:
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即不是在哲学逻辑里作为绝对来了解的那种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3](P92)
可以看出,黑格尔关于艺术理念的定义也可以概括为他关于美的定义,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P142)。 同时黑格尔将 “艺术美” 的概念与 “具体形象” “感性” “理念” 等概念联系起来,这些概念被别林斯基不同程度地移植进他的 “形象思维” 概念的语义之中,成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俄文版本[4]。不过1980年代前后,国内学界关于 “形象思维” 讨论的重新盛行直接肇始于革命领袖对于文学创作中 “形象思维” 重要性的大力倡导。1978年《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充分 “肯定了形象思维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5](P735),从而实现了对 “文革” 时期将形象思维视为 “修正主义” 认识论的反驳。
实际上,美学家朱光潜、李泽厚等人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移用源自西方尤其是苏联的文艺思想,对 “形象思维” 进行理论思考。当然,这些美学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移植苏联的 “形象思维” 概念,而是在重新阐释概念的过程中构建他们自己的美学思想,因为 “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6](P35)。李泽厚认为形象思维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也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过程。从李泽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基本上是比较纯粹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问题,但在 “文革” 期间这种比较纯粹的文艺理论问题不断地受到主流意识的质疑、批判和打压。
大致说来,直到《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一文发表之后,知识分子才逐渐从意识形态的讨论转移到学术领域的讨论之中。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认识过程及其西方的理论渊源,并将 “形象思维” 的讨论作为《西方美学史》近代部分的重要主题。与李泽厚稍有不同的是,朱光潜更加学理化地将 “形象思维” 诠释为 “想象” (Imagination),即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朱光潜提出形象思维属于感性认识范畴,这一范畴要求文艺创作从生活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所形成的成果是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同时,朱光潜还从美学史的知识脉络出发分析 “形象思维” 概念的生成与流变,认为柏拉图的 “理念” 说把诗人逐出了 “理想国” ,成为 “西方反对形象思维的第一人” ,其结果是限制甚至排斥了文艺的发展[5](P739)。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伦理学》等文本中则肯定了艺术是一种 “生产” “创造” 和 “虚构” , “亚里士多德这些观点已包含了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的精义,尽管他还没有用‘形象思维’这个词”[5](P739)。 不仅如此,朱光潜又把维科(Vico)美学思想的核心概括为 “形象思维” 。与强调 “理性” 的法国新古典主义不同,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维科,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寻找文化中各个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并强调 “感性认识” 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认为原始民族就是通过带有感性色彩的形象思维构建人类的初始文化。这种带有想象和虚构的初始文化是一种诗性的文化,只是随着人类进入 “人的时代” , “形象思维受制于抽象思维,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强旺的生活力”[7]。
朱光潜认为维科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对立的观念过于绝对化。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 “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8]不同,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 “按照诗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既是高明的诗人,又是高明的玄学家”[9],其结果是造成诗与哲学的绝对对立。与此相对应的是,李泽厚在讨论形象思维的论文中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常常是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的[10]。此后,人们对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入,如《形象思维与逻辑》就将这两种思维间的关系概括为 “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思维的形象性与逻辑性相互作用的关系”[11]。
(二)文学 “主体性” 的生成
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关于 “形象思维” 的论争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经历了 “文革” 十年的中断,到1980年代又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在1986年前后, “形象思维” 逐步被 “艺术思维” “创作思维” “艺术构思” “艺术想象” 等概念所取代,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热点也从 “反映论” 转向对 “主体性” 问题的讨论[12]。而不论是以 “形象思维” 为中心的反映论,还是关于 “主体性” 的讨论,在文学活动中都表现为以 “人” 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理论思考。不论是 “形象思维” 的论争还是对于 “人学” 问题的关注,都可看作是在 “本质主义” 思维模式下的文学本体论讨论。尽管形象思维讨论的重心是作家在艺术活动中如何想象性地、感性地反映世界,而 “人学” 的讨论则是为了实现对人的 “新启蒙” ,但它们实质都是要摆脱文革以来政治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束缚,进而重新回归人的主体性地位并最终回归文学的主体性。
学界一般认为,在当代批判性文化场域中 “文学主体论是在文学是人学-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间性的逻辑构架中确立和进展的”[13]。文学主体性的核心是讨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与 “人” 有关的 “主体性” 问题。1980年代关于文学 “主体性” 的讨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被夏中义称之为 “刘氏三论” 之一的 “文学主体论”[14](封底)。1985年刘再复在《读书》《文汇报》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4篇关于 “文学主体性” 问题的论文,由此在学界引发了有关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仅从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一书,就可以看出当时关于 “文学主体性” 讨论的大致情形。美国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一书中认为,文学活动涉及4个要素:作品 (work)、艺 术 家(artist)、世 界 (universe)和 读 者(audience)[15]。但刘再复的 “文学主体论” 并非专指文学活动的某一要素,而是以 “人” 为中心的整体:
所谓主体,对于整个文学过程来说,包括三种意义:一是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二是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三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14](P45)
可见,刘再复 “文学主体论” 中的主体包括作家主体、读者主体和作品中的人物主体。如前所述,1980年代从对 “形象思维” 的倡导到 “文学主体论” 的提出,实质上是与这一时期的 “人学” 话语一脉相承的,也即对文革时期压制人性的一体化思想的反驳。对此刘再复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主人翁的地位,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使文学研究形成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研究系统。[14](P49)
刘再复认为文学主体性的实现,就是要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而 “人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体,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14](P54)。这就要摆脱之前的以 “阶级斗争” 话语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参照体系,回归文学和生活本身,进而开拓属于人的更深层次的内在世界,强化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主体情感论等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为文学研究开拓更多的审美视野,从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符号学等多种角度去审视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还没有摆脱对 “人性” 的极化思考,只是 “将有关人的主体性理论阐述平移至文学领域”[16],进而把 “主体性” 这个具有超越性的理论问题与具体的文学问题甚至社会政治问题简单地勾连在一起,缺乏对该理论问题作更深入地挖掘。进一步说,刘再复的 “文学主体论” 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李泽厚 “主体性” 哲学思想的改造和简化,并将 “主体性等于人的主观能动性”[17]。
而李泽厚的的主体性哲学思想则是在阐述康德的 “先验主体” 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德的主体思想又是基于对欧洲 “经验论” 和 “唯理论” 的批判提出来的。从分析知识的源头出发,康德认为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18](P1)。 康德对 “知识” 与 “经验” 关系的论述看似矛盾,其实他强调的是从时间上看经验在知识之前,但从逻辑上看经验知识里面包含一些 “先天” 的成分,也即经验知识的构架或获得知识的能力,这就是康德的 “纯粹理性” 或 “先验” 概念。康德的纯粹理性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康德在其中构建了一个 “先验主体” ,也就是摆脱 “经验” 束缚的、纯粹的、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刘再复所说的 “精神主体” ,其语义内涵大多源自康德的 “先验主体” 概念。
于是,1980年代的 “人学” 思想就与康德的那种纯粹的、不受经验束缚的先验主体思想存在某种跨时空的契合。刘再复将之具体化为回归人的主观能动性,并由此回归人、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而这些恰恰是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关系形成的意识形态所极力反对的甚至是批判的对象。当然从根本上说,极 “左” 思潮不是要反对人道主义,而是在极端对立思维模式主导下,教条化地将人、人性、主体等概念简单地整合进 “资” 姓话语的语义场之中。
概言之,从主体性的话语流变来看,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冲破了此前加在文学活动中的种种束缚,为此后 “本质主义” 文学理论的提出作了知识和思想上的铺垫。不过,从 “主体/主体性” 的知识谱系来看, “主体/主体性” 的问题常常与启蒙、审美现代性、理性等理论话语勾连在一起[19],由此展开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随之确立了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性哲学建构”[20](P90),而这些又常常成为后现代理论话语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到了1990年代, “主体的退隐” “主体的黄昏” “主体的死亡” 等针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话语被后现代思潮裹挟而来。这种哲学反思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拉康的‘镜像自我’,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主体’等”[20](P91)。 尤其是随着 “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概念的不断介入,学者们认为文学活动的主客体之间只有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中,才能使客体成为另一个主体。于是,针对主体性的批判,使得 “主体性” 向 “主体间性” 发生理论转向,随即文学理论也从 “本质主义” 向 “反本质主义” “建构主义” 等范式转移。
二、转向 “作品” 的形式主义
前文所述对形象思维和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本质上是为了摆脱极 “左” 文艺思潮对于 “人” 的束缚。就文学活动或者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而言,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作家如何创作的问题,也即主要集中于作家的本体研究。尽管刘再复等人的本体论还涉及到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对象本体,但其论争的重点依然是如何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并借此回归文学本体。但此后随着 “向内转”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的理论话语的出现,学界关注的焦点逐渐从作家本体转移到作品本体,也就是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等人所说的 “内部研究” ,所讨论的问题从人性的本质转到文学的本质上来。从文学理论演绎的内在逻辑来看,以 “作品” 为中心的本体论也与20世纪文学理论关注点的转移有关,也即 “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21](P3)。由此,韦勒克等人更是直接提出 “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22](P139)。
(一) “向内转” 与文学理论转向
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理论界出现了 “向内转” 的学术争鸣现象。学界一般认为, “向内转” 的概念是1986年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 “向内转” 》一文中首次提出的[23]。这种 “向内转” 的文艺争鸣或文论思想的出现与198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有关。建国以后,在 “文学为政治服务” 话语的指引下,文学理论生产试图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互动中构建以 “政治” 为中心的 “外部研究” 模式,从而相对忽略了文学内在的形式、结构等本体性的因素。此外,文学研究 “向内转” 也与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知识 “旅行” 到中国并产生影响有很大关系。
从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 “向内转” 现象固然与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有关,但更多地是受到外来理论知识的影响。虽然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 “向内转” 》一文中较早地论述了 “向内转” 的文学创作新趋势,但其对于 “向内转” 概念的语义来源却语焉不详。彼时由刘象愚等人翻译、美国文艺理论家雷纳·韦勒克等人撰写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已于 1984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 “新批评” 文论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常为学界所提及的是韦勒克等人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的研究分为 “外部研究” 和 “内部研究” 。韦勒克等人的观点之所以在1980年代中后期让人耳目一新,主要就在于这些观念可被视为文学研究从 “外部研究” 走向 “内部研究” 的风向标。与此前文学究竟为何者服务的观念不同,文学的 “内部研究” 首先思考的是何为文学、文学的本质以及文学的作用等本体性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 “外部研究” ,其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 “外在的” 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 “因果式的” 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22](P65)
尽管学界倾向于认为 “向内转” 是鲁枢元首先提出的,但他本人却说这个概念 “并不是我的创造发明,只是我的引进与发挥”[24](P5)。不可否认的是, “向内转” 与 “新批评” 的理论话语是不谋而合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研究的 “向内转” 是受到了源自西方的 “内部研究” 思路的启发而提出的,而 “内部研究” 的提出又与自19世纪以来的心理学与文学的互渗性关系有关,它使得文学研究 “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24](P5)。 不过,正是由于 “向内转” 概念的移植性而非原生性,使得它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语境中遭到诸多非议。这些非议认为,向内转是要反社会主义、反现实主义、反对深入生活。鉴于这种情况,鲁枢元对 “向内转” 的概念作了详细的界定:
“向内转” 是对多年来极 “左” 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 “向内转” 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24](P7)
从鲁枢元的概念界定中,我们不难发现 “向内转” 既顺应了80年代文学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人文知识分子 “借助西方理论的话语优势来突破现实主义文学所构成的‘成规’和‘秩序’以及重述文学史的言说方式”[25](P51)。如国内学者陶东风就认为, “向内转” 是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自身的领域,从物质世界转向心理世界[26];白亮则认为,文学的 “向内转” 是从文学的叙述向作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转移,从文学的叙述向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转移[25](P47)。 实际上,作为 “向内转” 理论源头的 “新批评” 是对西方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注重作家的生平和主观情感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研究的理论反拨。也就是说 “新批评” 从 “外部” 转向 “内部” 可被视为其关注的重心从 “作家” 转移到了 “作品” 。因为过于关注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被视为是一种 “因果式” 的研究,而 “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22](P31)。
可见, “向内转” 是国内学界在吸收了 “新批评” 提出的 “内部研究” 的语义之后,结合中国当代 “去政治化” 的话语语义而生成的新概念。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世界文化共振的场域中,不由自主地生成了由对 “作家” 的关注向 “作品” 转移的趋势,并进而从对 “文学性” 的拷问回归文学的本体研究。
(二)形式主义文论的生成
本文把 “形式主义” 以及随后将要讨论的 “结构主义” 文学理论统称为形式本体论,是因为它们都是以语言学理论或 “语言学转向” 作为话语基础,继而形成 “形式中心” 的理论框架。如果说 “向内转” 大体上是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生成的理论话语,那么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则基本上是移植于西方的理论知识。当然,这种形式本体论的生成也并非偶然, “向内转” 使研究视角开始聚集于 “作品” ,客观上为形式本体论的生成提供了话语空间。
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经历了从 “伤痕” “反思” “寻根” 到 “新写实” “先锋文学” 等流变之后,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也从 “革命” 转移到 “后革命” 。同时,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实践也开始向日常生活倾斜。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生成于 “后革命” 语境中的私人化、生活化写作乃至先锋文本实验,使得曾经盛行于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逐步被淡化内容而重视形式的文本实践所取代。这不仅体现在文学活动的关注点从 “作家” 转移到了 “作品” ,也体现在从 “写什么” 变为 “如何写” 。如果说 “新写实” 从 “宏大场景” 走向普通生活,开始了 “如何写” 的技术探索,那么 “先锋写作” 则走到了 “如何写” 的顶峰。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当代文学实践相对应的文学研究从作家走向作品、从内容走向形式,为形式本体论理论话语的引进营造了适宜的接受语境。
就概念而言,较早提到 “形式主义” 的是袁可嘉。1979年袁可嘉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中提出,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过结构主义的先驱——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27]。从知识的源头来看,当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引介不无关系。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和《苏俄形式主义文论选》等书,类似介绍形式主义的文章和专著还有很多。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一书的主要翻译者方珊在该书的 “前言” 中说,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 “均是从国内能找到的有限文献中选取的”[28](P31)。
实际上,源发于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受到语言学理论的直接影响,并在文学研究中 “对形式的强调,突显了对文学表现性的、模仿的和认知方面的关注”[29](P602)。 这其中的 “文学性” (literariness)、 “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等概念就是基于语言学理论而对于文学语言的特殊要求。如俄国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这样描述陌生化(反常化):
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 “反常化” 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28](P6)
可以看出,什克洛夫斯基是将 “陌生化” 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而提出来的,有点类似中国传统文论中的 “文似看山不喜平” ,也即通过增加语言的难度来增强艺术的表现力。而对于 “文学性” , “雅格布逊于1919年写道,‘文学的学科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是那让一部具体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30]。这之后 “文学性” 以及由此带来的 “陌生化” 似乎成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或者文学本质的一个标准。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谈到 “文学是什么” 的时候提出, “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它并不是永远给定的特性”[31](P5),形式主义者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并假定 “使陌生是文学的本质”[31](P5)。
尽管 “形式主义者以语言学为研究基础,把重点放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29](P603),但他们并非不重视内容,而是认为 “形式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内容”[29](P606)。 需要强调的是,自 1980 年代以来形式主义旅行到中国,它并非简单地 “移植” 而是 “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32]。如陈建华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一文中就认为 “陌生化” “文学性” 等概念常常被用以分析文学语言的特性以及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不仅仅作为表现技巧和手法。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将 “陌生化” “文学性” 等作为元理论去解读中国的文学文本,如《杜诗语言的 “陌生化” 之妙》《从 “陌生化” 看李清照词的语言创新》《论张爱玲小说的陌生化效果》等文章,就是将 “陌生化” 作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视角,并借此对中国文学文本进行重新阐释。于是,形式主义旅行到中国,其 “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6](P35)。其实,这也是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见形式,即移植并重构源自西方的理论知识。不过这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生硬地用西方理论切割中国问题,以及由于对西方理论知识吸收过多,以致于几乎遗弃了中国古代文论,也就是1990年代曹顺庆所提出的 “文论失语症” 的问题。
应该说, “形式主义” 在国内的译介和移用,并非学界简单而随意的移植行为,而是形式主义与中国当代的接受语境相契合的结果。然而,目前所见到的不论是 “形式主义文论选” ,还是有关此种理论的研究性文字,大多是介绍或者阐述形式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或理论特点。这些研究要么介绍 “陌生化” 的问题,要么阐述文学之为文学的 “文学性” 问题,却很少讨论形式主义被译介到中国的必然性与接受语境或很少研究这种理论生成的话语逻辑。实际上,形式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当代接受语境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主义 “把作品作为考虑的中心”[33](P6),并认为 “不能根据作家生平、也不能根据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来解释一部作品”[33](P7)。这种理论主张与中国当代文论对于宏大叙事的反拨,并由此反对根据社会环境和作家生平等外部因素去研究作品的 “向内转” 的理论倾向相契合。当然,这种契合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任何一种外来文论知识与中国的特定语境之间都只是部分地契合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基于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形式主义视为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根本之处在于,作为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 “文学性” 等,常被用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就是认为文学具有区别于其他文本的本质特性。但与此同时,一些反本质主义者则认为文学性更多指向文本生成的语境,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惯例或机制。文学性并非特指文学的本质,而是可以存在于其他非文学的文本之中[34]。尤其到了1990年中后期,随着 “文化研究” 理论范式的介入,文学研究的对象从传统的 “作品” 向 “文本” 突围,文学性的概念也从本质主义向反本质主义发生流变。
三、回归 “写作” 的结构主义
(一) “结构主义” 的本土旅行
作为形式本体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话语——结构主义常常被视为俄国形式主义新的发展形式。当代文学研究 “向内转” 之后,关注的焦点从作家生存环境的文化政治学转移到了作品形式的结构诗学。文化政治学强调的是作家的生平、政治环境等因素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及后果,而结构诗学则关注作品的 “语言如何生产意义”[35]。形式主义理论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认为, “诗学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 ,因为文学活动就是语言实践的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则更接近研究语言的学科——语言学[28](P76)。由此托马舍夫斯基将 “研究艺术作品结构的学科称之为诗学”[28](P79)。在俄国语言学派或者形式主义理论家那里, “形式” 和 “结构” 都是与语言研究相关的、语义大体相同的概念。不过以这些概念为核心的理论话语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对此赵宪章在《文艺学方法通论》中指出, “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是在与现代语言学的相互影响中并行发展起来的,那么,结构主义则是直接导源于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都被结构主义所运用”[36]。
概言之,如果我们将1980年代的 “人学” 话语视作当代中国的 “人本主义” 文艺思潮的话,那么,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结构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学、叙事学等就可被看作是科学主义文艺思潮。不可否认,在当代中国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是移植性的而非原生性的理论资源,它们都是在自西方旅行而来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重构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理论的生成并非基于中国本土的文本实践经验,而是 “先验式” 的理论知识生产,并普遍地存在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就科学主义文艺思潮而言,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 “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21](P1),这就使得结构主义者强调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将文本视为与作者无关的 “结构” 和 “关系” , “以揭示文学文本表层结构底下的深层意义或结构”[21](P2)。
由前述可知,形式主义出于对作品本体的强调,反对将外部环境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借助于语言学的理论资源提出文学性和陌生化等问题。而结构主义则 “主要发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37](序言),最为常见的是将对语言的分析模式应用于整个文学文本、文学现象,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分析之中,以此去 “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37](序言)。这当中比较典型的是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理论话语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在中国的知识旅行。从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译介的情况,大致可以看出法国结构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除了理论原著的翻译之外,结构主义旅行到中国之后形成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罗钢的《叙事学导论》、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等。同时,在结构主义理论话语影响下的文体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王一川的《语言乌托邦》等。
不论是结构主义原著的翻译,还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叙述学、文体学等理论知识,本文都将其视为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知识生产。尽管原著翻译只是客观的理论知识译介,但 “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6](P35),而是一个建立在理解和解释基础上,构建诸如结构、符号、叙事等新概念和意义的过程。比较典型的是针对罗兰·巴特的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一书的翻译。1987年董学文等人将此书译为《符号学美学》,但到了1988年李幼蒸则将其翻译成《符号学原理》,此后这一译名一直沿用至今。法语词éléments包含成分、要素和基本概念等语义,因而将 éléments翻译为 “原理” 比 “美学” 更为合理。而董学文等人用 “美学” 一词去翻译éléments的主要原因是,此书被纳入由美学家李泽厚主编的 “美学译文丛书” 系列之中。
不仅如此,从《符号学美学》与《符号学原理》两个译本的 “译者前言” 中可以看到,它们对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解。《符号学美学》一书的 “译者前言” 称罗兰·巴特为 “结构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38](P1);在《符号学原理》中则是 “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9]。尽管两者区别并不是很大,但后者着重强调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的 “译者前言” 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知识的介绍和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界对结构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如1986年伍晓明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 “中译本初版译后记” 中概括了他对于 “结构主义” 的理解与认识:
结构主义是把索绪尔创立的现代结构语言学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尝试……结构主义认为,正像人们有了普通语言的语法才可以构造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语句一样,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受文学 “语法” 的支配。[40]
伍晓明将结构主义的理论源头追溯到索绪尔的语言学,并将语法意义视为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心。不过现在看来,伍晓明在1986年对于结构主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语法意义大多是表层结构关注的重心,深层结构则从语言的语法层面突围出去,转而关注在叙事话语与文化背景互渗过程中的共时性意义。与伍晓明的关注点不同,在《符号学美学》的 “译者前言” 中,董学文提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扩展,必然引起大部分人文科学中观察问题角度的深刻变化。从这一新角度出发,观察事物就再也不是搜集可以实验印证的资料的问题,不是一个用实证主义眼光看待客观世界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把一切表达形式都看成是符号;而这些符号的意义取决于惯例、关系和系统,而不取决于任何内在的特性。[38](P3)
董学文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从实证主义走向符号学或语用论。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客观地从语法结构中展示出来的,而是取决于某种惯例、关系和系统中的语言实践,也即日常语言学派的 “以言行事” 。
(二) “零度写作” 的话语实践
除了对原著的翻译和解释之外,当代学界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移植与话语建构,常常通过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或者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阐释的方式来完成。较为典型的是对文学活动的核心概念──写作的理解,从语法意义上的客观对象转向语用意义上的生成性事件。李幼蒸在《写作的零度》的 “译者前言” 中认为,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作者毕生思考的主题——写作(écriture)的概念。虽然在法国学界早已有人使用这一概念,但 “从《写作的零度》开始,‘写作’才正式确立其文学理论基本范畴的地位。写作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41](P1)。李幼蒸直接引用罗兰·巴特在书中的解释, “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réalité formelle)的空间:这就是写作”[41](P10)。李幼蒸认为《写作的零度》表面上是在论述文学话语的形式分析的问题,实际上关注的是文学话语真实性的问题,也就是 “巴特主张的零度的写作或中性的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41](P6)。 而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巴特也详细地阐述了其 “零度写作” 的概念:
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伤的形式)的话。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 “不在” 所构成。[41](P48)
可见,巴特把一种不动声色的、白色的、零度介入的写作称为 “零度写作” 。李幼蒸敏锐地意识到,《写作的零度》中所提出的、摆脱社会性价值判断的 “零度写作” ,对于长期隔膜于文学形式和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的国内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理论启示意义。正是基于此,在1984年李幼蒸归国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将《写作的零度》以及巴特的另一本结构主义理论著作《符号学原理》一并译介给中国读者[41](P7),继而使得 “零度写作” 这一文学理论基本概念以翻译的方式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知识场域中的新成员,并渗透进 “新写实小说” 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之中。如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部全国通用教材中,就将 “零度写作” 的理论话语融入对新写实小说的分析之中, “新写实小说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42](P309)。陈思和把 “新写实” 写作视为一种消解激情式的叙事方式,并有意弱化叙述者的主体性功能,使得叙事者成为单纯的旁观者[42](P309)。
与陈思和的看法稍有不同的是,洪子诚更多地是从 “原生态” 的角度去理解 “零度写作”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洪子诚认为就艺术风尚而言,新写实 “表现了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零度叙述’的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价值评价。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43]。此外,在《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一书中,旷新年也是以 “原生态” “零度” 等作为关键词对 “新写实” 写作进行理论概括:
它是一种 “生活的还原” ,所描写的是一种 “原生态的生活” 或者 “生活的原生态” 。作家在对生活的表现上不加剪裁和选择,是一种纯粹原生态的 “生活流” ,就像偶尔从生活中截取的生活的 “生理切片” 。叙述者主观情感的过滤,被称为 “情感的零度” 。 “新写实小说” 的叙述者被过滤掉了多余的激情,对于生活的表现是中性的、客观的,以所谓 “零度的叙述” 为显著特点。[44](P84-85)
旷新年等人对 “新写实” 写作的评述同时也是在构建中国化的 “零度写作” 理论知识。这种理论知识的构建是基于 “新写实小说” 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之上的,但正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 “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18](P1)。旷新年和洪子诚等人对于 “零度写作” 的理论概括都是从 “新写实” 写作经验 “开始” 的,但却大都 “发源” 于巴特的 “零度写作” 。也即 “在对‘新写实小说’的理论批评和阐释中,引人注目地借用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中的‘零度写作’和‘中性写作’等概念,同时注入了自己的内容”[44](P85)。
不过,从根本上说 “零度写作” 所倡导的 “原生态” “零度情感介入” 等其实是对巴特思想的一种 “形式” 上的理解甚至是误解。文学反映 “真实” 但绝不是生活原生态的 “真实” ,而永远是一种诗意的真实,零度写作对于文学真实性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对此,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表达了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
如果写作当真是中性的,如果语言不是一种沉重的、不可制服的行为,而是达到了一种纯等式状态,它在面对着人的空白存在时仅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内涵,于是文学就被征服了,人的问题就平淡地被发现和敞开了,作家就永远地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不幸,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不真实的了。[41](P49)
不难看出,巴特并不认同 “零度写作” 所表现出来的 “零度介入” 式表达,而是把它视为 “不真实” 的写作。在对这种策略式的理论话语的接受过程中,中国当代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与西方理论话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时间差” 。这有点类似于五四时期对于 “破旧立新” 尤其是 “破旧” 话语策略的误解,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未必真的能透过 “零度写作” 的表层结构看到其话语策略的一面,因为 “任何对于社会生活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纯粹’和‘中性’或者‘客观’的,它同样表达了一种主观选择和意识形态。它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真实’而已”[44](P91)。
除了新概念的译介以外,大学教材在结构主义文论的本土化旅行和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也功不可没。这其中初版于1992年且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就很有代表性。这部大学文论通用教材将结构主义理论浓缩为叙事学中的一个概念——结构,也即叙事内容的存在形态,并将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历时性向度)和深层结构(共时性向度)两种[45](P264-267)。只是出于大学教材的本土化和通俗化考虑,《文学理论教程》在阐释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候很少使用该理论的专业术语,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语用学、符号等。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于 “结构主义” 的引入并非整体式的理论搬迁,而是将其核心概念诸如 “写作” “零度写作” 等渗透进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之中,从而生成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学、符号学以及文化学等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虽然都 “发源于” 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话语,但它们总体上还是从本土的文学实践经验 “开始” 的。
四、结 语
在当代文论的知识场域中, “本质主义” 常常与 “反本质主义” 的概念相对应。国内学者陶东风从 “文化研究” 的理论视角出发,将大众批判语境中的文学理论视为一种 “本质主义” 的理论知识,也即 “审美主义” 的文学理论。尽管 “本质主义” 的理论概括遭到了以童庆炳为代表的 “文化诗学” 观念的抵制,但 “本质主义” 的文论观较好地概括了在大众批判语境中,持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理论观点。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前,以 “文化批判” 为主导的文学理论致力于对文学进行本质性的、本体性的研究与思考。1992年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一书,就将文学的属性定义为 “审美意识形态”[45](P56)。 这其中将文学的本质与 “审美” 勾连起来,也就是陶东风所说的 “审美主义” 立场。而以 “审美” 为中心的文学观念,也是自新时期以来文学针对之前的 “从属论” 和 “工具论” 而生成的当代中国第二次 “美学热” ,成为破除迷信、突破禁区、更新观念的 “显学” ,也由此形成了 “以审美功能论为核心的文学审美论观念”[46]。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也是1990年代之前主流的文学观念。在初版于1980年代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本教材的 “绪论” 中,编者将文学的本质概括为 “社会意识形态” “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语言的艺术” 等;而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将狭义的文学归纳为 “审美的含义”[47]。当然,本质主义文论的内容也很广泛,本文仅以 “形象思维” 为中心的文学主体性,以及以 “语言” 为中心的形式本体论在当代中国的知识旅行为例,探讨本质主义文论话语在当代学术界的生成与流变的过程,以期对当下新的理论话语诸如 “后人文主义” “物性诗学” 等有更为清晰地认识与理解。
此外,在当代文学理论界,本质主义文论如何过渡到反本质主义乃至后人文主义,这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在后文化研究时代重新思考 “本质主义” 的话题,也是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回应。比如文学研究空洞化的问题、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问题等。这些争议性问题的产生或多或少与文学的 “外部研究” 有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回到文学的内部或者回归 “本质主义” 文学研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