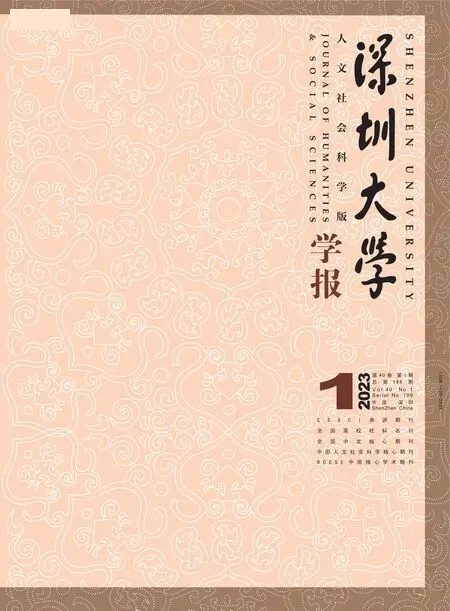“腐儒” 的话语流变与中国儒学转向
杨天保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①。渊源有自,儒家实属上古正统,其后来的发展却源不统流,竟然衍生出 “腐儒” 之属。此中变故,历代罕有学术思想史层面的专论。不过,缺失了检讨,它丝毫不影响 “腐儒” 的话语传播与再生产。例如,杜甫撰《宾至(一作有客)》诗,低吟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显以 “腐儒” 自怨自艾。今人读此唐诗,多以 “寒酸的书生” 疏解之[1]。索其最近较权威的注脚,乃清代段谔廷《群经字诂》卷二二: “寒酸者,形容书生迂腐之意,与措大之称,皆姗笑腐儒之语。” 可知, “腐儒” 是一份真实客观的社会存在,唐人撰诗、清人解经,早有所本,传统中国也基此认知对象建构了一套自成法度的知识谱系、话语策略与价值评判。
话语不仅是文学概念和修辞术,其能指与所指的转换、变动②皆涉及权力分配与运行,建构出霸权、文化政治和实现社会控制。但是,社会控制自始至终没有一成不变的话语及话语建构策略,因此,透过 “腐儒” 这个汉语概念的生成流变史,既可还原不同时段上儒者为谋求政治参与而积极开展的思想建构,又能在古今中国的 “大历史” 中揭开儒学与种种治权间的真实复杂关系,从一个崭新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国儒学史的整体认知。
一、 “非儒” :新话语生成的思想场域
话语都是一定历史时空规限下的产物,也是思想交锋进程中最便利的工具。所以,话语的生产总与特定的思想场域相关。
第一,周秦换代之际,百家并起;治国理政的策略学问接踵而至。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当年 “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他率领弟子周游天下,主动求售其学,忙乎大半生, “累累若丧家之狗” , “儒效” 艰涩,不为世用。究其根本,端在于他坚持以 “天下共主” 的西周旧制为正统,而对于正在崛起壮大的新兴王权的合法性——即治权的来源问题,存有难以言状的质疑、愤怒和顾虑。于是,他开创 “春秋笔法” ,打造《春秋》经典和政治道德法庭,一纸将诸多不安分的新王者斥为 “乱臣贼子” 。如此一来,汲汲于扩大治权的地方新贵们怎能对其保守主义立场和以伦理为中心的 “仁道” 学说深感兴致?相较之下,墨翟出身工匠,消歇对于权力是否合法的政治追问,直接去为权贵者提供免费服务;主张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革命,以 “能人政治” 确保各家的政治安全和有效行政。结果,墨学终成一代 “显学” 。总之,身份属性、问题意识、政治思维、价值取向和行政逻辑上的多重差异,既规定了儒、墨的时代命运,也激起多边的学术争锋。其中,《墨子·非儒》的问世,既是正式批判原儒的总集,也为 “腐儒” 的话语生成开拓出思想来源。
第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西汉官方知识生产者们对于 “亚圣” 孟子的正史叙事显然毫不避讳地援引先秦诸侯们 “迂远而阔于事情” 的口实。对此做法,今人却认为,孟轲的 “这种‘迂远’,正是孔子、孟子的坚守,其‘阔于事情’,是与违背仁义的事实人情保持距离,而不是不明事理。儒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强调孟学 “不能用” 的内因, “只是他们固守自己坚定的信念,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而不是真的‘迂远而阔于事情’”[2]。不过,此种 “以儒赞儒” 的辩解仍不免是自说自画。事实上,史学鼻祖坚持要以他人口实为客观史料,实足见传主当年留刻在治权谋求者心际处最突出的那一份 “共相” 了。
换言之,孟子治国理政的核心,一方面,希图以血缘宗法组织的自治主义去规范、限定新王权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基于日常伦理上的长幼尊卑等级,寻求一种 “人性善” 的哲学源头,从血亲关系中自然发展出权力关系,然后 “家国同构” ,推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逻辑程序,经由 “内圣” 而自然开出 “外王” ,最终赢得一种 “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的理想政治秩序(《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完全接掌孔子的 “合法性之问” ,且进一步基于亲疏长幼等社会关系,适时调整了先秦时代的正义性考量,为治权的合法性明确出新的社会源头——血缘宗法。结果,他这样做并未能扭转 “非儒” 们的学术批判,反而更加剧了诸侯权贵们的反感。相较于诸侯们努力破除血缘限定、建构 “普遍主义” 式的大共同体(如治权型新国家),孟子的人文治理设想简直就是一份彻头彻尾的 “特殊主义”[3]。所以, “迂远而阔于事情” 的贵族评判实为 “腐儒” 的话语生成提供了鲜活资源。
二、 “腐儒” 原型:荀子整顿学派的批判话语
面临 “非儒” 的时代压力,荀况承继孔孟法旨的同时,大力整顿儒学,以期于明辨学政关系,促成儒者健康的政治参与。其中,借助等级规范和边界意识的学理优势,他采用传统正名方式进行了一次大检讨——即将 “儒家者流” 的复杂构成和政治参与实践明晰为 “大儒” 、 “雅儒” 、 “俗儒” 、 “小儒” 、 “偷儒” 、 “贱儒” 、 “陋儒” 、 “散儒” 、 “瞀儒” 、 “腐儒” 、 “诵数之儒” 等不同层次[4],希图通过循名责实、清理异流,重新标榜出孔孟的主体性内核。
为澄清他者的 “非相” 之误,荀子在《非相篇》中进一步解释: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在他看来,面临权力与利益重新组合的纷繁之局,真正的儒者在政治参与进程中,一要检讨治权者是否 “效法先王” ,密切关注权力的来源和统系;二要看权力分配是否 “顺乎礼义” ,遵从社会秩序;三要考量是否 “亲比学者” ,让新的权力体系获得合法性认同和智性支持。换言之,一旦合法性出了问题,一旦行政不守正义,则 “君子必辩” ,通过拷问执政人格,彰显出儒者参政的不可替代性。其实,荀子时代的华夷之辨、齐鲁之争等严峻问题也亟待众儒开口抗争,为之一辨[5]。而且,他拟成 “三心论” ——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荀子·正名篇》),明授 “君子必辩” 的具体策略:(1)要超越 “有仁心必有仁政” 的理论假设,着实考究治权者 “效法先王” 的真实性,且以儒者独立的自由话语权,实现 “君子言道” 的政治愿景。(2)要超越小圈子利益,广泛听取不同政见和多元利益诉求,为建构新的治权体系积极配置合法性资源。(3)要完善道德学说,以人文规训新权,促成 “礼” “义” 等公共价值的不断生成。如此参政的结果,则 “元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 它与 “腐儒” 参政有天壤之别。因此,在荀况看来,孟子 “道既通” ,发展出新的心性道德之学,强调治权由 “法先王、顺礼义” 的仁者执政,且坚守 “君子必辩” 方法论,已经做到了知无不言;孟子非但不是他人口中的 “腐儒” ,相反,正好就是他要标榜的 “大儒” —— “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荀子·儒效篇》)。
可以说,荀子将孔孟的德治诉求引入学派自身的组织管理,既丰富了道德哲学中的 “君子论” ,也确实提升了学派组织的纯洁度。一方面,为了应对周秦社会转型期新的治政需求,有效扭转孔孟 “儒效不竞” 的命运,荀况及其后学们坚守 “道尊于势” 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君子人格,以上古 “括囊” 之属,状比混迹政治的 “腐儒” ,既修正了原儒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篇》)的处世哲学,又为其消极柔弱的底气注入新的活性元素。另一方面,他鼓励新一代儒者承继 “合法性之问” ,创新儒学方法论,坚守自身的话语权,非仁义就要说教,不合法则明辨之,这也为其建立健全一种籍 “鸣” 而 “名” 、由学及政的参政机制,以及重构新的学政关系,做好了理论和技术上的准备。但是,这样一份积极主动的政治热情和务心于内的治理智慧,既为后世儒家所误解,而对于正在谋求帝制的新王者来说,它更不合时宜。第一,为实现参政价值的最大化,荀子援引自家的德治学说,从内部组织上发起一场 “保洁战” ,封杀 “腐儒” 式参政不说,它又是对学派本身的一次 “分裂式” 大清理。结果,儒心惶惶,触犯多人。发展到后来,除了他自己的 “陪祀” 权惨遭剥夺,被人直接踢出孔庙之外。晚清学者谭嗣同撰著《仁学》,还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痛斥荀子就是一位中绝道统、将儒引入异端的元凶。第二,与之同时代的秦昭襄王极具政治野心,一度坦言: “儒无益于人之国” (《荀子·儒效篇》), 弃之若敝履。而且,此一评判及其立场后来成功衍成一份 “祖宗之法” ,迄至始皇称帝,被执行得更见彻底:秦初设博士70余人,多有叔孙通、淳于越等先秦儒生,但终因封禅一事合法与否,众议纷芸,激怒了皇权——先是骂他们 “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 (《史记·封禅书》),借此取消在朝儒家的议政权;接着,又认为侯生、卢生等在野之儒, “诽谤我,以重吾不德……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遂大行 “坑儒” 之政,儒者生存权亦横遭侵夺。
三、话语 “政治化” 与汉宋儒学转向 “守成”
据上述可知,从先秦轴心时代迈步即将来到的帝制时代, “合法性之问” 已成政治禁忌。妄议国政也好, “妖言” “诽谤” 也罢,祸从口出!防口甚于防川,刚刚浮现的中央皇权和帝国愿景,终与孔孟的宗法情结和荀学强守的自由话语权冲突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正面交锋。从东周末季战乱中走出的 “荀子们” ,既防治 “腐儒” 参政,以真君子自任,又倡导 “儒效” ,学政合一,希望为新生政权夯实合法性根基,将治国方向引入稳固持久的 “仁道” ,但结果是,政治参与继续失败不说,自身反被新 “霸道” 所摧残。
遭此浩劫,单就 “君子言道” “君子必辩” 等理念方法而论,无论是上层儒学还是下层儒学,日后其都未能长成主流。相反,一如司马光《保身说》所云: “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信,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6]。命悬一线之瞬,生存贵重,故避祸趋福、保全性命的圆滑智慧在政治参与实践中越发地疯长。作为汉唐儒学的总结大师,孔颖达《五经正义·周易》疏曰: “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 对于《易》理及阴阳学派最初主张 “藏器于身” 的韬光策略,他显然已极尽赞许。藉此可知,汉唐正统儒学及其知识构成实已放弃了千年之前荀氏的 “腐儒” 批判。而且,明哲保身的术略日趋破败着原儒学派的德治原则和纯洁性。一方面,直面终极关怀、维系公共利益和深究宇宙本体的纯洁真儒已凤毛麟角。另一方面, “腐儒” 参政大行其道:失却了 “勇者” 的胆识和担当,儒者谨言慎行、颐养时晦,整个儒林皆噤若寒蝉;原儒观念中的君子理想人格—— “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 (《论语·宪问篇》)只能畸形发展,造就一批生活 “无忧” 、生命 “无惑” 的儒学新贵以及 “难得糊涂” 的新犬儒。近人徐复观一度洞见其变,愤然道: “知识分子由先秦两汉的任气敢死,……逐渐变为软懦卑怯”[7]。受专制王权挤压,学术论域政治化,荀氏批判话语日遭失落,儒者新长成 “懦弱” 品性,这就为汉宋儒学的诸多调适与转向埋置了伏笔。既然如此,谁还会不识趣地常常忆起那段警惕自身腐败与防范学派堕落的批判史!
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被帝王直呼 “腐儒” 的当属西汉初年的随何。淮南一役,随何以 “谒者” 说服淮南王英布投降,如簧之舌 “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 ,居功甚伟。但刘邦 “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 (《史记·黥布世家》)。 “谒者” 专职禀报,强于口才辩术和话语策略。这一历史细节透露出刘邦故意折杀 “谒者” 之功,实乃为膨胀君权清扫障碍的政治信号。所以,秦汉两朝,姓虽异,治术亦异(法家/黄老儒术),但整顿原儒实属同一历史时段内的帝王要务;削减 “君子必辩” 话语权、消停 “合法性之问” 等阴谋策略,两家不约而同; “防口” 之虞,前后相承,亦如出一辙。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新帝王 “未可以儒生说” 的狂妄褊急,天下尽知。于是,儒家要实现政治参与,确需谨慎,切不可再在 “君子言道” 、 “君子必辩” 等理念上与当下的专制君权发生冲突。所以,高阳儒生郦食其先是央请同乡以 “狂生” 之名举荐之,亲见刘邦时,又聪明地隐却原儒礼仪, “长揖” 而 “不拜” 。结果,虽仍遭 “竖儒” 的脱口之骂,但郦氏毕竟还是通过主动调整身份,免遭 “腐儒” 之弃;且后来他 “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克陈留,取荥阳,据敖仓,劝降齐王等,仍旧以辩才赢得诸多 “儒效” 。
又如,秦朝儒学博士叔孙通辗转流落新王朝,反省 “秦鉴” ,亦渐出新机——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史记·叔孙通传》)显然,叔孙氏新的政治表态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尽释帝王心患:原儒耽于拷问执政人格,以至于唐突君王 “进取” 之雄心,故学政关系趋紧,咎由自取地陷入 “腐儒” 宿命;帝制新时代到来后, “合法性之问” 自属多余,汉儒理当修复原儒缺失,转换问题意识,通过强调政治 “守成” ,以 “共起朝仪” 的新政治参与方式重建学政合作关系。
虽说这只是汉初儒者避祸趋福式的自救与斡旋,但时日一久,它终长成一种路径依赖。于是,政治 “守成” 的呼声围绕着 “腐儒” 的话语再生产逐渐传遍儒林。众论当中,一是唐代颜师古总结汉唐经学最具代表性。他说: “腐者,烂败,言无所堪任。” (《汉书注·英布传》)二是司马贞也从传统史学角度作出典型解释,说: “谓之腐儒者,言如腐败之物,不可任用。” (《史记索隐》)所以,无论是正统注疏之学,还是官方史学, “儒效” 的敦勉与劝诫再度甚嚣尘上,与帝国真诚合作实乃 “腐儒” 与否的制度化检测标准。
进入宋代,新旧交替,兴革省易,变动殊甚。汉唐儒学至此作一停顿后[8],中华开始 “转向内在”[9]。藉此窗口期,又有人出来揭批汉儒之失。例如,在北宋王安石 “复兴儒学” 视域中,叔孙通确然是大罪人: “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10](P560)。 “黄金既遍赐,短衣亦已续。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初服? ”[10](P335)同样,贾谊更是认为不堪: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10](P561)。收获黄金、爵位和圣人名誉的同时,原儒道义、合法性主题与言论权均告凋零。相反,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10](P558)。王安石坚持着要与 “迂阔” 的孟子同道,且在后来发起一场 “孟子升格运动”[11],打造出《三经新义》和 “新经学” ,力图以新的知识生产越过汉唐儒学,链接孔孟,将汉宋之间的 “儒效” 范式颠倒过来,恢复 “合法性之问” 和修缮原儒的 “进取” 之方。
不过,汉宋以来的政治结构和思想世界显已大变。例如,欧阳修以大道自任,集儒士、史家和文学于一身,但新编《唐书》时,他别出心裁地挑出一个 “为人木强、无他能” 的国子博士朱朴,正式写进卷一八三《朱朴列传》,以儆效尤。此一精准构思实足见多数宋儒 “守成” 的真本色。所以,此情此景下,王安石身为执政大臣,昌明 “进取” 之义,也依旧无法扭转儒学的 “守成史” 。相反,他死后,其学被禁为伪学,其人被骂为国教罪人,而南宋诸儒既建构出 “王安石变法” 与北宋政权颠覆间的因果关系,又将 “反王学” 运动政治化,成功打造出一份新 “理学” ,再度强化 “守成” 之旨,继续主宰着明清帝制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章回小说《三国演义》载:名士祢衡被江夏太守黄祖所杀,身首异处,曹操得讯却笑骂云: “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明代作家巧借政治家孟德之口,一语道破帝制晚期儒家坚守 “合法性之问” 、维系话语权的终极宿命。
四、官方建构与话语霸权:明清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向廉政哲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摘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司马父子这段对于原儒的总讨论,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一方面,它集结了齐宣王 “不能用” 、梁惠王 “不果所言” 、秦襄王 “无益于人之国” 、秦始皇 “难施用” 、汉高祖 “不好儒” 等经典批判,为秦汉以后的治权者有效规避 “劳而少功” 的儒氏治策、稳固帝国治理体系出台了一个正统性的法戒。新的帝国安全优先原则取代轴心时代的正义性考量,特定时空中的帝国需求日渐遮蔽了诸子对普世性公共价值的政治追问。另一方面,它明揭儒者在确保政治 “守成” 上的学术优势—— “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 ,为此后的儒者参政、 “制度化” 儒学指明了方向。随着 “独尊儒术” 等帝王经略的出台,儒学功能及其强调德治的话语系统从制度层面上一步步被改写,先秦儒学从一种道德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结果,在中华帝制体系里,儒者坚守德治原则,高度整合精神象征系统、社会象征系统和政治象征系统,建成超稳定的伦理政治一体化政治文化[12],系统性支撑起东方帝制的长期运转,最终营造出中国本土 “儒表法里” 新格局和 “外儒内法” 的治安长策。此方面,西方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创建 “儒教中国” 概念,确实以 “他者” 的眼光,洞见了 “守成” 儒学的 “儒效” 新范式——以德治确保行政安全。
不过,即便发展到明清时期,新哲学依旧存在建构上的缺陷:第一,早期的道德人文关怀源出先秦宗法结构, “家天下” 情结及其廉善取向尚不能成功发育成面向普遍大众的公共关怀。相反,受其宗族社会及社会资本限定,修身持己等话语价值的超越性不够强大,德性主体难于形塑出崭新的政治主体。第二,士人由己达政的制度供给与路径创新长期性不足。其中,无论是世袭九品中正,还是征辟科举取士,精英的社会流动性及政治参与始终不及于官员总数的万分之一,多数儒者终其一生都不能跨出血亲组织空间及其纠纷之域。相反,德治实践多半陷于日常生活,家政精彩连篇,但 “清廉” 治政只是士人愿景。第三,儒学 “制度化” 后,治权 “合法性之问” 止步于帝王德性,不敢再度深究,故廉政哲学的本体论层面一直空泛,既无法衔接 “大同” “小康” “天府” 等先秦话语及其思想遗产,又未能为 “清廉社会” 或 “透明政府” 洞开新径。第四,无法超越农业时代的认知水平,让农本理念日趋陷入经济保守主义,既缺乏生产力意识和劳动正义观,又反对市场和技术新发明,结果道器分离,难成一体。近年,学者提出 “儒家资本主义” 新概念,既以之 “比拟” 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新教伦理,又自以为开出现代儒学新径,但是,此间的 “资本” 乱儒、惑儒之嫌,明矣!
同时,受 “制度化” 规范,儒学话语权渐为帝王禁锢后,原儒对执政人格的君子拷问突然反转为对儒者参政人格的道德追问;原本发端于早期君王的 “儒效” 质疑亦反而长成一份强势的倒逼机制,催出 “德生廉” 等参政人格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新逻辑关系——为确保儒者参政和实现政治 “守成” ,提前预置了新的 “制度化之问” 。于是, “莫作青衫老腐儒” 之类的话语警告[13],时刻修正和改塑着后世儒者的政治选择。一旦未能通经致用,开出达于时政的 “外王” 法度,那么,以 “腐儒忧国” 自嘲自解或自警自励,自然是儒者最常见的自我 “革命” 和政治书写。其中,杜甫辗转漂泊湖北,56岁壮心不已,写下《江汉》诗曰: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济南杜仁杰才学宏博,终生不仕,好友元好问两次向耶律楚材举荐其人,皆 “表谢不起” ,但其《金娥神曲》又偷偷唱道: “世俗,看取,花样巧番机杼。乾坤腐儒,天地逆旅,自叹我难合时务!”[14]学不济时的政治困顿和被边缘化的愧恼皆跃然纸上。
随着帝制空间的外向拓展,在新话语的鞭策下,众多儒者进驻且 “立功” 于帝制,终于 “合力” 地呈现出中国儒学自身的无限生命力——南传西播,东渐出海,一代代迁入异地的儒学因子, “学而时习之” ,结果既未做成抱残守缺的老朽儒学,亦没有跌落成让历代儒宗们颜面尽失的 “在地化” 末流。相反,它们立足本土,适时变通,相继谱写了一部优美的 “儒学地域化” 历史[15]。设若 “衰退甘为一腐儒”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遣兴》),缺失了 “腐儒” 的话语警醒,自然就白白浪费鲜活的本土元素和政治新空间。汉唐儒学中衰之后,宋代 “学统四起” 的繁盛美景,关(张载)、洛(二程)、闽(朱熹)、朔(司马光)等重组的 “宋学” 格局,明清儒学的出路,甚至于今人赞誉不休的 “东亚儒学”[16]……恐怕都只能是一场春光梦影。换言之,虽然 “参政之儒” 的主体性已模糊难辨,淡化了原儒的身份坚守,其哲学探讨亦多残缺,但那一场深受君王左右的 “制度化” 儒学及其话语 “革命” ,也确有其治理实效。自汉以降,围绕 “腐儒” 的话语建构持续且深入,迄至明清,理论上的自身缺陷与现实中的 “儒效” 皆相伴而行。
五、近现代 “腐儒” 的话语实相及政治批判
近代国门洞开,治权危机迭起;西学东渐,思想丕变。 “迷古” “信古” “返古” 或 “复古” 之流竞相登台。最著者钻进 “故纸堆” 后,修身养性,蜕变成 “蠹虫” 。基此, “儒家误国” 之论,举境沸腾;清理 “腐儒” ,高潮再起。甚至于矛头所向直指夫子的渊源统绪—— “打倒孔家店!” 同时,西人执得世界牛耳,成为全球中心后也不甘寂寞,跨洲越洋之骂一道随西学漂过来,将 “儒教” 的思想国度讥喻为一间收破烂的 “博物馆” ![17]实质上,告别帝制进程中的儒学话语建设与思想争锋,一方面,已彰显出在科技昌明之世人文与技术、农耕与工业二者间的此消彼长;另一方面,它又越出本土场域,汇入世界体系,呈现出东西制度文明接触交流后即将开始的一场新型较量与对话。此间的损益得失此不赘述。不过,近代语境中的 “腐儒” 之属,人文 “守成” ,其保守主义根基犹在,但 “误国” 之骂实属言过其实。中国政治与全球政治的重构与发展已让儒学及其儒家一同被建构成新的靶向,以供东西民主政治与 “技术共同体” 之无情批判。
今天,一方面,有人指出,现代 “腐儒” “可以指一个阶层,一个流派,一个集团,也可以指一种体制,一种主义,一种思潮。但最确切地说,‘腐儒’就是当今企图死灰复燃几千年以来曾经僵化腐朽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御用学说的某些利益阶层……,这种御用学说孕育了一大批腐败官员,孕育了一大批腐朽文人。这实际上就是动辄讲中庸、动辄讲和谐的现代儒学”[18]。此一新表达直指现代利益集团及其破坏性,但 “腐儒” 意蕴实迥异古意。据上文可知,儒学虽然非是一种自然而然且理论自洽的廉政哲学,但千载以来, “守成之儒” 确具廉政贡献,其思想创新和机制建设一直未曾中断。只是发展到时下,受全球化资本、市场及其自由主义原则的新激励,又有 “新儒者” 借助民主大开之机遇,常常越出边界,热衷于演绎、彰显和膨胀其主体性;甚至于在 “俘获” 权力后,以权寻租也在所不惜。所以,既然民主时代的透明参政、真实议政及为民主政等种种施为,犹不足以根除现代型政治腐败之儒的诞生,风雨摇摆中的新儒学又何足论焉!另一方面,为满足大众的 “文化饥饿” 或 “历史饥饿”[19],一夜之间,国境内外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批贱卖儒学的速成车间和火热市场;好端端的一部《周易》率被演绎成阴阳轮回、风水算命的经典大法;辟谷、房中、相面等奇门邪术也在民间日呈回春之势;借助纪念孔子、朱熹等先儒的名义,去鼓吹 “宗族优越论” 者,更大行其道……,表面上看,这场浅薄无聊的 “世俗化” 秀场、这些率性而为的 “大众化” 解读与消费的确已经越过西汉 “司马总论” 的制度化论域,让 “儒效” 大显于基层,也让 “劳而少功” 的旧意象走到了尽头。但是,引导民众如此迷信地捡起死人骨头,并沾沾自喜地啃个没完,这还不就是活生生的 “食腐族” !沉迷功利,借助于现代科技,上下其手,致用于败坏国本、消解灵魂和颠倒信仰,让现代儒学最终病变成一种 “腐蚀之学” ,又何谈于国于民的现代治效!
其实,进入21世纪的时空维度后,在工业文明新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上层儒学还是下层儒学,市场化也好,大众化也罢,它都是儒学告别 “制度化” 传统之后的路径选择,本无可厚非。但是,作别既往的仓促之间,继续着以 “儒效” 为本位,这彻底让现代儒学沦落为一份庸俗的 “致用” 工具,而将其道德学问、廉政哲学等消解得体无完肤。那么,儒学的现代发展之厄恐怕比其引发的政治腐败更令人深忧。
第一,真正的现代儒学不再只是儒士或王权的 “家学” ,人文 “守成” 之上更需复兴原儒 “进取” 之旨。特别是,其理当正视现代公民的合法性平等权利,基于 “主权在民” “权为民赋” “权为民用” 等现代公权观念,彻底超越自然血亲情结,通过 “合法性之问” 的知识再生产, “言道”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置合法性资源,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巩固社会主义的正义论,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合法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如此,它才能消除汉宋儒学不能实现 “源头治理” 的结构性障碍,成功规避自身的内卷化风险。
第二,真实的 “大众化” 儒学要革尽古今儒学新贵的等级偏好,开辟出群众路线、降落民间、亲近草根、 “君子必辩” 、为民代言。特别是,我们理当作别服务于权贵的、单向性的 “儒效” 范式,以及 “同情怜悯式” 的古典民生关怀,不断增进公共服务理念和宇宙关怀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产品创新,真正改写民众以原始神本文化为底色的政治文化传统构成,营造出中国特色的民主范式和民主热忱,最终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刷新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文明,作出最合理的文化解释和价值支撑![20]
注:
①本文所引古代文献中未作标注者,其版本皆出自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② 索绪尔(Ferdnard de Saussure,1857~1913)认为, “能指” 是内在的 “音响形象” , “所指” 是意义,即 “音响形象” 所表达的概念,二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