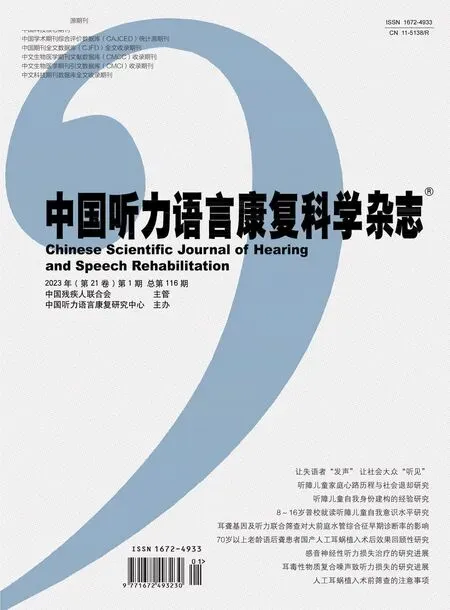让失语者“发声” 让社会大众“听见”
杨立雄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3.6亿人患有致残性听力损失,其中近一成是儿童[1]。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听力障碍总人数约2780万,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为1‰~3‰,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超过30万[2]。受传统文化影响,许多听障儿童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或被视为智力低下、能力较差,对听障儿童心理健康与自我效能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其自我认同感[3],同时,也对听障儿童家庭产生连带污名效应(affiliate stigma)[4]。在社会交往中,听障儿童父母常会遭受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5],部分家长产生回避社交、拒绝外界支持、隐匿残障等行为[6],儿童的失聪最终导致父母的“失语”,并由此成为社会支持政策的“盲点”。
基于特殊的交流方式,听障群体发展出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身份认同[7]。然而,听障群体的身份认同不仅表现为“聋人认同”,也受“健全人中心主义”影响,不同制度与文化通过权力运作对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进行建构,呈现复杂化、多主体参与的认同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交往环境、教育环境、家庭文化环境对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8]。听障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普遍低于普通儿童[9],尤其是在融合教育环境中,听障儿童不仅面临语言康复和学习困难,还面临来自同伴的社会排斥[10],社会参与水平较低[11],以上困境对听障儿童建构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产生了负面影响。
听障儿童往往被外界赋予“聋人”的污名化称呼,成为标签化的弱势群体,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排斥中,渐渐扭曲自我意识,不愿面对陌生人,制约了儿童在学龄期实现社会融合的脚步。不仅如此,来自外界的污名也产生礼节性成见(courtesy stigma)[12]。听障儿童父母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回避社交、拒绝外界支持、残障隐匿等行为,对家庭社会化功能、成员关系产生负面影响[13]。在外界对残疾人形象进行扭曲、变形后,许多残疾人家庭便对残障身份产生排斥心理,产生隐匿残障子女的社会心态,逐渐淡出社会参与和家庭活动,以社会隔离和社会退却行为降低融入社会的意愿[14]。
目前,学术界对残障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然而少有研究关注不同残障群体的特异性需求。少数研究将关注点聚焦于孤独症儿童、精神障碍群体,从社会支持、家庭支持与社区支持等视角梳理现有政策,以期改善上述弱势群体的社会处境。然而不同于其他残障群体,听障儿童具有身体健全与生理残损的双重特点,易被社会所忽视。因此,了解听障群体的社会诉求,让其“发声”并让社会“听见”,对重构家庭抗逆力、完善社会支持政策、促进听障儿童及家庭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特约长期从事残疾人事业理论研究的学者对听障儿童及其家庭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分析听障儿童家庭面临的压力和负担。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在北京、山东、福建、陕西、湖南等地对听障儿童及其家长与监护人进行调查,最终形成本期听障残疾人社会支持策略研究成果。
《听障儿童心路历程与社会退却研究》对12位听障儿童家长进行深入访谈,总结了听障儿童家庭的心路历程:由确诊后的震惊、难以接受到心存侥幸期待结果有转机,再到家人齐心协力为孩子康复努力的发展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在儿童康复期间,家庭内部分工明确,父亲支撑高额康复费用,承担经济压力;母亲作为听障儿童的主要照护者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家庭,承担较大的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使听障儿童受到污名、家庭受到连带污名的影响,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感受到社会排斥和旁人异样的眼光,逐渐向内收缩。同时,听力障碍与其他类型的残障不同,可隐匿的特点使家庭隐匿在都市社会成为可能,故听障儿童及其家庭为了避免遭到歧视和排斥,有意无意采取策略隐匿个体的污名特征,进一步减少社会活动、中断社会参与、淡出公众视野,最终在社会隐匿失声。通过访谈发现,听障儿童的“失聪”导致其家庭的“失语”。该文对听障儿童父母的心路历程、家庭社会关系重构及听障儿童家庭社会退却的生成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了听障儿童及其家庭消失在社会大众视野、在社会“失声”的原因,并提出建构听障儿童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议。
《听障儿童自我身份建构的经验研究》以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情况为研究对象,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听障学生及家长进行访谈,探讨身处两种环境中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建构路径,探索听障儿童的身份认同特征。该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框架,呈现本土情境下听障儿童身份认同的建构路径,并提出促进听障儿童形成积极身份认同的建议。研究发现,父母培养方式及学校教育方式、朋辈群体间的交往方式成为建构听障儿童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环境下听障儿童由于接受学校教育和家长灌输观念的差异,在辅助器具和沟通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与他人交往的态度存在差异,导致两种环境下听障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普通学校受“健全人中心主义”影响,极力推崇融合教育,致听障儿童“听人化”身份认同的建构;特教学校中听障儿童熟悉听障群体的特征及生活方式,更易对团体产生归属感,也更易对自身的身份产生认同感。不同教育情境下听障儿童身份认同作为一种自我及群体认知,对听障儿童在情感和价值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最终构建我国听障儿童身份认同双重路径。
《8~16岁普校就读听障儿童自我意识水平研究》对广东、陕西、湖南、吉林、山东5个省份普通学校就读的听障儿童自我意识水平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采用Piers和Harris的自我意识量表[15],涵盖儿童期和少年期自我意识评价的主要方面,是自我概念的一种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测量方法。在对数据进行清理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听障学生自我意识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并将分析结果与中国儿童常模进行比较,发现听障学生在行为、焦虑、合群及幸福与满足这4个子维度与总分显著低于中国儿童常模;同时,8~10岁、11~13岁及14~16岁3个年龄组在行为、焦虑及合群子维度及总分上的分值远显著低于中国儿童常模,自我意识水平较低。以往研究从局部指出了普通学校就读听障儿童的处境和面临的困境,该研究在复杂状况下对听障儿童心理状态,尤其是自我意识状况进一步探究。研究表明,年龄与地域两个指标对该群体的自我意识水平有显著影响。年龄的显著相关除了与不同年龄段自我意识发展的自然规律有直接关系外,也与我国听障儿童康复救助社会政策发展、教育提升计划、残障促进社会服务发展等政策促进息息相关,以儿童和家庭为中心的支持性发展政策和服务促进对医学康复社会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社会政策范围和实施的地区差异构成了不同省份听障儿童自我意识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对听障儿童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疗技术方面,基于社会政策和个体社会身份认同的深入研究不足,上述研究丰富了对听障儿童的理论研究,希望能引起实践部门对听障儿童群体的关注,进一步完善社会支持政策,为听障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包括经济、教育和心理等方面的系统性社会支持,促进听障儿童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