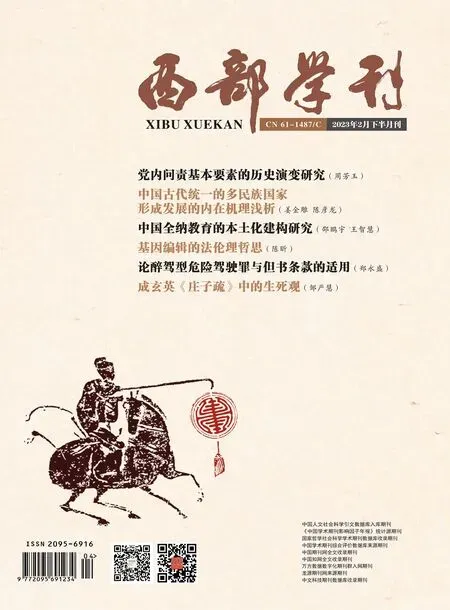《资本论》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探究
黄鑫鹏
实践—认识研究方法一般多用在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上。但在政治经济学上鲜有人运用和研究,如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上坚持实践认识论的观点[1]。而在《资本论》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也关注对社会实践的研究。比如,仰海峰教授提出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模型”观点[2]。但是,其研究依然基于哲学基础之上。而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又研究《资本论》的情况上,学者较多的是关注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科学抽象方法虽然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但是,马克思也强掉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运用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人的现实经济活动、人类经济实践史、经济学范畴概念的产生,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真理的力量,同时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提供了指向、现实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的内涵
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西方其他各种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都注重理性推理、抽象把握、数理公式图表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思维逻辑上把握经济的动向、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倡导类似“抽象”研究方法的运用,比如,商品和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从商品流通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成,等等。但是,马克思更注重“抽象”和“具体”联系的研究方法,这因为只有“抽象”和“具体”联系起来,才能使得研究更靠近客观规律,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实践—认识研究方法正是“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实践—认识研究方法主张运用矛盾对立统一、质量变的转化、否定之否定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经济实践问题。比如研究从最简单的商品价值交换矛盾出发,看到雇佣生产关系的形成。其次,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实践—认识研究方法不仅主张研究逻辑与实践历史的统一,更主张一切研究须从人类最根本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来研究整个经济问题。在这里,物质生产实践是研究逻辑发展生成的基础,同样也是一切经济范畴发展生成的基础。像“资本家”——这一人格化资本的经济范畴产生的土壤必然是现实的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中,而不可能是别处。最后,从两者统一方面来看,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必然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融合,即辩证的唯物史观或是历史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就表现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零散、碎片的经济范畴系统辩证地统一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主体之中。并以此为基板,历史辩证地探讨实现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实践可能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政治经济学认知过程的完整性。所谓研究认识过程的完整性是指在研究某个实物或者问题时注重认识过程的完整性,即“实践—感性认识—实践—理性认识—实践”的完整过程。它反对在研究中割裂整个过程而片面只强调某一个认识过程。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研究方法一大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完整联系整个实践—认识过程。人在研究中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历史、全面的过程,同时也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中统一实现的过程。而其中,人在研究中通过感性认识收集研究材料、在理性思维中把这些“片面”的研究材料,进行“概念、判断和推理”,从而“去粗去精、去伪纯真、由此及里、由表及里”,然后经实践检验成为真理[3]282-291这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提倡的。
调查,它是完整认识过程中最重的方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一手现实感性材料,从而打通研究者的认识和实际的连接。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种种限制,也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能通过直接实践获得第一手感性资料,仍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所用感性材料不完全是马克思调查的结果,也有前人创造的材料。这些素材乃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来源。
当然,从完整研究认识过程来看,调查或间接获取材料,并以此形成感性认识,乃是第一步骤。最重要还在于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论,并且这种上升了的理论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不在于它作为抽象的理论就能够“解释世界”,更在于它能够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成为“改造世界”的真理。
第三,从研究阶级立场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要求经济研究者的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创造的主体,无论是经济活动或其他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再者,从真理的标准来看,经济理论是否有效,不是看经济学家怎么说,而是看其是否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西方政治经济学虽然也在社会效益、民众福祉等方面做过不少的有益研究,在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上取得一些效果。但是,其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使其无法很好地研究群众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动创造作用的。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始终注重人民群众在研究中的地位。因此,这使马克思在研究方法、理论、方向上不仅具有科学性,同时更具有道义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
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内涵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初步建立对该方法的“感性认识”。但是,我们对于实践—认识研究方法的“理性认识”,还得要回到具体的案例中来。《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不仅在研究内容上给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珍贵的研究宝藏,同时它在研究方法上也给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上的重要参考。《资本论》的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体现在它对人的现实经济活动、人类经济实践史、经济学范畴概念的研究和考察。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把《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当中的有关精神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
首先,关于人的现实经济活动的研究。关于人及其人的活动的研究,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伊始就以“人”及其活动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在马克思担任德国《莱茵报》编辑时期,由于德国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剧,导致了所谓“盗窃林木”等行为成为了所谓“非法”的行为。基于此,当时普鲁士当局召开了有关林木盗窃发的辩论。马克思在辩论中越来认识到自己在辩论中的难——“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于是,这也就成了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原因。随后的在摩塞尔的调查更是激起了马克思对于“物质利益难题”的探讨[4]。由此,“物质利益难题”成为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开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关于“物质利益难题”必然涉及人的研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把人看作是理性而又利己的“经济人”。虽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复杂性,加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使得其不能从现实和实际的角度来阐释人的“物质利益”究竟怎么产生的。对于现实人的“物质利益难题”的研究既不能依靠单纯的哲学,也不能脱离客观的经济实际。为此马克思在研究此类问题时,虽然是从人出发,从现象到抽象研究。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是用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从最基本的人的现实经济活动出发,从最简单的商品贸易实践活动出发来对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进行剖析,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物质利益难题。”
在《资本论》的研究中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首先从最简单人的经济实践活动——商品交易活动开始,研究雇佣关系的形成乃至于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的产生,等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研究是基于道德、理性、个人情操等。像亚当·斯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认为道德的力量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人的自私行为,而这些制定出来的准则可以以上帝的指令相待[5]56-58;但是,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批判过类似的观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观。”人的经济实践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手材料,而这种材料不可能是宗教、也不可能是某个道德或者精神[6]1。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6]222。其中“生产”一词足以表明了人的社会物质生产、人的劳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来源。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为经济实践主体——资本家和劳动力出卖者(雇佣工人),以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其活动条件,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实践活动——商品贸易以及剩余价值生产实践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从而从科学的视角来揭示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的内幕,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引用了各种材料与数据,乃至像西方政治经济学那样也有公式、数量,等等。但是,这些材料除反映了当时人的客观的经济实践活动,更反映了马克思注重把自己所倡导的实践方法运用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中。
其次,对人类经济实践史的研究。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固然在政治经济学上注重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的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在早期批判过封建制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不同。但是,他们却吹捧资本主义社会永世长存,没有内部矛盾。虽然沿着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路径,产生了一个主张以研究经济演化规律、用归纳/历史方法研究的学派——德国历史学派[5]173-187。但是,这个学派只是把新方法——演化的方法作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补充,其依然没有讲明人类实践历史的发展。不论是在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演化,还是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都十分地注重以人的实践,即人的劳动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并看作是它们的发展根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个案例就是这种方法的应用:在《分工和工厂手工业》中从实践的视角探讨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即工场手工业如何一步步地形成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而其中在论社会内部分工形成时,马克思从“家庭的内部”分工实践出发:刚开始还是自然分工为主,但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一个氏族征服另一个氏族的战争的发生,“这种分工材料也就扩大了。”[7]407-408由于这方面的扩大,使得不同的共同体有了相互的来往,相互交换。这种交换就是人的一种经济社会实践,从而这种实践推动了商品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和更大分工的产生。在这里马克思完美地以实践观分析了家庭内部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进化历程,从而为人们认识社会分工规律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用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首先,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运用了资本主义“发家”的史料来无情地揭露这个现象。而这些史料虽然形式是主观的,但是它的来源却是客观的。这些史料就是时间的记录者,它把资产阶级一个个“血腥”的历史实践记录在案:15世纪土地掠夺、设立惨无人道的法案、对殖民地的侵略。其次,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商品交换”实践历程的描述,揭示了劳动力所有者如何在资产阶级设立好的“公平”交易的商贸活动中,一步一步陷入被剥削的境地,成为资本的被剥削者。这一切都把资本主义暴露得体无完肤。由此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并非像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美妙绝伦,同时也驳斥了某些空想家幻想通过改良社会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空想。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经济实践史的揭示,不仅让人们从资产阶级过去的实践中彻底认识其“真面目”,更是从实践的角度为广大无产阶级指明未来的方向。
最后,有关经济学范畴概念的产生。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7]8。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对于政治经济学无论是范畴还是其他各方面的内容也好,都不可能研究那么仔细的。由于现实的经济环境是复杂的。由此,马克思认为“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替代。”而在这里“抽象力”即为认识,从现实具体到观念的抽象必然需要用到实践—认识的研究方法,而马克思这种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7]8虽然,这些形式都是抽象的,但其来源依然是现实人的经济实践活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注重从现实经济活动实践中来对某个经济范畴进行探究,比如亚当·斯密在价值理论探究方面,他用了鹿和海狸的交换作为经济实践案例说明“劳动”是如何创造价值的。但是他这个例子却只是用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一旦进入“发达经济”就无法很好地解释“劳动”在“发达经济”条件下如何创造价值了,于是他不得不借助于“资本”来说明价值的来源。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发现了价值的产生,但是他们却没有继续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众不同,他通过对人类经济的实践研究发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真面目: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雇佣工人在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条件下“劳动”创造了价值!
这种方法的运用例子还体现在对“资本”这一范畴概念产生的探讨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是建立在发家致富上的,因此“资本”范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了“赚钱”的代名词。同样,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延续这一思路,于是“资本”概念慢慢地越来越成为一种“物”,成为了一种抽象的“生产要素”。但是,究其原因,会发现该范畴产生的思路基本上和个人的“功利主义”有关。而个人功利主义的产生脱离不了现实的个人的经济实践活动。前面已经讲现实经济实践活动必然与人的现实条件即社会关系有关。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缺点恰好就是在这里:它是几乎半脱离现实经济实践活动及其现实条件空谈“资本”范畴概念的。马克思批判到:“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的,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6]218。这些关系及其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是经济实践活动及其实践活动的历史,而这正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规律所必须的。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探究“资本”范畴的产生及内涵时,回到了现实的人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发现:“资本”并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述的那样,仅仅只是一种“财富”“赚钱”的代名词。它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归根到底是“集体的产物”,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也就是共同实践下“才能运动起来”[6]415。
三、透过《资本论》看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向
实践—认识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资本论》相比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更具有科学的力量,它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实践活动。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贴近中国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只有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经得起中国长期经济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
(一)现实指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了大量的现实素材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对素材的选择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经济实践活动的重视。正因如此,保证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这给予的启示就是:需要注重的是经济素材的真实性,而它的真实性就是现实或者当下人民群众正在经历的经济活动。例如,农村人的脱贫与发展、毕业生的就业、企业在疫情后的复工等等。虽然,这些经济活动有的是宏观的,有的是微观的。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素材。没有把握这些现实素材,就不可能通过正确的实践产生正确的理论。早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基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现实科学地对中国当时的各个阶层进行了系统分析[3]3-9。同时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基于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实提出了“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台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减息”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来看起到了对农村根据地的经济的保障作用[3]27。
(二)实践指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十分注重对经济实践的研究,尤其是第二卷中对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及周转周期的研究。正是通过对资本背后现实经济实践的研究与认识,不仅正确地区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范畴概念,还能精确地展示整个资本的周转。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主市场经济也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实践成为了当代主要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比如,国企改革的实践,必然带来国企发展的新机遇,但同时也会带来各种挑战,像职工下岗等;再有,调控房价,使房价降低,给购房者带来福音,同时,也必然会损及相关从业者的利益。在实践中有机遇和挑战并不是坏事,邓小平曾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问题》中不仅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同时还强调了“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发展问题”[8]。基于此,实践当中的机遇与挑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好的研究对象与素材。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研究中还可以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实践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们在研究视角和部分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差异。但从人类经济实践史的发展视角来看,解决当前经济实践问题,依然需要借鉴和参考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三)检验真理标准指向
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提出了另一指向就是: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加以证明[6]134。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仅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学说,还在于尔后的科学实践的证实。”[3]292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本质与自然科学有所差别,但是和自然科学一样,依然需要将理论运用于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一般而言,中国的经济实践活动,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形成等都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真理性的很好实践。同时,除了上述宏观的实践检验,还有微观层面的,即这理论的运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是否使得群众有很好的获得感、是否能带动某个产业的发展,同时是否能使每个企业都能在良好的经济环境运行中获得一定的利润、是否能在经济收入分配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协调好各种利益,使得在不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等等。这些都是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科学性的实践检验标准。
综上所述,实践—认识研究方法的三个指向:现实指向、实践指向、检验真理指向对于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及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十分重要。只有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