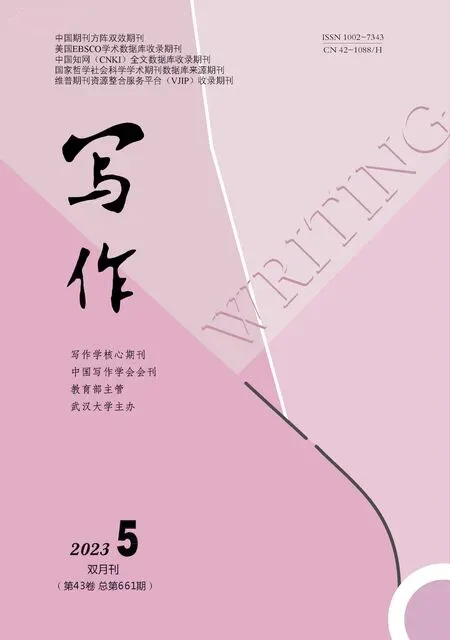写作,是为了在大地上翩翩起舞
——阿人初访谈录
白哈提古丽·尼扎克 阿人初
阿人初的诗集《顶碗舞》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出版发行后,引起文学界不俗反响。笔者对诗人进行了一次访谈,除了要进入阿人初的诗歌世界,挖掘出阿人初的创作理念之外,还希望通过他抛砖引玉,认识当前新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情况。
一、在创作上,决不能“原地踏步”“故步自封”
白哈提古丽·尼扎克(以下简称“白”):你好,非常感谢接受这次访谈,同时祝贺你最新诗集《顶碗舞》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以前有朋友给我推荐过你的作品,你是一位少数民族诗人,用汉语创作,作品内容丰富、深刻,很有意思,值得一看。后来,我看了你不少原创诗歌和翻译作品。在为《顶碗舞》写书评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深入你的创作世界。正如沈苇老师所说,你“从新疆和田偏远乡村里怯生生的小男孩到‘内高班’的成名诗人,从连一句汉语都说不流畅到娴熟掌握汉语并出版诗集”①阿人初:《顶碗舞》,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实现了人生的重要飞跃,如今,你成为“甚至比新疆许多同龄的90 后汉族青年诗人、作家都要出色”②阿人初:《顶碗舞》,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的当代青年诗人。你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历程?童年经历或者说成长环境,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阿人初(以下简称“阿”):很高兴跟您交流。如果真要追溯一个源头的话,应该要从上小学的时候说起。我出生于新疆皮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的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上,那是神话与传说的故乡,很多神话传说都是关于无边无际的沙漠和非常紧缺的水的,我也对那一望无尽的沙漠充满了无尽幻想。还有,家乡的月夜十分美丽,满天繁星,大地上的一切事物,树木、房屋、道路、农田还有人,都沐浴着柔软的乳白色月光,清澈的月光让一切事物都发光。现在回想,文学的种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播撒在我的心中的。我尚在上小学时,就喜欢看书。当时家乡很穷,很落后,我们家买不起书,学校又没有图书馆,所以我努力学习语文教材,能找到的课外书籍一本不漏地认真看,由此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我在老家上完初中,考上了内高班,去了北京读高中。高中母校的图书馆很大,我如同久旱遇甘霖般,一头扎进了图书的海洋里。而且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北京优秀老师,我的视野进一步开拓了。以前在老家,我主要看维吾尔文书籍,去了北京后,开始阅读汉语书籍,汉语水平也突飞猛进,我开始用汉语写日记。后来,青春的朦胧情愫促使我按照课本上的古诗词,写了一些模仿作品,再后来,我开始尝试写现代诗,来表达自己因为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和感受。那时候我开始读海子、顾城、北岛、帕斯等诗人的诗歌。一次偶然的机会,校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张丽君得知我在写诗,让我把诗歌拿给她看。张老师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把我的作品推荐给其他老师和北京的一些诗人、专家,他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我来说这是最初的鼓舞。写得多了,我开始以一种诗性的姿态审视世界、审视自我。我多说一句,高中母校北京潞河中学是百年名校,学校有很多百年老建筑、百年大树,由灰、红、绿三种基本色相辅相成的整个校园如同一个古朴的公园,当“诗和远方”成为当代人的一种追求,一种奢侈品时,我们作为学子诗意地“栖居”在潞园里,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求知求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本子上写了一百多首诗歌,由张老师整理成册,有些投稿,诗歌处女作《风的故事》2012年发表在《诗刊》上。后来在学校的鼎力相助下,我出版了首部诗集《返回》。再后来,我的作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诗歌月刊》《草原》《诗歌选刊》《大家》《民族文汇》《塔里木》等刊物上。我想成为一位诗人,所以断断续续都在写,一直到现在。
白:正如你说,你的作品不断发表在各大刊物上,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他人的评价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阿:在信息泛滥的当代生活中,“伯乐”固然很重要,在古代,作品是“口口相传”,尽管现在作品传播的载体很多,但好作品需要“被发现”,同样需要“口碑”,不然很有可能被信息和流量所淹没。但是,对一个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需要“拿作品”说话。对我而言,写诗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即我在大地上翩翩起舞的方式,我的诗歌是给自己写的,也是给那些喜欢诗歌的读者——阅读诗歌,至少说明他们是有所思考的——写的。所以,我对发表作品不是很积极,跟从心声,把诗歌写好就是。当然,写一首诗歌可能需要几分钟,但一首诗歌的诞生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我需要保持这个过程的连续性。
白:除了作品的发表和获奖,我还注意到你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等文学交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你有着怎样的感受和体验呢?这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阿:是的,我参加了不少文学交流活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形成后,是很难改变的。文学的本质决定了文学/创作观念的多样性。跟不同的作家诗人交流,不难发现,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参加文学交流活动,听名家的演讲,与自己的观念进行比较,不断丰富我的知识,不断开拓我的眼界,努力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新视点和切入点。这对创作大有帮助。如果仔细阅读我的三部诗集,创作风格每部都不同。这是不断学习探索和积累的结果。总之,在创作上,决不能“原地踏步”“故步自封”,因此,作家需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在文学创作中,学无止境,如果停止了学习,其必然结果是“灵感之泉枯竭”,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一个字”。
白:环顾中外作家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他们往往也是某些作家/诗人的读者,好像你也不例外。你最喜欢哪些诗人的作品?从中受到过什么样的启发?
阿:是的,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位忠实的读者。这里所谓的“阅读”,指的不仅仅是文字的阅读,一个作家必须阅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思考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的起伏,并把所思所想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读中外名家的诗歌,也读微信公众号里发出来的作品。我一直读小说比诗歌多。因为在内容的呈现、语言的使用、结构的设计上,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有着先天优势,如果一个诗人的阅读只限于诗歌,那他会很容易成为“井底之蛙”;同样,如果一个作家不阅读诗歌,那他写出来的作品是“有气无力”的。在我的经验中,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不一样的,但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永不会过时。至于吸引我的作品,它们一定能够给我想象的空间,作品的构成要素一定有着与众不同之处。一个作家刚开始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时,可能会特别喜欢某些作家,深受其影响,但成熟之后,要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和个性。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二、“非遗”的《顶碗舞》:我的诗会带着我的爱,跳着顶碗舞,去抚慰每个灵魂
白:你的第三部诗集《顶碗舞》入选了中国作协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2022 年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诗集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这部诗集与前两部诗集有什么不同?
阿:我初中毕业便离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故乡,开始了漫长的求学征途,上完高中,接着上大学,两次考研失败后,回到新疆,在离老家1500 公里多远的大城市乌鲁木齐定居下来,不知不觉过去了8年的时间。实际上,每一首诗歌都是我在不同时期的心灵史、精神自传。我在我的创作中,一直探讨着“人何为”的问题,并试图把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这是贯穿所有诗歌的一个内核。在创作第一部诗集《返回》时,我从近乎原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瞬间跨入现代大都市和生活模式中,对我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当时我在上高中,每每下雨我便跑到校园里的湖边,泡在雨水中,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滴滴雨水消失在湖水中,这时我的心是静的,也是孤独的。我时常陷入巨大的孤独中。在孤独中我看到,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纯粹了,人类也已经面目全非,人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被割裂,产生了一种真空状态,人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在此背景下,我写了第一首汉语诗《绝望的城市》,试图带着身上仅有的一切返回,以重塑自己的身份和人类的梦——因为种子在土地上萌芽,而人类的梦延续在每个人身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另一种意义所在。在第一部诗集《返回》中,我试图返回最初的生命体验中。我的生命体验源于故乡的一切:强烈的阳光、蔚蓝的天空、炽热的土地、纯真的身体、轻盈的灵魂,还有紧缺的水、一望无际的沙漠。我愿再重复一次:“信念、土地、沙漠、水、阳光、绿色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编织出一种既透视古代又映现未来的双重画面,这就是我最初的生命体验。”①阿人初:《愿每个灵魂都是翩翩起舞的》,《文艺报》2023年2月3日第7版。创作第二部诗集《终结的玫瑰》时,我在上大学,生命的体验较高中阶段有了很大变化,阅读经验也有所提升,在追问中我找到了玫瑰——尽管此玫瑰扎根在灵魂里,绽放在诗中,但终究是要终结的——因此,我们需要不停地创作,创作诗歌、小说、散文、音乐、绘画、戏剧、雕塑。创作第三部诗集《顶碗舞》时,我已经踏入社会,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年人,这些年来,我结婚买房,经历着一个普通人要面对的所有风风雨雨。这些年来,我经历过不少的事情,来来回回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在走过的足迹上能够长出花儿来,是一个人莫大的幸福,因为我们祝福他人时会说“愿在你走过的足迹上长出花儿来”。但是,这段旅途上陪伴我的是爱、反思、语言和不堪重负的灵魂。在我的足迹上,长出的不是花儿——于是便诞生了我的第三部诗集《顶碗舞》。
白:在《顶碗舞》中,每一首诗歌的素材和艺术表达具有独特性、新颖性和现代性。尤其是首先映入眼帘的书名《顶碗舞》。名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看上去充满了浓厚的“非遗”性,又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你在给诗集起名时,有怎么样的讲究呢?
阿:有一次我们到新疆麦盖提县观看演出。当我看到顶碗舞表演时,一股电流穿过全身——那是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顶碗舞——那一刻,水、瓷碗、舞蹈、女人、音乐等因素汇聚起来;那一刻,我看到了大地上一切轻盈的物体都在翩翩起舞。于是,我把“顶碗舞”作为第三部诗集的书名,也是想尽一切可能,把异化的、物化的负重不堪的人拉回人的最初的状态——因为只有灵魂纯粹、快乐和轻盈的人,才能翩翩起舞,才能爱。
白:《顶碗舞》的封面设计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你能说这个封面的来历,以及你的感受么?
阿:《顶碗舞》进入出版环节后,在责编发过来的两套封面设计方案里面都有顶碗舞元素。我把封面发给沈苇老师等人征求意见后,对颜色和舞蹈演员的服饰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后将具有古代岩画效果的红黑二色顶碗舞图片确定为封面。顶碗舞本身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个毋庸多言。但是,顶碗舞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与诗歌遥遥呼应,对我而言,诗不仅是诗本身,它还是人类思维的结晶。因此我坚信,无论人生如何跌宕起伏,诗依然会让我们感受到振奋和鼓舞,把诗的美好传达给每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以前也说过,“我的诗也会带着我的爱,跳着顶碗舞,去抚慰每个灵魂”①阿人初:《愿每个灵魂都是翩翩起舞的》,《文艺报》2023年2月3日第7版。。
白:你认为《顶碗舞》中诗歌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色呢?
阿:对任何作家诗人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这也是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至于我的诗歌与他人作品不同的特色,这个问题最好留给读者去评判,学者去研究吧。我应该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把诗歌写好。
白:在《顶碗舞》中写了乡村经验的诗歌为数不少,如《盲肠与故乡》《远方》等。对你来说,“乡村”对于你的生活和创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阿:正如前面所说,我出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那里的人们很朴实,生活和思想观念处于近乎朴素状态。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有了最初的生命体验。现在我离开故乡已经15 年了,现在回想,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差了一些,但人是快乐的、轻盈的,那种贴近自然、贴近大地的诗意生活状态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模式。这也是最近几年兴起的“返乡热”的原因吧。但是,我们一旦离开乡村,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在文字中返回。
白:再看这部诗集中,不难发现现代意识中的“舞蹈”“爱情”“生命”等意象融入每一首诗歌中,尤其是对“爱”的表达中读到了一种无限的力量,你是如何构思与完成这种“爱”的?对你来说,这些“意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你的三观和创作有什么影响么?
阿:当代科技重塑了人类,为人类生活提供种种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就像布满蚁穴的大坝,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我尝试用汉语的、维吾尔语的词语活灵活现地表达诗思,我想用我脑海中的所有词汇来表达对生活的热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那就是死亡。是的,每个优秀作品的塑造都离不开死亡的话题。诗作为一种追问,当然会追问母亲、舞蹈、爱和死亡。我的诗充满着对生活的探索,因此显得些许沉重,一首优秀的诗往往取决于诗歌创作人持久的思考,对待大地苍生的敬畏之心,其中不乏死亡。
三、诗人的工作是创造爱
白:正如沈苇老师说说,你在新疆90后诗人中算是很出色的,你有什么创作习惯吗?
阿:我刚开始创作时,喜欢用笔写在本子上。后来,就开始用电脑和手机。我会在脑子里一直思考着,并试着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表达成诗歌,在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之前,我会经过一个较漫长的酝酿过程,一旦成功把第一句写出来,那么这首诗歌便会一气呵成。有时候,我会把突然闪现在脑海中的关键词句记录下来,运用诗歌形式、结构、修辞等知识,进一步创作出让读者认可的作品,不断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热爱。我在写诗之前,会处于一种持续的亢奋的状态。我的很多诗歌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的,这样的夜晚我往往会失眠。所以说,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白:你读高中时出版过第一部诗集《返回》,中间隔了几年时间,去年年底才出版了第三部。社会身份和生活场景的转变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阿:离开校园后,我开始了角色转换的过程,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在读书期间我对人类社会只有幻想,对社会的复杂性、运行机制、人心善恶等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对我而言一切都那么美好,可以说我一直活在文学世界里,将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步入社会之后,角色转换、适应社会等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再者,我面临谈恋爱、结婚、买房等“人间烟火”的问题,同样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去经历,去解决。万幸的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较成功,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以后按部就班去生活,抽出时间把写作搞好即可。这些经历在收录《顶碗舞》中的一些诗歌中有所反映,但我的整体创作还是以“人何为”的问题为主,表达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反思。可以这么说吧,我倾向于表达“宏大主题”而不是“日常琐碎”。另外,创作中,有时候需要慢下来,静下心来观察和思考,反思所积累的人生经验。而这些都需要时间的考验和馈赠。
白:你是理科生,专业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你上大学以后怎么坚持文学创作的?遇见了一些对你有影响的人么?
阿:文学创作跟所学专业没有必然的联系,它靠的是勤奋和汗水。只要你愿意付出,善于学习,并坚持不懈,文学不会亏待你。我愿意再重复一遍,文学创作是我的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因此,一直在坚持。但需要把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平衡一下,因为目前仅仅靠文学创作还不能养家糊口,但这不能影响对文学的热爱。
白:在《爱的宣言》《深重的爱》《创造爱》等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的宣言”。这样的结构你怎么想出来的?
阿:我可以大胆大声说,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创造爱。因为爱不仅是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不仅是维吾尔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它是命运齿轮的润滑剂,是我们能够一直活下去并抵抗无意义的动力。我不能想象没有爱的人间。尽管以前有很多诗人写过“爱的宣言”,我也想把自己的“爱的宣言”公布于众,这完全是一种创作驱动力所使然,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创作活动,就像爱也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而我在我的《爱的宣言》中,吸收了中外诗歌中有关爱的一些表达因素,从而构造了自己的爱的世界。
白:在你的心目中,诗人最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对于未来的生活和写作创作,你有什么样的规划?
阿: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对每个作家诗人而言是不同的,这个从他们对诗歌或者文学的定义中能看出来。而对我而言,最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整个房间里或者整个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听不见其他声音,看不见其他人和物。这个时候我会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近乎狂躁,这种情况也是难熬的。当把不停地膨胀起来的句子写出来,心里才会恢复平静。当前,我边从事诗歌写作,一边在从事文学翻译,将来,我计划尝试一下小说写作,已经有一些小说提纲和思考。如果说,诗歌写作是为了在大地上翩翩起舞,那小说写作是在大地上驰马试剑。从小说的叙事容量、结构的设计、语言的使用等来看,小说写作是提升写作能力、超越自我的一种途径,我想,我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已经为此打下了基础,我必须试一试。
白:十分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访谈,今天的访谈让我收获颇丰,祝你今后的事业蒸蒸日上,再次致谢。
阿:谢谢,也祝白老师学业顺利,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