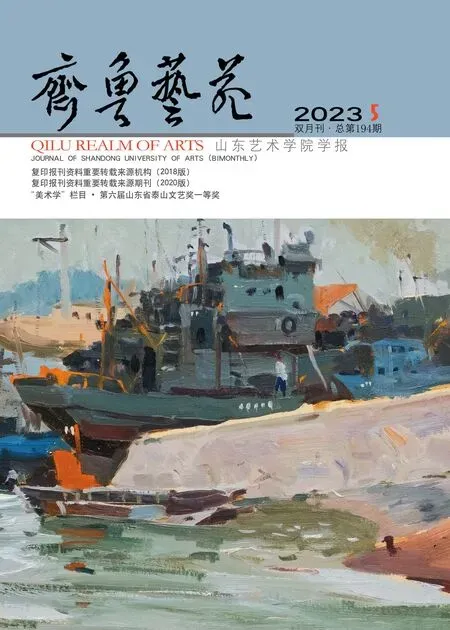关于综合艺术院校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王志扬,庞忠海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下文简称“专业目录”),将艺术学门类原有的五个一级学科归并为一级学科“艺术学”(学科代码:1301)。 这对于以一般艺术学为主体、兼容并蓄各门类艺术学的史论评而统合形成的艺术学学科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所谓“挑战”,是调整后的艺术门类仅余一个学术型专业归类,而其余六个一级学科则是135 开头,即着力培养专业型研究生。 这样看来好似弱“学”强“术”,对于艺术学(理论类学科)的学科发展,是一种“打击”。但又说“机遇”,则是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学科的史论评研究,全部被归入到“艺术学”之中了。 这实则是“攥紧了拳头”,会促成各学科间的身份同一认知,并助力实现艺术学“超学科”[1],这无疑都为专业目录调整后艺术学学科的借势发展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此次专业目录的调整正是艺术学在新文科建设中的理念回归与制度包容,艺术学学科建设必将其学理定位和学术研究提升至新的高度。[2]综合艺术院校一般涵盖多学科集群,易在学科发展中形成“合力”,是此轮专业目录调整中学科建设实践的“排头兵”。 在此基础上,根据综合艺术院校的办学特色与学科发展优势,提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路径,优化学科建设目标、完善专业队伍建设、重塑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学科发展思路,为艺术学学科建设顺应时代发展、进而迎来随后的艺术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提供完善的理论依据以及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基于艺术学“三大体系”构建与新文科建设要求,确立以“理论研究为主、突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与发展目标
艺术学学科建设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首先构建新时代艺术学的“三大体系”[3]。 并且以新文科建设为基本要求,确立突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目标。[4]综合艺术院校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一方面应坚守一般艺术学中的理论研究的主基调,另一方面则应凸显门类艺术学中的优势特色,确立主次分明、优势突出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目标。
(一)形成特色:完善专业目录调整后的学科体系
新文科建设要求打破专业壁垒、强调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基于此,调整后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不仅同时囊括了一般艺术学及门类艺术学中的理论(史论评)研究,还包含着艺术管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传播学等交叉(边缘)学科。 可谓对艺术学原先“拆解”状态的一次全新“统合”。 在此背景下,综合艺术院校应致力于完善调整后的艺术学学科体系,着力体现“综合”后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优势,同时发挥学科交叉的势能,为艺术学的各边缘学科重新定位,形成新“艺术学”的“合力”,并积极于其中挖掘学校的“特色”,体现此类高校“合而有专”的学科建设特色。
(二)文化内核: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术体系
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5],中国艺术历经几千年来形成了自有的气质、范畴、对象和鉴赏方式。 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应充分发掘中国艺术学的文化归因,意识到中国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的独特性,特别是在学术体系建设中兼顾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要求。 综合艺术院校应积极探寻自身学科发展中的本土性,以建立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为主要发展目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突破艺术学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困囿,用中国范式解决中国艺术的特殊问题,在艺术学学术研究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以艺为媒:拓展对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
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应坚持用中国艺术学理论阐释中国艺术实践,用中国艺术实践升华中国艺术学理论,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积极推动完善对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综合艺术院校应深挖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大特色,要充分把握艺术作为媒介在对内交流与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积极拓展对内与对外两个维度的话语体系。 对内发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声音,提升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中影响力,对外通过艺术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通过向世界展现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以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向世界展现中国艺术的风格与气派,提升中国艺术学的国际话语权。
(四)服务地方:构建艺术学学科的应用体系
无论是根据新文科建设要求还是基于综合艺术院校应用型大学的定位,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要实现理论突破、实践创新和全方位拓展,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于国际特别是地区的实际需求。 因此,综合艺术院校艺术学学科建设目标,应对接国家及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产业转型需求,对接地方民生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以服务地方为根本主旨,积极构建艺术学学科的应用体系。 特别是努力嫁接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实践与国家及地方需求的桥梁,打通学科应用与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政策、战略需求的结点,实现艺术成果向服务地方工作的实际转化。
二、根据重构后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目标,形成“内培与外引”“弹性管理与科学评价”为主旨的学科队伍建设
重构后的艺术学一级学科由“单一”走向“聚合”,实现了一般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在理论方向的部分“融合”,还吸引了艺术交叉(边缘)学科的加入,正突破艺术原有的“边界”。 这对于艺术学学科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艺术院校应根据重构后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目标,在人才培育、人才管理、人才评价等方面优化提升。 应充分认识到人才是综合艺术院校学科队伍建设的核心支撑[6],根据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予以完善是重中之重。
(一)坚持内培:打造人才高地、培育创新团队
调整后的艺术学学科因其对于艺术学理论及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进行的整合,故而在学科队伍建设方面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特别是根据专业目录调整后的艺术学学科“和而不同”的特点,需要在人才队伍中补充相应学科方向的人才。 综合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科建设较为齐全,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率先根据学科建设目标在其内部进行学科队伍的重组,坚持不懈在学校内部引援助力,抢占艺术学一级学科队伍的人才高地。 同时,积极培育并建设若干艺术学学科方向的创新团队,通过人才团队的跨学科重组,形成团队特色、广出研究成果,使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队伍建设中抢占先机。
(二)强化外引:柔性引进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艺术学学科队伍建设,既要坚持自有人才的培育、人才团队的孵化,又要以更为灵活开放的形式重视对外“引援”工作。 专业目录调整后的艺术学学科更为“国际化”,更需要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人才加入。 综合艺术院校应打破国家、地区及校际间的壁垒,面向海内外加大柔性人才的引进力度,体现其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领军作用,发挥其在创新团队建设中的提领效用,以点带面形成“蝴蝶效应”。 综合艺术院校还要注重领军人才、特聘学者与青年人才的作用整合,为柔性引进的人才“下任务”,通过“老带新”帮扶校内青年人才成长,最大程度地发挥柔性引进人才在学科团队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三)弹性管理: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艺术学学科队伍管理需强调“弹性”,一方面源于其学科特殊性,艺术人才需要相对弹性的时空进行艺术创作与思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弹性”兼顾着以人为本与制度约束,管理方式不仅灵活还更科学。 综合艺术院校通过弹性管理有助于提高学科建设质量和学科队伍的凝聚力,更易充分调动起艺术人才的积极性。
专业目录调整后艺术学学科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综合艺术学院的学科队伍也将日臻完善,施行弹性管理制度,将优化人才发展的条件与环境。此外,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制定考核标准分类,也为其工作设定硬指标和软绩效,给人才晋升提供充足空间,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和待遇留人有效统一。
(四)科学评价:建立适配的艺术人才评价标准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学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对人才的评价要注重教育教学实绩,为建立科学的艺术学学科人才评价标准提供了根本遵循。艺术学学科发展对人才的基本要求,要同时兼顾学科教学、艺术实践与学术研究,这既源于艺术学学科的特色,同时也符合新文科建设的理念。 综合艺术院校应制定适配于院校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就要平衡上述三点之间的权重,确立教学、实践、科研平衡的人才评价标准。 在艺术人才评价标准体系中,要坚持“破五维”,又要科学量化如高水平论文、专著、科研项目、学术获奖、学术活动等方面的绩效评价,给予学科队伍人才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环境。
三、明确艺术学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教学、质量评定等维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专业目录调整前,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旨在培养学术型学位研究生,重视艺术总体规律的理论研究。 专业目录调整后,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培养定位看似未变,但对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及培养质量发生了时代之变。 艺术学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定位,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需要具备丰厚的人文素养且精通艺术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兼具问题意识、创新意识与交叉意识。[7]因此,需在艺术学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目标维度、课程维度、教学维度、质量维度等方面进行调整,以全面提升艺术学高级人才的培养质量。
(一)强化复合:重塑艺术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综合艺术院校重塑艺术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要遵循三个“实际”。 其一是专业目录调整后的艺术学学科发展实际,其二是根据新文科建设的理念要求实际,其三是根据院校所在地区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实际。 根据上述三项重构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强调创造性,培养善用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进行中国艺术学理论深化研究的专业人才,以保证科研创新能力与学科发展要求相适配。 强调交叉性,培养善用跨学科思维与交叉意识突破学术前沿的专业人才,以保证思维意识与时代之需相适配。 强调应用性,培养用艺术理论解决艺术创作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以保证培养出口与行业实需相适配。
(二)交叉深化:打造立体多元的特色课程矩阵
综合艺术院校根据重新设定的艺术学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强调交叉与深化,调整并构建三个维度的课程群,形特色鲜明、层次递进的课程矩阵。 根据培养目标中的创造性,在原置课程中深化培养创新创造力的理论研究课程群;根据培养目标中的交叉性,开设跨学科思维导向的以拓展研究方法为目的的学科交叉课程群;根据培养目标中的应用性,打造有行业专家参与的以提升艺术实践力为要求的应用研究课程群。 在课程矩阵形成后,还应培育和孵化一系列优秀课、精品课、一流课程,并根据人才培养实际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矩阵的组合与排列。
(三)注重教学:完善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
提升艺术学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教学,完善课程教学的各项环节是重中之重。 综合艺术院校要根据艺术学学科建设目标,针对性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注重理论研究、艺术鉴赏、艺术实践等能力的培养。 要根据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际,针对性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与环节,注重问题思维、创新思维、跨学科思维的养成。 要根据教学队伍与生源情况,针对性优化教法与学法,注重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塑造。 要根据教育技术的发展,针对性打造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的教学环境,注重学生参与感、体验感的营造。
(四)明确指标:更新研究生培养质量评定标准
艺术学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评定,也要具象到各项评定指标,以指标来评定其人才培养的成效。 在这方面,综合艺术院校应根据调整后的专业目录中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实际,重新组织设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体系,要将专业目录调整后的变化在各级各项评估指标中体现。 重新核定艺术学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质量评定标准,是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 艺术学学科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应该有据可循、有理可依,综合艺术院校可以院校联盟的形式聘请校外专业机构制定统一的评估体系,以制定出极具科学性、适配性的评定标准,并根据研究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调整。
四、探索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创新体现“吸收外部经验、强化自身特色、重视学科交叉”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思路
专业目录的调整,为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艺术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方向,也为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立场下来看,艺术学学科发展是向好的,可以说,此次专业目录的调整为艺术学学科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8]综合艺术院校应把握学科发展的机遇,借势探索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创新艺术学学科建设发展思路,为艺术学的跨越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走出去:调研国内外艺术学学科发展情况
综合艺术院校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应提升站位,避免偏安一隅、闭门造车。 应借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努力实现“走出去”,一方面,赴国内各艺术学一流学科院校进行调研、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尝试了解国外的艺术大学、院校的艺术学学科发展情况。 通过掌握国内外各类艺术院校、大学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实际,不断总结规律与经验,以服务综合艺术院校自身的学科建设。 特别是在探寻新的学科增长点方面,要打开眼界,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与艺术学发展趋势,积极调研、探索、取经,以前瞻性思维去发掘别家优势,从而补足自身学科建设的“短板”。
(二)强特色:以综合艺术院校优势推动新艺科建设
综合艺术院校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结合未来的发展规划、根据地域内的文化社会之所需,找准未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特色与定位,把握新时代艺术学史论评研究的新趋向,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提炼出自身的特色,以探索并实施”新艺科”的建设与发展。 “强特色”一方面应对标上述提到的国内外相关院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实际,另一方面还应根据综合艺术院校的自身优势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 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是在全球视野下紧跟国家战略需求、新文科建设和学科监制三个层面而获得的。[9]对此,综合艺术学院应积极探索符合院校实际的新的艺术学科增长点,从而推动新艺术学的学科纵深发展。
(三)闯蓝海:构建艺术学学科交叉的新体系
综合艺术院校要根据新文科建设背景重视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建构。 此类交叉学科,曾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中一度被认成“边缘”学科,其学科方向的发展往往被忽视。 但根据新文科建设以及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实际,艺术学交叉学科将从边缘走向实际,并逐渐在学科发展与应用中形成为“显学”[10]。 综合艺术院校应借此机遇,积极探索学科“蓝海”,在学术研究中积极考辩艺术学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的可能性与应用价值,积极构建艺术学学科交叉的新体系,并尝试利用艺术学交叉学科解构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学科交叉的新增长点,为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