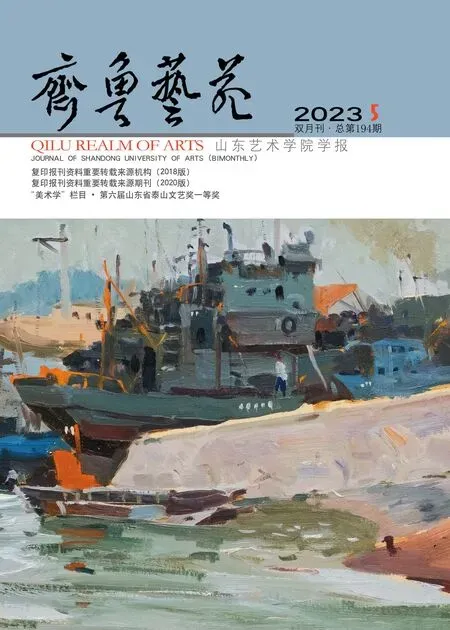情理辩证法与“中间距离”
——论谢晋电影中的传奇叙事
袁道武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谢晋,这个名字意味着一种执旗手式的身份,其地位如同新中国“影坛盟主”,无论是其作品的分量,还是人生经历的传奇况味,或者由他引发的学界公案,都是中国电影史学撰述不能绕开的路标,在谢晋诞辰百年之际,重思谢晋电影的意义价值,应是学界一份严肃庄重的工作。 此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的叙事研究一般侧重在“政治—道德”伦理情节剧范畴,在这个维度上形成“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伦理道德叙事的连接线,而与伦理道德最相关联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传奇叙事精神。 有论者认为:“长期拥有大量观众和良好的票房效应,是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又一个共同的电影文化现象。 这一个共有电影文化现象最坚实的支撑性基点就是影像传奇叙事。”[1]以“影像传奇叙事”为视野的谢晋电影研究,也是成果颇为丰厚的存在。①参见:虞吉. 影像传奇叙事视野里的谢晋电影[J]. 艺术百家,2011,27(2);包燕. 传奇叙事与喜剧精神——谢晋电影的世俗趣味及传统改写[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4)等。实际上也有论者提出:“‘传奇’作为一种审美趣味和叙述手法贯穿于谢晋的几乎所有电影中。”[2]另一方面,从谢晋的自述中,我们也可以确证谢晋对于传奇叙事的借用,其在《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一书中,以《红色娘子军》为例,明确指明了自身立足传奇进行创作的思路:
1. 情节结构上有“奇”的地方。 首先,戏不是平铺直叙的,一开始就有“奇”的感觉……都带有传奇性。
2. 人物出场、人物关系也带有传奇的色彩。
3. 出现的场面,如“蛇宴”“木头人”等,也带有“奇”的色彩。[3](P11-12)
以此为观照,我们试图承续前人关于谢晋电影传奇叙事的立论,并以其分支——“苦情戏”考察他的作品中相关的具体表征,探究谢晋是如何在传奇叙事基础上进行“情—理”二元结构的转喻融合,分析其在创作书写中所采取的修辞诗学范式。 而其之所以能够得到主流话语与大众感受双重认可的深层缘由,也同样值得重新确证。
一、传奇叙事:以“苦情戏”为中心的考察
谢晋电影中对于传奇叙事最为深刻的理解,除了对伦理道德的娴熟编码,还有他对于中国古代传奇中“苦戏”笔法的自觉运用。 所谓“苦戏”,也被称为“怨曲”“怨谱”,是晚清以将西方文化直接影响中国之前,古代评论家对悲剧题材戏曲的称法,有时它也被指称为戏曲传奇设置悲剧冲突的叙事样式[4],其代表性作品有《离魂记》《救风尘》《琵琶记》《窦娥冤》《汉宫秋》等。 《琵琶记》在开头的“水调歌头”第一句写道:“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 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沈既济在其所著传奇《任氏传》中阐述“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①转引自:李军均. 传奇小说文体研究[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P187。这些表述都指出了“苦戏”传奇注重情感接受的审美特征。 以此来对照谢晋电影,我们会发现,谢晋电影对于人物命运曲折多舛的展示,对善良终将战胜丑陋的笃信,以及将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勾连的繁复,都是通过将主人公置于悲苦命运的漩涡,并在整一情节的铺排和人物情感的渲染中,营造出令人嗟叹回味的共情效果。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具体分析。
(一)苦情女性:变化中的政治角色
我们把谢晋电影归结于对“苦戏”传奇的继承,而不是西方悲剧的引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电影作品中抒情主体的人物特征。 “西方戏剧的悲剧人物必须是高贵的,悲剧事件必须是崇高的……中国戏曲悲剧,特别擅长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强调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更富有人情味。”[5]谢晋电影作为“苦戏泪剧”,其承载对象落脚点亦在小人物。 确切地说,是处在悲苦命运中的女性小人物。 对此有论者提出:“注重女性形象在情节结构和镜头展示中的作用,是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惊人相似的叙事表现策略,也是影像传奇叙事源流中特征鲜明的承续性节点。”[6]中国电影史中最具“标识线”意义的三位导演郑正秋、蔡楚生、谢晋对苦情女性出奇一致的关注②在2009 年6 月13 日至14 日于上海召开的“谢晋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标识性联线”获得了倪震、虞吉等学者的普遍认同。,对于传奇叙事的熟稔运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和女性叙事策略的趋同,对应着更为纵深面向上的传奇中的叙事习惯和重心。
谢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往往与古代传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出身卑微且往往早失怙恃,命运的格外不公反而孕育了这些女性强悍的生命属性,进一步为营造人物的传奇感预留了空间,好让她们在悲欢离合的命运流转中生成吉凶悔吝的人生况味,这也是谢晋电影与观众形成“共情”机制的发生学前提。 《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韩玉秀……她们贤惠勤劳、任劳任怨的形象,她们主动承担舍弃自我的精神,让人不能不想起古典传奇中赵五娘、李娃、孟姜女等为士子或丈夫自我牺牲的薄命红颜。 《红色娘子军》中反抗地主剥削、向往革命的吴琼花,《秋瑾》中追求婚姻自由和国家富强的传奇女侠,与聂隐娘、红拂女、无双等奇女子类比,又有共同的性格特征。 《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邢月红,《红色娘子军》中的符红莲……她们受尽压迫的苦弱女子人设,又何尝不是现代版的窦娥呢? 陪着木头人“丈夫”过日子的符红莲与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又何曾不是同一种人呢?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谢晋(当然包括郑正秋、蔡楚生)在其作品里所刻画的悲苦女性,也是传奇中“苦戏泪剧”常见的叙事主体。 谢晋在导演阐述中也认为,其作品里的悲情女性,体现了一种古典性格[7](P83),这种古典性格指向的,往往是和古代传奇中的苦命女子一样,“通过自我的隐忍和牺牲,完成对于男性伴侣(通常为落魄的士子)的搭救”[8](P89)。
不过,谢晋电影中的传奇女性的意义附载,远比传统“苦戏泪剧”复杂。 通过观察比对,我们可以发现,谢晋电影中的女性人物,往往会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新时期之前的谢晋电影中的女性,比如吴琼花、田春苗,某种程度上带有聂隐娘、红拂女、无双式的精神气质,她们是历史变革的主动参与者,或者像竺春花一样经过进步人士的启迪后,迅速加入人民阵营。 她们早失怙恃的人物设定,反而成为符号意义达成的一个前提,即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是无父无母的,自然而然地,她们将在集体生活中,被指认为一个非肉身的共产党父亲的女儿。 而到了新时期以后,随着时代更迭,谢晋电影中的女性随即转变成赵五娘、李娃、薛宝钗一类的人物,以20 世纪80 年代“反思三部曲”最为典型。 无论是嫁给“落魄”许灵均的李秀芝,看望并示爱罗群的冯晴岚,还是“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胡玉音,谢晋在保留悲苦女性的“苦戏”特征前提下,将其置换为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灾难的被动承担者和殉难者,她们又成了箭簇式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身份游弋,让我们的主人公如同回到了中国古代传奇中人物的社会属性,即谢晋在对待女性主体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其“去中心”。 我们将会和其中的女性人物,一同处在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当时代风暴结束,这些女性也将香消玉殒(如同士子登科后,主动离去的李娃们),而有关历史事件中心的任何震动,都有可能是让这个女性作为最终的承担者和牺牲者,以此渲染出苦戏悲情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有论者认为“谢晋电影不过是通过女性表象,来为权威历史话语制造出它的历史无意识,女性表象成为他向权威历史话语献祭式中的被献祭者。”[9]
(二)情节的“苦情”触发机制
从情节铺展层面上看,传奇戏曲与西方戏剧有一个显著的不同。 “戏剧采用了史诗的客观原则和抒情诗的主体性原则经过调解(互相转化)的统一”[10](P242),即强调情节推进和人物情感/意志的结合。 传奇则更加强调人物必须充满情感,但这个情感又不是可以化为推进戏剧动作的意志。正如吕效平所说:“它(传奇笔者注)的人物行动可以来自作者的任意安排,而不必出自自觉到的意志;它情节的动力主要来自作者的意愿,而不是剧中人物的意志。”[11]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例,原著小说是以高干子弟赵蒙生为视角展开,侧重于揭露时代交替中的不正之风问题。 为了让这个故事更符合谢晋电影一贯表达的需要,影片将改编的视角放在了梁三喜及其家庭上,这是为了让情节铺展更有利于突出苦情效果。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故事依旧按照原著小说的视角来进行改编,相对于来自老区的贫苦战士梁三喜,赵蒙生这个家庭背景优越的宣传干事的事迹,将会在苦情效果上大打折扣。 学者应雄提出,谢晋“把握了古典写作的中国式‘泪腺’”[12],这个概括指向的是谢晋电影以情感驱动审美,贴合中国人普遍的对于煽情的阅读期待。 将情节的发生机制建立在苦情人物身上,几乎是谢晋在他每一部电影中贯彻的方法论。 《舞台姐妹》中,不愿做童养媳的竺春花跪求戏班收留,奠定了全片的苦情基调,而“舞台姐妹”以三年唱戏包银为代价买棺葬父,则将苦情推向极致。 《春苗》一片,开场也是以孩子夭折作为苦情叙事的触发点,而春苗的父亲,就是因为贫穷抱病离世。 如此一来,人物的苦情设定,就为春苗这个人物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述意义上采取行动提供了驱动力。 这种情节触动机制在谢晋20世纪80 年代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 《天云山传奇》一片,正在劳动改造的罗群又逢爱人离去,冯晴岚在风雪中送其就医治病;《牧马人》中,自幼父亲去国、母亲亡故的许灵均遭受冤屈;《高山下的花环》中,梁大娘用儿子的抚恤金还账;《芙蓉镇》中,卷入时代漩涡的胡玉音又遇丈夫自杀;其它如《清凉寺钟声》中,亦有秀秀含泪弃婴的段落,都是以人物凄惨命运所凝练出的苦情效果,作为对某种命运不公和遭遇控诉的促发点,此类情节在谢晋电影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总体而言,谢晋在他的电影中,首先将人物置于苦情命运,以这种情境而不是具体的矛盾冲突来激发人物采取行动,其情节推进无不注意赋之以催泪的效果。
(三)“重逢团圆”的闭合回环结局
中国古代传奇在对故事的最终处理上,往往存在一种“重逢团圆”的既定结局,如《牙痕记》《幽闺记》,以及《本事诗》中流传甚广的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 男女主人公往往在离散多年后又在一次没有征兆的巧遇中重逢,以形成故事的闭合回环结构。 有论者认为,传奇的情节艺术及其审美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一对张力和应力的矛盾:“张力的一面是尽可能把故事的曲折离奇推向极限,应力的一面则是通过尽可能巧妙的缝合照应,使这种曲折离奇被信服与接受。”[13]揆诸古代传奇,这样的双力拉锯所形成的闭合回环的情节结构实在不是少数,《古镜记》《李娃传》《柳氏传》《天仙配》《白蛇传》……在中国观众的阅读期待里,如影随形地不断重述诸如“邪不压正”“善恶有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古训,以至于不管如何铺垫“离人无语月无声”的苦情基调,最终都会通过作者干预式的情节缝合,将故事人为地引向“明月有光人有情”的圆满结局,这在谢晋电影中也比较常见。 《女篮5号》男女主人公田振华与林洁在经历家庭阻挠和误会分开,辗转多年因为后者的女儿林小洁而再次人海相遇;《舞台姐妹》中,竺春花、邢月红经历反目成仇,后在偶然的场合中不期而会,并最终在演出红色现代戏的神圣场合下,完成冰释前嫌的大团圆结局;《天云山传奇》中,分别多年的罗群、宋薇,最终又有了人生交集;《牧马人》中的许灵均父子多年后的重聚;《清凉寺的钟声》中,明镜和尚与日本生母在异国的人海重逢……无论重聚那天的到来如何遥远,无论天各一方的晚空如何凄冷,某年某月离人们终将渡尽劫波、重拾往事。 谢晋熟稔中国古代传奇中最常见的“离散—重逢”的闭环结构,由此所营造的哀怨婉转的情感低吟,关乎中国人向善重情的民族心理,所以同那些“苦戏泪剧”的作者们一样,他也很少将故事推向一个期待落空和价值毁灭的境地。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在经历千般磨难、万般辛苦后,往往会被安排一个对明天留有希望的结局。 同传奇叙事一样,这种人为介入叙事、以情感驱动逻辑形成团圆的闭环结构,本质上是将社会矛盾和秩序裂隙强行化解在突如其来的团圆结局中,以绵绵无尽的情愫,来消弭人生苦难。 综上而言,谢晋电影对于苦情戏传奇的继承,在其女性主人公悲情人设,以“苦情”驱动情节,以及“离散—重逢”的闭环情节结构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①实际上谢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淮剧戏曲电影《蓝桥会》也是如此。 从小青梅竹马、互生爱意的恋人韦郎保、贾玉珍因为兵乱而分开,后韦沦为流民,贾被迫做童养媳,街头又巧遇重逢。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蓝桥会》可以说是苦情叙事机制和离散团圆的闭环结构之典型,但因为其本身就是淮剧改编而来,不能完全代表谢晋的叙事意图,所以这里表过不提,但或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奇之于谢晋的某种关系。
二、“情理辩证法”:欲说还休式的评说
中国的苦情戏是“以‘动人’为重要的审美效应论,以‘苦境’包孕着的形象主体论”[14],所以将情感渲染到至高的地位,并以伦理公德的彰显达成感动人心的目的,正是其审美特征,也是其风格优势。通过对“情”的渲染,来完成对“理”的彰显,是谢晋电影传奇叙事意义达成的一个重要路径。 “情”与“理”都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概念,按照李泽厚的观点,“‘情’来自动物本能,常与各种欲望、本能和生理因素相关联结,它是非理性的。 ‘理’来自群体意识,常与某种规范和社会因素相联结,它常常要求理性”[15](P94-95)。 一般认为此两者在文化表达上天然具有对峙性(对峙的典型无疑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16 世纪不可避免的争锋)。 “‘苦戏传统’作为一种戏剧冲突模式所期待的情绪反映,正是由传统文化‘情’和‘理’的对峙所致,就是个体追求之‘情’与秩序之‘礼’的对峙。”[16]如前文所述,传奇化解这个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围绕整一性的情节线组织情感叙事,以人生冷暖所孕育出的“情”来代替人生的本质属性,充实经验生命的此在,弱化对于“理”的终极追问。
谢晋电影中的传奇叙事,可以说从整体上采用了古代传奇中“苦情戏”的基调,注重“苦情”驱动情节,并适时地将情节引向“离散—重逢”的闭环叙事结构。 正如谢晋自述:“影片中的人物的感情起伏的幅度较大,要切忌平铺直叙,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突出重点。”[17](P95)应该说,谢晋电影传奇叙事的逻辑于内在理路上与古代传奇有着相似之处。 “情”不仅具有审美功能,同时也是一种体悟伦理的认识论,以“情”作为依托发出有关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追问。 但是,谢晋电影并不是仅仅先将“情”与“理”放置到二元对峙的结构,然后再将理智渗透融化在情感之中。 他更重视将“情”的渲染引向“理”的意义的达成,而不仅仅将故事停留在某种情感审美的满足上。 这个“理”不是最终回到世情生活的基本面,而是指向历史表意的纵深。 具体来说,《舞台姐妹》中,竺春花和邢月红在反目成仇后分离多年,最终重逢在家乡的戏台,这本可以像古代传奇一样,将结局重心落脚在苦命姊妹和解带来的情感满足,但谢晋最终用一场《白毛女》的演出赋予了历史内涵。 《天云山传奇》的结尾,冯晴岚病逝,谢晋在使用了几个空镜后,转而借宋薇的旁白,交代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芙蓉镇》也是如此,已经疯癫的王秋赦的叫喊,影片在众人意味深长的凝视中结尾,最终将时代风暴施加于个人的受迫,引向对于逝去过往的沉思。
概括而言,谢晋对“情—理”路径的辩证改造,是既将“情”视为道德伦理叙事推进的润滑剂,又小心翼翼地向所处历史当下的意识形态“询唤”做出回应。 “情”则煽情动容以抓取观众的同情心,用强烈的情本体冲动诉说道德和伦理的悲剧故事;“理”则借助道德仁爱这套旧学的水瓢,将苦情传奇舀进历史意识形态的皿器中。 当然,他影片中的主人公也并未冲破某种历史枷锁,他们不发出对那个造成了他们困境的历史的质询,无论苦情如何渲染,最终都被小心翼翼地缝合进意识形态的收纳袋中,并对所处历史进行一个欲说还休式的评说。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退步,但是我要说的是,脱离了具体时代语境的局限而对谢晋提出表述上的保守批评,这种观点并不负责。 在其能被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谢晋仍然策略性地让他的作品与历史现实勾连,从而完成一种现代性话语的表达,这在新时期以后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中最为明显。 应该说,当谢晋向历史真实取材来进行创作时,他的作品便具有了历史写作所含有的史传韵味,所以对于谢晋电影的传奇叙事,我们既不能将之主要推向传奇的虚幻性层面,也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历史主义的表达。 谢晋电影的传奇叙事,实际上是保留了传奇的故事形态,又将之牢牢地与现实勾连进行历史阐释,这是谢晋电影传奇叙事相对于古代传奇一个最大的形态变化。
三、“中间距离”:历史现实主义修辞
揆诸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叙事文本所带有的史传意识,以及各种史书所带有的诗骚传统,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叙事,并偏好将叙事赋予历史阐释的传统。 “中国传统倾向于将大量异质性的叙事材料统一在无所不包的历史概念中去理解。”“在中国人看来,甚至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一个关于赋予人类社会体制(如父权制、帝王、父亲、国家、法律)合法性的宏大元叙事。”[18](P137,89)所以,即便是偏向超越现实逻辑面向的传奇,在作者调动各种具有奇异感的情节,将读者吸引到现实经验之外的奇异之地后,叙事者往往会在结尾出现(有时这发生在开端),以交代故事来源并发表道德性评论的方式,增加其真实性和史传意味。 如果说传奇的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是将故事纳入历史范畴的话,谢晋电影则直接将历史放在了优先于传奇的位置,所以他所叙述的历史并不强调如何奇异诡谲,而是将之引向现实世界的人间冷暖离合悲欢。 正如戴锦华所言:“他总是在用历史——刚刚逝去的世界与时代来阐述并界定着现实与今天……他要依据现实政治的主旋律来定义历史。”[19]实际上只要我们观察谢晋的作品序列就会发现,谢晋的电影几乎不脱离现实社会语境,这显然不是巧合。 “对材料的等级化组织方式是为了适应某种特定社会政治标准。 它要显得自然、非常规化、非问题化,其手段就是通过历史上写作的现实主义诗学。”[20](P78)从这个角度说,谢晋电影的传奇叙事策略是在对历史符合政治标准的改写中,加入作者基于当下现实的改造,营造出一种“历史现实主义”传奇的修辞意味。
考察谢晋传奇叙事的这种“历史现实主义”修辞,会发现有其必然性。 在新中国之后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历史的焦虑、担忧和期盼,成为当时切身的日常经验。 这个时间段的谢晋电影,其抒情的表达也不可能脱身于历史之外。 而传奇叙事既然面向的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那么对于历史叙事的把握,如果任由传奇“超现实化”的处理,等于说用一个非官方色彩的修辞学,来表现一个“当下此刻”的官方历史。 这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很容易受到场外变量的干扰,且受到驳杂的社会动机的解读(显然谢晋的电影很难摆脱这种命运)。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叙事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意识形态和某种形式感的结合,这意味着它必然应该具有历史阐释和诗学修辞法上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这种可信度是依托一种在场感和真实感,显然历史现实主义是比较合适的策略。 正如鲁晓鹏指出的:“中国叙事话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 一个是叙事诗学,它必须是现实主义、自然和逼真神似的。 另一个则是阐释学,它必须为人类历史进程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图示。”[21](P91)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叙事是关注一种非民间话语,使现行的观念和秩序合法化、常规化以及自然化,而现实主义叙事是将镜头聚焦芸芸众生佝偻之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谢晋所采用的这种“历史现实主义”的修辞法,使其站在这两极之间某个具有安全感的“中间距离”上。 它既不是表现,也不是再现;既不是幻像,也不是真实;既不是檄文,也不是投名状。 他努力地寻找话语表达上的平衡,对此我们或许不应该苛责谢晋的这种方式是一种“团团作揖”,而要看到谢晋作为一个传统道德伦理下成长起来的导演,在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中力求平衡的努力,这让他成为一个鲁迅意义上的夹在两种断裂历史之间的“中间物”[22]。 汪晖认为,“这个历史的窘境迫使谢晋采取一系列策略来重新表述他的政治信念,而重新表述的过程当然也包含了对于政治信念的修正和补充”[23],这指向的正是谢晋在这种环境中的创作之难。 尼克·布朗将这种创作环境归纳为“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24]。 谢晋的创作是在两者之间探赜,并且较早地找到了一种属于他的也是比较稳妥的方式。
但是必须要说,这种站在“中间距离”的历史现实主义修辞法,也有其必然的局限性。 本质上来讲,谢晋电影的历史现实主义修辞采用的是一种现在完成时态,即以历史的当下为界碑,在此基础上将叙事的意义保留在这个界碑之前的时空中。 也就是说,他永远关注的是昨日的殉难者,而不是造成这种灾难的背后的历史/权力结构。 无论历史发生了什么,谢晋都会将之与今天的现实对接,并赋予当下现实以最大合理性,完成一种“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也会变好”的表述,从而获得表述上的合法性。 正如汪晖所言:“既要揭示历史悲剧的残酷性,又要表明这个历史悲剧不足以动摇那个造成悲剧‘权力关系’的合法性。”[25]当谢晋自觉地将话语的表达退避到这个界碑之前的时空中,这个界碑便成了某种带有总结性的“一切到此为止”的思想墓碑,一种勘测表达话语是否形成某种僭越的标尺。 我们可以说谢晋电影的传奇故事是依托在现实的当下状态中的,缺乏走向历史纵深处的动力,更缺乏指出历史问题的决心。 这也是有关谢晋电影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局限。
结语
谢晋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旗帜意义的导演,其人其作品都带有中国电影一种连接线的意义。他的文化背景和所处的时代环境,让他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中传奇叙事的影响。 通过对其创作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谢晋对于古代传奇“苦情戏”叙事样式的采赜。 这种样式的流行以及它被观众普遍地接受的现实,也是中国人情感驱动审美的民族文化心理运转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种传奇叙事的策略性使用,谢晋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的修辞。 沈从文曾把历史分为事功的历史和有情的历史,前者面向的是历史人物与宏大的历史观,而后者却是在历史的肌理之中寻找鲜活的细胞,那是在冰冷的时间流中温暖的生命个体的故事。 “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成熟的书写“不仅仅是积学而来。 而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须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①转引自: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P65。从这个角度来说,谢晋电影的“历史现实主义”叙事修辞,尽管有其相当的局限,但却是将人提升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层面的。 这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导演,通过一种极具个人气质的电影风格的精心建构,以抒情主体的姿态赋予了传奇叙事新的范式,并饱含情感地从人间的悲欢中描绘了一幅审美和伦理的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