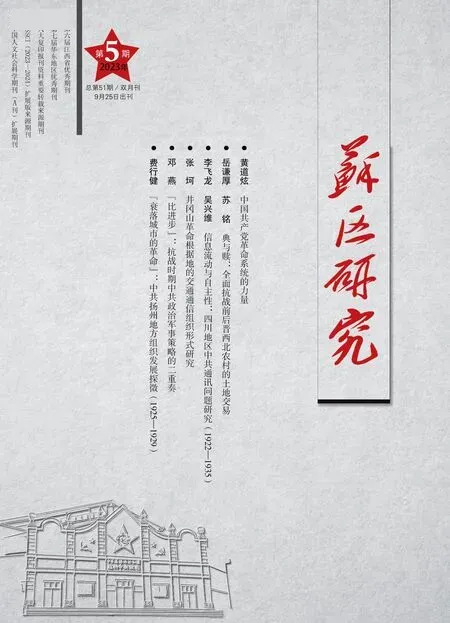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演进趋向研究(1927—1930)
王丽彩
毛泽东曾提及,“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发起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对其后开创红色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明晰“中共革命如何发生与成功”这一重要问题不可回避的部分。既有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中共革命暴动的总体性研究。(2)主要有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王明前:《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作为社会运动的1927年中国革命暴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6期;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李里:《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探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张永:《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余文华:《联合的大暴动: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探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李曙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工农武装暴动思想述评》,《苏区研究》2021年第4期。此类研究往往以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武装暴动的“共通性”为切入点,进而探索其内在机制。二是对中共革命暴动的区域性个案研究。(3)主要有曾耀荣:《抗争与妥协: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乡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动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第5期;黎志辉:《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王才友:《被动与主动之间:江西暴动的策动与终止(1927~1928)》,《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王才友:《从军事动员到日常斗争: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1927—1928)》,《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高静云、黄文治:《组织竞争与党团纷争:中共湖北暴动争议研究(1927—1928)》,《苏区研究》2022年第5期;贾牧耕:《地方因应与分途同归:中共湖南暴动的演进研究(1927—1928)》,《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近年来,随着地方档案史料的挖掘,学界关于中共革命暴动的区域性个案研究成果产出颇丰。这些研究或是将目光聚焦于所谓革命的“中心”——湘鄂赣地区,或是将目光聚焦于所谓革命的“边缘”——江浙地区。而河南省既不属于革命“中心”,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边缘”地区,其在革命暴动中的地位属于“第二等区域”且有一个明晰的上升过程,独具特色,相对而言,目前有关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研究稍显薄弱。笔者曾尝试从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视角出发,探讨1927至1928年间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因应。(4)王丽彩、黄文治:《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因应(1927—1928)》,《苏区研究》2021年第5期。基于此,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再次试图利用中共中央、河南省各地的革命档案文件及地方史志、回忆性资料,进一步剖析1927—1930年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演进趋向,探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革命的微观机制。
一、从自发暴动到自为暴动
1927年11月初,中共中央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5)《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虽遭遇暂时性挫折,但乡村社会中“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暴动有望造成新的革命高潮。然而,曾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李维汉,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却阐明,“当时的农民暴动,并不都是‘自发的’,其中大都是党组织领导的”,“‘总策略’(一)使用了‘自发的’这个形容词,实际上当时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多数场合是党组织在那里推动和领导的,其中有的还带有强迫命令的性质”。(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所以,根据李维汉的观点,所谓的自发暴动称之自为暴动更加合适。实际上,囿于大环境,彼时中共中央与李维汉个人回忆都有一定片面性。大革命失败后,乡村社会中的确存在不少农民自发暴动,这部分暴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并出台政策要求地方党组织注意引导,以期汇成总暴动。随着实践的深入,中央不断强调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自发暴动中的组织性,原有的自发暴动逐渐向自为暴动转变。虽然自发暴动与自为暴动相区别,但两者之间的界限却非常微妙,自发暴动向自为暴动演变的动态过程是构成整个中共革命暴动的重要一环,而河南地区的革命暴动即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环节。
河南省农民自发暴动的渊源可溯至大革命时期甚至更早。作为“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广袤且为进出西北六省的门户,具有相当的地缘优势。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河南省军阀林立,混战频发,成为各种军事割据势力汇集之处。仅1922年至1927年五年时间里,河南省就接连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与赵倜之战、憨玉琨与胡景翼之战、吴佩孚与岳维峻之战、靳云鹗抗奉战争等。随着冯玉祥二十万大军入豫,整个河南军事局面更加复杂。军阀混战必然会带来苛捐杂税与军事剥削,各方军队为在河南境内争夺地盘和扩张势力,往往就地筹饷,预征钱粮。如“1927年,靳云鹗部在河南期间,军费浩繁,饷需无着,靳当即饬其势力范围各县速摧征1930~1932年的钱粮,并于应交钱粮原数外每备加征现洋10元。1927年4月下旬,镇嵩军王老五的第七师师长李万如率部由陕州移防新安,即令该县人民交纳1929~1932年的粮漕,另交面粉3000袋;还派普通民衣2500套,上等民衣500套,鞋袜各3000双;另要妇女500名。限半月交清,逾期者军法从事。”(7)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军事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页。河南省1922年后开始预征钱粮,至1930年预征银已达3000余万两。军队派款征款的同时,当地“贪官污吏气焰极盛,握着全县政权,贪赃卖法,无所不为,每次借款派款,他们至少要卷一半入私囊”(8)《刘明佛对豫西工作视察报告——关于郑州、洛阳、渑池、陕州的工农运动及政治状况》(1927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1页。,人民负担更为沉重。
除了军阀混战及苛捐杂税外,民国时期河南旱灾频发,农村经济尤为衰败。1920年,整个河南境内发生特大旱灾,“安阳自春至秋,滴雨未见,传闻数百年未有此重灾。新乡是年大旱十多月,二麦歉收,秋禾全无,民食维艰。封丘五谷不登。7~9月间卢氏大旱。自6~9月间密县不雨,禾尽死,西至潼关,北达京师,赤地不止千里。7~8月确山不雨。内乡麦秋两季籽粒无存,10~11月后饿莩满野。”(9)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气象志 地震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1922年秋,信阳遭受旱灾,农田歉收,部分地区颗粒无收。(10)信阳县地方史志总编室编:《信阳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1927年河南大部地区又遭遇严重旱灾,众多农民走投无路,杞县、太康“粮食缺乏,贫苦的农民,只好锁着屋子,外出逃荒”;汝南的东北乡一带“百数十里,人烟冷落,骸骨遍野”;彰徳地区“秋收不够一半,种下麦子,又干死不生”。(11)《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形势、工农运动及党组织状况》(1927年11月2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330—331页。河南省旱灾频发不但使中小农民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而且更加速了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破产。
“要吃白面馍,杀死靳云鹗;要吃老绵羊,杀死冯玉祥”,(12)《河南目前政治状况》(1927年7月28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67页。这是流传于临颍一带的乡间童谣。童谣之下映照出河南残酷的社会环境与农民的艰难抉择。军阀混战、苛捐杂税、自然灾害频仍,乡村地区的农民为解决生存性压力,开始寻求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首先是拉伙结帮,投身为匪。河南省溃兵成匪的现象较为普遍,土匪数目众多,但是自20世纪初,动荡的社会使得相当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出于生计也不得不沦为土匪,与当地的官府相抗争。正如刘明佛在视察报告中所言“但豫西各县壮丁,都因战争关系而很少,就是有一部分无以为生的,也早已‘上南山’或‘吃粮’去了!”(13)《刘明佛对豫西工作视察报告——关于郑州、洛阳、渑池、陕州的工农运动及政治状况》(1927年7月15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40页。其中的“上南山”与“吃粮”皆指加入土匪的团伙;在豫北地区,甚至“彰徳全县的农民有打铁为枪上山为匪的趋势”(14)《河南省委通告第二十四号——目前政治状况及工作方针的决议》(1928年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42页。。结为土匪虽然暂时性解决了当事者的生存困境,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社会矛盾。被土匪抢劫、军阀压榨的破产农民再次面临生存性抉择,成为乡村社会中潜在的不安势力,形成恶性循环。其次,部分未破产的农民为抵抗军匪侵扰,常联结起来形成秘密会社,拥枪自保,红枪会、天门会等在河南盛行。关于此类秘密会社的兴起,中共中央曾有非常贴切的分析,“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15)《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16页。当然,中小农民组织秘密会社进行自发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至少使“有会之村落,兵匪皆不敢逞”(16)《豫省红枪会猖獗》,《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1月13日,第1版。。再者,受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影响,部分农民仍存在零散的抗捐斗争,至1927年下半年,河南省农民反抗苛捐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修武农民曾向代替军阀派捐的豪绅抗争,最终却屈于豪绅的讲和而未抗争到底,其他地区如扶沟、新郑、叶县、确山等也都曾酝酿过自发的抗捐斗争。(17)《河南省委关于河南政治军事形势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1月13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60页。未投身为匪或未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在乡间几乎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靠,但当军阀、贪官污吏之剥削过甚,威胁其生存,触及其忍受底线时,这些农民就会采取自发的抗捐斗争,尽管这种形式未必有效。由于生存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及乡村社会矛盾加深,秘密会社与部分农民的自发斗争渐趋暴力,“农民反抗征兵,反抗征马,杀卫役,杀村长(村长为冯走狗),已有好几处发出暴动”(18)《河南省委报告(节要)——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党内工作情形及枪会问题决议》(1927年9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83页。,“天门会且已经暴动占据河北数县,他们虽然是自发的无政策的,可是他们敢于暴动创造一个局面”(19)《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1927年9月2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109页。。河南地区的自发斗争便进一步发展成为自发暴动。
自发暴动是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若不及时加以引导,其性质很容易发生变化,成为中共革命的对立面或是归于泯灭。例如天门会,原本是由贫民组成对抗豪绅、进攻封建地主的组织,在政治觉悟方面甚至比其他枪会都要进步,但中共河南省地方党却疏于领导,天门会也就逐渐丧失了革命性,“走入帝王自为的路途”(20)《河南省委对于枪会的决议》(1927年9月2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105页。。中共河南省委在了解各方的暴动事宜后,逐渐意识到党在自发暴动中进行领导的重要性,认为“农民这一革命潮流,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必然陷于自发的凌乱的暴动,不遭军阀之屠杀,必走上政治的歧路,归于失败。”(21)《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118页。然而此时河南省委正忙于恢复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并未在引导自发暴动上添注过多精力。适时“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这一现象才逐渐被纳入中共中央的视野。中共中央认为乡村社会中的自发暴动是造成革命高潮重新高涨的重要条件,并在第十六号通告中明确要求各级地方党对自发暴动加以引导,要“发动农民间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的限度的组织性。”(22)《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98页。1928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各省革命暴动的议决案中,根据暴动条件,将河南省的暴动工作划为第二等区域,仅次于广州和两湖地区,并批评在此之前“全国各省工农群众的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斗争,党并没有充分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再次强调自发暴动的组织性以及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提出要“准备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最终达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效果。(23)《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95—110页。
在中共中央武装暴动政策之下,河南省党组织开始投身于引导自发暴动之实践。随着具体实践不断深入,中共河南省地方党由武装暴动的“领导者”成为武装暴动的“发动者”,甚至成为武装暴动的“创造者”,而无组织的、散乱的自发暴动逐渐开始演变成有组织性的自为暴动。一方面,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政策,强调党在自发暴动中的领导作用,提出工农自发的反抗与潜伏的革命情绪“全然是只待无产阶级的政党予以坚决的领导,与最大限度的组织不断的爆发起来,朝着总暴动的路上走,一致暴动夺取政权。”(24)《河南省委通告第二十四号——目前政治状况及工作方针的决议》(1928年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44页。通过地方党的领导,武装暴动的组织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暴动过程中,河南省党组织不但进一步明确暴动口号,如“不交租稞”“实行抗捐、抗税、抗粮、抗差”“不还豪绅地主的债”“工农兵联合起武装暴动”等,(25)《岳凌云、张芸生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73—174页。而且注重向工农宣传阶级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政治思想。这样一来,原本出于生存需要顺势而发的农民暴动,便增加了一层“自为”意识与政治意味。再者,河南部分市委、县委等地方党组织在进行暴动实践时,发现实际状况与上级期望存在落差,自发暴动的程度并不足以汇合为总暴动,所以其为达到暴动要求而“创造”暴动,此种情形同样是自为暴动之体现。1928年1月24日,焦作市委联合王旦丑、张铁头等农民党员在无详密规划的情况下,夺取沿途警察大刀,夜袭警察局,强行发动一起武装暴动。(26)《焦作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山东地区 河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600页。除此之外,唐河、潢川、临颍、郾城等地也有部分地方党沉溺于“黑夜袭击”而“创造”暴动的实例。(27)《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7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54页。因此,也无怪乎李维汉所言之多数革命斗争都是党在推动与领导的,甚至具有强迫命令的性质。
二、从自为暴动到暴动自为
在中共中央及省委政策影响之下,河南地方上的自发暴动逐步过渡到自为暴动。最初的自为暴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部分地区革命暴动局面,但所产生的总体效果却远远未达到中共“由零碎暴动汇集成总暴动”之预期,甚至出现了反作用,削弱了原有的革命力量,就连河南省委自己都承认过去是“作了些零碎的失败的工作”“未能得着城市乡村广大群众普遍的组织起来”。(28)《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7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50页。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这与“八七会议”及“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偏激进化的暴动政策密切相关。“八七会议”后,为因应中共中央的总暴动政策,河南省委三令五申河南各特委、市委与县委进行革命暴动。压力之下,河南各地方党组织“也无所谓定什么策略不策略,就知道以前‘等待政策’,是犯了‘机会主义’。现在应当发动群众自己单独来干了”,于是一系列的“大暴动”“小暴动”“秘密暴动”等自为暴动瞬时产生,又立刻衰落下去。(29)《河南代表关于豫南工作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24页。这不但助长了“盲动主义”盛行,党组织投入的革命力量也随之消耗殆尽。其二,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还存在很大落差,这使得初期的自为暴动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此时中共已经介入了工农自发暴动,并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展开领导,自发暴动也在具备一定组织性后演变成自为暴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革命暴动参与者的工农还普遍处于自在阶级,并未将自己所受的剥削压迫上升为理性认识,其暴动的目的仅在于达到经济要求。而作为革命暴动领导者的中共自身已经蜕变为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自为阶级,即便其已开始尝试向工农宣传政治思想,但短时间内工农政治意识无法得到大幅提高,二者之间难免产生落差。暴动参与者与暴动领导者在思想上不能同频,所以这种“不够成熟”的自为暴动注定会遇挫。其三,“有组织无计划”甚至“无组织无计划”等情况仍常发生。中共虽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一定的工运、农运经验,但实际上许多地方党并无系统的武装暴动经验。国共分裂后,面对如此迫切的革命暴动要求,部分中共党员在介入工农自发性运动时,往往将群众“呆板式”地组织起来,行动缺乏计划性,不顾及客观环境与敌我力量即进行斗争。如荥阳方面,地方党员在事先没有精密讨论、无行动纲领与计划、甚至无正式暴动组织的情况下即领导部分群众与区长斗争,结果自然不了了之。(30)《岳凌云、张芸生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82页。
由于初期的自为暴动不断遭遇挫败,加之中共六大又提出克服“盲动主义”与“军事投机主义”的要求,皆促使河南省地方党不得不反思先前的暴动策略,寻求更为规范、更具效率的革命暴动方式。首先,中共河南省委的革命暴动思维开始转变,不再急于催促各地进行暴动实践,而是更加注重统筹工作,有计划地统计各地组织力量、纠正各地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在整体统筹上,河南省委重新明确豫中、豫南、豫北的工作重点,力图摒除各地工作不连贯之弊端。1928年8月至12月,中共河南省委连续两次发布通告整顿内部组织问题,清楚地指出在前期革命暴动中地方党组织上存在的缺陷,“同志只有负[胡]干的精神,不能领导群众,党不能纠正一切错误的行动,只能跟着一部份急进的群众跑,反映出原始农民暴动的意识,完全失了领导作用。”(31)《河南通告第□号——关于组织工作问题》(1928年8月1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03页。不仅如此,省委还认为河南大部分党组织在支部工作、指导机关、各地关系、组织训练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河南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发布的改造党组织方针,将组织成份改造任务具体到每个县市,尤其是在组织纪律方面,各地方党部要“极力纠正过去脱离组织行动的危险倾向,必须运用组织来发动工作,经过纠正仍不改者,即与[予]以严重的处罚。”(32)《河南通告第□号——关于组织工作问题》(1928年8月1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14页。另外,河南省委决定清查全省的干部分子,并对全省各地工作人员重新分派。(33)《河南省委通告第×号——关于党的组织方针》(1928年12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441页。
其次,进一步强调兵士运动,开辟工农兵联合革命暴动之局面。在前期的革命暴动工作中,中共河南省地方党组织的目光主要放在职工运动及农民运动上,涉及兵士运动的政策少之又少,“过去的军事运动是零碎的工作,无整个的计划,甚至有许多党部,简直忽略了此项工作。”(34)《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7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57页。仅有的兵士运动也只在樊钟秀、任应岐、高桂滋、杨虎城等部队,占据河南主要势力的冯玉祥部却无任何兵士运动。河南省党组织认为,在后续兵士运动中应将冯部(即冯玉祥部队)放到首要位置,注意下层兵士工作,在非党群众中进行联络组织工作,加紧煽动,利用豫南、豫中加速士兵哗变,而且要组织兵士委员会、设负责人专门进行兵士运动工作。(35)《河南省委关于河南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1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96页;《河南省委兵士运动计划》(1928年),《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465页。而兵士运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等待总暴动机会到来”,以实现工农兵联合暴动。(36)《信阳中心县委书记贾子玉、中央巡视员郭楚声给确山区委的函——关于兵士运动与党的任务等》(1929年6月15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4)》,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58页。
再者,中共河南省各地方党组织着手完善宣传策略。中共六大后,在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环境之下,中共河南省地方党更加注重引导群众日常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因此对相关宣传策略也进行了调整:在经济方面,要迎合群众改善生活的需求,抓住粮食饥荒问题反对地主阶级,提出“大家不要逃荒不要当匪,起来分粮”“反对乱抢要有组织的分粮”“平粮放账不能使穷人有饭吃,要是有饭吃只有起来分粮”“工人兵士帮助农民分粮”等中肯且贴近实际的口号;(37)《河南省通告第十四号——关于粮食饥荒问题》(1928年),《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469—471页。在政治方面,“口号虽不要太高但决不是不要政治口号”,因此需要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宣传,侧重于启发群众阶级意识,打入群众进行煽动工作,纠正过去对群众“无宣传只命令”的错误,加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38)《河南省委关于河南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1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98页;《河南省委关于中央对河南工作方针决议案之决议》(1928年),《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448—449页。与此同时,中共河南省委要求党内进行理论学习,通过开设短期训练班、编印宣传大纲、出版党报与小报等方式改善“理论饥荒”现象,提高宣传动员能力。(39)《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7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59页。总体来看,这段时期内河南省党组织的宣传重心即在于由迎合工农经济利益逐步转移到启发政治、阶级意识上,逐步深化,以图弥合自在与自为之间的落差。
随着一系列调整与转变,中共在河南省的革命暴动也渐渐取得成效,尤其是红三十二师的成立以及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都昭示着河南省的自为暴动开启新局面。实际上,自为暴动也意味着暴动权力的下放,特委、县委等地方党组织灵活性增加,使其能够结合当地独特的社会环境,自主选择暴动方式,同时更注重组织技巧的运用,展现了革命暴动中的地方自主性。的确,地方党组织若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会有利于革命道路探索,然而这种自主权一旦得到扩张并超出合理界限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原来的自为暴动也会随之演变成暴动自为。
以商南暴动为例,1929年春,由于国民党的“清乡”运动,中共豫南特委、商城县委突遭破坏,特委书记余锡珍等人先后被捕,在商南地区交通堵塞,无法联系上级的情况下,中共商南党组织暂由鄂东特委领导。(40)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起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商南地区与鄂东地区地理位置上极具便利性,充分体现了商南地方党对中共中央“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灵活暴动要求的实践。(41)《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28年4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60页。徐子清、徐其虚、周维炯等人利用当地民团的社会关系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商(商城)罗(罗田)麻(麻城)地区形成了一股较为独特的革命势力。5月9日,商南暴动势力会师斑竹园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九十七、九十八两个团,此后在商城、固始边界游击,收缴地主武装,开仓放粮等,建立赤色割据政权。(42)《商城起义》,第9—12页。但由于红三十二师主要由民团哗变而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部分逃跑的军士、土匪等,成份较为复杂,因此出现了暴动自为,即不遵守组织纪律与土地革命的原则,自为打土豪、分田地的现象。1929年10月,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巡视豫南后,指出商城党组织存在“非组织观念与行动”的错误,批评他们在游击战争后“‘卖放豪绅’,下富农条子,有时侵犯到自耕农的利益”,(43)《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巡视豫南的报告》(1929年10月22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1930)》上,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188—190页。甚至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人员去城里的主要目的是“‘打土豪’拿东西”,缺少训练与纪律。(44)《郭树勋巡视河南商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1930)》上,第266页商南事变的发生也从侧面反映了河南省暴动自为之现象。由于商南事变牵涉甚多,情况复杂,且已有专门论述(45)相关论述可参见张飞龙、黄文治:《组织形态视角下中共“商南事变”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6期。,此处便不再赘述。
相较于河南省的四望山、大荒坡暴动,商南、罗南暴动的中共干部的“本土性”色彩更为浓厚,因此,其地方自主性愈加凸显,更易产生暴动自为的现象。大革命失败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联的情况下,河南的中共知识分子返回家乡,通过秘密串联等自觉行动,或是重新建立农民协会,或是利用当地社会关系嵌入民团、重塑传统会社等方式发展中共革命势力。不同的是,中共河南省委重建之后,派遣了王克新等外来干部入驻四望山、大荒坡地区。省委的有效领导贯穿于整个革命暴动过程,即使地方干部有权根据当地情形探索革命暴动方式,但在省委监督之下,其地方自主性并未特别突出。而商南、罗南暴动是在中共豫东南特委遭到破坏后,由鄂东特委领导进行的,河南省委始终“鞭长莫及”,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领导。省委对商南、罗南这种豫鄂边区控制力有限,使得这两地的本土干部拥有探索革命暴动之路的高度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一方面成功造就了“民团嵌入型”(46)概而言之,“民团嵌入型”革命暴动是指中共地方党组织通过派员嵌入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在其中担任相应的职位并发展党支部,待从内部分化瓦解后借助其下层武装队伍发起的革命暴动,商南暴动就为此类型。商南暴动与“会社重塑型”(47)概而言之,“会社重塑型”革命暴动是指为减少革命阻力,中共地方党组织利用红学会、黄学会等防匪的地方会社名目作掩护,直接创建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宣传革命思想,壮大党团组织,并依托于此发动的革命暴动。中共组织的所谓“会社”实质上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秘密会社相区别,可谓之通过重新塑造“会社”的途径以达到革命目的,河南省的罗南暴动即是此类型代表。罗南暴动的革命暴动范例,另一方面又在革命暴动后弱化了上级组织的权威性,使得“同志间感情关系大过于组织关系”,(48)《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巡视豫南的情况报告》(1930年2月1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1930)》上,第311页。加之群众的趋利性难以克服,所以频频发生暴动自为。暴动自为发生后,中共河南省委、特委陷入了一方面依靠武装队伍进行进一步革命暴动,另一方面又难以遏制混乱现象的两难境地,以至成为后期张国焘采取整肃措施的因素之一,最终不得不促使中共中央采取措施推动组织权力向地方伸张,以图削弱超出合理界限的“地方主义”观念,在自为暴动与暴动自为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三、从四大区域并重到以豫东南为中心
如果说中共河南省的暴动实践在纵向上经历了从“自发暴动”到“自为暴动”再到“暴动自为”的演进趋向,那么,在横向上河南省的暴动实践也经历了地域化演进,即从“省内四大区域并重”到以“豫东南”为革命暴动中心区的趋向。
1927年8月,在中共中央确立全国实行总暴动的方针后,中共河南省委紧跟中央决议,于9月份制定了暴动工作大纲,将河南省革命暴动分为四大区域,即豫南区(管辖信阳、罗山、息县、光山、潢川、固始、商城、汝南、确山、泌阳等);豫北区(管辖彰徳、临漳、汤阴、修武、辉县、卫辉等);豫东区(管辖杞县、淮阳、扶沟、考城等);豫西区(后改为豫中区,管辖郑州、荥阳等)。(49)《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1927年9月2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110页。豫南区主要以确山、四望山的农民协会为基础发动斗争,豫北主要以天门会为势力进行革命暴动,豫东区主要联合杞县、扶沟进行革命暴动,而豫中则以郑州等地的工人运动为中心。(50)《河南省委关于河南军事情况和工作计划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39—241页;《河南省委政治报告》(1927年11月1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71页。在河南省委最初的计划中,各区的暴动工作与中心县份虽各有侧重,但无论从组织上各区成立的暴动指挥机构特别委员会来看,还是从各区暴动资源分配来看,此四个暴动区域都是处于平等地位。1928年1月中下旬,河南省委根据工作形势,在原来四大暴动区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划分,成立豫南、豫中、河北(即豫北)、豫东、豫西五大区域。相较于前,这五大区域各自所辖县份仅略有调整,但各区的任务分配却产生了新变化。河南省委要求豫南区革命暴动应更迅速地发展,豫中应“组织革命群众巩固豫南的割据局面,促起整个河南暴动的实现”,而豫东“尤其注重开封和杞县,使动摇统治阶级的中心作各处暴动的牵制”。(51)《河南省委通告第二十九号——目前河南形势与我们的策略》(1928年1月18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64—65页。可见,豫南区的暴动地位开始有所上升,而豫中、豫东两大区域由先前的独立暴动逐渐变为“配角”。至2月份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委已明确提出“扩大信阳、确山、汝南的暴动,加紧南五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信、确取密切的联络,创造豫南暴动割据的局面,以为发动河南革命潮流之中心区域”,(52)《河南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决议案》(1928年2月3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88页。此时,以确山、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地区革命暴动地位已成为五区之首。另外,中共河南省委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另一重要举措便是组织南五县(光山、潢川、商城、固始、息县)特委,(53)《河南省委关于政治形势及省三次代表大会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 3月23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27页。同年9月,省委又将其重建为豫东南特委,这为河南省革命暴动中心向东南方向转移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后续革命暴动实践过程中,南五县的革命暴动效果愈加突出,尤其是1929年5月商南暴动成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潢川、固始、光山等地的武装暴动进一步拓展了红色区域,与商城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豫东南地区已从豫南区域剥离独立出来,河南省的革命暴动中心也正式转移到豫东南地区。
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实践地域化演进趋向并非无故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相较于其他区域来说,中共在豫南及豫东南方面工作根基更为强韧。根据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在1927年10月份,以确山为中心的豫南区便组织了约一万六千人、一千二百条枪、七百手榴弹的农民自卫军。(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河南军事情况和工作计划给中央的报告(节录)》(1927年10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山东地区 河南地区》,第399—400页。暂且不论省委在报告中对农民自卫军与武器装备数量是否有夸大成分,但这至少能体现出豫南特委在此地区具有一定的工作成效,而像豫北、豫东等区域,革命暴动工作根基相对薄弱。如豫北卫辉至1928年1月份仍无政治工作,党组织对工运未积极领导,农运方面工作基本没有;(55)《河南省委致卫辉县委的信(第三号)——对卫辉县委工作报告的意见》(1928年1月2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2页。豫东方面,党的力量一向薄弱,“对民众无多大影响,因此一般民众,尚不知走上革命的道路”“虽然作了一些工作,只是领着群众与豪绅打官司告状”。(56)《河南省委关于河南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1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86—387页。其次,河南省整个政治环境对革命暴动实践地域化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民党及各杂色军阀的统治情况来看,豫东区被冯玉祥占领,豫西区为豫陕咽喉,在政治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有“大河南主义”的军阀樊钟秀觊觎豫西,而且“冯常以重兵驻此,防范极严,各种布置亦比较周密,在农村中仍未改变豪绅封建式的统治。”(57)《岳凌云、张芸生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67—168页;《河南省委关于河南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11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387页。豫南区不属于冯玉祥部势力范围,农村环境较为宽松,中共嵌入豫南社会阻碍相对较小,也更有机会在此地“站稳脚跟”,所以,中共在河南的革命暴动中心于实践中逐渐向南部转移。最后,由于豫东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鄂东北地区接壤,中共鄂东北特委和黄麻暴动所成立的红三十一师对豫东南的革命暴动产生辐射性影响,就连河南省委都承认“河南工作在豫南一带与湖北比连的地方较有基础,同时直棣、安徽、山西工作都比较落后,而河南豫北、豫东、豫西的工作亦多比较着差。”(58)《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7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51页。因此,河南省内的革命暴动向东南方向发展,与鄂东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不失为大势所趋。
另外,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地域化演进产生了一系列隐性反应。如暴动主体在演进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即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暴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变为以农民为主体。从豫北、豫南、豫东、豫西四大区域划分来看,豫北区是整个河南工业与工人最集中的区域:彰徳、卫辉纱厂工人众多,郑州不但有裕丰纱厂的工人,其余小手工业者也较为丰富,焦作有福中公司的煤业工人,开封有兵工厂、造币厂、蛋厂工人等,另外,陇海铁路横贯豫北且与京汉铁路在郑州交汇,河南的路工也大多聚集于豫北。在连年战争、交通堵塞、捐税奇重等因素影响下,河南“新式产业的工厂,多数停业或裁减工人,而铁路工人兵工厂工人欠饷数月至数十月之久;小手工业者亦频于倒闭;加以物价飞腾,生活程度继涨增高,一般劳苦的工人频于饿死的境地。”(59)《河南省委关于工人运动决议案》(1927年10月28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06页。因此,中共河南省委认为工人的“革命情绪是蕴藏待发的”,遂将工人运动的中心置于豫北区,且一再强调工农联合,要求“在工会中提出农人方面的问题,在农民协会中提出工人方面问题,使彼此了解相互的关系,以坚固联合战线”等,力图实现工人革命暴动与农民革命暴动齐头并进。(60)《河南省委关于工人运动决议案》(1927年10月28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11页。但是,地方上的暴动实践却并未如省委所愿,京汉铁路分会、陇海铁路分会、纱厂工会等一般为军阀及其“走狗工贼”所把持,工人们虽怨恨军阀的经济压迫和白色恐怖,但是他们往往处于军阀势力的集中区域,难以有革命暴动之可能。(61)《河南省委政治报告》(1927年11月1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第271—272页。工人暴动发动了半年,其结果是“除了卫辉纱厂工人在几次斗争后,有点基础外,其余是一塌糊涂。”(62)《河南省委关于政治形势及省三次代表大会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3月23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138页。以工人为主体的暴动实践效果本就低于以农民为主体的暴动实践效果,且随着河南省革命暴动中心逐渐转移到农村土地较为集中的豫南、豫东南,工人在暴动中的主体性进一步削弱。尽管中共河南省委批评地方党过于偏重农民运动,并不断重申“中国的土地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起来,革〔命〕才能得到成功”“河南土地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放在工人肩头上,才能推动河南的革命和保证河南革命的成功”,(63)《河南省委关于河南职工运动的议决》(1928年8月5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第288页。但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农民依旧不可避免的成为暴动主体。从四大革命暴动区域并重到以豫东南为中心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共革命道路探索过程,即革命重心由国民党统治严密的白区逐渐过渡到中共建立的苏区,由全省范围逐渐过渡到省份边缘交界地带,由城市革命暴动逐渐过渡到农村游击战,直至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道路。
结语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演进趋向都与地域社会结构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河南社会处于失范状态,军阀林立,土豪劣绅纷起盘剥压榨,部分农民在生存性压力下主动与地方资源既得利益者进行抗争,这种潜在的对抗传统地方政权的因素为中共介入领导提供了基础。中共河南地方党在介入并领导革命实践时,对于武装暴动方式的选择也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此过程中,受制于当时河南省乃至整个中国的革命政治环境,直接领导暴动的地方党并未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中共六大前,以豫南特委为代表的地方党屡次与河南省委产生争执,甚至私自违抗省委的暴动“命令”,(64)此处具体可参见王丽彩、黄文治:《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因应(1927—1928)》,《苏区研究》2021年第5期,第42页。初步体现了革命暴动中的地方自主性。但由于此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初现端倪的地方自主性很快被盲动主义潮流掩盖。中共六大后,从中共中央乃至地方基层都开始纠正革命暴动中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这种政治环境下,地方党有充足时间策动暴动,再加之省委与商南、罗南等地方党处于悬隔状态,豫东南地区的地方自主性再次展现出来。地方自主性不仅纵向上推动中共由“自发暴动”向“自为暴动”演进,并在一段时间内使革命暴动走向成功,横向上也促进了河南省革命暴动实践地域化演进,使其逐渐集中于豫东南一隅,为后续鄂豫皖苏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后续地方自主性的无限制扩张却弱化了上级党组织的权威性,将地方利益置于党的纪律之上,在地方上造成“暴动自为”等不良现象,对革命道路的推进产生阻碍,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管控地方,进而削弱过强的地方自主性。
实际上,河南省的革命暴动实践虽有其独特的演进过程,但也仅仅展现了中共革命的一个维度。如何将处于社会失范状态中的农民有序的统合起来,纳入组织化管理轨道,使其在合理限度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甚至将政治诉求内化为行动原则,不仅是当时中共革命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也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