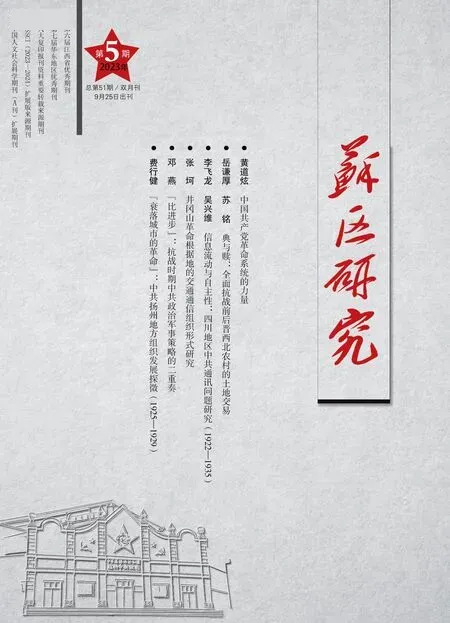信息流动与自主性:四川地区中共通讯问题研究(1922—1935)
李飞龙 吴兴维
保有顺畅的沟通渠道、建立稳定的通讯联系之于中共发展壮大而言,至关重要。1925年4月,在中共四大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指示,强调通讯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性,“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7—1949.9)》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不过,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周围崇山峻岭,地形封闭,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极为不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加之护国战争后,川内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严防中共通讯往来,故自1922年四川共产组织成立伊始,通讯工作就困难重重。面对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的不利因素,四川地区中共组织先是借助邮政寄递、人员往来等外在方式,后又设立了专门的内部交通机构,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息、人员和物资的往来,展示了中共在夹缝中生存的能力和极强的韧性。
对于党内通讯,学界已有涉及,如王奇生在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广东中共地下党时注意到了党内交通和情报传递问题(2)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24—36页。,王士花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网络(3)王士花:《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工作》,《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第57—63页。,周俊还专门指出了党内交通研究的不足及改进之处。(4)周俊:《组织的血脉:党内交通研究的再检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45—50页。上述讨论无疑深化了党内通讯制度研究。但是,对于中共中央联系较弱、自主性较强的边缘地区,还少有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础资料,尝试回答四川地区中共早期组织通讯工作的具体运转、所遇困境以及制度生成等问题,进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意识及其价值。
一、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外部通讯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四川地区共产主义组织是以一种网络状方式成长起来的,属于多中心的网络状、扁平型发展模式,如最早建立的成都、重庆、泸州等党团组织,多并行不悖、多水分流地自行生长。这一时期,四川内部各地方党组织间虽然交集不多,但均与中央保持不定期的通讯联系。
邮政寄递是四川地区早期中共组织与上级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在四川中共组织创建初期,组织成员较少,规模也不大,加之革命环境相对宽松,使得依靠邮政寄递进行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等革命活动成为可能。从1922年10月,自成都、重庆、泸县等地方团组织相继成立开始,主要负责人便通过邮局,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各地筹建情况,并随信附列了各地通讯处,以便与中央加强联系。四川地区中共的各类宣传品、各笔运作经费,也是通过邮局传递的。1926年1月,重庆团地委先后两次向中央报告,分别查收了由中央寄来的98—102号通告(5)《团重庆地委致团中央报告(第3号)——关于通讯地址和收到刊物的说明》(1926年1月2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3页。,以及100份《青工运动》(6)《团重庆地委给团中央的信——查收刊物、款项事》(1926年1月29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39页。。同年3月,重庆团地委还陆续收到团中央汇寄的30元和20元款项,以此作为团组织开展工作的活动经费。(7)童庸生:《童庸生向中央的报告——重庆党、团地委组织分工情况》(1926年3月5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73页。显然,在四川中共组织建立的早期,党内信件、各类宣传品以及活动经费,均能通过邮政传递。这些文件、报刊、经费成为四川党团组织发展的行动指导和物质基础。
大革命失败以后,四川中共组织在困境中得到发展,此时邮政传递仍是地方党组织之间、组织与上级沟通的主要渠道。1927年11月,四川临时省委整理和统计了10月份的收发信件情况,其中收入信件总数为144件,内含报告70件、闻讯11件、请示34件、其他29件;发出信件总数为103件,内含交给机关65件,交给同志38件。(8)《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务工作概况》(1927年11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32页。其中不乏邮政传递的信件。1929年4月,临时省委表示,尽管重庆当局严格检查密信,临时省委的第一号报告仍可通过邮寄送达中央。(9)《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3页。1933年初,四川省军委书记程秉渊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后中央便邮寄来一封指示四川党目前任务的信件。同年3月,团四川省委亦提及一月前的工作报告已由交通员寄来。(10)《团四川省委致团中央报告(新编第4号)——各级团部及省委近一月来工作情形》(1933年3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238页。由此可见,即便大革命失败后,邮政寄递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方式,一直为四川中共组织所使用。
然而,频繁的邮政通信和传输物资,以及四川地区中共组织力量的增强,也引来了四川军阀的警觉。为阻断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信息往来,遏制川内中共组织的发展壮大,四川各派军阀对邮政往来之信件进行了严格检查。1925年3月,涪陵团支部发现,其通讯处收件人“李用三”之名已被觉察,收到的18号通告“信封全开”。(11)《团涪陵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第6号)——关于通讯问题》(1925年3月22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26页。1926年1月,重庆团地委觉察到,团中央不仅突然变更了通讯地址,收到的封信和包裹也已被人拆阅。(12)《团重庆地委致团中央报告(第3号)——关于通讯地址和收到刊物的说明》(1926年1月2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3—4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更加大了对邮件的检查力度,同年7月,在南京戒严司令部下特设了邮政检查委员会,检查往来一切邮件,尤其严格检查“关于共产党及帝国主义者宣传之件”。(13)《南京戒严司令部检查邮政委员会抄报〈检查邮政暂行条例〉致中央宣传部函》(1927年7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8页。1931年,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清共委员会”,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检查邮件,寻迹查号,追踪缉捕”。(14)蒋维彦:《军阀对中共合川地下党的破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合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6页。四川军阀严查邮政寄递,无疑给处于成长期的四川中共党组织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为了躲避四川军阀对邮政通信的追查,四川中共组织开始启用秘密通信方法,1927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发布通告,决定按周发行《政治通讯》,并用米汤印写以便递寄,各地收到后需用碘酒擦出,方能阅读。(15)《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23号)——发行〈政治通讯〉加强政治学习事》(1927年10月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78页。1928年5月,临时省委常委刘坚予上报中共中央,建议中央此后寄发通告,以秘密方法书写。借助于邮政寄递的秘密通信方法,曾短暂地掩护了中共组织间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与经费输送。直到1929年4月,因重庆军阀检查密信,四川中共组织与中央约定的秘写法“已为敌人所发觉”,省委“不敢再用前秘写法做报告给中央”,秘密通信方法遂暂时中断。(16)《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页。事实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破解这种秘密通信方法并非难事,1927年9月,四川临时省委就曾向中央报告,“闻邮(17)邮,即邮局用水浸火烤及涂海碘酒三法检查”来往信件,经尝试用黄碘酒即可擦出,故建议中央“另约其它药水”。(18)《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最近政治组织状况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73—74页。由此观之,四川中共组织与四川军阀在秘密战线上的博弈和斗争,从未停止。
除邮政寄递外,四川党组织内部、四川地方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还可通过人员往来实现循环流动。即一方面通过巡视工作的推进,依靠巡视员传达上级指示或向上级汇报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依靠党组织的人员流动,由组织成员顺道携带消息、文件、经费等。
巡视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传达上级指示,指导地方工作,促进信息流通。1931年6月,在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固定巡视员的通知中,强调“要根本转变过去公文形式的指导而成为实际有效的活的指导”。在中共中央看来,作为“活的领导”的巡视员制度,可以实现面对面指导,破除官僚主义。同时,由于“采用活的领导,极力减少文件的来往”,客观上也造成了以巡视替代文件实现信息互通。(1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7—1949.9)》第8卷,第408页。四川地区巡视工作最早是在团组织中开展的,1926年3月,重庆团地委书记童庸生向团中央报告了泸州、江津、荣昌团组织建设的巡视情况,其中泸州团组织将近30人,江津已成立团组织(共13人),荣昌团组织未能建立。(20)童庸生:《童庸生向团中央的报告——巡视泸州团及江津、荣昌团情况》(1926年3月1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75—76页。此后,无论是四川团组织还是党组织,派遣巡视员成为常态。1928年5月,为加强对川东的领导,四川临时省委派遣刘坚予至川东巡视。1929年8—9月,四川省委由成都迁回重庆后,又派遣刘坚予巡视下川南,程秉渊巡视上川南,陈惠巡视川西。1931年5月,团四川省委还计划固定两名省委巡视员,轮流外出巡视,从7月起巡视中心县。同时,四川地方党组织还接受中共中央的巡视,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派小元到四川巡视并改组省委,1934年1月,中央巡视员徐平抵达成都,指导四川省委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21)《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第56、4页。四川中共组织的内部巡视和中央对四川党组织的外部巡视,共同支撑了四川党组织内部、四川地方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信息互通。
但是,巡视制度以及巡视制度所附加的信息互通不甚理想。1929—1930年,四川省委委员李宽怀巡视川东时,因未能完成巡视任务,“应去巡视的不去巡视”,导致四川省委上报中央,要求对其处分。(22)《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请示对李宽怀错误的处分》(1930年4月2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82页。1932年,四川省委发现,巡视员训练培养不够,不能很好完成巡视任务,只能“走马观花”解决零碎问题。(23)《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7月到“九·一八”工作情况)》(1932年9月25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06页。无可否认,巡视力度不够、覆盖面有限,固然有巡视员能力的问题,但仅将此归因于巡视员自身的工作态度和自身能力,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片面的。严峻且极为危险的外部环境、巡视制度初建时期的不成熟、地方党组织发展经费的匮乏以及人员数量的紧缺,都是巡视制度实践成效打了折扣的重要原因。以经费和人员为例,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曾感慨,“省委经费困难到了极点!来源既少,需要支出之处则甚多,是以各种工作均感到极大困难”。(24)《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31号)——节约经费增加收入办法》(1927年10月25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39页。1929年,四川临时省委在强调巡视工作重要性的同时,认为是“经费及人力的关系”,才使巡视工作“做得很少,而且没有什么成绩”。(25)刘方澈:《四川临时省委刘方澈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组织工作情况》(1929年1月15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25页。1933年,四川中共组织在总结全川巡视情况时,亦抱怨巡视人员匮乏,“两年以来培养出来的新巡视员不上五个”。(26)《四川省委关于全川党的组织工作决议》(1933年8月16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455页。四川中共组织的感慨和抱怨,都直接说明巡视制度实践的困境。
另一种依靠人员流动来实现信息互通的方式,是组织成员顺道携带消息、文件和经费。1922年7月,为寻求团中央的指导与帮助,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王右木离蓉抵沪,10月返回四川,并随身携带团章和团中央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24年5月,杨闇公抵达重庆,与童庸生接头并讨论团组织发展后,于6月初乘轮船东下,该月中旬抵达上海,并与中央取得联系。(2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党史人物传》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1928年4月,四川省委派遣刘坚予前往上海汇报四川中共组织在“三九”事变中遭到的破坏,并委托刘坚予携带省委二月扩大会议的多项议案,请求中央指示。(28)《四川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及省委各项工作的现状与计划》(1928年8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43页。1929年2月,考虑到邮政寄递的潜在风险,决定由临时省委委员刘远翔顺道携带上报中央的第二号文件。(29)《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第55页;《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页。
不过,依靠组织成员顺道携带消息、文件和经费,必然会受到人员流动频率的影响,譬如四川党组织派人去中央时,多是主动寻求上级指导、参加党代会或组织遭到破坏的汇报,这种人员流动的频率并不高。加之“蜀道难”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人员往来并非易事,1924年7月底,杨闇公由沪返渝,在归途中,杨闇公深感“吾川旅行之不便,真是匪言可喻”(30)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编辑整理:《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尤其在入川的地界,船行的异常缓慢,日走三四百里,常有盗匪出没。(31)《杨闇公日记》,第146页。杨闇公此次返渝,历时半月之久。
应该说,邮政寄递、人员往来是四川中共组织内部以及四川地方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的主要渠道,但同时,还有一些辅助方式。其一,是无线电报。中共使用专门无线电作为信息互通,时间较晚,直到1929年秋,才在上海大西路复康里9号租了一栋三层楼,安装了第一部秘密电台。1930年1月,中共中央与中共南方局试行了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讯,是为无线电技术使用的开端。由此判断,在此前后,四川地方党组织不太可能拥有独立的无线电设备。不过,没有独立的无线电设备,中共地方党组织仍可借用军事机关或者民用电报。1929年2月,四川临时省委曾向中央提出使用军用无线电传递重要消息,并告知自己的收电地址在成都,需党中央在上海或者南京找到军事机关收电和发电。依据军用电台、收电地址等关键信息,可以推测,这是四川地下党打入军阀内部,获得了使用军事无线电设备的便利。同时,四川中共组织还可使用民用电报,“三三一”惨案后,中共中央曾指派傅烈、周贡植等五人组成临时省委,由武汉到重庆并重建四川地区中共组织,在武汉至重庆途中,傅烈等人曾给武汉发去“两信一电”,不过因武汉方面地址变更未能收到。(32)《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第51页;《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最近政治组织状况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73页。这“两信一电”中的“一电”,极有可能是通过民用电报所发。需要强调的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无论是通过军事机关还是民用电报,都十分危险,前者由于高度机密,消息很容易被破获,后者因为没有加密,消息极可能泄露,因此使用频率极低。
其二,是根据报纸刊物以及民间传闻。这种情况多出现在组织彻底失联的情况下。1929年7月,四川省委指责第七混成旅在兵变工作中行事匆忙,不待省委回信指示便擅自行动,发动后也不给省委汇报,因此省委只能在报纸和传闻中得到部分消息。(33)《四川省委通讯第5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中错误的批评及今后工作的指示》(1929年7月1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11页。当然,由于战时紧迫,无法及时汇报,也是兵变和暴动中的常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四川省委要获取消息,进而判断形势,唯有根据报纸刊物以及民间传闻了。
总的来说,在四川中共组织成立初期,邮政寄递、人员往来是四川中共组织内部以及四川地方与中共中央之间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的主要渠道,无线电报、报刊和民间传闻是辅助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四川地区中共通讯的多维渠道。不过,这些渠道都是借助于近代以来搭建的通讯技术体系,抑或人员往来的携带,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临时性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讯体系极易暴露,因此建立中共领导下的专门的通讯网络,就显得尤为关键。
二、四川地区中共党内通讯机构与路线
从1922年四川中共组织建立开始,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止,四川中共组织都没有创建自己的通讯机构,这主要是因为邮政寄递、人员往来尚能勉强支撑中共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以及经费输送。当然,这并不是说邮政寄递、人员往来没有问题,实际上由于邮件延误以致信息传递不能及时之事常有发生。1925年3月,涪陵团支部就报称,每回接得中央之各种纪念运动指示,如“二·七”“三·八”等纪念运动,常是指示信到达时,运动时间已过。(34)《团涪陵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第6号)——关于通讯问题》(1925年3月22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6页。同年12月23日,泸州地方团组织在报告中也提到,因川内邮传太慢,曾多次接到中央“某事变之通告而某事变日期已过”,例如投考黄埔军校事宜。(35)《泸州地方团向团中央的报告——最近校务情形》(1925年12月23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48页。显然,此类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四川地域广袤、山高路远,交通工具落后所致。简言之,此时四川中共组织虽偶发邮政文件遭到拆封之事,但自然地理、交通工具,应是邮政寄递、人员往来所致信息滞后的主要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大量中共党员惨遭逮捕和杀害,利用传统邮政寄递、人员往来实现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不论是文件暴露和人员危险程度,还是信息传递和扩散速度,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为此,1927年8月21日,在《中央通告第三号》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建立单独的党内交通机关和交通网,要求:“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36)《中共中央通告(第3号)——关于建立党内交通网》(1927年8月21日),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同时,第三号通告还对全国交通网的职责、组织构成、交通员工作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部署。至此,全国性统一的交通网络逐渐在各地建立起来。
在《中央通告第三号》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也是在岌岌可危的斗争形势下,为了分担信息、文件的传递压力,四川省委着手建立党内交通机关。1927年8月,早在四川临时省委成立之初,就在省委秘书处之下设置了两名交通员,其中一人负责接洽各地组织并作谈话记录及收取信件,另一人负责川内各地的交通联络及发出信件。交通员每日上下午须到各通信处、接洽处收取文件两次,寄发在秘书处领取的应发文件,紧急文件要做到随收随送,不拘定时间。(37)《四川临时省委秘书处组织及办事细则》(1927年),《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81—383页。此时交通员的职责主要为书信和文件的收发,并未涉及专门的信息网络和人员通道。
1927年9月,在四川临时省委组织部的计划中,决定正式“设立秘密的交通处,传递各种文件及消息”。(38)《四川临时省委组织部工作计划》(1927年9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9—130页。到11月,四川临时省委进一步明确了省内交通路线,决定将四川划分为两个区域,共设置两名省内交通员,一人由合川从川北往成都,沿岷江至叙府、自井、泸州、合江、江津、返重庆,另一人沿扬子江下经长寿、涪陵、丰都至万县,再由宣汉、大竹、邻水返回重庆。(39)《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务工作概况》(1927年11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7页。通讯机构的设置和交通线路的规划,可视为四川地区中共专门交通网的开端。随着中共党内通讯机构和交通线路的建立,四川省内文件、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有了很大改善,至1929年底,四川省委已感受到党内交通的便利,“巡视制度与全省交通网,已经开始建立,上下级关系比较从前亲密得多”。(40)《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1929年11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288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交通员数量还是交通路线规划,此时四川中共的交通网仍处于初创阶段。
1930年3—5月,四川地区中共组织内部接连出现叛徒告密事件(41)《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第57页。,不仅使四川省委遭受重大破坏,叛徒还“每日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以致传统依靠邮政寄递的方式无法存续。基于外部斗争环境的变化,1930年12月,四川省委开始升级党内通讯机构,成立了省交通总处,并征调候补交通员3人在渝备用,计划建立三条干线交通,同时省交通总处还帮助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建立了各区交通线。到1931年2月,川西已走过一次,因潼川交通机关被破坏,不能到达成都;川南(由渝至荣昌再至自井)走过4次,均到荣昌站,因“荣昌县挪用交通费致未达自井”;川东线(渝—万)走过2次,其中一次因万县机关被破坏未能接头;渝顺线亦派遣交通员前往,可直达顺庆。(42)《四川省委致长江局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1931年2月1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26—432页。到1931年12月,四川地区的中共交通网已实现覆盖并顺利运行,据省委统计,自该年8月以来,川南自贡、泸州交通已来回5次,川北顺庆4次,川东重庆5次,川西南路2次,下东梁山1次。(43)《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政治路线和工作作风的转变》(1931年12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50—551页。此时,四川中共的党内交通线已不再是1927年底规划的两条路线,而是分别可抵达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各地,虽行走之路极为艰辛,但1931年底的党内交通线路显然更加密集且合理。
同时,四川中共组织依靠党内交通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927年11月,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收到交通员贺学礼带回的中央通讯、蜀字公函及8—11月经费,之后省委又依靠交通员将四川临时省委的各类报告、通告、计划书、宣传册等文件送抵中央。(44)《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信——关于干部、经费、宣传与军训材料的要求》(1927年11月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49—350页。不过,1928年10月,四川中共组织因地方军阀的大举搜捕,以及团省委内部叛变告密,四川党团省委机关均遭严重破坏,党内交通机关亦无法正常运行。为保持与中央的通讯往来,四川省委计划以湖北宜昌交通处为枢纽站,请求中央将汇款及文件暂交宜昌交通处,再由省委派人取回。(45)刘坚予:《刘坚予给中央的报告——党团省委被破坏情形及恢复工作》(1928年10月23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95页。该年11月,四川临时省委派宣传部主任刘荣简赴中央报告工作,并正式在鄂西宜昌建立交通机关。(46)《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临时省委的组建与川战爆发情况》(1929年1月1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59页。从此,宜昌交通处一度成为四川与中央保持通讯、输送物资的中转站。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1933年2月川陕苏区的创建,四川省委与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也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并成为中共中央联络川陕苏区的中转站。1933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文俊,将搜集到的军阀田颂尧29军的作战计划、军事地图等情报,转送到盐亭联络站,再由交通员经南部县最终送达川陕苏区。(47)唐宏毅、杨重华:《配合红军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三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7页。同年8月,中央特派员廖承志、交通员杨德安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奉调赴川陕苏区工作,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三台,后经盐亭、南部、阆中、苍溪交通站,在各地交通员护送下,于10月成功抵达川陕苏区。(48)唐宏毅:《廖承志赴川陕苏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2辑,内部发行,1994年版,第36—42页。1934年3月,四川省委还准备派遣两名地下党(其中一人当过兵,另一人是交通员),护送一名邮政局长前往川陕苏区,并计划输送一批失业工人、文化工作人员以及专业人才去苏区。(49)《四川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最近工作及中江、邛大党的状况》(1934年3月1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85—186页。经由交通线的大规模人员流动,说明了四川省委与川陕苏区之间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性。至1934年,四川省委与川陕苏区之间已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第一条由成都经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渡东河到达川陕苏区,负责人员输送;第二条由成都过三台(柳池)、盐亭、富村驿、南部(建兴)、阆中、苍溪,渡东河到达川陕苏区,负责情报传递;第三条由成都途径三台(泸溪)、柳池、盐亭、苍溪,最后渡东河抵达川陕苏区,负责白区失业工农群众的运送。(50)何薇、尚恩怡:《对1933年由成都进入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的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第76页。三条交通线均有专人负责且分工明确,足见四川省委与川陕苏区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
党内交通的创建和扩展,自然意味着交通经费投入的增加。1927年9月,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了8月份的经费预算,其中交通费为100元,约占总经费的15%。(51)《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最近政治组织状况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85—86页。不久,省委又上报了该年11月至1928年1月的预算,其中川汉交通费每月130元,省内交通费每月80元,并强调省内交通员只能“取步行或坐船,若全坐轿,此款当不足”。(52)《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务工作概况》(1927年11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6—337页。而实际上1927年8至11月中共四川省委接收中央下拨的交通费总额为260元,12月交通费100元。显然,中央下拨的交通费用并不能满足实际所需,特别是随着川汉交通线路投入运作,四川中共组织呈报的交通费预算也水涨船高,增加至230元,约为总预算的24%。(53)刘坚予:《四川省委刘坚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务状况》(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36、239页。但到1931年,由于四川中共组织工作内容增加,新添了巡视、工运、兵运等,挤压了交通费支出,故在省委提交的8月份预算中,交通费降为120元,约占总预算的15%,较1928年有明显下降。(54)《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政治路线和工作作风的转变》(1931年12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53页。
不过,经费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1927年12月,四川临时省委上报中央,“经费一钱没有,终日只是借债度日,工作几乎要无形停顿起来”,不仅无法递送省内的消息和文件,连给中央的“十一月报告,无钱派交通送上”。(55)《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请解决军事人才、党团省委关系、学习材料、经费等问题》(1927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79—380页。1928年5月,刘坚予感叹:“全靠省委工作同志到处东挪西借,勉强维持,无日不在筹款,无事不受经费之牵制(如前次派交通到中央,因无轮费,报告做好后,耽搁一月多不能动身)。”(56)刘坚予:《四川省委刘坚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务状况》(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36页。没有交通经费,不能坐船出川向中央汇报,足见四川地区中共党内交通建设的窘迫。尽管多次呈报中央,四川省委的财政困境并未因此得到有效解决,1931年7月,省委再次直言已欠债约1500元,但各地工作又不能中断,尤其是交通和印刷工作。(57)《四川省委给中央的信——关于经费、干部、器材等的要求》(1931年7月2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01页。1934年3月,省委报告中央:“川委目前工作展开,特别健全交通、巡视和训练工作,经费上感觉十分困难。”(58)《四川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最近工作及中江、邛大党的状况》(1934年3月1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88页。长期以来的经费匮乏,不仅导致党内交通工作难以保障,其他日常活动也被严重影响。
此外,在动荡的时局下,党内交通还会出现信件丢失和贪污行为。1933年12月,为了指导遂安暴动,交通员需往来于四川省委和遂安县委两地,便出现了交通员丢失省委指示信的情况,无疑增加了暴动被破坏的可能性。1934年7月,俞儿(交通员,后叛变)在负责四川地区中共交通工作时,曾从上海获取80元法币的活动经费,到成都后需兑换成川洋(四川本地货币),约为90元,但他却仅给交通人员川洋80元,多余款项未交付组织,若他“自己失掉一元钱又要党补他”。(59)《四川省委向中央的报告——省委遭受破坏的教训》(1934年7月24日常委会通过),《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330页。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交通员卷款潜逃之事,1930年底至1931年初,在川西交通线的开辟中,就出现过两次交通员的卷款潜逃。(60)《四川省委致长江局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1931年2月1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32页。当然,信件丢失非主观意愿,拿走余款属贪污行为,卷款潜逃是见利起意,并不应归因于党内交通制度本身。
综上,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障川内以及四川与中央之间文件、信息、人员以及物资流动的畅通,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四川地区中共组织逐渐建立了多条党内秘密交通线,此举无疑缓解了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的压力,有利于四川中共组织研判内外环境、整合多方资源,维系了川内中共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不过,受困于人员和经费的掣肘,文件、信息、人员以及物资常常无法准时送达,影响了党内交通的顺畅互动,以致仍需外部邮政寄递和人员往来作为补充。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这种通讯形势,一方面隔离和断裂了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联系,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一样,这种隔离和断裂,也保留了地方党组织发展的自主性,使其可在四川军阀的严厉政策下艰难成长。
三、通讯与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
在中共革命早期,四川地区的中共组织并不处于革命版图中的核心位置,也不像贵州地区一样,是在与上级失联,处于断线状态中自主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恶劣的自然和政治环境下,无法实现与中共中央的正常联系(也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和基层党部之间),属于时联时断的情况。那么,在上级机关鞭长莫及,无法提供实际指导之下,就产生了上级指示与地方党组织实际运作之间一种微妙的“落差”,以及这种“落差”所逐渐衍生的自主性。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上文所讨论的四川地区中共通讯与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兹举几例以示说明,内容分别涉及农民暴动、军队兵变以及建立苏区之争。
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江防第七混成旅属军阀邓锡侯江防军黄逸民部,1928年秋中共便在该军队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初曾领导过广安观音阁和遂宁罢操索饷,以及士兵代表团驱逐反动官兵的斗争。然而,两次斗争也给党组织的生存带来了隐患。为清除中共在军队中的影响,师长李其相开始拖延甚至断绝该部队的给养,以至部队一日三餐都成问题。鉴于此,同年5月,怡生特委(即江防第七混成旅旅委)一面派人赶赴合川县委,说明“军支所在部队有立刻被黄隐、李其相解决的危险”,请求合川县委给予援助。(61)《川东特委军委通告(行字第1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的军事工作任务》(1929年5月1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0页。同时,又直接上报至四川临时省委,决定举行兵变。但是,四川临时省委并不认可兵变的请求,认为兵变条件尚不成熟,要求怡生特委尽可能延迟一段时间。(62)《四川临时省委通讯第274号,维字第4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策略和组织问题的指示》(1929年5月16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56—57页。6月,怡生特委又请求批准起义,四川临时省委再次要求其不能轻举妄动,应该“尽量运用策略延缓一个时期,增加准备方面的工作”。(63)《四川省委通讯伟字第1号,觉字第1号——关于加强第七混成旅兵变准备工作的指示》(1929年6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86—87页。同月28日,针对怡生特委再次送来的请示报告,四川省军委开始作出让步,强调理解特委的艰难处境,但仍希望其“积极加紧准备工作,发动群众起来,尽可能使这一工作有充分把握”,并指示怡生特委一旦发动兵变,应先去遂宁乡打游击战,且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军阀等。(64)《四川省军委通讯伟字第1号,觉字第2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策略总路线的指示》(1929年6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92—108页。但该指示信还未送达旅委,29日午后1时,旅长旷继勋就以革命委员会代表身份通告支队,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举行兵变。午后8时,即带领军队,兵分两路向蓬溪进发。至7月30日,部队在梁山猫儿寨寡不敌众,起义最终失败。(65)《怡生特委书记周三元给省委的报告——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经过》(1929年7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63—68页。审视第七混成旅兵变的整个过程,怡生特委与四川省委的通讯可谓频繁,但双方对兵变的认知完全相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四川省军委的28日回信确实没有及时送达旅委,以致省委在兵变的经验总结中也批评怡生特委行事匆忙,连“省委的回信都没有接着就拖起跑了,发动后也不给省委的报告”。(66)《四川省委通讯第5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中错误的批评及今后工作的指示》(1929年7月1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11页。但28日回信仅是四川省军委的妥协和指示兵变后的行军路线及策略,对兵变能否成功、革命能否坚持至关重要吗?这也许是个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通讯的滞后并不是旷继勋发动兵变的主要原因,第七混成旅所处的生存环境和革命诉求,才是地方党组织长成的关键因素,而非通讯这一技术手段。
关于下东苏区的争论。193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接到中共中央要求创建苏区的指示后,梁山中心县委即在虎城区发动游击战争。同年4月,四川省委再次明确了梁山中心县委的任务,是实地“学习游击战争”,“夺取敌人武装”,“创造川东苏维埃政权”。(67)《四川省委致梁山中心县委信——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1932年4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40页。不过,围绕创建全川东苏区还是下东苏区,四川中共组织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部分四川省委成员认为,虎南赤区“虽是二个偏僻小场,但已跨着梁开二县,它的周围又有过去一、二、三路红军的影响”,故“成立苏维埃的一天就应是川东苏维埃”。同时,团四川省委和另一部分省委成员却认为,虎南赤区虽有60多名党员,1000名左右农协会员,2000余人的青农成员,但“党的工作不健全,差不多全是英雄领导”,故建议“在下东创造苏区而不是就建立川东苏维埃,由创造个别苏区而发展成为全川东苏维埃”。双方观点明确且互不相让。在相持不下后,中共四川省委写信上报中共中央,请求最终裁决。(68)《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关于创造下东苏区问题》(1932年5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59—62页。围绕创建全川东苏区还是下东苏区的争论,本质是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广泛建立游击区和苏维埃的问题,仅从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看,“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川东苏区显然更能表现立场坚定。不过,这种立场正确并未得到四川中共组织的广泛支持,甚至可以说,反对声音还要更高一些,不仅是四川省委的部分人员,还包括团四川省委的全部,甚至上报中央文件的起草者,也明确支持先在下东建立苏区。当然,在四川中共组织等来中央指示之前,梁山中心县委领导下的虎城区农民组织就遭到破坏,下东苏区最终失败。下东苏维埃的失败,主要原因仍是自身力量薄弱,敌对势力强大,通讯在上级与下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存在,但却不是决定性的。
关于遂安农民暴动。1933年夏秋之际,遂宁、安岳一带由于夏季苦旱、入秋苦雨,大季主要作物红苕的产量,仅为1932年的三分之一,“且在地内烂了些”。不过,地租并未减少,“捐税急如星火,借贷无门”,以致两县农民的生存遇到巨大挑战。恰在此时,川陕红军进入鼎盛时期,加之军阀留守于遂宁、安岳部队甚少。基于此,中共遂安县委认为,此地“组织迸(69)迸,即奔。腾发展,群众武装斗争情绪如狂潮一般”,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不即干,真是无产阶级的罪人”,并决定于农历11月9日领导通贤场、凉风店、龙台三区的农民暴动。(70)《四川省委关于遂安暴动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省委、省巡视员、遂安县委往来信件摘录》(1933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539—563页。不过,由于出现消息泄露,引发当地武装抓捕,遂安县委不得不将暴动时间提到农历11月6日,但暴动不久即被镇压。纵观遂安暴动的经过,从省委收到遂安县委第一封请求暴动的信件开始,便回信不同意其立即组织暴动,但交通员不慎将此信件丢失,之后遂安县委又多次向省委提出举行暴动,省委随之去信,亦力求“制止他们的冒险盲动”。(71)《四川省委关于遂安暴动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省委、省巡视员、遂安县委往来信件摘录》(1933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539—563页。关于遂安暴动是否应该发动,或者说,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日常斗争正确,还是遂安县委的暴动更符合实际情况,这里很难给予是非的判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交通员没有丢失指示信件,或者指示信件准时到达,遂安农民暴动是否还会如约而至,恐怕就要涉及上下层级关系以及遂安政治军事生态等复杂面向了。
无论是第七混成旅的兵变,还是下东苏区之争论,抑或是遂安农民暴动,都属于通讯阻塞或中断后引发的地方党组织自主行为,是基层党组织根据客观环境作出的一种形势判断。由此看,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通讯与自主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通讯受阻或许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党的自主性,但四川党组织所作的判断与行动,更多的是源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而非通讯是否畅通。质言之,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能否生存与发展是其自主性强弱的核心因素。
实际上,除通讯本身外,非中共革命版图中心的地位、组织架构的多层级性,以及“蜀道难”的地理条件,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
首先,在中共革命早期版图中,四川地区既不属于核心位置,又不属于边缘地带,客观上决定了四川地方党组织在集中与自主之间的游离。一方面,四川素来就有革命的历史传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共组织的创建,四川一直走向全国的前列,很早便产生了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团体。因此,四川中共革命的早期,基本是由四川本地骨干主导的,如王右木、杨闇公、吴玉章、廖划平、童庸生等。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力量有限,其精力主要集中于东部,对四川力有不逮,无法给予人员和经费的全力支持。1931年4月,团四川省委在上报团中央的信件中,直指“去年自十月以后即未得中央汇一款来”,向中央提交的几次报告和通信,也未见中央答复。(72)《团四川省委致团中央报告——省委补选与各部工作》(1931年4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208页。1933年11月,四川省委在上报中共中央的信件中,也强调中央对“川委工作的指导太忽视,自从有党以来,只小隅巡视过一次,来不过两天就走”,中央给四川的指示信也“迟得太厉害”,交通员“在沪等了两月余”,中央才把指示信写完,而省委“所要的中央通信处,一年余不发”,“要的游战小册、兵运指导信,不但不拿来,数次信都不回”。(73)《四川省委昆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四川经济政治状况、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1933年11月1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528页。中共中央对四川中共组织的行为,也许是对全国革命形势研判下的反映,也许是客观偶发因素或个人工作方式所致,很难给予贴近真实的历史还原,但这种行为,毫无疑问会激起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怨言,这种不满或许就是引发“自作主张”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中共组织架构的多层级性。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垂直传递并不必然导致弱化效应,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还可能出现强化效应,如“层层加码”现象的出现,这取决于上下层级的数量和归属关系的强弱。不过,在中共革命的早期,尤其在白区工作中,这种信息垂直传递的弱化效应是明显的。在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创建早期,各地党团组织基本上直属党团中央领导,直到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成为中共在四川建立的第一个最高机关,领导全省党组织。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中共五大党章规定,各地党组织名称都需依据当时行政区划更改,党组织层级也由原来的四级变动为“中央—省委—市县委—区委—支部”五级。除此之外,自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后,还在川西、川东和川南等地建立特委或中心县委,如1927年11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建立后,为便于指挥川西地区的政治军事,领导川西地区的党组织,于成都建立了川西特委。伴随着中共组织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消息与文件传递的压力也随之增加,而信息垂直传递的弱化效应,又是地方党组织自主性的土壤。对此,四川省委感慨道:“省委与各地方关系本就太不亲密,各地没有详细的报告,省委又缺乏巡视工作,中间还隔一层特委,中央的和省委的指示经过几道折扣,传达到支部,简直不成一个样子了。”(74)《四川省委两月工作总报告——从6月15日新省委成立到8月20日移回重庆》(1929年10月9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234页。
最后,四川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革命环境,也增加了中共地方党组织自主性的可能。四川地处上江上游,其核心地区属于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或高原,盆地内部地势北高南低、南部为长江干流所经,北部各支流分别穿经盆地中北部南流入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四川经济文化的内外交流常因“其间山峡崎岖,滩流冲突,水陆转运,皆有节节阻滞之虞”。(75)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58页。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下,文件、信息、人员、物资的流动,常常滞后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迫使地方党组织不得不自行选择行动策略。同时,四川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也极大阻碍了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活动。自袁世凯去世后,各地军阀相互混战、割据称雄,在四川地区,各军阀还实行“防区制”抵制其他军阀,保证自身地盘和军事实力。四川中共组织成立以后,川内各派系军阀势力此消彼长、分分合合,但对中共的打击却一直持续。因此,四川党团组织几乎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获取内外消息极为不易,在信息真空的环境中,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自然容易得到萌发。
当然,在考察四川地区中共组织自主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列宁主义政党集中的力量。从1922年成都、重庆、泸县等地方团组织的建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35年,中共在四川地区的发展几经波折,中间还经历了“三三一”惨案,但生命力极强,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把握,还是经费人员的支持,抑或是多次重建四川省委,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统筹与协助,仅靠四川地区中共组织的自身力量,恐怕多会出现贵州中共组织一样的结局,在遭到地方军阀破坏以后,即一蹶不振。四川中共组织1935—1936年的沉寂,亦可作为“央地”关系的佐证。由于叛徒的出卖,1935年6月,四川省委遭到地方军阀破坏,省内党组织元气大伤,次年2月,仅存的自贡中心市委也遭破坏,四川境内中共组织至此消失殆尽。但为什么之前四川党组织在遭到破坏后,可以重建,而此次就难以为继呢?显然,这与此时中共中央在西北刚刚落脚,还无暇顾及四川地方的党组织有关。或者说,在中央发展限于困境时,也就无力从人员经费以及方针政策上予以帮助。
结语
在四川中共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借助于传统通讯技术体系以及人员往来携带等方式,四川地区中共实现了组织内必须的信息沟通、指示传达和经费输送,这种通讯方式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临时性特征。不过,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限于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邮政寄递和人员往来很难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故从“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四川地区的中共组织逐渐建立了多条党内秘密交通线,此举无疑缓解了信息沟通、指示传达、经费输送的压力,维系了川内中共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非中共革命版图中心的地位、组织架构的多层级性,以及“蜀道难”的地理条件,都使得四川中共组织具有明显的隔离特征。正因为此,川内中共组织才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性,可以在四川军阀的严厉政策下艰难成长。论者认为,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屡犯“左”倾错误,而中央与各苏区相去甚远,正是在此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下,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过程中较少受到错误干扰,成功开辟了由“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独特发展道路。(76)应星:《军事发包制》,《社会》2020年第5期,第6页。与毛泽东的“军事地方化”成功不同,同样的交通通讯不便,并没有给四川地区中共组织带来成功,相反的是,四川中共革命在1935年后陷入了长时间的低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四川地区中共革命的挫折,就否认一定的自主性所带来的活力和灵动,尤其是政治压力和军事打击严厉之时,这种自主性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更进一步讲,正是由于屡次自主性的试错,才换来尤为珍贵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又可以被复制,并引导中共革命走向胜利。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挖掘和揭示各种“关系”的互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77)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页。就中共地下党而言,这种“关系”可以是隐性的,表现为组织成员之间疏离与矛盾、思想的碰撞与冲突,也可以是显性的,表现为组织之间信息、文件、物资的流动。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隐性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根据历史人物的日记,也较难判断其对事态发展的影响。相反,依据遗留之文献,通过信息、文件、物资流动的频率和内容,或一定程度上可以考察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显性关系的优势。文本所讨论的,无论是邮政寄递、人员往来,还是党内交通机构、交通网络,均可视为“央地”关系的显性样态。由此看,对中共通讯工作的研究,无疑就是对挖掘和揭示“关系”的一种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