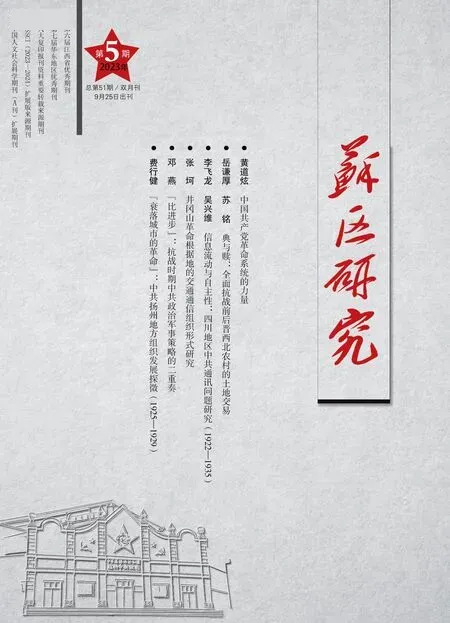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
岳谦厚 苏 铭
典地作为土地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村实现地权流转和资金融通的常见手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剧烈变动呈现出新陈代谢的发展态势。与之同时,身处战争与革命场域中的晋西北农村发生的典地交易亦在“变”与“不变”之间盘缠纠结。目前学界涉及这一时期农村典地交易的成果不少,(1)直接或间接涉及该主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有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岳谦厚、张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玮:《阅读革命——中共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的经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王志芳:《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玮:《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地主租佃关系考察——以1942年张闻天调查为中心》,《江汉论坛》2008年第8期;张玮:《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等等。但更多地是将其纳入农村借贷关系范畴内予以考察,而对于典地交易情形、发生原因、回赎政策或回赎办法流变,在一些细节考析上仍显薄弱。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晋西北农村土地典赎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史研究。
一、晋西北农村典地情形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晋西北农村典地活动比较常见,各地时有发生。据中共方面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县农村均有典地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典地交易的基本样貌。
首先,各地典地交易相对普遍,而程度各不相同。据档案资料所载,兴县石岭子村于1927—1941年间发生5宗典地交易,计有8户参与典产活动,其中包括典产物不明者1户和不以土地为典产者2户,这就是说该村土地典当交易的实际户数至多6户。其间,该村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数为106.8垧。假设该村全部户数和土地数未曾有过变化,仍保持81户人家和1672.6垧土地,则参与典地交易户数和土地数分占总户数和土地总数的7.41%和6.39%。(2)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保德县段家沟村战前(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下同)共有66户人家、725.2垧土地,参与典地者33户,占总户数的50%,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有125垧,约占土地总数的17.24%。该村战后(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下同)有地833.7垧,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有57垧,约占土地总数的6.84%。(3)《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兴县黑峪口村战前245户人家有地4706.9垧,1942年缩减到200户,土地下降到3648.41垧,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有20宗典地交易,涉及37户人家、294.37垧土地;其中战前12宗、典地224.07垧,约占土地总数的4.76%,战后8宗、典地70.3垧,约占土地总数的1.93%。(4)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1、50—51页。任家湾村战前有地789.75垧,战时下降至765.75垧,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4宗典地交易;其中战前2宗,出典位于外村的土地129垧,约占土地总数的16.33%,战后2宗,出典位于本村的土地8垧,约占土地总数的1.04%。(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8页。西坪村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6宗典地关系,包括战前4宗和战后2宗。该村就土地出典而言,战前典出13垧,战后先回赎4垧后又将其中2垧典出。(6)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72页。在土地入典上,虽无具体数据,但据其间使用土地中所包含的2垧和5垧左右典进地,基本可以推断典进土地数量极少。(7)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64页。花园沟村战前23户人家有地540垧,战后27户人家有地602.1垧,其间发生7宗典地关系,涉及11户人家、43垧地;其中战前6宗典地关系中有10户参与了38垧典出活动,战后1宗典地关系仅有2户参与了5垧典出活动,并在一年之后回赎。可见,花园沟村参与典地交易的户数虽在战前较多,即将近总户数一半,但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不算多;战后无论典地户还是典地数都少了,加之“土地价格的降低,买入土地的容易,该村今后典地恐将逐渐走向绝迹的道路”(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69、572页。。柳叶村战前36户人家有地1617垧,1936年有2户贫农将17垧地典给1户上升中农,并于1941年赎回,此后未见典地活动。(9)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630、632、635页。赵家川口村战前战后分别有地2597.28垧和2464.11垧,其间发生16宗典地关系,涉及7户人家、136垧土地;其中战前7宗典地54.3垧,约占土地总数的2.09%,战后9宗典地81.7垧,约占土地总数的3.32%。(10)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397—398、413—414页。临南县郝家窊村自全面抗战以来,全村59户人家有地2079亩,其中有18户本村户和329亩土地参与了典地交易,分别占全村总户数和土地总数的30.51%、16.95%。(11)《郝家窊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943年5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35。兴县中庄村在土地典入方面,战前有2宗,典入土地34垧。(12)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75、179—180页。换言之,若以中庄村战前土地总数570.5垧为参考,其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数所占比例不足5.96%。(13)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61页。而高家村典地交易与中庄村正好相反,其在土地入典方面战前战后均未发生,战后则有2宗典出活动,共典出土地16.24垧。再比之于战后土地总数2917垧,参与典地交易者仅占0.56%。(14)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318—319、321、323页。
从以上数据可知,各村典地交易并不发达,无论典地宗数、参与户数还是所典土地数,占比普遍较低。而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不同时段内,各村典地活跃度亦有明显差别,如段家沟、黑峪口、任家湾、西坪、花园沟、柳叶村典地交易表现出战前比战后活跃的情势,赵家川口、郝家窊村则与之相反;中庄和高家村却又分别表现出战前战后或无典出或无典入的情状。另外,还应注意到,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不限于村庄内部,诸如黑峪口、任家湾和郝家窊村,村与村之间典地交易常有发生。总的来看,就纵向方面,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基本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典地交易频次低、数量少是其具体体现;就横向方面,各地区间典地交易程度不尽相同,有的相对发达,有的相对落后,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倒退现象。
其次,各阶层均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典地交易。黑峪口村战前1户地主典出120垧,2户小商人典出19.5垧,1户富农典出12垧,3户自由职业者典出15垧,2户贫民典出9垧,1户军警典出4.5垧;2户贫民典入19.5垧,6户小商人典入39垧,1户小地主典入30垧,1户教员典入9垧。战后1户富农典出5垧,2户贫农典出7.5垧,1户小商人典出3.3垧,1户地主典出1.5垧,1户中农典出3垧;2户富农典入15.5垧,1户地主典入36垧,1户贫农典入3垧。(1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0—51页。这表明战前地主和小商人无论典出或典入土地数量均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是发起典地活动的主要推手;战后参与典地的主要阶层在典出典入数量上均大幅减少,仅富农和贫农超过战前水平。总体言之,该村战前典地交易中不使用土地的阶层占大多数,而战后地主、富农和贫农成为典地交易的主要参与者。窑头村在1937—1941年的五年间,中农典入73.5垧,典出23.4垧;富农典入53.5垧,典出40.5垧;地主典入27.5垧,典出17.5垧;贫农典入22垧,无典出;工人典入2垧,无典出;商人典入6垧,典出4垧。(16)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可见,该村中农在土地典入上表现最活跃,富农次之,其后依次是地主、贫农、商人和工人;在土地典出中,富农以绝对优势居于首位,随之依次是中农、地主、商人,贫农和工人则无任何出典活动。这不仅显示出各阶层间典地情形存在巨大差异,亦表明频频参与典地活动的富农正在分化之中,集中于地主、富农手中的土地已开始向其他阶层农民转移。段家沟村战前1户富农典出8垧,3户富裕中农典出7垧,10户中农典出40垧,14户贫农典出32垧,1户雇农典出3垧,1户贫民典出4垧;2户富农典入19垧,1户中农典入12垧。战后3户富裕中农典出24垧,10户中农典出5垧,14户贫农典出25垧,2户富农典入3垧。(17)《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这表明该村战前参与典地阶层广泛,基本涵盖了包括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贫民和雇农在内的全部农民群体,且以中农和贫农两大阶层表现最突出,是典地交易的主要参与者。赵家川口村战前1户地主典出25.71垧,2户中农典出11.43垧,2户贫农典出9.3垧;2户中农典入7.86垧。战后2户地主典出28垧,1户中农典出8.57垧,3户贫农典出12.14垧;1户富农典入14.29垧,1户贫农典入13.7垧,1户中农典入5垧。(1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3—414页。其中地主在典地交易中占明显优势,中农和贫农在战前和战后分别位居第二。任家湾村战前1户中农典给1户成分不明者69垧,1户成分不明者典给1户富农60垧;战后1户中农典给1户贫农3垧,1户贫农典给1户中农5垧。(19)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8页。由此可见,该村典地关系是在富农和中农主导下进行的,且富农和中农是主要的出典方或承典对象。
此外,有些发生典地交易宗数极少、涉及阶层相对单一的村庄,同样存在不同阶层参与典地交易且程度各异的情况。如临南县郝家窊村战后本村有3户富农典出土地102亩,1户中农典出12亩;3户中农典入39.5亩,11户贫农典入120亩。(20)《郝家窊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943年5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35。兴县中庄村战前1户中农、1户贫农分别典入29垧和5垧。高家村战后1户地主、1户中农分别典出7垧和2垧。柳叶村战前2户贫农典给1户上升中农17垧。花园沟村战前4户贫民分别典给1户中农7垧、2户贫农24垧、3户不明成分者7垧。(21)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79、323、572、632、637页。
可以看到,以上各村参与典地交易者成分或错杂多样,如黑峪口、窑头、段家沟村;或简单明了,如赵家川口、任家湾、西坪村;或单一纯粹,如郝家窊、中庄、高家村、柳叶、花园沟村,均能在相当程度上清晰地反映出各阶层在典地交易关系中的不同参与度,以及各阶层在典地数量上的参差性。
最后,土地出典多入典少。根据各村典地交易的具体情形,可以统计出一些具有代表性村庄的典出典入情况,如黑峪口村战前典出180垧、典入97.5垧,战后典出20.3垧、典入54.5垧;段家沟村战前典出94垧、典入31垧,战后典出54垧、典入3垧;赵家川口村战前典出46.44垧、典入7.86垧,战后典出48.71垧、典入32.99垧;中庄村战前战后均无典出,仅战前典入34垧;高家村战前战后均无典入,战后典出16.24垧;柳叶村战前典出17垧,战后未发生典地交易。由此可以判断,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典出多于典入,这表明该地区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农民尚无足够力量典入更多土地满足自身生产需要,相反地须依靠出典土地以获取短暂的经济收入来维持日常生产生活。
二、农村各阶层典地缘由
一般言之,农村发生典地交易主要是各阶层或主动或被动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虑及自身经济状况而自发选择的结果。然对于切实参与到典地交易关系中的出典人和承典人而言,由于其立场、出发点及目的不尽相同,诱发双方进行典地交易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与时局变幻、政策调整、经济变动,以及各阶层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密切相关。
战争为农村各阶层典地交易提供了契机,其减少了一批农业熟练劳动力,催生了一批新的农业劳动者,迫使许多原本不以农业或耕作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转向乡村,他们摒弃旧业,凭借典押买卖等手段挤入土地生产。如保德县,日军控制平绥路之后,该县传统的甘草销路骤然走向衰落,众多从事甘草行业的大小商人无奈转向农业,无数“走口外”谋生的草场工人纷纷被迫返乡,大量赶毛驴过活的赶脚户歇业转入农事活动,还有不少商人、小贩、市民、商号倒闭店员亦不断向农村转移,“他们都用各种办法弄得一些土地,农村经济朝着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了”(22)《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
新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刺激了农村各阶层典地交易倾向。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大力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政策,引起各阶层典地交易的剧烈变化。地主、富农的政治经济地位被严重削弱,他们不仅丧失了传统的钱粮税收操控之权,还需承担更多的抗战负担,只好将田地予以典卖;而中农、贫农借减租清债和合理负担等政策所得实惠,纷纷典入或买进或回赎土地,不断扩大生产资本。如晋西事变之后,临南县郝家窊村典卖土地者甚多,其中出典卖地者多系地主、富农,入典买地者多系中农、贫农。(23)《郝家窊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943年5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35。
战争与政策之间绝非相互孤立,而是互有关联,这种情形在黑峪口村表现得尤其明显。无论战前抑或战后,黑峪口均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一个带有农村属性的市镇。该村战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从地主到雇工总数不过36.33%,而战后上升到45%。从这些变动趋向可以看出,战后黑峪口农村色彩日益加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占比大大提高,亦即基本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在战后已与土地发生了更多的联系。(24)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2页。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黑峪口村许多不以土地和农业为生的人,诸如大小商人、地主兼商人及高利贷者等,在战争破坏和中共新政策双重作用下转商为农,补充进入到以土地和农业为生的农民队伍中。
物价涨跌亦会诱发典地交易。如兴县杏花沟贫民孟某于1929年欠白文镇商号货账30元,月利4.17分,本利80元。时逢粮价低迷,谷子仅值2—3角,孟某预测粮价未来可能更贱,于是借粮债变价归还了钱债。不料1930年晋钞贬值,一斗谷价涨至3—4元,所欠粮债本利在三四年间竟高达70—80石。为偿还高额粮债,孟某尽家所有变产还债,在将95垧地、4孔窑、1盘磨子、1盘碾子和18间马棚典粮50石尚不够还债的情况下,又将一切家具变卖以充债款。1931年粮价回跌,1石谷子值1.6元,孟某又以先前所典50石粮食作价80元将上述全部家资典给债主。然孟某因另借他人7石粮食,致使4孔窑被旁人“捉”去而无法抽回。为此,债权人和孟某到区政府打了一场官司。但当时孟某太穷,甚至连葬父都无能为力,区长只好劝说债权人再拿出8石粮食,替孟某抽回房子为债权人所用。最终债权人又借给其8石粮食用于抽窑,并在揭约上写明赎地时一起归还,此事才算作罢。而同村薛步云则是在粮价上涨之际将积攒下的余粮变卖,用30元钱典入32垧地自种。(25)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
战乱发生、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动等突发性事件,固然是引致农村各阶层典地交易发生的重要因素,然在农村经济发展常态之下,出典户典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应对生计困难、缓解经济压力。在不同的出典户看来,他们生活难以维系的具体原因各有差别,大致包括以下四类:(1)家庭突遭意外或筹办诸如婚丧嫁娶等事无钱支付。如桑蛾村地主王某因家中连年遇事急需用钱,便将位于中庄村的28垧地以55元白洋典给中农刘某。(26)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247页。辛窑上村中农兼小商人孙某因年老生病,于1938年以30元白洋将30垧荒地典给需要土地的上升中农举某。没落地主孙寡妇因儿子年幼,于1928年将30垧土地典给店员梁某,而后变为贫农的梁某又因患病治疗缺钱,于1938年将所典30垧土地以100元省钞典给上升中农举某。石岭子村贫农李某因无棺葬父,于1932年典出2.1垧地。(27)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柳叶村2户贫农因“问媳子”及死了人,于1936年以92元省钞将17垧土地典给1户上升中农。(2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632页。(2)因不会“受苦”或好吃懒做,且沾染上赌博、抽大烟、逛“破鞋”等陋习而致生计困难。如兴县贾家沟村1户下降中农因不会“受苦”,将7垧土地以13元白洋典给本村1户富裕中农。(29)《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任家湾村中农任某吸大烟致家用不足,于1941年以40元白洋将1垧水地出典给贫民任某。(30)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8页。兴县贺家川村4户贫农、2户贫民、1户小商人,以及孟家沟村1户中农、3户贫农、1户贫民、1户雇农,均因好吃懒做、抽大烟而将土地典出。(31)《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51页。(3)买卖经营不善,须典地使钱,解决一时困难。这种情形常发生在做投机买卖或贩运货物受物价影响赔钱的中小商人及中农身上。如兴县石岭子村中农李某因赶脚贩货赔钱负债,于1927年以300元白洋将6垧平地典给上升中农李某某。(32)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孟家沟1户贫农因倒卖牲口赔钱,将土地典出。(33)《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51页。(4)累债无法清偿而将土地典出,且预备将来回赎。如兴县阴坪村没落户孙朋保欠货本利累计20元无法归还,于1934年将4垧土地典给商人高某。辛窑上村富农奥某因省钞落价负债,于1933年将76垧土地典给商人兼高利贷者王某。石岭子村没落地主李某欠贷账无法归还,于1929年将15垧土地典给城内商人白某。杏花村没落户孟某因负债,于1931年将45垧土地典给三家李姓中农,后因承典人典地时曾借钱,又将所典土地转典出去。(34)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
当然,出典户典地并非皆因生活困难,有些是自己不经营土地又不愿卖地,则利用典价另投他业,有些则是怕当老财并逃避抗战负担,趁机典出坏地。如文水平川等靠近大城市的地方,就有许多弃农从商无资本者将土地典出,以典价作为资本从事其他行业。兴县辛窑上村中农兼小商人孙某于1928年将4垧地典出,得来的40元白洋用于转行经商。(35)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赵家川口村某地主自己不经营土地,又考虑到租出罢收不好租,索性将地典出,或换现钱抽洋烟或做别用。(36)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4页。临南县中庄村富农李某、中农李某某等人,于1943年冬至1944年大量典出土地,目的在于缩小目标摆脱老财嫌疑、躲避负担。(37)《临南中庄村十四种调查表》(1944年8月13日),《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临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2-29-2。
从上述众多实例中可以看到,出典户多系没落地主老财,兼有部分富农、中农、小商人和中农兼商人,而入典户多系高利贷者或商人兼高利贷者及中农或上升中农。对入典户而言,其典地原因有二:一是上升农民或暴发户略有积蓄,迫切需要土地,但买不起地,典地便宜;二是承典户放债收不回来,便将债务人土地典来以产作保。其中后者最易发生引诱或强迫债务人典地乱象,并滋生债权人重利盘剥。这其中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由借贷关系转为典地。某些高利贷者或商人高利贷者常会设法给债务人借钱或贷账,以寻求典产机会。而债务人一旦“上钩”,即遭重利盘剥,若到期交不上利,债权人即将地典去,企图长期或永久占有田产。如赵家川口村中农赵某曾在战前借地主牛某40元省钞,借时与白洋同价,积二年利息40元,写了一张100元的借票,将1垧水地典给地主。后因水地产量高,赵某又向牛某租回自种。(3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4页。如果说赵家川口村发生的这种先借后典之后又租的土地交易方式略带强迫性,那么辛窑上村郭某典地的过程则更赤裸裸地展现出商人高利贷者为占有他人资产而精心布局、威逼利诱和强取豪夺的丑态。跑卖商人兼高利贷者王某常在此村买货卖货,见郭某家境殷实,便允其赊账并借钱60元。1926年底王某与郭某结账,所借钱货利息计100元,郭某无法偿还,遂写成借约,月利3分。郭某仅付清过一年利息,此后常欠利。到1931年底,郭某欠款已达410元。为了还债,郭某于1932年以340元将107.5垧山地、2孔石窑、2间棚圈和1座大门典给王某,但仍欠70元。因王某知道郭某仍有房产、田地,想利用剩余70元债款谋取其土地和房子。1933年,郭某依旧还不起债,只好把仅剩的13.5垧地、4孔石窑、5间房子、3间棚圈、1座大门一并典给王某。至此,郭某从地主一变而成“穷光蛋”,此后只能租地自耕、租窑居住。(39)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另一种是由押地转为典地。保德县段家沟村出押者在借贷时将地契押给债权人,到期本息不还即由债权人将地典入,百姓称之为“赘地”,而且这种典地多半同时又转入租佃关系,形成地主兼高利贷二位一体的剥削形式。该村有50垧以上的土地均是通过此种方式变为了典地。(40)《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兴县柳叶村亦如此,该村于1936年发生的2宗典地交易在开始时均系押地形式,即“押地借钱”,月利3分,因到次年没钱上利而只好将土地使用权让给债主。但当时并未另订契约,仅仅口头约定“将来什时有钱什时赎地”,从此即变为“钱无利,地无租”的典地形式。(41)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632页。
缘何出典户和承典户均心照不宣地将典地视为双方利益置换的最佳选择呢?这实际上取决于典地双方对待风险的态度,亦即风险偏好。在特定环境中,典地恰好满足了出、入典双方风险回避的心理预期。对出典户而言,同样风险的土地交易类型,其更钟情于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典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晋西北农村经济十分落后,一般农户亦不富裕,普遍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如此脆弱的农家经济一旦失衡,便只能选择出让其唯一的资产土地来换取银钱以解燃眉之急。然土地之于小农家庭又是十分宝贵的生产生活资源,除万不得已时绝不肯放弃。所谓“地耕三年视如母”,就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爱惜之情。因之,许多生活困难急需用钱而又舍不得卖地的农民就选择将土地暂时典出,预备将来回赎。在这些出典户看来,典地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还可保留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大大降低了失地风险。
对承典户而言,当各种土地性投资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其更偏好于具有低风险的典地,而典地的低风险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典地典期灵活、价格低廉,相较于买地、租地等更经济实惠,需要土地的上升农民可借此较轻松地解决土地缺乏问题。晋西北农村典地期限有无限期回赎和限期回赎两种情形,前者为“活典”,赎期无限制,有钱即可回赎;后者为“死典”,即限几年内回赎,不赎即作绝卖,限期一般为三至五年。“活典”“死典”在习惯上都是一年内不准回赎,亦有特别约定三年内不准回赎者。典地价格分钱、粮两种形式。晋西北一般“典地一半价”,即典价当地价一半,亦有在一半以下者;若是“死典”则典价更高,当地价的80%。(42)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在兴县杨家坡村还存在依土地质量确定典价的实例,水地、平地典价当地价的60%—70%,梁地、塔地典价当地价的30%—50%。(43)《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以粮食作典价一般多用于山地,即使用钱支付,契约上依旧写为粮食,将来回赎亦用粮食。这是因为在币制混乱与不统一情形下,以粮食作典价更保险,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用钱典地者更稀少。(44)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247页。在赵家川口村,典地双方条件十分简单,仅需一方出地一方出典价而已,所谓钱无利、地无租亦无粮。这样的典地在典价不高、典期较长的条件下对承典户来说非常有利,不仅在支付典价后不再需要任何利息,还能以有限现款获取现有土地全部使用权。倘若出典户是贫苦农民,出典后很久都无力回赎,那么在这段时期内承典户不仅可以自由使用这些土地,还可将土地租出去收租。(4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5页。
值得注意的是,典价高低不可一概而论,还须看典出、入双方具体情形。典地双方目的也许不一致,有时一家想卖、一家想买,有时出典人准备回赎,在这种情况下典价则有高有低。价高者多半是已敲定死期且近期准备形成买卖关系,价低者则多半预备回赎。前者多是一些下降户将地典出,不准备回赎或为死期者;后者多为遇事急需用钱而将地典出,过两年便回赎者,这些典价最低。(46)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247页。如兴县贺家川村1.5垧平地的典价高达600元法币,承典者目的就在于将地典死而使出典者无法回赎。这种名典实买卖的土地交易形式,对典入者而言既无买地之名又有买地之实,对出典者而言则既无卖地之名又有卖地之实。(47)《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52页。又如花园沟村一些游民、破落户将地典出不准备很快回赎者,典价就较高,准备回赎者典价就较低。(4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72页。再如战前赵家川口村还有一种“被逼性”典价亦极低廉。该村侯某典出1垧平地得白洋75元,而1941年同一人典出1垧平地只得白洋20元。究其原因在于侯某在战前是中农而典价较高,到1941年时夫死妻单降为贫农,非典出地不可,典价不免要低些。(49)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5页。另外,兴县还存在某些缺钱承典户将典入地再转典出去的情形,转典价比原典价更低,且承典人转典时尚须征得原出典人同意之后方可转典,私自转典情况未见发生。(50)《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
其次,典进土地的经济回报较丰厚。据兴县贾家沟村典地调查材料,该村5家典入户所典土地纯收入占典价分别高达157.5%、170%、113.7%、170%和113.7%。现举其中一例说明:该村一下降中农以典价13元白洋典给本村一富裕中农7垧土地,1941年夏季1元白洋折8元法币,故承典户7垧土地在典价支出上合法币104元。在土地收益上,每垧若以4.5斗谷计,则7垧土地可收谷31.5斗,所交公粮平均占估产量的22.9%,31.5斗谷约需交公粮7斗,故实际收益为24.5斗谷,再以每斗谷合6升小米算,24.5斗谷可换成14.7斗小米。1941年秋收时,1斗小米值20元法币,14.7斗小米即得法币294元。在生产成本上,每垧地需10个人工,1941年1个人工约法币1元,共需工资70元法币;每垧地需两个牛工,共需14个牛工,而牛工不用支付工资,但每日需料约1.5升黑豆,14日共需黑豆2.1斗,时价黑豆每斗法币8元,共计法币16.8元;每垧需肥料5袋,共需35袋,合法币约35元;每垧需1升种子,共需7升,合法币8.4元,合计生产成本为130.2元法币。以7垧土地全部收益减去全部生产成本,则承典户盈余163.8元法币,当典价104元法币之157.5%。(51)《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50页。
柳叶村典进土地的收益甚至比放债收利还要高。该村2户贫农于1936年典给1户上升中农17垧土地,典价92元省钞。若将92元省钞作为利钱放出,月利3分,以一年12个月年利计息,则每年利息为92×0.03×12=33.12元。若种地17垧,以每垧3年(1937—1939年)平均产量3.8斗计算,每年可收粮17×(3.8÷10)=6.46石粗粮。耕17垧地需牛工12个,按每头牛每日用草连料0.25斗黑豆(按杂粮算),共需供给3斗;以17垧土地费去120个人工且每人按4个月计算,每月以粗粮1.5斗计,则4个月共用6斗杂粮。若除去1.9斗种子(平均每垧需1升),则每年收入粗粮6.46-(0.3+0.6+0.19)=5.37石。按当时3年平均市价,5.37石粗粮可卖白洋16.41元。1937—1939年白洋与省钞平均比价是1:2.4,16.41元白洋可折合16.41×2.4=39.38元省钞。这样,将土地典入耕种的收益要比放债多6.26元。若把柴草收入及瓜豆等副业计算在内,典进土地的收益比放债利息还要更高些。(52)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632页。
由以上两例可知,典进土地对承典者有利可图,其以较高年利率使承典户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此种典地利息虽在形式上与高利贷接近,但两者实质上并不相同。高利贷利息是农民从生产所得中提出交给高利贷者,其作用在破坏生产;典地利息则是典地者从典来土地上生产得来,其对生产有利。(53)《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52页。
最后,典地形式可以用来作为别种剥削的掩护或“保护伞”。如赵家川口村破产中农侯某于1941年8月以20元白洋典给富农赵某的1垧平地在出典时已下种,侯某为不放弃青苗便又将出典地伙种回来,并与赵某商定产粮对半分。两月后秋收,侯某一面以20元白洋将地赎回,一面又在未减租的前提下向赵某对半分出8斗粮。(54)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15页。这意味着作为承典户的赵某在典地“钱无租、地无利”名义下,不仅对出典户侯某收取了高额地租,还逃避了减租法令的减租要求,这种隐性收益在事实上已构成了剥削。
三、政策流变与典地回赎
影响典地正常回赎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规约无疑是一个重要变量因素。晋西北农村典地回赎办法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并不一致,随新旧政权交替、政策法规转变而几经更迭,大致以《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简称《民法物权编》)颁布施行、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和《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简称《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制定执行三个重要节点为界,划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一)1930年5月至1940年1月
1930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民法物权编》,有关典地回赎法令条目共5条,具体规定了典物回赎之典价、时期。据该法令第920、927条,出典人在回赎典物时遇典物损毁或增值,其典价需做相应调整;又据第923、924条,出典人回赎典物之时期要视典权是否定有期限而定。具体而言,出典人在回赎典物时,若典物因不可抗力致全部或部分灭失而使出典人只能回赎典物剩余部分,则其典价得由原典价中扣减典物灭失部分灭失价值之半数,且以扣尽原典价为限;若典物因典权人支付有益费用而使其增值,则出典人回赎时还须在现存利益限度内对典权人进行补偿。典物回赎期限有限期回赎和无限期回赎两种。前者于期限届满后,出典人以原价回赎典物,但若典期届满经二年未以原典价回赎,典物所有权即归典权人;后者不定期限,出典人随时可以原典价回赎典物,但自出典后经30年不回赎者,典物所有权即归典权人。这些法令并未对典物做出具体规定或解释,这就意味着若典物为土地也同样适用。该法令第925条还特别明确若典物为耕作土地,其回赎时间应于收益季节后,下次作业开始前。(55)民国政府颁行:《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上海民治书店1930年版,第49—52页。
据档案资料显示,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中央土地回赎典当办法》,拟在四年内清理以往一切土地回赎问题;而后山西省政府又于1931—1933年下令以三七折或白洋票子各半回赎典押产。(56)《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晋省各县典地则依民间习惯回赎。如兴县花园沟村典地回赎期限,一般民间习惯是典地一年内不准回赎,一年后任何时间均可回赎且没有期限。典地回赎价格是三年后回赎,赎价可比原典价少些,但具体赎价须参照典地双方生活情形决定。(57)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72页。又如与兴县接壤的方山县,则有“许赎不许找”“临冬到话,惊蛰交价”习惯。前者意为典产于议典时已具有绝产代价者,只许于期限内按价告赎,不得再行找价;后者意为出典人回赎典地,须于头年冬季先通知典种人,至冬季时始准交价赎地,若冬季不通知或虽通知而交价已在惊蛰后者,则不准回赎,应于下年冬季再行通知照办。(58)《山西省关于物权习惯之报告》,司法行政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1930年版,第259、309—310页。
(二)1940年1月至1941年11月
自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宣告建立后,晋西北农村典地回赎便呈现出新老办法并行的局面,一方面仍延续着民间传统习惯和旧政府法规,另一方面又接受和贯彻了中共新的赎地政策。
典价、货币金融及地价依旧是出典户考虑回赎土地的先决条件。典价愈低土地回赎愈快,典价愈高土地回赎愈慢,甚至不回赎。而货币跌价、地价高涨时往往又是典地回赎有利时机,反之则不回赎。(59)《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1939—1940年山西省钞落价时,赎地者甚多。到1940—1941年农钞落价后,赎地者益多。如河曲县元家寨村回赎典地61垧,何家坞村回赎典地365垧,整个河曲县回赎典地2227亩。(60)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当然,并非所有出典人均能趁机赎地,如若遭遇有钱有势的承典人则不能以省钞或农钞回赎。如1930年省钞跌价,出典人多以省钞回赎典地,但牛友兰却拒绝出典人用省钞赎地。(61)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有些出典人在估计到自己典地无法回赎时,便将典地卖与承典人,承典人按时价找贴,以补足典价与卖价差额,这样一来双方典地关系一变而成土地买卖关系了。若承典人因需钱又将典产再转典,该典地在回赎时一般按顺序回赎,亦有直接回赎者。(62)《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
另外,据兴县调查资料显示,地价降落亦为典地回赎提供机会。1931年后地价逐渐降落,水地值1931年前地价一半上下、平地三分之一上下、梁地五分之一上下,赎地时赎价受此影响,水地赎价应在原价一半以下、平地三分之一以下、梁地五分之一上下、荒地五分之一以下,如此原地主才可能回赎典地。然而,通常情况下,典地仍须照原价回赎。(63)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旧政府规定,如若货币、地价无大变化,回赎十分容易,立约后三年以上,经中人出款就可回赎,但印花税契等费用须由承典人负担,否则由出典人负担。(64)《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
中共在晋西北典地回赎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按减租减息条例中清理旧债办法,典地收租作为利息,利息超过典价两倍者本利均停,无条件回赎;一种是以农钞1元抵白洋1元回赎。(65)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如1940年12月河曲县政府典地回赎办法即规定典地已40月者,抽回地写缓债约,80月者则无条件回赎,否则40月者就以农钞1元抵白洋1元回赎。(66)《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当然,以农钞抵白洋并不固定,在各地实际情形中亦存在以1元法币抵1元白洋、1元晋钞抵1元白洋回赎者。此类典价一律以票洋回赎情形在河曲、保德地区最普遍。(67)《减租减息工作与回赎土地问题报告》(1942年5月31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兴县各村亦有之。如任家湾村任某1939年以典价白洋6元将5垧山地典给中农任某某,1940年以6元法币回赎;任某于1941年以典价白洋40元将1垧水地典给贫民任某某,同年用40元法币回赎。(68)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8页。又如兴县黑峪口村1939—1942年回赎的8宗典地中就有4宗是以1元省钞当1元白洋回赎,包括1户地主用120元赎回120垧梁地,1户富农用20元赎回5垧平地,1户贫民用16元赎回0.5垧水地,1户贫民被外村人用41元赎走15垧梁地。其余4宗交易中,1宗是用216元农钞赎回原典价20元白洋的1.5垧平地;1宗是用216元农钞赎回原典价284元省钞的1.5垧平地;1宗是要用省钞回赎,承典人不要,后商定再种一年无价抽回;1宗情况不明。(69)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2页。
中共典地回赎办法实施使大部分典地得以回赎,许多出典户因之受益,解决了土地缺乏问题。然相较于这些成绩,中共典地回赎办法亦存在明显缺点,其中以“左”的现象最显著。如1940年冬在河曲、汾阳等地发生赎地运动。(70)《减租减息与赎地》(1942年10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10-2。再如在时价1元白洋可抵30—40元农钞的情况下(71)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以1元农钞抵1元白洋,虽使许多出典户讨了便宜,将土地贱价回赎,但亦使某些农民因之失掉了土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1939—1940年间中共在赎地问题上,将以金融政策反对地主高利贷的典地剥削与农民间的典地一同看待,这种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偏向引致债权人强烈不满。保德县段家沟村一富农说:“我典了7垧地,种了10年,每年平均粗粮能收3.5石,10年间共打了35石粗粮,原典价白洋240元,赎时用160元法币和150元农币赎去,除给人家白种了10年,还要赔老本。”(72)《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还有些债权人为逃避典地回赎,以纸币支付,或托故推诿,或逃到“口外”,或私下请人说合了事。(73)《减租减息工作与回赎土地问题报告》(1942年5月31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77页。
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晋西北行署于1941年春对减租减息条例予以修正,使之更能符合实际。同时,晋西北行署下令暂停赎地,并于同年秋颁布新的赎地办法,规定不再采用以往清理旧债计息、农钞抵白洋及用原典价赎地等办法,转取赎价当典价成数依现在地价当典时地价成数,即地价跌落几成而典价跌落几成的办法,以照顾典赎双方利益和生产。(74)《减租减息与赎地》(1942年10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10-2。延安农村调查团在调查黑峪口典地回赎问题时对此办法亦有论及,认为回赎的已经回赎了,不同意亦无办法,今后应按地价跌落程度给回赎者以适当折扣,但须照出典时货币按市价折成农钞或法币回赎,禁止1元农钞抵1元白洋的办法。(7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2页。
可见,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初,中共典地回赎办法虽略显稚嫩,存在损害部分基层群众利益、破坏阶级团结、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及借贷关系持久发展的缺点或隐患,但在具体典地回赎实践中却又表现出超强的适应性和贯彻力。中共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法令,既完成了对农村典地回赎办法新旧参半多法并行混乱局面的梳理,还引导农村典地回赎问题逐渐走向以中共策略为主导的道路。
(三)1941年11月之后
1941年11月1日,中共晋西北行署颁布《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首次以专门的法律条文对边区各类不动产回赎(包括典地回赎)作了详细且具体规定。以此为开端,或为修正《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贯彻落实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为适应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局面,边区又相继出台《关于改正减租减息条例及补充回赎不动产办法的决定》《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信》《关于减租减息赎产等法令的补充说明》《关于减租增资运动中有关问题的决定》《新解放区特殊土地问题处理办法》《关于边缘区减租减息的意见的指示》等系列法令政策文件,其中关于典地回赎的相关内容概括起来,主要贯穿了以下几方面的精神。
第一,对典地回赎对象有所限定,不仅明确了各类法令适用范围,还明晰了典地回赎须满足的具体条件。如《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适用范围限于该法令公布前成立之典约,而该办法公布后所成立之新典约仍依《民法物权编》规定处理。(76)《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1-6-3。《关于减租减息赎产等法令的补充说明》强调边区颁布的减租交租减息交息及赎产等法令不仅适用于老解放区,同时基本适用于新解放区,且老解放区于1942年后、新解放区1945年后新典出土地依双方所订契约处理。(77)《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减租减息赎产等法令的补充说明》(1945年11月16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293、294页。在典地回赎条件上,各法令一致认同典产年代久远或转成买卖关系者不可回赎。一般规定典产有典期者以三十年为界,典产无典期者以六十年为界,逾期不可回赎,未逾期则准予回赎。《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还规定“典产契约载明典期时,在典期未满前,不准回赎”;“典期不明之典产,在三十年上下不满六十年者,限于本办法颁布后二年内回赎,但典期已满不为回赎,且以买卖关系,经双方同意,履行税契或换约手续者,不准回赎”。(78)《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1-6-3。当然,并非所有已履行契约或税契且构成买卖关系的典地均不准回赎,法令规定凡因累债折产、未按公平价格而被迫作绝的活契地及死契地不应以作绝论,仍可依法回赎。(79)《行署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1943年10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2-5-9;《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信》(1944年10月20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减租减息赎产等法令的补充说明》(1945年11月16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3、294页。“在典产回赎权存续中,承典人私将典产出卖者,出典人亦有回赎之权。”(80)《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1-6-3。
第二,详细区分典地与押地,保证典地回赎依法正确处理。《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对典地和押地相关概念进行了厘定,前者释义“承典人支付典价,使用出典人之产物,此种产物称典产;借债以产物作担保,此种产物称为押产”(81)《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1-6-3。;后者释义“债务人借钱,债权人使地,钱无利地无租,钱到回赎,是为典地;而债务人借钱以土地作担保,到期不能依约付利还本,土地的使用权即归债权人所有,有钱回赎,是为押地”(82)《行署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1943年10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2-5-9。。通俗地说,典地和押地的区别在于两者交易时出典人所让渡的权利和承典人典押地目的不尽相同,典地是出典人通过暂时让渡约定期限内土地他物权获取借贷的方式,(83)龙登高认为典是土地收益与资本利息之间的交易,指地权所有者出让约定期限的物权获得借款,以土地经营权与全部收益支付资本利息,但出典人保留最终所有权或自物权,在政府产权登记中不发生交割过户;期满之后,备原价回赎土地,出典人获得贷款,成为债务人,承典人即债权人获得约定期限内的土地占有权。参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银不起利地不起租,承典人目的大多在于使用土地;押地则是“债务人通过以土地所有权或物权的担保来获取借贷的方式,须按期付利还债,否则便只能以地权交割来强制清偿”(84)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第62页。,即债权人更倾向于吃租吃利或占有土地。然在实际生活中因典权具有担保物权的功能,且押地本身形式复杂多样,两者并不容易区分。为准确区别典地和押地,以防误判错赎事件发生,《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专门对似典实押的土地交易进行例举,认为“借钱当时,未以土地作担保,但到期本息不能依约偿付,债务人即以本利作成典价,被迫将土地典出者”,“欠商人贷账,不能偿付,即以贷账作典价,典出土地者”,“质地借钱,写死契文约,到期无法清债,即抽签作绝,被迫将地出卖者”,均系押地而非典地,当以押地办法办理回赎。(85)《行署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1943年10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2-5-9。同时,这里表明典地一旦无法回赎就会走上押地或卖地道路。
对于错赎典地,《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附则》亦规定了适当的回赎办法,强调于1940年9月后、1941年11月前所有错赎典产依本办法,视其赎产付价、典产使用期限等具体情况,以不予追究、补价或退还错赎之物等办法办理。
第三,秉持公平原则,尽量兼顾双方利益。法令要求,典地回赎须考虑双方富力实况确定,若承典人为无地可种的贫苦农民,回赎者为相对富裕者或回赎后拟出租出卖者,劝其不要回赎。(86)《行署关于回赎典押地办法的指示信》(1943年10月30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2-5-9;《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减租增资运动中有关问题的决定》(1946年4月26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299页。如回赎者为典期未满无地可种的出典人,则应予回赎。(87)《七分区生产委员会决定春耕中继续减租赎地》(1946年3月4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09页。回赎典地时,出典人须根据实际情况对承典人予以补偿。如“出典人和债权人回赎时对承典人或债权人在改良土地上所消耗之费用亦须酌予补偿”(88)《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改正减租减息条例及补充回赎不动产办法的决定》(1942年4月4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21页。;新收复区“已转典转卖之强占之地,应由强占人赎回退还,有特殊原因不能赎还者,以其它方式补偿之”(89)《晋绥边区新解放区特殊土地问题处理办法》(1946年3月25日公布,8月15日修正),《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26页。。已回赎的典产,若出典人再行出典出租,原承典人享有承典承租优先权。法令还规定典地回赎赎价“一律以本位币行之,如原典价非本位币时,按回赎时之市价折成本位币再以二折至六折扣之即为赎价”(90)《晋绥边区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1-6-3。,而折扣标准亦将回赎时双方经济情况作为重要参考因素。这即意味着赎价将会根据出、承典方经济力量有弹性地进行上下调整,兼顾双方利益平衡。
中共新的典地回赎政策在减租减息运动洪流推动下,很快在晋西北农村得到贯彻。如1944年临县万安坪村的减租斗争以解决回赎土地、非法夺地为突破口发动群众,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打破地主权威,迫使地主答应群众赎地退地减租等要求,并因此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群众运动。(91)《万安坪自然村减租工作总结》(1944年6月1日),《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临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2-20-1。根据晋绥边区行署工作报告,在减租减息运动影响下,1943年兴县回赎土地916垧,偏关回赎土地12132垧,临县30个区回赎土地4727垧,临南4个村回赎土地677垧;(92)《晋绥边区的减租工作》(1944年),《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98页。1945年保德回赎和买进土地7610亩,河曲回赎土地3万亩,岢岚回赎和买进土地2万亩,偏关回赎和买进土地53494.5亩,神池回赎土地1200亩,临县大川子8个自然村回赎和买进土地9684亩。(93)《晋绥边区的农业》(1945年1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821页。减租减息与赎地运动相互配合,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回赎和购买土地的欲望,从而使农民实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翻身。
毋容置疑,典地回赎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某些乱象。如《回赎不动产暂行办法》颁布初期,实施情形并不理想,各县在执行中产生了诸多偏向,违反法令者有之,未按法令者有之,或依人情面子或依减租减息法令而无条件回赎者有之,等等。如保德县在办理钱到回赎之地时,并未依法令二折折之,而是以原价回赎。(94)《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兴县辛窑上村农民奥某典给商人兼高利贷者王某76垧土地,在1941年冬季公粮工作中被“行署干部按减租减息法令还债法,没用一个钱,便把地抽回了”。同村郭某和孙某典出的土地亦是如此回赎,以致郭某十分兴奋地说:“我是服从政府法令!”(95)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941年12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这些不合理甚或错误现象的发生,实际上折射出该法令施行之初在晋西北农村社会中的水土不服。此后,中共在原有法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切实可行的意见,如规定:“典地回赎应按原价五折行之,战前典价当地价半额,战后地价降为战前二分之一,故回赎典地应按五折、六折对出典人,二折对承典人公平。理由是现在(1942年)地价当战前五分之一,故回赎时应二折。”(96)《减租减息与土地回赎问题》,《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21-2。诸如此类的规定,推动了典地回赎活动的相对平稳和有序进行。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尽管不甚发达,或者说无论典地宗数、参与户数还是所典土地数占比均较低,但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乡间民众“钱地置换”的需求,实现了农村资金和土地资源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出典户通过典地获得了维持生活或进行商业活动所需钱款,入典户以典地方式获得了能够满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扩大经营面积所需土地。尽管此间存在某些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利用典地逃避钱粮负担、兼并土地及恶意剥削等不良行为,但就各阶层参与典地原因和实际情形观之,此类事件毕竟属于少数,典地双方借之满足彼此间钱地互通有无的利益诉求才是典地交易的主流常态。当然,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典地参与者因典而致经济利益受损,甚至失去土地等事件发生,以及出于稳定地权和维持正常农村经济秩序的目的,晋西北农村民间习惯和这一时期各类政权相继出台施行的相关政策法令均在典地回赎问题上作出诸多规定,内中尤以中共典地回赎办法最具影响力。其在战争与革命的大环境下与减租减息运动相配合,共同搅动了晋西北农村社会原有的经济政治生态,不仅使失地少地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亦使中共借此强化了自身在基层社会的政治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