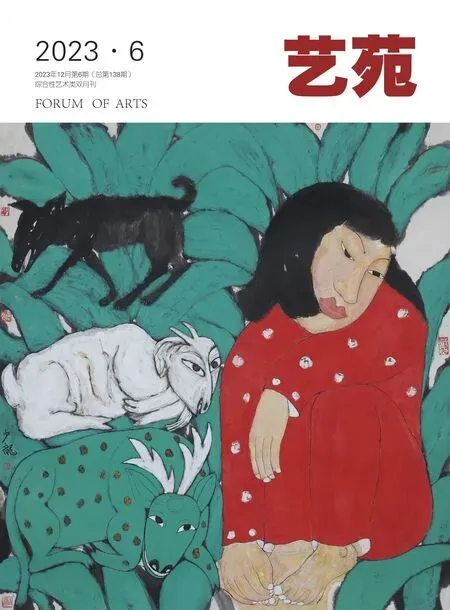情感、知识与革命的抵牾
——论夏衍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的困境
张轩岚 林清华
夏衍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革命文人,在他的艺术生命历程中,始终深切探索的是如何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特别是在戏剧领域,自《上海屋檐下》后,夏衍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抒情诗的戏剧风格。进入20世纪40年代,他相继创作了《心防》(1940)、《愁城记》(1940)、《冬夜》(1941)、《风雨同舟》(1942,与田汉、洪深合作)、《水乡吟》(1942)、《法西斯细菌》(1942)、《戏剧春秋》(1943,与于怜、宋之的合写)、《离离草》(1944)、《草木皆兵》(1944)、《芳草天涯》(1945)等。此时期的戏剧创作与抗战现实密切相关,并暂止于民族革命的结束。
身处于国家内乱外患的革命时期,夏衍以戏剧介入风起云涌的20世纪40年代,与历史进程融会贯通,与时代氛围相呼应。他的剧作“被看作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情绪史”[1]30。夏衍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群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自我价值,却又不断陷入身份焦虑、爱欲纠葛与精神围城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与革命相联系,唯有革命才能把他们从穷愁困苦中解放出来”[2]157。然而,当夏衍在深入描绘他们“如何克服自己的缺点,为创造新的生活而斗争”[2]166时,却体认到所谓的“缺点”是知识分子主体性分裂的表征。于是,夏衍以诗人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去呈现知识分子自身爱欲与革命事业的冲突,去书写知识主体与革命主体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试图化解爱欲、知识与革命之间的紧张性来引导现实斗争,并以此调适自身面对文艺与政治的张力。夏衍戏剧文本中的冲突映照出他置身于抗战现实与艺术追求之间的精神困境,而这一困境伴随他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始终,最终在政治理想实现后,因他身份的转变——作为革命者身份的终结,而成为艺术的问题。
一、情感叙述与革命表达的同构悖论
在某种程度上爱欲与革命是同构的,其共通体验是一种放恣渗透于人生又和谐于自身的生命激情,“一方面,借用恋爱的修辞,使革命呈现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在一个普遍分享着历史进化论的话语逻辑的时代,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强烈的“献身”激情,或许只有爱情可堪相比”[3]64。这既是一种欲望的革命化,也是革命的欲望化。
但同时,这种同构的革命激情与爱欲激情也是分裂的。它意味着革命主体与爱欲主体虽然共享着同一的生命激情,但在现实行动中,一个导向积极归宿,面对民族存续、社会改革、国家建设的现实危机,贡献出其全部生命热力,以群体姿态将自我消弭于宏大叙事中;另一个则消极地自绝于公众、远遁于现实之外,以极致占有所爱的他者为最终归宿,而这种占有昭彰了深度的个体意识。由此可见,这既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也是革命与爱欲的冲突,同时隐喻着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两难—现实/积极还是精神/消极。
由于知识分子的爱欲阻碍了革命事业,而对前者的放弃则带来身份的割裂,由无度索爱的主体降格为被革命所引导的客体。然而知识分子欲求成为客体的同时,悖论在于唯有主体才能有所欲求,且越是欲求,此种欲求就必然落空,因为欲求满足意味着增强自身主体性。于是,他们被反复拉扯在二者之间,并终将体认欲望的悖逆性。
(一)革命与爱情的叙述冲突
从《上海屋檐下》到《芳草天涯》,夏衍一直努力去调和革命与爱欲的叙事结构,选择以描绘三人的情感关系来揭示爱欲与革命的同构悖论。比如《心防》中的刘浩如、铭芳与杨爱棠,《芳草天涯》中的尚志恢、石咏芬与孟小云。而以《心防》与《芳草天涯》为代表,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
1.革命诱发爱情
在《心防》中,刘浩如与杨爱棠作为知识分子与革命者有共同的思想与话语,甚至二人有同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在他们为共同的革命信仰坚持做抗日文化工作时,这种革命激情推动了爱情萌发。刘浩如在杨爱棠的身上瞥见他精神的投影,看到同作为知识分子对革命身份的想象与依附,以及共同体认到由革命身份所带来的使命感与崇高性。而这种身份共享是他的妻子铭芳无能达到的,铭芳在剧中操持着繁重家务,她只能不断用衣食日常打断与闯入他们的对话,“饮食要当心”“衣服脱了线,纽扣掉了”这种种体贴叮嘱违和地嵌入在他们革命激情的表述中。而面对同等的现实困境,铭芳的忧虑细语与关怀泪水,甚或是她感受到丈夫离心却无力质问的沉默与小心试探,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此,生活流的对话与情感都太软了,仿佛没有骨头,只能作为一种与革命坚定的情感意志相对照的苍凉背景,铭芳唯有暗淡于此叙述。
但与此同时,对于刘浩如与杨爱棠而言,与革命激情所不同的是,精神的爱欲还是一种主体高度张扬的自我爱恋,刘浩如在杨爱棠的目光中确认了自身的理想形象—拥有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的革命斗士。他以远赴南洋躲避搜查来试探杨爱棠对自己的革命期待,试探也让爱意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又及时为革命所遮掩,因为一旦真正进入实在的爱情语境,爱欲不仅会损伤他们所投射的理想革命形象,还将玷污革命情感的纯洁性。最终,刘浩如只能在确认自身形象后,将二人的爱欲返还彼此。
事实上,爱欲的纠结与渴求,不仅因革命产生,还因革命情形而不断深入内里,蔓延开来。因战火封锁的现实处境激荡了他们的心魂,知识青年从精神围城中解脱出来,以自身之躯召唤一场慷慨赴死的革命邀约,不知何时就会降临的死亡加剧了当此之时的爱欲冲动。在这种高强度的意志情感产生之后,沉闷的婚姻日常便再也无法激荡其心。最终在激情的流转之间,理智复归,一切临界的爱欲面对革命现实,也不过是点到为止、不露痕迹,革命表达已然代替了他们的爱欲叙事,因为革命而诱发的爱欲,其归宿只能是非爱欲的。
2.爱情挫伤革命
正如夏衍在《芳草天涯》后记中所援引的托尔斯泰之语:“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笫间的悲剧了。”[4]416在夏衍看来,爱欲将知识青年投身于革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如果世间男女能从爱欲的焦虑中脱身而去,那么婚姻情爱对于革命事业便不再具有消极意义。
尚志恢与石咏芬,从理想伴侣沦为相互折磨的怨偶。一方面是兵荒马乱与物价飞涨的社会,加之琐碎家务与经济拮据的婚姻生活;另一方面则是爱欲的无可把握与占有。不同于没能进入革命话语的铭芳,石咏芬曾是投身于历史变革与社会风暴的新女性,但当她进入婚姻生活后,过去经历的吉光片羽被家庭经营所遮掩。为生活琐事奔波劳累的石咏芬,非但无法获得丈夫的体贴与理解,甚至感受到了尚志恢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爱意渐渐消亡与转移。她自身在同等折磨中,将种种委屈与不满宣泄于外,将强烈的情感需求转化为任生活摆布的歇斯底里。即使她在怨诉中,恍惚间体会到一种时间的冷酷,一种当下自我与过去两相对比的苦痛,但依然无能为力,便以向对方无度索求情绪价值来自赎。尚志恢的无能回应更加深了“爱之无能为力”,他的爱欲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象征革命与新世界的孟小云身上。然而孟小云并不是传统叙事中的革命引导者,她被石咏芬与尚志恢的爱欲深渊向下拽拉,她对爱情的温情想象,不过是一种“围城”之外的自说自话。面对石咏芬的幽怨倾诉与悲怆请求,她无意洞见到激情退却后的婚姻真相,看到了理想被抛却与生命力被绞杀,便仅仅在某一时刻,这种沉沦就此打住,从中抽身而去。
“爱之无能为力”意味着相爱之人,无论何种结合,都永远不能真正抵达,不能完全把握占有对方。而承认自己面对爱情与所爱之人的无能为力,他者便由此出现。但爱欲主体的无能为力无法指涉革命主体,二者虽有同构的生命激情体验,但并不同向,或者说不能同向。革命主体必定确信自身的力所能及,才得以把握与投入革命。爱欲的最终归宿是主体的无能为力与他者的出现,而革命的最终归宿是主体与革命已然浑然一体,或实现或牺牲,但在此过程并无他者的诞生。在此,爱欲对于革命的损伤正是因为主体的“无能为力”与他者的出现,破坏了革命的叙事逻辑。
(二)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悖论
然而,当爱欲主体让位于革命,接受革命主体的询唤,并不是从主体抵达主体,而是从主体降格为客体。也就是知识分子是通过让渡主体权力从而融进于革命队伍中。对于尚志恢、石咏芬与孟小云,他们选择净化爱欲的方式是投身革命,革命也由此成为爱欲主体的崇高客体|他者。但占有他者的同时,主客体由此颠倒。当爱欲主体通过成为客体才得以寄寓自身,主体的失落也就成为他们求仁得仁的结果。
与此同时,尚志恢的想象也好,石咏芬的遗憾与孟小云的期待也罢,最终都使欲望上演并落空。因为欲望成为客体一旦被满足,他者就不再是他者,主体也不再是主体,身份的割裂便由此产生。主体欲求成为客体的悖论在于,唯有主体才能有所欲求,越是欲求,欲求便必然落空,越是落空,欲求越加强烈。知识分子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饱尝主体欲壑难填之痛,只要还能有所爱欲与渴求,只要还存在爱欲主体这一身份,那么面对革命的询唤,这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便会始终上演。
夏衍的创作与援引证明了爱欲与革命这一矛盾的无解,更彰显了夏衍对这一矛盾的焦虑,消弭爱欲也意味着取缔革命的激情,所谓消弭只是无法实现的构想,唯有借助诗的叙事,与现实革命暂且割裂,在诗中寻找理想出路—快刀斩乱麻式地醒悟与出走。但这种处理非但没有解决本质矛盾,反而一方面损伤了诗,以革命召唤来书写人物们情感的纠葛与思想的归宿;另一方面却以情感的反讽指涉了无法消解的“最苦痛的悲剧”。而这种无能为力之事,或许也是《芳草天涯》此后遭受批评的原因。
二、知识主体与革命主体的动态关系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构成阶级,在社会整体上并无归属性,要么是依附与拥护某一社会形态,要么在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内审慎地越界与挑战现存社会秩序。[5]149-150当革命发生,原先稳定的社会形态被动摇,知识分子从此前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解放出来,在革命中重新寻找与确认自我身份。
(一)知识主体与革命主体的并行
在夏衍的戏剧中,无论是新闻记者刘浩如、知识青年赵婉夫妇、细菌学家俞实夫、参与过救亡运动的尚志恢,这类被深刻、细致描摹其精神世界的知识分子,还是与他们的意志、情感选择形成对照的沈一沧、仇如海、赵安涛、秦正谊等人,抑或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丑角,他们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并行的历史中并非革命主体,他们先要依附某一阶级获得身份,而后以其专业所长投身革命活动。他们或是隐匿于以工农联盟为主的革命主体中,将对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的理论阐释权让位给革命主体;或是被革命弃绝,最终因错误选择被推入历史深渊。
从《心防》到《芳草天涯》,这些知识分子从对理想的坚定不移到探索的反躬自省,最后迷惘于自我同革命之间的焦虑与期望、抗拒与想象,这一过程体现出革命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动态关系。《心防》表现了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文化工作者对民众思想防线的坚守,即“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地不被敌人征服”[4]407。在这一困厄时期,外部行动被暂时阻抑,内在的思想精神则成为革命斗争的一线命脉。所谓心防,既体现了革命主体的行动需求,同时也是知识主体的专业期望,刘浩如由此确认了自己的革命事业与身份—留守上海以笔墨为攻。
而刘浩如之所以能作为理想形态的知识分子,是源于革命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共生并行,革命的宏愿即是知识的理想,革命的冲突即是思想的冲突。这种并行的叙事使革命主体与知识主体不分彼此,在现实斗争中相互成全。而犹疑多虑的沈一沧、鲁莽冲动的仇如海,则代表了知识分子在确认自身身份与社会理想时的两种心境—“谨慎的智慧”与“深刻的坚信”。《心防》中的沈一沧最终克服了犹疑,确定了与革命并行的理想与行动,但在夏衍之后的几部剧作中,这种犹疑却被深入描绘。
(二)革命主体的询唤与知识主体的退让
而另一种情形是革命主体与知识主体无法并行。知识分子因自身的无归属性,往往容易遭受失败,由于无法具备革命的确定性与积极性,便只能从群众行动中获取力量与启悟,并使专业知识的理论原则顺应于革命秩序。“他们不断试图认同于别的阶级,却又不断受到拒斥。”[5]142因此,他们需要克服革命主体与知识主体之间的相互怀疑。
在《愁城记》中,赵婉夫妇穷尽启蒙后无路可去,长久沉溺在与左翼相悖的个体苦闷与混沌思索中,因李彦云这一革命者的现实教育,最终克服怀疑,与其一同投身于“别一个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知识分子具有无归属性与异质性,“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社会学的联结纽带,这就是教育。教育使他们显著地连接在了一起。对共同的教育遗产的分享,会逐渐消除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基础上,把单个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结合起来”[5]139。作为革命者的李彦云,因与赵婉夫妇有着共同教育经历,他既能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中,又能超越他们的精神困境,最终为革命所召唤到“别一个世界”。然而,当他最终返还并隐匿于革命群体时,标识出的只是当下的革命者身份,而非知识主体。
在《法西斯细菌》中,献身科学的俞实夫,面对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浪潮与民族革命,为保持知识主体的单纯性与独立性,对一切现实的阶级斗争、救亡运动避而不见,但这种科学理想最终惨遭毁灭。在此,其剧作主题的逻辑在于,知识分子经由探索与迂回,在千回百转的热情与危难之后,才会找到理想出路。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克服自己对革命主体的不信任,也克服革命主体对自己的不信任,最终才得以确认自己的革命身份。而这个克服过程是知识主体的自我退让,甚至是对原初身份的割弃,例如俞实夫的日本妻子便是通过放弃民族身份而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
然而《芳草天涯》却表现了克服的困境。当知识主体面对精神围城与困窘生活,革命在此成为天启式的救赎。但夏衍却走得更远,尚志恢与石咏芬也曾参与过革命运动,但革命并未长久地留下身份印记,反而成为一种被淡忘的“过去的辉煌与奉献”,生活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消减了知识主体在精神层面的广延与深刻。无论是革命或知识本身,都必然承受日常的搓磨与消耗。在《芳草天涯》中,革命是在场的,也是缺席的,它象征着一种不可追溯的辉煌过去与历史印记,一种革命与知识主体同行的宏愿。但这种宏愿的代价或许如前所述—知识主体的隐匿与退让。因而,最终典型的醒悟式结局并未真正解决困境,革命事业只是暂缓了爱欲、身份的焦虑。
(三)诗人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
与剧作互文,夏衍必然也要面对革命与知识的动态选择,也就是如何安置革命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的早期创作以历史剧与国防戏剧为主,多塑造革命者的形象,穿凿地呈现现实革命历程。当时中国文艺界经过启蒙主体的失落沉沦与无路可走,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6]21反思自省,整个文坛“向左转”,艺术的政治功用与意识形态性被极大展露出来。伴随着革命思潮与政治风暴,中国文学与革命政治关系日益紧密,“五四”以降的启蒙话语也渐渐让渡给革命话语。由于多年浸润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夏衍面对“为艺术”与“为人生”的选择,政治现实是他的第一性。其戏剧创作也在“左翼”“普罗列塔利亚”“国防”的历史律动中,形成了特定的审美形式与价值追求。
同时,因对上海“情节戏”与“服装戏”盛行的戏剧生态深感不满,于是曾热切投身于革命活动、积极追求政治表达的夏衍“逆流而上”,开始寻求源自生活、贴近现实的戏剧形式。终于他在曹禺处领悟到超越政治宣传剧之上、身为剧作诗人的艺术使命,并且洞见到戏剧在现实感召与社会批判层面的“诗力”之所在,转而思索诗人的审美追求如何与作为革命者的政治表达相互融会。在一番痛切自省后,夏衍创作了《上海屋檐下》,如其所言:“这是我写的第五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4]257
以《心防》为始,夏衍将知识分子直接推入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中。在创作过程中,此起彼伏、风云变幻的现实革命成为他天启式的狂喜经验,“通过这种狂喜,革命者得以挣脱世俗,进入诗一样的超越境界”[7]32。在此,夏衍戏剧的革命言说,既体现了革命的诗化过程,也是一种诗学的革命活动。
于是,他以诗人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从事戏剧创作,通过他所描绘的图景—知识分子身处在革命洪流中的自我纠葛、心路历程、情感爱欲与选择困境,革命与诗得以相互作用。夏衍将革命的激情寄寓于戏剧,希冀以此为现实革命寻找出路和归宿,但最终却在戏剧创作中呈现出政治革命与艺术价值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质言之,是艺术追求与革命夙愿的悖反。革命将夏衍引入了积极斗争的现实世界,而戏剧却把夏衍引入知识主体的精神世界—对历史现实的审美观照与对实践行动的审视质疑。最终,戏剧中越是在政治与知识、爱欲之间挣扎游离的知识分子,越具有诗的价值,但在现实中往往行动无能,从而自外于当下,遭受着自身缺憾的痛苦。但也正是这些徘徊困惑、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的漫长暗夜中,始终坚持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三、结语
夏衍在20世纪40年代的戏剧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创作追求与现实经验融会贯通的革命诗学。他以诗人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去描绘知识主体与革命主体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并演绎爱欲与革命同构的激情,以克服现实中知识分子沉浸于爱欲内耗而不能投入革命事业的困境。在革命结束后,夏衍的作品却遭到攻讦,那些复杂纠葛的人物形象,以及知识与爱欲的革命言说,冒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建构与国家叙事;此后,又因泛政治化的文艺批评的退潮,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被再度昭彰,而被革命表达所缓解与遮蔽的人性冲突,则成为了一种缺憾。或许这种种所谓的缺憾与价值,正如李健吾评论的那样:“千百年之后,或许有人重新要问,把这看作作品的一个小小的瑕疵。今天我们不妨先自说破,观众和作者全不错,作祟的另有一东西,叫作时代精神,在这下面我们生活着。”[8]228最终,我们看到,或许夏衍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困境与此后的现实遭遇,其本质是艺术创作中的情感与知识,如何随着历史流转与现实变革,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相调适。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