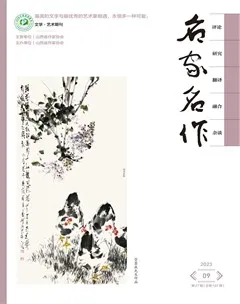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浅论伍迪·艾伦的情爱观
徐乙然
2023 年9 月4 日,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新作《幸运一击》(Coup de chance)在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作为他的第五十部作品,也是第一部法语片,《幸运一击》收获了不少影评人和观众的好评。《卫报》称“当伍迪·艾伦的名字出现在片头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Variety 的影评人欧文·格雷伯曼(Owen Gleiberman)认为这是伍迪·艾伦继2013年的《蓝色茉莉》(Blue Jasmine)以来“最好的影片”;影评人桑·布鲁克斯(Xan Brooks)发表在《卫报》的文章也认为这是伍迪·艾伦“十年来的最佳影片”。
在接受Variety 专访时,伍迪·艾伦表示本片很可能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并称 “取消文化”是“愚蠢的”。在这个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喜剧大师的晚年,却因为诸如感情和婚姻的私人生活问题导致了争议和不大体面的退场。由于伍迪·艾伦常常将电影角色与他的个人身份重叠和解构,这些都将使对他作品本身的叙事研究充满挑战。为了理清伍迪·艾伦的作品和本人的关系,本文将他电影中频繁出现的爱情与道德主题作为视点,从电影情节出发,尝试找到伍迪·艾伦对爱情和婚姻两者的某种一致性观点。
一、伍迪·艾伦的电影
(一)伍迪·艾伦的反讽爱情喜剧
伍迪·艾伦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导演和作家,一直被认为是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幽默大师之一。他在电影中所扮演的典型的、焦虑、神经质、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形象,常常被美国人视为民族符号(Pinsker,177)。另外,这种电影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身份“模糊不清”(Owens,85),这导致了电影评论界的困惑,也使得对他作品本身的叙事研究充满挑战。为了找到伍迪·艾伦电影中经常讨论的关于爱情和道德的哲学观点,学界基于其电影的文学范式和喜剧结构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莫里斯(Morris)指出,伍迪·艾伦的喜剧可以被分析为“黑色”喜剧,因为它们“颠覆了传统浪漫喜剧的循环模式”(175)。一些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根据弗莱(Frye)的“绿色世界”理论,在传统爱情喜剧中,恋人们有和解或撤退的地方(182)。然而,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这种角色之间或角色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和解似乎是不可能的。莫里斯指出,这是因为艾伦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爱情场景都被设想为“荒地”(177)。 此外,Baber 在传统喜剧中发现了“爱情公式”,即“暂时的、俏皮的性角色逆转可以更新正常关系的意义”(245)。在伍迪·艾伦的早期电影中,他也遵循了这一模式:立场、角色或身份的交换可以促进真正的爱情。但在他后来的电影中,这种模式被彻底破坏了。以电影《西力传》(1983)为例,当尤多拉·弗莱彻医生(心理医生)和泽利格(病人)互换角色时,按照传统的浪漫喜剧逻辑,我们理应看到爱情的滋生。然而,在电影中,浪漫或社会和谐的不可能实现,则表现了伍迪·艾伦蓄意破坏了这些经典期待——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
(二)伍迪·艾伦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本质
如果将伍迪·艾伦的电影与俄罗斯文学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瞥见伍迪·艾伦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本质。Chances Ellen 指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遗产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71)。 在艾伦的 《曼哈顿》(1979)中,伊萨克(影片主人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为什么值得活下去?影片中有一段伊萨克与崔西分手后的独白:
好吧,我想有些事情是值得的。 比如什么? 好吧,对我来说,我会说, Groucho Marx ,还有威利-梅斯(Willie Mays)、《朱庇特交响曲》第二乐章、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e Armstrong)录制的《土豆头蓝调》、瑞典电影、福楼拜的《情感教育》、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还有崔西的脸。
此外,在影片的哲学争论的高潮部分,即玛莉承认与耶尔再次约会后,伊萨克与耶尔对峙时,伊萨克宣称“拥有某种个人诚信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话表明,对伊萨克来说,更重要的是按照道德、伦理和美学的价值观生活,而不是沉溺于肤浅和浪漫的虚幻爱情中。从这个角度看,伍迪·艾伦的观点与俄罗斯小说的传统非常接近,后者坚持认为价值观和道德观才是完整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Chances 71)。
然而,在“什么才是完整的人生”这一关键议题上,伍迪·艾伦在电影里的回答却总以悖论和模棱两可而告终。以他的经典影片《安妮·霍尔》(1977)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片名来源于“anhedonia”,一个描述无法体验快乐的心理学术语(Chances,70)。影片中有一个闪回,当艾维在床上被安妮拒绝时,他回忆起了自己与前女友艾莉森的失败爱情:“然后,每个人都在密谋。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J.埃德加·胡佛、石油公司、五角大楼、白宫男厕所服务员?”当艾维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的政治观点时,艾莉森指出:“你在用这个阴谋论作为逃避和我做爱的借口。”然后,艾维转向观众进行反省:“我为什么要拒绝艾莉森·波特奇尼克?她很漂亮,她心甘情愿,她很聪明。 难道是 Groucho Marx 那个老笑话……我只是不想加入任何会有我这样的人的俱乐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性饥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艾维因自暴自弃(self-sabotage)而被拒之门外,这也反映了伍迪·艾伦某种扭曲的爱情观。
(三)作为悲喜剧的浪漫喜剧
悲喜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融合了悲剧和喜剧两种形式。这个词最早是由普劳图斯在他的戏剧《安菲特律翁》中创造的,剧中人物墨丘利宣称这出戏最好是一部悲喜剧:“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混合体:让它成为一部悲喜剧。我认为,当剧中有国王和神灵时,把它一直写成喜剧是不合适的。”(Mukherji and Lyne,8)在伍迪·艾伦的《双生美莲达》(2004)中,也存在着关于生活的本质是悲剧还是喜剧的争议。
电影中两位剧作家在晚餐时争论生活的本质是悲剧还是喜剧。接着影片在戏剧和喜剧之间穿梭,编剧们将一个女人意外出现在朋友举办的晚宴上,并受其影响最终导致通奸的故事加以美化,但每个版本都有所不同。拉达·米切尔(Radha Mitchell)饰演的美莲达(Melinda)在剧中(主人公是富有的劳雷尔和她酗酒的演员丈夫)是一位无聊的妻子,她在为了一个摄影师而离开了医生丈夫,并在随之而来的监护权官司中失去了孩子之后,憔悴不堪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她曾因抑郁症被送进精神病院,并被扣上紧身衣,现在她正与生活抗争。在喜剧版本中,她是一个未婚的快乐精灵,吸引了她的邻居霍比。霍比是一个失业的演员,他的妻子苏珊是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苏珊为了另一个富有的男人离开了他。
电影结尾处有两位剧作家和解的情节,“幽默存在于悲剧性的整体框架之中……看,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笑是因为它掩盖了我们对死亡的真正恐惧”。借由戏剧人物之口,伍迪·艾伦对人生的悲观看法昭然若揭:活着就是受罪,所有的喜剧都是对人生的逃避。因此,伍迪·艾伦的浪漫喜剧可以被解释为悲喜剧。此外,根据福斯特(Foster)对悲喜剧的定义:在悲喜剧中,悲剧和喜剧同时存在,但在形式上和情感上相互依存,各自改变和决定着对方的性质,从而在观众中产生一种混合的、悲喜交加的反应(445)。不难发现,悲喜剧的本质在于对立统一,而这也是伍迪·艾伦浪漫喜剧的本质。一方面,伍迪·艾伦既洞察了传统的喜剧理论,也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另一方面,艾伦对这些喜剧和文学范式的戏仿和颠覆,意味着他对所有常规形式的讽刺。然而,莫里斯注意到,伍迪·艾伦电影中的这种反讽无法解释电影中为什么反复出现关于爱情意义的讨论(179)。因此,本文旨在从悲喜剧的框架中,从情节分析和人物塑造方面寻找伍迪·艾伦的爱情观。
二、伍迪·艾伦电影中的爱情主题
爱情,作为一种情感和精神状态,通常是指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情感依恋的感觉,被视为一种美德,代表着人类的善良、同情和亲情,从最崇高的美德或良好习惯,到最深厚的人际感情,再到最简单的快乐。然而,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爱情的概念与字典中的定义大相径庭,爱情被表现为“邪恶”的根源和不道德的东西。 其中,通奸和婚外情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在《赛末点》(2005)和《罪与错》(1989)中,外遇显然是人物产生犯罪冲动的根源。
(一)爱情与性道德
1.《赛末点》剧情分析
网球专业运动员克里斯讨好一个富有的家庭,并发现自己成了他们女儿克洛伊的心上人。虽然克里斯并不爱她,但他还是娶了克洛伊,并因此获得了成功。后来克里斯迷恋上了诺拉,诺拉是克洛伊哥哥的未婚妻。 诺拉怀孕了,她要求克里斯离开克洛伊。克里斯不愿放弃婚姻给他带来的安逸生活,他谋杀了诺拉以及她的一位邻居,一位年迈的寡妇,为了迷惑警察,他拿走了邻居的珠宝,使谋杀看起来像是一起错误的抢劫。然后,他从河边的人行道上将珠宝扔进泰晤士河,却没有注意到她的结婚戒指从栏杆上弹起,掉回人行道上。当警察发现诺拉的日记时,克里斯成了嫌疑人。然而,就在一名负责此案的侦探确信克里斯有罪时,戒指却出现在一名暴力瘾君子的手中,克里斯因此逍遥法外。
2.克里斯的爱情模式
事实上,影片中克里斯的爱情模式可以大致为:对性的原始渴望,这是所有物种都存在的一种生物性驱动力;为了改变当前社会地位的一种理性协商。而通过克里斯分别与克洛伊和诺拉初次相遇的片段,两种模式的差异显而易见。克里斯被克洛伊的哥哥邀请去剧院看歌剧,这是克里斯和克洛伊的第一次见面。在这个场景中,他们之间没有实际的语言或非语言交流。当克洛伊向克里斯打招呼时,克里斯没有回应,镜头也迅速切换到舞台上两位歌剧演员的演唱。在表演过程中,克里斯全神贯注地演唱,对克洛伊的目光视而不见。作为对比,在乒乓球室里,克里斯第一次见到了诺拉,并展开一次非常露骨的对话。一开始,克里斯搂着诺拉的腰,教她如何击球。(克):“那么,告诉我,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混迹于英国上流社会是为了什么?”(诺):“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打球很有侵略性?”(克):“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嘴唇很性感?”两种明显不同的行为模式明确地表达了伍迪·艾伦预设的两种爱情行为逻辑。
伍迪·艾伦认为,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野心,可能是社会野心、浪漫幻想、对物质的野心,“关于地位的讨论是对道德的考验,看你会走多远来实现你想要的东西”(Lucia and Allen,41)。一方面,在与克洛伊的关系中,克里斯对她爱的表达只是一个标准的理性协商,并把她当作攀登社会地位的垫脚石。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理性协商的模式下的爱情与复杂的社会地位主题交织在一起。影片中克里斯和克洛伊第一次与她的哥哥和诺拉共进晚餐的场景,揭示了他们的个性,也暗示了故事的后续发展。Hole ová Andrea 认为,“电影中的食物和饮料既可以作为喜剧性和戏剧性的手段,也可以作为人生重大意义问题的醒目隐喻”(32)。在餐桌上,克里斯首先表达了他对克洛伊父亲成就的钦佩。“我一直很钦佩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富有,但不吝啬。享受他的财富。玩得很开心,支持艺术。”他对克洛伊父亲的描述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这段关系中获得的东西,彰显了社交野心。晚宴开始时,克里斯展现了上流社会的典型谈吐和谦虚的态度。然而,当克里斯对诺拉令人不满的演员生涯发表评论时,他的本质开始呈现:“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运气。努力工作是必须的,但我认为每个人都不敢承认运气的重要作用。我的意思是,科学家们似乎越来越多地证实,所有的存在都是盲目的偶然。没有目的,没有设计。”克里斯对待世界的看法再次印证了伍迪·艾伦关于人生意义的悲观态度。另一方面,“运气”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是这部犯罪电影最引人入胜的反转,即“犯罪却没有任何惩罚”。在悲喜剧的框架下,这个故事的喜剧元素在于世俗的爱情部分,它不仅包含生物的驱动力,还包含社会的野心,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认可,或许还有对家庭的责任。伍迪·艾伦似乎想让我们思考:“在一个由集体欲望驱动的世界里,情感或行动的真诚是否可能,在这个世界里,爱的概念往往被蒙蔽或误导。”(Lucia and Allen,40)“爱和欲望能否在摆脱身份观念的影响下发挥作用?”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他似乎总是宣称纯粹的爱是无法接近的。
回过头来看影片,克里斯与诺拉之间关系的变化,展示了生物本能驱使下的爱情是如何转化为罪恶之源的。在克里斯和诺拉第一次在草地上发生关系的场景中,克里斯对诺拉的爱慕、感官欲望和浪漫幻想变成了现实,导致了最终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通奸是外在表现形式,伍迪·艾伦悲观的爱情观才是核心。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他与诺拉的关系致命地走向了故事的悲剧部分。性的生物冲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是人们寻找真爱的前提,也是失去理性的陷阱。“我喜欢你喝酒的样子。你变得善于调情。”克里斯跟踪诺拉并与她调情,“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感到内疚吗?”“我们不能这么做。”“我知道。”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克里斯被情欲驱使,之后,打破禁忌的快感取代了浪漫的幻想。而当诺拉告诉克里斯自己怀孕的那一刻,克里斯开始比较自己婚姻的利益和这段偷情的利益,此时,爱情又回到一种理性协商。
克里斯在片中有两次忏悔,一次是向朋友分享这段秘密恋情,另一次是向想象中的诺拉悔过自己犯下的罪行。“我不是说我不爱她。只是我对另一个女人的感觉不同。也许这就是爱和欲望的区别吧。我不骗自己,我还没有习惯某种生活。我应该放弃这一切吗? 为了什么?”克里斯宣称他对诺拉的爱只是欲望,只是把诺拉当作满足欲望的工具。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第一次见到的是诺拉,或者他没有卷入其他关系,我们能把这种所谓“欲望”归结为爱情吗?伍迪·艾伦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担忧中夹杂着遗憾和悲观。“你知道,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总是找错女人。我想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当我母亲带我去看《白雪公主》时,每个人都爱上了白雪公主,而我却立刻爱上了邪恶皇后。”(《安妮·霍尔》)
3.性道德
外遇或通奸被认为是对传统性道德的反叛。而伍迪·艾伦对这段婚外情的结局描绘则体现了他认为克里斯的不道德性行为更接近于“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元伦理学观点,认为道德上没有对错之分。根据沙弗兰道(Shaferlandau)的定义:“我们不是在努力描述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是在宣泄情绪,命令他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或揭示一种行动计划。”(293)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如《赛末点》《罪与错》中,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都是在有外遇之后犯罪而没有受惩罚。克里斯和朱达(《罪与错》的主人公)都没有被描述成嗜血的怪物。“相反,这两个人物都体现了邪恶的平庸,他们犯下谋杀,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富和特权生活。”(Stuchebrukhov,143)影片结尾,两位主人公的生活都恢复了正常,则是再次挑战了观众的道德观点。事实上,关于两者的犯罪行为,伍迪·艾伦似乎不只是想让观众陷入某种道德困境,因为克里斯和朱达在影片结尾都对自己的罪行做出了忏悔。面对想象中的诺拉和被他杀害的无辜邻居,克里斯忏悔道:“如果我被逮捕并受到惩罚,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至少会有一点正义的迹象。 一些小小的……对意义的可能性的希望。”克里斯克服了杀害妻子、无辜邻居和腹中胎儿的罪恶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而在《罪与错》中,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朱达首先因妻子出轨和多洛丝的威胁而痛苦不堪。然后,他两次向病人(本)倾诉,最后求助于他的兄弟,后者雇凶杀害了多洛丝。
很多次我都想退缩,但我太软弱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她。在激情燃烧的时候,你会说出一些话。我只知道,经过两年可耻的欺骗,我过着双重生活。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我要输了。
朱达把忏悔变成了貌似委屈的抱怨,没有一点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朱达的懦弱,这也是他与克里斯的最大区别。他们都将婚外情视为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享乐,为了冒险,为了欲望。他们都不承认自己的性冲动是一种爱的模式,否定了一见钟情的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如果将“性”与“爱”分开,你会发现性的欲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爱本身则成为一个模糊的符号,最终导致婚姻危机的爆发。由于爱和性相互交融的本质,伍迪·艾伦在银幕上毫不掩饰他悲观的爱情观。在《罪与错》结尾,朱达摆脱了罪恶感,向克利福德做了最后的忏悔:
可怕的事情发生后,他发现自己被根深蒂固的负罪感所困扰……然后有一天早上,他醒了过来。 阳光明媚,家人围绕在他身边,神秘的危机解除了……他的生活完全恢复正常。他又回到了财富和特权的保护世界。
从忏悔中,我们可以发现朱达的内疚解脱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沉浸于犯罪的负罪感—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享受未被审判的自由。在第一阶段,他还沉浸在对多洛丝之死的愧疚中,而转折点则是朱达的闪回记忆。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犹太大家庭正在庆祝节日,整个聚会都在讨论道德和罪恶感以及上帝的存在。朱达发现他被谩骂了,他们争论的是如果一个人犯罪是否会受到惩罚:“如果他没有被抓住,源于黑色行为的东西就会以肮脏的方式开花结果……谋杀就会发生。”“我说,如果他能做到逍遥法外,而且他选择不被道德所困扰,那么他就自由了。”就这样,朱达接受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道德的,这给了他回归正常生活的勇气。换句话说,伍迪·艾伦的道德虚无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没有道德。相反,伍迪·艾伦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在道德结构中的世界。道德就是法规,但如果你无视它,它就不会存在。
因此从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可以发现他提出我们应该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性道德,否则就会被性冲动误导,导致感情走向悲剧的结局。艾伦也注意到了社会中存在的婚姻危机,这意味着由责任感、对物质获取和认可的集体欲望所驱动的世俗爱情也是有问题的。最终,无论你在关系中做了什么,爱的本质都是痛苦的。
(二)爱的遗憾
“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可以看作是对伍迪·艾伦电影中各种外遇事件的概括。为了进一步探究伍迪·艾伦的情爱观,笔者选择了两部能够代表艾伦经典电影风格的影片。 一部是《安妮·霍尔》(1977),该片通常被认为是艾伦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喜剧片之一。在文本分析之前,有必要追溯一下伍迪·艾伦对这部影片的创作思路。伍迪·艾伦对影片的构思总是无心插柳,他可能在某天晚上看完尼克斯队的比赛后回到家,在为她洗澡时,突然萌生了拍摄《你一直想知道却不敢问的性爱问题》(1972)。同时他也承认,“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但又如此夸张和扭曲,读起来就像小说”(Lax,6-7)。 因此,他在影片中的爱情观正是他现实生活经历的缩影。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伍迪·艾伦的爱情观既悲观又虚无,如果我们细细品读《安妮·霍尔》,就会发现这种悲观与爱情的遗憾紧密关联。
1.《安妮·霍尔》剧情简介
影片主要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恋人的故事。艾维·辛格(伍迪·艾伦饰)和安妮·霍尔(黛安·基顿饰)最终成为好朋友,但对艾维来说,这是第二好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某些方面与伍迪·艾伦和基顿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十分相似,“他们曾有过数年的恋情,但在影片拍摄时并没有”(Lax,9)。
2.艾维的人物形象
在影片的开头,艾维向观众讲述了两个重要的笑话,揭示了这个人物的本质:焦虑、悲观、虚无主义和神经质。此外,他对生活和女人关系的看法也在这一场景中显现出来。 “生活充满了孤独、苦难、痛苦和不快乐,一切都结束得太快。”艾维对生活的悲观看法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早熟的孩子,他总是在思考一些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当我们意识到宇宙的膨胀将导致万物毁灭之后,生命的意义何在”。与此同时,艾维因早熟而产生优越感,鄙视同学,这种自我满足感也是他和安妮分手的原因之一。
艾维对性也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片中有一个六岁的艾维亲吻同学的场景,这再次暗示了伍迪·艾伦的性伦理观,即世界上没有所谓性道德,而作为一个性饥渴的角色,伍迪·艾伦似乎主张任何年龄段的性冲动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我只是在表达一种健康的性好奇。”艾维的辩解可以理解为影片中的一种自私行为,他总是把对性的渴望凌驾于对他人的关心之上。影片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艾维和安妮在电影院外相遇,安妮抱怨自己头疼,而艾维回答说:“你心情不好。 你一定是来月经了。”“每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你都会认为我月经来了。”这段对话是艾维和安妮之间矛盾激化的缩影。即安妮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满足艾维性欲的工具,而艾维却将其视为一种幽默,这说明大男子主义在艾维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伍迪·艾伦对性的关注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总是试图传达性欲是人类的天性,是纯洁而浪漫的;另一方面,他又讽刺被欲望驱使的人最终会走向悲剧。
艾维与安妮之间的关系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非常特别,他自己宣称“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Lax, 29)。 没有过多的戏剧效果和一些引人入胜的煽情事件,伍迪·艾伦只是试图描绘现实中真正的浪漫关系。他们在影片中没有所谓的“大团圆结局”,这也可以理解为伍迪·艾伦的爱情观。“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大团圆的结局。”(Lax, 29) 再回到影片的开头,艾维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对人生和与女人关系的哲学看法之后,终于谈到了影片中最重要的问题:“安妮和我分手了,我至今无法释怀。我不停地在脑海中筛选这段感情的碎片……想弄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从两人关系的破裂,更能理解伍迪·艾伦想要阐释的爱情主题。
3 .故障原因
他们关系的破裂在于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破碎的,无法被伍迪·艾伦用惯例爱情模式解答的问题。不同于生物本能驱使下的性冲动,也不同于掺杂着社会因素和成见的世俗爱情。艾维与安妮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种浪漫的关系,为了讨论他们关系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整理影片中的情节。
艾维在网球场邂逅了安妮,很明显,他们的爱情属于先天性的。两人都被对方吸引,都想表现得得体、机智。在艾维与安妮在阳台上聊天的场景中,伍迪·艾伦使用了多种电影技巧,其中包括分镜头、人物自视、人物内心想法的字幕,这些都与他们大声说出的内容大相径庭(Lax, 26)。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物内心想法的字幕,就能从他们的自嘲中发现这种关系的纯洁性。“我涉世未深?”“听我说。真是个混蛋。他可能觉得我是个混球。”“我不够聪明,配不上他。坚持住,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很肤浅。天啊,我听起来像调频电台,放松点。”与之相比,人物说出来的话则为一些琐碎而空洞的事情,这放大了他们在这种状态下的喜剧效果。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艾维内心世界的字幕中,“她很漂亮。我想知道她赤身裸体的样子”,可见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性欲的驱使,这也可以说是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尽管艾维的性欲在某些方面让安妮感到厌烦,但他对生活的不同态度才是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艾维给安妮买了两本书,主要是关于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艾维向安妮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虚无的人生观:“我觉得人生分为可怕和悲惨两种。可怕的是绝症患者、盲人、残疾人。而悲惨的则是其他人。” 事实上,艾维悲观的人生观直接影响了他的感情生活,让他不敢在任何感情中做出承诺,也导致了他与安妮的第一次争吵。当安妮想搬来和艾维一起住时,他对婚姻的怯懦加剧了安妮的自卑:“你觉得我不够聪明,不值得你认真对待。” 暗示了艾维和安妮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
4 .遗憾对于爱情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悲喜剧的角度来解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伍迪·艾伦电影中关于“真爱”的描述是不可接近的,爱的意义就在于遗憾。有这样一个场景,艾维问行人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做错了什么。老妇人的回答很有启发性:“这绝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人就是这样,爱会消逝。”在与安妮的关系中,他鼓励安妮做的事情(在俱乐部唱歌、参加成人教育、定期看心理医生)变成了新的感情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伍迪·艾伦的爱情观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确,如果我们只看艾维和安妮之间的感情结果,艾维为安妮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讽刺和悔恨。但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对爱情的传统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是浪漫的。艾维和安妮都从这段感情中受益,对于安妮来说,很明显她在影片的最后成为一个更加独立、成熟的女性,而艾维则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具有了同理心。这样一来,伍迪·艾伦通过撕裂艾维和安妮的关系,完全颠倒了爱情的意义,暗示着只有分手之后,爱情的意义才会自动浮现。从这个角度看,伍迪·艾伦的爱情观符合悲喜剧的本质:对立统一。人们希望与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但只有当爱人离开时,人们才能充分理解爱情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伍迪·艾伦的浪漫喜剧中没有所谓的“大团圆结局”。
(三)妥协的爱
在《咖啡公社》(2016)中,伍迪·艾伦对爱情的阐释沿袭了《安妮·霍尔》中的模式,揭示了真爱的本质永远是遗憾和告别。鲍比和冯妮之间的关系又不同于后者,其中夹杂着社会因素。因此,研究他们在社会预设中的爱情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1.《咖啡公社》剧情简介
鲍比·多夫曼(杰西·艾森伯格饰)出身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梦想着在好莱坞生活的他为自己的叔叔菲尔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他爱上了菲尔的秘书瓦妮,并无意中听到了菲尔与瓦妮的绯闻。 当鲍比听说瓦妮选择嫁给决心与妻子离婚的菲尔时,他回到纽约,开始与黑帮兄弟一起经营一家高档夜总会,并在那里结识了离婚女人维罗妮卡·海斯,并迅速与她结婚。 一天,菲尔和瓦妮来到夜总会,鲍比发现他仍然爱着自己的“姑姑”瓦妮,两人开始了这段秘密的恋情。
2.瓦妮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世俗的爱情包含社会抱负,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认可,也许还有对家庭的责任,这些都很容易受到性冲动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形式就是婚外情。在《赛末点》和《罪与错》中,婚外情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也蕴含了伍迪·艾伦的警示:人们应该牢记道德标准,避免被欲望控制。这种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伍迪·艾伦的道德虚无主义,在前文已有分析。而在《咖啡公社》中,婚外情意外被描述得很浪漫,即使鲍比与瓦妮有婚外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令人反感。此外,《咖啡公社》《赛末点》《罪与错》在处理婚外情的方式上最大的不同则是:在《赛末点》和《罪与错》中,两位主人公都承受着被情妇威胁的沉重压力,并通过犯罪来摆脱当前的处境。而在《咖啡公社》中,人物之间的对抗并不尖锐。当瓦妮听说菲尔不会娶她并与妻子离婚时,她在与鲍比的关系中找到了解脱。同样,当鲍比被瓦妮抛弃时,他找到了维罗妮卡作为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冯妮和鲍比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承诺,但显然冯妮是鲍比心中的唯一,这也符合伍迪·艾伦对于真爱的解释。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瓦妮在影片中的选择,就会发现这些事情的相似之处。影片结尾处,瓦妮和鲍比在中央公园喝着红酒唠嗑的场景。第一次,瓦妮向鲍比倾诉了她选择的不情愿。“我能做什么呢?我必须做出选择。是的,我爱你,也爱菲尔。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半,你笨拙而可爱,疯狂地……试图找到自我。而我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很难……”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她把爱情的感觉放在了一边,向现实(财富、名声、体面的生活)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人物每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时,都会向现实妥协,为婚外情寻找借口和解释,将口中的爱转化为“欲望和性欲”的化身。
从这个角度看,伍迪·艾伦关于爱情的定义总是在角色关系的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艾伦对包括婚姻在内的世俗爱情的看法可以进一步解读为一种妥协的爱情,是脆弱的、没有生命力的。伍迪·艾伦电影的悲剧性再次显现:所有类型的爱情都将以世俗的爱情为结局,从而导致焦虑和压力。换言之,爱就是痛苦。
3.鲍比的爱情模式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鲍比的爱情行为,就会发现确实存在一种伍迪·艾伦认为的既浪漫又稳定的爱情形式,那就是单相思。鲍比和瓦妮之间关系的发展完美地证明了这一观点。鲍比继承了伍迪·艾伦笔下典型的健谈、性饥渴和敏感的知识分子形象,被描绘成一种真爱的追随者。他从不关心瓦妮的婚外情,两人的关系从最初的普通朋友关系发展为真正的恋人关系。然后,正如我们在伍迪·艾伦电影中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分手并向现实妥协。这样一来,伍迪·艾伦的世俗爱情观就可以明确地被解读为一种妥协的爱情观。
相反,单相思是一种浪漫而稳定的情感。它同样源于性欲,但因为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所以对象的魅力始终存在于你的幻想中。而婚外情则不同,它不受人的控制,而是受性冲动的驱使,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虽然在《咖啡公社》中,鲍比与小姨子瓦妮的婚外情并没有在影片结尾得到某种道德审问,但那是因为伍迪·艾伦并没有将整个故事呈现给观众,否则就会成为对他之前作品的一种模仿。事实上,即使在《赛末点》和《罪与错》中,偷情的过程也总是浪漫而愉快的。
(四)试图重拾爱情
爱就是受苦。为了避免痛苦,人必须不爱。但是,人又会因为不爱而痛苦。因此,爱就是受苦,不爱就是受苦,受苦就是受苦。快乐就是爱。那么,幸福就是受苦,但受苦会让人不幸福,因此,要想不幸福,就必须去爱,或爱而受苦,或因太过幸福而受苦。(《爱与死》)
在前文中论述了伍迪·艾伦电影中爱情主题的悲剧性和自相矛盾的本质,即在传统社会期望的爱情预设下,伍迪·艾伦的爱情观是悲观的、虚无主义的,爱情的意义在于遗憾。同时,包括婚姻在内的所有世俗爱情都被他解释为脆弱的、没有生命力的妥协之爱。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摆脱这种“爱与痛苦”的怪圈呢?事实上,在《曼哈顿谋杀疑案》(1993)中,艾伦提出了一个避免这种痛苦的一种平易近人的方法。
1.《曼哈顿谋杀疑案》剧情简介
拉里·利普顿和妻子卡罗尔发现他们的老邻居莉莲死于心脏病。利普顿夫妇对莉莲的死感到惊讶,因为莉莲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保罗(莉莲的丈夫)似乎对此很高兴。 卡罗尔起了疑心,决定进行调查。她潜入保罗的公寓,发现莉莲的骨灰盒不见了。卡罗尔求助于她的朋友特德,并达成了协议,他们开始一起调查这个谜团。同时,拉里发现卡罗尔无理取闹,并与一位作家调情。但在影片的最后,拉里将卡罗尔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2.爱的复苏
尽管谋杀案引人入胜,但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的本质仍然是在谈论恋人之间的关系。伍迪·艾伦指出,婚姻危机的起因在于激情的消退。当关系中没有了浪漫的幻想和性欲,爱情就会自我毁灭。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爱,它脆弱而没有生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婚外情看作是解决问题的被动方法,尽管它会导致这段关系走向悲剧。拉里与卡罗尔关系的复苏,也暗示着要想摆脱“爱与痛苦”的怪圈,唯一积极的办法就是“刺激”它。影片中,拉里明显被卡罗尔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惹恼,两人争吵不断,变得不信任他人,随着调查的进行,两人关系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感到不自在,认识到对方的弱点。卡罗尔发现了拉里的懦弱,两人之间的爱情在岁月中逐渐消逝。而拉里则对卡罗尔的浪漫幻想感到厌倦。第二阶段,尝试寻找替代者。卡罗尔从泰格那里得到了陪伴,泰格也支持卡罗尔的烹饪事业,他开始满足卡罗尔的幻想,这在与拉里的关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拉里找到了一位成熟的女作家,她也很有魅力。第三阶段,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当卡罗尔听到泰格想用她作为诱饵,吸引嫌疑人来杀他们时,她吓坏了,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浪漫幻想是多么疯狂。拉里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懦弱,并克服了它。就这样,两人的关系在重新认识中复苏。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大多数婚姻都毁于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实际上没有结局。当你与心爱的人分手并与他人开始新的关系时,也是你与心爱的人重拾爱情的机会。这也是前文所讨论的,“爱情的意义在于分手”,伍迪·艾伦总是用这样的模式来表明爱情的悲剧性。
三、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找到伍迪·艾伦对爱情主题的看法,从分析他的性伦理观入手,相关电影中关于外遇的情节则暗示了他电影中的道德虚无主义。此外,还从《赛末点》和《罪与错》中揭示了伍迪·艾伦悲观、虚无的爱情观,并将其电影中的爱情观划分为包含社会抱负、物质追求、对家庭的认可和责任的世俗爱情和性欲驱动的爱情。而在伍迪·艾伦的两部典型爱情喜剧《安妮·霍尔》和《咖啡公社》中可以探寻伍迪·艾伦电影中爱情的本质。对于两者电影情节的阐释表明世俗爱情的意义在于“遗憾”,并由伍迪·艾伦本人将爱情定义为不可接近的东西。这些发现意味着伍迪·艾伦喜剧的本质基本上是悲喜剧,他的爱情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爱就是痛苦”。此外,在《曼哈顿谋杀疑案》中,伍迪·艾伦提出了一种避免婚姻危机的可行方法。拉里和卡罗尔之间关系的恢复,暗示了摆脱“爱与痛苦”怪圈的唯一积极方法就是“刺激”它。
最后,如果我们回到《幸运一击》(Coup de Chance)这部可能是伍迪·艾伦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令人惊喜却又不意外的是,故事讲述了一位已婚女性与旧情人重逢后,她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产生了谋杀的念头——没错,似乎是《赛末点》的法国翻版。
附录
伍迪·艾伦的电影作品
《爱与死》,United Artists,1975 年。
《安妮·霍尔》,United Artists,1977 年。
《曼哈顿》,United Aritists,1979。
《西力传》,华纳兄弟,1983 年。
《罪与错》,Orion Pictures,1989 年。
《曼哈顿谋杀疑案》,TriStat Picture,1993 年。
《双生美莲达》,福克斯探照灯电影公司,2004 年。
《赛末点》,梦工厂电影公司,2005 年。
《咖啡公社》,亚马逊工作室和狮门影业,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