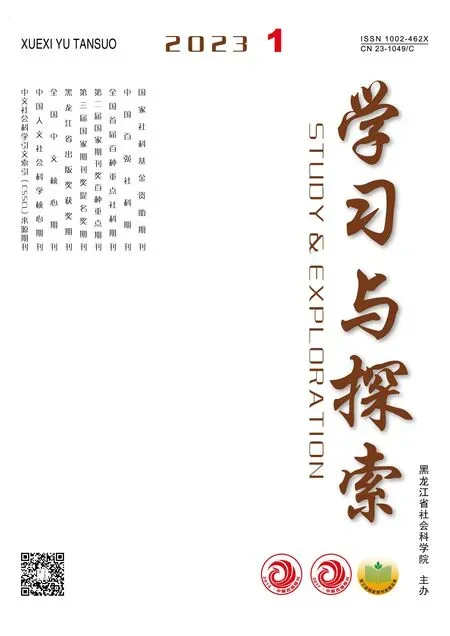新世纪新诗的“代际”命名与诗歌史想象
——以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为中心
邵 波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中国新诗的命名问题,特别是进入当代以来诗歌史的命名现象便“官司”不断,具体到新世纪诗坛就有“中生代”诗歌、“中间代”诗歌、打工诗歌、底层诗歌、新红颜写作、第三条道路等汇集了众多诗歌流派、诗学伦理和标准的讨论与问题,以上与命名有关的争论在推进诗歌运动和理论构建的同时,也凸显了诗界在追求诗歌史意义、“经典化”“好诗”“大师”等情结时的焦虑心理。而新世纪以来围绕着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命名事件和诗人群体内部诗学命名的价值纷争,也恰恰暴露出了当代诗歌史依然存在着时间滞后、撰写尺度、划分标准、批评立场等方面的缺陷。尽管如此,当下诗坛对命名的热衷,无疑对形成诗歌史写作、新诗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局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诗歌“代际”命名中的身份认同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代际问题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样,这种代际或世代的“想象的共同体”现象也普遍存在于文学史之中。埃斯卡皮分析指出:“如阿尔贝·蒂博代和亨利·佩勒所理解的那种世代,是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在各国的文学领域内,作家的出生年月在编年史的某些部分,就像‘小分队’似地一队一队聚集在一起。”[1]因而借助代际整合、归纳的研究策略,可以发现某些既定作家群的演变规律和历史走向。
纵观新世纪诗坛,“代际”命名中最具活力、冲击力的无非是“60后”“70后”“80后”诗人,但是,与“70后”“80后”对于此类“代际”命名呈默认态度,并主动“抱团”出击不同,围绕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则有“第四代”诗人、“中生代”诗人、“中间代”诗人等多种命名方式,堪称当代诗歌史上最为复杂的诗歌命名现象,这从某种侧面也证明了他们对“代际”命名犹疑、暧昧的态度。事实上,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身份更像是“准文化遗民”(赵思运语),在诗歌史中常常处于边缘、夹缝或尴尬的地位,这与他们本身的创作实力无法匹配,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童年少年时代的历史经历来看,1960年代出生诗人对于儿时懵懂记忆里的“文革”,常常采取隐晦甚至回避的写作态度,哪怕涉足也只把这段历史当作背景附着于诗中,潜意识里似乎在主动规避某种宏大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叙事,转而隐性地书写内在感受。“文革”中,由于父母忙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和政治会议,留给这群诗人相对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但是已到了“记事”的年龄,他们还是会被政治事件的余热灼伤,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感受到了家庭变故、血腥惊恐和焦躁不安。
作为幼儿园大班的儿童,已经从无处不在的画像、和大人们的教诲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个嘴角长了一颗大痣的毛爷爷,是所有人都爱的、不得冒犯的圣人。我小小年纪境界就挺高的,比如邻居逗我,问我最爱哪个,爸爸还是妈妈?我本差点脱口说妈妈,然而居然小心思一激灵,改口说了最爱毛主席……说多了“爱毛主席、爱党”,就跟念了咒语,感觉好像跟真的似的,分不清是爱还是怕了[2]。
三年级时,学校开始“批林批孔”,还要向黄帅学习反潮流,反师道尊严。所有孩子都被要求写大字报[3]。
可见,处于历史夹缝中的这代诗人,既不像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那样或肩负新时期历史启蒙的重责,或反讽戏谑中解构掉历史的崇高和庄严,也不似“70后”“80后”诗人摆脱了历史的沉重羁绊,以更加洒脱轻松的姿态面对诗歌创作,1960年代出生诗人留给诗坛的身份标签是沉潜、内敛、断裂、坚定,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张力和表现力,这使这群诗人整体迈入诗歌史之前,始终处于一种“夹生”状态。
其次,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来看,成年后的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文学资源显然比“70后”“80后”诗人更为丰厚。他们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正值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此时,人文主义环境、高等教育背景、启蒙运动勃兴、国外文学艺术思潮,以及多元的文学氛围和诗学文化,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群诗人,初步汇集成了他们的灵感源泉和创作意识,“最多的时候,到大学二三年级间,我已有十几个抄诗的本子了……它们按国别或流派分类,更多的则是诗人的个人诗抄。要是你认为抄录除了是细致的阅读,还是一丝不苟的仿写,那么,现在不知藏在哪里的十几个本子,留存的该是我诗歌学徒期最为实在的自我训练”[4]。同时,西方文学理论通过各类出版物译介“入关”,又形成了诗人诗学理论的资源,其中包括《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季刊》《上海文学》等流行刊物;而中国本土的文学与文化思潮更是繁花似锦,像朦胧诗论争、人道主义大讨论、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小说、先锋话剧等,以及港台流行文化、亚文化思潮,影视、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也都为1960年代出生诗人“广开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1960年代出生诗人在诗歌的学徒期幸运地赶上了一场“思想文化补课”,随即产生了先锋探索、艺术实验、自由创作、个人化写作等多种可能,这为其在新世纪诗坛持续性地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最后,从当代诗歌史与时代的关系来看,当诗歌进入1990年代,与“70后”“80后”诗人以相对轻松、自由的态度进入商业化社会不同,1960年代出生诗人面对社会政治的变迁,其身份认同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这段时间,他们感受到转型对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撕裂,作为这场时代剧变的亲历者,1960年代出生诗人难以摆脱历史现实因袭的负荷,这种无形的压力与失语状态甚至表现为对写作理念、价值信仰的自我怀疑和重新审视:旧有的写作理念、价值尺度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诗人重新解释世界、打量诗歌的原则和方法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份: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无论从道德理想,还是从生活方式,还是从个人身份来说,我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所以这时就我个人而言,尴尬、两难和困境渗入到我的字里行间”[5]。确实,与前后几代诗人相比,1960年代出生诗人充满“生不逢时”的感慨,大约十年的代际差异,却唤起了内心的“迟到感”(张枣语),但是也正是由于“迟到者”的身份,迫使他们在路上独行,撇开了诗坛内外不必要的牵绊、阻碍,沉潜于“个人化写作”的经验积累中,正如布罗茨基在谈及时间与节奏的关系时说过的那样,“一个诗人在技艺上越是多样,他与时间、与节奏源泉的接触就越亲密”[6]。时代的大浪淘沙过后,1960年代出生诗人窥探到了时间和艺术的隐秘关系,才愈加在时间的褶皱中冶炼写作技艺,探索诗歌承载历史、介入当下、触及现实的可能。
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集体性命名,凸显了鲜明的以年龄为准绳的代际特色,即一代人共同的经历、情感与命运,而当代诗歌史借助代际整合、归纳的策略,可以整合出某种既定作家群的演变规律。确实,这代诗人精神上与其前后诗人明显格格不入,历史时代强行预设的精神气质又规约了他们的写作走向、艺术维度和诗学形态,这使其精神和写作常处于一种夹缝之中,自我身份尴尬难辨。但是,代际之间的精神气质无所谓孰优孰劣,1960年代出生诗人遭遇的幸与不幸却恰如其分地暗合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几次起伏、变迁,鲜明地烙印下时代与历史的精神徽记——一切都处在相互拉伸的两端,他们身上那种80年代延传下来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以纸角做旷野”的“肉搏”精神在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洪流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曲高和寡,最终幻化为诗歌中的永恒风景和别样的诗写历程。
二、迟来的“代际”命名与诗歌史的缺席
由于时代和诗人性格的双重因素,196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虽然在1980年代末期便诗出江湖,但诗界和批评界并未给予他们公允的定位和相对合适的命名。直到新世纪初,广州诗歌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专号《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期间安琪大胆推出诗论文章《中间代:是时候了!》,率先启用“中间代”对这群“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7]的沉潜者加以“代际”命名。1969年出生的安琪,以一股为同代诗人呐喊的热情“代言”,对这代夹缝中生存的诗人进行一场“拯救式”打捞,希望赋予这拨坚守诗歌十几年,新世纪诗坛最为活跃的支撑者以“合法化”的身份。“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7]
诚然,当代诗歌史上命名本就纷繁复杂,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前后也经历了多次的命名之争,诸如“第四代诗人”“85年一代”“新世代”“中生代”等均产生过一定反响,相对来说,安琪命名的“中间代”的影响力更大。当初,诗人安琪综合多方因素适时道出自己的主张:
因为命名的艰难,人们至今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盘旋在他们头顶的是一系列没有统一的概念。这同时也成了我们着手本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难题,在多次的商谈探讨和征求意见之后,礼孩和我最终确定下“中间”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它彰显了如前所述的两种指认:一、沉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7]。
这群“无名”诗人与其前后两代相比,可谓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沉潜期,即使“中间代”命名后,还是难以摆脱其尴尬、犹疑的窘境,主要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中国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逐渐兴盛,迫使许多知识分子转移阵地,不再单纯地以诗为业,坚守下的诗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力量,重振旗鼓;其二,在“个人化写作”的大背景下,1960年代出生诗人已独自摸爬滚打多年,冠之一个集体的“代际”命名往往会使他们内心感到疑虑、别扭,所以常常对命名之争淡然处之;其三,1990年代末期诗界“盘峰论争”过后,这代诗人更是有意规避纷争四起的口水仗,不愿再为诗歌之外的“人事纠葛”耗费过多精力。因此,诸多原因使然,让“中间代”命名时运不济,无法真正做到“名正言顺”。
新世纪以来作为一种“追溯性”的诗歌命名方式,“中间代”是在个体创作不断精进,艺术水准较为成熟的阶段,形成的一个相对松散、自由的诗歌群落。同样,他们也是迫于前后两代诗人的挤压,以及诗坛整体格局的逐渐形成,才想借“中间代”杀出重围,以集体的力量获得公允、公正的诗歌史评价。因此,2004年《中间代诗全集》正式出版以后,部分1960年代出生诗人相对支持或默许了这一命名概念,以“代际想象”吸引更多诗人扎根于此。“如果说,由黄礼孩和我共同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意义在于为中国诗界贡献出了一个概念‘中间代’的话,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全集》则意图使这个概念吸纳更多优秀中间代人的进场。”[8]这种“全集式”突围与诗歌史的想象,虽然有目的性和策略性因素裹挟其中,但却集中展示了1960年代出生的82位诗人的2200多首诗作和大量诗论文字,为文学史打造了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文本资料平台。
她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可以说是继《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后朦胧诗全集》(万夏、潇潇编)之后最重要的诗歌总集了,是当代诗歌史上无法忽略的重要文献。虽说在概念界定和诗人的取舍上引发了一些分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它给“第三代”之后没有赶上90年代“经典化班车”的一大批诗人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通过这次集合而“进入历史”,成为当代诗歌谱系中一个有机部分,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9]。
可以说,《中间代诗全集》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当代诗人就有侯马、安琪、马永波、哑石、徐江、伊沙、臧棣、余怒、黄梵、潘维、叶匡正、娜夜、古马、唐欣、路也、树才、桑克、蓝蓝等,可见这代诗人阵容之强大。
时至今日,安琪“中间代”的命名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抛开历史的陈账,不管当初诗人们对命名出于何种盘算、立场或仅仅是美好的愿景,他们间接都促成了一个事实:诗坛、诗评界都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这场事件,努力实现新世纪诗人在保留创作差异性前提下的内部团结与“大同”。近十多年的时间里,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队伍又汇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像潘洗尘、李少君、古筝、凸凹、陈陟云、周瑟瑟、邱华栋、刘不伟、瘦西鸿等重归诗坛的健将,以及衣米一、歌兰、子梵梅、衣米妮子、樊樊等诗坛的加盟力量,均竞技于新世纪的时空舞台。可以说,命名之初,安琪的遴选原则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成熟于1990年代,由于年龄或个人原因并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和“两报大展”的一群被遗忘者。但是如前文所述,2010年前后,更多诗人怀揣对诗歌的向往进入诗坛,其中便有为数不少的1960年代出生诗人,况且很多个体诗人也萌生了加入群体的意识,希望依靠群体的影响力抱团取暖,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原有的“中间代”的划线标准愈发显得不适应当下诗歌的发展。因此,笔者根据时代的变迁和“中间代”命名二十多年后的诗人群体、艺术风格等方面新变的特点,倾向于使用更加中性、客观的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这一概念,囊括整个代际的诗人,以期从整体记录下一代诗人的精神履历,并对他们的创作实绩和文学史意义予以公允的评价。
三、沉潜中的灵魂:四十年的诗写履历
四十年左右的写作时间里,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走过了从沉潜到自救再到获得诗界认可的坎坷道路,其间心酸只有个中人知晓。然而,这代上百人、上万首诗作可以证明,那清寂冷峻的社会生存现实不但没有导致诗人大面积的“逃亡”或者精神空转,反倒夯实了他们相对扎实、隐忍、谐和的内敛气质,自觉地向僻静、崎岖的诗路探险,从而征服了“个人化写作”的制高点,他们的经历和诗写恰恰组成了新世纪诗歌史鲜活、生动又复杂的侧影。
2001年安琪对“中间代”的命名俨然成了这代诗人命运和诗歌创作的分水岭。大约在1990—2001年间,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重组与建构,他们默默地履行着诗人的职责,于极度贫瘠的文化土壤中坚守自己的诗学理想,自始至终地葆有纯然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像余怒的《守夜人》《苦海》这两首诗便是1990年代前期诗人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写照。《守夜人》中作者将夜晚飞来飞去的苍蝇编排入诗,讲述自己被它侵扰难以入眠的心理活动,“我”梦寐中并未把苍蝇马上拍死,而是诅咒般地以威胁的口吻给它下了最后通牒,“十二点三十分我取消你”,当然,当作者再度沉入梦乡的时候,已无力执行苍蝇的死刑,只能无奈地留其在耳边嗡嗡作响。这是一件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琐事,但余怒却略带幽默地以事态因子的流淌展现出了现代人真切的存在状态:细琐、无奈、乏味,同时那深夜中不绝于耳的响声也渗透出生命的孤苦、尴尬与困顿。《苦海》则可看到诗人遭遇各种外力挤兑时精神的铮铮反抗,诗中人生好像一片绝望的“苦海”,作者漂浮其上却神经质似的反对“一个水泡冒出水面”,实则反对着一切政治与商业权力在体制内部不断置换、合谋的现象,以及那些千篇一律的躁动的时尚与物欲,他将自己置于“布道者”的“先知”位置,在精神泥淖中汲汲营求灵魂的超越和救赎。
新世纪前后,受惠于“个人化写作”的1960年代出生诗人,虽然分散各处冶炼自己艺术的琴瑟之音,但他们还是拥有共通的精神“内环境”,不约而同地朝长诗领域拓进。繁育长诗的土壤在人们心中似乎早已沙化,为追求“加速度”,诗人们操练的大多是短小精悍的短诗,1960年代出生诗人却知难而进,变相地把长诗导引入写作的版图。安琪便凭借其形体怪诞、语言盘诘的长诗“异军突起”,有《轮回碑》《庞德,或诗的肋骨》《九寨沟》《加速度》《灵魂碑》《在北京》《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清明上河图》等二十余首。经过漫长的长诗写作,安琪业已形成了日后的艺术风格和先锋品质,最关键的是蓄积了足够的精神能源来抵御众语喧哗的消费社会而不被吞没,从中彰显出这代诗人坚定的诗写品质。如安琪的《轮回碑》,诗人把个体生命、个人记忆与历史现实、人生人性绾结于一处,使长诗中包蕴更多的精神内涵与感知体验,提高了诗歌容纳智性思考的比重和分量。
直到成年我甚至不懂如何简单地犯罪。/我有一个希奇古怪的老舅公。/他说,剪刀可不是用来修理地球和迷雾?/我像喜欢呼吸一样喜欢陈词烂调。/在我身上,长着两只可持续发展的抽屉。/它们总是处于白痴状态。/无穷无尽的白日梦浪费了我的气味和感觉。/以至我出去两次都不能找到地狱。/我发火了!/我的拇指捆着一封自杀症患者的信。/它威胁我它可以报复我用强奸或嫉妒。/我们只好抽签决定胜负。/一些尸体堆积起来无法整容(《轮回碑·二 我生活在漳州[教条小说]》)。
作者以谵妄式的语言和荒诞的结构诠释生活中那些平常却又触目惊心的事物,仿佛“庞德的肋骨”嵌入安琪的体内,乖戾地默念出了诗歌的谶语。诗中,诗人分裂的性格本质暴露无遗,血腥粗粝的语词纠结根植于胀裂的思维,缺少连贯性的诗句又组合成了日常生活的怪诞细节,让所有历史、事件、场景幻化为不知所终的文本实验,扭曲地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后现代状况”。
新世纪以来,1960年代出生诗人度过了他们情感的迷茫期和精神与写作的沉潜、酝酿期,然而“70后”“80后”诗人迅速抢滩登陆,将相对平静的诗坛氛围打破,这是1960年代出生诗人始料不及的。新世纪诗歌史的自觉意识于心头萌生,此时无论诗人数量还是诗作,都出现了一个井喷期,其中不乏品牌佳作,如侯马的《他手记》、徐江的《杂事诗》、雷平阳的《云南记》《出云南记》、李少君的《草根集》《海天集》、臧棣的《慧根丛书》、余怒的《饥饿之年》等等。这个时期,许多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艺术倾向性更加明显,他们或向古典传统诗词“借火”,或从自然天籁中寻求滋养,或在细腻的语言打磨下提炼诗情等等。如谙熟中国传统文化肌理的李少君,就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语言渗透着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的凝思默想,浅白、简隽中不但让诗人拥有了儒家的性命道德之学,也流露出了佛性之悟和生命感怀,玄想宇宙天地生灭相继、循环轮回的法门与奥秘,并通过自然景象的推衍和铺展,将语言锋刃上的诗情与禅意嵌合起来,使视线所及内化为心中所感,融汇于“心无所得”“缘起性空”的佛性体验之中,营造了一个空灵、飘逸的大自在圆满之境。同样,川美的长诗《追梦桃花源》也独具出世之思和魏晋风雅之情,似乎古代诗文的精神原型和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已融合为诗人现实需求的一部分,缔造了一个忘却凡尘忧扰的世外仙境,复兴了文化母体的勃勃生机,在种桃树的间歇“种下一种简单生活”来“洗濯我们蒙尘的眼”。不难看出,魏晋风骨与唐诗宋词对1960年代出生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情感节奏、言情方式和心灵慰藉等方面,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从而使诗人穿越古人“夕阳无限好”“夜长人奈何”的意绪闲愁,从人性、历史、文化的角度反思危机四伏、污浊不堪的现代社会,化解了语言与现实、现代性与古典文化、技术理性与自然美学间的矛盾。至此,1960年代出生诗人从写作到精神步入了一个多元、全盛时期,诗歌显露出了一种少有羁绊的自如与洒脱,形式因而趋于自由、开放,诗艺水准得到广泛提升,这都为他们进入文学史增添了筹码。诚然,由于1960年代出生诗人人数众多,所以诗集质量可能良莠不齐,具有从众心态和沽名钓誉心理的也不乏其人,但从中可以窥探到诗人群不同以往的精神气候:他们宁静地恪守艺术圭臬,延存自身敛静节制的写作风格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使其晋升为他们“傲立群雄”的资本,抵御浮躁社会的法宝;而他们绵绵十几载蓄积的艺术源泽,又保存了诗人追逐“先锋”的足够动能,以致那不可胜数的文本,足以与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数量相媲美。
不可否认,新世纪诗歌史以时间为准绳的命名标准可能是“讨巧”“偷懒”的行为,代际诗人群体的划归也确实可能会遮蔽诗人之间的个性和多样性,有“贴标签”的嫌疑。但是综合考虑,每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时代的共性,这种相近的艺术实验也是社会历史背景的记录和凝缩,尤其是在新世纪诗坛个人化写作如此兴盛的时代,此种兼具社会学、文学、美学的命名规则,正是通过对相同代际的显著特点、不同代际的比较研究,以整体视角关注当代诗歌史的发展脉络。作为新世纪诗坛的重要诗人群之一,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对当代文学及当代诗歌写作的贡献不容抹杀,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借助“代际”命名整合多样性的诗歌文本,搭建诗学的传播空间,这有助于归纳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共性美学价值和发展脉络,重塑代际诗人群的组成结构、筛选标准以及诗歌史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