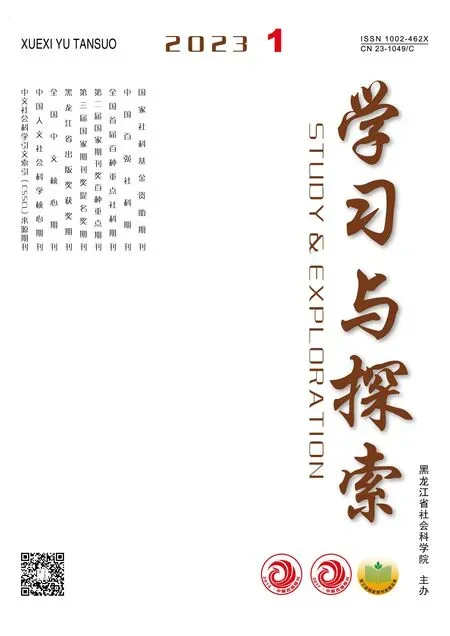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系统的整合
朱 志 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自己的概念系统,而依托于中国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古代画论、书论和诗论等,其概念又在此基础上彰显各艺术门类自身的特点,出现了一系列术语、范畴和命题,贯穿在整个美学思想体系之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征。这些概念有着自发的潜在系统,又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概念,需要我们在尊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特征的基础上,从适应当代美学学科要求的维度进行理论建构,使中国古代美学概念得到充分阐释,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体系建构中呈现其价值。先秦孔子强调“正名”,荀子强调“名定而实变”,韩非子强调“循名责实”等,都是在强调概念研究的重要性。
一、美学术语的基本特征
概念是对事物规律和特征加以概括的名称,是知识的体现,是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概念体系中,我们可以把概念分为术语(一般概念)、范畴(核心概念)、命题(用短语或短句所呈现的概念)三个方面。因此,美学概念的基础是美学术语,美学范畴是美学中的核心术语。广义地说,所有的美学范畴都是美学术语。而命题的含义则是比术语更明晰、更丰富的表达。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把美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等都统一在“范畴”的名称之下,他在《引论》中也承认是:“统而论之,不作严格区分。”[1]中国古代的美学概念,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献之中,与西方美学有内容类似和相近的概念,但是也有着更多含义不同的概念,这正是中国古代美学独特价值的基础。
术语主要指本专业的专有名词,或在本专业有独特的含义的一般名词,是专业内的一般概念和基本概念。中国古代大量的美学概念,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都是基于具体生动的审美现象的概括。我们在当代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特别是把它们带进全球化语境中的时候,需要根据当下的学术规范,尽可能对它们加以科学的界定。西方不同的理论家在使用相同的概念的时候,含义有所不同,他们也都会各自做出清晰的界定。
中国古代的美学术语,具有开放性特征。术语通常是名词或名词性的词语,其中包含着单一名词或合成名词,常常由近义词词素和反义词词素构成双音词,在新的组合中拓展自己的表达能力,从而扩大术语的运用范围,使审美现象中的丰富意蕴不断地得以表达,是一种有效的阐释工具。在历代注经著作中,也有对字词的简要解释,但是与西方从学科的角度定义是明显不同的。具体的术语虽然有提出的背景,独特的视角和问题意识,但主要是作为工具使用,需要运用相关的词素,从方式、途径和效果等方面加以整合。
西方的美学术语大都是抽象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美学术语大多并非纯抽象的。中国古代的术语,大都具有名词的性质,也有不少是感性具体的运用描述和比喻等形象性的语言。这些术语常常具有具象特征,并且从具体审美现象中凝练范畴,反映了古人重视审美体验和类比的思维方式。比如妙、神、象、风骨、气韵等范畴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有一个线索存在。中国古代的文字和语言表达有着摹物等感性特点。中国古代运用语言摹拟外物情态,摹拟中有概括和归纳,许多术语中包含着具象特征。古人通过感性形态揭示其本然面目和特征,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比拟和抽象方式看待外物,如阴阳、五行也是一种抽象和归纳的结果。许多术语,出自主体的直觉体验,以通感和诗性的思维方式加以表达。中国美学中的味和滋味,乃是从感官的生理体验到心理体验,是一种超越视听感官的心灵体验的描述,是运用感官感受对心理感受比拟性的表达。包括作为动词的运用,用味表述心理体验和感悟。“滋味”等概念最初从原本是一个具体感官味觉的名词概念,经过刘勰和钟嵘等人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逐步上升到具有普遍规律的核心概念,即范畴。我们在今天的继承和发展中,需要科学地加以界定。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大都是在哲学术语的基础上,结合文学艺术实践向前延伸的。它们虽然延伸到具体学科时会有含义的差异,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解读依然可以以哲学概念为参照。哲学术语与艺术如音乐、绘画术语的结合,气韵就是一例。在思想的展开过程中,气韵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日渐呈现出核心术语的特点,成为美学范畴。
艺际交流对中国美学术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同门类艺术,曾经是综合一体的,后来逐渐分化。例如诗歌是中国古代诸艺术门类的纽带和灵魂,无论是诗书画的一体,还是诗乐舞的一体,乃至戏曲艺术、园林艺术都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值得我们加以提炼。不同的艺术门类,多有借用、化用术语和范畴的情况。如“本色”本来源于绘画,移用于戏曲,“白描”也源自绘画,后来被用到小说评点之中。再如绘画中的“色调”,涉及绘画对音乐知识的借鉴。我们需要从人文学术思想的总体背景中提炼美学思想,美学术语的提炼也同样如此。
古人从物我关系中审视审美现象,提出美学术语。心物关系是审美活动中的核心关系。中国古代美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中,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审美活动中的物我关系,包括意与象的关系、情与景的关系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优秀而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周易》的“立象尽意”开始,到景中情、景生情、情景交融,情与景、情中景、情生景等,古人都是在探讨审美活动中的物我关系。
在汉语中,许多美学术语是本义的一种引申和拓展。借用日常术语,又超越日常一般的认知,赋予其审美的含义,具体表达主体的审美体验。中国古代常常以身体和生命比喻艺术作品的本体,许多人体形态和内在精神的术语被用来譬喻艺术作品和审美现象,从中体现出生命意识。其中既有有形肉体的骨、肉、血、脉、筋等身体成分,又有无形的神、气、风等。中国古代学者通过生命意识来看待书画艺术,作为隐喻或转喻,用它们来形容书画的生意,以具体的物象表达抽象的意蕴。所谓的品味和品,是从味觉借鉴过来的术语,重在评价审美对象的层次、格调和风格。当然,古代的这种拓展有的在今天看来也有不当之处,例如把五音视为相应的社会症候的象征与呈现,颇多牵强之处。不过,通过诗性思维方式所呈现的审美特征,依然有其启发意义。
美学术语的含义是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的。一些哲学术语和艺术术语发展成核心的术语,即范畴,衍生了若干相关的美学术语和范畴,其中体现了人们审美趣味的变迁。在具体美学思想的阐发中,一些美学术语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以及情感色彩的变化,都推动了美学思想的丰富、深化和发展。有一些艺术门类的专业术语由于艺际相互借用,或者扩大了内涵和外延,在发展历程中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特定术语的含义在变迁过程中的丰富性,对我们的继承发展意义重大。美学术语的生成和发展,影响着相关思想的进程,在今天看来,也影响着美学学科的进程。
二、作为枢纽术语的美学范畴
中国古代的范畴一词,源自“洪范九畴”,指天地大法的九类规则、九种类型,由于它的含义包括典范、模式的类型,在哲学领域被用来翻译亚里斯多德的Kategoria和康德的Kategorie,意指典范的名词和术语。范畴是历代学者提出的描述基本规律和特征的核心概念,是学科概念系统中的关键概念和核心概念,是本学科从具体事物和现象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基本规律和根本特征,揭示了事物相互之间的联系。范畴经过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的选优汰劣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包含了思想家们的卓识。中国古代重要的范畴虽然在形式上未能得到科学的界定,但在学术共同体中其内涵有着固定的含义,并且长期沿用,约定俗成,获得了继承和发展。
范畴具有普遍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比一般术语更为抽象,起着统领作用。它支撑学科,对学科起到统领作用。张岱年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等,不能叫做范畴。”[2]与一般概念即术语相比,范畴属于大的部类,属于种概念,而一般概念属于子概念。范畴与一般术语的关系,类似于种概念与子概念、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气”“兴”等作为核心概念和种概念,就是范畴。范畴中包含着特定的范围和类型,是一种类概念。范畴中大的类概念衍生出小的类概念,如由“气”衍生出“气韵”。
作为美学一般概念的美学术语和美学范畴的关系,是相对动态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并且与时俱进,逐渐演变。在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人们充分意识到一部分美学术语对于美学理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样可以升格为范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范畴是不断产生、丰富的,有继承和发展,不断有新生的内容。范畴的地位与具体美学术语的使用史和研究史有关。如“意象”在刘勰那里还是一般的概念,经过1700多年的使用,它就逐渐成了范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美学范畴带有学科的特征,在美学学科概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美学范畴在美学术语系统中,起到一种纽带作用。范畴在学科内更具有普遍性,在学科中起着支撑和骨干作用。范畴是一种种概念、类概念,有渊源的是种概念,有类型分别的就有类型差别范畴,有结点意义,揭示诸多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范畴是体现特定现象基本规律和特征的概念。相比于一般美学术语,美学范畴更进一步体现了审美的内在规律和内在联系,从中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和体系性。范畴的系统性特征,包括内在特征和外在范围、界限。许多中国哲学的范畴,理论本身就是抽象的,但对于美学来说,抽象的理论又是奠定在具体的现象之上的。
一方面,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古人又从艺术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提炼出一些范畴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有潜在体系的,这个体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独特的范畴体系为基础的。从老子开始,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就有一个潜在的逻辑系统。美学范畴及其系统乃由哲学范畴转化而来,如“道”“气”由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转化。其中体现了古代哲学家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形神、和等范畴,都是从事物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其中也包含着审美规律,体现了自身的系统性。在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许多范畴经历了从哲学范畴到艺术范畴的转变过程。风骨范畴则从人物品评拓展到艺术品风神和风格的评价,再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审美范畴。许多美学范畴源于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展开,与哲学思想及其潜在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如《老子》和《周易》等思想中的美学范畴。意境范畴是在佛学思想的启发下,对意象思想研究的补充和深化,指“意象的境界”。王夫之从佛教因明学中借用的“现量”说,也是对哲学范畴的移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范畴常常讲究词义的对称,体现了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和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相反相成如阴阳、动静、虚实、言意、形神、巧拙、清浊、疏密、文质、雅俗、阳刚与阴柔等,反义或相对应的词素构成的范畴,具有辨证性的特点。中国书法中的黑白、浓淡、枯润等,都是相反相成的范畴。它们都从传统的一般哲学术语到哲学的元范畴,又被移用到具体审美范畴。
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各门类艺术思想中的范畴,都依托于中国哲学中潜在的逻辑系统,同时又从艺术实践中提炼范畴,或在整合中体现两者的统一。例如节奏和风格与阴阳的关系,五音与五行思想的关系,作品中的虚实、动静、形神关系,乃至言意关系等,都是从哲学系统出发影响到艺术欣赏的。中国艺术思想不只是借鉴哲学范畴,而且在本质上体现着哲学精神。这也是哲学本身体现事物普遍规律的特质所决定的。许多源自哲学的美学范畴被运用到艺术作品的品评之中。例如,“气韵”就是在抽象的“气”的范畴的基础上,基于具体的音乐韵律内容,形成一个新的虚实统一的“气韵”范畴,上承哲学理论,下启具体的艺术特征。再如“传神”,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形色”“神气”等,都是形神范畴在中国美学中的具体展开。美学范畴既有从基本哲学思想中抽取的,也有从艺术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概括和总结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范畴,有许多是对艺术创作、作品本体和欣赏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古人常常从具体的思想表述中提炼范畴。
范畴包括本体范畴和风格范畴。诸种艺术风格范畴,正是审美意象个性风采的呈现。更多的美学范畴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后续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得以丰富和成熟,并且指导和评价后续的审美实践。例如墨戏作为绘画范畴上升为一个美学范畴。再如意象的范畴,可以用来评价现代艺术、西方艺术,获得了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许多美学范畴源自具体的艺术范畴,后来又拓展为更为抽象的文化范畴。
历代各种艺术风格的名称,就是典型的源自艺术作品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代对诗词等文学作品和书画、乐舞、戏曲的研究,概括出多种艺术风格,体现了基于意象的意境整体特征。其实在审美对象中,也存在着各种风格类型,只是在艺术作品中更为典型,并通过艺术语言加以固定。其中既有与西方艺术风格相同或相通之处,如阳刚与阴柔、豪放与婉约、优美与壮美等,也有着各种具体的中国独特的审美风格。其中主要以清(如清雅、清奇、清丽、清婉、清扬、清越、清辩、清远等)、淡(如平淡、淡泊、冲淡、古淡、闲淡、枯淡等)、远(如清远、悠远、闲远、萧散简远等)、逸(如飘逸、野逸)等具有代表性。而风骨(包括风力、骨力、格力等)则体现了特定风格的神采。中国古代常以“品”称艺术风格,也有以“势”(如王昌龄《诗格》中的《十七势》)等概念描述风格。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最早,后继有清代黄钺的《二十四画品》(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淡远、朴拙、超脱、奇僻、纵横、淋漓、荒寒、清旷、性灵、圆浑、幽邃、明净、健拔、简洁、精谨、俊爽、空灵、韶秀)和清代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等。直至今日,依然有人仿作《二十四书品》等。(1)二十四是中国古代的吉利的数字,故多沿袭使用,不代表二十四种风格是严格区分了这些风格的不同,其间未必有严密的分类,也未必穷尽。
范畴之中又有元范畴和复合范畴。元范畴一般是一种单一范畴,是组成复合范畴的基础。和一般美学术语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有着衍生的特点。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是历史生成的,范畴内涵的扩展和变迁,体现了词义的衍变规律。上古更多的是单音词元范畴,如气、韵、神、象、意、境等。后来组合、衍生了诸多的双音词复合范畴,若干范畴衍生出系列范畴。在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两个元范畴可以熔铸成新的复合范畴。不同范畴加以组合,各自构成诸多范畴,体现了生命意识,如骨,形成了“风骨”“骨力”“骨气”等一系列新的术语和范畴。在美学概念体系中,元范畴以单字为基础,由元范畴通过组合衍生出双音词复合范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有众多由观、韵、趣、味等元范畴所组成的双音词复合范畴。如“观”作为元范畴,则有“观物”“观道”“观妙”“观化”等;“韵”作为元范畴,则有“气韵”“韵致”“风韵”“神韵”等;“趣”作为元范畴,则有“情趣”“理趣”“逸趣”等;“味”作为元范畴,则有“趣味”“滋味”“韵味”等。唐代将“兴”与“象”两个元范畴整合成一个复合范畴“兴象”,使其含义获得了拓展和深化。
三、命题作为术语和范畴的源泉与展开
美学命题表达一种对审美规律和特征的判断,陈述美学家的一种观点,通常是短语或短句,言简意赅,说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主张。西方如古希腊西摩尼得斯的“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法国18世纪学者布封的“风格即人”,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等都是命题。中国古代,则有虚实相生、刚柔相济、气韵生动、澄怀味象、传神写照等一系列的命题。我们需要在比较中西命题异同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价值和意义。
经典命题能否视为范畴,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不过,它们通常起着范畴的作用,只是在分类的逻辑意义上有探讨的价值。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其中所收的条目,包括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和重要命题,也包括许多一般美学概念即术语。他把一部分重要的命题看成是范畴。其中的许多命题被后来的历代学者所继承、阐释和传播,值得我们今天发扬光大。如果从范畴形式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则有过于宽泛的不足。
在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中,有许多是美学术语和范畴的展开,常常是学者在术语和范畴的运用过程中所提出的深刻见解,值得后来的学者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言意关系思想,包括“得意忘言”和“言不尽意”等命题,都是将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的。《文心雕龙·神思》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3],就是言意关系思想在文学传达中的具体展开。后代截然不同的思想命题,也常常是在前人相关思想命题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例如李贽的“发于情性,由乎自然”[4],便是在《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5]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命题。
古今中外美学家的伟大思想,常常都寓于命题之中。如中国古代老子的“大巧若拙”“虚一而静”、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6]、孟子的“以意逆志”[7]688、顾恺之的“迁想妙得”[8]118、刘勰的“感物吟志”“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神与物游”[9]等。其中的许多命题作为著名学者的判断和具体观点,是术语和范畴的具体运用,或作为术语和范畴的有效补充,或是凝练为术语和范畴的基础,具体、深刻地表达了美学思想,在思想的表述中有着重要的特色。“汉魏风骨”“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就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时代精神的特定命题。
中国古代的许多美学命题,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依托于理论,对哲学术语和范畴的衍生。命题以范畴为基础,又衍生出新的范畴。如道家提倡以大为美。老子提出“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庄子提出“大美”的范畴,都在后世形成了一个传统。司空图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在韵、味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思考。再如从哲学上的“气”的范畴出发到书画美学中的“气韵”“气象”范畴,再到“气韵生动”“盛唐气象”等命题,把现象和效果表达了出来。由“象”衍生出“澄怀味象”和“象外之象”等命题,乃至进一步衍生出类似的新命题。“味象”作为范畴,“澄怀味象”作为命题。顾恺之在“传神”范畴的基础上,从人物画的具体情境和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的命题。
相反相成的范畴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拓展了相关美学思想的丰富和深化。由文质范畴,出现了“文质彬彬”“文不灭质”等命题。雅俗有关范畴的组合,则出现了“化俗为雅”“俗为雅用”“从雅到俗”“以俗为雅”“避俗尚雅”“雅俗并陈”等一系列命题。《老子》的“大巧若拙”命题,涉及“巧”与“拙”的关系,又发展出了陈师道的“宁拙毋巧”、王世贞的“愈巧愈拙”。虚实范畴在中国古代书画思想中衍生出了“虚实相生”“化实为虚”“以实为虚”等命题。黑白作为相反相成的范畴,衍生出老子的“知白守黑”、邓石如的“计白当黑”等命题。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形神”范畴,在艺术思想中衍生了顾恺之《论画》中的“以形写神”[8]118和“形神兼备”等命题,对作品的创作方法进行概括。“言意”范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美学命题,如“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还有极少的命题与术语和范畴是重合的,如“物感”“比德”“畅神”等。它们是简洁归纳的动宾结构的双音词,实际上是命题的简称。新生成的范畴和命题,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尽管与术语和范畴相比,命题通常用词组、短语甚至句子表达思想,但在美学学术论文和著作的整体内容中,命题依然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
有的美学命题源自哲学命题,如“似”作为术语和范畴,衍生了“形似与神似”“离形得似”等命题,引发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产生新的思想。如在“似”与“不似”的基础上,产生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创新见解。“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命题,具体体现在审美活动的思维方式中。“书画同源”“诗画一律”“乐舞相生”“诗书画三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等命题,都是艺际借鉴的体现,说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通性和相互影响。许多命题会在学科内被反复讨论,甚至成为争讼不已的学术问题。如《溪山琴况》“指与音合,音与意合”[9],就在学界被广泛评价和继承。有的命题则因有争议而不断被讨论,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有一些美学命题常常通过具体不同的现象反复验证,论证思想的深刻性和准确性。
中国古代的核心命题也会进一步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如“天人合一”命题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 等都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苏轼的所谓“身与竹化”[11]、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12]、明代唐志契的《绘事微言》所谓“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13]等,虽然未必都能算得上是对传统命题的发展,但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开。
命题在陈述之中体现判断,通过直接陈述或象喻,提出美学的判断。有的命题是后人在原话的基础上作了简单概括,如苏轼的“胸有成竹”。有的命题是由长句压缩、提炼为命题,如韩愈的“不平则鸣”。许多象喻的命题,既有对哲学概念和范畴的具体展开,也有以象喻的方式对艺术特征认知的表达,简明扼要,点到即止。因此,经典的命题在美学思想系统中,常常起着一种纽带作用,类似于范畴作用。
命题之中包含判断和观点,有的是相关文献中的论断和结论,体现了思想家们的理论主张,确实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值得继承的内容,不同于一般的术语和范畴。中国古代的美学命题中,有许多是相关思想的加工、提炼和概括。 如“知人论世”“发愤著书”等命题,都是相关思想经过加工和提炼而成的。例如“胸有成竹”本来是对创作过程的描述,也被凝聚成了富有哲理的美学命题。也有的命题是此前术语的运用,包含着不同术语之间的关系,也有的命题后来被简化和概括,提炼为术语和范畴。如“虚静”一词,是从《荀子》的“虚壹而静”[14]中提炼出来的;“意象”一词,是从《易传》的“立象尽意”提炼出来的。有的命题有大同小异的多种运用,如“风骨”“风力”等,其中一部分会流传更广,必然性之中有时也有偶然性。因此,概念和范畴从命题中提炼出来,命题之中又常常包含着概念和范畴,包含着对概念和范畴的运用,例如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8]198,阐释了“造化”和“心源”对于艺术创造的价值和意义。郭若虚的“气韵非师”[15]阐释了气韵的天赋特征。
四、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通过诸多美学术语、范畴和命题加以呈现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以范畴和命题为筋骨,其中的潜在体系是经,而各类文艺思想中的术语、范畴和命题则是纬,共同组成了中国美学思想的整体,包含着完整的美学知识体系。历代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品是当时产生相关美学思想的基础,是我们验证美学思想的基础,也是我们进一步概括和总结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许多美学术语、范畴和命题在沿袭传承中有自己的嬗变规律,需要加以厘清。揭示这些术语、范畴和命题中的思想渊源,有助于我们揭示美学思想的深刻性,使其含义变迁的历程得以呈现。
中国古代美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理论特征。这些术语、范畴和命题在学术的发展历程中,推动了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流传至今的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术语、范畴和命题,在美学史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体现了学术发展历程中的选择。每一个术语、范畴和命题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术语、范畴和命题形成一个家族,其中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有力地拓展和延伸内在意义的表达。意象范畴形成了一个范畴家族,生成了相互关联的术语和范畴。同一家族之间有着相似的特征。其他如气、趣、韵、味、境等,都是元范畴,衍生出范畴家族。因此,我们要重视美学思想中术语、范畴和命题的演变史,要重视对术语、范畴和命题追溯的重要性。根据中国古代美学术语、范畴和命题的特点,建构以某一核心范畴如意象范畴为中心的美学本体系统。
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产生了特定的美学思想,其中包括基本的术语、范畴和命题。“天人合一”的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对古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都产生了影响。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美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经历了组合、衍生和含义的丰富与变异等变化发展。中国古人交流所用的术语、范畴和命题都运用了学术共同体当时交流的语言,包括儒、道、释思想中的语言,也包括具体艺术圈里的行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术语、范畴和命题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道”从本来具体的“路”的名词概念,上升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范畴。但同样的“道”,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易传》的“道”,含义都是有差异的,后世如刘勰的文之道,宋明理学家的道,含义也都是不同的,又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中国古代的美学术语、范畴和命题,体现了古人的理论主张。中国古代从老庄开始,讲究“朴”和“自然混成”的效果。质朴体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老子》第十五章“敦兮其若朴”,第十九章“见素抱朴”,第二十五章“复归于朴”。受此影响,诗歌领域也强调自然、清新的风格。如推崇谢灵运诗如“初发芙蓉”,李白强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6],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也要求“宁朴勿华”。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把“逸品”置于张怀瓘的《画断》的神、妙、能三品之上,到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在此基础上提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四格,将“逸格”置于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内涵丰富,意在言外。中国古代美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重视主体的体验和感悟,重视主体的直觉了悟,如虚静、妙悟、神思、心源、兴会、趣味、滋味等。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的模糊性,是由所指称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有的概念取象比类,拓展了表现力,以象状意,以象尽意。运用象征性符号,通过特定的概念传达精微丰富的思想,以拓展概念的表现力。有些概念朦胧多义,指月式的表达方式和象喻等特征,触发人们的联想,便于理解丰富的含义。庄子多次说“不可以言传也”[10]437“天地有大美而不言”[10]649“道不可言”[10]667,强调语言表达的困难。中国古代诗论中擅长“以禅喻诗”,许多禅宗范畴成为美学范畴。
中国古代的许多术语、范畴和命题,或并列或偏正,使两者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其中许多概念都受到了中国语言骈偶形式的影响,具有对称的特点。“形神”是含义相对的两个并列词素,“神思”是偏正结构。“妙悟”是偏正结构的范畴,以“妙”形容“悟”的状态、层次和效果。一些成语典故成为美学术语,用来解释审美现象。在词义的拓展中,从生理走向心理,从自身走向外物,语义从自然生命和生理特征拓展到人的精神生命,从生理领域、现实领域引申到精神领域。如“味”,从生理感官拓展到精神体验。“远”本来是一个空间范畴,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把现实与心理打通了。“势”本来指自然现象,转而表现社会现象,再到艺术品的评价。
我们需要适度参证西方美学学科的基本范畴,但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求同弃异,不能舍弃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我们阐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术语、范畴和命题,不是用它们来佐证西方美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在于印证西方美学的普遍价值,而在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贡献。中西美学在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本身虽然带来了交流上的困难,但是也带来了异质文化会通的优势。
中国现代美学家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的同时,也直接移用了一些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和命题来阐发自己的美学主张。例如邓以蛰在他的美学理论论文和艺术批评文章中,直接移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些范畴,其中对唐代王昌龄等人的“意境”范畴、袁宏道的“性灵”范畴从现代美学意义上加以理解和阐释,认为性灵是艺术和美的重要特质,意境由性灵产生。“意境出自性灵,美为性灵之表现。”[17]167他把气韵生动与克罗齐的表现说联系起来,揭示气韵生动的意蕴。“气韵生动可谓美之活动之结果,而为美之至极之价值焉。言语之表现为美之活动,此克氏之独到也,然未及此表现之结果,之价值,换言之,犹不知有气韵生动之事也,言表现而不及于气韵生动,犹之乎言思想不及于名理也。”[17]258运用中国古代的范畴和命题,在中西参证中阐发自己的理论。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美学概念系统是历史生成的,需要我们追源溯流。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需要系统清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概念系统,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等。其中元术语、元范畴的组合和建构,术语和范畴的衍生特征和规律,具有开放性特征,超越了原有的含义视域,拓展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内容。这种在语用中拓展语义的方式,也需要从当下语境中加以匡正。我们所运用的中国古代的美学术语、范畴和命题里包含着感性形态,如范畴之中常常包含着主体的体验和感悟,包括象喻的语境表达等,需要进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要尊重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规律,从术语、范畴作为哲学范畴的普遍意义,寻求它对于美学学科的具体意义,把它们置于新的语境、新的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