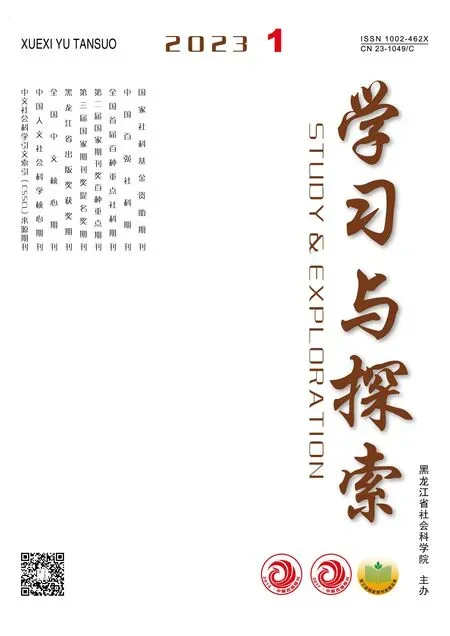五四时期汉译英诗与新诗词汇的现代建构
王泽龙,李小歌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语言总是充当着文学革新的急先锋。五四时期要实现文学的现代变革,只有首先突破文言文的壁垒,攻克旧体格律诗的坚固堡垒,才能开通现代白话新诗的道路。晚清也曾有过诗界革命,然而不论是“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还是“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都未能动摇中国古典诗歌的绝对地位。因为“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1]。“语言是活的东西,它不断地发展、变化,不断地有新生、有衰亡。”[2]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动态的却又相对稳定的词汇系统。词汇的不断更新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类似,只是词汇的代谢周期较为漫长,且不易为人察觉。只有当外来词像同化激素般注入本国语言时,才能明显感受到词汇的新旧更替。五四新诗人普遍意识到,只有革新诗歌语言才能表现现代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外来诗歌语言的翻译与借鉴成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重要来源。”[3]五四时期的汉译英诗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词汇系统的更新,拓宽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空间。
一、外来专有名词与新诗语言的现代思想内蕴
一些表示地名、人名、概念、术语的音译词、意译词和外文单词成为新诗语言中最显眼的存在。这些外来词主要来源于日语和英语,不过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根源还是在西方,因为“这些词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4]。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有外来专有名词入诗的例子,例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一枝斜映佛前灯,春入铜壶夜不冰。”(陈与义《梅花》)这些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汉译外来词(楼兰、禅、佛)反映了古代中国与外界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古典诗歌中的外来词数量很少,大都不露痕迹地融入古诗体中,逐渐达到归化效果。然而,五四新诗中大量的外来词入诗,不仅带给读者新鲜、突兀的感觉,还向读者输入了现代思想和新的诗歌观念。以郭沫若的《夜》《晨安》《电光火中》等诗为例,德谟克拉西、苏伊士、帕米尔、喜马拉雅、华盛顿、泰戈尔、加里弗尼亚、Millet、Beethoven、Symphony等音译词和英文单词直接入诗,诗人这样做“不是在故意卖弄,而是出于语言上的必要。这不仅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相应的汉语词汇,可能更在于诗人有意要把一种陌生的、异质的语言纳入诗中,以追求一种更强烈的、双语映照的效果”[5]。郭沫若新诗中也存在大量意译词入诗的情况,在《胜利之死》《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夜》《夜步十里松原》《巨炮之教训》《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歌中,有权威、自由、纤维、精神、解放、社会等由日本人从英文意译而来的外来词。这样一批意译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打上了五四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现代思想烙印,成为“时代肖子”郭沫若诗歌的突出语言符号。
五四时期的汉译英诗广泛发表在当时的各种刊物上,成为新诗人创作的借鉴范本。译诗语言中有许多音译词、意译词和英文单词出现。例如,朱湘译约翰·黎里诗歌《赌牌》(《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1号)中有音译词“维纳斯”,译约翰·多恩诗歌《死》[6]中有音译词“鸦片”。傅东华译弥尔顿诗歌《与夜莺》(Tothenightingale,《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11号)中有约夫和缪斯两个外来词。郭沫若译葛雷《墓畔哀歌》(ElegyWritteninaCountry)中有诗句:“或许有乡僻的翰登胸地光明,/抵抗那小暴君的地主殒命;/或许有湮没无闻的弥尔顿在此埋身;/或许有克伦威尔未曾屠过国民。”(《创造季刊》1924年第2卷第2号)鸦片、维纳斯、约夫、缪斯、翰登、弥尔顿、克伦威尔都是外来专有名词的音译形态,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鸦片”一词源于英文“opium”,但在汉语语境中,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毒品,而是近代中国人民漫长苦难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开始。约夫、缪斯、维纳斯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神的名字,约夫(Jupiter)是众神之王,缪斯(Muse)是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女神的统称,维纳斯(Venus)是爱与美之神。五四译者在翻译外来名词时,把蕴含着人文精神的异域艺术介绍给中国读者。此外,爱国战士翰登、民主诗人弥尔顿、反抗王政的克伦威尔都是当时身处战乱之中的中国人民向往与拥护的伟大先驱,他们的名字构成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图像。
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中同样有英文单词直接入诗的情况。例如,金明远译泰戈尔诗歌《天文家》(Theastronomer)里有诗句:“我只说,‘当晚上的时候,那个满的月,照在加特Kadam树枝中间,可有人捉得他么?’”(《民国日报·平民》1920年第5期)汤鹤逸译惠特曼诗歌《奇迹》(Miracles)中写道:“无论我散步曼哈顿(Manhattan)的街头,/或遥望对面空中人家的屋顶。”(《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0日)译诗里不仅有加特和曼哈顿两个音译词,还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出现。陆觉译王尔德诗歌《他底情爱》中写道:“啊!你是幼年的Endymion,/你有接吻的唇儿!”(《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7月21日)英文单词Endymion直接进入译诗。印度花树Kadam、(1)Kadamba,源梵语,现译为迦昙波(婆),花树名。纽约辖区Manhattan、希腊神话中月之女神的美丽恋人Endymion出现在译诗中,不仅为英文单词直接进入新诗提供了借鉴范本,还给读者带来丰富、广阔的想象图景与新鲜的阅读体验。
此外,徐志摩翻译哈代诗歌《她的名字》中有这样的诗句:“她像是光艳的思想的部分,/曾经灵感那歌吟者的欢欣。”(《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1期)郭沫若译雪莱《西风歌》中写道:“时间的权威严锁了我,重压了我。”译雪莱《死》中有“男儿哟!振作起你的精神。”“那时候,天堂地狱两都听你自由,/你将超越了那定运的宇宙。”“神经中枢的纤维不是钢铁绕成。”(《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郑振铎译泰戈尔诗作《世纪末日》中有诗句:“不要羞馁,我的兄弟们呀,披着朴素的白袍,站在骄傲与权威之前/让你的冠冕是谦虚的,你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0期)陈肃仪译泰戈尔诗歌《秋》里写道:“我在每茎草里,每粒沙里,我自己身上各部分里,能看见的或不能看见的社会里,行星里,太阳里,星里,听见这些微小的分子不住地在那儿举行极欢乐的跳舞。”(《民国日报·平民》1920年第25期)灵感、时间、权威、精神、自由、神经、纤维、社会、分子等科学名词和抽象名词皆是从日本引进的意译英语词,蕴含着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
在诗歌里,实词的变化意味着人们接触的世界发生了变化[7]。首先,新诗中出现的喜马拉雅、苏伊士、华盛顿、泰戈尔、Millet、Beethoven等表示地名、人名的外来专有名词展现出包罗万象的世界图景。这些词语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发着五四青年一代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其次,外来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宣称本誌同人极力拥护德莫克拉西(emocracy)与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8]。在五四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民主、科学、自由、解放成为时代的思想主题。社会、权威、德谟克拉西、自由、解放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名词;纤维、神经、分子、灵感、Symphony等自然科学、艺术方面的新名词,适应了现代人生活与情感的表现,顺应了现代科学思维的要求。最后,外来专有名词入诗推动新诗语言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外来专有名词不仅丰富了新诗词汇,而且突破了中国古典诗歌以主观体验、直觉感悟、取象比类为主的感性思维传统,“开始向现代汉语诗歌知性重理或情与理互渗,感兴与知性结合的诗思转变”[9]。科学主义要求诗人具备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读者也更加期待视野广阔、意义凸显、逻辑顺畅,能够提供新鲜审美体验的现代诗歌文本。
二、人称代词与新诗语言的叙述化趋向
除了最显眼的新名词外,人称代词大量进入新诗,同样受到了译诗语言的深刻影响。这类词语入诗,直接促进了新诗形式的现代转变,推动中国现代诗歌朝着叙述化方向发展。
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有人称代词出现,但与新诗中大规模的人称代词入诗相比,古诗中的人称代词整体上处于隐匿状态。人称代词大量进入新诗主要受到了汉译英诗的影响。进入新诗的人称代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说话者,这类人称代词背后隐藏着人物的主体意识和观察角度;另一类是沉默者,他们通常是被看、被叙述的对象,扮演着接受者、倾听者的角色。这两类人称代词在诗歌中的多样用法,形成了独语与对话两种诗歌主要类型。在此,我们把只有一种声音出现的诗歌称为独语型诗歌,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说话者发声的诗歌称为对话型诗歌。
(一)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叙述主体的分合
五四时期,稳定、规范的人称代词词汇系统尚未形成,在早期的白话译诗和新诗里,牠、佢、伊、吾、俺、卿、喒们等来自方言和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时而出现,昭示着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两大词汇来源。此外,受英语人称代词的影响,新诗中的人称代词由原本不分性别的“他”衍生出“她、它、他”三个区分性别的人称代词。这三者虽读音相同,但书面语上的区别一目了然,使得现代汉语更为精密、准确、富有表现力。
当人称代词指向说话者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二是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分离。前者往往构成独语型诗歌,表现为诗中说话者声音的单向抒发或自言自语;后者则形成对话型诗歌,表现为诗中角色各持己见,众声喧哗,呈现出对话特征与复调效果。在英语诗歌中,人称代词指向说话者的这两种情况都较为常见。
作为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第一人称代词“我”的身上。“我”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无我”状态。“我”成为抒情和叙述的主体,成为观察和感觉的焦点,强烈的自我意识从“我”中透露出来。这是“惠特曼《草叶集》里‘Song of Myself’的语态”[10]217。徐志摩曾把惠特曼SongsofMyself中的部分诗节(31 & 32节)里的部分诗句挑选出来,合译成一首诗,题作《我自己的歌》:
我看来一片的青草与天上的星斗的运行是一样的神奇,/泥里的蚂蚁也是一样的完美,一颗沙,鹪鹩的卵蛋,/树根里的青蛙,都一样的是造化主的杰作。/我看来蔓延着的荆条可以装饰天上的厅堂,我手里绝小的铰链比得上所有机器,/我看来在草田里低头吃草的黄牛胜如美术的雕像,/一只小鼠是一个灵迹,可以骇倒无数自大的妄人……(《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3号)
徐译《我自己的歌》的前半部分,出自惠特曼SongsofMyself第31节前七行。诗歌以第一人称“I”引领长句,剩下六行皆用“And”开头,链接诗行,形成头韵。惠特曼在这几行诗中使用的人称代词比较单一,第一人称主格“I”和物主代词“my”分别出现一次。徐志摩在翻译时,没有逐字译,他四次用到第一人称代词“我”,有效地模仿了原诗的头韵。诗中的“我”既是抒情主人公,又是叙述主体。作为说话者的人称代词“我”与诗中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惠特曼的Dirgefortwoveterans和AstoilsomeIWander`dVirginia`sWoods两首诗同样是人称代词与诗中说话者身份合一的典例。谢六逸把第一首诗译为《挽二老卒》,中有诗句:“我见着悲哀的行列,/我听着前进的全调的角鼓之音,/是声音,是珠泪。/我听着军鼓正鸣,/小鼓发出坚实的响声,/激烈震荡的军鼓的各声,/往来的打击我。”(《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0月8日)第二首被译为《在维吉尼纳森林中迷途》:“我在树根儿看见兵卒的坟墓”“我很久的沉思,仍向前彷徨”“无名的兵卒墓在我的面前”(《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0月9日)。“我”是观者、听者、感受者、思考者、叙述者、抒情者,“我”带给读者的是沉浸式的自我体验模式。诗中的“我”的自主性得到彰显,表现出诗人对个人价值的充分尊重与肯定。“中国新诗向西方学习所得的最突出之点,便是诗中‘我’的出现,这打破了中国古典诗歌长期‘无我’的状态,‘我’成了新诗里再也祛除不掉的色调。”[11]
在徐志摩的新诗创作中,也有许多“我”与诗中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的例子。例如:“我有一个恋爱;——/我爱天上的明星;/我爱他们的晶莹:/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我有一个恋爱》)[12]309“去罢,人间,去罢!/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去罢,人间,去罢!/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去罢》)[12]310“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经络。”(《灰色的人生》)[12]310诗中的声音是由“我”发出的,“我”是叙述主体,“我”敢于诉说自己的真实想法,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我”是赤诚、坦率、勇敢的,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叙述主体的隐藏与无我,这是一种典型的惠特曼式的自我形象呈现形态。郭沫若同样是直接从惠特曼诗风中汲取力量的新诗人。他在《创造十年》《序我的诗》《我的作诗的经过》等文章中,多次强调惠特曼的《草叶集》给他带来的震撼与影响。他把自己在五四高潮时期所作的豪放、粗暴的诗歌称为惠特曼式[13]。例如:“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先生辍课了!’/我的灵魂拍着手儿叫道:好好!/我赤足光头,/忙向自然的怀中跑。”(《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Venus)诗中的说话者“我”与诗歌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形成典型的独语型诗歌。这类诗歌往往选用较为单一的人称代词“我”做话语主体,营造单声部的发言模式,重在突出“我”的形象与自我意识。当多个人称代词交叉入诗,且都指向说话者时,会出现叙事/抒情主人公“我”与其他人称代词对话的情况,形成复调型诗歌。郭沫若翻译的惠特曼诗歌《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OutoftheRollingOceantheCrowd),属于这一类型:
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缓缓儿的来了一路水,/向我耳边说道:“我爱你,我不久要死,/我走了远远的路程,专诚来见你,专诚来念你,/我要见你一次,我才能够死,/因为我怕我死了之后,我会失掉了你。”//如今我们相遇,我们相见,我们都无恙;/我的爱,你请平平稳稳的回向大洋;/我也是那大洋的一份子,我的爱——/我们并不是十分相离……(《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3日)
诗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称代词“我”是诗歌的叙述主体,第二个出现的人称代词“我”是诗人设定的角色——“一路水”。由于视角不同,“我”和“你”指代的角色发生互换,对话由此产生。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中尝试了对话形式:“我踏只脚在门上,/我正要翻出监墙,/‘先生!你别忙!’/背后的人声/叫得我面皮发烧,心发慌。”(《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14]127诗中的工人虽然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人称代词“你”的出现并发声,打破了“我”的独语形式,与“我”构成对话,使诗歌中出现了第二种声音。此类诗歌的经典例子首推胡适与其译诗《关不住了!》,诗中写道:“我说,‘我把心收起,/像人家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地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新潮》1919年第1卷第4期)在诗人创设的戏剧性情境中,第三人称指示词“他”与抒情主人公“我”展开平等对话,增添了诗歌的趣味性与客观性。胡适在自己的新诗创作中借鉴了这种手法,例如:“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我们的双生日》)[12]4诗中的叙述主体“我”与“他”展开情景对话,诗歌呈现出多声部特点,诗意在理性与趣味中生成。
当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分离时,诗中的人称代词往往是诗人设定的角色,是诗歌叙述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上述多个人称代词交叉入诗,形成复调型诗歌中的“你”,便是作为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叙述主体分离的典例。哈代擅于在诗中创设戏剧性情境,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在一家饭店里》中有这样的诗句:“‘可是你听着,你不走的话,这孩子生来,/算是你丈夫又多添了一个,也就完了’……‘嗳可是你哪懂得做女人的地位,我爱,/真叫难:整天整晚的叫你不得安宁,我就怕事情一露亮就毁。’”(《语丝》1925年第17期)诗歌纯粹由女子与情人的对话构成,二人围绕私生子的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典型的复调型诗歌。诗中的“你”显然与叙述者分离,但同样具备自主意识,能够灵活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外,在大多数叙事诗中,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述主体都是分离的。叙事诗人倾向于模仿现实生活场景和真实的人物对话,总会让诗里的你、我、他直接发声。傅东华翻译的丁尼生长篇叙事诗《多拉》(Dora,《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12号)、王统照译朗费罗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TheBlindGirlofCastelCuille,《文学旬刊》1925年第169期)、C.F.女士译惠蒂埃长诗《玛德密露》(《诗》1922年第1卷第4号)等,都是叙事者以全知视角展开叙述,他通常不在文本里现身,诗中作为说话者的人称代词全部指向角色。
当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述主体分离时,很容易产生对话型诗歌。因为在人称代词入诗之前,诗歌中本身就有一个说话者,人称代词进入诗歌后,为之增添了第二种乃至多种声音。他们或与叙述者交谈,亦或各自交流,充分体现了声音存在的意义。中国古典诗歌缺少对话意识,五四新诗人受到外国诗歌影响在诗歌中积极进行对话尝试。在哈代对话型诗歌的启发下,徐志摩也在新诗创作中尝试运用对话体。例如:“‘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阿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海韵》)这几行诗里的“你”和“我”都指代“女郎”,女郎与叙述者对话,形成诗歌的复调性。五四时期丁尼生、朗费罗、惠蒂埃等诗人的诗歌作品被大量译介,发表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月刊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刊物上。这些翻译诗歌对新诗产生了广泛影响。鲁迅的诗歌《爱之神》[12]22是运用对话创设戏剧性情境的典例,诗中的叙述者和爱神都分别用“我”指代自己,“你”指代对方,在人称代词的指向变换中形成诗歌的多声部。周作人的《小河》[12]77中也有大量由人称代词引领的对话描写。诗中除了叙述者的声音还有稻和桑树的言谈,他们用第一人称“我”来指代自己,谈论着“他”(小河)带给“我们”的隐忧。闻一多尤其擅长创设戏剧性情景,塑造多种角色形象。诗人在《闻一多先生的书桌》[12]261一诗中让静物开口说话,营造出众声喧哗的景象。诗人让多个人称代词交叉入诗,诗中的“我”先后指向墨盒、墨水壶、主人,“你”分别指向书、桌子,“他”依次指向字典、钢笔、毛笔、铅笔、笔洗,“我们”和“你们”都指向静物。诗里的人称代词有序发声,不论是由叙述者直接描写,如“墨盒呻吟道‘我渴的要死!’”,还是间接转述,“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诗中的角色都实实在在地发出了不同于叙述主体的声音,形成多声部诗歌。
(二)指向沉默者的人称代词:作为被叙述对象
当人称代词指向沉默者时,虽有多个人称代词交叉入诗,但只有叙述者在发声,此时指向沉默者的人称代词与叙述者分离。当然,不存在指向沉默者的人称代词与叙述者合一的情况,因为叙述者必是说话者。因此,当人称代词指向沉默者时,只能形成一种诗歌类型,即独语型诗歌。独语型诗歌在中外诗歌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独语型诗歌里的第二人称指示代词“你”通常指向沉默者。例如,赵景深翻译的拜伦诗作《没有一个美神的女儿》中有这样的诗句:“没有一个美神的女儿/有你那样的魔术;/你的声音使我欣愉/有如水上的音乐/那时,好像是你的声音/使这着魔的海波不兴。”(《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号)朱湘译雪莱诗歌《恳求》(To——)中有诗句:“我不敢呈献爱情给你,/我呈献的是崇拜,/凡人的崇拜神也看起,/我的你该不见外?/好像猿猴愿捞月,/好像灯蛾愿得到光明,/你难道忍心拒绝?”(《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1号)梁实秋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约翰我对不起你》中有诗句:“你知道我从来不爱你,约翰;/我也没错处该使我做你的飨牢:/你为什么以新鬼似的青白的脸/不时的想着我?”(《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1号)这些诗歌里反复出现的“你”常常意味着说话者在自言自语。“你”总是指向特定的对象,与“我”之间存在着一种宛如对话的关系。然而,“你”与“我”之间的对话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你”是沉默者,是“我”的倾诉对象,“你”的存在只是为了避免独语型诗歌的主观色彩和陷入说教。
五四时期有许多新诗人模仿英语诗歌中的第二人称使用方法创作了大量的独语型诗歌。例如:“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胡适《一念》)“悲哀是无边的天空,/快乐是满天的星星。/吾爱!我和你就是那星林里的月明。”(汪静之《无题曲》)“现在梦神又将香花洒我了,/我不由自主的又想睡了;/秋姊姊,请你不要恼我。”(赵景深《秋意》)“鸡呀,你又何必,/在如死的黑树影下,/偶闻遥犬的岑寂中,/供着颈高啼?/时候到了,/自有自身的营谋/唤醒他们的不安之梦。”(朱湘《你何必啼呢》)“我的朋友!/看潭久了,渊潭也要看你!/嗅香花久了,香花也要嗅你!”(梁实秋《送一多游美》)
通过举例可知,英语诗歌中的第二人称代词“你”大多指向沉默的人,尤其指向爱的对象。新诗在继承这一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诗中的“你”不仅指代爱人,还指向地球、月亮、秋姊姊、鸡、朋友等。由此可见,新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这些诗歌中出现的“你”与其说是在与“我”对话,不如说是“我”在对“你”讲话。因为当对谈双方有一方保持沉默时,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陷入一种“我”说“你”听的单向输入模式。五四新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创作独白型诗歌,与其肩负的启蒙使命有关,他们想以诗歌为媒介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先进思想传递给民众,“这使命反映在语言上的是‘我有话对你说’,所以‘我如何如何’这种语态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10]217。可以看出,五四对独语型诗歌的选择与其时代语境密切相关。
当第三人称代词指向沉默者时,“他”同样与叙述者分离,“他”成为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客观性、陌生化、距离感由此产生。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她的名字》《公园里的座椅》《我打死的那个人》均属此类创作。例如:“在一本诗人的书叶上/我画着她芳名的字形;/她像是光艳的思想的部分,/曾经灵感那歌吟者的欢欣。//如今我又翻着那张书叶,/诗歌里依旧闪耀着光彩,/但她的名字的鲜艳,/却已随着过去的时光消淡。”(《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1期)与第二人称代词“你”营造的在场感不同,第三人称代词“他”产生的是疏离感。因此,诗人描绘了“她”的名字随时光消逝而产生的渐远感。“要是我与他在那儿/老饭店里碰头,/彼此还不是朋友,/一同喝茶,一起吃酒,//但是碰巧彼此当兵/他对着我瞄准,/我对着他放枪。”(《晨报副刊》1924年9月28日)这首诗同样是“我”在独语,诗中的说话者和“他”都是诗人创设的角色。指向沉默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入诗,便于诗人隐藏自己的情绪,体现出诗人的非个人化创作立场。第三人称代词“他”以角色的身份进入诗歌,昭示着诗人的冷抒情倾向,推动诗歌朝着叙述化方向发展。除哈代之外,约翰·黎里的诗作《赌牌》(《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1号)、柯勒律治的《印度之夜歌》(《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拜伦的《唉当为他们流涕》(《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王尔德的《伊底坟墓》(《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7月2日)等诗歌都运用了指向沉默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在这些诗作中,虽然诗人有意把自己的感情降到冰点,但诗人对他者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或释然、或怜惜、或爱慕、或同情。
五四新诗中同样有许多指向沉默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入诗的例子。例如:“秋风把树叶吹落在地上,/它只能悉悉索索,/发几阵悲凉的声响。//它不久就要化作泥;/但它留得一刻,/还要发一刻的声响。”(刘复《落叶》)“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沈尹默《三弦》)“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个平静的样儿,/可他嫩绿的绢衣却遮不过他心中的激动。”(郭沫若《日暮的婚筵》)此外,汪静之的《伊底眼》、冯至的《我只能》、徐玉诺的《跟随着》、戴望舒的《我底记忆》、闻一多的《忘掉她》等诗中都用到了指向沉默者的第三人称代词:伊、它、他们、他、牠、她等。
在汉译英诗的影响下,人称代词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新诗。人称代词的指向,人称代词与叙事/抒情主体的分合都会影响到诗歌话语模式的走向。“诗歌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历史叙述性,可以零星地记载时代生活,至少能够记载人们对时代生活的感受,记录情感。”[15]大部分诗歌都是既包含抒情性因素,又包含叙事性因素。当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合一时,人称代词作为叙述主体具有发起、引导话语的能力。当指向说话者的人称代词与诗中的叙事/抒情主人公分离时,人称代词作为角色具有链接故事情节、串连戏剧场景、引出人物对话的作用。当人称代词指向沉默者时,沉默者成为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诗歌整体朝着叙述化方向发展。
三、语气词与新诗语言的抒情性与口语化
语言中流露出来的说话者的各种情绪叫做语气,表示语气的虚词叫做语气词[16]。语气词一般用于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大句类,辅助语调来表达句子的多样情绪。语气词本是来自口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是人类情感发之于声的直接表现形式。在我国早期的诗歌中,语气词较为常见。据统计,“仅《诗经》中的‘国风’这一部分,就用了:兮、矣、也、哉、乎、且、止、焉、只、而、忌、思、其、琦等14个语气词,计564次。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兮’,共277次,其次是‘矣’‘也’,各76次”[17]。语气词的大量使用体现出民间诗歌自由不拘的开放特点。唐代以后,随着诗歌创作技法的日益成熟,古典诗歌的诗体形式逐渐定型,对字数和格律的要求趋于严格,诗词中的语气词更多地“负担‘义’的责任,与真正的‘本声’有一定距离”[18]。因此,唐及唐以后的诗歌中语气词用得极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语诗歌擅于灵活地运用语气词。五四时期,在汉译英诗的广泛影响下,大量的口语语气词进入新诗,它们“是带着平民主义与大众文学观念挤进贵族化典雅文学殿堂的”,不仅“破坏了古典诗歌贵族化的审美雅兴与格律规范,也破除了诗歌与广大民众的语言障碍与观念隔阂”[19]。为新诗输入了现代气息与思想活力,推动新诗语言朝着抒情性与口语化方向发展。
(一)语气词与诗歌语言的抒情性
在英语诗歌中,诗人们往往运用语气词来增强诗歌语言的抒情性与感染力。弥尔顿在其十四行诗Tothenightingale中运用了语气词:“O Nightingale! that on yon bloomy spray/ Warblest at eve, when all the woods are still.”(2)https://www.poetry.com/poem/23902/to-the-nightingale.傅东华将其译为:“夜莺呵,你在那蓓蕾枝头,/趁夜里群林静寂把歌声放。”(《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11号)原诗中,句首语气词“O”奠定了全诗神圣、庄重的情感基调,并且带来咏叹气韵。译者把句首语气词译为“呵”,且将其置于句中,用句中停顿打破了原诗的流贯气脉。译诗中语气词的移位阻梗了诗人情感的直泻,弱化了语气词的抒情作用。显然,译者未能充分理解弥尔顿诗歌中语气词的用意。
热衷于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都是灵活运用语气词的能手。在顾彭年翻译的拜伦诗歌《唉!当为他们流涕》(Oh!WeepforThose),赵景深翻译的《别雅典女郎》(MaidofAthens,《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号);西谛译雪莱诗歌《给英国人》(SongtoTheMenofEngland,《文学旬刊》1922年第52期),郭沫若译雪莱《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创造季刊》1924年第1卷第4期),C.H.L翻译济慈《你说你爱》(YouSayYouLove,《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1号) 等诗歌中,都用语气词来增强诗歌语言的抒情性。例如,雪莱在OdetotheWestWind这首七十行长诗中有八处用到语气词,郭沫若基本完成了对原诗语气词的移译,还在译诗中额外添加了不少原诗中没有的语气词。(3)https://www.litcharts.com/poetry/percy-bysshe-shelley/ode-to-the-west-wind.雪莱诗中的语气词大都用在句首或句中,郭沫若把原诗中的语气词“O”音译为“哦”,把句中语气词“oh”译为“哟”,把句首语气词“oh”译为“啊”。这些语气词发而为声均有一种雄浑豪迈之气,蕴含着诗人乐观、坚定的情感,是雪莱感受大自然的灵动而作成的诗篇。诗中语气词的使用,有助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抒发。
浪漫主义诗人之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在其著名诗歌HomeThoughts,fromAbroad(4)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3758/home-thoughts-from-abroad.中也用语气词来表达情感:“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朱湘把原诗开头两行译为:“啊,要是回了英伦/当如今四月去了那间。”(《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10期)朱湘用“啊”来对译原诗句首语气词“Oh”,充分体现出诗人无比喜悦、感慨的情思。诗人回忆起故乡的美景喜不自胜,这一声叹息中寄予着诗人对家乡的深刻怀念与眷恋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朱湘在诗歌结尾处增添了一个原诗里没有的语气词,他把结尾行“—Far brighter than this gaudy melon-flower!”译为“——咳,比起牠来这瓜棚上耀目之花差的多远!”诗人从回忆中回神,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语气词“啊”与“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情绪张力,故乡的归属感与异域的飘零感交错缠绕,写出了世间游子的普遍心声。不过,原诗中并没有语气词,诗人用破折号“——”表示从回忆中转醒的过程,用感叹号“!”表达自己不能看到故乡美景的失落之情,表达较为含蓄。朱湘显然体会到了勃朗宁写作手法中蕴含着的深义,增添一个语气词,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
语气词作为人类情感发之于声的直接表现形式,能够便捷地表现情感。语气词是诗中说话者主观感情和意念的自然流露,包含着说话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与切身感受。在汉译英诗的影响下,五四新诗人借鉴了英语诗歌中语气词入诗的创作方法,以此增强新诗语言的抒情性。
五四时期,最爱用语气词的诗人首推郭沫若。《凤凰涅槃》里写道:“啊啊!/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14]36在这一节诗中,句首、句中、句尾均有语气词出现。句首语气词“啊”起呼唤作用,能够增强语气。诗人连用两个“啊”,语气强度加倍,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满腹激情跃然纸上。句中和句末语气助词“呀”具有舒缓语气的语用功能,试将语气词去掉与原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呀”起到了缓和语气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说话者的态度由强硬疏远转为柔和亲切,通过弱化说话者语气的刚性,提升了话语的可接受度[20],更有助于诗人情感的表达。
胡适的新诗创作中也有运用语气词来帮助诗歌情感表达的例子,如《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里写道:“往日归来……老亲望我,含泪相迎。/‘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只今到家时,更何处寻他那一声‘好呀,来了!’”[21]诗中的语气词“呀”包含着母亲对儿子的亲切关怀,而这首诗写“奔丧”,昔日母亲的亲切口吻与今日母子天人相隔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诗人悲痛欲绝的心情跃然纸上。
刘半农的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12]16语气词“啊”中包含着诗人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周作人《儿歌》里有:“小孩儿,你为什么哭?/你要泥人么?/你要布老虎么?”[12]44语气词“么”体现出诗人对孩子的温和与慈爱。此外,王统照的《小的伴侣》:“瓶中的紫藤,/落了一茶杯的花片。/有个人病了,/只有个蜂儿在窗前伴他。/虽是香散了,/花也落了,/但这才是小的伴侣呵!”[12]92;汪静之的《在相思里》:“于今不比从前呀——/夜夜萦绕着伊的,/仅仅是我自由的梦魂儿了。”[12]145潘漠华的《足迹》:“常在门前柳树下,/寻我童年游戏的足迹,/寂寞的母亲呀!”[12]148等诗歌中的语气词无不蕴含着抒情主人公对蜂儿、爱人、母亲等的真挚感情。语气词的运用使诗歌语言更具感染力,更能引发读者共情。
(二)语气词与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丘浚《答友人论诗》)诗贵自然,而“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22]。艾青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23]语气词本就来自口语,口语语气词入诗能使诗歌语言质朴自然、活泼生动、通俗易懂,充满生活气息。
罗伯特·彭斯擅于“以苏格兰白话作诗歌”[24],他在OpenTheDoorToMeOh一诗中连用十个语气词“Oh”,诗歌第一节为:“Oh, open the door, some pity to shew,/If love it may na be, Oh;/Tho’ thou hast been false, I’ll ever prove true,/Oh, open the door to me, Oh.”(5)https://www.poetryverse.com/robert-burns-poems/open-door.王独清的译诗高度还原了原诗语气词的用法:“哎,开门,好表现几分怜爱,/哎,给我开门,哎!/虽然你是假的,我总可证明永远实在,/哎,给我开门,哎!”(《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3日)译者将原诗中的语气词“Oh”译作“哎”,且没有更动语气词在诗中的位置。“Oh”用于句首表示提醒,以亲切的口语语气引起听者注意;用于句尾则表示悠长的遗憾与悲叹,能够引发读者共鸣,语气词的使用为诗歌语言增添了口语化色彩。
泰戈尔的《云与波》(cloudsandWaves)是一首用口语写成的对话体诗歌,诗中写道:“I ask, ‘But how am I to get up to you ?’/They answer, ‘Come to the edge of the earth, lift up your hands to the sky, and you will be taken up into the clouds.’/‘My mother is waiting for me at home,’I say, ‘How can I leave her and come?’”(6)https://allpoetry.com/Clouds-And-Waves.郑振铎用口语语气翻译了这首诗,并增添了语气词“呢”。译诗为:“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他们答道,‘来到地球的边上,举你的手向天,你就可以被举于云端了。’/‘我母亲在家里等我呢,’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语气词“呢”在译诗中分别用于反问句和陈述句。反问句句尾的语气词具有舒缓语气的语用功能,“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明显比“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语气柔和;陈述句句尾的语气词使口语语气更加灵活自然。口语语气词的运用使原本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更加活泼生动,将孩童天真烂漫的天性表露无遗。
惠特曼在晚年创作的抒情诗Tears中同样用语气词来增强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色彩。诗中写道:“O storm, embodied, rising, careering, with swift steps along the beach;/O wild and dismal night storm, with wind! O belching and desperate!/O shade, so sedate and decorous by day, with calm countenance and regulated pace.”(7)http://www.americanpoems.com/poets/waltwhitman/tears/.东莱将诗歌译为《泪》:“哦!石矶边飙飙吹起的暴风雨,/漫野凄凉的暴风雨,激湍与怒号!/影哟!昼间沉着从容,安详规矩的影哟!”(《文学旬刊》1922年第30期)这是一首独白型诗歌,译者在前言中说:“这首诗是对于神秘而写自己的感情,诗里仿佛看见须发苍白的惠氏,坐在海岸冥想一般。”(《文学旬刊》1922年第30期)与惠氏以往诗歌中塑造的光明形象不同,这首诗塑造了“在黑暗中流泪”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的主人公时而哭泣,时而审视哭泣中的自己。在黑暗里卸下伪装坦露真实的自我,独自面对死亡将至的恐惧。诗中语气词的使用增加了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色彩,便于诗人进行内心剖白。
五四时期本就提倡用通俗浅显的白话来作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避俗字俗语”[25],认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26]。受汉译英诗影响,五四新诗人借鉴了外国诗歌中语气词入诗的创作方法,“这些感叹呼告之词模拟出现代人的口吻,展现喜怒哀乐惊,合乎现代人说话时的自然状态”[18],为白话新诗增添了口语化色彩。
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歌中有许多包含语气词的口语对白,郑振铎也将这种口语化语气词应用到新诗创作中来。《云与月》里写道:“我若是白云呀,我爱,/我便要每天的早晨,在洒满金光的天空,/从远远的青山,浮游到你的门前。”[12]198诗人用自然淳朴的语言写日常所见之景,抒发普通人的真实感情,语气词的运用使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效果更加明显。朱湘的《采莲曲》同样是一首口语化诗歌,诗中语气词的运用增加了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色彩:“小船啊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12]296句中摹声语气词“呀”具有舒缓语气,增添活泼、亲切感的语用功能。此外,刘半农诗歌《民国八年的国庆》里有“眼泪呢,终于是要流的;/但在这一天上,也何妨忍它一忍呢?”[27]闻一多《太阳吟》中有“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12]247王独清诗歌《我从Cafe中出来》有诗句:“啊,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12]224这些诗歌中语气词的运用促使新诗语言更加日常化和口语化,语气词言简意丰,使诗歌语言余味无穷。
受汉译英诗影响,外来专有名词、人称代词、语气词大量入诗,赋予了新诗语言鲜明的现代思想内涵,促使新诗语言朝着理性化、叙述化、口语化方向发展。这三类词之外,英语诗歌中广泛使用的冠词、副词、介词、助词、关联词等,均对新诗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诗语言增添了“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10]16,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