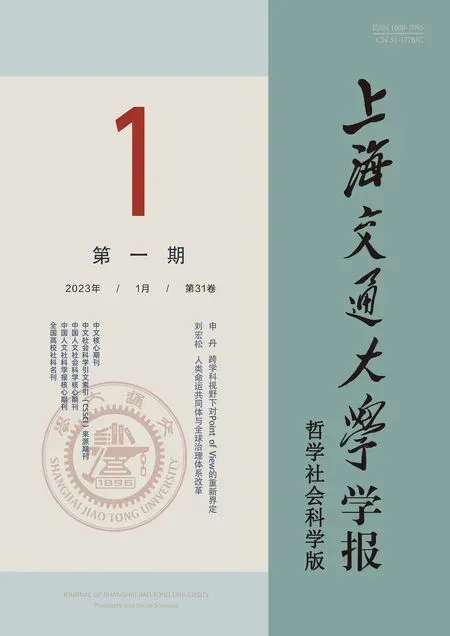跨学科视野下对Point of View的重新界定
申 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1)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创始人亨利·詹姆斯将“point of view”(视点、视角、眼光)视为主要叙述技巧以来,这成了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研究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叙事学和文体学都十分关注这一话题。表面上看,两个学派对“point of view”进行了大致相同的探讨,而实际上两者在理念和路径上分道扬镳,有意无意地相互排斥。当今叙事学界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将视野局限于观察者的“感知”(区分“谁说”和“谁感知”),这种自我限制实际上不合情理。与此相对照,文体学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聚焦于叙述者(说话者)的立场态度,这种自我限制也造成了很大问题。这两个学派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各自的片面性以及相互之间的排他性还导致了不少理论上的混乱。
本文将阐明叙事学和文体学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如何各看一面,对其做出相去甚远的理论界定和实际分析。而正是由于这两个学科各自的片面性,它们之间存在互补性——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对“point of view”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本文将在剖析叙事学和文体学各自的片面性和清理相关混乱的基础上,对“point of view”重新界定,使这一概念同时涵盖观察者的“感知”和叙述者的“态度”。
一、结构上的观察角度与叙述者的立场态度
在叙事学界,众多学者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追随著名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仅关注结构上的观察角度,而不关注叙述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热奈特认为对“point of view”的理论探讨经常“令人遗憾地混淆了”两个问题,一、叙述的观察角度是由哪个人物的point of view决定的?二、谁是叙述者?(1)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86.为了消除这一混乱,热奈特区分了“谁看”和“谁说”,后来又把“谁看”改为“谁感知”。(2)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64.在区分了观察者与叙述者之后,就可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与亨利·詹姆斯的《专使》这样的第三人称叙述在观察角度上的相似——在《专使》中,第三人称叙述者放弃了自己的全知,转而采用故事内主人公的眼光来观察。
为了更好地区分观察者与叙述者,热奈特提出了“focalization”(视角、聚焦)这一术语。众多叙事学家追随热奈特,仅关注“谁看/谁感知”,并用“focalization”取代“point of view”。此外,叙事学界也普遍关注了不少分别采用第一和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在观察角度上的本质相通(均通过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
在文体学领域,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像众多其他文体学家一样,杰弗里·利奇和米克·肖特这两位著名英国文体学家认为“point of view”是由叙述者暗暗表达态度和判断的“价值语言”体现的。(3)Geoffrey Leech and Mick 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2nd editi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7.为了说明这一点,它们引用了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第一章中的一个片段:
他不是一个坏心肠的(ill-disposed)年轻人,除非冷酷无情(coldhearted)、自私自利(selfish)就是坏心肠;但总的来说,他是很受人尊敬的(respected);因为他在履行日常职责(duties)时举止得体(withpropriety)。倘若他娶了一个更和蔼可亲(amiable)的女人,他可能会比现在更值得尊敬(still morerespectable):——他甚至可能自己也变得和蔼可亲(amiable);因为他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而且很喜欢(veryfondof)他的妻子。但是约翰·达什伍德夫人构成对他自己的强烈讽刺(caricature)——更加狭隘和自私(narrow-mindedandselfish)。(4)引自Geoffrey Leech and Mick 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2nd editi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7,p.219,斜体为原作者所加。
上面用斜体标示的文字就属于“价值语言”,这种语言是文体学家心目中“point of view”的重要载体。利奇和肖特将上引价值词语划分为不同种类,包括表达道德倾向的“坏心肠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和蔼可亲”“狭隘”,表达社会接受程度和地位的“受人尊敬的”“得体”“职责”“值得尊敬”,以及表达积极情感态度的“喜欢”。以这种划分为基础,利奇和肖特探讨了“作者会如何引导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出价值上的反应”。(5)Geoffrey Leech and Mick 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7,pp.219-220.
另一位著名英国文体学家罗杰·福勒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借鉴了俄国结构主义学者和语言学家鲍里斯·乌斯宾斯基提出的理论模式。(6)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两人的理论综合而成的福勒-乌斯宾斯基模式在文体学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亚于热奈特的模式在叙事学领域产生的影响。福勒沿着乌斯宾斯基的基本思路,区分了三个层面的“point of view”,分别为心理/感知层面、观念/评价层面、时-空层面。(7)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7-146.观念层面的英文是“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而由于乌斯宾斯基将“ideology”与“evaluative”视为同义词(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8),因此也可以翻译成“评价”层面。乌斯宾斯基认为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观念评价层面。他指出,该层面主要涉及这一问题:作者在评价其所描述的故事世界时,采取的是谁的立场态度或者世界观——可以是作者自己的,可以是叙述者的,也可以是人物的。他同时指出,在同一作品中,不同主体的观念/评价上的point of view可以共存。这是福勒和其他文体学家非常重视而叙事学界未予关注的一个层面,但不少文体学家在分析时没有像福勒这样将叙述者和人物的观念立场混为一谈,(8)应该指出的是,“point of view”作为一种叙述技巧,应该仅仅指(作者创造出来的)叙述者在叙述时采取或者体现的观念立场。诚然,叙述者可以放弃自己的观念立场,转而采用或者借用人物的来叙述(参见下文从《黑暗的心》中摘取的文字),这样后者也会成为叙述技巧的一部分。但若把仅仅是所述对象的人物的观念立场与叙述者的相提并论,则会造成混乱。而是集中分析叙述者的语言选择。在探讨这种point of view的特征时,乌斯宾斯基十分关注作者采用的价值语言(9)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12-15.,这与利奇和肖特对价值语言的关注本质相通。
就心理/感知层面而言,福勒认为“point of view”涉及谁是故事事件的观察者(“究竟是作者还是一个人物”),以及“与作者和人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相关的各种话语”(10)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134.。乌斯宾斯基将心理层面的“point of view”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大类,福勒又在每一大类下面区分了两种亚类型。就“内在的”这一大类而言,第一种亚类(福勒的A类型)是第一人称叙述。福勒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指称上采用第一人称单数,有时会采用现在时来指涉目前的叙述行为,人物—叙述者的在场“可能会用前景化的情态”加以凸显,“强调其判断和看法”;叙述者的词语选择可能会体现出其属于某种心理类型或社会阶层的特点;此外,“句法的类型、小句的及物性等等可能会体现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念立场”。(11)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35.作为实例,福勒分析了在菲茨杰拉尔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自我介绍,指出其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内在的”亚类型的语言特征。福勒和其他文体学家在探讨该亚类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关注的是叙述者;其二,聚焦于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而这正是以热奈特为代表的叙事学家不予考虑的。
第二种“内在的”亚类(福勒的B类型)“属于由‘全知’叙述者进行的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报道人物的动机和情感”。(12)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37.这也与当今叙事学界的探讨形成截然对照:叙事学家把“全知”叙述视为“外在的point of view”,(13)热奈特在本文开头提到的Narrative Discourse一书中,将全知叙述界定为“零聚焦”——因为没有固定的观察角度,但热奈特这方面的追随者为数甚少,绝大多数叙事学家追随Mieke Bal和Rimmon-Kenan,将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划归“外在型”视角,因为全知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详见下文)。因为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与之相比,文体学家之所以把全知叙述视为一种“内在的point of view”,则是因为全知叙述者能像第一人称叙述者那样报道人物的内心活动。
福勒认为自由间接引语体现了两种“内在型”亚类之间的共生或对话关系。所谓“自由间接引语”,就是用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来表达人物的口头或内心话语,但不做其他变动。由于不加“他说”或者“他心想”这样的引导句,人物的话语就不会从属于叙述者的话语。福勒说:“就自由间接引语而言,第一人称叙述(“内在的”A类)中人物的主观情感变成了第三人称,又与第三人称叙述者(“内在的”B类)对人物内心的叙述相交织”(14)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38.。他以詹姆斯·乔伊斯的《伊芙琳》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内在的”亚类之间微妙的相互交融(15)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8-139.:
曾经那里有一块田地,他们过去每天晚上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玩。然后一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人买下了这片土地,并在那里盖了房子——不像他们的棕色小房子,而是明亮的砖房,屋顶闪闪发光。这条街的孩子们过去总是在那块地上玩——迪瓦恩家的,沃特家的,邓恩家的,瘸子小基奥,她和她的兄弟姐妹……蒂齐·邓恩也死了,沃特一家去英格兰了。一切都变了。现在她要像其他人一样离开(Now she was going to go away like the others),离开她的家。(16)引自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39.
正如括号中的时间状语“现在”和过去进行时所示,这一片段是女主人公伊夫琳的内心想法,第三人称叙述者没有采用直接引语而是采用了自由间接引语来加以再现。福勒身为文体学家,关注的是叙述者和“谁说”,因此他混淆了两种叙述类型(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与表达人物话语的两种方式(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上引片段原为第一人称叙述,现在则变成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因此上引片段体现了这两种能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内在型”亚类的混合。与此相对照,面对这样的片段,叙事学家看到的则会是:在全知叙述中,故事外的叙述者放弃自己的视角,转而采用人物的意识来聚焦(我们直接通过伊芙琳的想法来观察故事世界)。也就是说,虽然这里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叙述,但视角仅仅是人物的,因此并非是两种内在型points of view的混合或者共生,而是由外在型视角转向了内在型。
另一位著名英国文体学家保罗·辛普森在采用“福勒-乌斯宾斯基”模式时,将心理/感知层面的point of view界定为“指涉故事事件如何通过故事‘讲述者(teller)’的意识这一中介来调节”。(17)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11.这一界定与叙事学界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将故事的讲述者(“谁说”)排除在外相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叙事学家在区分了“谁说”和“谁感知”之后,不仅能将采用人物意识来观察的第三人称叙述(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内)和通常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加以区分,而且在第一人称叙述中,也能区分两种观察位置:如果一位五十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现在的“我”)回顾自己二十岁时(过去的“我”)发生的往事,现在的“我”的point of view是“外在的”(观察角度在往事之外),而过去的我的point of view则是“内在的”(观察角度在往事之内)。如果叙述者放弃自己的回顾性眼光,转而采用自己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那么观察角度就会由外在的转为内在的。
由于叙事学家注重的是结构上的观察位置,因此在借鉴乌斯宾斯基的理论时,有效避开了一个陷阱。杰拉尔德·普林斯在为《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撰写“point of view”这一词条时,对乌斯宾斯基的模式进行了如下总结:“这是对point of view最为全面的探讨之一。乌斯宾斯基区分了其四个不同层面:观念层面、措辞层面、时空层面、心理层面。在每一层面,他都进行了一种本质区分,其依据是究竟聚焦者(focalizer)是在故事之内还是在故事之外,究竟信息是来自对人物内心的透视还是外在观察”。(18)David Herman,Manfred Jahn,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10,p.44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其实,两个“究竟”所涉及的问题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不妨看看乌斯宾斯基在心理(感知)层次上所区分的两大类型:一种外在观察人物,另一种则透视人物的内心。(19)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84-85.不难看出,这仅仅涉及第二个“究竟”,而第一个“究竟”则被搁置一旁。为了说明这两大类型的不同,乌斯宾斯基举了这么一个简例:
如果在一个叙事作品中,人物甲的行为是通过人物乙的观察来描述的,那么人物甲就是通过外在的point of view来叙述的(乙只能观察甲的外在行为),而人物乙则是通过内在的point of view来叙述的(可以看到乙的内心活动)。(20)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84.
这样的区分实际上站不住,因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作品的point of view到底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乌斯宾斯基接着说:
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到人物乙的内心活动(其对甲的观察),而内心活动是旁观者看不到的。这种对内心活动的透视可以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对自己内心的观察,也可以是一种外在于故事的特定point of view——作者将自己置于全知叙述者的位置。(21)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84-85.
乌斯宾斯基一方面将身为作者代理人的全知叙述者的观察视为一种“外在”的point of view(根据第一个“究竟”做出的区分),另一方面又断言只要观察者能够透视人物的内心,那么point of view就是“内在”的(根据第二个“究竟”做出的区分)(22)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84-85.。这就难免造成混乱——全知叙述成了既属于“外在”又属于“内在”的类型。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也是如此——回顾往事的叙述者也处于往事之外,也可以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因此也出现了既是外在型又是内在型的混乱。
乌斯宾斯基在实际分析中,把第一个“究竟”搁置一旁,而仅仅考虑第二个“究竟”:究竟叙述者是否可透视人物的内心,并根据这一标准,将全知叙述划归“内在型”。这与叙事学界将全知叙述划归“外在型”的做法形成对立,这种对立也说明必有一种区分缺乏理据。毋庸置疑,乌氏的区分不合情理。他在明确提出以第一个“究竟”为区分标准时(这与叙事学界的标准一致),又提出了以第二个“究竟”为标准,而这两个标准相互冲突。其实,即便仅仅以第二个“究竟”为标准,也难以避免混乱:全知叙述者不仅透视人物的内心,也经常观察人物的外在言行,因此仅以第二个“究竟”为标准,也会在“外在型”和“内在型”之间频繁转换。若同时应用两个“究竟”的标准来区分全知叙述,则会更加混乱:故事外(“外在型”)的全知叙述者既频繁透视人物内心(“内在型”)又频繁观察人物的外在言行(“外在型”)。也就是说,若同时运用两个标准,全知叙述就会在“外在型”和“内在型”之间更加频繁地转换,造成更多混乱。
那么,为何乌斯宾斯基会偏爱第二个“究竟”呢?这与他关注叙述者的语言表达相关。第一个“究竟”仅仅涉及全知叙述者在结构上的观察位置——叙述者总是处于故事之外,而第二个“究竟”则涉及叙述者的语言选择。乌氏十分注重“他做”“他说”“他声称”这样的叙述表达与“他心想”“他觉得”“他感到羞愧”这样的叙述表达之间的差异。(23)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84.文体学家之所以会选用乌斯宾斯基的模式,也与这一模式注重叙述者的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然而,无论是文体学界还是叙事学界,都未注意到乌氏理论区分中的混乱。前者落入了这一混乱构成的陷阱,而后者由于实际上仅仅考虑观察者的位置(第一个“究竟”),因此避开了这一陷阱。
在看到乌斯宾斯基理论模式中的混乱之后,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清除相关混乱?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仅仅需要做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分。就心理/感知等结构层面的point of view而言,我们只应根据观察位置(第一个“究竟”)来区分“内在型”和“外在型”。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另外的术语来区分叙述者对人物的内心透视和外在描述,譬如“inner view/内心透视(内透)”和“outer view/外在观察(外察)”。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不能像乌斯宾斯基和福勒等文体学家那样用“内透”和“外察”作为区分point of view的标准。无论全知叙述者是“内透”还是“外察”,其“point of view”都是“外在型”,因为其观察位置始终处于故事之外。诚然,若全知叙述者放弃自己的观察,而转而采用人物的视角(如上引《伊芙琳》中的片段),就会发生从外在型向内在型的转换。不难看出,就结构上的point of view而言,叙事学界的区分更胜一筹——仅有一个标准,没有混乱。但其对point of view的探讨有其自身的片面性(见下文)。
值得一提的是,文体学在探讨心理/感知层面的point of view时,也有强于叙事学之处。福勒区分了两种“外在型”的亚类,两种都仅仅对人物进行“外察”。第一种(C类型)是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述,不对人物做任何评判,因此看不到任何评价性的语言。与此相对照,在第二种“外在型”的亚类(D类型)中,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虽然对人物仅仅外察,但却会对人物进行主观性的推测和评判,例如“他看上去是位安静、聪明、儒雅和善良的成功人士”。(24)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1-143.这两种亚类和全知叙述一样,观察位置均处于故事之外,因此都属于“外在型”的point of view,但这两种亚类的观察眼光存在差别,一种冷静客观,另一种则进行主观推测和评判。这种差别通过叙述者的语言选择来体现,因此引起了文体学家的关注,而忽略语言表达的叙事学家则未予关注。应该说,文体学对这两种不同亚类的区分具有一定价值。
除了心理/感知层面,乌斯宾斯基和福勒也较为关注观念(评价)层面的point of view。福勒写道:“语言在稳定、复制和改变观念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探讨叙事文本中观念层面的point of view时,我们指的是通过文本语言传达的一套价值观或者信仰体系”。(25)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30.也就是说,在探讨观念层面的point of view时,仅仅需要关注语言表达。这与利奇和肖特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集中关注“价值语言”本质相通。
在此,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向著名英国文体学家保罗·辛普森的《语言、观念与Point of View》一书,(26)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11.该书聚焦于对观念(评价)层面的探讨,所借鉴的理论模式也正是“乌斯宾斯基-福勒模式”。辛普森是非常注重借鉴叙事学的文体学家,他在综述不同研究方法时,将热奈特的模式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性模式加以介绍,同时指出,其他叙事学家后来修订了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的分类,譬如将全知叙述划归“外在型”的point of view。(27)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p.30-34.然而,辛普森也对叙事学模式表达了不满,因为在区分不同的point of view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语言选择,而他认为“point of view必须在语言中表达,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28)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34.
辛普森的专著聚焦于观念/评价层面的point of view。在探讨这一层面时,他同样聚焦于“谁说”。其专著的简介为:“本书系统介绍语言中的point of view,探讨其如何与观念体系相交织并如何为观念体系所塑造。本书特别关注作者和说话者在各种不同媒介中如何编码他们的信仰、兴趣和偏见。”(29)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2.与叙事学家聚焦于结构上的观察角度(“谁感知”)相对照,身为文体学家的辛普森的聚焦点是“文本中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角度’”(“谁说”)。(30)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2.
二、两方面综合考虑:对Point of View的重新界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叙事学和文体学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各自关注一个方面,并且排斥对方的关注面。其实,“point of view”一词本来就有两个不同指涉对象:其一,考虑事情的特定态度或方式;其二,观察某物或某人的位置。(31)Angus Stevenson and Maurice Waite,eds.,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108.第一个是文体学界所聚焦的分析对象,第二个则是叙事学界所聚焦的分析对象。在《小说文体论》一书中,利奇和肖特认为第一种point of view(即作为发话者的作者或者叙述者的态度和判断)更加受到小说研究界的关注。(32)Geoffrey Leech and Mick Short,Style in Fiction,Harlow:Pearson Edacation,2007,p.140,p.218.他们自己也聚焦于这一分析对象,尤为关注叙述者的话语所体现或蕴含的反讽、语气以及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与此相对照,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普林斯认为“point of view”的持有者是作为观察者的聚焦者(focalizer),因此他在综述学界对“point of view”的不同分类时,基本上仅仅涉及了聚焦者所处的结构上的观察位置。(33)David Herman,Manfred Jahn,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10,pp.442-443.如前所述,普林斯在简要概述乌斯宾斯基的模式时,通过两个“究竟”,无意中把乌氏的模式展示为一种结构性的模式,而实际上乌斯宾斯基也十分关注叙述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立场态度,尤其是在观念/评价层面,(34)Boris Uspensky,A Poetics of Composi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8-15.这与文体学界对叙述者态度的关注不谋而合。而叙事学界因为仅仅关注结构上的观察位置,因此根本没有考虑由叙述声音体现出来的观念/评价层面的point of view。
在叙事学界,有的学者追随F.K.斯坦泽尔,对“叙事情景”展开考察。表面上看,“叙事情景”中包含了叙述者的声音,而实际上其仅仅涉及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这两种叙述类型之间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叙述者的立场态度。(35)Franz Karl Stanzel,A Theory of Narra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46-58.热奈特断言:“在对不同的‘叙事情景’加以区分时,若同时考虑语式(point of view)和叙述者的声音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若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同时考虑这两种因素,则是不合法的”。(36)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188.其实,热奈特在排斥叙述声音时,考虑的也是叙述类型,而没有真正关注叙述者的立场态度,而后者才是“point of view”所涵盖的一个层面。
如前所述,叙事学界对“谁感知”和“谁说”的区分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结构上观察位置的区分得以清晰化——不仅可以将全知叙述与采用人物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如上引《伊芙琳》片段)区分开来,而且可以区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现在的回顾视角与“我”当年的体验视角。另一方面,对“谁感知”和“谁说”的区分又将叙述者的声音明确驱逐出“point of view”的范畴,造成对“point of view”探讨的片面性。与此相对照,在文体学领域,学者们聚焦于为叙事学界所排斥的叙述声音,集中探讨其所体现的立场态度。两者都未意识到“point of view”的这两个方面对于大多数叙事作品的阐释均十分重要。诚然,倘若叙述者不进行任何评判,仅像摄影机一样客观记录,那么就无需关注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但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多。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领军者苏珊·兰瑟1981年出版的专著《叙事行为:散文小说中的Point of View》可以很好地例证在叙事作品研究中,十分有必要考虑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37)Susan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学界通常将这一专著视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部开山之作,而实际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著作。在该书绪论中,兰瑟写道:“如果‘看’(seeing)与point of view密不可分,那么‘说’(saying)就更是如此了。人类话语不仅基于观察主体与看到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基于说话主体与一位或多位听者、被感知的客体和语言本身之间的多方面的互动关系……因此,语言互动必然反映人类活动的两个层面,语言层面和感知层面,两者都受一种point of view的支配”。(38)Susan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4.在对小说中的“point of view”展开实际分析时,兰瑟聚焦于“叙述声音与作者写作行为的物质、社会和心理背景之间的联系,以及意识形态和技巧之间的联系”。(39)Susan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5.尽管兰瑟的这部著作很好地展现了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关注叙述者的语言选择所体现的立场态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其在叙事学界却影响甚微。这是因为叙事学关注结构关系而忽略语言选择,因此在热奈特的带领下,很快将注意力囿于结构层面的point of view,聚焦于对不同观察位置的区分。就文体学来说,因为其特点就是采用语言学模式来研究作者的语言选择,因此自然会聚焦于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而忽略结构上的观察位置。这突出体现了学科分野造成的关注面上的片面性。
有个别西方学者注意到了文体学和叙事学在“point of view”探讨上的片面性,并试图采用两种不同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均未成功。其中之一是干脆规避界定,以英国文体学家保罗·辛普森为代表。他在没有意识到文体学研究的片面性之前,曾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将point of view囿于叙述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立场态度,集中关注“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角度’”,且强调指出“point of view必须在语言中表达,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见上文)。由于对此坚信不疑,他还认为他在界定point of view时仅仅考虑叙述者的语言选择不仅正确,并且有可能得到广义上的学术界的公认。(40)Paul Simpson,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11.然而,在2004年出版的《文体学》一书中,辛普森看到了叙事学的界定也有其道理,因此在介绍“point of view”时,干脆放弃了任何界定,用规避的方法来应对两个学科之间的冲突。他写道:“文体学家和叙事学家对point of view已经有了很多著述,以至于现在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理论、术语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介绍point of view的最佳方法是直接进入文本示例”。(41)Paul Simpson,Stylistics: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4,p.28.这种对界定的规避显然不是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试图通过提出新的术语来解决问题。查特曼是文体学家出身的叙事学家。在转向叙事学之后,他从关注遣词造句转向关注结构关系。(42)Seymour Benjamin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10-11.然而,由于他从事的是修辞性叙事学,重视作者—叙述者—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因此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也需要考虑叙述者的立场态度。他在《叙事术语评论》中写道:
现在必须对“point of view”的两个载体——叙述者的和人物的——进行术语上的区分了。我提出“倾斜”(slant)这一术语来指涉在话语层面报道事件的叙述者的态度以及其他微妙的思维特点,同时用“过滤”(filter)这一术语来指称故事世界里人物更为广泛的心理活动——感知、认知、态度、情感、记忆、幻想等等。(43)Seymour Benjamin Chatman,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43.斜体为原作者所加。
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身为叙事学家的查特曼将叙述者的语言所体现的立场态度纳入了考虑范围,这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他不承认叙述者具有观察故事事件的能力,这带来了新的问题。就全知叙述来说,其他叙事学家都认为全知叙述者既是讲述故事者又是观察故事者,而查特曼则认为既然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世界之外,就不可能看到故事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只有人物才能看到。(44)Seymour Benjamin Chatman,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142-145.这显然是将现实生活中的标准运用于虚构世界。就后者而言,文学规约赋予了故事外的全知叙述者超人的视觉,不仅能观察故事中的一切,包括超出人物视野之事,而且能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至于第一人称叙述,查特曼也认为回顾性叙述者虽然在过去看到了所发生的事,但现在只能回忆,而无法再次看到。然而,回忆也涉及在大脑中的重新观察。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事经常历历在目、“清晰在耳”,与现场观察并无实质区别。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看”其实“就是视觉记忆”。(45)Ulric Neisser,Cognitive Psychology,Des Moines:Meredith,1967,p.164;Manfred Jahn,“Windows of Focalization: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a Narratological Concept,”Style,vol.30,no.2(1996),pp.258- 259.
查特曼否认叙述者具有观察能力也使我们无法正确认识第三人称“摄影式”叙述。他将这种模式视为“仅有倾斜(slant)而没有过滤,也没有叙述者的评论”。(46)Seymour Benjamin Chatman,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49.然而,“倾斜”指的是叙述者的语言所体现的具有倾向性的态度和评价,在“摄影式”模式中,根本不存在“倾斜”——叙述者冷静客观,仅进行摄影机般不偏不倚的观察。另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查特曼不承认叙述者具有观察能力,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外在型”视角,这显然过于片面。
查特曼用“过滤”这一术语将作为观察角度的“point of view”囿于故事之内,这无疑是不可取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point of view”在指涉结构上的观察角度时,涉及的是一种叙述技巧或方法,是叙述者调控叙事的“主要手段”。(47)Percy Lubbock,The Craft of Fiction,New York:Viking Press,1957,p.251;Mieke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5,p.50.当第三人称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者采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时,point of view属于话语表达层;当叙述者放弃自己的眼光,转而采用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时,人物的眼光也会既属于故事层,也属于话语表达层。我们不妨看看取自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第三章中的一个片段:
我给汽船加了点速,然后向下游驶去。岸上的两千来双眼睛注视着这个溅泼着水花、震摇着前行的凶猛的河怪的举动。它用可怕的尾巴拍打着河水,向空中呼出浓浓的黑烟。
(请对比:我给汽船加了点速,然后向下游驶去。岸上的两千来双土著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船,他们以为溅泼着水花、震摇着前行的船是一只凶猛的河怪,以为它在用可怕的尾巴拍打河水,向空中呼出浓浓的黑烟。)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为船长马洛,他无疑不会将自己的船视为“河怪”。不难看出,他在叙述时暗暗放弃了自己的眼光,转而采用土著人的眼光来观察。土著人的眼光也就具有了双重性质:作为人物的眼光,其属于故事层,而作为叙述者用于叙述的眼光,其同时成了话语表达层的叙述技巧的一部分——短暂地成为“叙述视角”。与此相对照,在比较版中,土著人的眼光则仅仅是叙述者的观察对象,仅仅属于故事层。在这一实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结构上的观察还可体现观察者的情感和观念等方面的特点——土著人的视角蕴涵着土著人独特的思维风格以及对“河怪”的畏惧心理。(48)参见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London:Routledge,2002,pp.80-96.
为了纠正学科分野和以往的理论探讨所造成的片面和混乱,我们需要重新界定“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涉观察者的感知,另一方面则指涉叙述者的立场态度。前者主要涉及观察位置——究竟是在故事之内还是在故事之外,但也涉及感知的特点:究竟是客观中性的摄影式观察,还是带有情感、观念等方面的色彩。后者则主要涉及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或观念评价。如果叙述者叙述的是自己所观察之事,探讨“point of view”时,就需要既考察其声音(立场态度)又考察其感知(观察角度)。如果叙述者采用人物的感知来观察,那么就需要同时考察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和人物的观察位置以及其感知是否带有情感和观念等方面的色彩。
在国内学界,若要重新界定“point of view”,就需要一个既能涵盖叙述观察角度又能涵盖叙述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的术语。应该说,在汉语中,能够涵盖两者的是“叙述眼光”。首先,“眼光”本身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中一种涉及叙事学意义上的point of view(即观察角度),词典的定义为:“视线 eye”;另一种则与文体学意义上的point of view(立场态度)基本重合,词典的定义为:“观点point of view”。(4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2210页。然而,中国学界在引入西方叙事学的过程中,无意中剥夺了“眼光”的第二种指涉。前文提到,热奈特区分了“谁看”(eye)和“谁说”(voice),将后者驱逐出“point of view/focalization”的范畴。我国叙事学界相应区分了“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在探讨“point of view”或“focalization”时,将其囿于“叙述眼光”的第一种含义(视角/聚焦),而有意无意地排斥了“叙述眼光”本来具有的第二种含义(叙述声音所体现的叙述者的立场态度)。笔者曾经是这一做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因为当时未能认识到西方叙事学界在这一方面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上文揭示了西方叙事学界的这种偏误,我们也就需要将“叙述眼光”从第一种含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其可以重新涵盖叙述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应该说,只要我们能打破以往的相关研究所造成的禁锢,我们就能看到汉语的“叙述眼光”具有与英语的“point of view”同样宽广的涵盖面,不仅能指涉叙述视角(叙述者自己观察或者借用人物的感知来观察),并能较好地涵盖观察所带有的情感和观念等方面的色彩,而且也能很好地指涉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诚然,在探讨观察角度时,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视角”“聚焦”“视点”等术语,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point of view”或者“叙述眼光”的一个方面。
结 语
自20世纪初以来,“point of view”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界也很受重视。西方叙事学和文体学的学科分野,导致了对“point of view”的片面界定和片面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混乱。西方学界的片面性也影响了国内学界。国内叙事学界也普遍认为“视角”或“聚焦”就是“point of view”的代名词,将“叙述眼光”囿于这一方面,对“point of view”的另一方面——叙述者的声音所体现的立场态度——未加关注;而国内文体学界聚焦于叙述者的遣词造句,对叙述视角/聚焦也缺乏关注。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叙述的声音和视角交互作用,联手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形象,在作品分析时不可偏废。
个别西方学者认识到了叙事学和文体学在探讨“point of view”时标准不一,相互冲突。然而,他们或者不敢直面问题,干脆放弃理论界定,或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新的界定,带来新的问题和混乱。本文力求清理混乱,真正解决问题,对“point of view”(叙述眼光)提出符合实际的新的界定。希望这一新的界定一方面能帮助推进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中外叙事学界和文体学界认识到各自在point of view/叙述眼光探讨上的片面性,看清以往理论探讨中的相关混乱,并加强跨学科研究,以便对叙事作品进行更好、更为全面的分析。